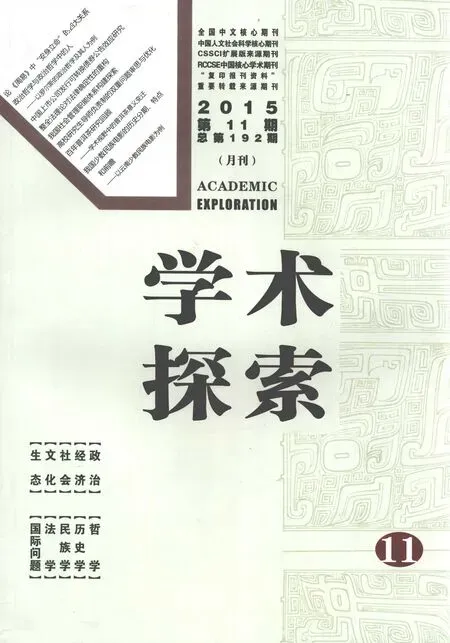旅游开发与少数民族村落日常生活的异化——基于元阳县箐口村的实例
旅游开发与少数民族村落日常生活的异化
——基于元阳县箐口村的实例
钟小鑫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人类学强调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使其对日常生活有着特殊的关怀,相信诸多社会与文化的事项总是会在日常生活中显现出来,而日常生活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变迁。本文关注云南省元阳县哈尼族箐口村的旅游开发对于村落日常生活的影响,试图指出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村落日常生活发生了异化,即镶嵌于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日常生活在不断消解,以经济为基础和目的的单面向日常生活在不断扩张,也即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体系的脱嵌,而村落日常生活异化的背后是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与重构。通过这一实例,本文试图探讨现代性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箐口村;旅游开发;日常生活;异化
作者简介:钟小鑫,男,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西南及东南亚民族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3BTY069)
作者简介:张成胜,男,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一、日常生活及其异化
日常生活最早是在哲学的领域中被探讨。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指出,“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1](P64)胡塞尔所强调的日常生活世界是知识阐释之前的直观世界,并为一切知识提供现实性的前提。赫勒将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1](P67)赫勒同样强调日常生活是其他非日常生活的基础,同时决定着个体的再生产,并在更深远的层次上决定社会再生产,赫勒还强调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而非自为性。[2](P114)这在一定意义上为人类学探讨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列斐伏尔认为日常生活是每个个人最直接的生活领域,是“总体性的人”的实践本身。[3](P164)综合这些对日常生活的界定与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的基础性、自在性、总体性的特征。
如果跳出哲学的抽象思辨而直面具体的情境,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定界为:镶嵌于社会文化体系中总体性的实践。在此,我们可以将“日常生活”与人类学中所言的“近经验”结合起来理解。格尔茨认为,近经验就是处在特定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人们不用借助于阐释就能直接阅读出意义的实践。[4](P69)当人们面对的是近经验,就不会有“眼睛痉挛”还是“眨眼做鬼脸”的疑惑,因为这些实践都是镶嵌于社会文化的整体性之中,都被赋予“地方知识”的意义。从这一层面出发,日常生活就是近经验范畴内的实践。
与日常生活相对的是非日常生活,也可以称之为被异化的日常生活。胡塞尔提出的“欧洲科学危机”指的就是以日常生活为基础而产生的理念体系反过来“偷偷摸摸地取代了”日常生活世界。[1](P70)在此,胡塞尔为我们呈现了日常生活在现代性历程中被异化的一种形式,即科学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异化。列斐伏尔则更多地关注到现代性中的工业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异化,他指出,“日常生活在现代社会中既发展不足又组织过度……并被新技术和消费社会殖民化”。[5](P116)列氏认为步入现代性的过程是人的世界从日常步入非日常的过程。
本文针对一个具体的社会文化情境,呈现其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日常生活具体被异化的景致。本文将这种异化的过程概括为作为镶嵌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总体性日常生活走向了以经济为基础和目的的单面向日常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讲,这正是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强大的自足性,进而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彻底的殖民。[6](P26)但必须指出的是,本文无意于批判主旨在于促进少数民族村落现实发展的旅游开发,而只是在理论和抽象的层面上做出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
二、箐口村及其旅游开发概况
箐口村是云南省元阳县新街镇土锅寨村委会属下的一个自然村,坐落在海拔约1600米的半山腰上,是哀牢山区众多山寨中的一个,箐口村距新街镇6.87公里,距县城南沙镇30公里,占地面积约5公顷。[7](P1~3)村寨及周边是呈舌叶形的泥石流冲积扇,地势西高东低,村民沿晋思公路东侧起修筑梯田,顺着地势,梯田从西向东一直延伸至麻栗寨河。[7](P3)箐口村现有耕地面积为857.76亩, 其中水田453.3 亩, 旱地404.46亩, 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为0.951亩。从这一数据看来,箐口村民基本都面临着耕地缺乏的困境。根据2011年底的人口统计数据,箐口村有家户210户,人口总计966人,其中哈尼族人口占村民总人口的98%以上,是一个典型的哈尼族村寨。[8](P2)箐口村的哈尼语名称为“欧补”, “欧”是水的意思, 而“补”意为翻滚, “欧补”有洪水泛滥的意思, 同时也可用作对泥石流的称呼。从这一地名释义出发,我们可以看出村寨的名称来源于村寨地域形成的方式。箐口村村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区域与周边黄草岭、大鱼塘、全福庄等哈尼族村寨和土锅寨彝族村寨交界,并与其他周边村寨有着密切的交往。
箐口村至今仍旧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哈尼族传统文化形式,特别是一些核心的宗教仪式得以传承,如祭寨神林,“昂玛突”“苦扎扎”等仪式,而摩批、咪古、尼马这三类传统的哈尼族神职人员现在仍旧是村寨中的重要人物。哈尼族的传统文化在其服饰和住房建筑等方面也有保留,其中诸多老人、妇女和孩童更为频繁地穿着传统服饰,而传统民居蘑菇房也保留了一些基本的形式。
由于箐口村占据着观赏元阳的“云海梯田”景观的绝佳位置,再加之村中的树木茂密,构成所谓的“森林—村寨—梯田—溪流”四度同构的自然景观。而样式独特的传统民居——蘑菇房,充满着浓郁的哈尼族风格的祭祀房、祭祀场、磨秋、秋千、水磨房、水碾房、日常服饰等综合元素都构成了箐口村的独特人文景观。而箐口村也是电影《诺马的十七岁》的拍摄地,由著名导演章家瑞执导,并在国内外获得诸多奖项,随后姜文的著名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也在箐口村取景,村中至今还保留了拍摄电影时留下的一处房子,而杨丽萍、宋祖英等名人的到访也使箐口村增添了一些热门话题,并且极具传播效应。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这个极富特色的哈尼山寨凭借着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走上了旅游开发之路。
在正式规划旅游开发之前,就有不少摄影爱好者与文化研究者时常来到箐口村,只是当时还没有旅游开发的意识和条件。2000年初,红河州委把以元阳梯田为核心区的“红河哈尼梯田风景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随后元阳县领导在箐口村进行考察,为箐口村的发展出谋划策,提出要将箐口村作为哈尼族村寨旅游的试点,并提出完整保护原有村寨传统建筑和自然风貌,展示浓郁的民族地域特色,挖掘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以创造绿色和文明的生态环境为主旨,充实吃、住、行、游、购、娱六大旅游要素,完善旅游功能,维持村民原有日常生活轨迹,逐步提高其生活环境和质量的指导思想。[9]
2001年,政府首批投入400多万元支持箐口村的旅游开发。在村口修筑了停车场、景观台、村寨入口、大门、公共厕所以及由公路至村寨的机车行道,并对村寨中的小学进行了搬迁,修建了村寨中心广场及文化展览室、休息亭,对原有的民俗活动场所(主要指宗教仪式场所)进行了环境整治,对村中的道路、水沟以及“破坏”风貌的建筑进行了整治,主要表现在为82户非蘑菇房的民居“穿泥衣戴草帽”,使其也变成了传统样式的蘑菇房(住房改造的家户由政府补贴2万元),并修建哈尼族文化陈列馆以及3片文化广场,分别是图腾广场、祭祀广场及文化广场。
箐口村从2001年底开始接待游客,2003年的游客量约为10.6万人次,门票收入总计72580元,村民每户分得144元。[10]而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推进,村里还建立了2家农家乐,兼具饮食和住宿的功能,而大大小小的杂货店也增至了十多家,以及5家民族工艺品商品(如银饰店),还组建了一支表演哈尼族传统歌舞的文艺队,一些老人和孩童也特意穿着哈尼族的传统服饰来吸引游客的眼球,并在游客拍照的过程中收取一定的费用。除此之外,长街宴、大众捉鱼、打磨秋、荡秋千等参与体验式的活动逐一兴起。可见,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村民以往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生计模式正在一步步消解,不可否认的是,村民的生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收入也有所增加。
2008年,云南省世博集团有限公司和元阳县旅游局签订了为期50年的旅游开发协议,政府出资33.7%,世博公司出资66.3%,共同出资8700万元,组建“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箐口村旅游经营权在此过程中也被元阳县旅游局转让给云南省世博元阳分公司。世博公司也采取了一些旅游开发的措施,然而其中一些并没有得到村民的认同,并引发了一些矛盾,而世博公司的开发与管理工作,一直延续至今。
以上只是关于箐口村旅游开发过程的大致描述,试图指出箐口村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主要包括村落的自然景观的改造,文化展演形式的再造,以及村民生计方式的变迁。
三、村落日常生活的异化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有过如此界定,村落日常生活的异化是指作为镶嵌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总体性日常生活走向了以经济为基础和目的的单面向日常生活。也即哈贝马斯所指出的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在现代社会中获得了强大的自足性,进而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彻底的殖民。[6](P26)而在下文中,让我们来看看这种被异化的日常生活的具体情景。
(一)宗教性日常生活的异化
在一般意义上,一个越是传统的社会,其宗教生活就越是重要。也许有人质疑作为宗教性的生活根本不能称之为日常生活,但是我们在此讲的日常生活并非是与事件对立的生活,而是指那些总体性的生活,即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能够被直接理解的生活,从这一界定出发,宗教生活不仅是日常生活,而且是日常生活中核心的一面,因为其与社会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让我们首先来看哈尼族箐口村的宗教生活是如何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被异化的。在箐口村,在宗教生活方面最为主要的元素包括昂玛突、苦扎扎、祭山神、封火神、十月年等仪式和节庆。
苦扎扎是哈尼族祈求农业丰收的宗教祭祀节庆,节日总共进行13天,在这一节庆期间,村民们便搭起秋千架,架起磨秋,以在一起荡秋千、打磨秋的游戏形式进行这一宗教活动。但是在以前,荡秋千和打磨秋的游戏只准男性村民及村里的孩童玩耍,禁止女性参与。还有一个规定是一般秋千架和磨秋场只有在苦扎扎的节日期间才可以开放,其余时间是不可以进行这些游戏活动的。但是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不将女性游客排除在外,禁止女性参与的禁忌被打破,这样,女性也可以荡秋千和打磨秋了。而且为了满足游客的需求,不仅仅苦扎扎期间可以荡秋千和打磨秋,一年的其他时间也可以进行,性别与时间上的禁忌都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消解了。这样,苦扎扎这一宗教节日的意义实际已经发生了改变,已经不再是箐口社会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宗教事项。
寨神林信仰也是哈尼族的地方性宗教信仰。一般每一个村寨都会有一片森林被格外指定出来,作为村寨的寨神林,除了举行一些相关的宗教仪式与祭寨神林时可以进入,在平时,寨神林被视为禁地,村民和外人都严禁进入。但是在箐口村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寨神林也对游客开放了,并且游客可以参与和观摩在寨神林中举行的祭祀活动。为了让游客观光寨神林,世博公司在寨神林的前边修建了一条便于行走的小道,小道旁边建了一些栏杆和凉亭以及观光的平台。不管是苦扎扎还是祭寨神林的宗教生活,都在旅游开发中发生了改变,它们的宗教性在慢慢消解,而展演性在不断增强。
而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神职人员的生活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他(她)们主持宗教仪式的活动也不再仅仅是宗教事项了,还兼具着表演的性质。例如村里有名的咪古李正林,他现在每天的生活是管理着村里民俗展览馆以及哈尼哈巴(哈尼族的传统歌谣)传承中心的相关事务,给游客和外来人员介绍哈尼文化的各个方面。他将家里的一楼也设计成一个文化展示的空间,墙的四面挂满了一些哈尼族的传统服饰,家居设计也是刻意突显传统的元素,他还将很多国家的纸币裱起来挂在墙上,可能是向进来访问和参观的人说明,他去过这些国家进行文化表演。
面对这种变迁,有学者认为这是正常的文化发展,文化本来就是在不断流动的,处在不断变迁之中。[11]笔者完全认同这种观点,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用另一种视角去阐释这些现象。在笔者看来,这不仅关乎文化的发展与变迁,这些现象还是经济体系化约了其他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使宗教性的日常生活从总体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脱嵌出来,成为一种单面向的日常生活。
(二) 经济性日常生活的异化
本身就已经作为经济性的日常生活何以还会走向异化?在此,笔者想表达的是内嵌在社会文化体系中的经济性日常生活与脱离社会文化体系后成为主导性力量的经济性日常生活的不同。[12]例如在哈尼族箐口村,村民养鸡这种生计活动是跟宗教祭祀紧密相关的,梯田里养鱼、放鸭也是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认知基础上进行的,对牛的经济利用也是跟牛在自身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密不可分的,基于这样的经济生活,我们就可以认为其是内嵌于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日常生活,但这样的经济性日常生活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被异化,下文我们来看异化的具体表现。
在旅游开发之前,我们可以说箐口村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型体系,但是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那些原来用于自给的生计产品被急切地要求变成商品,这是一次关于经济性日常生活的大转型。以前用于自给的红米、梯田鸭、鸭蛋、梯田鲤鱼等等都成为旅游中的传播符号及宣传要素,而这些产品也由此转变成为商品,所以到此旅游的人离开时往往都要买点红米带回去,而旅游公司也因此而策划起了在梯田里大众捉鱼的体验式旅游项目。这些经济活动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表面上突显了哈尼文化的元素,但在实质上又使其脱离了原来的社会文化体系而演变成单纯的经济行为。
以前箐口哈尼族还自己织布、染布、制作服饰用于家庭内部成员的日常穿着,但现在织布、染布、制衣的劳动过程都被商品化,成为民俗展演的一部分,而制作出来的服饰也成为了游客竞相购买的纪念品。我们也可以视这样的过程为经济性的日常生活慢慢从哈尼文化中脱离出来,也慢慢从箐口村特定的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自足性的日常生活,而它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也是以经济为目的的。
相对于前文中那些对于以前就有的经济活动进行重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箐口村的经济状况其实在向着一个不断分化的过程演进,一些新的经济行为与活动产生了。在以往,村民们都差不多从事着农业生产的活动,也基本维持在家庭自给的起伏不大的范围内波动,但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劳动分工也进一步发生了变迁。村里有人开起了农家乐,为游客提供饮食和住宿的服务,还有村民成为“导游”,带着游客穿梭于各个景点与各个村寨之间,村里还组织了歌舞队,为游客进行哈尼族的歌舞表演。有的村民刻意穿着哈尼族的传统服饰,或为游客表演织线、染布等,吸引游客拍照,从而收取一定的费用。在这一劳动分工的过程中,同时也是贫富分化的过程,一些村民已经开起了小汽车,而在旅游开发的大潮中没有把握住机会的村民却仍旧在贫困线上挣扎。[13]这种经济上的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村民的市场意识,并且提高了经济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往大家都一样,或者说区别不大,经济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指标,但现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逐渐显现出来,经济因素成为衡量村民与家户的重要标准。在这样的转变中,经济性的日常生活也在慢慢走向异化,它不再是一种总体性的日常生活,而成为一种自足并主导其他事项的实践。
对于经济性日常生活的转变,也有诸多其他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村民自主选择与政府指导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处于边缘地位的民族地区为了参与到主流话语体系中去而进行的民族文化商品化、资本化。[14]笔者也同样认同这些观点的解释力,但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同样可以有多种解释的路径,笔者更侧重地认为这是一种经济性日常生活脱离总体性的社会文化体系的过程,即经济性日常生活异化的过程。
(三) 公共性日常生活的异化
在一个传统的民族地区村落中,最为常见的公共性日常生活往往是宗教性的日常生活,在前文中,我们已经分析了箐口村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宗教性日常生活是被如何异化的。在此,笔者试图呈现一些箐口村旅游开发后才兴起来的公共性日常生活,即那些新兴的将村民们聚集在一起的事件与生活。它们并不是像原来宗教性的仪式与民族节庆那样内嵌于总体性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而是因为旅游开发而被频繁组织起来的公共性日常生活,而且难以找寻到这些日常生活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有何关联。
随着箐口村旅游开发的不断深化、推进,箐口村与外界的联系不断加强,一些政府、企业、学校或其他性质的机构举行的公共性活动也频繁选址在箐口村。如基于巴丹的调查,在2004年的3月和4月两个月期间,在箐口村举办的类似活动就有11次之多,其中包括元阳县离退休老干部联欢会;省、州、县农资公司前来视察学习;省组织部前来视察学习;云南省副省长一行前来视察学习;曲靖师范学院学生与美国学生联欢;县组织部与宣传部前来视察学习等。[8](P27)基于这一调查情况来看,箐口村村民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衍生了许多新型的公共性日常生活,在这样的活动中,他们往往被要求穿上传统的哈尼族服饰,将村寨整体打扫,聆听领导们的讲话,有时还被要求上台发言。而大多数的情况是,村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跟他们有什么关联,就好像电影场景中的群众演员和道具,这是与他们没有关联但经常性被组织的公共性日常生活。
笔者在箐口村调查期间,类似于上文中提到的公共性仪式与事件仅2015年1月份中旬和下旬就举行了3次。第一次是2015年1月22日由市委宣传部和县委宣传部组织的“箐口村道德讲堂——文明礼仪知识专题讲座”,主要宣读的内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八荣八耻等内容。宣讲时首先由宣传部的一个相关成员开头,随后由一个红河州里的会哈尼话的公务员来宣读,因为很多村民不能听懂汉语,只能用哈尼语来进行。而这一公务员又很难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八荣八耻这些内容准确翻译成哈尼语,笔者问村民最后都讲了一些什么,村民反映主要讲了“现在快要过年了,回到家里的人们不要去赌博,讲文明卫生等等,说村子里时常有外国旅客到来,要注意地方与国家的形象问题,村子里什么都好,风景好,其他方面都很突出,就是人的素质还要提高”。而一个更有趣的细节是,村支书在广播里通知村民来文化广场集合时,说的是有上级政府来发钱,结果却并非如此,很多村民失望而归。
第二次是2015年1月28日由中宣部、学习出版社、省委宣传部、州委宣传部共同举办的赠书活动。来赠的书是学习出版社出版的《法制热点面对面》,村民们都被要求着哈尼族传统服装来参加这次活动,其中还有一个环节是村民代表讲话,而那位“村民代表”却并非是箐口村的村民,而是新街镇里的一位公务员。活动后,很多村民向笔者反映自己不会看这样的书,显然村民也无法真正理解法治到底是什么。
第三次是2015年1月30日由红河州及元阳县相关部门举行的送温暖活动,他们选了箐口村中的3户有着年纪较大老人的家庭去“送温暖”,送的东西包括每家有一床被子、一瓶5升的食用油,一袋5公斤的大米。每到一户家庭领导们都问村民搞旅游,生活水平有没有提高,有的村民说有,有的说没什么变化。领导又建议可以多搞一些农家乐、开展斗牛表演之类的。其中斗牛表演的建议非常有趣,在红河地区,斗牛其实是作为彝族的一种文化习俗或者娱乐形式。从这一建议我们可以看出,旅游开发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以经济为目的的过程,文化的传承与展示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只要能够在经济上有所收获,展演的是不是哈尼文化并不是最重要的。
这些公共性的日常生活是箐口村旅游开发之前很少有的,但在旅游开发之后却频繁出现。村民们虽然大多都觉得这些活动与自身没有多大的关联,但是他们也懂得这也是将箐口制作成名片对外宣传的渠道。因为伴随着每次活动的是全程的记录与拍摄,也正是这样可以将箐口频繁地出现在电视新闻和报纸的报道中,而这样的日常生活实际上也化约为了村民们对于经济的考量,它们虽然与总体性的社会文化体系无关,但却是旅游宣传的另一种方式。
四、日常生活的异化与社会文化变迁
在上文中,我们呈现了箐口村旅游开发的大致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村落日常生活的一些变迁与影响。笔者大体认为旅游开发是箐口村制度化地与外界接触的开始,同时亦是其逐步从传统步入现代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常生活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最为主要的表现是镶嵌于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日常生活在不断消解,以经济为基础和目的的单面向日常生活在不断扩张,也即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体系的脱嵌。
然而,伴随着日常生活异化同时进行的还有哈尼族箐口村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变迁。透视这一种变迁,在社会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生计模式的改变以及经济分化的加深。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哈尼族箐口村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的生计方式正在慢慢消解,而逐渐趋于多元化,当然这种自给农业仍旧还是其中的核心生计方式之一,但是其绝对的主导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即使现存的这种农业方式中,也同时夹杂着展演的成分,成为旅游经济中可供体验的消费方式,而以往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主导下的生计方式,也决定了村民某种程度上的同质性,起码在经济上的发展程度是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随着经济性的日常生活占据主导,村民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上出现了差异,而且不难预见,这种差异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化将进一步拉大。
旅游开发对箐口村社会层面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对其他传统家庭制度的影响,具体而言是对箐口哈尼族“幼子继承制”的影响。在过去,幼子继承制是箐口哈尼人在家庭制度上践行的一种方式,即当扩大型的家庭要分裂为几个核心家庭时,房子和父母的田地都由家中最小的儿子来继承,而其他儿子及其核心家庭的成员将与他们分开生活,各自建立自己的家庭。然而随着元阳梯田成功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箐口作为这一景观的核心景区,出于对景观独特性的保护,村民不能再随意造住房,即使是面临非建不可的紧急特殊情况,也要经过相关部门的一级级审批,村民张明华告诉笔者,现在申请建造住房要盖7个章,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箐口哈尼族的幼子继承制度实际上很难再执行下去,而在这种大的社会制度的变迁下,村民们的日常生活也将发生更大程度上的改变。
而在文化层面上,伴随着日常生活的异化呈现出来的变迁主要表现为文化的展演化和文化的商品化两个方面。在一个传统的民族地区村寨中,当与外界还没有形成一种制度性的交互时,其文化也是更多地指向内部成员,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被实践着。但是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文化不断成为一种与外界相互交流的媒介,文化也不再只是针对“近经验”群体,而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异文化的碰撞,以及异文化人群的参与观察。在这样的情境中,文化逐步走上展演化的道路,例如宗教仪式不再仅仅是为了祈求丰收、驱鬼、叫魂、治病,还是为了让外界来观摩、猎奇并愿意为之消费,所以在驱鬼的同时也在表演驱鬼,在叫魂的同时也在表演叫魂。这一过程中,一些原生的意义被解构,一些新生的意义被建构,而文化展演化的过程其实也是文化商品化的过程,例如原本所谓的“长街宴”只是为了庆祝丰收、村民内部聚会的文化习俗,但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长街宴成为了让陌生游客聚集的体验性商品,对于村民而言,更像是在庆祝另一种丰收的情景。不仅长街宴如此,苦扎扎、昂玛突、歌舞艺术、口传史诗、建筑风格、民族服饰都成为了商品。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处于互变共存的相互关系之中,特定的社会文化就会有特定的日常生活,而不同的日常生活也将对应不同的社会文化。在此,我们并不仅仅强调异化概念所承载的批判性,同时也要看到日常生活的异化是社会文化发生重大变革时的正常现象。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社会文化的重大变革将导致日常生活的异化,异化的同时也是日常生活合理化的过程,当已经异化的日常生活再次镶嵌于新的社会文化体系之中时,可视为日常生活合理化过程的完成,然后再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日常生活又将再次走上异化与合理化之路。就像箐口村的旅游开发过程置换来的新的社会文化导致了日常生活的异化,但同时这种日常生活也在进行着合理化,而最终也将与新的社会文化相匹配,呈现出非异化的状态。当然,现代社会中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力量足以化约一切的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和批判。
五、 结语
日常生活世界是客观实在,是衍生其他非日常事项的基础,亦是个体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是那些镶嵌于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总体性实践。本文关注箐口村的旅游开发过程,以及该过程中村落日常生活的异化。这种异化具体表现为镶嵌于社会文化体系中的日常生活向以经济为基础和目的的单向度日常生活转型。在日常生活异化的同时,伴随着哈尼族箐口村社会文化的变迁,在社会层面,主要表现在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以及家庭制度等方式的转变,在文化层面,则呈现出文化的展演化和文化商品化。
哈尼族箐口村的旅游开发是一个村民自主选择与政府指导相结构的过程,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与物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是箐口村社会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笔者无意于对这一种发展项目进行批判,并肯定其具有的正面意义。本文试图在更深层意义上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反思现代性过程中总体性的人逐步异化为单向度的人。就像胡塞尔反思科学对日常生活的异化,列斐伏尔反思工业对日常生活的异化一样,本文实际反思的是现代性中经济体系对日常生活的殖民。
还需指出的是,日常生活与异化的日常生活皆为学理上的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日常生活总是在纯粹与异化之间徘徊、迂回。即没有哪一种日常生活是完全内嵌在社会文化中的,亦没有哪一种日常生活是与社会文化完全脱嵌的,而异化只是表明一种趋势,一种由内嵌逐渐步入脱嵌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赫勒.日常生活[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5]Sruart Elden.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rve.London and New York Community,2004.
[6]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7]马翀炜.云海梯田里的寨子——云南省元阳县箐口村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8]巴丹.元阳县箐口村旅游开发利益博弈的人类学分析[D].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9]朱良文.从箐口村旅游开发谈传统村落的发展与保护[J].新建筑,2006,(4).
[10]唐雪琼,车震宇.哈尼族村寨旅游开发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初步研究[J].红河学院学报,2004,(3).
[11]卢鹏,李钰.民俗展演的生活本真——基于哈尼山寨箐口的个案研究[J].红河学院学报,2010,(5).
[12]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3]何作庆.旅游开发中元阳县箐口哈尼村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研究报告[J].红河学院学报,2005,(5).
[14]郑宇,曾静.民族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的转化——以箐口民俗文化旅游村为例[J].民族艺术研究,2006,(4).
Touristic Development and Alienation of Minority’s Daily Life
——A Case Study of Qingkou Village at Yuanyang County
ZHONG Xiao-xi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outhwest China Ethnic Minorities,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650091,Yunnan, China)
Abstract:Anthropology that emphasizes holistic perspective pays more specific attention to daily life, and holds that many social and cultural matters can usually be seen from daily life while the changes in daily life also mean the changes on socio-cultural aspects.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he touristic development of Qingkou village of Hani people at Yuanyang County in Yunnan province affects the daily life of the local residents there, and tries to point out that during the touristic development, life in the village has been alienated. A life embedded in the holistic socio-cultural system gradually has diminished while one based only on economy is expanding. That is to say, everyday life has drifted away from the socio-cultural system. And behind this is the chang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and culture. Through this case,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ity and daily life.
Keywords:Qingkou village; touristic development; daily life; alienation
〔责任编辑:左安嵩〕
寸亚玲,女,云南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李晓通,男,文山学院体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