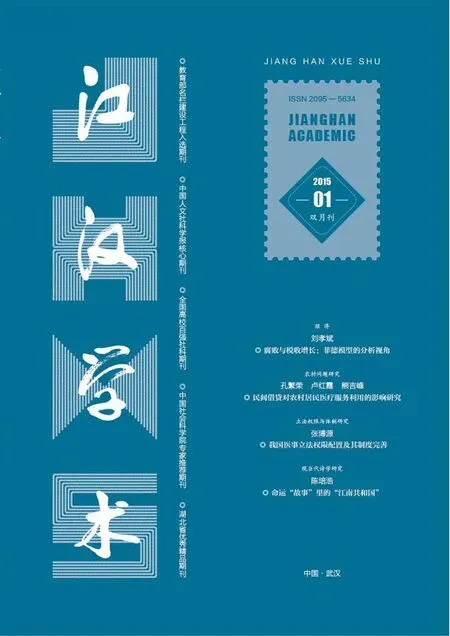中层管理者的意义构建活动:脉络梳理和框架整合
丁宁宁
(山东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济南 250014)
中层管理者的意义构建活动:脉络梳理和框架整合
丁宁宁
(山东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济南 250014)
意义构建是阐述中层管理者复杂活动来源和作用的重要解释方式,目前国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和相关成果介绍还十分有限。从不同研究领域的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的相关研究中,我们发现可将意义构建看成是整合中层管理者大部分管理活动的统一解释方式。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是为了应对多变的工作情境和复杂模糊的组织环境而利用自身知识积累、社会位置和信息占有等优势而采取系列构建、解读、影响等各种社会活动的总和。按照情境—活动—作用的研究脉络,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可分为三种类别:规范化意义构建活动、关系化意义构建活动、结构化意义构建活动。由于意义构建是中层管理者大部分管理活动机理的统一解释方式,又具有在不同组织情境下解释中层管理者分散活动的机理优势,因此,厘定其基本活动范式和可能作用途径,能为未来意义构建活动研究及其他管理领域拓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组织情境;管理领域
一、引 言
在复杂组织变革日益常态化以及地理分散化不断涌现的今天,中层管理者在组织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广度和深度。[1]特别是我国正处在转型大背景下,很多组织仅有大的战略方向,但战略计划和运营细节都模糊不明,中层管理者在创造、阐述与推进变化过程中起着重要、多变的作用,但当前研究对他们的关注仍非常有限。[2]
这种局面可能与中层管理者活动的复杂性有关:一方面中层管理者是变化代理者,是组织中各分离部分和各区域重要的跨层次枢纽,对组织结果负有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组织内的利益多样性和资源有限性,中层管理者可能出于维护个体利益的目的,做出抵制创新和抵制变化的行为,从而损害组织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不同研究对中层管理者作用机理和施加方向的解释往往有冲突的情况,这为全面审视中层管理者活动带来了挑战。
意义构建(sense making)一般用来指个体层面的认知结构化或重新结构化的过程,可以有效帮助理解中层管理者如何诠释周围环境并应对差异化。基于该范式来理解中层管理者活动,可以将组织变化源和中层管理者活动内容、活动过程结合在一起,突破因果关系链条分析范式的单一性,特别适合比较和概括具有复合多元作用的中层管理者管理活动。
当前国外的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的研究,已经从对机理的一般解释研究向动态情境下的活动趋势研究演化,但国内相应研究还不多见,对其详细介绍有助于构建中国的中层管理者活动研究框架。本文首先对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概念做出界定,然后对不同方向的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研究进行了回顾,最后基于“情境—活动—作用”的对应逻辑,给出了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的分类情境整合框架。
二、研究背景和概念界定
1.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兴起的背景
通过对1977年到2013年多项研究进行归纳,我们发现与中层管理者相关的研究繁多,且多散落在不同目的的研究领域中。早期的中层管理者管理活动研究,并没有采用意义构建作为解释其活动的核心机理。当时的研究经常用中层管理者影响力、中层管理者角色行为、中层管理者战略角色等[3,14]来作为核心概念,中介变量和因变量也大都使用中层管理者活动可以直接影响的指标,如主观绩效、商业绩效、组织有效性、新技术运用的倾向性、战略决策质量和执行质量等[4-6],这与早期相关研究主要是为了证明中层管理活动与组织效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有关。由此,其研究设计也大都从职位角度或功能角度来分析中层管理者,尽管认可中层管理者的活动分散也具有多元作用,但从其假设每种作用的行为边界大致可以确定,按照某类管理目标要求来回溯中层管理者应有的活动模式,可以形成对中层管理者行为的预期集合。早期研究认为分散化的行为和根据变化来相机决策的行为对组织起的作用并不显著,故对此不做重点考虑。
该类研究思路很快面临来自多重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不同的研究对中层管理者的作用方式和作用方向持有不同看法,因此对中层管理者管理活动和组织效果之间的关系预测并不一致,[7]这不利于相关实证结果在实践中进行推广,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另一方面,不断变化的组织情境加剧了研究解释力的不足,研究界开始质疑早期研究无法刻画中层管理者影响的多元性,也无法解释其作用机理的深远性和复杂性。
为了解决该类研究的不足,也为了满足进一步解释组织变化中中层管理者的贡献方式,后续研究大都不再用“规定空间”来限制中层管理者活动内容,对管理活动的考察也从预期行为转到实际行为中来。由此,管理者如何认识周围复杂多变的环境,并通过认知重构来识别和应对环境的要求变得特别重要,[8]这决定了中层管理者管理活动的内容和影响范围。意义构建成为研究中层管理者管理活动的“核心”机理,进入到大量研究的关注领域。
2.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的概念界定
意义构建最初用来对高层管理者的活动进行解释,当出现战略变化时,高层管理者需要创造对战略变化的新的认知图示,同时也要向与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解释这种战略变化。随后,中层管理者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构建活动也受到重视。但不同研究者们对意义构建活动的核心认识不同,因此对意义构建的定义也有不同的阐释。
意义构建的最初定义十分广泛,是指“管理者为了理解组织情境和环境时,通过理解、翻译、释义来重构其认识的社会过程”[9-10]。Gioia和Thomas也基本认同上述概念,认为中层管理者的意义构建活动是指中层管理者通过理解、翻译和创造组织变化中的各种信息来源来对组织情境进行认知构建,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问题进行判断并采取行动的各种活动的过程。[11]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意义构建活动是双向的,是以循环、互动为基础的意义读写活动,个体认知层面的意义构建活动隐藏在个人深层次的认知基础上,很难探究,因此互动层面的活动具有更重要的意义。[12]Balogun则将意义构建活动看成是交互作用的多重活动,他认为意义构建活动不仅嵌入在个体的翻译和活动激发过程中,而且在一定阶段内会塑造个体的主要活动和附加活动范式,同时还会受到其他个体的翻译过程和活动的影响。[13]概括来讲,不同的概念都大致认同意义构建活动是持续进行的,一般会经历下列阶段:首先对外部环境给出的各种信息进行评价、解释;其次建立自身的认知框架并内化为决策标准;再次是社会化过程,即和周围主体互动,形成相似或一致的共享意义体系。
由于当前扁平化趋势的出现,研究对中层管理者的界定是依据其“作用”而不是依据其“职位”,中层管理者不仅是不同层级战略活动和业务单元日常活动的协调者,[14]而且是组织结果来源的关键解释者和汇总者。[1]因此本文认为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是指为了应对多变的工作情境和复杂模糊的组织环境而利用自身知识积累、社会位置和信息占有等优势而采取的系列构建、解读、影响等各种社会活动的总和。
这一界定将意义构建作为通用的“活动解释逻辑”来看待,基于该前提:日常的适应性管理可以看作中层管理者基于简单修订的认知框架自动行动;战略和开拓性活动可以看作中层管理者是在以往认知框架失效的情况下,对新情境进行认知构建后再主动行动,只不过有些意义构建活动面临的约束条件和决策空间更为严格,而有些活动自由裁量权更高而已。该界定可以把中层管理者大部分活动都纳入到意义构建活动的范畴中来。
三、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研究的相关脉络梳理
基于上面的概念界定范围,本文根据中层管理者活动范式回顾相关的中层管理者的意义构建活动进行研究。Floyd等认为中层管理者管理活动可以分为分散性活动和整合性活动,[2]Christian认为中层管理者对组织实施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其一是垂直层面的影响;其二是水平层面的影响。[15]在垂直层面上,中层管理者起到了联系高层和基层的信息传媒角色,并影响了核心竞争力的产生方式;在水平层面上,中层管理者的作用可以看作是整合者,通过帮助确定知识基础的资源在整个组织的分布方式来实现。由此,我们将中层管理者管理活动根据方向和目的性划分为自上而下的执行类活动、自下而上的整合性活动、水平的自发性活动三种。同理,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研究也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镶嵌在中层管理者战略实施研究中的意义构建活动研究;第二类是探讨中层管理者战略作用的战略性意义构建活动研究;第三类是组织社会情境下的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研究。
1.镶嵌在中层管理者战略实施研究中的意义构建活动研究
传统研究一直认为中层管理者的主要贡献在于促进战略计划中各项任务按期按质执行,从而使“目标要求”得以实现,如果中层管理者能够在这一过程中遵循既定的行为要求,会减轻组织的内耗,最大程度地实现既定目标。显然这一思路并不强调中层管理者的灵活作用,但研究者在对战略实施进行分析时,还是不可避免地探讨了中层管理者自主性活动的价值和作用方式。
首先中层管理者日常执行活动会存在一些类意义构建活动,如为了获得既定产出,根据已有组织规则和决策范式进行变通工作,进行与其他主体就当前工作变化交换意见、获取支持、取得许可的活动。[15]这些意义构建活动在相关研究中大都被看作是完成既有工作任务的手段。如Wooldridge等认为中层管理者可以通过改善工作环节的决策质量和沟通策略来提高执行效率,并认为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战略影响力;[1]而Alexandros等则分析了中层管理者如何与质量管理体系结合,并提高组织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他认为中层管理的有效自治、授权等活动可以促成质量管理理念的出现,并提高组织产出。[16]Jerry等剖析了中层管理者在处理日常变动工作时的活动范式:首先中层管理者将面临的问题转化为执行要求;然后形成对新管理体制的预期;随后这种预期会影响中层管理者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并反映在其与下属的非正式沟通中,这种非正式沟通与预期的一致性对问题能否解决有直接作用。[17]
其次在探讨中层管理者战略执行活动的研究中,意义构建活动成为各研究一致考虑的要素。如Christian等认为,中层管理者的战略实施功能与其信息传递角色有关,中层管理者一方面收集了组织中两个或几个不相联系部分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谈判、翻译等活动改变了水平层面的信息整合方式,显然,中层管理者通过一定的意义构建活动丰富了信息传递达成的路径,也对执行质量产生了一定影响。[15]Saku Mantere认为中层管理者可以被看作是“组织知识基础”的代理者,这种代理者因为具有组织实践经验,可以更加自由和灵活地作出反应,并且对社会结构条件和组织情境对其代理要求有清楚的认识,因此中层管理者战略实施行为和面临的战略代理情境有关。[18]根据上述观点,Saku Mantere提出了自上而下五种战略代理情境(具体化、情境化、资源分配、尊重授权、信任),并分析了不同战略代理情境对中层管理者的行为要求,在这些情境中大部分代理行为需要中层管理者通过比较、判断、相机决策来采取不同策略,都基本符合意义构建活动的范式。
总之,尽管中层管理者战略实施活动目标和行为边界都比较明确,但意义构建活动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影响其执行效率。一方面,中层管理者负有战略形式化的责任,其能否准确理解战略,并将其转化为合理的日常活动议题与执行效率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中层管理者对下属负有管理责任,其领导方式、对已有任务解释的方式、沟通策略和销售效果等也会影响员工对任务的理解和执行结果。
2.探讨中层管理者战略作用的战略性意义构建活动研究
在上述战略实施研究中,意义构建活动只是丰富和补充了对中层管理者影响方式的解释,但在战略动态调整过程中,意义构建活动可以差异化分析中层管理者的反应和行为,特别适合解释造成组织模糊的可能原因,因此成为探讨中层管理者在战略层面起作用的主流范式。
很多研究在探讨中层管理者如何通过战略性意义构建活动来形成战略议题时起作用。Floyd对企业在厘定战略议题时中层管理者对相应备选方案的支持、推销和弥合不同主体认知的活动进行了简要分析。[3]韩玉兰基于中国企业的情境,分析了中层管理者的对当前“不确定环境”的构建和解读,并提出了管理觉知这一概念作为中层管理者意义建构模式的概括。[19]她认为导致组织环境不确定性的中国情境文化因素主要有三种:关系取向、和谐导向和高语境沟通,因此中层管理者会采取一种行动前小心谨慎、主动觉察当下情境并进行深入思考的意义建构模式,该模式对组织的战略形成有深远的影响。Charlotte从综合视角探讨了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是如何影响组织层面的企业家精神形成的,他将模型分为预先的策略搜寻阶段和策略形成阶段,在预先的策略搜寻阶段,中层管理者对相应方案的评判是影响企业家精神备选范围的重要因素;在策略形成阶段,中层管理者是否具有动力向利益相关者进行阐释和销售决定了组织企业家精神的实际内容。[20]
也有些研究从灵活适应和快速应变的角度来阐释中层管理者战略性意义构建活动。Rouleau认为意义构建活动是中层管理者以其具备的实践中的默会知识为出发点,通过信息传递重构最终得到组织认可或象征合理化的结果的过程。[21]基于此,他认为中层管理者的意义构建子过程包括:根据收集的信息讲述“故事”的翻译过程;在对话中根据对方的社会文化背景编码强化信息和活动再编码过程;根据变化围绕主题施加客观和情感影响的纪律过程;最终则是给予理由采纳该意义的判断过程。Lüscher等讨论了中层管理者如何对组织中面临的悖论情境进行意义构建,他基于活动研究的视角,将悖论问题解释为绩效悖论、归属悖论、组织悖论三种情境,并概括了中层管理者在这三种情境中将采取“问题—两难—悖论—稳定化”的意义构建模式。[8]
最新的研究则开始关注对组织影响更大的中层管理者的开拓性活动,探讨底层的战略意义构建活动是如何开展的。Balogun将视角放在了组织语言规则体系发生正式变化的背景下,研究了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时中层管理者进行的意义重构活动。[22]作者基于纵向的案例分析方法,将规则分为核心部分、工程部分和服务部分,最初中层管理者基于共享规则进行意义构建活动,但在组织变化后,中层管理者则根据现有活动分边界来进行意义构建,这可能会带来不同部门中层管理者的冲突,关系紧张,随着冲突的逐渐解决,核心规则体系得到修正,逐步占据了主导位置,工程规则和服务规则体系则通过谈判和再协议的方式重新规划,最终又形成统一的局面。在这种组织规则体系混乱—有序的过程中,规则的再诠释、统一和发布到最后认同的过程,都建立在中层管理者的意义构建活动之上。Rouleau则将研究焦点放在了中层管理者对语义规则体系的渐变作用上,认为中层管理者的言说能力并不仅是基于组织通用的语言和符号进行说服和推销工作,其本身就可以看作是对组织意义体系的构建和重构。[23]基于上述前提,他给出了中层管理者言说能力的来源,即结合组织符号语言体系和社会文化结构,审慎分析后对组织情境的概括。基于对规则体系的改良性概括,中层管理者一方面可以设定情境,将相关人等召集在一起,通过其言说活动促使工作团队围绕战略进行重组;另一方面则可以召集组织谈话,将信息以合适的方法传递给利益相关者,这种交流对协调各利益相关者需求和利益分歧有积极的作用。在这些情境构建活动中,形成对话要求和设置情境成为关键,中层管理者的言说能力成为联系着两个子活动的核心能力。
总之,战略层面的意义构建活动研究是在“中层管理者多元性活动如何影响战略层面的效果差异性”这一问题上展开的。由于意义构建可以将多方向分散的中层管理者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因此既可以用来直接解释中层管理者的战略影响路径,也可以用来间接解释模糊的组织能力是如何形成的。
3.组织社会情境下的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
尽管从影响组织效果的角度能够探讨大部分的中层管理者活动,但由于组织情境的复杂性,利益相关者的多样性,中层管理者的很多活动具有自发性和效果模糊的特征。为了最大程度地了解中层管理者的自发性活动内容和动机,也有一些研究基于组织社会情境展开。
政治视角成为分析中层管理者自发活动的重要切入点。由于组织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利益团体、亚单位和亚文化,中层管理者具有一定资源优势和信息优势,因此具有为了获得一定的个体利益而采取政治性活动的动机。Tempel等整合了跨国公司面临的不同制度变量,并探讨了次级管理者在面临制度冲突性环境下如何调整管理行为并应对外部限制以获取更大裁量权的。[24]Saumitra分步骤地分析了不同利益团体的政治驱动方式以及项目管理者的应对策略和活动内容。[25]Edmund认为中层管理者如果受到较高的政治支持可能会做出更加大胆的决策,由此会减少组织目标的模糊性从而提高组织有效性。[26]谢俊等则分析了在我国情境下,经理人的政治技能以及其主动寻求反馈信息行为的关系,反映了经理人的一部分活动是为了构建其自身的社会资本这一状况。
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探讨则可以深入到中层管理者活动的内部和变化过程,也极具借鉴意义。Anneloes等分析了中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者在互动界面上双方的互动方式和互动机理。[27]作者认为双方通过信息整合和人际互动的影响过程,形成了认知弹性(cognitive flexibility)和整合契约(integrative bargaining)。所谓认知弹性是指双方成员拥有不同情况的知识和展望方式,从而形成对不同可能处理当前境况方案的意识和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弹性;整合契约则是指两者通过互动所发现的能够体现双方共同或者互补性收益项目。认知弹性和整合契约能否形成与双方意义构建模式是否匹配,互动中能否及时调整,调整后收益能否弥合有关,认知弹性合和整合契约最终影响了战略决策质量和实施质量。Yang等则认为中层管理者和周边群体的活动通过两种作用方式而施加,其一是跨层次作用;另外一种则是属于级联式作用。[28]Pappas则认为占主导逻辑的中层管理者活动都与组织中的社会关系结构有关,他比较了在社会网络中和在其边界上的中层管理者分散活动和其影响力,并得出了在社会网络中心的中层管理者具有更大的协调能力和组织支持,而在边界上的中层管理者自发性活动更多元的结论。[29]
总之,综合对上述三类意义构建活动的回顾可以发现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的几个重要特点:首先是其广泛性,程序性活动和意义构建活动像一个连续体,在中层管理者活动层面很难区分;其次是情境性,面对不同情境,中层管理者认知失效程度不同,意义构建的方式和强度也有较大区别;最后是效果模糊性,在中层管理者实践层面、实施层面、战略层面、社会情境层面的多种要求往往交织在一起,意义构建活动和组织效果的关系很难用简单线性关系来表达。
四、情境—活动—作用整合框架
尽管意义构建活动给出了审视不同层次中层管理者管理活动内容和原因的有效思路,但大部分意义构建研究囿于中层管理者活动的局部分析。为了全面刻画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本文引入组织情境变量,来解释不同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起作用的差异方式。
通过对不同的意义构建活动的回顾可以看出,由于主要是刻画个体的认知定位,因此意义构建活动的认知来源和重构内容特别重要。当前相关研究基本从三个角度来分析意义构建活动的认知来源和重构内容:其一是组织现有的工作规则体系;其二是组织现有的社会文化体系;其三是组织现有的编码体系,包括组织中默会知识以及组织采取的语义规则等。显然,这三种因素都属于组织情境因素,将不同要素组合起来可以刻画组织变化的水平,也可以判断中层管理者认知失效的程度和意义构建活动的范围。另外这三个层面的因素与Rousseau对不同层次的组织文化规范界定基本吻合,也符合个体认知从表层到底层的认知变动规律,侧面证明了本文情境区分范式和以往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本文根据组织现有的工作规则体系、现有的社会文化体系,现有的知识编码体系来区分组织情境,将中层管理者活动分为规范化意义构建活动、结构化意义构建活动,关系化意义构建活动三种(见表1),下面对不同情境下的意义构建活动展开方式和转化作用做深入分析。

表1 基于情境区分的意义构建活动分类
1.规范化意义构建活动
当中层管理者的意义构建认知来源是组织已有标准和既往经验,其主要行为模式是依据组织已有工作规则并基于外部变化的细微偏差校准为主时,本文将其意义构建活动称为规范化意义构建活动。这种行为在组织结构比较稳定时具有高度借鉴意义(如图1)。在这种情境下,中层管理者在处理问题时可以直接参照以往情境化构建的经验来进行工作。尽管在某些责任模糊,相互依赖的问题处理环节中,中层管理者需要对情境重新进行理解、解释和认知内化,来完成对组织工作和情境的正确解读,但由于文化价值一致和工作规则底层内核稳定,中层管理者只需要采取较为标准的认知构建方式来采取行动。如果中层管理者采取的大部分是这种意义构建活动,则组织可以事前形成对中层管理者系列行为的预期,并且通过干预手段来约束管理者的行为。这种管理目标——管理行为实际上是组织既定战略常用的计划实施手段,因此规范化意义构建活动可以与完成既定的组织产出路径结合起来。

2.结构化意义构建活动
在某些情境下,由于环境和组织变化,组织中的既有行为规则已经不能适应当时情境了,因此中层管理者面临的各方面信息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这种冲突既增加了中层管理者工作的难度,也赋予了中层管理者可能具有“增加灵活性”战略收益的空间。
本文认为所谓结构化意义构建活动可以看成是“不确定情境”下的意义构建模式,即中层管理者先多方面搜索信息并审视相关决策背景,然后谨慎定义相关问题,在多方深度思考下审慎采取行为。和上一种情境化模式相比,中层管理者在这种环境下需要面临更多的压力,负起更多的责任,中层管理者需要尽可能迅速建立起自身的认知规范,以帮助组织在不确定性的工作情境下能够处理和解决问题。总之,结构化意义构建模式和一定的冲突情境是相伴相随的,在冲突和混乱产生时,中层管理者对于冲突的解决方式是首先对其进行分解,然后再依据自身的解读,通过沟通、调节、推销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使工作回归到确定性的状态。可见,在这一模式中,中层管理者的行为往往是自发性居多,既有的组织认知规则只能提供大略的指导作用,情境中不确定性的成分增多。中层经理在获得各方面信息后,需要首先对自我的认知做出现有意义的“梳理、规则化、解释”,然后才能对上影响,对下指导,从而配合未来环境的工作(如图2)。在这种情况下,中层管理者能否快速识别环境要素,做出合理反应、快速适应成为能否提高组织产出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中层管理者具有较高的意义构建能力和意义解释能力,一方面会提高组织“意料”之外的产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构建组织灵活应变的能力。

3.关系化意义构建活动
中层管理者关系化意义构建活动不是单一个体视野下的社会情境构建方式,而是建立在与其相关主体的互动之上,这是因为在某些剧烈变革诉求之中,组织过去的知识积累和内隐规则无法承担对当前情境进行解释的功能,这时组织编码体系和语义规则也无法弥合不同个体的认知差异,意义构建活动已经不再建立在单一个体的认知标准之上了,反复推进的协调沟通活动成为核心,谈判和妥协是必然选择。
尽管互动过程可能经过多次的反复和变化,但中层管理者在这种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一方面,中层管理者可以配合其关键互动对象的诉求,将中层管理者自身形成的社会情境要求以合乎诉求的方式来展示给互动对象,并最终形成共识;另一方面,中层管理者也可以借助这种过程,将双方对事物的不同认知进行细致的讨论和“讨价还价”,从而满足双方对工作“内隐收益”的要求。这种充分的沟通过程有利于组织战略和变革的顺利推进,也有利于组织新编码体系的顺利形成(如图3)。在这种过程中,中层管理者的对组织效果的作用也具有多元作用:一方面,中层管理者适应能力,沟通谈判能力,自主裁量权力可以最大效力地发挥,对组织能否形成长远的绩效机制起到决定作用;另一方面,中层管理者也可以更有空间利用自己手中的影响力,为一定的“自我利益”创造条件, 因此可能对组织的未来产出产生消极作用。

五、结论与展望
总之,由于意义构建可以看作是中层管理者大部分管理活动机理的统一解释方式,又具有在不同组织情境下解释中层管理者分散活动的机理优势,因此成为探讨中层管理者活动的主要研究思路。但当前的研究对中层管理者如何统一不同层次的意义构建活动没有更具一般性、更有解释力的结论,研究大都以小案例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构建为主要路径,实证研究数量明显不足。为此,未来研究应该从以下几点进行:
1.虽然现有研究已经从不同层次对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进行了分析,但仍然局限于侧面分析,没有正面探讨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内部发生冲突时如何平衡这一机理,特别是正式要求和非正式要求如何作用并平衡的机制。未来应该在界定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方向和方式的前提下,结合组织制度环境和非正式环境两种作用机制来进来探讨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的内在平衡机制。
2.目前大部分研究对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的分析仍没有超越个体活动的层次,这不利于分析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对现有组织知识规则体系如何补充、转化,并形成积累性效果的动态过程。要突破这种局面,需要基于活动发展的视角,理解组织因素影响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方向的内在机理,形成完整展现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性模型。从我国现有研究状况来看,下一步研究需要结合中国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组织要求,探讨中层管理者的典型意义构建过程,跨层次转化作用的一般性规律等理论问题,为引入实证方法奠定基础。
3.目前,对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的研究大部分仍然采取定性研究方式,这是因为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活动面临的约束条件众多,且具有分散化复杂化的特点。下一步需要结合质化研究,开发适用于我国不同组织情境下的中层管理者意义构建活动测量量表,并利用已有实证统计方法的研究创新来进行大样本验证,客观审视中层管理者的行为动力状况和组织影响路径。
[1] Wooldridge B,Schmid T,Floyd S.The Middle Manager Perspective on Strategy Process:Contributions,Synthesis, and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34):1190-1221.
[2] 高静美,陈甫.组织变革知识体系社会建构的认知鸿沟——基于本土中层管理者DPH模型的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13(2):107-188.
[3] Floyd S W,Wooldridge B.Middle Management Involvement in Strategy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trategic Type:A Research Note[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2(13):153-167.
[4] Antonio Giangreco,Riccardo Peccei.The Nature and Antecedents of Middle Manager Resistance to Change:Evidence from An Italian Context[J].Int. J.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05,16(10):1812-1829.
[5] Felix Yip Wai-Kwong,et al.Th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rs’ and other Middle Managers’ Involvement in Strategy Making under Different Business-level Strategies:the Case in Hong Kong[J].Int. J.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01,12(8):1325-1346.
[6] Raman S. Raghu.Middle Managers’ Involvement in Strategic Planning:An Examination of Rol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J].Journal of General Management,2009,34(3).
[7] Bottom W P.Building a Pathway to Cooperation:Negotiation and Social Exchange Between Principal and Agent[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6,51(1):29-58.
[8] Lüscher L S,Lewis M W.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Managerial Sensemaking:Working Through Paradox[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8,51(2):221-240.
[9] Weick K E.The Collapse of Sensemaking in Organizations:The Mann Gulch Disaster[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3,38(4):628-652.
[10]Weick K E.Enacted Sensemaking in Crisis Situation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1988,25 (4):305-317.
[11]Gioia D A,Thomas J B.Identity Image and Issue Interpretation:Sensemaking During Strategic Change in Academia[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6,41(3):370-392.
[12]Mangham I L,Pye A.The Doing of Managing[M]. Oxford:Blackwell,1991.
[13]Balogun J,Pye A,Hodgkinson G.Cognitively Skilled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Making Sense of Deciding[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4]Steven W. Floyd,Bill Wooldridge.Dinoscnirs or Dynamos?Recognizing Middle Management’s Strategic Role[J].Academy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1994,8(4):47-57.
[15]Christian Buss W.Perceptions of European Middle Managers of Their Role in Strategic Change[J].Global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1,5(5),109-119.
[16]Alexandros G. Psychogiosa.Getting to the Heart of the Debate:TQM and Middle Manager Autonomy[J].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2009,20(4):445-466.
[17]Jerry Hallier.Embellishing the Past:Middle Manager Identity and Informal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Technology[J].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2004,19(1):43-62.
[18]Saku Mantere.Role Expectations and Middle Manager Strategic Agency[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8, 45(2):294-315.
[19]韩玉兰.中国情境下的意义建构:中层管理者的管理觉知及其影响[D].北京:北京大学,2010.
[20]Charlotte R. Ren,Chao Guo.Middle Managers’ Strategic Role in the Corporat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Attention-Based Effects[J].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1, 37(6):1586-1610.
[21]Linda Rouleau.Micro-Practices of Strategic 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How Middle Managers Interpret and Sell Change Every Day[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5, 42(7):1414--1430.
[22]Julia Balogun,Gerry Johnson.Organizational Resrtucturing and Middle Manager Sensemaking [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4, 47(4):523-549.
[23]Linda Rouleau,Julia Balogun.Middle Managers, Strategic Sensemaking, and Discursive Competence[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1, 48(5):954-983.
[24]Tempel Peter Walgenbach.Subsidiary Managers and the Transfer of Human Resource Practices i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Institutional Work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pl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J].Schmalenbach Business Review, 2012,64(3):230-47.
[25]Saumitra Jha.Analyzing Political Risk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Practical Framework for Project managers[J].Business and Politics,2013,15(1):117-136.
[26]Edmund C. Stazyk, Holly T. Goerdel.The Benefits of Bureaucracy:Public Managers’ Perceptions of Political Support, Goal Ambiguity,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Advance Access Publication, 2010,21(6):645-672.
[27]Anneloes M L.The Interface of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and Middle Managers:A Process Model[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11, 36(1):102-126.
[28]Jixia Yang, Zhi-Xue Zhang,Anne S. Tsui.Middle Manager Leadership and Frontline Employee Performance:Bypass, Cascad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0,47(4):654-678.
[29]James M. Pappas,Bill Wooldridge.Middle Managers’ Divergent Strategic Activity:An Investigation of Multiple Measures of Network Centrality[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7,44(3):323-341.
责任编辑:郑晓艳
(E-mail:zhengxiaoyan1023@hotmail.com)
2014-10-09 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人力资源管理构型,工作结构与组织创新能力研究”(12YJC63003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组织情绪能力形成、结构及其对组织创新的影响研究——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71172109)
丁宁宁,女,山东日照人,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F272.9
A
1006-6152(2014)06-0099-08
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