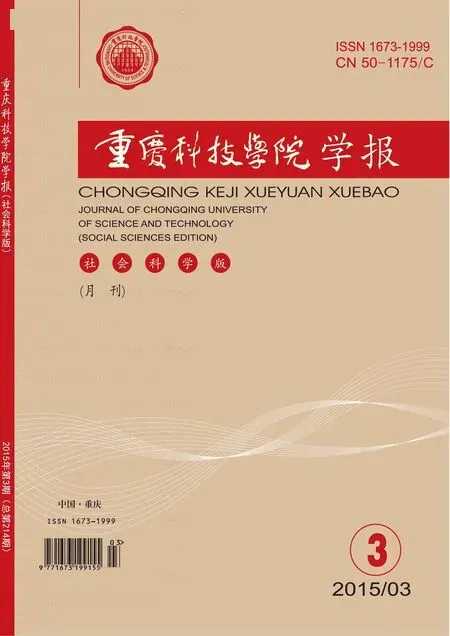贺昌群两汉政治制度历史研究论析
徐涛,陈春
贺昌群(1903-1973),字藏云,四川马边县官帽舟黄桷溪(今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县建设乡官帽舟村)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教育家。贺昌群在敦煌学、简帛学、考古学、中西交通史、汉唐历史与文学、宋元戏曲等诸多学科领域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贺昌群身处动荡变幻的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新文化运动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等一系列运动,这些运动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向西方学习都失败了。对此,贺昌群反思了模仿欧美国家做法的不足,开始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希望对当时的社会提供可借鉴的探索研究。他尤其重视对汉、唐时期的历史研究,其中在两汉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引人注目。
一、对两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论述
贺昌群将汉制优点总结为:“总汉家政制之优点言之,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大小相维、内外相统,如网之有纲、衣之有领,而复能异官通职。”[1]307也就是说,相对于秦汉以前和贺昌群所处的中国近代社会的“无实质性中央”的政治状态,两汉这种“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更能够显示出它的优越性,给时人带来复兴中华的希望。在对两汉政治制度的认识中,贺昌群从中央三公权力、地方太守权力、监察系统的独立性角度来叙述,认为这是两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关键。
(一)中央:三公总政,燮理阴阳
贺昌群在《两汉政治制度论》中指出:“两汉中央政府,按掌权时间来统计,以三公之职为重:丞相上佐天子,总理庶政;太尉掌军政;御史大夫察举朝廷遗失、官吏非法。上述三公主要都是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务,所谓‘遂万物之宜者’,职责是在使政治社会得其平衡而已。政治社会得其平衡,即可臻于治平之世。”[1]307
贺昌群分析认为,汉朝丞相与太尉、御史大夫同为三公,地位、待遇都很高,其中,尤以丞相之位最宠。
首先,从其地位之高而言,丞相只对天子负责,总理万机,在三公之间地位最高。贺昌群引《汉书·百官表》记载:“丞相金印绿绶,太尉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三公秩万石,月俸三百五十斛谷;发放谷物的同时,丞相月俸钱六万,太尉月俸钱五万,御史大夫月俸钱四万。”[2]721
汉朝初年,丞相一职,与皇帝非常亲近。贺昌群引《汉书·周亚夫传》记载说,周亚夫为丞相时,汉景帝特别倚重他,就连窦太后要求景帝给她的一个兄弟封侯,汉景帝都说要跟丞相周亚夫商量之后再回话。这既是因为与周亚夫个人关系好的缘故,也是由于当时丞相与皇帝之间没有像东汉末年那样横亘着宦官或者外戚,使得汉初的丞相地位相当高。
贺昌群又引《汉书·申屠嘉传》记载说,汉文帝时,因先前与晁错有旧仇,申屠嘉当丞相后的某天,两人在皇宫后院单独相遇,吓得晁错急忙躲避,慌忙翻过祭祀的庙墙逃遁而去,可见丞相之威。申屠嘉还不解气,觐见文帝时,又奏请诛杀晁错,汉文帝因爱晁错之才没有允许,申屠嘉后悔不已:“应先斩错而后奏”,可见当时丞相的权利多大;又引《汉书·刘屈髦传》记载:戾太子被江充诬陷,被逼造反,失败后,被丞相司直(丞相府监察官,秩同九卿、郡太守,真两千石——中二千石月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钱五千,米三十四斛。中郎秩比六百石(月六十斛),侍郎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郎中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汉朝的县,大县(万户以上)设县令,小县(万户以下)设县长。县令秩六百石至千石,县长是三百石至五百石。)田仁放出城门。丞相刘屈髦想将田仁就地斩首,被御史大夫暴胜阻止,说丞相司直位居两千石,应该先请示皇帝,不能擅自杀之,结果暴胜被皇帝大骂一通,说“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可见丞相威权之大;又引《汉书·卫绾传》记载说,汉景帝生病不能亲政,则由丞相卫绾代天子处理政务,等等例子都说明汉朝丞相的地位非常之高。
其次,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重要作用言,主要是“总秉机枢、燮理阴阳、遂万物之宜”[1]307。
贺昌群引《汉书·王陵传》记载:
“文帝问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问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上又问左丞相(陈)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为谁乎?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则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君所主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扶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上称善。勃大惭,出而让平曰:君独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独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盗贼数,又欲强对邪。”[2]2023
贺昌群认为,上述故事一方面说明陈平聪明狡猾、随机应变,周勃老实忠厚、善于持重守成而变通不足;另一方面更说明当时丞相的地位相当地高,但其作用不是具体操作某些事物,而是“遂万物之宜”。又如,《汉书·丙吉传》记载:
“吉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住,使起吏问逐牛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被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以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2]3135
陈平、丙吉这两位丞相的为相之道效果如何呢?有没有怠慢政事呢?通过归纳《汉书》中关于朝代治平的评价,贺昌群认为陈平这种“各有主者”的为相之道,完全调动了其它官员的积极性,配合了汉初“休养生息”的总政策。丙吉的为相之道,宽大好礼让,对汉朝的宰相制度有许多建设性的开创,帮助宣帝最高程度地发挥了汉朝政治制度优点,使汉朝的昭、宣时期成为中国古今治平之冠。
贺昌群通过对汉初中央政治体制的研究,得出其具有各就其位的任职状态之优越性。认为许多朝代所谓能干的官员,最终却没有能够完成一个时代的治平工作,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官员没有各就其位,虽然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但真正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去做,也不敢去做。他认为要达到这种各就其位的政治状况,不是少数某些人参与就能做到的,而需要整个政治体制的配合。对这种三公总政、燮理阴阳、各就其位、天下大治的政治制度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贺昌群对当时政治状况的认识。
(二)地方:上下相维,地方得治
贺昌群在《两汉政治制度制度论》指出:“太守,初名郡守,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掌一郡之事,凡治民、进贤、劝供、决讼、检奸,皆太守之职。常以春时巡行所主各县,劝民农桑,拯救乏绝。秋冬遣公平无害之吏按讯诸囚,平其罪法,论课殿最。岁尽上计簿丞相、御史府。有奏上丞相、御史以闻天子。”[1]334贺昌群认为,两汉地方郡国的官员在具备相当独立性的同时,亦以中央政府为榜样,各就其位,认真做好作为郡守应该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实实在在地成为地方百姓的“父母”官,造福了一方百姓。
首先,贺昌群在太守地位方面的考证举例:《汉书·循吏传》记载:“宣帝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为两千石乎”[2]2624。这是盛世之君汉宣帝对当时地方郡守政绩的高度评价,历史事实也证明,昭宣时期的汉朝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堪称盛世。而贺先生时代的官吏:溜须拍马、事故奉承、明听号令、暗自为天;乔扮能廉、招骗名声、垄断政策、搜刮百姓。两相对比,昭宣之政治,简直就是贺先生之类志士仁人的梦想。又引,《汉书·季布传》记载:“文帝谓季布曰:河东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2]2624,可见对太守之职的重视。又引,《汉书·严助传》记载:“武帝赐会稽太守严助书曰: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勿以苏秦纵横”[2]2776,可见赋予太守多大的独立权威。又引,据孙校《汉旧仪》记载:“太守每年以八月都试材官骑士,习摄御战阵,课其殿最”[1]335。此项史书记载得到贺昌群等西北考察团专家在居延发现的汉简的证实:
“功令第册五士吏侯长烽燧长当以令 秋试射以六马程过六赐啬夫十五日。”[1]335贺昌群考释:功令,是指根据国家之法令,第册五是指第四十五燧,士吏、侯长、烽燧长皆皆应秋试骑射之令。此简是以骑与射一并考试。这说明两汉太守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力,能够为他们在职位上尽力工作做好保证。
综合《汉书》的职官升迁记载,贺昌群认为汉时的太守有的由中央尚书令仆射出任,例如钟离意、黄香、桓荣、胡广等,有的太守工作出色,直接升任三公,例如虞延、第五伦、桓虞、鲍昱等。他认为中央三公职位与地方太守之职交换频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官员一旦升迁,就永不降级,致使用人制度僵化的弊端。
其次,在治理地方的政绩方面,贺昌群引《汉书·薛宣传》记载:“宣以陈留太守迁左冯翊。栎阳令谢游贪猾,宣移书责之。游解印绶去,宣更调人代守其职。县令繁简不称职,太守得据当时条令对调之,薛宣以粟邑县小,僻在山中,其民谨朴易治,而尹赏久于郡事,迁在粟。频阳县令薛恭本以孝行称著,未尝治民,而频阳为上郡、河西数郡辐辏之地,多盗贼。宣即以令奏赏与恭换县。二人视事数月而两县皆治。”[2]3385薛宣为吏,“赏罚分明,法度公平,所居皆有条教可纪,多仁恕爱利。为人好威仪,进止雍容,甚可观。性密静有思,思省吏职,求其便安。下至财用笔研,皆为设方略,利用而省费”,最终升任御史大夫、丞相。贺昌群的分析说明,当时的“丞相—太守—县令”直接汇报制度,运转非常高效,在拥有相当独立权威的同时,能够迅速地将中央政府的正确决策运行到地方,直至每一个民众。这是贺昌群对两汉地方权力是否合理的判定。
(三)监察:监察独立,四方清平
贺昌群在 《论两汉政治制度的得失》一文中指出:“自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崇五经,各置博士,立为官学,以教弟子,儒者乃讲求通经致用,董仲舒、公孙弘、倪宽之居官,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为时君所器重。朝廷每大事或官府每决大狱,多援引经义以折中是非。”[1]325这直接导致“谙熟律法之奸吏因缘弄法,所欲活则傅生意,所欲陷则予死比”的窘困政治态势。于是促成了汉朝监司权利的增大。监司权力的增强、独立,造就了汉代较长时间的官场清廉状况。
贺昌群认为汉代监司权利的扩大和独立,确实为汉朝的盛世到来做了巨大的贡献。如:汉代执掌监察大权的有司隶校尉和十三州部刺史。司隶校尉专察皇亲、三公、九卿及三辅(扶风、冯翊、京兆)、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弘农等七郡违法者。史称初期的刺史专道而行,专席而坐,廷议处九卿上,朝贺处九卿下。又,《汉书·百官表》记载:“哀帝时,司隶校尉由天子直接除授,初,似独立无所隶属,后隶属于御史大夫,尊崇过于御史中丞”[2]722。这可见司隶校尉权力的威严和独立性。
贺昌群认为这种威严和独立性致使司隶校尉敢于直接弹劾当朝宰相、贵戚,使得拥有巨大行政权力的丞相受到合理、有效地制约,使其在合法、合理范围之内充分地发挥才干、治理国家。最关键的是这种监察力度的强大与独立性,可以直接影响到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选拔为丞相或其它官职,而不仅仅是选拔出来之后的严厉监督。
贺昌群认为十三州部刺史是武帝时期开始设置,十三州部刺史的设立是汉朝真正完成大一统的标志。因为吴初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官吏任免之权,完全被中央政府收回。但是,大量的小藩国仍然存在,加上防止地方政府专权,所以又设立刺史监督二者。刺史权力甚重,专察强宗豪右和两千石太守。一般是在每年的八月秋分出巡,考核百官优劣,省察政绩,黜陟能否,断治冤狱,年终回京师向皇帝禀报。这种制度的实行,即保证了地方藩王、太守能够在独立任事、清廉执政的同时,又不脱离中央政府监督,保证了全国政令的有效实施。
在刺史专察两千石太守的同时,刺史的秩禄却很低,只有六百石,不如有些县令之秩。既然这样低,为什么还有人愿意担如此大的怨愤而领不相对称的俸禄呢?贺昌群认为,这也正是刺史制度的巧妙之处所在:爱财者贪禄,爱名者贪功,天下之人,无奇不有,各取所需,有何不可?何况,刺史权力重,就能独立于同级行政之外不受影响,可以避免名曰“监察”,而实际上却要受到同级行政长官的限制,而不敢真正实施监察权力的情况出现。另外,拥有重大权力的刺史只享受较低的秩禄,可以防止刺史肆意妄为,滥用职权,如此“以小治大”的妙法,被贺昌群十分推崇。所以,贺昌群认为上述这种独立、权威监察职位的制度完全可以和前述“中央权力强大”、“地方权力独立”并列成为为对盛汉形成的“三大功臣”之一。
二、两汉政治制度的典范性
贺昌群在《两汉政治制度论·引论》中说:“三代之制,书阙有间,世所称《周官》,其书之真伪,与其制度之曾否实施,或曾为局部之实施,或竟为儒家之空中楼阁,此皆经学范围,非论史者所敢言也。汉承秦制,世称秦人每事不师古,虽不必尽然,然其始实未尝取法成周,故言中国制度,不能不以秦汉为嚆矢。秦汉内设九卿,外置列郡,古来制度为之一变。东京以后,事归台阁,虽分置尚书六部,而政在中书,其权独重,汉魏之制,至唐宋而又一变。明太祖废中书省,罢丞相,尽归其职于六部,永乐间复设内阁而参以七卿,唐宋之制至是而又一变。”[1]306认为两汉沿袭、改进的秦朝政治制度,使得中国从春秋战国以来酝酿了几百年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融得以稳定成型,真正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稳定的中华文化,成为后世华夏民族的典范制度。对此,贺昌群对两汉政治制度的典范性做了归纳。
(一)官吏升降制度的规范
汉之官制概况,贺昌群评价为:“总汉家政制言之有点言之,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大小相维,内外相统,如网之有纲,衣之有领,而复能异官通职。中央以三公之职为重:丞相上佐天子,总理万机,用人行政,无所不统,在三公之间其位尤为尊崇;太尉掌全国军政;御史大夫察举朝廷遗失、官吏非法。皆以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为务,所谓‘遂万物之宜者’,盖三公之职,在使社会平衡而已。政治社会得其平衡,即可臻于治平之世。”[1]307这种上下相续,各司其职的管理制度,使得政府工作效率非常的高。《汉书·魏相丙吉传》记载:“丙吉居相位,掾吏有罪过,或不称职辄长给休假,令其去职,终无所案验(以法律重处)。或谓吉曰,君侯为相,奸吏成其私,然无所惩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窃陋焉。”[2]3133后人代吉,以为范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这也可知汉代丞相的雍容大度、聪明平淡、总达众材,而不以事自任,使得汉代丞相所见者远、所虑者深、所务者大,真宰相之体也。
贺昌群认为,中央以三公统筹大政方略的同时,地方以太守为吏治之本,具体负责治民、进贤、劝功、决讼、检奸、教化等工作,这使得中央和地方内外相应、轻重相依,并且成为两汉常制,使得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和融合,为华夏民族认同感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为后世捍卫国家领土统一开启了心理认同之门。
官吏是社会公共资源的管理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官吏制度的好坏,直接影响那段历史的发展。两汉官吏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中央与地方大小相维、关系畅通,形成一个机整体,整个社会运行流畅。虽然大多都是沿袭秦朝的旧制,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在文景之时,由赢秦之苛烦变得简易;第二次是在武帝之时,由简易变为庄重;第三次是在光武、明、章之际,由庄重变为繁复。
秦统一之前,华夏各诸侯国政治制度迥异,各霸一方,各行其是,形成了许多独特性的文明区域。秦统一后,将这些区域性文明联合起来,形成了新的华夏文明,可惜未能长期延续。接踵而至的两汉王朝因为多出明君贤相、政治制度优良、统治时间较长,终于完成了中华文化的交融稳定。
(二)人才选拔制度的规范
三代时期,由于分封制的推行,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士大夫都世代享有官职与俸禄的特权。“王官世守”、“官爵世及”,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也是人们所奉行的社会准则,这一准则的支撑与基石是社会宗法制度。其核心是“亲亲”,即根据家族内部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确立家族政治地位与财产的继承分配关系。西周建立之后实行的分封制度即是以宗法制原则,对国家管理权及政治资源进行的一次大分配。这种以井田制为经济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世代相袭秩序,是三代王朝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急剧变迁的时代,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庶民地主阶级的产生,以及长达数百年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招贤养士之风盛行,使军功、事功升迁成为可能。过去只有贵族才能染指的国家机构,也有了平民阶层的一席之地。后来,军功、事功制度逐渐取代了西周的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封闭的世卿世禄制度,成为当时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国家组织的初步定型。国家官吏选任制度在经历夏到战国近两千年的发展,也达到了初步成熟。秦代及汉初,官吏选任以军功爵制为主,并辅以荫任制和征召辟除制等为官形式。不过,上述方式仍不能满足汉初日益膨胀的国家机构对人才的需求。为解决经邦治国之士缺乏的难题,汉武帝于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以备国家选用,从而确立了孝廉察举为官的制度。《汉书》记载:“武帝初即位,征天下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2]2841另外诸如:“公孙弘年六十,以贤良方正征为博士,出使匈奴,建立功业”[2]2613;“董仲舒以贤良著称,进而得以献策武帝,成就儒家大业。如此征召之名士得以数百。”[2]2495
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以往的官吏世袭制,打破了汉初军功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选拔了一大批国家急需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才。对此,贺昌群在《两汉政治制度论》中说:“考两汉仕进之途,为征辟与察举二事。”[1]319认为这两种举人方法改变了汉以前的举人制度,为“两汉得人之盛”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后世选官用人树立了榜样,是两汉留给后世的重要财富之一。
到东汉晚期,由于世族地主把持国家权力,察举制的作用略受削弱;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久乱之后对国家权利的再分配,曹魏于延康元年(220年),在两汉察举制的基础上始行九品官人法制度;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的崔、卢、王、谢,南方的顾、陆、朱、张,这些名门大族高踞政府要津,连皇帝也要让他们三分,这种门阀政治造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平民百姓中优秀人才的晋身之路,使得两汉察举制度有所变味;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隋唐,进入了它的繁荣时期,在长期的国家管理与政治实践中,官吏的选拔与任用制度,经历了不断的改革与变化,也逐步进入了它的成熟期,最终产生了运行1 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而科举制度可谓两汉察举制度的深入和完善,可见两汉人才选拔制度对后世造成多么重大的影响。
贺昌群通过对两汉政治制度的研究,认为东汉之后,制度上日渐恶浊,最终演变成为近代官僚政治;文化上儒、道、法三位一体构成政治社会,政治家若不兼具三者之精神必遭失败。得出:“大约历史之演变,其动因或为经济,或为政治,而中国历史之演变,往往属于政治的成分较多,属于经济的成分较少。盖经济之支配力,必随交通之发达始能增高,持此以论汉晋间史事之演变,知其不尽为经济之故也。由上以言,则汉末大一统帝国之解体,先由其政治机构之崩坏,而后有外戚宦官之擅权,外戚宦官之祸愈烈,政治上之破坏愈大,国家大权,遂渐由三公而旁目于刺史州牧之手,即由中央而转落于地方,形成豪杰割据之势。刘焉,刘虞,并自九卿出领州牧,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孙、刘之世。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疆亡,汉末之疆.疆之婪尾,是以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论世者所深悲也。”[1]305的结论。这个结论反映出贺昌群在历史研究中,注重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特殊性的独到之处,值得继续深入探究。
[1]贺昌群.贺昌群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