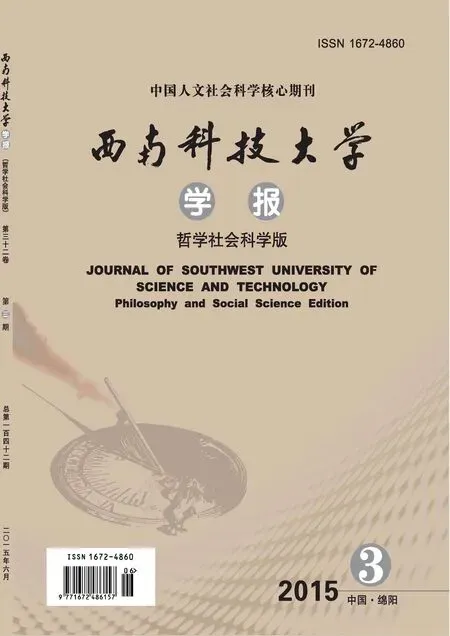女性原则的丧失与重构——汤婷婷《女勇士》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许 娟 杨贤玉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北十堰 442002)
生态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由环境运动与女性运动结合而成的、主动适应社会变革需求的文化思潮。生态女性主义尝试探索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性与贬低自然之间的特殊关系,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二元式思维方式统治下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倡导用关怀伦理理论来建构一种新的环境伦理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性;人对自然的尊重不仅应来自义务;人对自然应有情感回应;关注具体经验基础上的人对自然的关怀、保育和爱[1]。对此,不少文学家们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积极地关注,参与并思考着。作为美国华裔文学代表人物,汤婷婷在她的代表作品《女勇士》中,从自然和女性的双重视角进行文学创作,将生态思想与女性主义完美结合起来,让女性从自然元素中汲取力量,从而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原则的构建,使之获得与男权社会抗衡的实力。作品旨在唤起人们对自然和女性的尊重和理解。汤婷婷的和谐生态观是建立一个生态的、可持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平等相处、相互依存、和谐发展、共同繁荣[2]。
一、男权中心论下女性原则的丧失与毁灭
“女性原则”这一概念由著名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梵当娜·希瓦(Vandana Shiva)提出。她将自然与女性紧密联系起来,并认为自然过程遵循的是女性原则,即能动的创造性、多样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和生命神圣性。然而,在父权社会,男性通过控制自然和社会中的优质资源来支配女性,使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上都依附于男性,潜意识地顺从和取悦男性,从而迷失自我,丧失本性,最终导致生态危机和女性原则的丧失。在《女勇士》中通过揭示几位悲惨女性命运的社会根源,汤婷婷为我们展现了女性原则逐步丧失的过程。
月兰是中国封建社会造就的典型,她的一生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不敢面对也不愿面对。显然,月兰在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低微、从属的社会地位。软弱、顺从,甘愿自己命运由他人摆布,注定是悲惨的结局。当被告知“没有遮掩你的树,没有草坪能使你脚步声变轻”[3]18,她就像在途中看到的葡萄树一样,“蜷缩在田间,像侏儒一样”[3]21。无名姑姑也同样生活在由男性主宰的封建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体系中,男性自然而然地掌控着一切,他们才是权力的象征。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最初源自“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给予男性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养家糊口,成为男性的责任;女性则在家中“照顾子女,赡养公婆”。女性在物质上对男性的依靠,无疑使自己丧失了公平的对话权,成为男性在精神和肉体上控制的客体对象,并自觉接受男性的价值观和男性制定的行为准则,自觉接受被统治的定位,放弃拥有自由的权利。
女性从属于男性地位还表现在婚姻生活中。在封建男权社会,婚姻是女性借助男性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途径,且只能听从父母之命,从被一个男性的控制变成由另一个男性主宰。“她很幸运,他和她年龄相仿,她将成为他的正房,她就万无一失了。”[3]5男权主义下的一系列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的产生,都以男性的利益为出发点,并强调男性统治的自然基础。他们将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行为变成貌似合理的“社会准则”或“传统规矩”;他们认为男女社会分工基于自然赋予的男性统治社会的准则,男性对自然和女性的主宰是不可改变的。因此,男性通过控制自然和社会中的优质资源来支配家庭中的女性,从而使她们依靠男性,最终从属于男权社会。由此一来,女性没有话语权,更无法决定自身的命运,包括自己的身体和家庭地位[4]。
小说的叙述者“我”因为华裔女性的身份,一方面受到美国白人社会的歧视,另一方面还受到父权制度的压迫。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女孩在夹缝中寻求着自我身份和价值,“我”越来越不爱说话,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以致成了“公鸭嗓”。在种族和父权的双重压迫下,小女孩的话语权在不断的丧失,这显然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严重伤害。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也折磨着小女孩幼小的心灵。在美国的华人街,同样流行着“养女好比养牛鹂鸟”,“宁养呆鹅不养女!”[3]24的观念,“我”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承袭着同样的价值观。正如文中所述:“在一次有女孩们到一个亲戚家吃饭时,那个远房的曾祖父会‘瞪着双大眼’吼道:‘蛆虫……全是些蛆虫!’还会‘逐个指着我们’说:‘蛆!蛆!蛆!蛆!蛆!蛆!’”[3]20。在残酷的压迫之下,小女孩幼小的心灵变得扭曲。一方面,“我”因仇视压迫自己的父权制度而模仿男权社会的话语,讽刺了追求“我”的华人男孩:“他智力迟钝,口舌笨拙,他的腿像‘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一样僵硬’,是只‘呆鹅’”;“他坐在那里,腐肉一堆,似乎在放射着细菌,那会降低我的智商。他像一只水蛭,正从我的后脑勺里吸取我的智能。”[3]179另一方面,主人公又渴望在白人社会中得到认可:“我”总是把自身“想象成轻浮粗暴的孤儿,白皮肤,红头发,骑白马”。小女孩在潜意识中流露出对白人社会融入的渴望:“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像其她白人一样,拥有她们的体貌特征,因为“白皮肤”才是以白人为主的男权社会的审美标准。肤色和人种在自然界中本无优劣,尊卑之分。然而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它却被赋予了社会和文化的概念,成为种族和性别压迫的借口。这无疑是对自然的误读和歪曲[5]。
二、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原则的重构
基于自然和女性的密切联系及其共同受掠夺、压迫的命运,生态女性主义者倡导推翻父权制世界观,强调自然和女性的觉醒以及她们的自身价值[5]。汤婷婷创作《女勇士》,让女性从自然元素中汲取力量,从而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原则的构建,使之获得与男权社会抗衡的实力的故事,旨在唤起人们对自然和女性的尊重和理解,其中主要是通过对母亲勇兰这一角色的塑造为读者展现的。
勇兰,是一位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的坚强女性,有着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个性独立、要强,勇于吃苦,对美好生活有着不懈的追求。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不能回家,她独自一人苦苦地支撑着家庭。为了分担家庭重任,她凭着坚强的意志学医成为一名医生。跟随父亲来到美国后,她既承担了家庭主妇的职责,又开洗衣店挣钱养家。虽然生活艰辛,但只要能感触到自然,她的胸中便会涌动着一股力量。“没有鸟,没有树,只是一座城市”,在这样的环境下,“勇兰觉得一股疲惫在向下拽她”,但当她下了车之后,“她觉得踏上地面,尽管是水泥地面,她也从中获得了力量……就感到强壮”。[3]90在家乡,她是闻名乡里的乡村医生,享有盛誉;远赴美国与父亲团圆,很快便适应异国的生活并将家庭和工作(经营洗衣店)处理得有条不紊。面对父权,她敢于说“不”,敢于违背父亲不能将“无名女人”外传的禁令,依然将该事情讲给孩子;无法容忍月兰的丈夫抛弃妻子而在美国重新结婚,毅然将妹妹接到美国,鼓励支持她重新抢回自己的丈夫和家庭。在自然面前,她表现出对自然的无限依赖。她本人是一名医生,但在月兰生病时她也不忘寻求大自然的庇护和帮助,劝说月兰多晒太阳,还挑最嫩的植物为她煎药。可见在她眼里大自然俨然也是无形的医生,可让她们获取力量,驱除身心的疾病,成为她们的精神动力。月兰进疯人院后,勇兰“打开窗,空气和阳光又回来了”[3]82。在小说中,勇兰就像光辉的“太阳”,充满生气,给别人以能量和温暖,象征着生生不息的自然界。作者通过勇兰对自然的密切依赖告诉我们:在父权制社会中,只有自然才能安慰并抚慰女性所遭遇的身心痛苦。自然,就像充满慈爱的母亲,用它的博爱和包容抚平她们肉体的创伤,慰藉她们受伤的灵魂[6]。自然是她们疲惫身心得以休憩的永久的港湾。于是,自然与女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得以强化。在文中,勇兰与自然是融为一体、互为象征的关系。
三、平等,包容,和谐的生态观的构建
汤婷婷的和谐生态观“生态女性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生态的、可持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平等相处、相互依存、和谐发展、共同繁荣。”作者通过对花木兰和蔡文姬两位女性形象的移植和改写,展现出自己对构建平等,包容,和谐的生态观的渴望。
(一)花木兰故事的移花接木——对男女性别二元对立和男权中心论的消解
在中国民间传说中,花木兰的形象是:替父从军、舍生杀敌、效忠君王,体现出中国儒家忠孝的思想。在汤婷婷的笔下,花木兰的传说被移植和变形。从目的上看,花木兰之所以从军,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尽孝,更是为了不再听命于双亲,从而摆脱女子被赋予的职责和家务,真正实现自我价值。
正如文中所述:花木兰只有7岁时,就已厌恶了整日挖山芋,和鸡粪为伴,于是她决心拜师学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在“人”字形鸟儿的引领下,她进山学医。显然,花木兰也并不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在小说中,她竟然与统治者的军队为敌,敢把皇帝拉下马,砍下其头颅,公然向封建专制挑衅。同时,花木兰对父权中心论和性别对立提出了质疑。在师从一对年老夫妇学医时,她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这里没有父权制,也没有男女对立,有的只是相互尊敬、相互爱戴。在作者笔下,这对老夫妇仿佛合为一体,举案齐眉,相依相存。这不禁使人想起了太极图中的阴阳双象,两者无尊卑之分,相互融入、平等互存[7]。这对神仙眷侣仿佛已化身为自然,包罗万象、超脱世俗、宁静致远的意境尽在其中。在这种氛围中,人与自然、男性和女性之间,都实现了高度的合二为一。通过这些描述,汤婷婷试图消解父权中心论和性别对立。“神仙老夫妇”寄托了她期望男女平等、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此外,文中人字形鸟和深山象征着自然,寓意深刻。小鸟形状似人,代表了人类对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大自然的无限向往;深山作为自然的表征,给花木兰足够的养料和力量,使之日后女扮男装,与男人们一起奋勇沙场,随后嫁夫生子,幸福美满。这些,无不显示了主人翁向往的男女平等、相互融合,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相处的和谐生态观。正如文中所述:“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地金人儿,在那里跳着大地之舞。他俩旋舞的很美,简直就像地球旋转的轴心…”。[3]17可见,无论是人与自然,还是人与人之间,都能平等相处、和谐共存。
汤婷婷在花木兰形象上,也进行了大胆突破,使其身上既有比较明显的女性特征,同时又具备显著的男性气质,从而成为“双性同体”的新形象。西蒙娜·德·波伏娃认为,男性人格特征和女性人格特征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在汤婷婷的笔下,花木兰也不是天生的“女勇士”,她是经过移植变形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原本是一位普通女子,在小鸟带领下进山苦学十八般武艺数十载,拥有了一身男性般的阳刚之气;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之后,木兰身上又注入了一股强悍的英武之气,化身为双性同体,“我穿上男装,……我跃身上马,不觉为自己的强劲和高大而暗暗称奇”[3]33。与此同时,她依然保持着女性的自然属性,爱慕异性,结婚生子,尤其身怀六甲还冲锋陷阵时,对于性别的模糊混淆使她显示出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状态:“我把孩子放进背兜,……催马杀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3]36她承担着作为母亲的神圣使命抚育儿女,同时又担负着男性的职责英勇抗战。花木兰的这种阴阳相融的新形象,给予读者双性合二为一的美感。花木兰这位坚强不屈、勇敢果断、自强不息的女勇士形象充分表明:在很多方面,女性不仅不比男性弱,而且还更胜一筹。作者通过对花木兰的塑造,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男女二元对立的保守落后意识,向父权制社会的不合理分工提出抗议和挑战。花木兰这一“双性同体”的形象也展现了作者渴望男女两性之间实现融合、互为补充、平等相处的美好夙愿。在作者的笔下,花木兰作为女子同时也具备贤妻良母的特质。战争结束后,她脱去战袍,母性回归:关爱丈夫,孝敬公婆,养育子女。这一“双性同体”女性的塑造,不仅表达了自己对消除二元对立、消解男权中心论的愿望[8],也表达了作者对女性成长的祈愿。
(二)蔡琰的“羌笛野曲”——对种族、文化对立的消解与融合
“羌笛野曲”主要是“我”回忆自己从幼儿园到长大成人的一段经历。“我”,是在极其压抑郁闷的环境氛围中长大的。为了使“我”讲话“活泛”,母亲代表封建势力割掉了“我”的舌筋,自此,每当听到自己断断续续的声音轻飘飘从口中发出,自卑感就有如一片阴霾时刻笼罩着“我”的心头。“幼儿园的3年我的沉默到了极点,我画的画全是黑色的”[3]149。然而,黎明前的黑暗正等待着幕布升起的那一刻,之后将是“明媚的阳关和丰富多彩的节目”。在小说最后一章,作者将自己比作被匈奴掳到蛮地10多年的蔡文姬,在异国他乡也能够谱写出民族融合的精彩乐章。显然,在汤婷婷笔下,蔡琰的《胡笳十八拍》已然少了几分思乡之情、别离之痛,也不再是无可言诉的悲剧性的结局。作者认为,尽管存在着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胡汉之间也可以通过歌声互相理解,互相沟通,从而达到民族的融合[9]。
“蛮人们听到了女人的歌声,似乎是唱给孩子们听的,那么清脆,那么高亢。恰与笛声相和。”[3]21蔡琰借歌声思念故土和故土的亲人,蛮人听不懂汉语,但分明听到了里面的悲伤和愤懑。当然,她的歌词中也不全部是汉语,也有匈奴词语。在匈奴的12年流浪生活,使她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汉人,她开始同情和感叹匈奴人常年漂泊不定的生活,对于这种情感在她的歌中也时有流露。她的孩子们不会说汉语,但也似乎听得懂她的歌声和心声:“她的孩子们没有笑,当她离开帐篷坐到围满蛮人的篝火旁的时候,她的孩子也随她唱了起来。”[3]90在这里,孩子就是希望,是民族融合共生的希望。解决“他者”与“自我”之间的矛盾的唯一途径是交流和沟通。我们要消解矛盾,而不是更加对立激化矛盾。因此,汤婷婷认为各民族间经过沟通,融合,消除对抗可以解决彼此间文化意识的冲突问题。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得知汤婷婷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可见,在汤婷婷的意识里,自我与他者、男性与女性、强势与弱势文化都是可以从根本上消解、融合与共生的,她反对任何形式的单方强势文化给予的定义和分类。部分学者认为汤是“解构主义理论者”,然而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她的视野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消解两性、种族、文化的对立上,而是触及到了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领域。在重建两性二元对立、人与自然对立这些概念间的互动和融合的同时,她又深刻地揭示出这种互动融合带给人类无限深远的意义。由此可知,汤婷婷并非只是“解构主义理论者”,除了大胆尝试如何实现多元文化融合共生,她还将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付诸实践,折射出她对文化全球化的无限期望,这些都在《女勇士》中有所揭示。通过对角色的塑造,作者告诉人们:“现在我们属于整个地球了,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这块地方就属于我们,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10]
结语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对将人类与自然分割开来的二元对立理论进行批判,宣扬建立男女平等,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环境污染日益恶化,受女性主义运动的启发,很多女性逐渐意识到自然环境的改善和女性的解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不可分割。同时她们也认识到,父权制和男权中心论是导致女性遭受剥削欺凌和自然环境惨遭掠夺破坏的罪魁祸首。此后,生态女性主义成为一种思潮并在世界各国迅速扩展。近代父权制批评家们认为,轻视贬低自然的父权思想造成了男性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这种承认并接受男性统治女性的观念意识同样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贬低。在《女勇士》中,作者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巧妙地在过去与现在、梦幻与事实之间转化,从自然和女性的双重视角进行文学创作,将生态思想与女性主义完美结合起来,让女性从自然元素中汲取力量,从而实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原则的构建,使之获得与男权社会抗衡的实力。显而易见,作品意在唤起人们对自然和女性的尊重和理解,同时作者在不断寻求、确认“自我”的身份。然而,小说中的人物对话虽然紧密联系女性价值和文化定位,但却没有终结,寻求也似乎还没有答案。
[1]罗蔚.另一种伦理观: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与建构华[J].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99-100.
[2]郭继德.美国文学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401-410.
[3]汤婷婷.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4]Glazebrook,Trish.Karen Warren’s Ecofeminism[J].Ethics & The Environment,2002,7(2):12-26.
[5]Bow,Leslie,Betrayal and Other Acts of Subversion:Feminism,Sexual Politics,Asian American Women’s Literature[M].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P,2001.
[6]蔡青,张洪伟.无尽的探寻-对美国华裔女性文学传统的研究[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9:107-108.
[7]宋阳.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勇士》[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46-47.
[8]Ed.A.LaVonne Brown Ruoff,Jerry W.Ward,Jr.Chinese American Women Writers:The Tradition Behind Maxine Hong Kingston.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M].New York:MLA,1990.
[9]蒲若茜.对性别、种族、文化对立的消解——从解构的视角看汤亭亭的《女勇士》[J].《国外文学》,2001(3):101-102.
[10]Chae,Youngsuk.Politiciz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Towards a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M].New York:Routledge,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