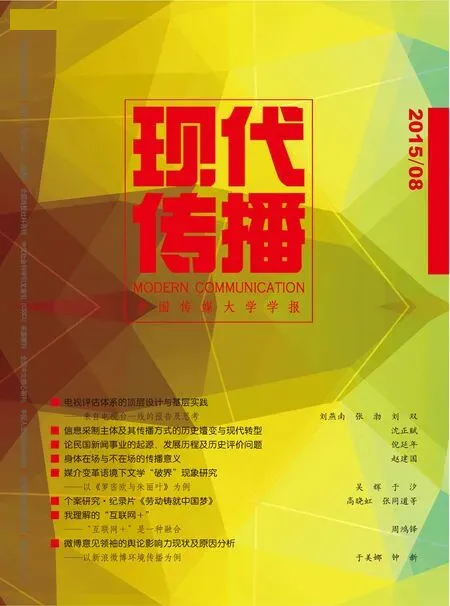媒介变革语境下文学“破界”现象研究
——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 吴 辉 于汐
媒介变革语境下文学“破界”现象研究
——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 吴 辉 于汐
语言、文字的诞生、演进与完善,使得以其为载体的文学日益体系化并在横向与纵向上都形成了一定的疆界。然而20世纪以来,大众媒介的兴起和传媒艺术的发展,使文学的疆界逐渐被突破、剔除。本文从传统文学的疆界构成与破界的必然性、文学破界的表现——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以及文学在媒介变革语境下的传播与创新三个方面对该论题进行了阐述。尽管媒介的特质会不同程度地消解传统文学的某些精妙和韵味,但事实上,媒介变革语境下文学疆界的突破与延伸,其根本就是跨界融合。并且,随着这场革命的深入进行,跨界越来越巧妙而不露痕迹,融合越来越复杂而多变。
媒介变革;文学;《罗密欧与朱丽叶》;传媒艺术
20世纪,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一切固有元素都被视为阻碍发展的屏障,都面临着剧烈变革的挑战,这其中也包括文学。
文学,特别是西方的传统文学,早在20世纪之前就已构筑起一座辉煌的殿堂。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已触及到人类情感和欲望的一切体验。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各种流派也已尽最大可能地融汇了人类文艺复兴以来对世界、对自身的深度思考,而文学理论的概括与提升又几乎可以阐释自上古神话至近现代小说的所有文学现象。
正因如此,一道难以逾越的文学疆界悄然成形,使得后人的破界举步维艰。然而,20世纪以来,新媒介、新思潮冲击着文学领域,在进与退、扬与弃的博弈中,看似牢不可破的疆界却被逐步打破。为此,本文以一个跨越千年的爱情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试析20世纪媒介变革语境下文学疆界破除的表现及影响。
一、传统文学的疆界构成与破界的必然性
在诸多关于“文学”的定义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汇是“语言”和“文字”。换言之,没有“语言”或“文字”就没有文学,它们是人类交流时用于表达的一种符号系统。除此以外,这一符号系统还包括图形或绘画(尽管东方的象形文字是由壁画演变而来的,但西方的拼音文字却完全与之独立)、带有示意性质的肢体动作、抒发情感的音符以及某些可以代替说话的音效(如汽车喇叭的声音)等等。显然,壁画、图像逐渐形成了美术,肢体动作逐渐衍生出舞蹈,丰富的声音逐渐发展为音乐,这些都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无关。所以,文学的疆界,归根结底是语言与文字的疆界。
在所有用于表达的符号系统中,文字在记录信息方面所独具的高精度、易保存等优势,使其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便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从记录先人的经验教训,到制定规则对人进行约束,再到早期的教育,文字逐步成为统治者的权力工具,从而获得霸权地位。文学也凭借着文字的特殊地位,成为“艺术之母”,与音乐、美术、舞蹈等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具有明显的主流优势。与此同时,文学也与其他艺术门类都各自形成了相对完整、相对独立的表达规范,如文学的语法、音乐的乐理、绘画的法则等,同为人类创造的表达方式,彼此之间却鲜有融合。这种艺术门类划界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其语言学专著《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认为:语言具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特点。事实上,这两个特点也是语言的局限。语言的共时性使其形成了地域、民族的疆界,不同民族无法仅依靠本民族语言就能读解其他民族的语言。而语言的历时性又使其形成了时代的疆界,语言在不同时代的演变,导致即使是同一民族的人生活在不同时代,其使用的文字符号与语法规则都有所不同,例如英国的古英语和现代英语,汉语亦如此。所以,文学的疆界不仅表现在与其他表达方式或艺术门类的差异上,也表现在不同民族或不同时代的差异上。
然而,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海外殖民以来,世界各民族的联系随之广泛而紧密,通过文字来强化民族国家意识与文化身份认同的行为也愈发获得认可,文学保持其传统的疆界也就越发勉为其难。19世纪摄影技术与录音技术的发明,成为继文字之后又一种新的信息记录的方式,且其对信息的还原比文字更有优势。尤其是影像“所拍即所得”的效果,使信息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进入20世纪,胶片、唱片、磁带、录像带,直至数字化的保存与复制方式的发明层出不穷,不仅在更快、更远的传播过程中还原了信息,还诞生出更具活力的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等传媒艺术形态①。这场史无前例且持续至今的媒介大变革,不仅动摇了文字作为信息记录工具的首要地位,也动摇了传统文学在艺术领域的霸权地位。
与此同时,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引发信息爆炸,促使生活节奏加快。尽管文字的逻辑性使其在记录思维过程、阐述思辨性观点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但影像可以将大量客观实在的信息更加直观、生动地呈现出来,使受众对信息的解读也更为便利。因此,相比于抽象的文字,直观的影像在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上更具优势,这种现状被认为是人类进入了“读图时代”。而社会快节奏运转的结果是产能过剩,使得整个社会需要由原来的生产型转向当下的消费型,艺术也呈现出商业化、娱乐化的倾向,更何况影像自身声画结合的特点,使其自诞生之初就具备刺激受众感官以达成娱乐的目的,这也是影像的又一个优势。
此外,不可忽视的是,这场媒介变革也深化了人们对媒介本身的认知。尽管媒介古已有之,从口头到纸张,再到印刷,但人们对媒介的理解也只是作为传播信息的载体,是内容的附庸。然而,20世纪传播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认为:媒介不仅对信息的传播,同时也对信息的内容起着巨大的反作用,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感知、思维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甚至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观点,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各种媒介相互融合并形成网络,其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种语境下,一切内容都被纳入无所不在的媒介网中,自然也包括文学。所谓文学的疆界,是建立在以单一的印刷为主宰的传统媒介观的基础之上的,而在当今全媒体、融媒体的语境下,文学固有的疆界已然过时,文学的“破界”势在必行。
二、文学破界的表现——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事实上,莎翁的这部剧作本身就是一个破除疆界的故事,即两位主人公的爱情先破除了家法族规的疆界,又破除了宗教礼法的疆界,最后破除了生与死的疆界。以该剧在四百年间的演变为例,本文从表现形式、思维观念、叙事功能三个维度试析文学在媒介变革语境下的“破界”。
(一)表现形式的“破界”
早在影视媒介诞生之前,同一个事件就已然存在于诗歌、寓言、小说、戏剧等不同文体中。莎士比亚让“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两个人物家喻户晓,但这个凄美的悲剧并非莎翁原创。通过药物“假死”以逃婚的故事原型至少可上溯至公元前5世纪色诺芬(Xenophon,前430—前354)的寓言故事《以弗所传奇》(Ephesiaca)。15世纪意大利诗人马萨丘·萨勒尼塔诺(Masuccio Salernitano,1410—1475)在他的《故事集》(Novellino)中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直到1562年英国诗人亚瑟·布鲁克(Authur Brooke)的叙事长诗《罗密乌斯与朱丽叶的悲剧历史》(The History of Romeus and Juliet),被认为是莎氏1594年创作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的直接来源。此外,在同年问世的一部名为《维罗纳的故事》(Storia di Verona)中,意大利作家科尔泰(Girolamodella Corte)考证了这段爱情绝恋发生在1303年维罗纳城的一个真实事件。尽管这只是一家之言,但至少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早在莎剧之前就已形成大致的框架。
由此可见,文字语言本身就具备了跨界的灵活性。随后,《罗密欧与朱丽叶》于1785年首次在威尼斯被改编成芭蕾舞剧。1867年,该剧又在法国被改编成歌剧。所以,在20世纪该剧被无数次改编成影视作品就不足为奇了。其中,1968年意大利导演杰夫瑞利(Franco Zeffirelli)的版本被认为是最为经典的一部电影。其改编已最大限度地忠实了原著,然而表现形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审美感官上的差异,以“化妆舞会”情节为例。
第一,在视觉上,不同于文字的抽象性描述和舞台的假定性情境,电影还原出真实而完整的中世纪舞厅,观众的眼睛跟随摄像机亲临舞会现场并漫步其中,既不像读剧本那样全凭读者的想象,也不像看演出那样始终保持着舞台与观众席之间的界限,画面瞬间就将观众带入了故事所发生的环境,削弱了受众与情节的间离感。
第二,在空间上,电影所呈现出的空间丰富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传统的空间转换必须按照线性顺序依次进行,而在影片中,一边是舞会现场的轻歌曼舞,一边是大厅侧室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谈情说爱,两个并存的空间通过镜头剪辑而平行发展、相互交织,形成呼应关系。此外,拍摄过程中,在空间内部的场面调度上,镜头可以任意穿越各个空间或一个空间的各种位置与角度。于是,一个看似立体而真实的空间就在摄影机与观众的眼睛的合谋下诞生在一个仅是平面空间的银幕上。
第三,在节奏上,电影更加收放自如、张弛有度。例如,在表现众人群舞的场景时,镜头或是跟随人物快速运动,或是用小景别捕捉生动的瞬间,用短镜头、快剪切来表现画面的动感,用多种蒙太奇来变换影片的节奏,进而调动情绪。这是文字描述和舞台表演都是无法达到的效果。
第四,在人物塑造上,文字描述的不确定性使“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在舞台上,真人表演将人物形象明确化,于是产生了有“莎剧王子”之称的著名演员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所扮演的一系列经典的人物形象,但传统的舞台表演略显夸张。银幕上的表演则更加追求真切、自然、生活化。比如,舞会上朱丽叶接受罗密欧的表白时,眼神从好奇到犹豫,到慌张,再到萌动,最后是羞怯的变化,都在特写镜头下完整地呈现出来。此外,戏剧舞台上经常可见一个中年演员可以去演青年人,但在影像中这种现象则较为罕见,这同样也源于影像的仿真性。
第五,在听觉上,该电影的主题曲《青春是什么》甚至超越了电影成为一首名曲,“玫瑰绽放,转瞬凋零,正如青春,恰似少女”——哀而不伤的歌词,悠扬又惆怅的旋律,在影片里贯穿始终。通过声画对位的手法起到升华主题、渲染气氛、抒发情感的作用。由此,对青春的羡慕、留恋以及对爱情悲剧的惋惜之情无须过多语言的表达,一首歌曲足矣。
视听化,是电影、电视与新媒体艺术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和媒介特征,它深深依赖于工业科技的进步,没有摄影、电影、录音等技术的发明,就没有影视艺术。因此,科技和媒介似乎划分了传统文学、艺术与视听综合艺术的界限。但事实上,科技对传统文学也同样具有影响力,文学、戏剧在与影视艺术的并行中也逐渐吸取其优势,比如“蒙太奇式小说”和舞台用光区划分不同空间的舞美设计等都是对影像“语言”的借鉴,或者说是艺术与科技的联姻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审美体验。
(二)思维观念的“破界”
媒介变革往往不只带来新的艺术形态,更能在民众心中催生新的思维观念。如果说印刷术的出现最终结果是促成了理性思维,那么其后的媒介变革最终将从各个方面瓦解理性思维,因为影视作为以刺激感官、调控情绪为主的艺术形式,天生就具备“反理性”的特点。其实,媒介只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任何世界观的颠覆首先都来自人们内部固有思维与现实生活的矛盾。1996年澳大利亚导演巴兹.卢汉姆(Baz Luhrmann)的影片《威廉莎士比亚的罗密欧+朱丽叶》,利用“拆解”“戏仿”“拼贴”等方式对文化大师和权威进行了反叛与消解,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精神。
首先,在宗教上,原著中劳伦斯神父这一形象凝结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对“人”的最深沉的发现,是他帮助这对俗世恋人实现他们的人性之爱,体现了人文主义情怀。然而,在卢汉姆的电影中,被丑化、矮化的神父只剩下为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搭桥的功能,而抛弃了他原有的神圣价值。这种去中心、去本质、去意义、去联系而只保留元素本身的“拆解”之法,其目的是对传统思维中任何有意义的人与事的否定。
其次,在爱情上,在原著中赋予这个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以纯洁、浪漫、悲壮之美。而在卢汉姆的电影中,情节、台词都没有变动,但演员的表演极尽夸张、戏谑,演成一场滑稽可笑的闹剧。这种刻意模仿原文本,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内涵、效果的“戏仿”,其目的是对权威建构起来的传统思维的嘲弄和贬斥。
此外,在影像上,卢汉姆还运用了“拼贴”手法,主要表现在时代置换与各种风格的杂糅上。如中世纪的故事配上20世纪的背景,幕前致辞以电视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枪战片、黑帮片甚至广告、MV等元素的融入,形成古老与现代、爱情与暴力、电影与电视的全方面混搭。各种元素在反逻辑的语境下任意组合,供人们在消费中娱乐。无独有偶,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布莱纳(Kenneth Branagh)的《亨利五世》、钟格(Jil Junger)的《我恨你的十件事》等改编自莎剧的电影都存在着颠覆经典的现象。这说明,后现代主义在文学艺术上已经成为一股潮流。
而电视媒体营造的更加大众化、娱乐化的文化氛围以及互联网等新媒体提供的更加个性化、更加开放的环境和低成本的运营方式,为后现代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尤其是普通民众能够直接参与创作与表达,使得思维观念的变化也从叙事内涵向制作策略扩散。例如,加拿大的一档名为《Just for Laughs Gag’s》的恶作剧真人秀节目中,有一期便是对《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阳台会”桥段的戏仿。当男主人公手举一束红玫瑰爬上梯子与阳台上的女主人公约会表白时,突然被女主人公的家人用拖把推倒并掉进楼下的垃圾车里。
与此同时,事先被隐藏好的镜头暗中记录下那些毫不知情的路人们看到男主人公被推下来时的各种反应,最后这些路人们或是惊愕恐惧或是幸灾乐祸的表情、动作以及叫喊声等被拼凑在一起,形成一段纪实且富有情趣的片段集锦。从叙事内涵上看,这段视频是对传统爱情观的极大讽刺,将这段纯洁的爱情视为与垃圾为伍,且这一过程是在大众围观的场合下公然进行的;从制作策略上看,它充分体现了节目创作对大众参与的依赖,这个完整的表演是由演员和路人一起来完成的,二者缺一不可,“路人”既是观赏者同时也是表演者。因此,“大众参与性”是从传统艺术到传媒传媒艺术的一个鲜明的特征。
而新媒体构成的文化产品的“超市”景观,在平台容量扩充的同时也伴随着准入门槛的降低,赋予普罗大众之前从未有过的创作权利,这种权利不仅包括自制原创新内容,也包括对已有内容的重新整合与编排。比如,上述提到的那期加拿大电视节目被上传至搜狐网、PPTV、PPS等多家网络媒体后被重新命名为《史上最戏剧整蛊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如此直白而富有诱惑力的命名方式也反映着视频上传者对媒体环境、用户心理的领悟,这同样也是大众参与性的体现。而在新媒体上颇为流行的“弹幕”观影方式,正是基于影片本身与诸多个性化的、甚至怪异的大众点评融为一体,并共同完成一个节目的创作、传播与接受的整个过程。
如此解构或许显得过于轻浮,但其体现出来的后现代主义支持者对自身前途、命运的积极探索,以及对突破制度框架而实现自由发展的创作热情与渴望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它也将继续构成未来文化格局的重要板块之一。
(三)叙事功能的“破界”
记者从中物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获悉,该所将与中广核研究院合作,利用中国绵阳研究堆(CMRR)开展事故容错燃料(ATF)芯块和包壳的辐照考核与评价。这标志着中广核研究院牵头的ATF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已在前期材料研制的基础上迈入辐照考核的重要阶段。
1999年约翰·麦登(John Madden)执导的电影《莎翁情史》,首次让莎士比亚本人成为银幕上的主角,并与公爵小姐薇奥拉“反串”演出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台上台下、戏内戏外的两人双双坠入爱河。尽管“反串版”已经极具笑点,但真正令观众期待的绝不是这个经典的故事,而是其诗人、剧作家的浪漫“情史”。于是,从一个完整、闭合的爱情故事到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原著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媒介与信息的分析中,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概念。“互文性”的本质就是不同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尽管这一概念的提出相对较晚(20世纪60年代才由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符号学》一书中正式提出),但它一直贯穿着古往今来的文艺创作,只不过是后现代主义将这一特性迅速扩展了而已。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的观点是,“后现代主义认为形象之间相互关联并且能彼此跨越。它转移了符号学分析家单一、仔细凝视的视线,认为可以用多元、破碎且时时中断的注视取代”②。于是,新旧文本之间的联系变得碎片化、元素化,从而使得在组建新文本的过程中,支解旧文本完整的叙事功能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
《罗密欧与朱丽叶》在《莎翁情史》里只是一个“戏中戏”。这种叙事手法早在《哈姆雷特》的“捕鼠器”情节中就有。然而,传统的“戏中戏”结构,无论大故事还是小故事都承担着独立完整的叙事功能,而在《莎翁情史》里,作为片段出现只是一个悲剧的符号,其功能是让台上的一对恋人与台下的一对情侣形成对照关系并起到影射的作用。所以,在对后现代主义互文性的理解中,新文本不是照搬、照抄旧文本,而是将旧文本拆解并符号化,继而融入新文本的叙事里。此举虽不乏创新之意,但同时也在利用并消费着大师的作品,某种意义上更消费着所谓大师的情欲和身体。
如果说《莎翁情史》至少还保留了一些《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节,那么盖瑞·温尼克(Gary Winick)指导的电影《写给朱丽叶的信》(Letters to Juliet)却让“朱丽叶”仅仅以一个人名(或广告)的形式出现,影片内容与莎翁原著毫无关系。在此,“朱丽叶”的功能同样被符号化,作为“真爱”的象征和追求“真爱”的信念,以此寄托着生活在当下社会中的人们对永恒爱情的渴望与期盼。
如今,“罗密欧与朱丽叶”已经不仅仅是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与爱情象征,也是穿梭于各种形态文本,尤其是商业广告文本的产品创意的灵感。例如,网上一条名为《罗密欧与朱丽叶新传》的“杜蕾斯”产品广告,同样截取原著中“阳台会”这一经典片段并用性符号将其与性趣用品相关联,以达到吸引受众眼球的目的。当元素化、符号化的方式进一步运用于电影营销时,便能形成所谓的“高概念”(high concept)。这种源于好莱坞的营销策略,不惜以最为简明甚至粗暴的方式将影片卖点放大到极致,达到快速引人注目的效果。
比如2005年上映的中国电影《情人结》,这部曾在中国创下海报数量之最的电影,在其诸版宣传海报中反复向大众灌输的是“现代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名导霍建起最新浪漫唯美力作”“人气明星赵薇、陆毅倾情演绎”等语句,“罗密欧与朱丽叶”与“霍建起”“赵薇”“陆毅”以及“浪漫唯美”等符号一同成为突出影片类型、风格、明星等卖点的“高概念”。虽然“高概念”这一术语的使用目前仅限于电影营销范畴,但其背后蕴含的理念、思路与模式可被任意一种产品的营销套用,且随着营销活动日益在容纳海量信息的新媒体平台上不断深入,这种方式也必将被普遍使用。
三、文学在媒介变革语境下的传播与创新
广播、影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的发明,促成大众文化的兴盛,文学也经历了从作家“作品”向文化“产品”的演变,以受众为争夺战场,以媒介为制胜武器,通过对文化市场的占领,实现其价值定位。显然,面对全球化的时代,固步自封、自娱自乐已是不合时宜。传统文学,尤其是经典文学,如何在媒介变革、文化转型的语境下依然保持其鲜活性与影响力,这既关乎到文学生命的延续,也关乎到传统文化与民族记忆的保存之大事。
(一)文学在媒介变革语境中的传播
媒介变革催生了后现代主义,所以媒介变革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的语境。后现代主义要求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彼此打破疆界而相互融合,那么文学在这种语境下的传播也主要呈现出融合的姿态,具体表现为跨学科、跨媒介、跨文化的传播特点。
1.跨学科
古希腊时期,哲学作为“万学之母”网罗人类的全部认知,系统之间的边界模糊。近代理性主义为了追求更加细致、精准的研究,对各类知识进行了严格界定,从而形成相互独立、体系完整的学科门类。然而,20世纪后半叶,学科边界逐渐成为限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桎梏,使得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成为大趋势。于是,从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来阐释文学作品,以文学为中心向多个领域发散,成为文学解读的一大亮点和新的方法。
比如,在政治学领域,《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莎剧在近代中国的上演以及在高校的传播被看作是新兴的民主思想对封建的宗族礼教的反抗,而19世纪的英国向海外输出莎剧也是其文化殖民的一种策略。在心理学领域,德斯考尔(Driscoll)通过人物心理活动分析,提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的概念诞生,用于描述面对外界压力时逆反心理所呈现的状态。而在历史学领域,新历史主义要求让历史意识参与文学批评,从而阐释文学文本的历史意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莎剧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被用于探索人文主义在特定时代下发展状况的研究样本。跨学科传播赋予文学更加丰富的内涵和价值,使文学真正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人学”。
2.跨媒介
从语言发展的历史上看,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因媒介的承载而得以流传,也都在一次次的传播中更加生动鲜活。19世纪末以来的媒介变革,大大扩充了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范畴,也让文本的意义发生变化。在此基础上,一个融合多种媒介方式的“大文本”的概念。而这一过程伴随着一个跨越近百年的关于“电影是语言”的论证。
正如肢体语言、画面语言归纳出的程式和技法已被人们习以为常地称为“语言”一样,电影在诞生后的半个世纪之内形成的表现技法也被早期的电影理论家总结出相应的规律,并冠以“语言”来称呼,如1955年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尔丹(Marcel Martin)写下的《电影语言》等。但是,20世纪索绪尔等人对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使得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电影作为一门语言而饱受质疑。直到20世纪末数字技术的发明才使电影也能像文字那样拥有以“词典”为标志的系统化单元库,并作为一种语言逐步走向成熟。同时,数字技术也能记录有史以来存在过的一切传递信息的符号,一个媒介融合的时代到来了。
从传统文本的记录功能来理解,“有数万年之久的有声语言被当成‘心’的声音(即古之所云:言为心声);有数千年之久的文字被当成有声语言的无声记录;有一百年之久的电影是对声音(包括语言)和形象(包括文字)的记录;有数十年之久的‘数字’能记录上述一切”③。因此,在数字技术强大的记录能力下,文本的构成从仅有的文字组合扩充到融合着文字、语音、音乐、音效、图像、视频等多种元素,从而形成广义的“大文本”的概念,各种形态的“语言”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一个表达任务。影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甚至手机应用等,都综合运用了各种表达元素,都是“大文本”概念下的具体体现。
由此看来,在媒介变革语境下,语言即表达,那么一切表达也都少不了文学语言的身影。如文学中的抒情、叙事手法同样可以运用到影视剧故事的讲述中,文学中的论证、结构手法也同样可以运用到专题片、新闻片的结构中,这也正是传媒艺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与发扬。正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从戏剧文本到影视作品,再到网络视频、广告创意等,其来自于传统文学的基本元素都能运用于不同的媒介表达并形成多种多样的传媒艺术形式。
因此,“大文本”概念的意义在于构建了传统艺术与传媒艺术之间的联系。传媒艺术并非具体指向某一种艺术门类,而是“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借助工业革命之后的科技进步、大众传媒发展和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在艺术创作、传播与接受中具有鲜明的科技性、媒介性和大众参与性的艺术形式与品类”④的总称,它几乎涵盖了包括文学、音乐、美术、戏剧、舞台在内的人类全部的艺术表达,吸纳了历史上所有的艺术成就,并将这包罗万象的庞大族群与影像、数字等新型记录介质相结合,放置在分别具有点对点、点对面、点面互动等不同传播特征的大众媒介的舞台之上。所以,“跨媒介”的传播方式正是传媒艺术生命力之所在,“大文本”因媒介而形成的丰富性也正体现了传媒艺术对传统艺术的继承、改造与整合。
当下“跨媒介”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跨屏”,即同一文本在电视、PC电脑、平板电脑、手机等不同的新媒体屏幕上实现的自由转换。无论是加拿大电视节目《Just for Laughs Gag’s》,还是网络视频《史上最戏剧整蛊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其碎片化叙事、小景别拍摄(以确保在小屏幕上画面信息清晰可见)等特点,正是切合了因“跨屏”传播而至的伴随性、零散性观赏方式的需要。媒介融合使语言更加多元、灵活,而文学也可以以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在跨媒介传播中延续着属于自己的基因。
3.跨文化
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但这一概念并不新鲜。纵观历史,全球化共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14世纪以麦哲伦环游地球为标志的地理全球化,到19世纪以世界市场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再到20世纪由影视、网络等媒介技术形成的文化全球化。然而,文化很难像经济那样呈现出全球“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支持“美国化”的学者曾预言各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会导致文化的同质化。但事实证明,相互联系反而使文化的差异性越来越得到彰显,同时也越来越得到尊重。因而,跨文化传播是当今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方式。
跨文化传播既是对异国文化的包容与尊重,也是对异质元素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与接纳。比如日本版的动画片《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人物造型上明显地表现出日本动漫的风格。而中国电影《情人结》则是一个套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原型而完全“中国化”的故事,甚至结局也采用了中国式的“大团圆”。此外,中国戏曲改编,如京剧、越剧、豫剧、二人转和花灯戏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进一步使东方与西方在跨文化传播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引进与改造、交融与丰富。
(二)文学在媒介变革语境下的创新
事实上,《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每一次改编,本质上都是一次创新,而始终伴随这一过程的,则是经典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的对话。前者内涵深刻、表现手法精湛,彰显精英阶层的尊贵;后者迎合时代、贴近世俗,体现普罗大众的情趣。看似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二者之间却始终密切关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具体到某一个文化元素,我们已无法明确地将其归为经典文化或流行文化。即使是同一个文化元素,在不同时代也可以被赋予不同的意义。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在文艺复兴时期,以舞台为媒介的艺术就是流行文化,人文主义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尚和流行的观念,再加上莎剧蕴含着丰富的人情世故,因此其深受大众喜爱。然而,伴随着英国的崛起、殖民文化的输出,莎剧研究被誉为“学术里的奥林匹亚”。于是,莎剧从流行文化变为经典文化,成为高雅艺术的典范与大学课堂上的教材。进入20世纪,影视媒介让莎剧重新回归流行文化,并以新的形式被普罗大众再度认知,甚至在中国上个世纪的80年代曾出现过“莎士比亚热”的现象。
流行文化不是凭空捏造,其脱胎于经典文化,而经典文化又是流行文化的沉淀。比如在中世纪后期及文艺复兴时期,作为流行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其很多故事原型来自于宗教、历史故事等经典文化,经过历史的筛选和读者、观众的考验,留存下来的以莎剧为代表的戏剧最终成为了经典文化。再比如,17、18世纪时,气势蓬勃、抑扬顿挫的戏剧是当时的经典文化,相比之下,借鉴了戏剧的矛盾、冲突与人物的刻画手法但情节更为琐碎、情感更为起伏的小说则属流行文化,然而经过百年光阴的提炼,那些优秀的小说在19、20世纪也成为了经典文化。由此可见,二者之间是彼此承袭、相互成就的关系。流行文化是经典文化的变异,它保留着部分经典文化的元素,但又融合了时代的情愫。反之,流行文化也在自我扬弃中铸就精品,从而丰富了经典文化的原有容量。
就整个文化系统来看,文学因其悠久的历史、完善的体系而获得作为经典文化的霸权。但是,媒介的变革需要文化的创新,而创新之“新”则需要吸纳从内容到形式的某些流行元素。正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从诗剧、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中国戏曲到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动画、网络视频,再到以此为原型创生出来的新故事,不断地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才有了一条绵延四百年,且辗转于书本、舞台、银幕、电视、电脑屏幕等多个传播载体的创作链的形成,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尤其是以家族矛盾作为爱情阻力的故事原型,在这四百年间被反复用于各种叙事中。无论故事的形式如何改变,“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创意的起点,其核心情节或是精神内涵始终如一。可见,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代表的经典文学可以为后世提供并延展出新的创作。
创新的另一个方面,则来自于对媒介的认识和理解。“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改编史完整地呈现了一个传统艺术向传媒艺术逐步渗透、演进的过程。文学剧本重在台词描写,电影重在视听化的具象表达,电视广告重在噱头的营造,网络视频重在碎片化叙事、狂欢式解构与大众参与,这一系列变化都深刻地立足于不同媒介的特殊性之上,同时也让受众从被动观看、欣赏作品变为主动参与、体验创作。如果说传统艺术的创作忠实的是生活逻辑并附有作者个人签名,那么传媒艺术的创作忠实的则是媒介特征并通常是集体创作。惟其如此,艺术的创新才能在媒介变革的语境下获得延续和新生。
既然媒介变革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是后现代主义的语境,而“后现代文化,特别是当今的大众文化则与市场体系和商品形式具有同谋关系,它们把艺术包装成商品(如后现代的怀旧电影),作为纯粹审美消费的实物提供给观众。并且,后现代通过合作的方式使高雅艺术与商业文化之间的界限难以厘清”⑤。所以,媒介变革的语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商业运作的语境。那么,传媒艺术也必然旨在将文化产业化,于是创作链本身就是产业链,故事原型就是这条产业链中的原始智力成果。正如很多畅销小说被争先改编成影视剧或是动漫作品,甚至还会以小说为原型创造出网络游戏或是桌游、手游产品等一样,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不会过时,随着媒介的发展其可延展性就越能得到体现。
毕竟,在追求文化多元的今天,流行文化的目的是要与经典文化共分一杯羹,绝不是要取代经典文化,传媒艺术也不会将传统艺术“赶尽杀绝”。喜爱阅读书籍的群体依然存在,甚至可以阅读“电纸书”,只不过人们有了更多的个性化的选择。如果文学作品本身拥有足够的影响力,那么便会因其具备“高概念”的营销基础而被视为强IP(IP即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意为“知识产权”,强IP指有影响力的原创作品)而在文化市场中获得更多创新开发的机会,其衍生产品也会更加丰富,从而使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和经济效益上获得双赢。
当然,一个更需要警惕的状态,就是市场对现有强IP的无序争夺与无节制地利用,使得原创作品的发展空间被鲸吞蚕食,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本应多元的文化形态趋向单一化、同质化,直至僵化。
四、结语
从莎翁的经典名剧,到影像、动漫,再到作为经典元素或故事原型融入新的叙事,传统文学在媒介变革语境下的疆界被逐步打破。然而,传统文学本身并未消亡,它将自己的基因与其他艺术门类、各种媒介形式相融合,跨越时空,衍生出更多新鲜的艺术形式,共同营造更加多元、开放且更具亲和力的文化环境。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文学为代表的传统艺术与当今的传媒艺术之间并非孤立对立,而是相承相融、优势互补的关系。前者的历史积淀,为后者的成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后者的活力与朝气带领着前者走向新的天地。所以,在当下传媒艺术的创作中,仅仅考虑到媒介与科技的特殊性而不充分汲取传统艺术的营养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只会让传媒艺术陷入无源之水的境地。而面对业已全球化的媒介变革语境,文学等传统艺术更不应固守所谓高雅的闺阁或霸权式的“疆界”,这样的结果只会让传统艺术走向偏执与狭隘,只有积极参与到媒介环境中并适当调整,实现新形式、新功能的转化,才会产生新的价值。
注释:
①④ 胡智锋、刘俊:《何谓传媒艺术》,《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
② 转引自[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吴靖、黄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③ 王志敏:《电影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
⑤ 胡亚敏:《文化转型》译者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作者吴辉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汐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电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