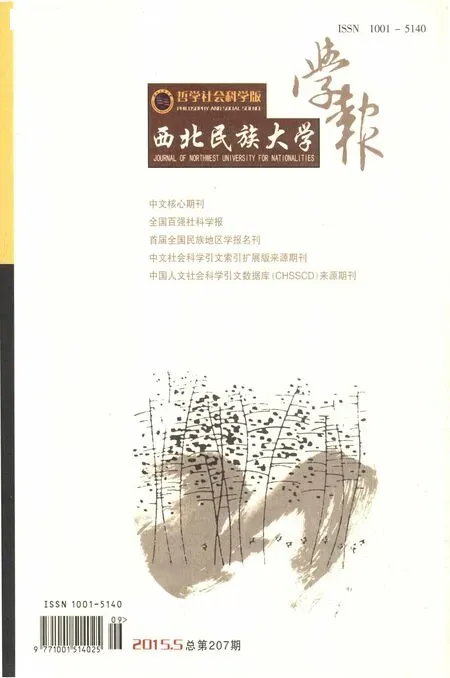元代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
张虽旺,王启龙
(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 西安710061)
藏传佛教史所称的“后弘期”,王辅仁等称其为“西藏佛教”,“西藏佛教与吐蕃时期的佛教在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是“西藏化了的佛教,或者称之为佛教在西藏的地方形式”[1]。藏传佛教后弘期各教派次第形成。
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从11世纪中叶开始,完成于15世纪初[2]。至元代,藏传佛教除格鲁派以外的其他教派基本上已经次第形成。形成于卫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各教派主要致力于在卫藏地区发展,向外传播始于12世纪中后期。①周生文、蒲文成《噶举派在青海的传播与现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3月2日;蒲文成《元代的藏传佛教宁玛派》,《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蒲文成《藏传佛教诸派在青海的早期传播及其改宗》,《西藏研究》1990年第2期;崔红芬《藏传佛教各宗派对西夏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孙昌盛《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及其地位和作用》,《西藏研究》2006年第1期。虽然藏传佛教于12世纪中叶以后在西夏境内有所影响,②王尧《西夏黑水桥碑考补》,《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3月2日;崔红芬《藏传佛教各宗派对西夏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孙昌盛《试论在西夏的藏传佛教僧人及其地位和作用》,《西藏研究》2006年第1期。以及噶举派在康区建寺传播,③周生文、蒲文成《噶举派在青海的传播与现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蒲文成著《青海佛教史》,青海人民出版社,第48-66页;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等译《安多政教史》,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陈庆英蒲文成《西纳格西西纳喇嘛和塔尔寺西纳活佛》,《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但对于河湟地区来说,藏传佛教没有任何传播和影响的迹象[3]。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始于元代。据史籍记载,藏传佛教噶举派、萨迦派和噶当派先后在河湟地区传播。虽然藏传佛教在元代被定为国教,并且在蒙古王室和贵族中间也有不少人信仰藏传佛教,但是在蒙古族下层民众和汉人中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4]。即使在河湟地区,藏传佛教在元代也只是初步传播,其影响远没有明末清初格鲁派在河湟地区的影响那么广泛。关于这一点,成书于公元1865年的《安多政教史》中绝大部分内容为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发展状况的史籍记载即是最好的明证。《安多政教史》一书,关于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的内容不仅简单,而且在河湟地区传播佛教的高僧数量也是很有限的。
一、萨迦派在河湟地区的传播
《安多政教史》载:
从前,有一斯纳·多杰坚赞者,曾消灭过多康绷波岗的一直凶悍的军队,是一位英雄[5]。
绷波岗又译作包波岗、包柏尔岗,是康区六岗[6]之一,地在今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斯纳(又译西纳)族是唃厮啰政权时期活动在河湟地区的吐蕃部落的一支。《安多政教史》又载:
他(西纳·多吉坚赞)的儿子斯纳兰巴和斯纳格西兄弟二人前往卫藏。哥哥在彼处建立基业,后又发展为宗吉坚赞桑波和多杰仁钦官人等支系。弟弟到了萨迦,读了许多经典,学习显密教法,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他于结业后闭关修习期间,见到文殊菩萨及度母圣容,度母还授记“汝去北方蒙古地区,弘扬佛法”,于是他从后藏觉莫隆、拉萨和贡塘三地各带领一位最好学识的格西作为随从,前往北方。觐见正在相多地方居住的成吉思大汗。
关于西纳家族迁徙康区的时间,研究认为“西纳多吉坚赞由青海到康区大概也在角厮罗政权走向衰落之时”[7],即12世纪初。笔者以为西纳家族迁徙康区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200年前后。公元1200年前后,由于气候寒冷、干旱,①竺可祯著《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邹逸麟、张修桂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5页。河湟地区的人民大量外迁,西纳家族也应该在此时迁往康区。西纳格西又由康区前往萨迦学习萨迦派教法。如此解释才能解决西纳格西觐见成吉思汗[8]的时间问题,虽然西纳格西觐见成吉思汗之说没有依据。如果说西纳多吉坚赞于公元1100年后迁往康区,那么西纳格西无论如何也无法觐见成吉思汗。史料中说西纳格西是在成吉思汗驻军上都(shang to,汉译本《安多政教史》译为相多)时拜见成吉思汗的。②陈庆英、蒲文成《西纳格西西纳喇嘛和塔尔寺西纳活佛》,《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等译《安多政教史》,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页。上都即开平(金莲川,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滦河的北面),始建于蒙古宪宗六年(公元1256年),刘秉忠(虚照禅师的弟子,法号子聪,公元1242年禅宗临济宗僧海云荐其入忽必烈幕府。至元元年即公元1264年,忽必烈命其还俗,复刘氏姓,赐名秉忠③[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57《刘秉忠传》第12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687-3694页;赵建坤、陈红《元代名臣刘秉忠》,《档案天地》2005年第6期;魏琛《刘秉忠其人其事》,《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贾洲杰《元上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3期;杨曾文《元初禅僧子聪刘秉忠的历史贡献》,《佛教文化》2006年第1期。)受忽必烈之命选址金莲川建开平城。④[明]宋濂等撰《元史》卷4《世祖纪》第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0页;王大方《元上都遗址申遗的新成果——<创建开平府祭告济渎记>碑文被发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5期;周良宵、顾菊英著《元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中统五年(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始改名上都。成吉思汗时开平城尚不存在,当然上都也不存在。公元1211年~1216年是蒙金战争的第一阶段。公元1211年秋,金国的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抚州(今河北张北)三州之地尽失。成吉思汗领兵攻打金国时到过金的抚州,没有到过开平城(当时尚不存在)西南部的桓州,⑤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瑞典]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5-71页。因此,西纳格西在上都拜见成吉思汗之说只能是附会之说,“大约是公元1211年~1215年成吉思汗攻取金朝黄河以北地区时的事”[9]之说法也不可取。即使在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率军攻打河湟地区时,成吉思汗也没有亲自到西宁。⑥芈一之著《青海蒙古族历史简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芈一之《散论章吉驸马及其他》,《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蒙古军并没有在今青海境内的河湟地区发动战争,西纳格西拜见成吉思汗之说没有依据。《安多政教史》还载,有西纳堪布喜饶意希贝桑布被委任为宣政院院使和西纳贝本被封为宗喀万户。①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等译《安多政教史》,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61页;陈庆英、蒲文成《西纳格西西纳喇嘛和塔尔寺西纳活佛》,《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据张云考证,历任宣政院院使并无西纳堪布喜饶意希贝桑布[10]。宗喀万户在《元史·地理志》中也不能找到相应的设置,因此宗喀万户的设置与否只能存疑。史籍明确记载西纳喇嘛却帕坚赞于明朝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被封为国师,西纳寺建于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②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等译《安多政教史》,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1、162页;陈庆英、蒲文成《西纳格西西纳喇嘛和塔尔寺西纳活佛》,《青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由此可见,西纳家族重又在湟水流域定居应该是在元代,在忽必烈继承汗位以后。由于西纳家族的喜饶意希贝桑波因服侍八思巴受比丘戒、护送八思巴到大都之功,由忽必烈和八思巴赐给文书,将湟水流域一带的土地赐给他。③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等译《安多政教史》,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页;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77页。而这与蒙古弘吉剌部赤窟系获得湟水流域封地④芈一之《散论章吉驸马及其他》,《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太宗七年(公元1235年)只是命阔端征秦、巩。太宗八年的分封只是说封阔端、按陈等于东平府(府治在今山东东平县)户内拨赐有差,也被耶律楚材加以否决,只允许诸王设置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租颁之,也未言明封阔端河西之地。见[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太宗》,第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4、35页。胡小鹏在《元代西北历史与民族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一书中只是猜测可能还分封阔端于西夏故地。相矛盾。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西宁州又为弘吉剌部赤窟系章吉驸马的分地,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章吉驸马被封为宁濮郡王镇守西宁。⑤[明]宋濂等撰《元史》卷60《地理志三》第5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52页;[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4《世祖十一》第2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96页;芈一之《散论章吉驸马及其他》,《青海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由于西纳格西学经于萨迦派,萨迦派教法在湟水流域的传播始于其后代定居河湟地区以后。但是,元代萨迦派在湟水流域传播的具体情况,《安多政教史》也是语焉不详。
萨迦派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始于八思巴(公元1235~1280年),但据史籍记载看,八思巴并没有在今天青海境内的河湟地区有过传教活动。
研究表明,八思巴与忽必烈会面有两次,即公元1251年和公元1253年的两次会面。⑥王启龙《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王启龙著《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公元1251年的会面可以说是被迫的;公元1253年的会面则是八思巴主动的,其目的是为萨迦派寻找政治上的靠山[11]。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说:
八思巴在政治的混乱迷宫中按他自己的方式控制局面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最初他的角色是一个被动者。是忽必烈,他在若干可能性之间的踌躇之后,选择八思巴作为自己在藏族问题上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八思巴作为一位政治人物,是大皇帝的一部作品,在一个不情愿的情况下,还是在最阴沉的西藏,大皇帝通过军事武力两次征召八思巴。八思巴的最后一张王牌是和皇帝家族成员的亲近,而且上述所有成员就包括皇后察必和皇储真金。自然,皇帝的宗教政策带有在原则上对佛教的偏爱,而实际上西藏人这张招牌之所以获得皇帝的特别青睐,在相当的程度上得益于萨迦堪布的精心培植。但是,我们应该放弃有关八思巴在政治事务中作为一名有影响的参事的概念,对此,不存在任何证据。甚至居住在汉地时,他在很长的工作时间里不在首都,而住在临洮和其他地方,他通过个人关系对皇帝影响的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最后,对于西藏人把八思巴的形象,变成为伟大的宗教领袖和作为忽必烈在佛教事务上有权威的顾问的这类传说,应该稍微降一些调子[12]。
对于忽必烈第一次召见八思巴,《佛祖历代通载》载:
初,世祖居潜邸,闻西国有绰理哲瓦道德,愿见之,遂往西凉遣使,请于廓丹大王。王谓使者曰:“师已入灭,有侄发思巴,此云圣寿,年方十六,深通佛法,请以应命。”至都旬日,即乞西还。上召问曰:“师之佛法,比叔如何?”曰叔之佛法,如大海水;吾所得者,以指点水于舌而已!”问答允称。上喜曰:“师虽年少,种性不凡,愿为朕留,当求戒法。”寻礼为师。①[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见[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史传部一》卷2036,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印行第725页(c)、726页(a)。
《汉藏史籍》载:
当(萨迦班智达)伯侄到达凉州幻化寺后,蒙古薛禅汗传来令旨说:“有名萨迦喇嘛之殊胜者抵达凉州,应作我之上师。”法主因年老未去,喇嘛八思巴与凉州的王子蒙哥都一起,前往汉地,与驻在汉地六盘山的薛禅汗忽必烈相见。(忽必烈)大喜,赠给凉州蒙古马军一百,留下萨迦人(八思巴),结为施主与福田。(八思巴)担任刺嘛以及在凉州为法主圆寂举行超荐法事等,在汉地和蒙古住了多年[13]。
《红史》载:
众生怙主八思巴罗追坚赞,生于阴木羊年,十岁时作为伯父的随从一起到凉州。后来,当忽必烈汗驻六盘山时,凉州大王蒙哥都与上师一起前去会见,大喜,王子忽必烈赠给凉州大王蒙古马军一百,留下了萨迦人,传授灌顶,结为施主与福田[14]。
据研究考证以上三则史料记载的都是公元1251年忽必烈召见八思巴的情况[15],而此时八思巴尚未受比丘戒,也未留在忽必烈身边[16]。公元1252年,八思巴准备返回萨迦从萨班弟子伍由巴·索南僧格受比丘戒,当行至多甘思时,听说了伍由巴大师去世的消息。而此时蒙哥汗括户以后将吐蕃按教派势力分封给诸王②五世达赖喇嘛著,刘立千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71页;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57页;陈庆英、高淑芬著《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80页。的做法严重动摇了自阔端时形成的萨迦派的特殊地位。③王启龙《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57页;王启龙著《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陈庆英、高淑芬著《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80页。这就迫使八思巴不得不重新寻找政治靠山,八思巴也就于公元1253年主动投奔忽必烈。与忽必烈于忒剌(今四川松潘④张云认为是地约在今甘肃迭部之达拉,见张云著《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页注释(2)。)之地相见。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忽必烈是八思巴政治上的靠山,而八思巴是忽必烈一家宗教上的导师。⑤[美]莫里斯·罗沙比著赵清治译《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40页;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75页;王启龙《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王启龙著《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期间,公元1255年(岁乙卯)忽必烈驻桓、抚间[17]。关于八思巴受戒的地点有两种说法:一是《汉藏史籍》说是公元1255年5月,八思巴到河州(今甘肃临夏)由涅塘巴·扎巴僧格、恰巴·却吉僧格、藏那巴·尊追僧格、楚·宣穷僧格等人任堪布,由羌塘巴·觉敦索南坚赞、乃巴堪布洛追扎等人任阿闍黎,由雅隆巴·喇嘛绛曲坚赞担任密教师,与具信比丘喇嘛叶巴、堪布喜绕意希、仁波且涅官等严守戒律之21名比丘一起在僧伽大众之中接受了比丘戒律;《萨迦世系史》只说了八思巴于公元1255年受戒,并未说明受戒的地点。⑥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籍》,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等译《萨迦世系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131页;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63页;王启龙《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另《雅龙觉卧佛教史》说是在汉蒙交界的脱剌[18](又译忒剌,今四川松潘)之地。
关于忽必烈第一次接受八思巴灌顶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公元1253年。⑦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55页;王启龙著《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张云著《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265页;王启龙《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根据《萨迦世系史》记载的八思巴所说“我也未受比丘戒,故授给灌顶亦无效用,可先筹划我受比丘戒之事”[19]来看,忽必烈接受灌顶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255年5月八思巴接受比丘戒之后。《萨迦世系史》说是在八思巴受戒期间,忽必烈接受了萨迦派特有的喜金刚灌顶[20]。这与公元1255年(岁乙卯)忽必烈驻桓、抚间[21],而八思巴受戒的地点在河州,在时间、地点上都有冲突,因此忽必烈接受灌顶的时间和地点只能是在公元1255年5月八思巴接受比丘戒重返忽必烈驻地之后,并且是在公元1255年与噶玛拔希斗法[22]之后的事情。《萨迦世系史》在忽必烈接受灌顶的时间记载上也是前后抵牾。记载中先说八思巴牛年(公元1253年)到宫中,又说“当法王八思巴十九岁的阴水牛年(公元1253年)新年,薛禅汗请求传授灌顶,封其为帝师”[23]。不说受封为帝师的时间(公元1270年)之误,但就这次灌顶的时间记载来说,牛年(公元1253年)到宫中,阴水牛年(公元1253年)新年就进行了灌顶活动[24],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十二月,八思巴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国师,统释教。①[明]宋濂等撰《元史》卷3《世祖一》第1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8页;王启龙著《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5页;陈庆英著《元朝帝师八思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86页;王启龙著《八思巴评传》,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立总制院(即宣政院前身),而领以国师”[25]。八思巴于公元1264年返回萨迦,于公元1268年奉旨回京,八思巴在往来萨迦与京师时,于玉树地区新建或改宗为萨迦派的寺院有十余座[26],尕藏寺成为玉树称多地区的宗教中心[27]。然而直至公元1271年八思巴出居临洮②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王启龙著《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1页。以前,河湟地区没有留下八思巴传播藏传佛教的踪迹。八思巴在临洮住了三年,公元1274年在皇太子真金的护送下返回萨迦,③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第146页;王启龙著《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01、205、214页。直到公元1280年圆寂,再没有返回汉地。
八思巴旅居临洮的三年时间萨迦派教法得到了传播。《安多政教史》载:
在这座城市里,有达温巴奉怙主八思巴供施双方的命令修建的寺院,当年聚集着数千名僧伽[28]。
“直到清代,临洮还有8座属于萨迦派的寺院。《三世达赖喇嘛传》记载,三世达赖喇嘛到临洮时,还亲自修复过临洮大寺④陈庆英高淑芬著《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80页。此临洮大寺(香衮寺)在明代已经由宝塔寺所替代。本章第四节有论述。五世达赖喇嘛依然称其为“香更寺”,(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等译《一世——四世达赖喇嘛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清代方志记为宝塔寺。的八思巴塑像。洮河以南著名的卓尼禅定寺,也是八思巴派遣弟子喇嘛格西巴在卓尼土司家族的资助下兴建的。八思巴通过一系列的传法建寺活动,扩大了萨迦派在甘青藏族地区的势力。”[29]临洮成为元代甘青藏区的宗教文化中心[30]。然而,据《安多政教史》记载,从临洮大寺有许多汉族支寺[31]来看,汉传佛教仍是河湟地区居民的佛教信仰主流,如此大规模的寺院却与汉文史籍无证,令人怀疑。
二、噶举派在河湟地区的传播
噶玛拔希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二世活佛,是最早到蒙古宫廷的西藏高僧之一,也是忽必烈较早接触的藏传佛教高僧之一。《红史》载:
初,他(噶玛拔希)居于多康地方时,忽必烈带兵在绒波域色都地方会见了噶玛拔希,他使忽必烈发菩提心,见到诺桑和龙树等很多菩萨。忽必烈听到噶玛拔希当时的名声以及看到将来能成为大成就者的各种征兆,又有金字使者前来迎请噶玛拉希,当噶玛拔希为是否前往而犹豫不决之时,龙王和密主显现,说:“为利益众生,还是前去为妥。”因此决定前往[32]。
史籍记载含混,没有明确说明噶玛拔希与忽必烈相见的时间。研究认为噶玛拔希与忽必烈有两次相遇,即公元1253年和公元1255年[33]。根据公元1253年八思巴在忒拉(今四川松潘)之地再次与忽必烈相见,而噶玛拔希在绒域色堆(今四川嘉绒地区)与忽必烈相会,两人没有相遇的历史事实,又根据《萨迦世系史》八思巴与噶玛拔希两人斗法的记载来看[34],噶玛拔希确实是两次与忽必烈见面。第二次见面的地点是在桓、抚间(开平城于公元1256年修建,忽必烈也就没有开府开平),时间在八思巴于公元1255年5月在河州受比丘戒之后。可见,巴卧祖拉陈瓦在《贤者喜宴》中把两次相见的时间和地点混在了一起[35]。
对比噶玛拔希和八思巴二人,忽必烈虽然对噶玛拔希更感兴趣[36],然而噶玛拔希没有选择留在忽必烈身边,而是前往甘州、凉州一带建寺传教。①陈庆英、高淑芬著《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王启龙《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清华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周润年《十三世纪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高僧——噶玛拔希》,《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这里面的原因应该是噶玛噶举派在发展的早期就没有与地方势力相结合,不愿意受地方政权的影响,而这也是噶玛噶举派在宗教上的地位和影响逐渐超过其他教派的原因[37]。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元代后期皇帝邀请噶玛噶举派三世活佛饶迥多吉和四世活佛若贝多杰到朝廷做法事,以及帝师的作用已经受到影响,就可以发现噶玛噶举派的宗教地位和影响已经超过了萨迦派[38]。公元1256年受蒙哥汗的召请到蒙古地区传教,蒙哥封其为“国师”,还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39],直到公元1265返藏[40]。在“临洮,将汉地、西夏、蒙古、维吾尔各族信仰佛教之僧侣百姓召集起来,为他们讲经说法,灌顶授戒,并以严格的佛教戒律及修行次第整顿旧有的僧团。总之,噶玛拔希在返藏途中,屡次平息战乱,消除各种流行的瘟疫,并修建诸多旧寺破殿,使佛教教法得以弘扬。”[41]八思巴于公元1271年才旅居临洮。可见,嘎玛噶举派在临洮的传播早于萨迦派。
据《红史》记载,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三世活佛饶迥多吉(公元1284~1339)于元顺帝时第二次(公元1337年3月)到大都后,在临洮建有噶尔寺。②蔡巴·贡嘎多吉著,陈庆英等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2页;陈庆英《噶玛巴·攘迥多吉两次进京史略》,《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巴卧祖拉陈瓦著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公元1358年,元顺帝召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贝多杰(公元1340~1383年)去北京,他取道青海,途中在湟水流域一带居住活动,并且于公元1359年在今平安县境内的夏宗寺曾向刚满3岁的宗喀巴授近事戒。③王森著《宗喀巴传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编印,1965年第29页;班班多杰著《宗喀巴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第16页;王尧褚俊杰著《宗喀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页;法王周加巷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9页;唐景福著《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页;赛仓·罗桑华丹著,王世镇译注《藏传佛教格鲁派史略》,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9页;周润年《十三世纪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高僧——噶玛拔希》,《西藏研究》1997年第2期。
然而,有元一代,噶举派在玉树地区建有不少寺院,包括噶玛噶举派在内的噶举派分支都没有在今青海境内的河湟地区修建寺院[42],直到明初,三罗(又译三剌)喇嘛才于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在今乐都曲坛乡修建了瞿昙寺,朱元璋赐名“瞿昙寺”[43]。
三、噶当派在河湟地区的传播
噶当派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始于顿珠仁钦(公元1309~1385年)。顿珠仁钦是青海同仁县夏布让地方人,是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启蒙导师。顿珠仁钦年轻时到卫藏学习佛法,被布顿大师誉为“安多一杰”,后来返回安多,曾在临洮兴棍新寺④王森著《宗喀巴传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编印,1965年第30页;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毛继祖等译《安多政教史》,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649页。(临洮新寺,藏语称临洮为香根或香衮,此寺不是临洮大寺)担任堪布。前藏聂塘第瓦仅寺邀请其去担任堪布,结果他到达第瓦仅寺时已经有人担任堪布,于是再次返回安多。
公元1341年,顿珠仁钦返回安多后,在其家乡同仁修建了夏布让寺(夏卜浪寺、夏章寺),收徒弘法。后来,他将夏布让寺交给其侄子释迦桑波主持,自己来到了尖扎昂拉地方(今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并在这里修建了赛康寺[44]。公元1349年他又在今青海化隆县查甫乡修建了柴庵,是为夏琼寺(甲琼寺)的前身。⑤王森著《宗喀巴传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编印,1965年第31页;班班多杰著《宗喀巴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第14页;谢佐《一代大师的起点——青海夏琼寺与宗喀巴的少年时代》,《法音》1984年第3期。并且在这里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建者,后来被誉为“第二佛陀”的宗喀巴大师进行了启蒙教育。隆务寺的创建者桑旦仁钦幼年时也曾学经于顿珠仁钦[45]。
从确切的史料看,噶当派应该是第一个在今青海河湟地区建寺传教的藏传佛教教派,而此时已是元代末期了。
四、史籍所载元代的河湟藏传佛教寺院
寺院是僧人修行的场所,是其周围民众宗教信仰的活动中心。元代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寺院数量仅有数所,与明清时期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相比,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这也正是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初步传播的见证。
夏宗寺,噶当派寺院,位于今平安县寺台乡(原为三合乡)寺台村。宋代建有静房,南宋建炎年间得以扩建。顿珠仁钦曾在此修行。元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西藏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杰(公元1340年~1383年)应元惠宗(顺帝)之召去北京,路过青海曾居住夏宗寺,在这里给刚满3岁的宗喀巴授近事戒[46]。
夏卜浪寺,噶当派寺院,位于今同仁县年都乎乡夏卜浪村。顿珠仁钦于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修建,后来他将夏布让寺交给其侄子释迦桑波主持[47]。
赛康寺,噶当派寺院,位于今尖扎县昂拉乡西北侧。元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曲结顿珠仁钦在故乡建成夏卜浪寺(在今同仁县年都乎乡)后,为寻找修建夏琼寺的寺址来到今尖扎县昂拉乡,以顿珠僧格为施主建成昂拉赛康寺[48]。
夏琼寺,噶当派寺院,公元1349年顿珠仁钦在今青海化隆县查甫乡修建了柴庵,是为夏琼寺(甲琼寺)的前身,①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王森著《宗喀巴传论》,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编印,1965年第31页;班班多杰著《宗喀巴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第14页;谢佐《一代大师的起点——青海夏琼寺与宗喀巴的少年时代》,《法音》1984年第3期。并且在这里对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建者,后来被誉为“第二佛陀”的宗喀巴大师进行了启蒙教育。
噶尔寺,噶举派寺院。据《红史》记载,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三世活佛攘迥多吉(公元1284年~1339年)于元顺帝时第二次(公元1337年三月)到大都时,在临洮建有噶尔寺。②蔡巴·贡嘎多吉著,陈庆英等译《红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2页;陈庆英《噶玛巴·攘迥多吉两次进京史略》,《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巴卧祖拉陈瓦著,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一)》,《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卓尼禅定寺,萨迦派寺院,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卓尼县。由八思巴倡议,于公元1259年在一座宁玛派小寺的基础上修建[49]。这座寺院可能是宁玛派与萨迦派共有的寺院,因为如果专属萨迦派,这与八思巴请求忽必烈让各教派自由传教是相矛盾的。
临洮寺,萨迦派寺院,位于今甘肃临洮。《安多政教史》记载,“在这座城市里,有达温巴奉怙主八思巴供施双方的命令修建的寺院,当年聚集着数千名僧伽。”[50]今已不存。据《陇右金石录》记载,在明代临洮城东北有圆通寺、广福寺、宝塔寺、圆觉寺和隆禧寺五座寺院[51]。《狄道洲志》记载,此五座寺院都在府治东北,并且都是建于明代,其中圆通寺是原由唐时尉迟敬德监修的圆通寺[52]。《甘肃通志》记载,圆通寺是元代法王寺,明代在旧址上重建圆通寺[53]。据《陇右金石录》记载,明初宝塔寺内八思巴说法台遗像仍在,寺僧端竹领占被封为大敏法王,又是僧纲司所在地[54]。又据《安多政教史》说宝积寺即宝塔寺,可推知宝塔寺应即《安多政教史》所载的香衮(临洮)大寺。据《安多政教史》记载,临洮大寺有许多汉族支寺[55]。这些汉族支寺在当时是否都属于萨迦派寺院,是否修习萨迦派教法,已无据可查,《安多政教史》也无说明这些寺院的情况。但是,根据元代的佛教政策,这些汉族支寺应该并没有改宗萨迦派。又据《陇右金石录》记载,明代在广修寺院的情况下,临洮有九大寺院[56]。根据《狄道洲志》和《甘肃通志》对寺院的记载,其中只有圆通寺是元代法王寺外,其他的临洮寺院均为明代及以后所建的寺院来看,当时的许多汉族支寺的存在也许说的是明清时期的事情。
临洮新寺,据《康乐史话》,建于元成宗大德元年(公元1294年)①[宋]志磐《佛祖统记》卷48,见[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史传部一》卷2036,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印行第435页(b)。的临洮新寺是在原唐代“大圣寿宝积寺”的基础上改建的,明代改名正觉寺[57]。而据《狄道洲志》,西峰窝寺和正觉寺是两座寺院[58]。然而《安多政教史》所说的宝积寺和《康乐史话》所说的“大圣寿宝积寺”是否为同一座寺院,如果是同一座寺院,说明《安多政教史》将宝积寺和宝塔寺混为一谈了。《康乐史话》所说的“大圣寿宝积寺”是建于元成宗大德元年(公元1294年)②[宋]志磐《佛祖统记》卷48,见(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史传部一》卷2036,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印行第435页(b)。的临洮新寺。
报恩寺,在今临夏。据(明)吴祯《河州志》卷二《祠祀》,至元十二年由土官平章答立麻坚藏建,洪武二十六年立僧纲司,属卫[59]。此寺应是明代所设河州卫番僧纲司的所在,是否属于藏传佛教寺院,待考。
五、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的特点和影响
蒙元初期,藏传佛教开始在河湟地区传播。河湟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民族化过程中的汉化、吐蕃化现象,以及河湟佛教的基础,给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造成了一定的民众基础。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有其独特的特点。
第一,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元朝皇室对藏传佛教的尊崇促进了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在西藏地方归属蒙元统治以前,其内部的封建割据势力各据一方,争夺土地和人民限制了藏传佛教向外扩张。西藏地方接受元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加上皇室的尊崇,为藏传佛教东向发展提供了安定的政治环境。处于藏汉黄金桥位置的河湟地区,当然首当其冲要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第二,往返于内地的藏传佛教高僧是传播藏传佛教的主体。由于元朝皇室尊崇藏传佛教,特别是帝师的设置使得来往于内地的帝师和藏传佛教高僧络绎不绝。河湟地区又是其必经之地,这些来往于内地的藏传佛教帝师和高僧在河湟地区的暂住成了传播藏传佛教的主体。首先是八思巴在临洮居住三年,八思巴曾经在临洮寺讲经说法。八思巴的弟子胆巴也曾暂居临洮。③[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见(日)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史传部一》卷2036,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印行第726页(a)。噶举派的二世活佛噶玛拔希、三世活佛攘迥多吉和四世活佛乳必多吉都曾在河湟地区传教。噶当派的顿珠仁钦曾任临洮新寺的堪布。
第三,临洮成为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传播的中心[60]。根据史籍记载,临洮是来往于内地藏传佛教高僧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高僧在临洮的讲经说法,使临洮成为了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中心。
第四,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尚未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对藏传佛教来说,“佛法僧三宝”齐备,有严格的讲经学法制度,是衡量是否是正规寺院的重要标志[61]。对于元代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来说,是否有完整的讲经学法制度,目前尚无史料可以支撑。即使是在《安多政教史》的记载中,元代临洮也无常居的藏传佛教高僧,关于藏传佛教寺院的建造也是一笔带过,具体的讲经学法制度更是无从谈起。即使是顿珠仁钦在河湟地区建寺传播噶当派教法,据史料记载来看,当时所建造的寺院规模尚小,如果说其有完整的讲经学法制度似乎有点勉强,因此,我们可以说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有所传播,但是并未形成完整的藏传佛教教育体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今四川岷县的大崇教寺先是“按汉族的规矩进行讲辩”,“于宣德三年(公元1429年)进行扩建,建立讲辩制度,皇上赐额为大崇教寺”[62]来佐证。
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对当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和对后世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和发展都带来很大的影响。
首先,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使得河湟地区有了一定的藏传佛教基础。鉴于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基础,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三月设置“番僧僧纲司”[63]以羁縻统治河湟人民,同时设置有汉僧僧纲司,首任都纲是番僧。《明太祖实录》载:
立西宁僧纲司,以僧三剌为都纲。河州卫汉僧纲司,以故元国师魏失刺监藏为都纲;河州卫番僧纲司,以僧端月监藏为都纲。盖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64]。
《明会要》载:
永乐十八年,帝以番俗惟僧言是听,乃宠以国师诸美号,赐诰印,令岁朝。由是诸番僧来着多[65]。
元代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的传播不仅影响了明中央政府在河湟地区的施政,而且也为明末清初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大规模传播奠定了基础。
其次,为安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66]奠定了基础。安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的具体表现就是明代安多藏区的僧职土司[67]的出现。
第三,元代藏传佛教在河湟地区的传播也造就了一批藏族佛教高僧。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不但为卫藏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到河湟地区传播佛教带来了有利条件,也为河湟地区的吐蕃人到卫藏地区学习佛法提供了便利。如噶举派僧人三罗(又译三剌)在河湟地区修行和传法,明初在朝廷的扶持下修建有瞿昙寺[68];顿珠仁钦前去卫藏学法以后返回河湟地区传播噶当派教法;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于公元1376年前往卫藏学法。史籍记载也有一些高僧虽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到卫藏地区学习佛法,并且其教派归属也不清,但确实存在不少的高僧。如明初任朵甘卫都指挥同知的佛宝国师索南兀即尔[69];明初临洮僧端竹领占(俗姓石,应该是汉人,抑或是汉化的藏人,足见河湟地区汉藏融合的双向性),圆寂后被追封为封为大敏法王、西天佛子;①张维《陇右金石录》卷6,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1943年版,卷6第校补第15页。[清]呼延华国篡修《狄道洲志》卷10《人物下》,成文出版社,1960年版第662、663页。河州卫汉僧纲司都纲故元国师魏失刺监藏;河州卫番僧纲司都纲端月坚藏;于洪武二十三年被封为上师的临洮僧已什领占[70](耶希任钦[71])等。《明史·西番诸卫传》载:
永乐时,诸卫僧戒行精勤者,多授刺麻、禅师、灌顶国师之号,有加至大国师、西天佛子者,悉给以印诰,许其世袭,且令岁一朝贡,由是诸僧及诸卫士官幅辏京师[72]。
《明会要》载:
永乐十八年,帝以番俗惟僧言是听,乃宠以国师诸美号,赐诰印,令岁朝。由是诸番僧来着多[73]。
虽然史籍并无明确说明河湟地区的藏传佛教高僧姓名、数量,但是这样的高僧应该不仅仅是史籍所载的几位。
[1]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4.
[2]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86.
[3]张虽旺,王启龙.试论宋代河湟地区佛教的发展[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4,(6).
[4]赵改萍.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和影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57-158.
[5][6][8][28][31]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Z].吴均,毛继祖译.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161,2,27,648,648.
[7][9]陈庆英,蒲文成.西纳格西西纳喇嘛和塔尔寺西纳活佛[J].西宁:青海社会科学,1985,(1).
[10]张云.元代宣政院历任院使考略[J].西北民族研究,1995,(2).
[11][15][16][22][24][33][35]王启龙.忽必烈与八思巴、噶玛拔希关系新探[J].清华大学学报,1997,(2).
[12][意]伯戴克.元代西藏史研究[M].张云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47-148.
[13]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籍[M].陈庆英 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202-203.
[14][32]蔡巴·贡嘎多吉.红史[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43,79.
[17][21][明]宋濂.元史(卷3).世祖一(第1册)[Z].北京:中华书局,1976.60,11.
[18][19][20][23][34]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M].陈庆英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165,119,119,106-111,122-123.
[25][明]宋濂.元史(卷87).百官三(第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2193.
[26][29][30]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89,146,146.
[27]王启.八思巴生平与《彰所知论》对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9.
[36][美]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M].赵清治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40.
[37][38]克珠群佩.嘎玛噶举派黑帽系活佛述略[J].西藏大学学报,2004,(1).
[39]王辅仁,陈庆英.蒙藏民族关系史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4.
[40][41]周润年.十三世纪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高僧——噶玛拔希[J].西藏研究,1997,(2).
[42]周生文,蒲文成.噶举派在青海的传播与现状 [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1).
[43]谢佐.青海乐都瞿昙寺考略[J].青海民院学报,1979,(1).
[44]班班多杰.宗喀巴评传[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14.
[45]蒲文成.藏传佛教诸派在青海的早期传播及其改宗[J].西藏研究,1990,(2).
[46][47][48]蒲文成.甘青藏传佛教寺院[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69,439,439.
[49]杨世宏.卓尼名僧考略[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2).
[50]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Z].吴均,毛继祖译.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648.
[51][54][56]张维.陇右金石录(卷6)[Z].兰州: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1943.31,31,15-32.
[52][58][清]呼延华国篡修.狄道洲志(卷5).寺观[Z].台北:成文出版社,1960.365-366,368.
[53]四库全书·甘肃通志(卷12).祠祀[Z].5.
[55][72]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安多政教史[M].吴均,毛继祖译.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89.648,645-649.
[57]徐正文.康乐史话[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24.
[59][明]吴祯.河州志(卷2).祠祀[Z].25,
[60]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146.
[61]蒲文成.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历史变迁[J].西宁:青海社会科学,2000,(6).
[62]谢重光,白文固.中国僧官制度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266.
[63]明太祖实录(卷226)[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3307.
[64][71][73][清]龙文斌.明会要(卷78).第4册[Z].北京:中华书局,1956.1524,1524,1524.
[65]吴均.论安木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统治[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4).
[66]王继光.安多僧职制度初探[J].西北民族研究,1994.1.
[67][68][清]张廷玉.明史(卷330)·第28册[Z].北京:中华书局,1974.8541,8542.
[69][清]张廷玉.明史(卷331)·第28册[Z].北京:中华书局,1974.8588.
[70]明太祖实录(卷220)[Z].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