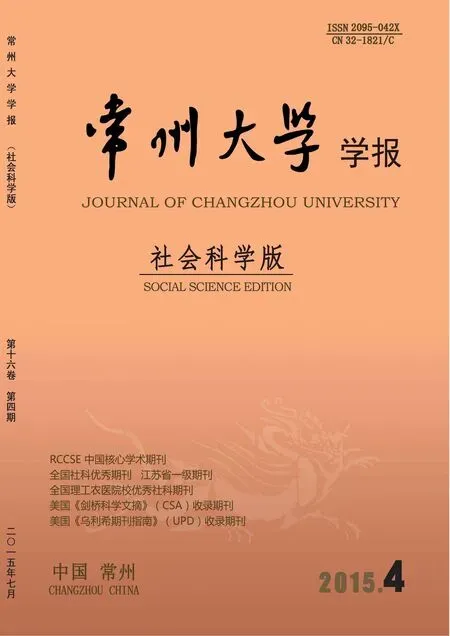浅探王船山晚年工夫论思想——以《庄子解》的“凝神”与《张子正蒙注》的“存神”为例
王宇丰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100875)
WANG Yu-feng
(School of Philosop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工夫是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在中国哲学中,工夫总是在一套本体理论的架构中彰显其实践维度,而工夫论即是与本体论、心性论相为配应的一整套关于其实现渠道与修养方式。无论儒释道,皆具各自的工夫论。工夫论是作为通向它的本体论理想的实践哲学,也是宋明理学的核心环节。本体论作为工夫论的形上依据 (客观根据),心性论作为工夫论的内在本质,是儒家最高真理落实到个体的实现路径。按牟宗三先生的说法,工夫论是儒家道德实践所以可能的主观根据。儒家对于个体生命成就最高人格理想的愿望,必须要讨论每个个体生命自身实践的入手问题,同时也是个体实践对心性论、本体论的自证性和确定性。可以说,没有工夫论,本体论或心性论则虚浮无根。因此,宋明儒者在论证其理论自足性时,无不涉及工夫论问题,且在颇多理学家那里,形成繁复、严整的工夫论体系,蔚为可观。
《庄子解》与《张子正蒙注》成书于船山六十岁以后,体现其晚年思想的发展趣向。本文从工夫论的角度,发现船山在《庄子解》特标出“其神凝”三字为“一部《南华》大旨”,并在诠释语境中随处隐含“凝神”这一思想,可见其对“神”或“凝神”问题之重视;在后来的《张子正蒙注》,船山则又多语及“存神”,以彰显“神”在工夫论中的特殊地位。如此大量凸显“神”这一概念,在船山作品中,大概以《庄子解》与《张子正蒙注》为最多。若将《庄子解》中的“凝神”与《张子正蒙注》中的“存神”加以比较,虽然限于不同文本的特殊诠释语境,而使特殊范畴或概念的阐发不能系统地深入,但可知其大概以“神”为工夫的对象或中心。然船山对庄学或褒或贬的态度,以及后来以横渠 (张载)为正学的学术指归来看,这二者工夫必然有其学理上的不可融通性,如从二者的转变过程来看,对发现船山晚年工夫论的基本态度应该可以找到一条思想线索,同时也可以探讨船山晚年思想发展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
一、“一部《南华》大旨”
船山在《庄子·逍遥游》中特表彰出“其神凝”三字,并指出此三字为“一部《南华》大旨”[1]88。船山之所以如此重视“凝神”,并非随意判定。综观《庄子解》,“神”或“凝神”的思想可谓隐现于通篇之终始,以“凝神”为大旨,深刻地体现出船山对庄学工夫论的格外阐扬,甚至影响到他哲学体系的建构。由于受注疏形式的拘限,船山并未全面阐发对“神”或“凝神”的命题内涵,只是在特定语境下稍作提点,诠释较为零散。不过,仅就这些内容,本文集中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船山论“神”,往往与“志”兼论。神志关系在古代原有一种理论传统。在船山论述中,对气的调节方面, “以志凝神”, “志”似乎比“神”更具对气的直接主导性,他说:“志者,神之栖于气以效动者也。以志守气,气斯正焉。不然,则气动神随,而神疲于所骛。齐以静心,志乃为主,而神气莫不听命矣。”[1]304通过 “志”持守气以使之纯正,“神”才不被气所疲役。这里神志关系中的“神”,涉及志、气生理层面的关系,其含义侧重于心神而言。另一方面,船山特为强调“持志”“凝神”不可迫操,“欲凝神而神困,欲壹志而志棼”[1]299。另外,船山往往结合物来论“凝神”:“神不凝者,物动之”;“神凝者,窅然丧物,而物各自效其用,奚能困己哉?”[1]301为物所扰动,是因为心气本身缺乏定主,“持志”正是为了“凝神”,一旦“神凝”,便越出自我的认知局限而通达物的本然状态,这样,物各付其用,不受其累。所谓“窅然丧物”,即“忘物”,在船山看来,只有通过“审于重轻之分”的致知之功,才能实现志定神凝。这就迥别于一般的神秘体验了。在船山那里,“盖神者,气之神也。”神本身是“天气之醇者”,但是天命所授于人之气本来就是纯的,由于心气易受物的阻滞和搅扰,神便在逐物过程中遮蔽起来,但是神终未被物所涣散,“夫物岂能间吾之纯气乎?”[1]297因此,“凝神”不是逃物、绝物所能实现的,此工夫需心物交养、内外兼治,船山说:“神者,不滞于物而善用物者也。”[2]88便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其次,船山在形神关系上把神定位在“生之主”,突显神作为生命本体的意义。船山统观世间养生修行之法,指出:“养生之说,吾知之矣:下者养形,其次养气,太上养神。”[1]554船山认为,庄子所谈之“养生”,并非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养生”,通常所谓的“养生”只不过是“养形”而已。“养形”只看到人之有生死,却未曾关注到生之所以为生的真正本质。对此,他说: “生死者,人之形生而形死也。寓形于死生,皆假也,假则必迁。”[1]145如果我们只热衷于对有形之生死的保养与守护,那也不过是徒劳,因为生命形体终必消逝。船山告诫我们说: “养生者非徒养其易谢之生也。”[1]293有形之生死固不免于天地间的生成毁灭,而对于人而言,不能仅仅听凭有形、无形的迁移,就把生死直接等同于生命本然的意义与价值。船山坚持认为“夫生必有所以为生,而后贤于死”的观点,把“养生”从世俗的观念里摆脱出来,相对应地阐扬出“善养生者,不养其生,而养其不可死者。”[1]165“养不可死者”即意味着 “养其无形之真”。就此在本末主宾的关系上,船山特重《庄子》自身的义理独特性,他对《养生主》题解曰“养生之主”,即凸显出“生之主”,而将形、心知一类都置于宾位。船山认为养形之生死就好像“以薪为火”,舍本逐末;而他所注意到的则恰恰是真正不灭的生生者—— “神”,他说:
盖人之生也,形成而神因附之。形敝而不足以居神,则神舍之而去;舍之以去,而神者非神也。寓于形而谓之神,不寓于形,天而已矣。寓于形,不寓于形,岂有别哉?养此至常不易、万岁成纯、相传不熄之生主,则来去适然,任薪之多寡,数尽而止。……传者主也,尽者宾也,役也。[1]125
寓于形之中的神乃是一“生之主”也。在形神关系中,我们看到,神之所以为主,是因为它能够“至常不易”、“相传不熄”、“来去适然”。据此,对“养生”背后的生死观应该真正明白其内蕴所在:“知死生者,知形神之去留;不生不死者终古而不遁。”不遁者超越有形之生死,船山以昼夜关系比喻神在生死问题上的地位与价值,他指出:“昼夜分两端,而天之运行一;生死分两端,而神之恒存一。气有屈伸,神无生灭。”[2]23船山想强调的是,“养生主”的提法比一般的“养生”更符合对生命本体的关切与正视,这样就把神的价值体现在对待生命的态度之中了;而我们往往遗忘掉对“生之主”的涵养呵护,以至于残生损性,妨碍“性命之情”的健康发展,船山担忧人们“残其生者即其生,唯得宾而忘主”,故而在这个意义上凸显庄学修养工夫的极端重要性。
复次,船山还从认识论阐发神明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神主明辅,而知为中介。明向外征知,而神之本体独立自存,离明之神也还是神,无所益损:“知所自生,视听导之耳。乃视者,由中之明以烛乎外,外虽入而不能夺其中之主。”[1]132明外泄而离神,故要“葆光”,使神所处之虚室空灵明净,则所照皆明。以此照物,彻体皆天。他说:
神使明者,天光也;明役其神者,小夫之知也。故至人以神合天。神合天,则明亦天之所发矣。神与天均常运,合以成体,散以成始,参万岁,周遍咸乎六宇。故休乎天均者,休乎神之常运者也。[1]461
以神使明,则保证明是由天光发出的。“神与天均常运”,即“以神合天”。神与知明根本不同在,知明照见的只是可照见的有形之物,“神无幽明之异”,神贯通幽明两间、知幽明之几。“神自幽而之明,成乎人之能,而固与天相通”。这种超越于幽明的神通,“源在我也,繁然有彼,皆受于天也。”[1]389神寄寓主体而显在,不受有形器质之蔽塞以知明自囿, “形之与貌,号之为人者,非我也!我一天也,寓于形貌而藐乎小者也。”[1]155如此之“我”,以神而论,便是与天同合,那么,知明在这种神的所使下,“一知于所知之大宗,则杂出之心知皆止矣。”[1]147
船山在《庄子解》对神作“生之主”的解释,又发挥“以神合天”的观点,以及对“凝神”直断为“大旨”,跟他自己对工夫论一以贯之的反思有关。船山大赞庄子“能移” “相天”,是围绕“神”为核心的工夫论体系展开的。当然,在《庄子解》只是隐为指出,未作深入系统的挖掘,但到了《张子正蒙注》则大加发挥,这中间其实保持着船山对庄学工夫论的吸收与批判二者的思想张力。
二、“因而通之”与“唯差一间”
船山《庄子解》多以“持志”来落实“凝神”工夫,而志在心气关系中强调工夫的主体自为性。“凝神”的根本目的即在于对从形神关系中所凸显的“生之主”的保养与守护,而船山所认定的“生之主”有他自身的特殊含义,即通过神明关系揭示出“神无幽明之异”,由神观照一切,指向了一个实有的宇宙整体,以神合天,天无幽明之异,从而消解对一切事物有无分判的本体态度。
船山拒斥有无对立的本体论,努力从宇宙论角度重新挖掘庄子思想的立论基础,他站在气学立场解释“浑天”“天均”等概念。“浑天”实际上回归到一种原始朴素的气学宇宙论,浑然一气未分,既是对外在客观世界进行实存性看待,同时又未加诸主观对事物存在的绝对分殊。正因为宇宙是气的整体统一性和实存性存在,宇宙是幽明无间的,而非有无决裂的,这典型反映在对待人之生死的问题上来。在船山看来,生死不是有无问题。船山在这个层面驳斥佛教的生死观,也包括批评了一些儒者“人死气散”的看法,船山指出:“浮屠自私以利其果报,固为非道;而先儒谓死则散而之无,人无能与于性命之终始,则孳孳于善,亦浮沤之起灭耳,又何道之足贵,而情欲之不可恣乎!”[1]303在船山看来,佛教是“画以界限”的个体轮回,轮回果报还是自私念头所致,故曰“非道”;而宋明儒者所主张的“死则散而之无”之说则无法从根本上立足于人的身心性命最终安顿之所在,主体价值成了无根的存在。船山既以气之实有否定“死则散无”的看法,又以气之聚散变化作为生命的自然现象对抗佛教的轮回说。船山尤为赞许庄子“能移而相天”的说法,“能移”解释了生死不是有无生灭的绝对分殊,而是气在幽明之间的转移变迁,而“相天”则说明了生命形式的转移并非毫无意义的,而是通过自身的转化可以实现“相天”之功。从这个意义讲,这样的一种以气本体为中介的天人互动之说, “较之先儒所云死则散而全无者,为得生化之理,而以劝勉斯人使依于道者为有实。”[1]294在船山看来,这一庄学大旨,与《周易》“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以及《论语》“知生”的义旨可以相互印证,是值得肯定的。
船山在生死观念上认可庄子的“能移” “相天”等观点,主要源自佛老等存在论上的虚无主义对于生命存在价值的渗透与冲击。这种对抗虚无主义的立场,从更深层次反映了船山对其体用关系的自觉批判。船山在《庄子解》中寻着“与心理不背”“尤合辙”之处,亦与儒学“因而通之”即在体用上一定程度承认了庄子“寓体于用”的思维方式。船山发现,庄子思想有一种拒斥从本体论上分裂体用、有无的内在意图,尤其“立体废用”或“立理限事”那种观念,而是往往以相对之用揭明事物的整体性和变动性,庄学那种去实体化、去绝对化的自然态度也符合船山以气学实存性对抗虚无主义的理路,并推证庄子“浑天”中所本具有的宇宙论姿态。曾昭旭先生指出,船山认同庄子之学在体用问题上“护道于不裂”,因而“可通于圣人之道”[3]243。庄子虽然随处描述“天均”、“环中”之用,但这一“用”背后必有其“体”;庄子意在“无体为体”,却未曾明确否定此体,故所谓“道之不裂”即在于此体“隐然而有”。张学智先生认为:“庄子在最终层面上合于儒家之道,为儒学之助。”[4]这一“最终层面”即可以通过这一体用关系的理论旨趣上发现一定的相通性。
不过,船山站在儒家立场,坚持庄子“非知道者”,这在《庄子解》之外的文本都能看到相关的批评[5]。一方面,船山在体用相即、“护道于不裂”方面肯认儒、庄之间可以“因而通之”,虽然庄子忧患“无能复其体用之全”,道术之裂“往而不返”;但另一方面,庄子只一味立足于“寓体于用,而无体以为体”的立场,“消极地遮拨群言之执著”[3]243。在船山看来, “用者必有体而后可用”[2]98,庄子对“用”的彰显与对“体”的隐晦实在容易造成对“体”的遗忘而只滥其“用”。船山对此作一尖锐的批评:“佛、老之初,皆立体而废用。用既废,则体亦无实。故其既也,体不立而一因乎用。庄生所谓‘寓诸庸’,释氏所谓‘行起解灭’是也。”[6]20庄子“寓诸庸”本来可以引向“寓体于用”的思理,但是庄子不明言体,而所用便令人感到“无一实之中道”[2]135,因此,船山认为庄子也属于“诬有为无”之一流[2]15,指出:“庄老言虚无,言体之无也。”[2]324与庄子相比,儒家“承体起用”,用就能够落实与贞定。如果不立体,反则“一因乎用”,以此来看庄子所谓“逍遥”便只是“狂之痼疾”[7]133。正如曾昭旭先生所说,庄学与儒学“唯差一间”,所差的这一间,“使庄学不能有积极之赞天地化育之功”,庄子也不可能从“体”上正面肯定儒家仁义礼乐的人道价值,“虚笼群言之用,而不能还以建立真实之道德事业也”[3]243。这种立论的基调也就体现出船山通解《庄子》的立场不单纯放在一个“异端”的位置,或者说,不完全是一种外在的批判,而更多的是一种内在的批判。萧汉明先生就曾强调说,船山晚期的学术思想对“‘异端’之类的字眼,已主要偏重于学理,而并不完全出于对儒学正统的维护。”[8]这也就是说,船山解《庄》不能说只是做一外在的批判,实则在诠释过程中,对庄学思想的合理性部分有所启发和吸纳。曾昭旭先生也指出:“儒家之圣人之道,而有别于道家中无实体之虚歉者也。然道家之虚与儒家之实,则其间正无截然之分际,而可以引而通之者,唯待其人以善通之耳。”[3]246船山对历史上那些体用分裂的本体论深恶痛绝,或许隐藏在庄子中那种宇宙论的整体性意识影响到船山对于人生价值与工夫论地位的重新思考。船山通过把“唯差一间”指点出来,意识到庄子的“浑天”“天均”“通天下一气”之旨固然可以抵制或对抗存在论上的虚无主义,但另一方面,庄子的“无体之体”却未必彻底消除价值论上的虚无主义的尾巴,然而“无体之体”本身未隔绝“立体”之可能性,故可以改铸或充实成为儒家之“体”,而这一理路本身并非自相抵牾。
总之,船山预留了庄子“浑天”“天均”的宇宙论的理论背景,扬弃其作为“唯差一间”的“无体”之弊,更在《张子正蒙注》里大加发挥,从更高的太虚、絪缊健顺之本体复归横渠,把“能移而相天”的命题表述成为“全而生之,全而归之”。“全归”是在气之聚散变化的过程中对生命形态作出解释,但就气在人生死上的循环、转化的形式而言,与佛教轮回说似无大异,而且在劝善去恶方面,又具有某种价值倾向上的相似性。不过,轮回果报与船山“全归”说本质上有着截然的对立。唐君毅先生曾指出,佛教的轮回果报说“初虽所以劝善惩恶,然终不免本于人之固守其个体之私心。故谓轮回之说,足以怙私崇利。人既各成一永存之个体,各自独立不相依,则何妨叛其君亲。此即船山破轮回,而只言气化往来不穷之说之微意。”[9]409就个体存在方式与普遍性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而言,唐君毅先生进一步指出:“个体虽无轮回,而个体之气不丧失。人之身体,固由气之所凝,人之精神,亦属于气。人之理想为气之理,理想中之价值,为仁义礼智之善。此人之精神内容,所谓性是也。人之精神能力,所以显仁义礼智者,为气之才。”[9]408佛教以个体轮回的形式主张劝善惩恶,就其个体言,君亲等人伦关系为个体在外者,人道原则的联系性和必要性未从本体上给出,故易于超脱而置之;但是船山以个体之气返还太虚之中为言,强调个体与整个世界的整体性存在方式,故个体无所逃遁,必把自身理想落实或表现在人道原则上,而并非仅仅依托于个体。船山便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对人之生命现象作气轮回式的诠释,把人生理想价值立定在儒家道德伦理精神,并且,这一义理的发挥在《张子正蒙注》中通过“存神”工夫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存神尽性”与“全而归之”
在体用之辨,船山一定程度上认可庄子,但对庄子的批判也恰恰还是在体用上。船山坚持“有体则必生用,用而还成其体”的体用观,以否定庄子“一因乎用”而未能“还成其体”的流弊。但是,就庄子“凝神”以“能移而相天”之工夫而言,船山却显然有所吸收,并在《张子正蒙注》大加阐扬。严寿澂先生说:“船山为功于气以相天的思想,大发于《庄子解》,重申于《张子正蒙注》。”[10]《张子正蒙注》代表船山晚年哲学思想的成熟和精深,以至船山最后呼出“希张横渠之正学”,以横渠之学为正学,可见其志愿与旨趣之所在。
船山之所以注《正蒙》,在《序论》明确提及: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则为善为恶,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见为寄生两间,去来无准,恶为赘疣,善亦弁髦,生无所从,而名义皆属沤瀑,两灭无余,以求异于逐而不返之顽鄙。《正蒙》特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而至当百顺之大经,皆率此以成,……善吾伸者以善吾屈。然后知圣人之存神尽性,反经精义,皆性所必有之良能,而为职分之所当修,非可以见闻所及而限为有,不见不闻而疑其无,偷用其蕞然之聪明,或穷大而失居,或卑近而自蔽之可以希觊圣功也。[2]3
船山其实还是延续了在《庄子解》中的思考,他关心善恶价值之于生死的究竟意义。故船山溯源宇宙本体之目的,意在重新给善恶价值或人道原则寻找到一条本源性的依据,以回应存在论上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谬误倾向。船山就此所关心之事,既非独立在外的客观宇宙,也非仅仅是仁义中正的具体的诸德目,而是寻求它们之间的维系方式。船山似乎有意识地强调“存神”工夫来提示这样的一种存在与价值之间的内在共通性。
就一般理解来说,气是物质性的存在。气作为自在之物,本无人所赋予的价值属性,而是作为自然之天的范畴。船山如果把神只界定在气的领域,那么,死后的神气最终还是陷于一些儒者所主张的“气散则无”之说,物质形态的转化并不添置人道价值的内涵。这是船山所担忧的。陈来先生说:“船山的思想,在一定的意义上看,具有自然主义的特点,因为他要把善恶的问题追溯到自然的生死,追溯到阴阳的屈伸,试图以阴阳屈伸的自然来说明价值的根源。”[11]368船山试图寻找一个圆满的方式重新解决人作为自然形态的生命存在与善恶价值的融通问题。因此,我们会看到船山提过“善气”、“恶气”、“治气”、“乱气”等概念[2]5,气具有善恶治乱的价值属性,便无法用物质与精神二分的对立模式去解释了。船山把善恶价值的根源追究到气之本,例如他说:“有生之善恶治乱,至形亡之后,清浊犹依其类。”[2]5善恶治乱之气随着其清浊状态而仍旧留存于宇宙,船山即以此打破价值虚无主义的理论怪圈。故船山所谓“存神”之功夫,便意在把气之存在与人道价值打并为一。他说:
聚而成形,散而归于太虚,气犹是气也。神者,气之灵也,不离乎气而相与为体,则神犹是神也,聚而可见,散而不可见尔,其体岂有不顺而妄者乎!故尧舜之神,桀纣之气,存于絪缊之中,至今而不易。然桀纣之所暴者,气也,养之可使醇,持之可使正,澂之可使清也;其始得于天者,健顺之良能未尝损也,存乎其人而已矣。[2]8
所谓“气犹是气”或“神犹是神”以及神气“至今而不易”,即从存在论角度把人的实践工夫的价值作用肯定下来。正因为气要解释价值根源的问题,“气之神”就承担着工夫所含具的结构性意义。
需要注意的是,船山并非持抑理扬气的态度,他非常注意“气化有序”问题。他说:“气至而神至,神至而理存者也。”[2]130船山特别从“神之理”的角度来阐释:“神者非他,二气清通之理也。”[2]2这就直接把神说成是气之理了。由形气聚散而呈现幽明状态,对于神而言却没有幽明之异。因此,气之屈伸往来,“唯神能见之,不倚于闻见也”[2]72,神能够不受耳目闻见的拘限去“见几”、“知几”,因而强调“以神治物”,而非具体感官来判物,这就看出“存神”对领悟神之理的重要作用,他说:“非存神者不能知其必然之理。”[2]276但存神作为工夫,不是人人一开始就能够知几、知理的,“天之神理,无乎不察,于圣人得其微,于众人得其显,无往而不用其体验也。”[2]56又说:“昧其有无通一之性,则不知无之本有,而有者正所以载太虚之理。此尽心存神之功,唯圣人能纯体之。”[2]326只有真正实现“存神”工夫的圣人才能够彻察神理之微,而一般人只是体验其显著表象而已,故往往昧于有无对待之中而不见太虚通一之性理。
船山所谓的“神理”,是以气之实有打破有、无对立的太虚絪缊宇宙本体论为基调的。实有即诚, “诚,以言其实有尔,非有一象可名之为诚也。”[2]58船山以实有义提炼出诚之精义,使之高度抽象化并足以涵括神、气以及理等哲学范畴,故他又说:“诚者,神之实体,气之实用。”[2]95气之实有即从实有的宇宙论把作为工夫的“存神”与“存诚”联系起来。船山强调“神也,必存之以尽其诚,而不可舍二气健顺之实,以却物而遁于物理之外。”[2]80二气健顺之实,即需要尽诚、存诚,指出“神存而诚立”,“终始尽诚于己也。此至诚存神之实也。”[2]146人若能尽诚于己,便能达到 “存神”的结果。一方面,船山“存神”的目的,即通过以诚观之,使人们认识到神气“始终相贯,无遽生遽灭之理势”[2]68。这显然是针对佛老生灭观而发的,因此,船山批评“未能穷理知性而言天人之际”是一种“躐等”行为,并以此把“存神”与“役神”相区别:“心思之贞明贞观,即神之动几也,存之则神存矣。舍此而索之于虚无不测之中,役其神以从,妄矣。”[2]73可以说, “役神”便无法“立诚”或“存诚”。另一方面,船山注重“天理之节文”,认为“气,其所有之实也。其絪缊而含健顺之性,以升降屈伸,条理必信者,神也。”[2]60气实有健顺之性源于神之条理作用,承认“知之必有详略,爱之必有区别”[2]97。所以,这种“神理”便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物理,它更是人道原则的基础和仁义价值的依据。船山认为:“清虚之中自有此分致之条理,此仁义礼智之神也。”[2]65仁义礼智便是清虚神气的内在条理,他还说: “神者,天地生物之心理,父母所生气中之理。”[2]317这便意味着,此“神理”原本就是作为道德生发之地,故“存神”本身便是实现人道价值或道德境界的根本途径。这种内在条理所灌注的价值精神,并不因落实于具体道德践履中而被湮没或贬抑,反而需要通过这种现实特殊性的条理而实现形而上的理想,船山说:
人生于天地之际,资地以成形而得天以为性,性丽于形而仁义礼智著焉,斯尽人道之所必察也。若圣人存神以合天,则浑然一诚,仁义礼智初无分用,又岂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因感而随应者。然下学上达,必循其有迹以尽所得为,而豁然贯通之后,以至诚合天德,固未可躐等求也。[2]46
“存神”并不是玄而又玄的外在超越,它本身即要求人以诚对待天人之际的道理,“存神”体现的恰恰是现实品格和实践品格,它不主张“躐等”而“登天而别求企及之道”,“必循其有迹以尽所得为”,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礼智等人道原则有其内在必有之理,存神便是要人们发现“气质之中,神理行乎其间,而恻隐羞恶之自动,则人所以体天地而成人道也。”[2]241对人道的切实体验即通过“存神”而明白我与天地之间本然的沟通性。
由于特定的诠释语境,船山诠释《庄子解》时“神”尚未展开完整的义理结构,而在《张子正蒙注》则谈得更为充分和丰富。作为“气之神”,船山把它表述为气之清通的本然状态,以别于形质器物。与《庄子解》所不同,船山关于“气之神”往往落实到“性”上谈。“气之与神合者,固湛一也,因形而发,则有攻取,以其皆为生气自然之有,故皆谓之性。”[2]104神与气合,原本湛一清通,故性之本然无分人物,即所谓“气之所至,神必行焉,性必凝焉,故物莫不含神而具性。”[2]321人物之性,初为神气所撰, “性者神之撰,性与天道,神而已也。”[2]77但是物之性与人之性本质不同,物之性浊碍固滞,而人之性由心神而感通,故有主动创造之功。人的生命活动突显在对于神的关切上,“气无可容吾作为,圣人所存者神尔。”[2]6“神”作为工夫被提出来。若从“存神于心”角度讲,“澄心摄气”“善用其气”的面向止于强调个体工夫的具体方法,这在《庄子解》的“持志”“凝神”多有阐述,并不新奇;但《正蒙注》还有一个重要的面向的表达,即“道运于心”或“尽性”“尽心”。这便是船山援庄归正的关键所在。
“存神”并不仅是对此知性意义上的觉解,它尚要通过性来实现。故“存神” “尽性”往往连用。在船山那里,性是神凝于人身上的东西。并且,气之清虚湛然者即气之神,由气净化凝合成神,并通过神发挥义理的作用,亦即一种在人身上的性之显发作用,“合气于神,合神于性,以健顺五常之理融会于清通。”[2]3由于性为神所合凝,“即性而知天之神理”[2]100,从这个意义上讲,性便是沟通天人的具体中介,亦即存神之下工夫处。性因由天所赋予,故不受形质才气而限制,这就保证了存神对于每个人都是有效的。“性性则全体天德而神自存。”[2]79性性即尽性、成性,船山有时也把存神与尽心合说。“由性生知,以知知性,交涵于聚而有间之中,统于一心,由此而言之则谓之心。顺而言之,则惟天有道,以道成性,性发知道;逆而推之,则以心尽性,以性合道,以道事天。”[2]18这样,船山把存神又落实到心性工夫之上,由上而下,天把道凝结为人性,由下而上,人通过尽心尽性便把天道实现出来,顺逆有序,次第分明,亦不容混同。“合天存神之学,切于身心者如此,下学而作圣之功在矣,尽己而化物之道存矣”。[2]343这样,存神既有形上学的依据,同时又在义理节次中表现出具体的行动准则,防止了一味从高远一路脱落掉,使工夫废弛于情欲的一边,蹈空凌虚,不分天理固然的先后本末;而从宇宙论重新开出儒家“下学”的实践品格,实则是对于“上达”一贯下来的形下推衍。
存神尽性,最终即显“同归之理”。气之屈伸,乃鬼神之良能, “伸者天之化,归者人之能,君子尽人以合天,所以为功于神也。”[2]84为功于神,从气上说,使气正神清而全归于天;从理上说,“全健顺太和之理以还造化”[2]4。全理,也就全性,全性便最后以全归的方式返回宇宙大化中。“神伸而生,神屈而死,死则返于神。”[2]77船山的存神、全归之说,即把个人工夫与宇宙整体密切联系起来,这种个体工夫虽然以道德践履为鹄的,但这绝非以个体全性而宣告价值理想的完成,它关乎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存者,不为物欲所迁,而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守之,使与太和絪缊之本体相合无间,则生以尽人道而无歉,死以返太虚而无累,全而生之,全而归之,斯圣人之至德矣。[2]6
存神,即抓住生命的根本而充分实现其价值所在,“圣人知化之有神,存乎变合而化可显,故能助天地而终其用。”[2]281即,存神不仅是个体生命的事情,它同时也能够有益于整个天地宇宙。这也就站在儒学立场上远远超出了《庄子解》中“能移而相天”的思想水平,也充分把儒家“参赞天地之化育”的精神理想推向更为宏阔广大的境界。
四、结语
萧汉明先生曾指出,综观船山一生学术脉络,“《庄子通》与《庄子解》是他学术态度转换的重要标志”[8]。若从 《庄子解》中的 “凝神”到《张子正蒙注》中的“存神”的角度看,似乎可以发现船山晚年在工夫论上自觉的发展理路。一方面,船山有取于庄子“能移而相天”之说,把“凝神”提升到宇宙本源的高度去观照,启发了船山“从本体宇宙论之进路入以说人性”[3]210的维度,船山就此在一定程度上肯定庄子的运思方式,钱穆先生也说:“船山精研老庄,所谓观化而渐得其原者,途辙有似于庄生。”[12]另一方面,庄子“凝神”之工夫“实并不涵有四端五常等道德内容,船山则使此辅于自然之道儒化,把儒家的道德观融入庄子式的气化宇宙论”。[10]故于体用观上批评了庄子“离物以自高,绝物以自洁”之弊,从太虚、絪缊健顺之性作“存神”工夫来复归横渠正学,并明确以气学立场坚定宇宙本体为一个幽明无间、始终恒在者,“存神尽性”的依据便在于神与性是此宇宙本体内在所显发的恒存不亡之体,生死问题通过“存神”以“全归”于太虚的方式保留了终极的价值意义。
船山有见于佛教轮回果报说和宋明儒者“气散则无”之论,以及其他一些“专己保残之曲学”,对生死的价值问题作了宇宙论上的重新安置。这无论从《庄子解》还是《张子正蒙注》都能够感受到船山这一苦心和襟怀。陈来先生指出,船山晚年的思想趋向于“宇宙论中心取向的体系”[11]368。关于工夫论的宇宙论色彩,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船山提出“神”概念,包括“神气”和“神理”两种含义,似乎有意避免程朱和陆王各走的一条偏蔽之路,但需要指出的是,船山斥陆王甚于程朱,乃至于后来对程朱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或许可以从中看出一些迹象来。唐君毅先生即从宇宙论谈及了这一隐含的问题:“船山之言人性,乃取客观宇宙论之进路,与周濂溪张横渠略同,而大异于象山阳明之直接就本心与良知、以自见其性之进路。亦异于程朱之兼取心性论与宇宙论之进路者。”[9]354亦可以说,船山之工夫论,异于陆王纯粹的心性路径,反倒对程朱的心性论与宇宙论相互结合的进路更接近,以新的理论高度复归周濂溪和张横渠,并与《周易》的宇宙论和人生观遥相契应。总而言之,船山试图以“神”为下工夫处,即通过为功于气,把个体的修养工夫与气化流行的宇宙联系起来,把工夫论纳入宇宙论的视域中来,以宇宙情怀从事道德实践的工夫,使内圣之学不拘囿于心性论的领域,扩充或提升人对宇宙万物的责任意识。
[1][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3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1.
[2][明]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曾昭旭.王船山哲学[M].台北:远景出版社,1996.
[4]张学智.王夫之《庄子通》对庄子的改铸——以《人间世》为中心[J].哲学门,2003(4):90.
[5]邓联合.庄生非知道者——王船山庄学思想的另一面相 [J].文史哲,2014(4):65-73.
[6][明]王夫之.思问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7][明]王夫之.尚书引义[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萧汉明.“庄生之说可因以通君子之道”——论王夫之的《庄子解》与《庄子通》[J].中国哲学史,2004(1):68-74.
[9]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0]严寿澂.近世中国学术思想抉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1]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精神 [M].北京:三联书店,2010.
[12][明]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6册 [M].长沙:岳麓书社,1996:1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