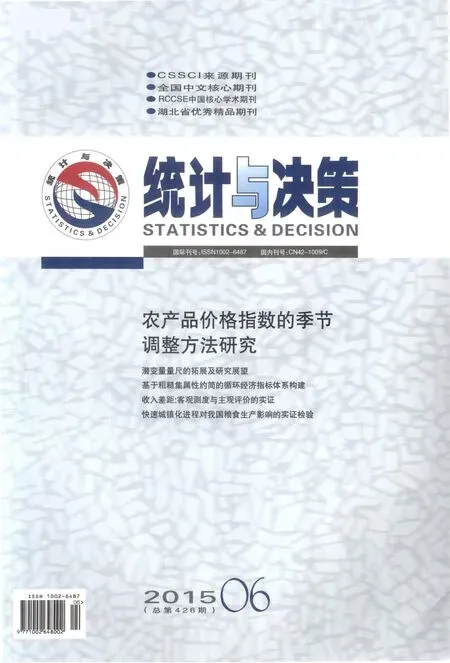快速城镇化进程对我国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检验
陈 欣,吴佩林
(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0)
1 问题的提出
中国正经历快速城镇化发展阶段,伴随快速城镇化而来的城镇建成区扩展、非农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和农业水资源占用、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农村劳动力数量减少和素质下降等因素,是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严峻挑战。2012年尽管我国粮食产量达到58957万吨,实现了历史上罕见的“九连增”,但全年粮食进口超过了7000万吨,是历史上粮食进口量最多的一年,如果算上大豆,粮食自给率已经不足90%,粮食安全问题依然严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L.Brown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他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农民将失去大量土地和水资源,粮食产量下降;而居民生产和生活的粮食需求则大幅度增长;中国必将出现粮食短缺。F.Christiansen则认为,虽然中国粮食产量最近几年有所上升,但人均粮食产量和消费量相对较低,工业化和城镇化、耕地流失、农业劳动力减少等是中国粮食生产能力和产量继续增长的严重障碍。国内学者研究多关注于城镇化进程、趋势,城镇化进程对耕地面积、水资源、农业劳动力等单一因素影响,以及粮食安全评价指标的确定等。人口学、城市地理学和资源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对于城镇化及其人口、资源、环境响应有较深入的探讨,但进一步延伸至粮食生产领域的研究较少;农学、经济学和农业产业管理研究者则侧重于对粮食生产潜力、供需平衡、市场调控、农户行为、农业经济政策的分析,通常与快速城镇化背景的联系不足;把城镇化发展与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作为一个整体,探讨城镇化进程对农业生产投入要素的作用机制进而分析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影响,既有利于防止城镇化冒进式发展,也有可能提供确保粮食安全的有效建议。
2 城镇化发展对粮食生产作用机制分析
城镇化发展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到粮食生产,一方面从供给的角度来讲,城镇化进程会对粮食生产的若干投入要素如耕地面积、劳动力、农业用水等产生影响,继而影响到粮食产量;另一方面,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膳食结构发生变化,对粮食的需求也产生影响。
2.1 城镇化发展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定性分析
(1)城区面积挤占耕地面积。
土地资源是农业生产的最主要载体,耕地的数量与质量是农业生产得以保证的基本条件。1997~2006年,伴随着超过3%的城镇化增长速度,我国耕地面积快速下降,由129903.1千公顷一度减少至121775.9千公顷。2009年国土资源部提出了以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基本思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耕地面积有所增加,但是许多地方新增耕地的质量却难以保证,“劣地换良田”的现象时有发生。
(2)农业劳动力转移迅速,农村“空心化”问题凸显。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大量青壮年涌入城市工作,农业劳动力数量及比重迅速下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对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的全面实地调查显示:3/4的村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正在逐步向供不应求转变。而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来看,九十年代初期,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接近4亿人,2011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仅有2.65亿,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亿,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已从九十年代的50%左右下降至35%左右。伴随着农业劳动力的短缺还存在农业劳动力的结构失衡,多数青壮年男性外出打工,老人、儿童、女性留守村中,粮食生产难以实现大规模机械化作业,高科技成果难以转化。
(3)灌溉用水短缺,水资源污染严重。
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水平的1/4,属于中度缺水国家,在一些省份,如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等人均水资源量甚至低于5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地区。快速城镇化进程带来城镇用水量增加,特别是生活用水量增加迅速。在水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先要满足生活和工业生产的用水需要,而后考虑农业用水,城镇用水挤占农业用水的现象目前已十分普遍,干旱缺水已成为我国农业稳定发展和粮食安全供给的主要制约因素。随着水资源紧张态势的加剧,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多地区形成了大面积的地下水沉降漏斗区,农业灌溉难度加大,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与此同时,水污染形势不容乐观,随着人口不断增长、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废污水的排放量急剧增长,2012年我国废水排放总量达到684.7亿吨,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
(4)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收入的增加,居民膳食结构发生了一定变化,肉、蛋、奶的消费比重上升而粮食的直接消费比重下降,面对农产品市场需求结构的调整,农民选择低附加值粮食生产的意愿降低。种植业在大农业(含农、林、牧、副、渔)中的比重有所下降,2012年这一比例仅为52.4%,比90年代初期下降了大约10个百分点。
2.2 多维中介变量模型
从定性分析可以发现,快速城镇化进程可能通过对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农业用水、农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我国的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因此可以考虑将城镇化进程作为自变量、将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农业用水和农业结构作为中介变量,将粮食生产作为因变量构建多维中介变量模型,进一步判断这些可能影响的显著性并定量的刻画影响程度。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城镇化率、第一产业年底就业人数、种植业占大农业的比重、粮食产量分别作为城镇化进程、农业劳动力、农业结构和粮食生产的衡量指标(图1)。

图1 城镇化进程对粮食生产的多维中介变量模型
变量定义如下:
x-城镇化率
m1-耕地面积
m2-第一产业年底就业人数
m3-农业用水量
m4-种植业占大农业比重
y-粮食产量
2.3 数据来源与研究假设
样本选择期间为1997~2012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水资源公报》、《新中国农业60年统计资料》、《中国国土资源公报》等统计资料,详细数据如表1所示。

表1 1997~2012中国城镇化及粮食生产数据
基于本文构建的多维中介变量模型,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城镇化率的提高会使得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农业用水量、种植业在大农业中的比重减少。
H2: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农业用水量、种植业在大农业中的比重会对粮食产量造成影响。
H3: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农业用水量、种植业在大农业中的比重对城镇化率与粮食产量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
2.4 定量分析结果
2.4.1 描述性统计
表2中列示了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结果表明城镇化率与粮食产量显著相关(B=0.663),第一产业就业人数、耕地面积、种植结构与城镇化率显著相关,而在定性分析中可能会对粮食产量形成影响的四项因素中仅有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与粮食产量显著相关(B=-0.898)。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
2.4.2 多重中介变量模型检验
在PASW软件中运行indirect.sps脚本,以对图2中构建的多维中介变量模型进行检验。总效应、直接效应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
(1)总效应和直接效应的检验结果满足中介效应模型的基本条件,模型总体显著,拟合优度R2达到0.9385。
(2)快速城镇化进程使得耕地面积、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种植业比重显著下降,但对农业用水的影响在95%的置信水平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3)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来看,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是影响粮食产量的最重要因素,其余三个变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4)快速城镇化进程主要通过对农业劳动力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到粮食产出,农业劳动力是影响粮食产出的显著中介变量。
借助多维中介变量模型进行的定量分析结果并未完全验证之前的定性分析,非常可能的原因是文中考虑的耕地面积、农业用水与农业结构并不是对农业产出带来直接影响的显著因素。譬如农业播种面积相比较耕地面积会更加显著的影响粮食产出,而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节水农业的发展,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得以改善。在本文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中也曾发现(陈欣,吴佩林,2013),近阶段山东省粮食产量连续十年增长的主导因素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持续改善,主要包括农机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化肥使用折纯量、农村用电量及支农支出的有效保障。而化肥使用量增速过快、复种指数偏低等制约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粮食持续增产的可能性。
3 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的建议
(1)避免城镇化的“冒进式”发展。
从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城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城镇化需要工业化的带动,同时需要有稳定的农业予以支撑。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难以实现城镇的稳定和繁荣。追求城镇扩张扩容,甚至将设定的城镇化率作为既定的发展目标,盲目地追求城镇化发展速度不仅不利于产业结构的综合调整,由此带来的空间失衡,对耕地的恣意占用更会给我国的粮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
(2)努力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供给。
农业劳动力是农业生产中人的因素,也是影响农业生产的最重要因素。而在当前环境下要想方设法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供给,一方面要重视城乡的均衡发展,努力减少城乡差距,让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回流农村,让他们有机会在自己的家乡有田可种、乐于种田。另一方面也可以考虑适度放松农村的生育政策。
(3)保障耕地面积,提高复种指数。
耕地面积是粮食生产的基本保障,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优质耕地流失较快。应尽可能保障现有耕地面积,挖掘潜在耕地并保证耕地质量。在耕地面积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让农村留住人才,让种田者看到实实在在的效益,通过间作、套作,或结合本地气候条件与市场需求,合理安排茬口衔接,尽可能提高土地复种指数,加强土地的充分利用。
[1]Brown L R.Who will feed China?: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M].WW Norton&Company,1995.
[2]Christiansen F.Food Security,Urbanization and Social Stability in China[J].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2009,9(4).
[3]Li C X,Zhang Y L.Analysis on Stability Factors of Grain Price in China[J].Journal of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English Edition),2012,19(3).
[4]Siciliano G.Urbanization Strategies,Rural Development and Land Use Changes in China:A Multiple-level Integrated Assessment[J].Land Use Policy,2012,29(1).
[5]郭剑雄.城市化与粮食安全目标间的协调[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25(4).
[6]王济民,肖红波.我国粮食八年增产的性质与前景[J].农业经济问题,2013,(2).
[7]周靖祥.发展陷阱:城镇化建设何去何从[J].科学发展,2013,(3).
[8]陈欣,吴佩林.山东省粮食产量连续十年增长的保障因素分析[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