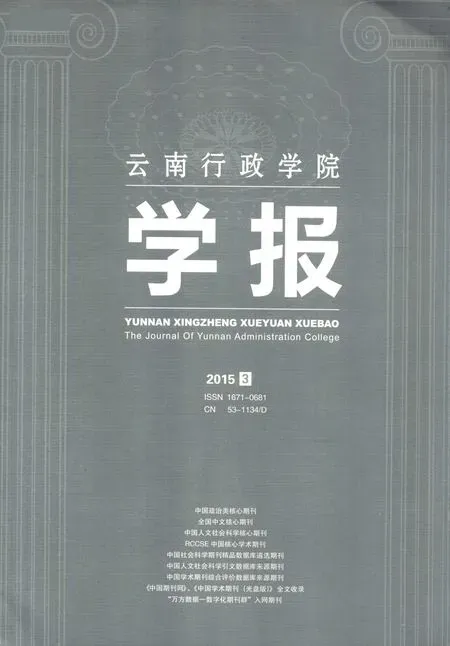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批判
唐立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北京邮编,100089)
汉娜·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批判
唐立新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北京邮编,100089)
汉娜·阿伦特以一个政治学学者的身份审视极权主义和反犹主义。她从极权主义的结构和起因来批判极权主义,指出极权主义是恐怖与意识形态共同推动的野蛮宰制,精英﹑暴徒与群氓组成其基本结构。她从政治—经济而不是历史—文化的角度批判反犹主义,认为反犹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同时,她认为犹太组织对纳粹屠犹同样负有责任。她站在中立的立场解剖分析艾希曼个案来阐述自己对反犹主义的独特理解。
极权主义;反犹主义;恐怖与意识形态;帝国主义
汉娜·阿伦特是美国著名的犹太政治学学者。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她师出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阿伦特曾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1933年阿伦特流亡巴黎,随着二战爆发,她不得不离开法国。1941年,在美国外交官的帮助下,阿伦特前往美国。阿伦特抵达美国后,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也做过出版社的编辑。1950年,阿伦特成为美国公民。1952年阿伦特担任“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50年代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几个大学里担任教职并陆续出版了她的主要著作,1959年她被普林斯顿大学任命为教授。作为杰出的政治学学者,阿伦特对历史与现实进行了诸多的反思和批判。阿伦特自身作为犹太人的各种不幸的经历,对二战和大屠杀的亲身体验,使得她不得不思考“我们时代的重负。”面对“重负”,“既不否认它的存在,也毫不怯懦地屈服于它的沉重,简言之,领会就意味着未经准备地﹑专心致志地直面现实和抵抗现实。”
一、对极权主义的批判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理论构成了理解西方现代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视角。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则是源于现实的体察。正如汉斯·摩根索指出:“她(阿伦特)是第一个参透法西斯的人。数年之后,教授们才纷纷进入她开创的领域来阐述细节。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阿伦特几乎堪与修西底德相比。”纳粹统治和大屠杀是阿伦特有着切肤之痛的政治记忆,阿伦特深谙这场政治灾难的深重和残酷。她理所当然地称之为“极权主义”。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是现代西方社会一条最具毁灭性的道路。因此,阿伦特全力加以揭露极权主义,反对乐观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理念。阿伦特于1951年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年再出修订版,阿伦特增加了一篇《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的文章,分析极权主义跟过去的专制政体在本质上的差异。人类崇尚的理性主义为特点的现代性为什么会衍生出极权主义,这显然是阿伦特重点思考的问题。阿伦特对现代性的批判首当其冲体现在对现代极权主义的批判。她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阿伦特不是要对极权主义进行经验型的描述,也不是对极权主义进行一般性的批判,而是要挖掘极权主义的原始起因和深层结构。
理性主义主导的政治现代性发展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极端形式——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则表征着西方现代性的衰落和崩溃。极权主义的出现,也是人类文明的一场大灾难。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并不特指野蛮的政权,而是意味着某种更新更危险的东西。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之新并不在于它造成的痛苦,也不在于戕害了多少人;而是在于它使人性处于危险当中。很显然,极权主义就是要毁灭人性。毁灭人性并不等于从肉体上毁灭人。毁灭人性远比杀人要艰难。极权主义相信自己是遵循自然和历史的法则的,而且必须强制人类执行这些法则。统治者执行这些自然和历史的法则,谈不上政治的正当性,只是无条件地执行。那么,这些法则的执行靠的是什么样强制的手段呢?极权主义有两个法宝:恐怖和意识形态。
恐怖只是一种手段。恐怖的主要目的不是毁灭单个的人,而是要取消人的个性,失去作为个体人的基本属性,失去自主行为和自主思考的能力,成为一个整齐划一的人类的样品。恐怖通过有步骤的行动来达到上述目的。首先,恐怖首先通过国家命令和成文法取消人的公民权和基本人权,再从道德层面上剥脱人的基本道德良心,最后再诉诸无情的杀戮。这种剥夺与杀戮,总体上传递这样一个观念:在极权主义的制度安排下,诸多的人都是多余的,多余的人留有何用?因此,屠戮他们也是理所当然的。
极权主义的另一个有力武器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一旦被极权主义掌握,便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助推器。意识形态一旦掌握在极权主义者手里,就成了一切政治行为的原动力。意识形态比恐怖更加有力地为极权主义服务,因为它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意识形态无所不能,“极权主义宣传之所以需要在大众中反复不断地进行,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内容原本便是虚构的,非事实、非经验的;但是无庸置疑的是,某些观念通过逻辑推理,能够产生长期不变性,也可称为‘彻底性’。阿伦特认为群众由于缺乏自由交流的空间,已然丧失由常识所提供的现实感,极权主义宣传正好利用逻辑演绎的强制性,以恐怖的力量,为他们提供现实感的另一种代用品——‘科学’的谎言。如果说在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需要和恐怖相互为用的话,那么,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宣传便为灌输所代替了”。极权主义者采用首尾一贯的逻辑演绎自己的意识形态,宣播鼓吹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对人类整体发展做出全盘的解释,同时厘定人类的终极目的,乃实现无阶级社会或纯粹人种的乌托邦。极权主义靠的是宣传,它开动一切国家机器和可能的形式,甚至精英领袖们也赤膊上阵来宣传人种理论和扩张主义。极权主义宣传的效果可以颠倒黑白,混淆真伪,老百姓对它莫辨是非且如醉如痴。因此,意识形态虽然不只属于极权主义的宣传工具,但一旦与极权主义嫁接,它的威力就无比强大。
总之,极权主义借助恐怖和意识形态两个有力的工具,实现了对人性的毁灭。人在极权体制下,消灭了思想和人性,对统治者惟命是从。人被原子化﹑平面化,整齐划一归于统治者的意图。
那么,极权主义是怎样的一种内在的操作机制呢?阿伦特认为,从本质上讲,极权主义运动是一种“群氓”运动。“群氓”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术语,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也是阶级解体的产物,有着一定的“阶级基础”。“群氓”并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有着不同诉求的人民群众的集合。“群氓”有着整齐划一的思想,毫无异议地被原子化和平面化。“群氓”是相对于统治阶级而言的,统治阶级绝对领导和左右“群氓”,“群氓”对统治阶级的领袖绝对服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多余的资本,也产生了“多余的人”。他们在丧失现实感,也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客观正确的判断,所以极易被极权势力所支配。
极权主义的组织结构也是独特的。领袖处于核心位置,精英﹑暴徒和群氓众星拱月,位于外围,层层紧扣,结构如蛛网,把忠诚和服从辐射至核心之上。这种结构有一个特点,各个层面彼此联系,又彼此分离,“极权主义通过防止组织中的各个层面了解事实真相的做法来建立和展开它的虚构。运动中的每一个层面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紧挨它的较低层面总是将虚构视为现实,与此同时还防止较高的层面接触事实。”
极权主义的有效组织是党国合一。党国合一取消法制,以领袖的意志为国家意志,一人掌控天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加上恐怖和宣传,国家的暴力特征得到进一步加强,最后完全蜕变为“警察国家”。极权主义治下的人民,完全丧失了自由意志,灭绝了一切可为的自由创造。
另外,使极权主义发酵的另外一种思潮就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不同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强调血统的高贵与低贱,而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内各个成员的平等。维系种族主义的是血统,当然这种血统高低的论调完全是种族主义者自己臆造出来的。民族主义是以内在的文化和经济关系来维系的。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民族主义赖以存在的民族国家消失,民族主义式微。因此,种族主义的论调沉渣泛起。极权主义接受种族主义理论,将人分为“优等”和“劣等”,不但分门别类,还义无反顾地屠杀“劣等”民族,剥夺“劣等民族”的生存权。种族主义在极权主义的官僚体制的操纵下,共同摧毁了普遍人性和普遍人权。
二、对反犹主义的批判
作为一位犹太人,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理论建构就是从分析反犹主义开始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一部分就是《反犹主义》。究其实,极权主义的产生也是从反犹主义开始的。反犹主义在阿伦特的眼中,是一个政治经济现象,而不是宗教文化现象。她认为,反犹主义只有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通过种族范畴,而非通过宗教信仰范畴进行区分时才开始出现。同时,反犹主义不是可以简单解释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反犹主义,只有理解“社会的差异演变为政治论争”才能理解反犹主义。
阿伦特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帝国主义的形成来解释反犹主义。阿伦特认为,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发挥了犹太人经商理财的天赋。犹太人在欧洲民族国家里合纵连横,扮演着金融掮客的角色,在国家金融关系当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甚至稳定了国家间的关系。因此,犹太人的理财天赋得到了民族国家的赏识和保护。况且,在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是平等的,各民族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因此,犹太人虽然没有完全融入到民族国家的社会当中,但他们至少是安全的。但是,一俟帝国主义的产生,犹太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失去了他们在近代西方国家经济和政治事务当中的独特作用。“帝国主义扩张,以及暴力手段的日渐完善和国家对他们的绝对垄断,使得国家成了一个有趣的商业事业。这意味着犹太人渐渐自动失去了他们的独特的地位。”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的反犹主义的必然性。“一方面,巨量的金融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非常广泛而稠密的关系和联系网,这个密网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和业主,而且控制了最小的资本家和业主;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金融家集团同其他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分割世界和统治其他国家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结果,就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尽量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垄断了民族国家的金融业,犹太人的金融行为是对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拿犹太人开刀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他们不识时务,逆潮流而上,破坏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和金融秩序。阿伦特注意到,“当财富与权力与国民身份相分离时,憎恨就开始产生了。”更何况,“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统治的趋向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也变本加厉了。”
作为一个犹太人,阿伦特对反犹主义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她不仅对反犹主义有着深刻的洞悉,还展开对反犹主义的批判。她不是站在种族的立场上,而是站在一个公正中立的立场上来展开批判的。与批判反犹主义有着紧密联系的著作就是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阿道夫·艾希曼是屠杀犹太人的执行者,战后逃往阿根廷,后来被以色列特工抓获,1961年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对其进行刑事审判。阿伦特冷静旁察,最终以此个案写成了这本书。
根据艾希曼在法庭上的表现,阿伦特陷入了沉思。艾希曼显然对自己屠杀犹太人的罪行认识不清,他的辩词荒诞可笑,但并不是装糊涂。艾希曼签发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源于他对领袖的忠诚以及对职责的履行。艾希曼辩解,他是在执行任务,并没有考虑过其他东西。他像机器一般顺从、麻木地来执行上司交给他的任务。据此,阿伦特提出的一个著名的术语:“平庸的恶”,以区别于“根本的恶”。“根本的恶”是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阐释的重要概念。“根本的恶”就是取消人的差异性和复数性,使人变得整齐划一,再取消人的道德良心,毁灭人性。人因此变成多余的,完全丧失了作为主题性存在的能力和意义。极权主义是造成“根本的恶”的罪魁祸首。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中,她再次运用极权制度来分析这样一个平庸无奇的人为什么卷入罪恶渊薮而无法自拔,也就是阐释“平庸的恶”存在的理据。
艾希曼在他的辩解词中,极力说明自己是遵从上级的命令,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自己的职责。艾希曼的所有辩解词表明,他是一位忠诚的下属﹑合格的党员﹑慈爱的父亲。他没有太大的野心,他只是对自己的职位晋升有所兴趣而已。他平庸无奇,能力平平,充其量就是一架机器而已。阿伦特说:“艾希曼既不是埃古,也不是麦克白,而且也不像理查三世那样‘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恐怕除了对自己的晋升非常热心外,根本没有其他的行为动机。这种热心的程度本身也绝不是犯罪……他不是愚蠢,而是完全的无思想——这绝不等同于愚蠢,无思想使得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这就是平庸……这种脱离现实与无思想能导致比内在与人类中所有恶的本能更大的浩劫。事实上正是我们在耶路撒冷所能得到的教训。”
阿伦特她认为艾希曼只是制度的杀人者,艾希曼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他是一个“无思”的人,缺乏判断是非,辨别善恶的能力,失去了行为选择的道德标准。正是由于艾希曼的“平庸”,才使得他作恶而不自知。阿伦特创造性地把犯罪与“平庸”协同起来,并且断言平庸的恶可以毁灭世界。事实上,正是像艾希曼这样“无思”人太多,所以他们都跟随着“领袖”走到一起来了,他们表现出来的无知和麻木,正是“无思”的结果。阿伦特看来,由于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维,才会有纳粹上台,才会有那么多人投身纳粹运动。这种“无思”的盲从状态才是纳粹犯下滔天罪行的主要原因。
阿伦特之所以是伟大的政治学家,在于她能够跳出狭隘的种族观念,对极权主义和反犹主义有自己清醒而独到的理解,这是难能可贵的学术品质。阿伦特憎恨纳粹,揭露他们的罪恶,但她是带着理性的思考的。她认为审判艾希曼的目的是表现正义,不是为了简单的“复仇”和“雪耻”。阿伦特还认为艾克曼犯下的是“反人类罪”,而不是“反犹太人罪”。她还认为,审判艾希曼在法理和程序上都有问题。她认为,艾希曼应交给国际法庭审判,而不是由以色列来审判。她这些言论,与以色列审判艾希曼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她遭到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攻击,甚至给她扣上了“犹奸”的帽子。
更为大胆的是,阿伦特对犹太组织在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过程中的协同和助虐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她指出犹太人委员会,犹太组织的领导对大屠杀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阿伦特揭露犹太人委员会给纳粹提供“遣送名单”,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行。她指出,犹太人委员会在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迫害的过程中无所作为,也是一种事实。纳粹有罪,因为它是施害者,犹太人领导和犹太组织同样有罪,因为他们几乎是纳粹的“同谋”。她还指出,犹太领导人很多都跟纳粹进行过实质性的合作。她断言,没有犹太领导人的积极配合,大屠杀的规模必然要小很多。“无论由犹太人居住在哪里,总有一些被认可的犹太领导人,这些领导阶层——几乎毫无例外地……与纳粹合作。整体的事实是,如果犹太人人民实际上是没有组织和没有领导的,无疑会产生一片混乱和大量的不幸,但受害的总数很难达到四百五十万至六百万之间。”
[1]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
[2]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World,Inc.,1968.viii.
[3][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阿伦特为什么重要[M].刘北成,刘小鸥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
[4]Margaret Canovan,Hannah Arendt: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2,23.
[5]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court,Braceand World,Inc.,1968,pp.156—157.
[6]林贤治.沉思与反抗———纪念汉娜·阿伦特诞辰[M].www. baidu.com.
[7]川崎修.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M].斯日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8][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阿伦特[M].王永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
[9][苏]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M].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0]Dana Villa,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32.
(责任编辑马光选)
D512
A
1671-0681(2015)03-0042-04
唐立新(1974-),男,湖南平江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在站博士后,深圳大学副教授。
2015-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