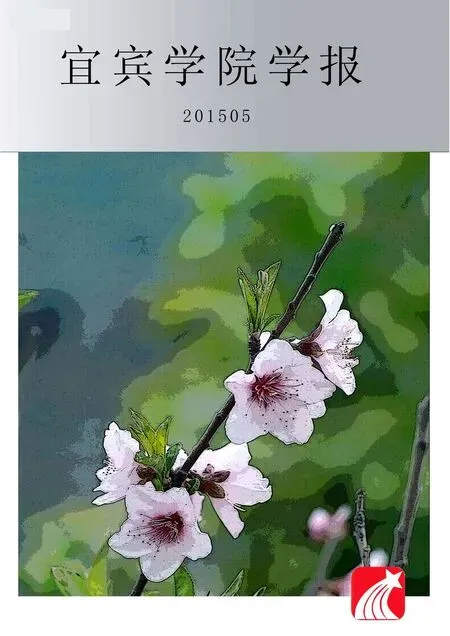钱穆的朱子学研究
陈 勇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44)
钱穆对宋明理学的研究用力甚勤,著有《王守仁》(1933)、《宋明理学概述》(1953)、《朱子新学案》(1971)、《宋代理学三书随劄》(1983)等专书,尤其是晚年所著煌煌五大册的“尊朱”巨著《朱子新学案》,对朱子的思想、学术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现,成为今人研究朱子学不可绕开的著作。
一 钱穆早年的朱子学研究
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孔子与朱熹无疑是两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师级人物。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朱子则集北宋以来理学和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使儒学重获生机,益臻光昌。钱穆对孔子、朱熹推崇备至。他说: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1]1
关于孔子研究,钱穆写有《论语文解》《论语要略》《孔子与论语》《孔子传》《论语新解》等书;对于朱子研究,则是他晚年主要从事的一项工作。钱穆在一篇关于他辞职的文章中说,他离开新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卸下行政担子,潜心书册,立志在三五年时间里写出一部有关朱子学术思想方面的著作。他在致杨联陞的信中也道出了晚年潜心朱子研究的原因:“自朱子以来逾七百年,而学者困于门户之见,非争朱陆,即争汉宋,于朱子学术思想之‘真’与‘全’则绝少有人加以探讨。黄全《学案》,疏略已甚,而朱子一案则更甚。王白田(懋竑)穷一生之力,为朱子作《年谱》,钩稽考索虽勤,而识力不足以副。其着眼处,几乎只在是朱非陆,而不知朱子遇象山时其学术思想大体固已树立,今专着意在反陆一面,则何从得朱子之真与全。其他各有陈述,各有发明。要之,亦无以胜过《学案》与《年谱》之上者。穆有意以三年精力为朱子作一《新学案》,不仅专为朱子,亦为中国理学史与经学史在其大关键处有所阐述”。[2]219
1966年1月,在吉隆坡马大讲学的钱穆,书写了“晚学得新知,汇百川以归海;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一春联,集中表达了他晚年以“尊朱”为其一生学术归趋的愿望。钱穆晚年“综六艺以尊朱”,《朱子新学案》便是他晚年研朱的杰作。当然,他读朱子之书,治朱子之学,并不始于这一时期。钱穆在早年著作《国学概论》第八章《宋明理学》中,对朱子之学的精义就多有阐述。1945年,在成都华西大学任教的钱穆完成《朱子学术述评》—文,后来发表在《思想与时代》上,这是他早年研究朱子学术思想的用力之作。该文从学术史层面着眼立论,分析了朱子的三大贡献。
其一,以周张二程直接孟子,创立了儒家新道统说。钱穆认为,朱子在学术思想上贡献最大、最应注意的问题,就在于他创立了儒家的新道统。道统观念,源于佛学,隋唐间台贤禅宗诸家皆有述说。韩愈《原道》,始为儒家创道统。下及北宋初期,言儒学道统,大多举孔子孟荀以及董仲舒、杨雄、王通、韩愈。惟第二期宋学,即所谓理学诸儒,颇已超越董杨王韩,并于荀卿多有不满。朱子承之,始摆脱荀卿董杨以下,而以周张二程直接孟子,开始确立新儒学的正统地位。
其二,治儒学尊《论》《孟》《学》《庸》四书。朱子于孔孟之间增入曾子、子思两传,而有孔曾思孟四书的汇集,这就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学。《论语》《孟子》素来为儒学所尊,《中庸》之书,起于秦代,其书融汇儒道思想,与《易·系辞传》相先后。南北朝释道思想盛行,《中庸》《易系》即为时所重。唐人李翱《复性书》开宋代理学之先河,其篇中理论即据《中庸》。北宋初期,诸儒皆重此书,张载初谒范仲淹,即劝其读《中庸》。《大学》则由二程始特推尊,所以程门专以《大学》《西铭》开示学者。至朱子,遂汇《学》《庸》《论》《孟》成一系统,并以毕生精力为《论》《孟》作集注,为《学》《庸》作章句。元明以来,迄于清末七百年,朝廷取士大体以朱注四书为圭臬,学者论学也以朱注四书为准绳。钱穆认为朱子治四书,如同孔子修六经。孔子修六经,未必真有其事,而朱注四书影响之大,则无与伦比。
其三,对经学地位的新估定。先秦儒学虽原本经术,但儒学与经学毕竟不同。两汉博士始以经学代替儒学,此一风气,直到唐人未能改变。宋儒开始逐渐从经学中摆脱出来复兴儒学,朱子正是这一事业的继承者和完成者。钱穆称:“朱子的《周易本义》,说《易》为卜筮书,较之王辅嗣、程伊川注《易》,更多开明。他的《诗集传》,全用后代文学集部眼光来解说《诗经》,更为脱尽前人窠臼。他对《尚书》,早已疑及今古文之不同,远开将来清儒门路。他亦认《尚书》为一部古史,其间有关上古天文、历法、地理、制度以及种种名物,全需专家知识来整理,所以他把《书集传》的工作让他门人蔡沈去完成。朱子对于孔子《春秋》也只认为是一部通史。史学应该注重近代,在孔子时修史,自然偏重春秋时代,在后世则不应仍是看重春秋。他以司马光《通鉴》来代替《春秋》,而他有意来写一部《纲目》。他把司马光《通鉴》当作《左传》,自己的《纲目》则是一部新《春秋》,这又是一种极大胆而极开明的见解。他对于《礼》的—部分,也认为古礼不能行于后代,而制礼作乐则不同社会私人事业,故他只有意写一部家礼。这样,在他手里,把自汉历唐,对古代经学的尊严性与神秘性全剥夺了,而重新还他们以应得之地位。后来阳明六经皆史的理论,其实在朱子已透切发挥了。从此以下,四子书占据上风,五经退居下风,儒学重新从经学中脱出。”[3]161-162
钱穆认为,朱子思想的最大贡献,还不重在他自己个人的创辟,而在于他能把自己理想中的儒学传统,上自五经四书,下及宋代周张二程,完全融成一气,互相发明,归之条贯。他在中国思想史里,独尊儒家。在儒家中,又制成一系统,把其他系统下的各时代各家派,一切异说,融会贯通,调和—致。此非朱子气魄大,胸襟宽,条理细密,而又局度开张,不能有此成就。钱穆认为,朱子思想从表面上看似乎多承袭、少创见,其实朱子所创见,都已融化在承袭中,而不见其痕迹,这正是朱子思想之伟大处。
传统的看法认为,朱子只言理,不讲心。钱穆不同意这一说法。1948年他写成《朱子心学略》一文,刊在徐复观、张丕介主办的《学原》杂志上。他在文中指出:“朱子未尝外心言理,亦未尝外心言性,其《文集》、《语类》,言心者极多,并极精邃。有极近陆王者,有可以矫陆王之偏失者。不通朱子之心学,则无以明朱学之大全,亦无以见朱陆异同之真际。”[3]131钱穆在文章结尾中总结道:“我常说,一部中国中古时期的思想史,直从隋唐天台禅宗,下迄明代末年,竟可说是一部心理学史,问题都着眼在人的心理上。只有朱子,把人心分析得最细,认识得最真。一切心学的精彩处,朱子都有。一切心学流弊,朱子都免。识心之深,殆无超朱子之右者。”[3]157
关于濂溪(周敦颐)、二程、朱子的学术师承,钱穆在1948年初写成的《周程朱子学脉论》中多有阐述。文章指出,朱子推崇周敦颐,奉他为理学开山,故对其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作注解,大加阐发。二程早年受周氏启发,其学术实师承濂溪。朱子的学术则直接承周程而来。比如朱子的理气论,乃直接综合周程而成。所以,周程朱子四家虽有种种异同出入,但是在大节目上,其主要血脉处,则—气相承,形成了宋代理学上的正统地位。
钱穆认为朱子之学胜过周程处,主要在于他能融贯周程学术而上通孔孟。关于此点,他后来撰文作了重要补充。他说自孔子下传孟荀有儒家,自孔子上溯周公有五经,汉代罢黜百家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孟子博士亦遭罢黜,孔子《论语》,仅为小学教科书。因此,汉儒之微言大义,通经致用,着眼点重在政治与历史,以上跨暴秦,回复三代。孔子素王,为汉制法,所争在上层政治制度。魏晋以下,王统中辍。庄老代兴,随之佛教东来,社会下层人生的领导权,乃操于道释之手。唐代恢复两汉之统治,惟道统仍在释而不在儒。中经五代丧乱,宋儒所求恢复者,不仅在汉唐之统治,更主要的在孔子以下儒学之道统。濂溪所重,在于如何由道释而返之儒,故其注意力偏于现实人生方面。二程之学承自周氏,也在人生问题上作研讨。自濂溪二程以来,人人尊孔子,排释老,以为新人生蕲向在此。朱子则移新儒学之重于《论》《孟》,为《论语》《孟子》作集注,又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以四书的结集取代汉唐的五经,而成为后代儒者人人之必读书。所以朱子以濂溪二程之新儒学,直接回溯先秦儒,一以孔子为宗而完成一大系统,而朱子也因此成为中国儒学史上继孔子而起的集大成者。
钱穆在20世纪50年代还写有《朱熹学述》《朱子读书法》《朱子与校勘学》等文,在新亚文化讲座中还作过“朱子的思想”“孔孟与程朱”的学术演讲,俱载《新亚文化讲座录》中。以后续写有《记朱子论当时学弊》《朱子从游延平始末》《朱子泛论心地工夫》《谈朱子的〈论语集注〉》《朱子的史学》《朱子之辨伪学》等文。上述诸文的观点皆采入到他后来所写的《朱子新学案》一书中。可以说,钱穆早年的朱子学研究,为他晚年撰写《朱子新学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忘年为述古,综六艺以尊朱”:《朱子新学案》的结撰
钱穆离开新亚后,潜心朱子学研究,《朱子新学案》便是他晚年精心结撰的以“尊朱”为一生学术归宿的巨著。
钱穆认为,治朱子学的基本方法是“就朱子原书叙述朱子”。所以,他研究朱子学的第一步就是从头到尾认真研读朱子的著作。朱子书可分为二大类,一为自著书,最为后世传诵的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近思录》等,一为《文集》《语类》,两书卷帙浩繁,合为280卷。钱穆特别重视阅读《文集》《语类》,他说:
若专读其著述书,而不读其《文集》、《语类》,则如朱子教人常云吃馒头仅撮一尖,终不得馒头之真味。本人为《朱子新学案》,于其《文集》、《语类》二百八十卷书,逐篇逐条均经细读,乃见朱子著述各书,其精义所在,其余义所及,多为只读各书所未易寻索者。又见朱子为学之会通处,有在其各著述之上之外者。乃知不读《文集》、《语类》,即无以通朱子之学。[1]154-155
在钱穆看来,《文集》《语类》中的语句、画面、场景都是朱子思想的生动体现,惟有把握、理解《文集》《语类》,才能对朱子思想、学术有真实的认识和感受。钱穆第一次通读《朱子语类》是在抗战时期的四川,当时他在华西大学任教,因胃病大发,卧床达数月。1944年春夏,他在华西坝居处楼廊中置一沙发,白天卧其上,细读《朱子语类》。暑假移居灌县灵岩山寺,向寺中方丈借用《指月录》全部。数月内,一气连读《朱子语类》及《指月录》两书,“对唐代禅宗终于转归宋明理学一演变,获有稍深之认识。”[4]251
1964年7月,钱穆辞新亚书院院长职后,在青山湾避暑楼中,又将朱子《文集》《语类》通读一遍。此次通读用心在《文集》上,读《语类》费时仅2月。1965年7月,钱穆去马来西亚大学讲学,课暇之时,“尽日夜专读《朱子语类》”,这是他继成都华西坝病中通读全书后的第三次。当年12月2日,钱穆在致香港《人生》杂志主编王道的一封信中述说了他当时读此书的兴奋心情:
(到马大后)所看惟《朱子语类》一部,绝不旁及,初看每日只数条至十数条而止,后来逐渐增多至每日数十条,然亦绝少以一日终一卷。自七月下旬以来,已逾四月,所读《语类》逾九十卷,所剩不足四十卷,预计在明年春返港以前,当可全部阅毕。此为穆看《朱子语类》之第三遍。第一遍通体阅读,乃抗战时期在成都……第二遍在去年辞去新亚职务以后。此次第三遍,最为沉潜,反复细嚼缓咽,预计当以八阅月竣工,而自问所得亦以此次为最多最深而最大。初读第一遍时,重在通体循览;去年读第二遍,则重在学术方面;此次第三遍,则侧重在义理精微及其全部思想之体系与组织。有一向素不注意而今始知其意义之重大者;有一向误认当如此解说,今始知其不然,必如彼说之而始合者;有一向逐项分别认取,以为各不相涉,今始悟其内在相通,有甚深关联者。此数月来,不仅在穆个人自认为增长了不少新知,而凡所窥及,亦有朱子身后七百年,不论述朱与攻朱,乃亦从未提醒到此者。当其骤获一新知,往往惊喜交集,累日自奋兴,然力戒不捉笔为文,因此仍只有藏纳胸中,积而久之,新知络绎而又渐相融贯,汇为一体,初视期以为新鲜奇特之处,至是莫不一一转归于平实,新奇之感日褪,而深厚之味日增。自念明春返港,获逐夙愿,闭户不出,专一以撰述《新学案》为事,竭三年之力,傥能完成此书,一则稍赎十数年学殖荒落之内疚,一则庶期于吾中华儒学之传统,朱子之真面目与真体系,薄能有所贡献。[2]294-295
钱穆把《文集》《语类》常置案头,时备研寻。他边读书边摘录书中要旨,并加以分类,共得三千余条。这三千余条涉及极广,几乎包括朱子学的各个方面,这为他正式撰写《新学案》打下了札实的材料基础。在马大讲学期间,钱穆还撰成《朱子早年思想考》一篇,为他正式撰述《新学案》的第一篇文章。所以,1964-1966年是钱穆撰写《朱子新学案》的准备阶段。钱氏自言,“其先读《大全集》,读《语类》,抄撮笔记,作准备工夫,亦历二年”。[4]355
1966年2月,钱穆不适应南洋湿热气候提前返港,在沙田寓所里正式开始了《朱子新学案》的撰写。他主要就前两年所读《文集》《语类》录下笔记,分专题阐述。钱氏此项研究得到了哈佛燕京学社在经费上的资助。钱穆在卸下新亚校务后,曾以个人名义向哈佛燕京学社提出撰写《朱子新学案》的三年计划,希望能得到该社在经费上的补助。由于燕京学社的补助对象一向都是学术机构,不是个人,这就给该社出了一道难题。后来,在杨联陞的鼎力帮助下,才使这一破天荒的申请案得以顺利通过。所以,在撰写过程中,钱穆常与杨氏通信,报告写作进展,讨论问题。杨氏建议《新学案》除在朱子思想、学术部分用力外,还须研寻朱子学对此下的影响,得到了钱穆的部分采纳。
1967年10月,钱穆回台北定居。第二年7月,迁士林外双溪新居,在素书楼中埋首著述。至1969年11月,全稿完成。
《朱子新学案》逾百万言,为了方便读者阅读,钱穆在全稿杀青的第二年(1970年),又写《朱子学提纲》一长文冠于书首,为全书的总纲。该文不仅对书中的主要论点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和提炼,而且还从整部儒学史、整部中国学术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上自孔子,下迄清末,以见朱子学术承先启后的意义和价值。杨联陞读《提纲》后赞叹不已,他私下对受业弟子余英时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像这样的《提纲》,胡适之先生恐怕是写不出来的。”[5]186
《朱子新学案》分五卷两大部。卷一、卷二为思想之部,下分理气和心性两部分。卷四、卷五为学术之部,分经、史、文学三部分。经学部分再细分为《易》《诗》《书》《春秋》《礼》《四书》诸题。又于三部外添附校勘、考据、辨伪诸篇,并游艺格物之学一篇。介于思想、学术两部分之间的为卷三,分朱子评述濂溪、横渠、二程诸篇,下逮评程门、评五峰、评浙学,又别著朱陆异同三篇,辟禅学两篇等,专论朱子思想之发展及其在当时理学界中之地位。
三 对朱子思想、学术的全方位呈现
钱穆对朱子推崇备至,他眼中的朱子,不仅是北宋以来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而且也是自孔子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因此,朱子仅作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钱穆在著作中不仅叙述了朱子的哲学思想,而且从经史文学各个方面对朱子的学术成就作了全方位的展现。
(一)关于朱子的思想
钱穆认为,“叙述朱子思想,首先当提出其主要之两部分,一为其理气论,又一为其心性论。理气论略当于近人所谓之宇宙论及形上学,心性论乃由宇宙形上学落实到人生哲学上”。[1]25所以,他着重从理气论、心性论两方面来考察朱子的思想。
朱子论宇宙万物本体,必兼言理气。无理,将不能有气;但无气,亦将不见有理。所以朱熹的理气论,既不主唯心,也不主唯理,或者主理气对立,他只讲理气一体浑成。钱穆认为,在北宋理学四大家中,二程在宇宙形上学方面较少探究,周濂溪(敦颐)、张横渠(载)在此方面贡献最大。所以,朱熹只论理气,主要依据濂溪的《太极图说》,而以横渠《正蒙》副之。
朱熹的理气论虽是承继濂溪、横渠之说而来,但并不是只有因袭、继承,而无创辟。濂溪只讲太极与阴阳,此上承《易经》系辞而来,但“物物—太极”,究竟不如说物名有理更恰当。因此,朱熹以理、气两个新名词换之,讲得更为明白、确切。而横渠《正蒙》说太虚与气,还不如濂溪无极太极深切、准确,故朱子对横渠之说亦有辨证。所以钱穆认为,朱子“理气一体的宇宙观”,从理论思想上讲,实是一番创论,为“周张二程所未见”。
钱穆把朱熹的理气论与心性论联系起来考察,提出朱子思想的核心不是“理”而是“心”的观点。学术界一般认为,陆九渊讲心即理,朱熹只讲理,不讲心,故把宋代理学划分为理学与心学两大派,陆九渊是心学坚定的捍卫者,朱熹则是二程的忠实继承者。钱穆对这一传统说法作了重大修正,提出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此一观点在他1948年发表的《朱子心学略》中已有道及,在1952年出版的《中国思想史》中续有阐述。在《朱子新学案》中,他又用了差不多七、八章的篇幅,专门讨论“心”的问题,而此一问题在该书其他许多章节中也占据突出的地位。
钱穆指出,伊川言性即理,主要在于发挥孟子性善义,只就人生界立论的,而朱子则用来上通宇宙界。所以,伊川言性即理,偏重在人生界;朱子言性理,则直从宇宙界而来,此乃二人之异。就心而论,朱子论宇宙观,言理更重于气。但论人生界,则心之重要性尤过于性。因论宇宙界,只在说明此实体而落到人生界。要由人返天,使人生界与宇宙观融通为一,则更重在工夫,而工夫则全在心上用,故说心字更为重要。
钱穆认为,朱熹与陆象山在鹅湖寺进行的那场著名辩论,并不是各人在心与理之间有不同的选择,只不过是关于“心”的两种不同理解罢了。陆象山偏重在人生界,朱熹则把人生界和宇宙界二者兼顾。所以他说:“谓陆王是心学,程朱是理学,此一分别,未为恰当。若说陆王心学乃是专偏重在人生界,程朱理学则兼尊人生界与宇宙界,如此言之,庶较近实。”[1]38-39在钱穆看来,凡是陆学中合理的,朱学亦有;不合理的,朱学则免;陆学没有的,朱学亦有,故言:“朱子学可包象山,象山说却不易推到朱子。”[1]397
(二)关于朱子的经学
钱穆认为,朱子在治经学方面有突出的贡献,这集中表现在他治五经和四书学两个方面。
朱子治五经,多有创见。他不赞同伊川(程颐)以理学说《易》,认为《易经》非哲学著作,乃为卜筮之书,可谓“石破天惊”。①他用后代文学集部眼光解《诗经》,疑《诗》小序不可信,尽破毛、郑以来依据小序穿凿之说。他治《尚书》,发伏(生)、孔(安国)两家今古文之同异,疑《古文尚书》为伪作,开明清两代辨《古文尚书》之伪的先河。②不仅疑古文之伪,且言今文亦多可疑,此为明清诸儒所未能及。只是因恐推到了六经,于书经方面末加详细发挥。对于《春秋》,朱子未有撰述,认为“《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朱子于五经中特重“礼”,一生致力于《礼》的研究。他认为儒家三礼,《仪礼》是根本,《礼记》是分枝,而《周礼》是关于古代制度自成体系的专论,所以朱子生平多考礼仪文章,晚年编修礼书,耗力尤多。
钱穆对朱子治经评价甚高,认为朱子以理学大师而岿然为经学巨匠,其经学业绩,在宋元明清四朝中,无人能及。他把朱子治经与清儒治经之异作了比较,归纳出五点不同:
其一,朱子治经,分门别类,找出诸经的特殊性。清儒治经平视诸经,以为皆孔子遗书,治经重会通,力主“非通群经不足以通一经”。然无分别,亦无会通可言。
其二,朱子治经,除经之本义外,必兼罗汉唐以下迄于宋代诸家学说而会通求之,以期归于一是。清儒则重限断,先则限断以注疏,宋以下皆弃置不理会。继则以两汉为界线,对以前存而不论,其结果造成相互争门户。
其三,朱子在解经时,对不同意见如有可取之处,都加以采纳。清儒对不同意自己立场的均不加采纳,对朱子经学的独到之处,多采取回避态度。
其四,朱子说经,极多理据明备创辟之见。如以《易经》为卜筮书,孔子易与文王、周公易分别看,清儒不加引申,只依汉儒的说法。朱子辨毛序,事据详确,清儒仍有专据毛序言诗者。朱子言《尚书》有不可解,清儒乃有专据郑氏一家解尚书者。朱子分别春秋三传,言其得失,清儒则有专主公羊而排左氏,而扩大成经学上今古文之争。朱子治礼学,不忘当前,每求参酌古今而期于可行。清儒则一意考古,仅辨名物,不言应用。
其五,朱子论《尚书》,论《春秋》,每及于史,并有置史于前之意。清代史学,仅为经学附庸,治史亦只如传统,不见有大分别。
朱子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四书学可谓他全部学术的结穴。钱穆指出,自唐以前,儒者常称周公孔子,政府所立太学,必以五经为教本。《语》《孟》《学》《庸》四书并重,事始北宋,而四书之正式结集,则成于朱子。“朱子平时教人,必教其先致力于四书,而五经转非所急。故曰:‘《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其为《语》、《孟》集注,《学》、《庸》章句,乃竭毕生精力,在生平著述中最所用心。”[1]1355钱穆认为,宋代理学,本重四书过于五经,至朱子而为之发挥尽致,提高了四书在经学中的地位。此后元明两代,皆承朱子此一学风。清儒虽号称汉学,自擅以经学见长,然亦多以四书在先,五经在后,“以孔孟并称,代替周孔并称”。故云:“朱子学之有大影响于后代者,当以其所治之四书学为首,此亦无可否认之事。”[1]1356
钱穆认为,朱子治四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绾经学与理学而一之”,即是以理学与经学、考据与义理结合起来治四书。朱子以前的理学家治《论》《孟》,多以孔孟语作为开头,然后断以己意,缺乏一种经学精神,势必会使理学与儒学传统相脱节。朱子的四书学,重在就《论》《孟》本文,务求发挥其正义,力戒主观玄想。而后孔孟儒家大传统,得以奠定。这就是一种经学精神。朱子在注《大学》《中庸》章句中,不免有主观发挥,这体现了治经的理学精神。所以,朱子“绾经学与理学而—之”,从而使经学益臻邃密,理学益臻深沉,对后世影响既深且大。对此钱穆赞道:“盖自有朱子,而后使理学重复回向于经学而得相绾合。古今儒学大传统,得以复全,而理学精旨,亦因此更得洗发光昌,此惟朱子一人之功。”[1]116
(三)关于朱子的史学
钱穆认为,朱子之学,重在内外合一,本末兼尽,精粗俱举,体用皆备,故不弃百家文史之学。在史学方面,他能将训诂考据,辞章义理,兼通为一,故能道前人所未道,其训释之精,考据之密,不让清儒。故称在理学家中,“能精熟史学者,实惟朱子一人。不惟他人无可望其项背,即求其肯在史学上真实用心者,亦不多见。”[1]134-135
钱穆对朱子在史学上的贡献颇为注意,在《朱子新学案》完成以前,就写有《朱子与校勘学》《朱子的史学》《朱子之辨伪学》等文。在《朱子新学案》中,他对朱子在史学上的贡献亦详加论说,多方发掘。他认为朱子的史学,可分著史、论史、考史三项。其著史有《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伊川年谱》,对后世写史多有影响。如《通鉴纲目》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纲目体史书,《伊洛渊源录》实开后世学案体之先河,黄、全二学案,实受朱子《伊洛渊源录》体例的影响。其考史,博及古今,对天文、历法、地理、水道、形势、风土习俗、衣冠制度、花草鱼鸟等皆有所考。其考证多尚事实,不凿空言,成绩卓越。其论史主要体现在论治道、心术、人才、世风等方面。朱子论史,多折之义理。钱穆以程颐、朱子对范祖禹《唐鉴》一书的不同评价作了具体考察。
《唐鉴》是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写的一部历史评论著作。范氏生活在理学开始形成的时代,其谈论史实、褒贬人物,多受程颐等理学家的影响。史载“范淳夫(祖禹)与伊川论唐事,及为《唐鉴》,尽用先生之言。”[6]朱子在《伊洛渊源录》中引鲜于绰语也称:“《唐鉴》议论亦多资于程氏”。[7]程颐自己也说:“《唐鉴》议论,多与伊川同”。[8]所以,范氏之书多从“义理”出发评判史实,褒贬人物,深得程颐好评,称《唐鉴》“足以垂世”,“自三代以来,无此议论。”[9]朱熹对《唐鉴》论史“守经据正”“折以义理”深表赞同,他曾在比较孙甫《唐论》与范祖禹《唐鉴》时说:“孙之翰《唐论》精练,说利害如身处亲历之,但理不及《唐鉴》耳。”[10]3208但又对《唐鉴》言义理“犹未精透”也有批评。他说:“范淳夫论治道处极善,到说义理处,却有未精。”[10]3105又说:“大抵范氏为人宏博纯粹,却不会研穷透彻。如《唐鉴》,只是大体好,不甚精密。议论之间,多有说那人不尽。”[10]1132钱穆对朱子之语评道:“朱子称赞范氏《唐鉴》者亦甚至。卦向嫌其向上义理一关犹未精透。论史必本诸经术,论治道必本之理学,此乃朱子论学特见精神处。”[1]1610
(四)关于朱子的文学
钱穆认为,理学家对于文学“最所忽视”。周濂溪虽有文以载道之论,其意重道不重文。惟朱子文道并重,并能自为载记之文,把经学、文学贯通合一,理学精神亦包孕其中。在钱穆看来,朱子不仅揭文道合一之论,以文学通于经学,而且进一步以文学通于史学,重乱世之文尤过于重衰世之文,谓战国乱世之文有英伟气,非《国语》衰世之文可比。
朱子在文学上著有《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三书。关于《诗集传》,钱穆在《朱子之诗学》一节中有专门论述。他说:“盖朱子为学,博学多方。其为《诗集传》,实是兼会经学、文学、理学之三者而始有此成就。若专从经学途径,则终不免于依据毛郑,最多旁及齐鲁韩三家,不脱汉儒牢笼,如清儒之所为。若一守理学范围,又不免陷于以理说诗之病。朱子《诗集传》之所以能卓出千古,尽翻前人窠臼,无复遗恨者,盖以其得力于文学修养方面者为大。”[1]1280关于《韩文考异》,钱穆在《朱子之校勘学》中详加论说,认为该书校勘精密,识解明通,对后世影响极大,故曰:“至其晚年《韩文考异》之撰者,则为朱子平生从事校勘最大之成绩,实开出后来校勘学上无穷法门,堪称超前绝后”。[1]1740“盖自有《考异》,而韩集遂有定本可读,后人亦卒莫能超其上”。[1]143关于《楚辞集注》,钱穆在“朱学之文学”一章中加以讨论,认为朱子晚年注楚辞,与赵汝愚罢相“谪死于永”有关,但并非专为赵氏而作,著述之主要目的乃在“忧时”,故云:“今读其《楚辞集注序》,性情义理,相通兼得。尤其如放臣屏子及见古人于千载之上两节,俯仰今古,彼我死生,真如一体。就文论心,即心见道,其当时之遭遇,与其内心之所感触,而斯道即流行昭著乎其间,诚非仅止乎文章与著述而已也。”[1]1722钱穆指出,“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1]143
结语
钱穆对朱子学术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的系统研究,克服了研究者由于专业所限在治朱子学术、思想时所出现的片面性和狭隘性。钱穆从经史子集各个角度去阐发统摄朱子学术,为人们展现出了一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肖像。他晚年之所以大力表彰朱子,“综六艺以尊朱”,正是因为朱子学术有吞吐百家、汇纳众流的气魄,这与他追求的求通不尚专的学术风格有近似之处。所以钱穆晚年归宗朱子,以述朱、尊朱为其学术的最后依归,其用意就在这里。[11]195
《朱子新学案》对朱子学的宏大体系进行了系统而完整的梳理,展示了朱子在整个儒学传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开创了朱子学研究的新局面。是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杜维明说:“钱穆在阐释朱熹之学上确实作出了重大贡献。自从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在18世纪出版以来,在中文著作中,还没有哪一部作品对朱熹的思想和学术作出过这样广泛深入而且又慎重负责的研究。从钱穆的五卷著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朱熹的形象,表现了汉学文献中难以找到的完整性。钱穆这种整体性的观点,无疑将为今后评判对朱熹的各种偏见提供资据。毫无疑问,朱熹的哲学在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中得到了更明白的分析;朱熹的生平历史则在王懋竑的《年谱》中得到了更生动的描绘;但是,对朱熹的伟大体系的完整构图,我们是在钱穆的著作中找到的。钱穆的著作做到了把朱熹在整个儒学传统中承前启后的主要关系都加以了展现。”[12]240-241刘述先也说:“近年来,关于朱子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成就。牟宗三先生出版的三大卷的《心体与性体》,钱穆先生出版的《朱子新学案》,都是卷帙浩繁的伟构。钱先生考证精详,牟先生义理精透,在今日研究朱子不能不注意两先生的研究成果。”[13]1-2
注释:
① 钱穆称朱子“疑伏、孔《尚书》相异,又疑《书序》不可信……于理学,既集北宋之大成;于经学,则为此下明清两代之开山。伪《古文尚书》一案,即由朱子提出。就中国全部学术史言,朱子之伟大,洵是古今难匹。”参见《朱子新学案(中册)》,第1287页。
② 参钱穆:《朱子新学案(中册)》,第1238-1252页。钱穆指出:“从来治易不外两途,一曰象数,一曰义理。朱子独曰易为卜筮书,其中义理不过因卜筮而见,使言义理者有所根著,不至于支离散漫而无归。又曰象数一本于自然,使言象数者亦知其由来,而不至于牵合傅会,索之太过而支离。中道而立,使治易者可以得其纲宗,不背不失于易之本义而弛骛益远,此为朱子治易之大成绩。”
[1]钱穆.朱子新学案[M].成都:巴蜀书社,1986.
[2]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53册[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
[3]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M].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
[4]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6]程颢,程颐.二程外书:卷8[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7]黄宗羲.宋元学案:卷21[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程颢,程颐.二程外书:卷12[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9]朱熹.伊洛渊源录:卷7[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0]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M].南昌: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12]杜维明.儒学传统的重建:钱穆《朱子新学案》评介[C]//李振声编.钱穆印象.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13]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发展与完成:自序[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