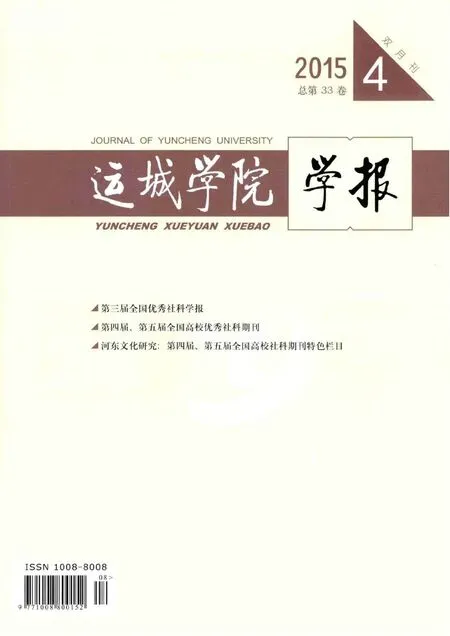论《红楼梦》神话叙事的生态美学意蕴
武 建 雄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0)
论《红楼梦》神话叙事的生态美学意蕴
武 建 雄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256600)
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中,人、自然、社会是三个最为重要的核心要素。三者关系的和谐、平衡构成了生态系统具备美学特征的基础。用生态美学的理论来考察《红楼梦》中的神话叙事,“石头”神话和“还泪”神话寓含的是对个体生态美学理想的标举;“太虚幻境”神话则通过对“大观园”的对应,展现了“诗意栖居地”的生态审美理想。三个神话又一致地暗示了作者对生态美学理想不可能实现的悲观情绪。
生态美学;《红楼梦》;神话叙事
生态美学是后工业时代人类活动致使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危机日益突显的语境下诞生的新兴学科,“是以生态哲学为基础,把生态的观念引入美学研究的一种理论尝试,它的出现也是美学界对环境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积极回应”。[1]
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中,自然、人与社会成为最为基本的三个核心要素。在现代学科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受哲学系统论的影响,自然、人与社会均被证明是以独立生态系统的形态而存在和运行着。美学与生态学融合以后,美学的统一、平衡、和谐的原则被运用到对生态的审美评价之中。曾繁仁先生认为,生态美学的特征“是一种人与自然和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2]在生态美学要素之间的审美关系实现之前,各个要素系统自身处于审美状态成为生态系统具备美学特征的前提和基础。
小说《红楼梦》文本叙事中有着明显的神话成分,小说第一回从《淮南子·览冥训》中记载的“女娲补天”的故事为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出生时口中所衔之玉的来源进行了“石头”神话性的杜撰;同一回中,作者又用“绛珠还泪”的神话为林黛玉的人世活动做了神话式的暗示;第五回中,贾宝玉在侄媳秦可卿屋里睡着,梦中神游了“朱栏玉砌,绿树清溪”“人迹不逢,飞尘罕至”的神仙世界“太虚幻境”,“太虚幻境”的设置,为全书“大观园”中多情女子的身世命运作了提前预示。关于这三处神话叙事对全部文本所具有的重要表意功能,不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这里主要运用现代生态美学的理论对《红楼梦》的神话叙事中的生态美学意蕴进行阐述。
一、“石头”神话与“还泪”神话展现的个体生态审美理想
《红楼梦》的作者对“女娲补天”神话的大胆改造明显流露了其在创作表意上的动机,“石头”神话中弱化了创世补天的女娲的地位,有意突出了石头的形象,这块因“无材补天”而被遗弃的“石头”在显性层面与贾宝玉“一落胎胞,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相呼应;隐性层面与贾宝玉人世生活的生命存在状态紧密联系。
“石头”神话对于贾宝玉在《红楼梦》中的生态存在具有明显的预示作用。石头为自然界之物,石头天然质地的坚硬与不轻易随自然环境变化而改变的特性,与小说中贾宝玉的生命状态相一致。人作为生态性的存在,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生命天性在于“情”。脂砚斋在石头被弃之地“青梗峰”时批道“自谓落堕情根,故无补天之用”(《红楼梦脂批汇校本》第一回),正是独具慧眼,指出了神话在对人物生态特性提示上的精巧构思。
贾宝玉的生命状态体现在他保留着人类最丰盈的生命情感状态。他对自己“情”的生态本性的维持与保护,像石头一样坚硬执着。贾宝玉对“情”的执着,表现为他对大自然的一切事物都倾心喜爱,他认为自然界的花草鱼虫都保有着美好的生态自然本性,因此,他“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的”(第35回);他在沁芳闸桥边石头上读《西厢记》,风吹桃花“落的满身满书满地皆是”,他“只得兜了那花瓣,来至池边,抖在池内”(第32回)。贾宝玉对“情”的执着,还表现为他对青春女性的偏爱上。他认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第20回),也就是他觉得只有“女儿”最好地保持了人的生态本性。他说“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2回)因此,他不论“女儿”的年龄、身份、出身、地位等差别,都一视同仁地爱惜有加。他称赞学诗的香菱道“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性情”(第48回);刘姥姥胡谄雪地抽柴的姑娘茗玉,他听后跌足叹惜;丫鬟晴雯去逝,他赞她“金玉不足喻其贵”、“冰雪不足喻其洁”、“日月不足喻其精”、“花月不足喻其色”(第78回)。他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来表达对有着美好生态本性的“女儿”的偏爱,说“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第34回)。当然,贾宝玉对“情”的生态本性的执着,更多地体现在他对林黛玉的用心专一的爱情上。在他的观念里,“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的林黛玉没有受到世俗的沾染,她的身上有着最完美的人类美好而纯真的生态本性。他认为林黛玉与薛宝钗最大的不同在于她从来不说仕途经济的“混账话”。他们之间的感情甜蜜而融洽,“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止同息,真是言和意顺,似漆如胶。”(第5回)他们发生矛盾,一时难以化解时,能互剖心腹,林黛玉说“我为的是我的心!”贾宝玉也说“我也为的是我的心。你难道就知道你的心,不知道我的心不成?”(第20回)他们的爱情在别人眼里是“‘是姻缘棒打不回。’这么看起来,人心天意,他们两个竟是天配的了。”(第90回)清代陈其泰则评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情说:“凡人爱博,则情不专,独宝玉不然。彼固以女色为命,到处留情。然只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雪中之鸿爪,梦中之鹿肉;原在何有何无之数。其饥渴饮食性命以之者,惟一林黛玉耳。”[3]70
《红楼梦》开卷的“石头”神话对贾宝玉“情”的生态本性的暗示,体现了作家对人自身生态审美理想的标举。小说文本中用贾宝玉对自然界生物、女儿与林黛玉的钟爱来诠释其对人生态本性“情”的推崇与维护。孔子说“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4]105“情”是人作为生态系统中一分子与其他生物的天然关联,是人所具备的最宝贵最美好的生态特征。《红楼梦》卷首“石头”神话对贾宝玉性情的关联暗示,表达的正是作者对人生态美学特征理想的标举与呼唤。
如果说作者用“石头”神话暗示了贾宝玉的生态本性,并用贾宝玉对人生态本性的推崇表达了作者的生态审美理想的话,“还泪”神话所寄寓的作者的生态表意功能就要简单得多。神话中绛珠草的天然特性对应于林黛玉性情的天然,神话中用“还泪”的前世设计规定了林黛玉的人生行为,林黛玉的生态美学展现与贾宝玉并无二致,同样表达的是作者对人天然性情崇尚的生态审美理想。按小说的神话设计,林黛玉的前世为绛珠草承天地雨露精华而成的“绛珠仙子”。这一构想其实是中国古代神话中“香草美人”文化传统的体现,“在中国神话中,香草具有神奇的健体祛病的功能,并且与女性即‘美人’也有神秘的联系。”[5]
“还泪”神话中香草对林黛玉的人世影响,主要体现在她天然的性情上。作者对此在文本中有一系列的暗示,第3回中,贾宝玉对林黛玉名字的解释是“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第28回中,林黛玉也对贾宝玉说“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人儿罢了”;第37回中,贾探春说:“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那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做‘潇湘妃子’就完了。”这些都提示了林黛玉性情中对生态自然的高度认同,而林黛玉自身的性情也的确展现出一副天然之美。她性情纯真,以天怀待人,不存机心,不沾世俗,脂砚斋在第19回中评黛玉为“情情”。第31回中,黛玉称袭人为“嫂子”,直率地说:“便是你们鬼鬼祟祟干的那事,也瞒不过我去。”但黛玉与袭人之间并没有因此生分。第45回中,黛玉曾当面告诉宝钗自己曾经怀疑她“有心藏奸”,宝钗没有在人面前因她说错了词而当场揭穿让她难堪,便真心认为宝钗厚道,从此与宝钗结成金兰之契。至于林黛玉对爱情的忠诚、执着与专一,前人论述甚繁,是不需要这里再进行说明的了。
可以见出,《红楼梦》第一回通过“石头”神话与“还泪”神话,寄寓的是作者对个人天然性情所展现出来的生态之美的思想。从文本的表意功能上看,两个神话的指向是一样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作者通过贾宝玉与林黛玉展现了个人生态的美学理想,然而这种理想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作品中,贾宝玉为“情痴情种”,作者评其“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第3回),他母亲称”其“混世魔王”,他奶奶称其“孽障”(第3回),他与现实世界的不协调,以致想“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就散了”(第19回);而林黛玉身在钟鸣鼎食的贾府中鸟语花香的大观园里,也深感“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第27回)。贾、林个体生态与环境的冲突,反映的正是作者对个体生态理想在那个时代无法实现的悲观和失望的情绪。
二、“太虚幻境”神话展现的人与自然生态的“诗意栖居地”
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中,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诗意地栖居”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人与自然生态审美关系的最高美学标准。曾繁仁先生认为,“所谓‘诗意地栖居’,就是‘审美的生存’”[6]。《红楼梦》通过“太虚幻境”展现了作者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诗意栖居地”的美学境界。
事实上,我们看《红楼梦》第5回中作者所设计的太虚幻境的世界,人与自然是并不和谐的,那儿并不是一个“诗意栖居地”。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看,太虚幻境无疑是美的,这里“画栋雕檐,珠帘绣幕,仙花馥郁,异草芬芳”,但是这里的各处景点“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无一不充满着悲凉的气息,提示着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这里的主人警幻仙姑对前来游玩的贾宝玉一直态度冰冷;其管辖下的仙子对贾宝玉也态度严厉,怪其“引这浊物来污染清净女儿之境”;这里还有“荆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道黑溪阻路”的迷津所在。贾宝玉游太虚幻境,没有感受到与人间一样的温暖,最后惊恐而逃。
然而,太虚幻境的神话设置用意并不在本身,而是贾府大观园的人间反向投影。首先,贾宝玉在太虚幻境遇到的都是女性,警幻仙姑也说此处有“素练魔舞歌姬数人”,而贾府的大观园也是一个男性的禁区,第18回贾母说:“无谕,外男不敢擅入。”其次,太虚幻境的总管警幻仙姑虽然“司人间之风情月债,掌尘世之女怨男痴”,但是文本中主要突出的还是对“金陵十二钗”过去未来命运的掌管,而“金陵十二钗”正是生活在或至少去过大观园的女性主体。再次,作者第5回写太虚幻境的设计“珠帘绣幕,画栋雕檐,说不尽那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宫。更见仙花馥郁,异草芬芳,真好个所在”时,脂砚斋批曰“已为省亲别墅画下图式矣”,所谓省亲别墅,当然就是大观园无疑。
作为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大观园显示了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生态美学样貌,是真正的“诗意栖居地”。大观园的设计尽显自然景物与人文精神高度融合的风貌。这里沁芳桥畔佳木茏葱、奇花烂漫,潇湘馆千百竿翠竹遮映,稻香村桑、榆、槿、柘编就两溜新篱,蘅芜院异草牵藤引蔓、吐芬气馥,山水花鸟草木等生态自然环境,与其中建筑的亭台楼阁廊榭等人文建筑,相映成趣,组成一个充满生态气息的人居环境。大观园所熔铸的生态之美还深入到了居住其中的人的精神气质、性趣志向与自然生态的高度和谐一致。贾宝玉偏爱青春女性,怜香惜玉,被李纨称为“绛洞花主”,意为百花之王,其居所植芭蕉与海棠,取“怡红快绿”之意;林黛玉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喜欢抚琴作诗,一副传统文人风骨,其居所所植凤尾竹正映称了其傲岸不屈,清峻脱俗的气质与品格;薛宝钗出生于皇商世家,精于生计,过早熟谙世事,清心寡欲,故其居所“一色花木也无”,其房屋“如雪洞一般,一色玩器全无”。作者的设计安排体现出其深邃高超的生态美学思想,把大观园打造成一个人居环境的理想伊甸园。
如果说大观园的理想化设计寄寓的是《红楼梦》作者的生态美学理想的话,熟悉作品的读者都知道,这个理想最后是破灭了的。大观园的生态浪漫的确曾娇艳地绽放过,如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海棠诗社赛诗、群芳开夜宴、史湘云醉眠芍药裀等,那是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绝美画面。然而,就是这样的环境里,金钏投井而亡、晴雯招怨病故、探春无奈远嫁、惜春心死出家,大观园因人事纷争而被抄检,日渐荒凉,园中人悉数搬出,“风声鹤唳,草木皆妖”,以致贾赦“只得请道士到园作法事驱邪逐妖”。大观园的衰落昭示了作者精心营造的生态美学理想的“诗意栖居地”的毁灭。“太虚幻境”神话作为照应文本中现实叙事大观园的超然存在,不仅寄寓了作者人与自然相谐相融的生态美学理想,也揭示了这种生态理想破灭的原因。我们看太虚幻境的主人警幻仙姑所警贾宝玉之“幻”为何?第5回中,贾宝玉眼中看到的太虚幻境门匾上写的是“孽海情天”“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太虚幻境各司名为“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警幻仙姑让贾宝玉所阅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中的女性多为大观园中的多情女子;贾宝玉听“红楼梦十二支曲子”开首就唱“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警幻仙姑最后警示贾宝玉“好色不淫”、“情而不淫”。种种证据表明,警幻仙姑所警之“幻”为“情”,她认为痴情纵情的结果到头来只是一场空幻而已。而“情”正如前一节笔者论述的,是人最具本质性的生态特征。如果结合《红楼梦》开首作者说的“本书大旨谈情”来理解,就不难看出,“太虚幻境”神话的设置,不仅用现实映射的方式表达了作者人与自然相融相谐的生态美学理想,也提示了正是因为个人生态的把握不当而造成了这一生态美学理想的破灭,其中包含着作者不可能实现审美理想的悲观和失望,这与“石头”神话以及“还泪”神话的表意意图是完全一致的。
综上,《红楼梦》用神话叙事的超拔方式暗在表达了作者对个体生态以及个体生态和自然生态关系的美学理想的关怀,寓含了作者对理想喻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悲凉,同时也揭示了美学理想不可能实现的原因。
[1] 宋薇.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自然美学辨析[J].晋阳学刊,2011(4).
[2] 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3).
[3] 孙逊.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4]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刘怀荣.“香草美人”与“双性同体”比较研究[J].东方丛刊,2002(1).
[6] 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5).
【责任编辑 马重阳】
Ecological 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Myth Narration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U Jian-xiong
(The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BinzhouUniversity,Binzhou,Shandong, 256600)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are the most three important core elements in ecological esthetics research, and their balance and harmony are the basis of the ecological esthetics appreciation. Research into the myth narr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by adopting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esthetics tells us that the myth “stone” and the myth “returning tears” advocate the ecological esthetics ideal of the individuals, the myth “fantasy land” showed the ecological esthetics ideal of poetic habitat through correspondence of “Grand Garden”. The three myths implicate the author’s pessimism and despondency for the impossibility to realize his ecological esthetics ideal.
Ecological Esthetic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Myth Narration
2015-03-11
武建雄(1978-),男,山西忻州人,滨州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I207
A
1008-8008(2015)04-004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