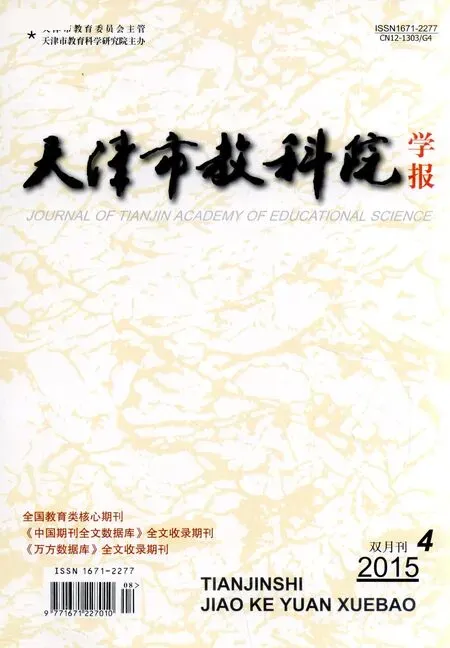中德两国职业教育法的内容比较及启示
江 军
目前,国内关于中德两国职业教育法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从两国的法律体系、立法过程、发展轨迹等宏观层面进行分析,较少全面地从两国法律的具体内容比较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的视角对两国法律具体内容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找到一些启示,为我国现行《职业教育法》的修改提供相关参考与借鉴。
一、中德两国职业教育法的概况
本文是对中德两国职业教育法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法律文本分别是德国2005年颁布的《联邦职业教育法》与我国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职教法》)。德国在2005年颁布的《联邦职业教育法》由1969年颁布的《联邦职业教育法》与1981年颁布的《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合并及修改而成。[1]该法分为总则、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组织、职业教育研究、规划与统计、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罚款规划、过渡条款和衔接条款七大部分,共105条条款。我国《职教法》自1996年9月1日实施以来,至今尚未修改。[2]它分为总则、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的实施、职业教育的保障条件、附则五章,共40条条款。
二、中德两国职业教育法内容比较与分析
(一)职业教育目标
两国法律对于职业教育目标的表述存在明显的差异。我国《职教法》指出“职业教育的目标主要是职业知识的传授与职业技能的培养”。这样的定位没有凸显职业教育的特色。职业教育是培养专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而法律条款中表述比较抽象笼统,没有明确可操作的标准,对具体的职业教育工作指导与规范效用不强。相比较而言,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中对职业教育目标的阐述则更为切合实际,它将整个职业教育分为不同的阶段,包括职业准备教育、职业教育、职业进修教育、职业改行教育等。进而,对各个阶段的职业教育制定具体的目标,如《联邦职业教育法》中指出“职业准备教育的目标是学习行动能力的基础内容,以达到国家认可的标准”。德国将职业教育目标细分为各个具体阶段的目标,目标具体明确,针对性强,能够真正起到对职业教育指导与规范的作用。而我国《职教法》很显然对职业教育的定位不明确,目标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
(二)职业教育主体
两国法律对职业教育主体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在具体的要求上存在明显差异。我国《职教法》对职业教育主体要求比较宏观笼统,而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则比较微观具体。笔者主要从职业教育相关主体权责利、学校资质及教师资格两方面进行深入比较。
1.职业教育相关主体权责利
职业教育相关主体主要包括教育提供者与受教育者。教育提供者主要是指学校、教育企业等,受教育者主要是学生。两国法律对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义务都有规定,但德国更为详细、全面。我国《职教法》只规定教育提供者的义务,受教育者的权利。如《职教法》第一章第5条规定:“公民有依法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在这里,法律只规定了受教育者的权利,未规定其义务。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教育的权利与义务是相统一的,缺乏其一,不利于规范教育主体的行为。第三章第19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及行业组织举办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并指导本行业的企业及事业组织的工作。”这一条款规定了行业组织对本行业的企业及事业组织指导作用。第三章第20条规定:“企业应当参与实施职业教育。”这一条款规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义务。两项条款都只明确了企业及行业组织的责任,而对它们的权与利没有相关规定。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益性组织,而职业学校则是公益性的机构,要使两者合作办学,需对企业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否则校企合作难以奏效。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对受教育者与教育提供者的权利与义务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第13条规定:“受教育者必须履行的义务包括遵守针对教育机构的制度、爱护工具机器及其他设备、保守企业和业务秘密,等等”。第71条共9大条款规定了各个行业组织的权利及义务,突出行业组织的指导作用。另外,德国法律也规定了企业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运用很大的篇幅来详细阐述。相比而言,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对企业行业的权责利规定更明确更全面,而我国《职教法》则比较片面,规定不明确,操作性不强。
2.学校资质及教师资格
两国法律都对学校资质及教师资格作出了规定,但在具体的标准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规定:“只有通过州法律规定的主管部门认可的教育机构才有办学资质。”至于对教师的资格要求主要是从人品资质与专业资质两个方面来作出具体规定,人品资质主要是指教师的思想道德,专业资质主要是指教师的专业能力。在这两个方面德国法律都有详细的规定。如对教师的专业资质是这样表述的:“专业资质合格指的是具备传授教育内容必需的职业及职业教育学和劳动教育学的技能、知识和能力者。”可见对教师的资格标准规定具体明确。而我国《职教法》对职业教育教师没有作出具体的要求,法律条款中的表述很简单:“有合格的教师。”这样的表述很宏观,具体的操作性不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教师法》对教师已作出相关规定,但职业教育教师与普通教师存在很大的差异,没有单独作出相关规定是欠妥的。关于学校资质在《职教法》第三章第24条有基本条件要求,主要从组织机构、教师队伍、教学设施及经费要求等方面作出规定。但这样的规定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对学校资质及教师资格有严格具体明确的规定,保证了职业教育的质量。而我国《职教法》显然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不足。
(三)职业教育管理
两国法律关于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存在明显的不同。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教育是由行会组织管理,不同的行业组织管理相关的职业领域。如《联邦职业教育法》第71条第5款规定:“经济审计员协会主管经济审计领域的职业教育。”另外,《联邦职业教育法》也规定,若没有相关职业领域的行会组织,可由各州指定主管机构。这样的规定明确了相关管理部门的职责与权限,能够更好地指导职业教育实践。而我国《职教法》关于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表述不清晰。国家、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以及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等都有一定的管理权,各部门各行其是,管理容易出现混乱。我国《职教法》中对整个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没有做到统一规划,在相关条款中既规定了各级政府的管理职责,又规定了其他相关部门、行业组织权责,但没有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如《职教法》第18条要求县级政府举办职业教育及技术培训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但同时第19条又对政府相关部门及行业组织赋予一定的管理权限,这容易造成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导致管理混乱,效率低下。
(四)职业教育体系
两国法律都按不同的阶段来划分职业教育,但在具体分类上存在明显的不同。我国《职教法》第二章第12条明确规定:“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普职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职业学校教育按不同的层次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等多种培训,并根据具体要求分为初级、中级、高级。然而,这种分类将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割裂开,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德国将职业教育分为四个阶段,包括职业准备教育、职业教育、职业进修教育、职业改行教育。职业准备教育与职业教育可以归为职前培养这一类,职业进修教育与职业改行教育可以归为职后培训这一类。德国将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合为一体,从法律的高度明确建立一体化的培养培训体系的要求。相比较而言,我国《职教法》没有将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统一起来,没有形成一体化的培养培训体系。
(五)职业教育监督
德国法律明确了职业教育监督的主体及权限且单列章节规定处罚条例,而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要求,比较模糊。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监督进行了相关的规定,主要是通过主管机构为参加职业教育者提供咨询。同时,对教育企业进行监督,教育企业有义务回答主管机构监督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如第76条第2款规定:“职业教育提供者有义务回答监督部门的询问并允许其参观教育机构。”德国通过对职业教育进行监督,一方面维护了受教育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促进职业教育机构提高教育质量。而我国《职教法》对职业教育执法监督主体及违法后果规定不明确,造成法律本身操作性、强制性不足。执法监督的主体没有明确,执法监督的权利范围也很模糊,这很难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
(六)职业教育保障
我国《职教法》对职业教育的保障主要从经费、师资、生产基地等方面作了相关的规定。如《职教法》第四章第26条规定:“国家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这是从经费方面为职业教育提供保障。第四章第36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规划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工作,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这从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提供保障。第四章第37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政府等主体,应当加强职业教育生产实习基地的建设。”这是为职业教育建立生产实习基地。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保障没有单独列出一章,但为了保障受教育者的利益,规定要签订劳动合同以保证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如获得实习工资津贴、享有休假权利、规范工作时间等。另外,德国对特殊群体也积极关注,保障他们顺利地接受职业教育。两国法律对职业教育保障规定存在明显的差异,我国法律大多从宏观视角进行阐述,可操作性低。而德国法律则是从微观的视角入手,相关规定细致、全面,可操作性强。
三、中德两国职业教育法内容比较的启示
(一)立法要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我国现行的《职教法》原则性条款过多,具体可操作性的条款较少,整体来讲过于宏观笼统,缺乏针对性,这必然导致对职业教育指导、规范效用不强。而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内容翔实,条款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职业教育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做好顶层设计有助于引导职业教育更好地发展。因此,我国在《职教法》的修改中,要转换条款表述的方式,增强可操作性。同时,要结合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与未来的趋势,增加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内容,使法律能够更好地指导职业教育工作。如职业教育的目标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将其划分为适合我国实际的职业教育分阶段的目标,使其既有层次性又有针对性。
(二)明确企业、行业等主体的权责利
我国现行《职教法》只规定了企业及行业组织等主体的责任,忽视他们的权与利,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私益性组织,而职业学校则是公益性的机构,要使两者合作办学,需对企业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否则校企合作难以奏效。相比较而言,德国法律明确企业、行业等主体的权责利,建立了高效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在这其中,企业与学校各自明确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各司其职,从而保证校企合作机制的良好运行。因此,要借鉴德国的立法经验,在我国《职教法》的修改中,要注意相关条款的修改,明确企业、行业等主体的权责利,促进校企深度合作。如可以增加激励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条款,减免税收、政府财政补贴等具体内容。
(三)统一管理部门的职责权限
我国现行的《职教法》对整个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没有做好统一规划,没有理清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职教法》的相关条款中既规定了各级政府的管理职责,又规定了其他相关部门、行业组织的权责。这导致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比较混乱,职业教育相关管理部门多、杂。各部门都有管理权限,这往往会出现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职教法》对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规定不明确,没有统一管理部门。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等各行其是,导致管理混乱。而德国法律明确规定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管理中的主导作用,职业教育培训、考核等方面都由行会完成。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赋予行会组织更多的权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建议我国《职教法》的修改中,要明确统一管理部门的职责权限,突出行会组织的作用。如可以建立由地方政府统筹,教育、人社和其他行业部门归口管理的管理体制。[3]
(四)构建一体化的职业教育培养培训体系
由于职业教育的动态性,职业教育的培养与培训必须前后衔接为一体。但是,我国现阶段的职业教育体系还不完善,尤其是一体化的培养培训体系尚未建立,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这导致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滞后,与市场需求、职业岗位不能很好地对接,造成大量的人才浪费。德国法律明确要求统一职业教育的培养与培训,各个阶段衔接紧密,形成了完善的培养培训体系。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紧密联系,这较好地满足了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因此,在我国《职教法》的修订中,要增加相关条款,构建各阶段衔接紧密的、一体化的职业教育培养培训体系。
(五)加强职业教育的执法监督
我国现行的《职教法》强制性不足,没有明确职业教育监督主体及违法后果。法律条款表述如“可以、应当、鼓励”等非刚性的词较多,而涉及违反法律后果的词较少。这使得职业教育的相关主体即使没有履行规定的义务也不用承担法律后果。[4]另外,我国法律对职业教育的监督权限、范围也不明确,导致执法监督不到位。而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专门单列章节规定职业教育的监督主体、权限以及处罚条例。因此,我国现行的《职教法》要加大这方面的修改,要专门规定职业教育的执法监督,明确执法监督的主管部门及权限。如可以设立专门的职业教育委员会进行监督。同时,要加大执法力度,严肃处罚违法行为,提高违法成本。
(六)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保障机制
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保障机制不健全,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明显不足。这主要在于当时的背景下,对职业教育重视度不高。因此,经费投入、师资队伍建设等相应的保障比较滞后。但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技能型人才缺口突出,职业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这需要建立健全相应的保障机制,如多渠道地筹措资金、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生产实习基地,等等。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的保障明确具体,积极保障受教育者的合法利益。因此,我国的《职教法》在修改中,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建立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体系,明确“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加强生产实习基地建设。总之,要在法律中明确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保障机制的具体要求,保障职业教育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
[1]姜大源.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译者序[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10):71-88.
[2]教育部网.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19/200407/1312.html.1996-5-15.
[3]邢晖,等.《职业教育法》重要问题修订意见的调查[J].教育与职业,2014(7):76-78.
[4]郭广军.《职业教育法》修订的对策与建议[J].教育与职业,2015(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