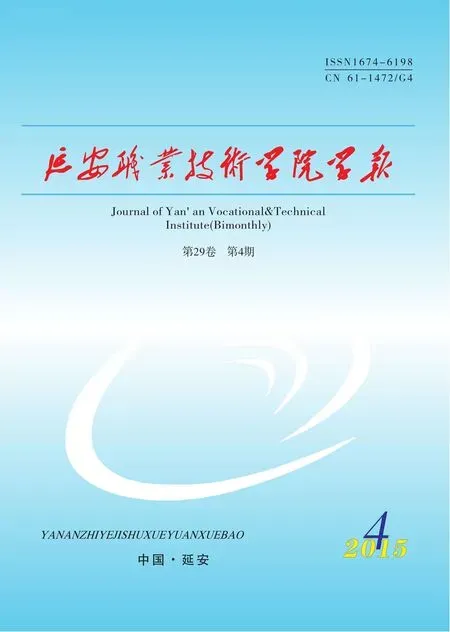《接骨师之女》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
陆丹路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江苏 镇江 212000)
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以在作品中生动描写华裔母女关系而著称。她出版于2001年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接骨师之女》沿袭了这一主题,展现了外婆、母亲、女儿三代人之间由冲突到理解的情感历程,深入表现了华裔女性的内心世界。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看,《接骨师之女》成功实现了女性叙事话语的权威,对读者具有了权威性。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叙事学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有效结合,苏珊·S·兰瑟在《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这本书中把女性作家的声音分为三种类型: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她认为“这三种叙述方式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汇合以及不断变化的叙事技巧常规的表现形式,女性作家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形成这三种权威。”[1]
谭恩美被美国的《新闻周刊》称作是“当代讲故事的高手”,[2]《接骨师之女》中,她主要使用了作者型叙述声音和个人型叙述声音,同时融入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话本叙述模式来实现女性叙事话语的权威性。
一、作者型叙述声音
“作者型叙述”是指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1]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他与虚构人物分属两个不同的本体存在层面。作者型的叙述因其全知角度而往往被理解为虚构,但其叙述声音又显得更具有可信度。[3]在《接骨师之女》中,谭恩美通过作者型叙述声音,树立了一个无所不知的现实而客观的讲述者形象,为她自己和整个华裔女性作家群体实现了“话语权威”。
在《接骨师之女》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作者型叙事者以真实而客观的方式进行讲述,对人物行为、心情的所有细节了若指掌。
露丝的故事就是使用了作者型叙述声音,让读者清楚地了解华裔女性在美国的真实生活状况。谭恩美用第三人称叙事呈现了露丝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麻烦:每年8月12日的心理性失语;替人“捉刀”、没有自己声音的影子作家;和母亲之间令人困扰的关系。在感情生活中,她觉得无法与她同居10年的情人亚特坦诚相对、产生共鸣:“(露丝)有点难过地注意到,亚特是说“你”而不是说“我们”打算怎么办。自从中秋节的聚餐以来,她越来越觉得她和亚特不像一家人”[3]“他们两人之间沟通如此之差,露丝觉得很是失败”。[3]这两句陈述不仅表达了露丝的感受,同时也达到了加强叙述者客观性的目的。
在叙述宝姨的爱情故事时,茹灵成为了作者型叙述者。她描述了母亲和父亲之间第一次相遇的场景:“宝姨在里屋,透过帘子看得到他。小叔当时二十二岁,身材瘦削。五官生得很标致,仪态自如,不卑不亢。”[3]她听到了她母亲内心的声音:“况且,何必让未婚夫疑心,以为她做了什么对不起张老板的事呢?反正好多人都说她性子倔,凡事自作主张。”[3]
对茹灵而言,她似乎和母亲生活在了同一时期,目睹了不同事件,记录下了所有的事情。茹灵所扮演的作者型叙述者的角色加强了叙述其母亲故事的生动效果,和茹灵一样,读者似乎也处于宝姨出现的相同的场景。作者型叙述者置身叙述时间之外,因此,所有事尽在掌控之中。通过茹灵对宝姨经历的叙述,谭恩美想强调的是宝姨在刘氏父权家族中真实、沉默的处境。
二、个人型叙述声音
“个人型叙述声音”是指叙述者讲述自身的故事,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1]个人型叙述声音里的虚构在形式上与自传难以区分,从而使得其叙述声音的权威往往名正言顺。[4]
在谭恩美的小说中,女性的个人叙事声音能够传达过去的隐秘,暗示不同女性角色经历过的受压制或扭曲的情形,是展示不同女性体验的主要方法。叙述者“我”的再现表明了华裔女性的需求得以表达和倾听。同时,女性个人声音的使用也拉近了读者和人物之间的距离。
《接骨师之女》通过个人型叙述声音讲述女性的经历,表达其独特的生理和心理感受,展现出女性的性别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男性话语权威的否定。茹灵的个人声音公开、显著、引人注目。“我知道这一切,但有一个姓氏我却记不起来了。它藏在我记忆里最深的一层,我怎么也找不到。我曾成百上千次地记起,那个早上,宝姨把那个字写给我看。那时我才六岁,聪颖过人。我能写会读,知书识数,也懂得记事了。”[3]自传开始时的肯定语气用于声明茹灵在叙述过程中的权威角色。“我知道”,“我能”,“我懂得”,“我记得”表明它是茹灵自己的故事,没有人有权取代她成为最可靠的叙述者。
在肯定茹灵在其自传中主要声音的过程中,谭恩美还希望揭示茹灵在叙述中的复杂感觉,以确立更为立体的茹灵形象。在以下这一段落中,谭不断地变换代词。“宝姨,我们到底姓什么?我一直想找回那个姓氏。快来帮帮我吧。我已不再是个小孩,不再害怕鬼魂了。你还生我的气吗?你不认得我了吗?我是茹灵,你的女儿。”[3]这里,代词“我们”、“我”、“你”、“你的”的改变成功阐明了茹灵的复杂情感。通俗用语和直接引语的使用建立了一个茹灵在同宝姨真正对话的场景。
三、话本叙事模式
(一)说故事
话本叙事源于“说书”这样一种古老的“极具叙述话语权威”的中国民间艺术形式,而由话本发展而来的话本小说叙事自然也沿袭了“话语权威”的优势。《接骨师之女》中,谭恩美吸取了这一中国特色的叙事模式,通过“说故事”的叙事形式,使小说中的女性们能够畅所欲言,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不仅增添了作品的独特性和新鲜感,也自然建立了女性叙事话语权威。这样的叙述对华裔女性有着特别的意义:它变成女性自我肯定的一种重要形式。
小说中,母亲就试图通过“说故事”这种传统的叙事形式讲述自己的故事,以宝姨对其脸上骇人伤疤的众多解释为例。从表演食火艺人演出的失误,到幻想的扫把星掉到嘴里,宝姨又编了一个“吃了烧菜用的火炭”的故事。在这里,谭利用了情节悬念,让读者好奇宝姨是怎么伤到脸的。直到在茹灵自传中,谭恩美安排茹灵作为作者型叙述者讲述了宝姨的故事,才揭开了形成伤疤的真实原因。
(二)话本叙事结构
《接骨师之女》包括了话本叙事结构中除了“入话”之外的四个部分:篇首、头回、正话和篇尾。这种有意识的模仿和套用就是为了借用话本叙事的优势,实现女性叙事话语的权威性。
小说开端作者介绍了小说的写作目的:“母亲在世的最后一天,我终于知道了她还有我外婆的真实姓名。仅以此书献给她们两位。”[3]类似于篇首,这一部分揭示了故事的中心和外婆、母亲、女儿三代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谭恩美以“真”为标题作为小说的序幕,担任着话本叙事结构中“头回”的角色。以“这些事我知道都是真的”开始,茹灵用个人型叙述声音讲述了童年经历,一个真实、典型的中国故事——奇异、神秘、吸引人。就像话本叙事结构中的“头回”,这一部分的叙事目的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引导他们进入主要章节。
如同话本结构中的“正话”,小说的正文部分包含三大部分,系统性地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第一部以作者型叙述声音讲述了露丝和母亲茹灵在美国的生活。第二部分则分别以“心”、“变”、“鬼”、“命运”“道”、“骨”、“香”为题通过茹灵的个人叙述型声音讲述旧时在中国的生活。在茹灵的故事中,宝姨的故事同时被呈现,蜿蜒曲折而动人心魄。第三部分又回到了露丝和母亲的现代生活,以作者型叙述声音全知而客观地“说故事”。
类似于话本模式中的“篇尾”,“尾声”重新回到了小说的主题——母女三代人的关系。从自传中露丝最终意识到外婆和母亲的力量,激励她实现个人成长,开始执笔为自己、为亲人创作,确立了另一种女性话语权威。“露丝下笔写作的时候,想起了这些。故事写给她的外婆。还有那个将成为自己母亲的小女孩。”[3]p334
通过话本叙事结构,“说故事”的人扮演了权威说教者的角色,小说的主题——母女关系开头被提及,在尾声又得到重申。由于有说教的效果,话本叙事结构成为了权威的象征,能够取得权威叙事声音。这也正是谭恩美在小说中采用这一叙事结构的重要原因。
结语
《接骨师之女》中,不同叙述模式的运用使小说独树一帜、与众不同。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与话本叙事模式的融合使小说的叙事声音充满了信服力,能够吸引和打动读者,目的就在于使女性、尤其是美国华裔女性获得叙述话语的权威。
[1](美)苏珊.S.兰瑟,黄必康,译.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美)谭恩美.灶神之妻[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3](美)谭恩美著,张坤,译.接骨师之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陈妍.实现叙述声音的权威—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解读谭恩美的作品[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2):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