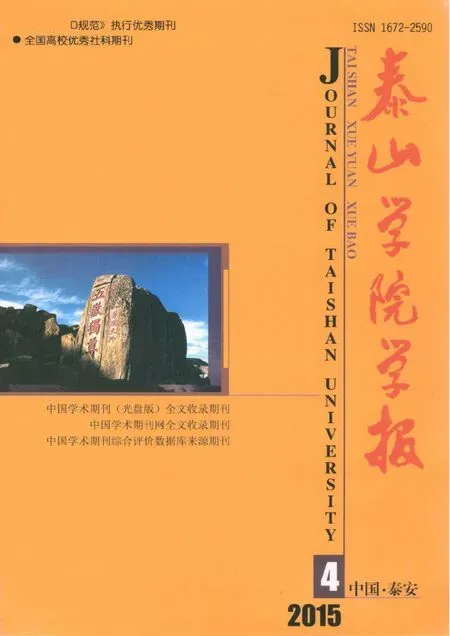利益博弈:略论上海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与各方关系
李东鹏,张庆桐
(1.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5;2.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上海 200235)
利益博弈:略论上海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与各方关系
李东鹏1,张庆桐2
(1.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5;2.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上海 200235)
近代上海公共租界是一块由中西文化碰撞产生的“飞地”,而纳税人会议作为上海公共租界权力机关,贯穿公共租界的发展始终,在其形成、发展和繁荣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在沪外侨的公共集会,纳税人会议所代表的是在沪外侨的整体利益,通过掌控工部局,来实现外侨在公共租界的各种利益。纳税人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权力秩序运行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董事会、驻沪领事团、清朝地方政府、北京公使团等不同利益团体博弈,时而共生、时而对抗,这种博弈的关系,推动了近代上海城市的繁荣,亦是分析上海城市演变的线索之一。
纳税人会议;工部局;利益博弈;权力秩序
自1842年上海开埠,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侨和华人“华洋杂居”,组成了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结构。由于上海公共租界移植的是近代英美(特别是英国)的政治模式,纳税人会议以一种“类似议会”的地位而存在,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权力机关,并以此形成了纳税人会议制度。[1]因纳税人会议并未有常设机构或特定事务处理机构,工部局作为行政机构,在纳税人会议赋予的权力之下,秉承全体纳税人的意图处理与各方关系,促进了上海公共租界的稳定、繁荣。
一、在华外侨政治体系中的纳税人会议
纳税人会议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最高权力机关,工部局各项工作对其负责,受其领导。如纳税人会议制定规章和工部局的工作计划,工部局则执行纳税人会议的各项决定,若纳税人会议对工部局不满,可以罢免工部局董事会。1896年12月8日,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将小车每月缴纳的执照捐增加到600文[2](P575),1897年1月12日由会审公堂谳员发布公告自下季度开始征收。4月1日,小车夫罢工表示抗议。5日,800余名手持扁担的车夫和大批声援罢工的各业人员涌入公共租界抗议,工部局出动巡捕、万国商团镇压抗议。此次事件造成车夫死2人,伤无数,印捕、英捕各伤1人,商团伤2人。4月6日,工部局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暂缓至7月1日起执行增捐决定[3](P490)。事态平息后,在沪西人界对工部局的处置措施相当不满,流言四起,如“工部局听从于道台”[3](P492)等,租界西人于1897年4月21日举行特别会议,指责“工部局董事会无能”[4],致使工部局董事会于4月22日致函领袖领事,转达辞职意图。此事对工部局董事会影响甚大,使得租界当局在处理对华事件中逐步走向强硬。但这只是特例,正常情况下由工部局扮演的执行人角色很好地管理着公共租界,因纳税人会议并无常设机构,对外交涉工作或任务均由工部局承担,故纳税人会议与工部局可合称为“租界当局”。
纳税人会议与领事最重要的联系,乃是由领事发布纳税人会议的召集令,并由年长的领事担任纳税人会议主席,20世纪后也可由有名望的西人担任。不管是由工部局还是25名以上纳税人联名提议召开纳税人会议或特别会议,最后都要经英国领事(后期要由领事团集体签字)批准,方能召开。纳税人会议主席一般由英国或美国驻沪领事担任,俄国、德国领事,也偶有担任。据统计,从1846年到1939年召开的历次纳税人会议中,纳税人会议年会主席人选,英国领事一共担任过23次,美国领事9次,德国领事1次,大英按察使署法官28次,其它人士共10次。[5]而大英按察使署法官也都是英国政府官员,可以说在纳税人会议主席这一席位上,英国系实力最为庞大,这也反映出英国在华势力之强大。
纳税人会议进行的第一项议程便是选举会议主席,因各国领事为在沪各国侨民的最高行政长官,与主席对话,社会公共舆论可以直接传达到最高领事。这样,纳税人会议便充当了领事与驻沪西人沟通的桥梁,民情传达的畅通通道建立起来。
进入20世纪,领事在纳税人会议主席的位置上退居次席,以大英按察使署法官担任纳税人会议主席居多。分析其原因,应与这一时段中外司法交涉增多有关,如苏报案、修改地产章程、华人参政运动等。纳税人会议主席人选由工部局提前联系,待纳税人会议召开之时通过选举任命,因华洋纠纷日益增多,工部局与法官联系频繁,必然为其首选。因1898年《增订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规定“当赴会议事时,如有领事官在场,即以在任较久之领事官为会中首领,如无领事官在场,则于例得有阄议事诸位之中公推一人(须允行人数在大半以上)为此次议事会首”[6](P807)。大英按察使署法官担任会议主席合乎章程规定,亦符合西人宣扬的“法治”精神。
纳税人会议由驻沪领事或其它政府官员主持,纳税人会议达成的决议案为领事和在沪侨民共同商议且皆可接受。另外,两个团体都住居上海,虽然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双方根本利益一致,容易合作、妥协。各国驻沪领事并非各国在华的最高行政长官,其上有各国驻北京的公使,公使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在保护既得利益的同时争取其它权益,维持“中外和好”为其根本原则,故驻华公使们的意见时常与纳税人会议相左,突出的例子就是19世纪60年代北京公使拒绝上海英、美领事和驻沪侨民的“自治”方案。
早在工部局刚刚成立之时,英国政府于1855年5月批准了英使鲍林给阿礼国的训令,着即通知中国当局,英国并不赞助此种“自动组织”,即上海工部局。[7](P355)1862年,租地人大会选举的防卫委员会提出了改上海为自由市的大纲,即将上海县城及其郊外附近地带,置于与中国有密切关系的英、美、法、俄四大国的保护之下,由中外产业所有人选举人员,组织强有力的政府。对于这一提议,英国公使布鲁斯反对尤甚,在给英领事的训令中说道:“所谓上海外人租界,其地位有极大误解。上海英租界,其土地既非转让与英国政府,亦非租赁与英国政府,仅议定在某地方内,容许英人自便取得土地,俾得聚居之利益而已。英人如此取得之土地,仍为英国之土地,须照常缴纳地税”,“盖吾人保护上海,使不为匪众所蹂躏,不能认为吾人即已准备干涉华人与其政府之天然关系也”。英国公使的强烈反对,使得驻沪西侨的企图落败。可以看到,即使公共租界市政管理高度自治,但仍需母国保护伞,这是双方关系的真实写照。
通过上文可以看到,租界当局对于各国在华的政治代表——驻沪领事团和北京公使团,存在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领事团负责公布工部局董事选举日期、纳税人会议举行日期等;二是要由领事团中“年长”领事担任纳税人会议主席;第三,纳税人会议通过的有关租界重大决议案和制定的任何市政新附则,必须事先或事后由工部局负责征得领事同意;第四,关于地产章程的修正或对章程条款进行解释,由领事团负责与当地政府商洽,且必须经各国公使及中国政府承认,效力高于纳税人会议的决定。
尽管领事团与公使团所代表的各缔约国的势力,为租界不可或缺的保护盾,但双方的博弈关系却日渐凸出,如20世纪里关于华人参政运动,各方的分歧便很大。1920年工部局总办在1月5日召开的董事会特别会议上就说道:“工部局董事是受纳税人委托并代表纳税人的,因此他们不应仅仅由于受到领事团或外交使团相反意见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如果要改变观点,就应全面重新考虑整个问题及其有利之处,问题只能是这样。”[8](P536)1920年1月6日召开的董事会特别会议,工部局往届董事会成员维尔金就对领事团背着工部局、西人纳税人会议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提出抗议,认为“这些领事在公共租界境内并不如纳税人拥有同样的利益”[8](P537)。可以看到,纳税人会议、工部局与领事团之间,双方利益、诉求不全相同。在共同利益的领域,如租界防卫、扩大商务利益等方面,可谓展开全面的合作。但一旦危及西人的独享利益权,诸如扩大华人权力、增加中国政府的影响力等,又有着不同的价值取舍,双方经常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相互的博弈不断进行。正如在1月6日召开的工部局董事会议上,谈到传闻:“外交领事团背着工部局与中国政府谈判,即将同意中国政府在公共租界境内征收印花税”,董事们认为只有“召开纳税人大会一途,并将大会结果发往欧洲,因为纳税人不准领事团与外交使团全部放弃此间的地位。”[8](P537)诸多事例都表明,公共租界纳税西人自始至终有城市自治的企图,但此种企图需宗主国给予外交保护,但又不希望宗主国干涉市政,在沪外侨群体即以此为原则来处理、指导与领事团、公使团的关系。1920年2月4日工部局董事会上董事们的意见很形象地说明了各方的关系:“为了领事团、外交使团与工部局之间的共同利益,凡与中国当局签订有关协议之前,或表达其明确观点之前,影响公共租界各项问题的各董事的意见理应为各方所了解。因为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工部局的同意,则有关各方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将不可避免地陷于不协调的、令人为难的处境。”[8](P548)
下述事例亦反映出西人与领事在处理问题过程中的分歧与矛盾:1921年,租界当局欲在公共租界外釜山路上修下水道,对此沪北工训捐局向英国领事抗议,而英国领事则认为其抗议有理。工部局总办认为“代理英国领事加斯廷先生对其本国国民的权利和特权十分不熟悉,他放弃了这一事件中所有的权益。”[8](P709)总办还认为加斯廷还在另外一件事上表现出极端的无知,即由英国国民让给工部局作筑路用的土地,他们享有土地的复归的权利,而且土地仍保留在他们的地契中,工部局仅只有在他人土地上通行权而不是绝对所有权。总办的抗议使得英国代理领事转变了态度,双方遂拟定9条协议[8](P709):
(1)一家英国公司已正式委托工部局按照《土地章程》的规定在其产业上修筑道路并在该路上修建下水道;
(2)闸北警察无端进入此产业,并且干涉工部局工人的工作;
(3)其结果是工部局不得不在此路上保留岗位,以防止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4)闸北警方因此次行动丧失了威信,因而同意;
(5)闸北警察完全从该路撤出;
(6)工部局的工人和工务职员将继续其工程,不再受到干扰;
(7)工部局的巡捕岗位将从该路撤离;
(8)作为临时措施,工部局捕房将不在此路上执行任务,通过谈判使困难得以和平解决;
(9)中方明确地理解,工部局决不放弃其有权管理此路的要求,而中方则没有这种权利。
上述材料涉及租界当局、中国政府和驻沪领事三方面之间的关系。后工部局董事们回忆起英国总领事曾明白指出“北京的公使不支持租界范围以外与产业有关的争端”。而在此事件中,注册业主们承认与西人的利益并无关联。最后工部局得出结论:以拒绝接受该边界以外的地产为妥,理由是没有西人的利益与该项地产切实有关,而且整块土地的地契并不存在。[8](P725)
当然,不管双方争论如何激烈,在中国土地上成立的公共租界,其一旦脱离缔约国的权力保护,便失去其继续存在的根基,因此租界西人对驻沪领事和公使的依赖关系,到了20世纪依然如故,正如费唐形容“工部局依赖代表各条约国之驻沪领事,并经由领事团以倚赖各条约国公使之限度者,咸依然如旧”[9](P292)。
二、纳税人会议与清政府的关系
因历次地产章程并未赋予租界纳税人会议、工部局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的权力,即没有外事权,此类事件的处理全靠上海领事团各个领事充当沟通的媒介。纳税人会议与工部局均十分注意此点,即便与华人团体的交涉,亦谨小慎微,如1906年华商公议会要求工部局将某些出版物给其参阅,工部局董事会在给虞洽卿的公函中说到:“按照纳税人大会新近做出的决议,董事会不能与该委员会有任何官方交往”。[10](P636)公共租界纳税西人、工部局与清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谓充满着尖锐的矛盾,费唐形容工部局与中国官署之间“不仅为两对敌政府当道间之冲突,抑亦为两种相反之政治原则之冲突”[9](P434)。概括说来,“飞地”中存在的不同施政理念、文化传统,是两种文明碰撞的结果。
公共租界本为外人居留地,华洋分治。但由于小刀会起义和天平天国运动的冲击,租界出现“华洋杂居”的局面。大批难民避居租界使得租界异常拥挤,但是给租界带去财富,租界当局在房捐与地税方面的收入猛增。[11]租界的繁荣、租界的财富必然吸引清地方政府的目光,双方最大的博弈点在于租界税收。
租地人会议时期(1846-1869)的公共租界,清道台多次加强对租界华人的控制,以便对租界华人征税。小刀会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恢复对上海县城的统治,1855年上海道台蓝蔚雯公布《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12](P443)规定:
凡华民在界内租地、赁房,如该房地产外国人之产业,则由该业户察明领事官,系华民之业,则由该业户察明地方官,将租户姓名、年、籍,作何生理、欲造何等房屋、做和应用、共住几人、是何姓名,均皆注明,绘图呈验,如地方官及领事官查视其人无碍,准其居住。该住户即出具甘结,将同居各人姓名、年、籍填写木牌,悬挂门内,随时察报地方官查核,遵照新定章程,并按例纳税,倘若漏报,初次罚银五十元,后再漏报,将凭据追缴,不准居住。该住户若系殷实正派之人,即自行具结,否则别请殷实之人两名代具保结。
上海道台发布这一命令,实为获得对逃到租界内华民的管理权,另一方面也默认了租界“华洋杂居”的现状。新成立的工部局按照当年租地人会议的旨意,在第二次董事会上即决定向华人征税,因在沪西人可将房屋租赁给华民而赚取租金,租界当局亦通过征收华人房捐来获取财政收入,从华民身上获益的在沪西人和租界当局便承认“华洋杂居”局面,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华洋杂居”的社会形态,也即熊月之先生所称的“上海开埠初期混杂型社会形成”[13],租界内形成“租界与上海地方政府权力交叉,租界西人与华界官绅在历史特定时刻利益的一致性”[13]的局面,这种庞杂的社会导致各方调整关系,也即“自适应性”,这是此后公共租界运转的基本条件之一。
1862年清道台致函英国领事麦华佗,要求向工部局管辖范围内的华人征收捐税。对于此事,各方的意见如下:
美国领事西华认为工部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明智和必要的,我将做我能够做的一切,以表示支持”[14](P666);葡萄牙领事韦伯在给工部局总办函中,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允许中国官府行使征收捐税的权力,或者,除了征得某些西方国家官方的批准外,甚至都不允许在任何方面干预本地居民的事务……我将不得不就这件事向上海道台阐述我与工部局的一致意见,如果道台坚持采取这一方针,我将不得不向英国公使申述此事”[14](P665);英国公使普鲁斯则认为“条约中没有授权他可在中国官厅和他们的国民之间进行干预,道台享有随意征收捐税的权利……只要道台仅仅是像征收居住在县城和郊外那些人所支付的捐税一样,谋求向居住在租界内的华人征收捐税,那么他就认为既没有剥夺官府财源,也符合我们和华人的利益,就没有理由反对这种做法”[14](P665);英国领事麦华佗在致工部局总办函中表示,将“再次向普鲁斯先生阐明,把请求工部局行政管理保护并得到许可的,为数众多的当地人置于中国当局管辖下的危险性”。1863年4月4日,领事麦华佗在租地人大会上陈述了他不准中国官厅在租界行使这种权力的决定,上海道台对此妥协,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上海道台放弃在公共租界的征税权,换取界内华人房捐收入的一半。[15](P368)1863年9月16日,工部局董事会命令总办,立即做好本季度内开征华人房捐的准备,8%给道台,8%给工部局。[14](P692)与此同时,因码头捐不对华人征收,而华商却享受着租界码头等便利设施,因此道台每年都要提供一笔补偿经费以补偿工部局在码头捐收入上的损失,此外,对于租界内的重大市政项目,租界当局在财政窘迫之时,多次向道台提出分摊费用。
上述材料显示中外双方矛盾尖锐,但又不乏合作,特别是在租界市政和对华人管理等方面,西人和当局不得不借助上海道台的力量。众所周知,租界成立初期,上海道台多次为租界捕房提供补助资金,1855年1月11日召开的工部局董事会上,总董表示已收到“中国政府支援捕房至本月12日止为其6个月的一笔津贴3000元,另外还有用于加强租界防御力量的费用1000元也已收到”,3月10日,总董表示又收到中国政府给捕房的一张1500元的银行汇票捐款。1873年,上海道台在给英国领事的信中就道台资助问题,写到:“虽然由道台资助洋泾浜上桥梁的建造及其维修费用的做法已成为惯例,但按照一位前总督于同治六年五月(1867年5月)发来的公函,规定今后禁止这一做法。”[16](P672)但不同的是,尽管中国政府对于早期租界的巡捕制度的创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租界当局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巡捕协助捉拿中国犯人或其他有关租界华人的事宜,大都采取博弈的态度,使得上海道台的支出与收益存在着严重不平衡。例如1872年清政府提出关于捕房参与中方强行征收鸦片及某些外国货的厘金一事,工部局董事会则从两方面考虑:一是如果拒绝给予协助,则会为中国官府采取强制措施来执行,并开创干扰租界华民的先例;二是不拒绝的话,则将形成一种惯例,即中国政府在租界采取行动,必须与租界当局合作。[16](P584)可以说,租界当局在与清政府的关系处理之中,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即避免丧失对租界的管理、控制权,又防止扩大清政府对租界的影响。
又如1873年5月12、13日在规矩堂召开的纳税人年会中,在沪西人各界,包括领事团一致同意要对交通工具征收捐税,最终通过第9号决议:“与会一致同意由工部局代表驻沪领事团公布会议对华民独轮车、马等交通工具征税的意见,但因目前的土地章程中并没有对此征税的条款,因此要起草一个征税的额外条款,提交驻沪领事团同意后,交与北京公使团核准”[17]。纳税人会议的主要观点是增加对华人征收的捐税,修改土地章程以便获得征税的法理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条约内容所限定,长期以来在沪西人界,包括工部局和领事团,都对华民征税持有着不合法想法。稍后对华民征收土地税问题的交涉中,领事团在给工部局董事会的信函中表示“道台从未或由其本人或代表其政府正式宣布同意该《土地章程》,面对这一事实,提出华人地主应遵守该章程所规定的义务这一问题是很不恰当的”[16](P634),工部局自身也认为因在5月份召开的纳税人大会上通过的决议“章程对于解决目前的问题而言是存在缺陷的”[16](P634),于是工部局不得不继续按照先前的税制实施。
1875年5月18日纳税人年会第9号决议所载“要求中国当局与工部局和公董局合作,清理苏州河与洋泾浜”[18],由华人和西人组成的租界社会,其运转必然离不开中国地方政府和租界政府的合作。
进入20世纪,随着上海商业地位日益隆重,租界已容纳不下激增的人口,而工部局的实力日益壮大,其权力范围早已超出租界。下面的案例可以清晰地展示此时华洋关系。
1906年,因工部局向租界外北面地区使用自来水的居民住户编造门牌号码,并以此征收5%的捐税,引起了中外双方的交涉。上海道台瑞澂在致外务部电中称“工部局在租界外,宝山境内之北,四川路及天葆里、南林里、虬江桥、殷家木桥、永顺里、承德里、德生里等处,编钉门派,派捕收捐,也经职道四次照会租界领袖,请将门牌、巡捕一律撤回,仅以领事公会尚须会议空言照复,而工部局悍然不顾。昨又在来安里收捐,并言如不出捐,定欲拿人。居民积忿难平,集议抵拒。”[19]瑞澂认为:“惟英领向惟工部局之言是听,此外各领虽不以工部局为然,而扩充势力未免同情,亦皆不作公论,若不亟行阻止,众怒难犯,必致生事。”[19]瑞澂的观点正确性与否先不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各国领事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各国驻沪领事都妄图从清政府手里不断攥取权益是其合作的基础,瑞澂的观点也揭露了此中关系。
清政府榷算司就此事照会英美大使称“本部查租界内设立工部局本有一定权限,乃辄在租界以外派捕收捐,经该道迭次照阻,仍不中止,如居民因此积忿,势必酿成暴动,殊为可虑。相应照会贵领衔大臣,大臣查照,迅即电知上海领袖领事官,在上海贵国总领事官转饬工部局,即将门牌巡捕一律撤回,以符约章而保公安,是为至要,并望见复为荷。”[19]。在6月13日工部局董事会复函领袖领事道:“5%的捐税不是也不可能是强迫性的,而在征收过程中也未使用威胁手段,因此,在该地区的华人若不缴纳税款,就停止向他们供水。”[10](P645)必须要看到一点,仍如上个世纪60年代一样,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因从宏观、稳定的角度看对华关系,一定程度上抑制租界西侨社会和租界当局无序扩权的进行。
随着交涉的进行,事情愈见眉目,7月9日榷算司就此事致美国大使柔克义的照会中称:
上海工部局在租界外编钉门牌、派捕收捐一事,本大臣已电知上海美总领事官,并抄来照行知去后,兹据复称,该工部局并无于租界以外勒捐。惟因上海自来水公司曾与工部局商,租界外如有购此水者,必应酌量加价,各该处有产业之中国人,均已愿交水价,并编钉门牌之事,只钉于用水之家,并于查记,如不愿出价之家,亦无人相强。等情。由此观之,上海道似有误会,于租界内不应与闻之件亦将有干预之心,转使租界华洋人往来和睦之情致有互相猜忌。等因。查本部将此事照会贵大臣,请饬将门牌、巡捕一律撤回,并一面由本部电饬上海道设法解释,勿令华民暴动。嗣据该道先后电称,已派员与领袖领事妥商办法,并剀切示谕居民静候商办。领袖复文谓,工部局本未便在界外抽捐,因与自来水公司订有合同,故按水价收捐。职道当以租界铺户应纳水价,向由房主纳于公司,界外事同一律。该公司尽可向房主订认,不能由工部局与房客直接,以清界限等词,先行照复。一面会同绅董,招集该处房东商劝担认公司捐项均无异词。等语。兹准照称,前因本部查上海自来水公司,系商家集股设立,其水费自应由公司取诸房东,不应由工部局向房客索取,庶权限分析,不致居民或有误会,此时已经上海道集劝各房东认捐,是水费既有着落,应即由该道与各国总领事妥商办法,将此事议结,相应照复贵大臣查照,转饬遵照可也。[19]
7月11日,工部局董事会商讨后认为“工部局不如赞成自来水公司征收双倍水费,定期将所收税款一半转给捐务处。如果道台根据这些原则提出一些建议,董事会将批准接受。”[10](P650)最终在此基础上各方达成了协议。
假定我们抛开殖民入侵的民族观点,仅根据双方签订的各种协定基础上形成的稳定社会为基础,看待近代上海租界发生的冲突问题,固然是由于外人侵犯华人权力而引起了冲突,但更多的是由于双方风俗习惯不同、管理理念不同,以及双方沟通渠道不畅通而引起。沟通渠道不顺畅,加之华人社会长期以来对收捐问题的排斥与怨恨,以及在应对问题时各方所秉承的理念不同,是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
由于近代中国城市管理制度未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加之积贫积弱的政府不能伸张自己的合理诉求,租界的管理大权一直掌握在西人社会手中。西人掌控下的租界当局,不断要求满足自身利益,而其所享权益的超然于众,也取自构成租界主体的华人社会的贡献,以此为背景而出现的华洋交涉问题,必然以双方的矛盾为主流。但出于中外共同希冀维护“中外和好”的局面,矛盾还是可以调和的。
三、余论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上一切都是互相关联的,特别是经济活动,它不能脱离周围的政治和信仰环境,不能离开当时当地的可能和限制而孤立存在。[20](P4)近代上海的兴盛依托于商业的兴盛,而上海公共租界的商人自治是商业兴盛的重要原因,纳税人会议即是商人自治的重要特征。
在近代上海中西合璧、华洋杂居的特殊社会中,在沪西侨为实现商业目的,展开各种经济活动,作为商人参与自治的重要途径,纳税人会议与工部局、领事团、公使团、清政府和租界华人拥有各种相互交错的利益。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之下,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社会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因,它们的博弈过程也就是社会演化的过程。
依托于列强强有力的武力威慑和保护政策,租界当局与各国领事团、公使团不断拓展租界,扩展自己的权力,事实上形成了以西人对华人的管理之下的社会生活圈。进入20世纪后,民族运动的高涨,华人不断要求满足自己的合法权益,租界的原有结构逐渐打破,租界原有的运转体制加入了华人的新鲜血液,形成了新的政治体制,租界也迎来了20世纪30年代的黄金发展时期。
[1]李东鹏.上海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制度研究:从《土地章程》、《议事规章》看纳税人会议[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
[2]上海市档案.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12)[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13)[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 SPECIAL MEETING OF RATEPAYERS(1897).上海: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公共租界西人纳税人特别会议材料,档案号:U1-1-820.
[5]李东鹏.上海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3.
[6]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1)[M].北京:三联书店,1957.
[7]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8]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2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9]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2)[M].上海:工部局华文处译述,1931.
[10]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16)[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1]李东鹏.租地人会议时期上海工部局财政收入研究[A].上海史国际论丛(1)[C].北京:三联书店,2014.
[12]上海华民住居租界内条例[A].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13]熊月之.开放与调适:上海开埠初期混杂型社会形成[J].学术月刊,2005,(7).
[14]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5]《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上海租界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16]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7]MEETING OF RATEPAYERS(1873).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纳税人会议记录册(1871-1893).档案号:U1-16-4813。
[18] MEETING OF RATEPAYERS(1875).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纳税人会议记录册(1871-1893).档案号:U1-16-4813。
[19]上海道瑞澂为工部局在租界外派捕收捐事致外务部电[C].清末上海公共租界史料选编[J].历史档案,1991,(2).
[20][法]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3)[M].北京:三联书店,1993.
(责任编辑 闵 军)
Game Interests:A Brief Review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Ratepayers' Meeting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nd the Others
Li Dong-peng1,Zhang Qing-tong2
(1.College of Communications and Humanitie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200235;2.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200235)
In modern times,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is an "Enclave" by the colli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s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uthorities, the ratepayers' meeting is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in the process of 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and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The ratepayers' meeting is an alien public gathering which represents the alien's overall interests in Shanghai and by hand of municipal, to realize the alien's variety interes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atepayers' meeting 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through the operation of the order of power and the public concession of municipal board, based in Shanghai consular corps, local governments, the Qing dynasty Beijing envoy group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such as game, from time to time is symbiotic, confrontation. And this kind of relationship promotes the prosperity of modern Shanghai city, as well a clue of the analysis of Shanghai urban evolution.
The Ratepayer's Meeting;The Municipal;Game Interests;The order of power
2015-06-10
李东鹏(1987-),男,山东淄博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K25
A
1672-2590(2015)04-007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