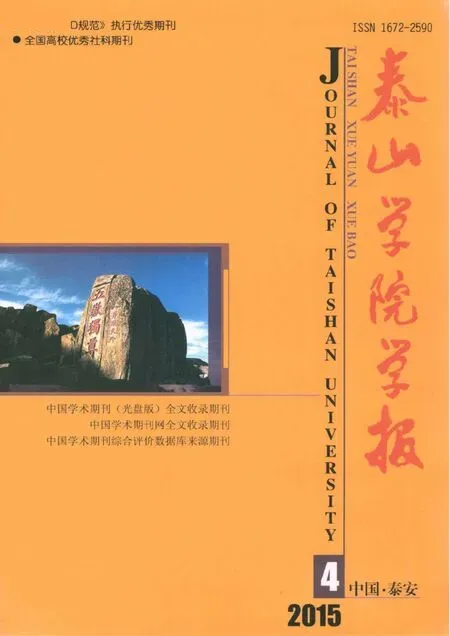四顶山奶奶庙“抱娃娃”习俗的人类学考察
郭 福 亮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四顶山奶奶庙“抱娃娃”习俗的人类学考察
郭 福 亮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安徽寿县四顶山的“顶”是与泰山信仰有关的道教建筑物的称谓,而非人们普遍认为的“山顶”的意思,每年三月十五奶奶庙庙会期间的抱娃娃习俗,是当地群众对碧霞元君信仰的一种体现。根据田野调查,对参与抱娃娃习俗的不同角色,从许愿者、还愿者、管理者三个视角进行解读,对“抱娃娃”习俗的灵验性、功能性、象征性、仪式性进行分析,得出抱娃娃习俗是人们精神层面的认知模式,是作为文化符号嵌入民俗的。
四顶山;抱娃娃;碧霞元君;庙会
一、四顶山奶奶庙的解读
四顶山位于安徽省六安市寿县境内,坐落于八公山脉。汉代淮南王刘安曾在此召集宾客,著成《淮南子》,传说刘安与“八公”在此修道炼丹,后得道成仙,现在山上仍留有“羽化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遗迹。
关于四顶山名字的来源,据当地一些居民讲:“四顶山有四个山头,所以叫做四顶山”,可知“顶”为量词,但由于开采石料,山体面积大幅度减少,周围已看不出其有四个山顶。关于“顶”的另外一种说法是:“顶”为名词。如武当山“金顶”,“碧霞元君庙无论建在山上,还是平地,都称之为顶,北京有东、南、西、北、中五顶,东顶在东直门外、大南顶在左安门外马驹桥、南顶在永定门外、西顶在西直门外蓝靛厂、北顶在德胜门外、中顶在右安门外草桥”[1]。“京师各顶,主要指北京城外几个有名的崇拜碧霞元君的寺庙,之所以称之为‘顶’,是指“祠在北京者,称泰山顶上天仙圣母”。清人则说得更具体:“祠庙也,而以顶名何哉?以其神也。顶何神?曰:岱岳三元君也。然则何与于顶之义乎?曰岱岳三元君本祠泰山顶上,今此栖此神,亦犹之乎泰山顶上云尔”[2]。“当然,除了碧霞元君各顶,也有其他寺庙被称之为顶,但无论如何这些顶都与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发生了一定的联系”[3]。嘉靖《寿州志》四顶山条:“州北七里,八公山上有东岳祠”[4],据皖西学院关传友先生考证:“四顶山庙为‘东岳庙’,始供奉神妃碧霞元君”[5]。据前文所述,可知四顶山的“顶”是与东岳庙有关的道教建筑物的称谓,而非人们普遍认为的量词四个“山顶”(山头)的意思。
有关四顶山老奶奶的传说,可谓家喻户晓。据李家景(男,46岁,寿县人,安徽文化网资深版主)讲:“前跟头,有一个小孩在四顶山上耍,遇到了一只老虎,老虎要吃掉这个小孩,这个时候老奶奶刚好路过,就踢出一只鞋,把老虎吓跑了,救了小孩。老奶奶救了小孩后,就走掉了,小孩家人为了感谢老奶奶,就到处找她,在山上找了很久,没有找到老奶奶的下落,只发现了老奶奶留下的一只鞋。后来,人们为了感激老奶奶,就在发现绣花鞋的地方建了个庙,来纪念她。”“每年三月十五有上百万人上山进香,开始山高头是个木头雕的老奶奶,面容慈祥,木雕不高,下面是莲花,大家都喊老奶奶,可能叫碧霞元君,五连洲公司开发四顶山,在泰山请来了碧霞元君,把碧霞元君的形象具体了,和全国各地的碧霞元君都统一了”。
现在四顶山上建有碧霞祠,供奉碧霞元君。碧霞元君作为泰山神之一,在“明代中期以后,一方面被道教吸纳进神灵系统,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另一方面又被民间宗教所吸收,使她在民间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6]。北京丫髻山的碧霞元君庙就是“明嘉靖中有王姓老媪发愿所建”[7]。明中叶以来的民间宗教大多是由北方向南方扩展,逐渐演变成南方本地的民间宗教,碧霞元君也渐渐传到南方,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历史上,寿县“北阻涂山,南抗灵岳名川,四带有重险之固,是以楚人东迁,遂宅寿春,徐、邳东海亦足守御,且漕运四通无患空乏”[8],为兵家必争之地,另外当地位于淮河、淝水交汇处,水灾频发,长期的战争和水灾造成大量群众死亡和流离失所。明朝初年徐贲(曾任河南左布政使)曾有《舟行经寿州》载:“问知古寿春,地经百战后;群孽当倡乱,受祸此为首;彼时土产民,十无一二有;田野满蒿莱,无复识田亩。”“战争、灾荒、疾病和贫穷导致群众存在较高的死亡率,人们不得不祈求神灵保佑平安健康,祈求多子多福,并导致了同样普遍的对生育的重视及高生育率”[7]。所以,即使引起高死亡率的因素逐渐减少以后,那种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及重男轻女等传统观念,造成了碧霞元君信仰的延续。由于寿县地区多战乱和灾祸,土著死亡较多或流离它处,现在的居民多为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迁山东济宁老鹳巷充凤阳府的移民后裔,所以寿春镇现在的饮食、方言等与山东济宁保留一些相似处。如:胡辣汤、蛤蟆、“银个子”(硬币)、“黄子”(脏话“东西”)等。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和淮河航运的发展,一些江淮商人来到山东经商,山东商人也到江淮地区经商,他们不仅发展了经济,而且促进了文化的交流。济宁“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9],“士绅之舆舟如织,闽广吴越之商持资贸易,鳞萃而蝟集”[10]。寿县地区的上述情况,都为碧霞元君信仰在当地的传播提供了文化生境,也保证了碧霞元君祠香火久盛不衰。
四顶山奶奶庙庙会是以四顶山上的庙宇为依托,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举行的群体活动。民国时期,淮河水运发达,寿县城内商业繁盛,庙会期间,居民祭祀神灵、祈求愿望,并伴有商业贸易、文艺表演等,山上和山下到处搭满各种棚铺,出售货物,更有各种特色小吃,北京烤鸭、天津大麻花等,应有尽有。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抓住香客心理和商机,在路边卖洗脸水,给进香人洗脸净面用,顺势吆喝着:“洗洗脸,净净面,前面就是阎王殿。”据李家景讲,“过去阎王殿位于山脚下,是上山进香的第一站,殿内有阎王塑像,烧香人在这里开始烧香上山,我老奶奶活着的时候,每年都去烧香,烧拜香,带磕头的,就是拿个小板凳,非常小,板凳上有个插香的香座子,到森林公园的山坡下面,就开始对着了,对着就开始一走一跪,往上一直到顶子,磕头到上面,看你真心不真心。还有过去呢,烧肉香,他把香,过去那盘香精彩,搞身上,使针线串上,从身上串通、挂上,用针扎通,使线串上,挂到肉高头,磕头上去,这类人呢,都是有大难之人,或者犯了很多大错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赎罪,香灰落在身上,烫的全是疤”。去阎王殿进香有诗云:“四顶高山庙接天,烟云袅袅情绵绵;河南信女敬香客,一叩一瞻到山巅。”卖香人喊唱着:“烧香敬敬神,保你头不疼;一步步,一层层,抬头就到南天门。”现在五连洲公司整合进香路线,把阎王殿改建为“白事阁”,内供奉阎王和地藏王菩萨,旁有牛头马面。“南天门”现为景区的十字路,向前直走,为奶奶庙建筑群,向西南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景点,向东北为“福禄寿”景点。
新中国成立后,道教活动在一段时间内被看作封建迷信,庙会也被作为“破四旧”对象,长期封杀。改革开放后,附近居民又自发地于农历三月十五日上山烧香、还愿、抱娃娃,庙会逐渐兴盛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地人民政府因势利导,利用古庙会举办物资交流大会,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二、“抱娃娃”仪式的“民族志”描述
四顶山奶奶庙,因传说老奶奶“虎口救子”,保佑孩子平安,人们纷纷山上进香,香火日盛。随着四顶山老奶奶信仰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碧霞元君神通广大,能疗病救人,尤其能使妇女生子,儿童无恙。于是,庙会期间居民多来此“抱娃娃”。抱娃娃习俗兴起于何时,今已不详。现存史料最早记载“抱娃娃”习俗的是嘉庆《凤台县志》:“士人相传祈子辄应,每岁三月十五,焚香膜拜者,远自光、固、颍、亳,牵车鼓楫而至,云集雾会,自昏彻旦”[11]。民国时期学者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寿春岁时记》载:“奶奶殿侧有一殿,亦塑一女神,俗呼曰送子娘娘。庙祝多买泥孩置佛座上。供人抱取,使香火道人守之,凡见抱取泥孩者,必向之索钱,谓之喜钱。抱泥孩者,谓之偷子,若偷子之人果以神助而得子,则须更买泥孩,为之披红挂彩,鼓乐而送之原处,谓之还子”[12]。当时,胡朴安认为“其事最可笑”,时过八十多年,中经“文革”,庙会期间上山抱娃娃者仍不计其数。
笔者曾于2010年、2011年两次参加庙会,并对“抱娃娃”习俗进行跟踪调查。根据“抱娃娃”期间不同角色的参与,可以分为许愿者、还愿者和碧霞祠管理者。
来抱娃娃者多为婚后不孕不育者或者想生儿子者,偶尔有一些新婚夫妇在父母的陪同下来抱娃娃。被抱取的娃娃分为男女,有布料、石膏、彩绘等材料制作,首先,许愿者要寻找要抱取的娃娃,古时称为“偷子”,是在庙里进行,现在要去草丛中寻找还愿者隐藏的娃娃。其次,许愿者找到可以抱取的娃娃后,要进行筛选,大多数先选择红布包裹着的“老娃娃”(注:老娃娃为之前许愿者抱走的娃娃,生孩子后归还的娃娃),然后看“老娃娃”是否完整,身体各个部位无裂纹、无残缺,选择性别、美丑,接下来选择一个或者两个娃娃,多数抱娃娃者会选择一个男孩或一男一女。选择好娃娃后,抱娃娃者则用自备的红布,将娃娃包裹起来,放在备孕的妇女怀中(腹部),然后给老奶奶磕头、烧香、捐功德钱。完成上述仪式后,许愿者要抱着娃娃回家,回家途中不要回头,如果离家较远,晚上赶不到家,需要投宿在宾馆或旅店,绝不能住亲戚或朋友家。抱娃娃者回到家后,将娃娃放在床头右侧七日,七日后取出放在安全的地方,妥善保管以免损坏。如果许愿者三年内生了娃娃,则要等庙会时上山还愿,如果三年之内,没有生娃娃,也要去还愿,将抱回家的娃娃送回山上。
还愿者,分为祈愿应验者和不应验者。许愿者愿望实现后,要上山还愿,将在山上抱回的娃娃取出,这个先前抱回的娃娃,此时则转化成“老娃娃”,老娃娃被赋予了灵验的神力。还愿时,除了将老娃娃送回,还要准备一些新娃娃,这些新娃娃被抱娃娃者赋予了老娃娃的子孙或下属,并且还愿者通过这种形式实现了自己子孙繁盛和高贵无比的愿景。同时,还愿者准备糖果、红鸡蛋(喜蛋)、香火、鞭炮等,上山还愿。还愿时,要把“老娃娃”和新娃娃放到一个石膏做的圆盘中,然后将其放到纸盒内,趁天黑放到山坡的草丛中,放置娃娃也有一定的技巧。放置娃娃,隐蔽程度一定要适中,人们认为如果放置的太暴露,容易被人发现,自己的娃娃长大后则不尊贵,不会成为人上人;当然,更不能太隐蔽,太隐蔽许愿者找不到自己隐藏的娃娃,娃娃不被许愿者抱走,不吉利,说明自己孩子没人“接”,没有被延续,象征无人“接子”,人们认为有断后之嫌。还愿者隐藏好娃娃后,则放鞭炮、烧香,向参加庙会的人们发糖果、鸡蛋,然后进大殿给老奶奶捐钱磕头。等到第二、第三年时,还愿者只放鞭炮、磕头、捐钱即可,则不需要准备娃娃。
当然,一些抱娃娃者,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愿望,等许愿后的第三年庙会,许愿者也要上山还愿。大多数不应验者还愿,抱男生女者,要购买几个女娃娃,其它仪式和应验者差不多。当然,一些许愿者三年之内无生育者,要将自己抱回的娃娃,送回山中,这个娃娃被认为“恶婴”,如果继续留在家中,会不吉利,所以许愿者不管情愿不情愿,都要上山还愿,将这个抱回家的娃娃放回山上,然后磕头,捐钱,这种情况只需上山还愿一次。
现在,四顶山归五连洲公司经营管理,庙会期间的抱娃娃,管理方也希望从中实现经济利益,于是规定不允许百姓自发的抱娃娃,许愿者和还愿者都要去公司指定的地点举行仪式,许愿者要统一购买管理人员准备的娃娃,捐喜钱;而还愿者则要购买他们的香,然后在老奶奶面前磕头,捐钱。同时,为了阻止抱娃娃者的自发行为,在许愿者和还愿者经常出现的地方,安排了一些工作人员负责没收还愿者的娃娃。
三、抱娃娃习俗的人类学分析
当地人谈到四顶山老奶奶,都会讲非常的“灵”。他们首先会从庙会期间的“洗山雨”和“刷山雨”说起。据说每年3·15庙会期间,四顶山都会下很大的雨。李家景讲:“庙会前,老奶奶会下雨,让那些心地善良、一心虔诚的人,干干净净、心情爽快的上山进香,此雨叫做“洗山雨”;三月十五庙会过后,老奶奶又会下雨,因为庙会期间人来人往,鱼龙混杂,好人坏人都来进香,老奶奶通过下雨将这些不够虔诚的人的气息、污秽,全部冲刷掉,所以叫“刷山雨”。2010年农历三月十四下午,开始非常晴朗,但走到半山腰,天气骤变,大风狂做,降起大雨,虽然当时有伞,但山上无处躲闪,人还是被淋湿,好在大家已经习惯了庙会期间的下雨。2011年庙会期间没有下雨,直到十七日才下了雨,但当地居民还是无数次向笔者讲“洗山雨”和“刷山雨”的故事,说老奶奶是多么灵验。灵验是老奶奶受到祭拜的最为核心的特质,这种灵验暗示着一方在“求”,而另一方要“应”的顺畅交流。因为灵验,权威才可以被称为权威,当然如果不灵验,“求”和“应”的交流便终结了,这种权威自然也就随之消亡了。显然,抱娃娃者大多知道许多时候他们抱娃娃并不能时时都能够应验。据调查,许多患有不孕不育症者,虽然抱了娃娃,但仍坚持治疗,直到看好病,生了娃娃。虽是在医院看好了病情,人们仍坚信是老奶奶保佑,并不能抹去老奶奶在他们心中灵验的地位。赵旭东教授在对河北范庄龙牌进行考察时指出:“社会的灵验,并不遵守物理因果律,它强调无一例外的灵验,这种无一例外的灵验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其背后有一种基于时间意义上的历史感在支撑,这种历史感是依循社会的秩序得以建构的。许多口头流传的灵验故事,正是因为有这种历史感,其影响力才会如此长久,随时讲来对于听者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13]。四顶山奶奶庙“洗山雨”和“刷山雨”的灵验故事,“老奶奶虎口救子”的传说,当地群众抱娃娃实现了求子的愿望,这些最初产生于个人的经验,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了公共表述的确认,进而演变成一种“地方性知识”得到认可。“这种认可便不能够通过不断的试验而得到否定,它永远是在对后来的肯定性灵验的个体经验加以吸收,而对不能应验的个人体验加以排斥。因此,个人祈求的不灵验,并不能够否定社会建构所直接强加来的灵验,很多时候祈求失验者往往都会反躬自问,反省自己的行为是否有什么不周全的地方惹怒了神灵,由此而出现了失灵的情形,而不会把责任追究到龙牌自身的不灵验上去”[13]。同样,抱娃娃中许愿者经历的不灵验,也会追溯到抱娃娃仪式过程中的各种禁忌,个人和家庭成员的品行、经历,甚至祖先的保佑、风水等都会成为不灵验者扪心自问的因素,总之,他们不会归罪于老奶奶的不灵验。反而,一些所谓灵验者的体验,即使是因为治疗或者试管婴儿得以生子,也归结为老奶奶的保佑,这种灵验的经验一传十、十传百的累积传播,更奠定了四顶山奶奶庙的灵验神奇,崇信者增多,而不灵验者也就更加怀疑自身,也变得“失声”。
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大师涂尔干,指出我们在研究某个社会现象的时候,应当注意区分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它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满足的功能。抱娃娃习俗,是我国子孙观念的反映。“在我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两代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夫妻生儿育女不仅是个人之间的事情,而且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社会性的关系总是相互的,父母一代给予子女的是抚养、教育、经济与服务性的支持和帮助,子女给父母的是赡养和情感安慰。所以,造成了东、西方社会具有不同的代际关系模式。中国社会主张家庭养老,相邻上下两代人具有抚养教育和赡养的相互责任与义务,因而两代人的关系是‘反馈’模式”。“你小的时候我养你,但等我老了的时候,你要养我”的简单行为逻辑。而“西方国家大多没有家庭养老的传统与习惯,只有上代人对下代人的抚养义务,而没有下代人赡养上代人的责任反馈,这部分责任转移到社会机构上,比如养老院、福利院等,因而两代人的关系是‘接力’模式”[14]。中国社会代际之间的反馈模式造成了中国人子孙观念的强烈,无子求子心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抱娃娃习俗的出现,也奠定了碧霞元君信仰在全国的传播。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可以使用符号。我们知道象征符号是具有至少两层意义的符号,第一层是符号的本意,第二层是符号经过类比或联想获得的具有象征性价值的意义。福柯认为:“符号与其所指的关系形式,通过适合、仿效、特别是同感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又说:“为了让符号成其为所是,符号在呈现为被自己所指称的物的同时,还必须呈现为认识的对象”[15]。抱娃娃的仪式过程中,“娃娃”则为符号,所谓巫术的符号,象征参加抱娃娃仪式习俗者的孩子,是具有生命的,所以与现实中的孩子一样,具有男女、美丑、健康与不健康、祖先和子孙、高官和平民,仪式过程中,充满了选择,这选择即是情感行为,也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泥娃娃作为表述、交流和传达居民生育、生活观念等信息的媒介,泥娃娃大致包含有三种功能。一是“指述功能”,主要指泥娃娃具有指述“娃娃”本身的命名、泥娃娃泥质、形似孩童的物理属性及其象征人们“子孙”的功能;二是“表述功能”,主要指泥娃娃具有显示人们的子孙观念、重男轻女观念、家庭观念,隐喻或象征着人们对子孙的期盼,反映了子女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三是“传达功能”,主要指泥娃娃在抱娃娃仪式过程中传达“神灵”与抱娃娃者的恩赐与感应,传递碧霞祠工作人员与“神灵”神圣与世俗,体现了工作人员与抱娃娃者、祈愿者与还愿者之间的互动。老娃娃和其他还原的娃娃,比工作人员卖的娃娃灵验,因为这些是象征着老奶奶的孩子,具有灵性,是神赐的;而山上卖的娃娃,则带有“商业性质”,许愿者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购买。工作人员卖娃娃,其认为作为“文化产业”的娃娃,是可以被消费的文化符号,所以他们采用垄断娃娃来源,进行宣传和促销,而对于抱娃娃者来讲,这个文化符号是嵌入民俗的,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无法用来买卖的。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治疗不孕不育征的医学水平得到提高,出现了试管婴儿,甚至可以实现“克隆人”,但是当地居民在相信科学的同时,仍上山抱娃娃。这说明,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情感的缺失,这个时候上山抱娃娃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要,是他们心灵的追求和寄托。科学的、现实层面人们进医院治疗不孕不育,而抱娃娃则主要体现他们的精神层面,两种不同的认知模式,并不冲突。总之,抱娃娃习俗为我们了解寿县地区民风民俗,理性认识乡土社会提供了契机和思路。
[1]李鸿斌.庙会[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3.
[2][3][7]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353.354.23.
[4](明)栗永禄纂修.嘉靖寿州志[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33.
[5]关传友.皖西地区庙会的文化考察[J].皖西学院学报,2011( 1).
[6]叶涛.论碧霞元君信仰的起源[J].民俗研究,2007,(3).
[8](清)曾道唯修.葛荫南纂.光绪寿州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31.
[9][10]康熙济宁州志(卷2).
[11] (清)李师沆.石成之修.凤台县志[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88.
[12]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284.
[13]赵旭东.从交流到认同——华北村落庙会的文化社会学考察[J].文化艺术研究,2011,(4).
[14]许宪隆.家族构成与近现代穆斯林家族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4).
[15]米歇尔·福柯.词与物[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2:80-81.
(责任编辑 梅焕钧)
An Anthropology Study of "Bao Wa Wa" Custom on Four-top Mountain Nai Nai Temple
Guo Fu-lia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iao Cheng University, Liao Cheng 252000, China)
The “top” in Four-top Mountain means the Taoist building appellation about Taishan, rather than the wide belief of being “the peak of the mountain” in Shouxian of Anhui province. Local people take part in the Nai Nai Temple Fair on lunar month March 15th every year. During the fair there are“Bao Wa Wa” custom, which expresses the belief of Bixia Yuanjun. This article is on the basis of my fieldwork, to analyze from the different roles of the wishers, the votive person and administrators involved in the custom. Then conclusion is drawn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efficacious, functional and symbolic rituality of the custom that the custom reflects local people's spiritual cognitive mode, a cultural symbol embedded into folk life.
The Four-top Mountain; Bao Wa Wa custom; Bixia Yuanjun; Temple fair
K892.4
A
1672-2590(2015)04-0024-05
2015-05-17
郭福亮(1985-),男,山东济宁人,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