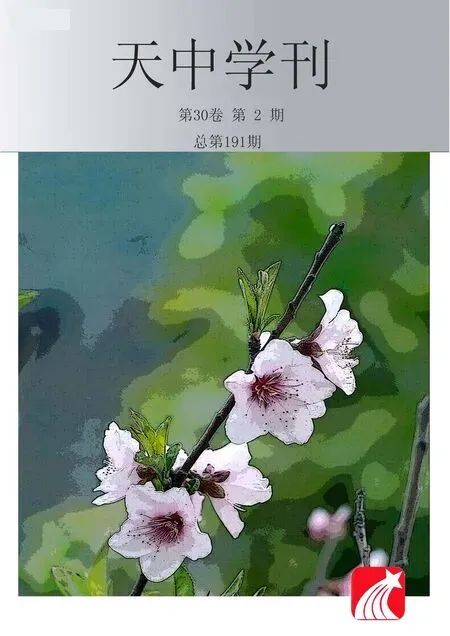闫玉立
“谐里耳”与“入文心”——李渔与金圣叹戏曲理论比较
闫玉立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 450001)
金圣叹的《西厢记》批评和李渔的《闲情偶记》都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史上的经典之作。对于金圣叹的戏曲批评,李渔声称“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而对自己的创作实践,李渔则自评为“好看词多,耐看词偏少”。从戏曲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造成二者差别的原因主要是:一者求“谐里耳”,一者求“入文心”。
戏曲理论;李渔;金圣叹;谐理耳;入文心
金圣叹(1608―1661年),生平颇具传奇色彩,姓名也多异说。清人廖燕《金圣叹先生传》载,金圣叹,名采,字若采,吴县诸生;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喜欢饮酒,又善衡文评书,明清鼎革后绝意仕进,除友朋谈笑外,惟于贯华堂中以读书著述为务。金圣叹所评诸书俱能领异标新,其中《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为其戏曲批评力作。
金圣叹的《西厢记》批点,包括篇首总序、总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以下简称《读法》)及各章总批、节批和夹批。圣叹评点问世以后家传户诵,然毁誉参半。毁者如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甚至认为金圣叹“于戏曲是门外汉”,“他的评论是门外汉的评论”[1]525;誉者如清代小说评点家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认为金批《水浒》《西厢》,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
对于后世抑扬过实、褒贬悬如天壤的金圣叹戏曲批评,李渔可谓鉴而能精,玩而能核,做出折中之论。李渔,初名仙侣,后改名渔,字谪凡,号笠翁,明末清初文学家、戏曲家。在创作实践上李渔有十部传奇剧作,他还亲自带领家班四处演出,理论上又有一部《闲情偶寄》,其中“词曲部”论述戏曲创作方法,“演习部”论述戏曲教习、搬演方法,其评价自是行家之见。我们认为,如对金、李二家理论加以比较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二者在评批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认为自从《西厢记》问世四百余年来,推《西厢》为第一者不计其数,而能道出其所以为第一者只有金圣叹。然而,“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极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然以予论之,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自撰新词几部,由浅及深,自生而熟,则又当自火其书而别出一番诠解。甚矣,此道之难言也”[2]85。可见,李渔与金圣叹对于戏曲之见解同异互出,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比较。
一、金、李二人对人生及戏曲功能之认识 金批《西厢记》序一《恸哭古人》开篇即云:“或问于圣叹曰:《西厢记》何为而批之刻之也?圣叹悄然动容,起立而对曰:嗟乎!我亦不知其然,然而于我心则诚不能以自已也。”[3]1为什么不能自已呢?金圣叹接着说:“今夫浩荡大劫,自初迄今,我则不知其有几万万年月也。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然而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而消遣之?……无端而忽然生之,又不容少住者,又最能闻声感心,多有悲凉。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同欲失声大哭乎哉!乃古人则且有大过于我十倍之才与识矣……嗟乎!是则古人十倍于我之才识也,我欲恸哭之,我又不知其为谁也,我是以与之批之刻之也。我与之批之刻之,以代恸哭之也。夫我之恸哭古人,则非恸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3]1 置身绵邈宇宙,个体生命曾不能以一瞬,其短暂渺小如蜉蝣寄于天地,如沧海一粟。不仅“暂有之我”的生命及平生作为将如水逝云卷,无不尽去,“十倍于我之才识”的古人亦复如此。居此无情天地,怎能不放声恸哭?于是,金圣叹的批书行为就成了恸哭古人与自我消遣的方式。同样,古人作书也正是为了记载自己的生命轨迹,承载自己的才识。这样一来,作者所作之书中的人与事皆不必实有,即使为实有,其人亦必不能知身后有作者会写之而告诉之,而作者也不能超越时空追问于古人。因此金圣叹作书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书中人与事皆不过是其传达胸中情感之道具而已。恰如韦勒克所说,“小说家的各个潜在的自我……都是作品中潜在的人物”,作家“所描绘的各种人物的内在生活是来自他自身警觉的内省经验”[4]87。所以,谢柏梁也指出金批包含这样的意思:“金西厢绝不是‘愉快其心’、自娱娱人的喜剧作,更不是写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艳情作乃至宣淫作,而是一部‘泄尽天地妙秘’、展示生活苦痛无常而情感终归虚空的人生悲剧之形象教科书。”[5]351 同金圣叹非常相似,李渔同样认为人生是大可悲伤的。他在《颐养部·行乐第一》中说:“伤哉!造物生人一场,为时不满百岁。彼夭折之辈无论矣,姑就永年者道之,即使三万六千日尽是追欢取乐时,亦非无限光阴,终有报罢之日。况此百年以内,有无数忧愁困苦、疾病颠连、名缰利锁、惊风骇浪,阻人燕游,使徒有百岁之虚名,并无一岁二岁享生人应有之福之实际乎!又况此百年以内,日日死亡相告,谓先我而生者死矣,后我而生者亦死矣,与我同庚比算、互称弟兄者又死矣。噫,死是何物,而可知凶不讳,日令不能无死者惊见于目,而怛闻于耳乎!是千古不仁,未有甚于造物者矣。”所不同的是,面对如此不仁天地,李渔没有采取“恸哭”的方式,而是认为“乐不在外而在心。心以为乐,则是境皆乐;心以为苦,则无境不苦”。他不但自己要及时行乐,而且劝人及时行乐。他发现戏曲最能引人入胜,进入无限快乐境地。《词曲部·宾白第四·语求肖似》云:“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觉富贵荣华,其受用不过如此,未有真境之为所欲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致仕,则转盼之际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元配;我欲成仙作佛,则西天蓬岛即在砚池笔架之前;我欲尽孝输忠,则君治亲年,可跻尧、舜、彭篯之上。”[2]63−64而且,李渔身经易代家道中落,故自称“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而著书”[6]130。他填词非但不卖愁,且以一夫不笑为忧,他要给观众带去欢笑以赢得观众,从而为数十口家人筹得生计。李渔《笠翁诗集·偶兴》称“尝以欢喜心,幻为游戏笔”,他要发挥戏剧的娱乐功能,以戏剧自娱娱人,而非发愤著书寄托人生悲苦之情。苗族人民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可以说是顺其自然。当地婚庆大典时新郎、新娘以及双方的家人亲戚均会盛装出席,特别是新娘的服饰更为整齐,由于苗族银饰的整体性特征,新娘一般会同时佩戴银凤冠、银项圈、银披肩、银钻花腰链、银脚环等。举办大型活动时也是如此,居民们也会穿上特色的服装,戴上苗族银饰以示隆重。这些活动也无形中促进了苗族银饰的流传以及其锻造艺术的传承。 所以,李渔剧论注重演出效果,以适于演出为目的。然而长处也造成其短处,正因他刻意迎合士绅声色之娱及其道德伦理要求,加之创作轻率,故而殊乏深致。选择我院2016年2月—2018年5月收治的90例胃部疾病检查患者作为实验对象;男41例,女49例;年龄分布范围为19岁~81岁,平均年龄为(65.39±5.35)岁;伦理委员会对于此次研究均同意批准,所有胃部疾病检查患者以及家属共同完成知情同意书签署。
二、“取其文心”与“专为登场” 金圣叹在《读法·第二十三》中说:“仆幼年最恨‘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君’之二句,谓此必是贫汉自称,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计耳。若果知得金针,何妨与我略度。今日见《西厢记》,鸳鸯既已绣出,金针亦尽度,益信作彼语者,真是脱空谩语汉。”[3]13他批点《西厢记》就是以庖丁解牛的方式将这些“眼法”“手法”“笔法”“墨法”一一呈现于人们眼前,并且认为如果自己将“金针”略度,使人掌握了这些“眼法”“手法”“笔法”“墨法”,人们便“不单会写佳人才子也。任凭换却题,教他写,他俱会写”[3]18。那么,金圣叹是形式主义或唯技巧论者吗?当然不是!要想达到他所说的“若教他写诸葛公白帝受托,五丈出师,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孤忠老臣满肚皮眼泪来”;“若教他写王昭君慷慨请行,琵琶出塞,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高才被屈人满肚皮眼泪来”;“若教他写伯牙入海,成连径去,他便写出普天下万万世无数苦心力学人满肚皮眼泪来。”[3]18这样一种审美效果,仅仅依靠形式、技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观者与作者的情感共鸣,故而他说:“《西厢记》不是姓王字实甫此一人所造,但自平心敛气读之,便是我适来自造。亲见其一字一句,都是我心里恰正欲如此写,《西厢记》便如此写。”[3]19他认为《西厢记》绝不是作者王实甫一人的文集,而是他“平心敛气向天下人心里偷取出来”的“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也只有如此才能成为“妙文”。反之,如果“非天下万世人人心里所曾有”,则是“不妙之文”,就不可能使人共赏进而产生情感的沟通与共鸣,“便可听其为一人自己文集”[3]19。也就是说,妙文来自“天下万世人人心里”,方成妙文。尽管引起人们或忧或喜的具体事件是千差万别的,但思亲怀友与男女怨慕、爱国忧时与劳人思妇自有其情感相通之处。所以刘永济说:“夫情,公也。事,私也。私者因人而异,公者亘古无殊……然则作者之本事,虽不可知,而文中之公情,自不难见矣。”[7]33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正是通过具体事件,又超越具体事件以寄托人们心中普遍的情感,来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亦如柏格森所说:“艺术家把我们带到情感的领域,情感所引起的观念越丰富,情感越充满着感觉和情绪,那末,我们觉得所表现的美就越加深刻、越加高贵。”[8]12金圣叹的理论正是要将观者引入这种情感的领域。 李渔在充分肯定金圣叹《西厢记》批评的前提下,认为其批评是“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那么,李渔所说的金圣叹“犹有待”的“优人搬弄之三昧”究竟是什么呢?李渔是戏曲班主,他的戏曲理论最显著的特点是剧场性、商业性,他要的是适合演出的能够吸引观众的戏剧。李渔之所以要“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2]17,“词采似属可缓,而亦置音律之前”[2]18,正是因为他有“填词之设,专为登场”[2]86的认识,并认为惨淡经营、用心良苦的时髦所撰,之所以“不得被管弦、副优孟”,只能置于案头供文人把玩,并非因为韵律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结构全部规模之未善也”[2]18。他自己作剧时“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2]65。他又提倡戏剧的娱乐性:“戏法无真假,戏文无工拙,只是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2]83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是一种全球性栽培、适应性广、营养价值高、适口性优良的饲料作物,有“牧草之王”的美誉,已成为我国农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决定着我国农业生产和发展动脉,对畜牧业发展起到大力推进作用[1-3]。苜蓿在国内是优质饲草,每年进口的苜蓿干草市场份额占总进口干草总量的90%[4]。我国苜蓿在北方种植利用较多,但近些年随着对苜蓿研究及其利用的深入及南方畜牧业发展的需要,苜蓿种植区已由原来的北方逐步向南方扩展[5]。目前,贵州省对部分引进紫花苜蓿品种正进行大量的推广种植[6]。 可见,李渔的戏曲理论是以适于舞台演出和满足观众需要为第一位的。这是他对当时戏曲创作偏颇及自身创作、演出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折肱之识。于是,李渔自诩秉持“文章者,天下之公器”以为心,要将生平底里和盘托出,为人们传授一套可供戏剧创作演之场上的“法脉准绳”。因此,尽管金圣叹与李渔同样重视作者在文学艺术中的作用,同样声称要为人拈出“金针”、总结“法脉准绳”,二人的出发点却不同,一者为“文心”之“金针”,一者为“登场”之“法脉准绳”。
三、“止为写得一个人”与“止为一事而设” 戏曲创作要塑造人物与叙述事件并重而不可有所偏废。金圣叹的《西厢记》批评实际上是一种抒情理论,以塑造人物、表现人物情感为中心,通过“我”之枢纽作用,以沟通古人、后人为旨归;而李渔的理论则带有强烈的娱乐追求,他关心的是如何上演一个有趣而人人爱看的故事。也正因此,“金圣叹的小说、戏曲已以人物为中心,李渔却又回到了以事件为中心”,“换言之,不是写事为写人服务,而是写人为写事服务。这种情节中心论就显然比金圣叹的理论倒退了。但绝大多数的观众和读者对戏曲和小说的兴趣都集中在情节,李渔的这种理论也还是要作者迁就绝大多数观众的艺术趣味”[9]312。精读部分,笔者按照文章段落设置,分成三个环节,每个部分设计了不同的任务;三个环节的任务设置由易到难,并且每个环节结束都有小结,忠于原文而又高于原文。第一段的阅读任务是将原因和结果匹配起来(见图1)。 金圣叹认为《西厢记》中的主要人物有三个:一个是莺莺,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其余如夫人、法本、白马将军、欢郎、法聪、孙飞虎、琴童、店小二等,都不过是写三个主要人物时“所忽然应用之家伙”。而三个主要人物中又有主次之分,只有崔莺莺才是中心人物,所以在《读法·第五十》中他又说:“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若使心头无有双文,为何笔下却有《西厢记》?《西厢记》不止为写双文,止为写谁?然则《西厢记》写了双文,还要写谁?”另两个主要人物红娘、张生都是作者为了表现中心人物崔莺莺而不得不写的人物,也就是说写红娘和张生都不过是手段,说到底是为写崔莺莺服务的。所以,“《西厢》之作也,专为双文也”[3]48。 与金圣叹不同,李渔所期望的是能够演之场上娱乐大众的、好看的故事。因此,与金圣叹全力塑造“此一个人”论根本不同,他认为戏剧的中心是事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2]24其中,j、r国分别代表对象国 (中国)和参照国 (世界),m国代表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Ijm、Irm代表中国和世界向m国出口的机械运输设备产品 (SITC Rev.3第7类的214种4分位产品的集合),Ijm⊆Irm,x、q、p代表出口产品的价值量、数量和价格。EMjm等于中国对m国出口的Ijm种机械运输设备总额占世界对m国出口的Irm种机械运输设备总额的比重;从经济学的含义来看,扩展边际实际上表示了中国与世界出口到m国重叠商品贸易量占世界总贸易量的比重,则EMjm值越大,说明中国向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的产品种类越多。 为了实现其“登场”目的,比之金圣叹的“止为写得一个人”,李渔的“止为一事而设”确实是有所倒退的。然而,李渔对戏剧适俗性、商业利益的追求并不总是与其艺术性相抵触,如他提出要“说何人,肖何人,议某事,切某事”,要“说张三要像张三,难通融于李四”[2]38,为人物安排宾白要设身处地充分发挥想象,“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2]64。可见,李渔对于人物形象塑造也并非全无认识。
四、论“曲折”与“贵显浅” 圣叹所重在发明文心、塑造人物并表现人情,笠翁着眼于如何上演一个有趣的故事以赢得观众。因此,一以曲折高雅为妙,一以显浅适俗为贵。 金圣叹眼中的读者是欣赏水平较高的“才子”,他们面对“文心漩洑”的曲折妙文,能够“纵心寻其起尽以自容与其间”,以之为“天下至乐”,而不曾顾及戏剧演出的时间性及不同观者参差不齐的文字理解能力。在《读法·第七十九》中,他甚至说:“《西厢记》乃是如此神理,旧时见人教诸忤奴于红氍毹上扮演之,此大过也。”然而,到了李渔那里,这种曲折妙文却“止可作文字观,不得作传奇观”,非加以转换不可。戏剧文本由曲文和宾白两部分组成,李渔与金圣叹的“曲折”理论截然异趣的“显浅”处,也就于此两部分体现出来。就曲文而言,李渔认为曲文的遣词造句要与诗歌散文判然相反。诗文之词采贵典雅含蓄,而词曲却不是这样,因为“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2]40。所以“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2]34。他推崇元人的本色自然,不满惨淡经营、语欠明爽的剧本,甚至批评汤显祖《牡丹亭》中精彩的“惊梦”“寻梦”二折“虽佳,犹是今曲,非元曲也”。至于宾白,李渔道:“尝谓曲之有白,就文字论之,则犹经文之于传注……故知宾白一道,当与曲文等视,有最得意之曲文,即当有最得意之宾白,但使笔酣墨饱,其势自能相生。”[2]61李渔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对曲文与宾白的不同作用有着清楚的认识,他认为:“至于新演一剧,其间情事,观者茫然;词曲一道,止能传声,不能传情,欲观者悉其颠末,洞其幽微,单靠宾白一着。”[2]66宾白承载着向观众传递剧情的作用,故其通俗易懂也就格外重要了。
五、关于“淫”的问题 《西厢记》自问世以后,誉者无数,有人比之《春秋》;毁者亦无数,将其入“秽恶”之列。金圣叹说:“《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他先是诅咒那些骂《西厢记》是淫书的人“定堕拔舌地狱”,既而宣称《西厢记》“乃是天地妙文,自从有此天地,他中间便定然有此妙文”。虽然“酬简”一折有关于崔张性爱的描写,但“细思此一事,何日无之,何地无之?不成天地中间有此一事,便废却天地耶!细思此身自何而来,便废却此身耶?”于是,“今后若有人说是妙文,有人说是淫书,圣叹都不与做理会”[3]8。 金圣叹深悟古人寄托笔墨之法,对于《西厢记》中“此一事”的描写,他坚决为其辩“淫”,但他决不提倡为淫而淫、哗众取宠的色情言行。他认为古人著书是自我抒写,其命意吐词绝非漫然为之,必定自爱其言。“所撰为古人名色”,实际却是“我一人心头口头吞之不能,吐之不可,骚爬无极,醉梦恐漏”,“如径斯曲,如夜斯黑,如绪斯多,如蘗斯苦,如痛斯忍,如病斯讳”“胸中若干日月以来七曲八曲之委折”。作为《西厢记》的知音,金圣叹极力维护崔莺莺,“开卷惟恐风吹,掩卷又愁纸压,吟之固虑口气之相触,写之深恨笔法之未精”。对于书中续作部分抵突莺莺的描写,表现出“王蓝田拔剑驱苍蝇,着屐踏鸡子”般大怒[3]257。故而,金圣叹对“于生旦出场第一折中类皆肆然早作狂荡无礼之言,生必为狂且,旦必为倡女”的“近今填词之家”甚至破口大骂:“是则岂非身自愿为狂且,而以其心头之人为倡女乎?”[3]47并呼吁“自今以往,慎毋教诸忤奴于红氍毹上做尽丑态,唐突古今佳人才子哉”[3]79。同时,对于读者也加以限制,《读法·第六》说:“当初造《西厢记》时,发愿只与后世锦绣才子共读,曾不许贩夫皂隶也来读。”以免有人“不惟不解其文,又独甚解其事”[3]192。 对于“动及淫邪之事,有房中道不出口之话,公然道之戏场者”的做法,李渔似乎是不满的。然而绎其实际,他不过是不满恶声有污雅人正士之耳,男女同观而有伤风化。为此还特特教人以“善谈欲事”之法,如“说半句,留半句,或说一句,留一句”或“借他事喻之,言虽在此,意实在彼”,其效果却是“欲事不挂齿颊,而与说出相同”“欲事未入耳中,实与听见无异”,并不无得意地宣称“得此二法,则无处不可类推矣”[2]74。那么,对于淫亵,他究竟是戒是劝,也就不言而喻了。李渔之所以要这样做,说到底是为了迎合世俗,赢得更多的观众。验诸其创作实际,李渔一些剧作存在着严重的媚俗、趋俗倾向,如《玉搔头》中就存在大量不必要的秽亵之语,就连其代表作《风筝误》也未能免俗。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评曰:“然根本立意之近乎儿戏,以及趣味低级,遂令吾人有所不满焉……然秽亵之语,往往屡出不惮,则大损雅意矣!”[1]525 可见,对于“淫”的问题,李渔与金圣叹看似有相同处,实际则相去甚远。金圣叹是辩而实戒,为了成就其妙文而“借家家家中之事,写吾一人手下之文者,意在于文,意不在于事也”[3]192;而在李渔那里,恐怕就是戒而实倡,为了赢得俗众而不惜“意在于事,意不在文”。 王国维曾说:“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10]32而“圣叹评《西厢》,全是文人见地,于戏曲之甘苦,未能深知。至李渔则以戏曲家而论戏曲,其中甘苦,言之娓娓,此则吾国文学批评中仅有之人才也”[11]335。当然,如本文所述,李渔之论亦非全璧。正所谓“成也登场,败也登场”,笠翁戏剧理论及剧作实践之长处是适于登场演出,能够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而其短处也恰恰是因为要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而牺牲了丰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因媚俗而不惮屡出的低级趣味与秽亵之语。金、李二家,诚能合其两长,各去所短,方为兼美之作。明代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中说:“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我们认为金、李二家理论正复类似,其差异正是一者要“入于文心”而求雅忌俗,一者要“谐于里耳”以争取观众的不同理念所致。 参考文献: [1] [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M].王古鲁,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2] 李渔.闲情偶寄[M].江巨荣,卢寿荣,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林乾.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2卷[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4] 韦勒克.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 [5] 谢柏梁.中华戏曲文化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李渔.李渔全集:1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7] 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M].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9] 章培恒,等.中国文学史新著:下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Whether using medications or acupuncture,the doctors of Chinese Medicine tried to change the law of Qi and blood,promote follicle and egg development,and improve ovulation disorders.16-19,21 ②饮食目标:根据患者的饮食习惯、病情,为患者固定饮食方案,注意饮食搭配,并控制脂肪、蛋白质、钠盐摄取量。教育患者学会自我计算食物营养值,学会采取食物代替法,保证日常营养所需的同时,控制血糖水平。除此以外,患者还需要摄入高纤维食物和新鲜水果。 [10]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除上述的问题外,税改之前建筑企业在计算营业稅时,所根据的主营业务是含税收入,而税改之后的主营业务收入为不含税收入,增值税被独立出来。因此,财务指标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11] 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刘小兵〕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2015)02−0083−05 收稿日期:2014-10-12 作者简介:闫玉立(1982―),男,河南辉县人,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