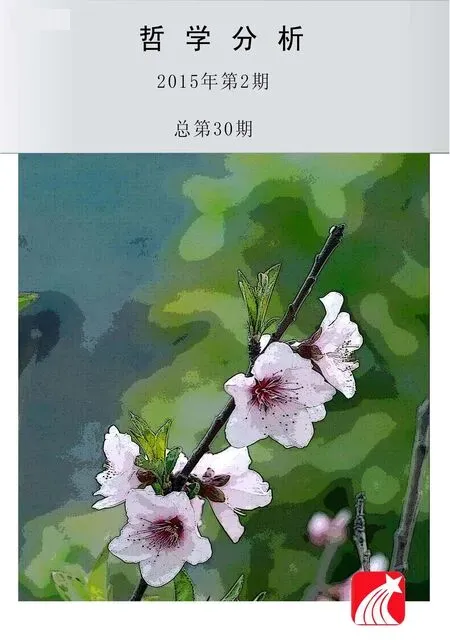当代法国哲学的美利坚之旅①
杨兆锭
随笔与访谈
当代法国哲学的美利坚之旅①
杨兆锭
法美之间可以说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从15世纪开始,欧洲列强,尤其是英法对美洲大陆所进行的大规模殖民为这种情结播下了种子。法美之间的关系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浪漫,它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彼此政治经济利益斗争中的一盘棋。两国的关系经历过很多次危机,但从来没有彻底破裂过。众所周知,美国独立战争的敌人是英国,而英国也正是当时法国的敌人,所以后者选择支持美国。德·拉法耶特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这位杰出的年轻法国将军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与华盛顿并肩作战,最后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重要历史人物。现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有以这位法国将军命名的街道。这可以说是法美情结的真正开始。
在强调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时,法国喜欢提醒美国不要忘了德·拉法耶特将军和自由女神像,美国则炫耀诺曼底登陆和马歇尔计划,俨然是当代法国的救星。总之,当代法美的历任总统,不管他们之间存在多大分歧,都不得不把两国关系看得至关重要。戴高乐总统曾经采取过很多遏制美国霸权的行动,而且他所领导的法国也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不过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他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美国。“9·11”事件后,美国对法国不支持伊拉克战争耿耿于怀,以至于美国国会有些议员气愤之下提议把法国薯条改为“自由薯条”,以表示对法国的强烈不满。但是后来小布什还是接受了新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伸出的橄榄枝,两人携手改善法美关系。奥巴马总统也不例外,他从进入白宫的第一天起就把美法关系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追溯法美关系史,人们可以发现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直到19世纪才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法美关系一度相当紧张,几乎停止一切来往,直到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时两国才重新开始一些小型的文化交流。托克维尔(Alexis Tocqueville)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834年访问美国的,并于1835年出版了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从普法战争到二战爆发,法国是欧洲唯一重要的民主共和国(第三共和国),美国特别看重这一点,所以也特别支持法国。这使两国关系趋于稳定并不断巩固,因而也激活了彼此间的文化交流。因为倾慕法国文学、哲学、艺术、戏剧、电影、时装、葡萄酒以及烹饪,一时间,美国知识分子、画家、作家、艺术家等纷纷来到巴黎。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巴黎获得了巨大成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黑人占主导的爵士乐得到巴黎人的青睐。当代法国哲学的美利坚之旅正是法美思想文化交流在当代的继续。
一
在纳粹肆虐的10年间,美国逐渐变成了欧洲文学艺术的避难所。欧洲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大量涌入,使美国本土的文学艺术直接接触并吸取了欧洲的前卫因素,客观上结束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文化闭关自守。其结果则是文学艺术的霸主地位渐渐从巴黎转向纽约。
纵贯法美文化思想交流,三个“历史事件”构成了当代法国哲学登陆美利坚的三部曲。第一个“历史事件”与“流放”二字连在一起。这是因为二战期间,大批法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纷纷被流放到美国,其中大多数是犹太和左翼知识分子及艺术家。尽管美国当时对移民尤其是难民控制很严,但是大学教授是宗教领袖之外唯一不受入境数额限制的人群。仅1941年就有两万多法国人来到美国,其中不乏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结果,这些被流放到美国的法国大学教授和学者成了法美大学及研究机构之间合作的开拓者。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洛克菲勒基金会先后与巴黎人类博物馆的人种学研究所(Institut d’Ethnologie du Musée de l’homme)以及巴黎社会资料中心(Centre de Documentation Sociale de Paris)签署了合作协议。在多所大学的支持下,由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牵头,高等研究自由学院(魪cole Libre des Hautes魪tudes)于1941年11月在纽约成立。这是迄今为止法国在美国的唯一一所高等学府。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cobson)等都在这里授过课。流放生活使流放者失去了以往的优越感:社会上成了弱势,文化上没有了根基,语言上成了瘸腿,政治上被视为另类,这种处境直接影响当代法国哲学的观点和立场。
第二个“历史事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对美国的知识出口。这里所说的知识出口主要是指战后法国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和巴黎“年鉴学派”对美国的影响。美国二战前和二战后对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的态度截然不同。法国超现实主义艺术展于1931年首次在美国纽约举行,当时引起关注的并不是大学校园和其他学术机构,而是时装杂志、广告公司、电影娱乐行业和新闻媒体。超现实主义艺术一时间被看作是时髦前卫的象征。当超现代主义艺术成为红极一时的文化消费品时,它不仅成为道德卫士讨伐的对象,而且也被左翼理性主义者斥为站在“当今最反动的运动”一边,是对那种奴役人的黑暗力量的过分挖掘。二战后美国对待超现代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时候关注它的主要是大学校园,而不是战前的大众文化圈;有关这方面的争论也不再引起愤怒。这实际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被美国大学规驯和制度化的过程。这个文学艺术流派所持的反教会和亲共立场有意被忽略,最后在“法国文学”的标签下被放在象征派和存在主义之间,成功登上学术殿堂。20世纪50年代后,随着超现实主义日益成为文学史的服贴对象,研究它的学者专家应运而生。他们的研究总体上都倾向于把超现代主义看做是纯粹的文学艺术运动,完全去掉它的认知和政治方面的内涵。虽然法国学者高梯叶(Xavière Gauthier)的《超现实主义与性》①Xavière Gauthier,Surréalisme et sexualité,Paris:Gallimard,1979.一书引起了一场女权主义论战,但是60年代以后,除了在大学校园内,超现实主义已基本上从美国公众的视野里消失。
美国观察家们习惯于把欧洲文化生活归结为一系列时髦。在超现代主义失宠之后,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又成为美国人的新宠。追随这个新时髦的正是战前推崇超现实主义的那群人。实际上,美国知识精英被萨特所吸引是一件很自相矛盾的事:首先,萨特其人以及他所代表的法国式的彻头彻尾公众知识分子形象与美国人的理想大相径庭;其次,虽然萨特对自己1945年在纽约所体验到的美国式自由欣赏有加,但他毫不掩饰自己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反美态度。②参见Jean-Paul Sartre,“Americans and their Myths”,in The Nation,18 October 1947。他经常拒绝和任何美国人对话,并认为不可能和美国有任何真正的学术交流。萨特在大学之外的时髦既短暂又流于表面,这多半出于异国风情的吸引力和新闻媒体的渲染。相比之下,萨特和存在主义走进美国大学校园的过程则是循序渐进和深刻的。虽然美国哲学一向对欧洲大陆哲学抱有成见,但它还是为研究萨特留下一片空间。美国哲学家们解读萨特作品时选择性很强,其目的就是要使后者的思想观点美国化。例如,面对有神论和宗教问题,他们把萨特哲学装扮成一种主观主义唯灵论;面向女大学生,他们把德·波伏娃的某些作品,尤其是她的《第二性》吸收到教学大纲里,希望借此在哲学系里听到女性的声音和开始将女权问题理论化;面对美国实用主义,他们把萨特解读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式的“激进经验主义”,因为两人都特别关心意识如何在一个能产生意义的世界里形成;最后,面对自由主义传统,他们把萨特说成是“激进个人主义”,这比集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存在主义于一身的那个萨特更能被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接受。这样,被美国化的萨特一度吸引了大批学生,使招生不足的美国大学哲学系出现生机,使存在主义一步一步走进美国高等学府。《存在与虚无》于1956年在美国出版,以后多次再版;美国哲学协会多次举办萨特哲学研讨会;1962年美国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哲学协会①哲学家约翰·威尔德(John Wild)与其同事以及过去的弟子于1962年创建了“存在哲学和现象学学会”。威尔德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哈佛大学讲授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后于1961年离开哈佛,前往西北大学哲学系担任该系系主任。的成立标志着萨特被最后认可。不过,即便是美国化的萨特研究也好景不长。由于学生运动、大学专业化、人文学科尤其是哲学学科的危机,萨特的存在主义在美国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急剧下降。
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于1947年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创立了第六研究所,即历史研究所,并同时创办了名为《年鉴》(Annales)的研究刊物。巴黎“年鉴学派”因此而得名。这个学派主张历史学科既要涵盖思想和知识等丰富领域,充分肯定横向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要注重对历史进行形而上反思,后者主要受德国社会学影响。这种新思维、新方法和新视角给当时沉闷的历史学科带来了生机。因为当时的美国史学界已经进行了大调整,所以巴黎年鉴学派的影响受到限制,不过当时美国的年轻史学研究者还是从中受到很大启发,纷纷尝试从巴黎年鉴学派那里为自己的研究寻找理论根据。他们在探索元历史的同时,开始对有关部门知识的历史发问,使社会生活历史化。年鉴学派的这种影响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福柯②作为历史学家,福柯深受年鉴学派的影响,主张从文化、政治、社会和文学等不同方面综合考察历史,他和年鉴学派的反人本主义立场一致。在美国的影响铺平了道路。
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和代表“新历史”的巴黎年鉴学派之所以能被出口到美国,那是因为这些思潮正好与当时美国所感兴趣的主题相呼应:当时的美国人热衷诗歌和神秘主义,超现实主义正中下怀;他们推崇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存在主义受到欢迎;他们对社会史和思想史等感兴趣,巴黎年鉴学派便赢得了美国市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危机四伏的年代。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被刺杀、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以及断送尼克松总统政治生命的“水门事件”等举世闻名的大事件充分体现了当时美国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美国的高校自然也受到这种大环境的影响,最后被迫放弃长期以来主导大学建设和发展的人本主义传统和原则。从此以后,大学必须全力以赴遵循专业化、竞争和适应就业市场要求的原则。正是在这种政治、社会和学术环境下,决定当代法国哲学登陆美利坚的第三个“历史事件”发生了。
这第三个“历史事件”刚开始实际上只是一个1966年在美国巴尔的摩举行的正常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组织者千方百计地请来了统治当代法国哲学的头面人物。首先有必要强调一点:1966年法美学术环境和氛围区别很大。当时的法国是结构主义风行的时候:巴特、福柯、拉康和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主要著作相继问世;诸如“人死了”和“转型”(paradigm shift)这样的口号不仅占据法国主要报刊的头版头条,而且出现在夏日度假的海滩上。德勒兹和德里达双双承认,结构主义不是一个具有本质共同点的严谨学派,而是一种能让人为之疯狂的思想试验。但同样是1966年,美国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的美国大学校园可以这样来形容:一边是读着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的大学生们游行抗议,另一边则是教授们在教学内容受到严格限制的课堂上讲着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和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但面对同一个充满危机的市民社会,两者都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迷茫态度。至于结构主义为何物,美国人既不了解也不关心。那时候的美国书店里一般找不到有关法国结构主义的书,就是其他当代法国哲学家的著作也是寥寥无几。虽然列维·斯特劳斯的《原始思维》(La pensée sauvage)一书于1966年在美国翻译出版,而且《耶鲁法国研究》杂志也同时出了有关结构主义的专辑,但人们没有任何反应。事实上,上面这个专辑的编辑爱尔蔓博士(Jacques Ehrman)正是当时唯一建议开设结构主义导论课的美国教授,而且他教授的是法国语言文学,并非哲学。
也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空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学者多纳托(Eugenio Donato)和麦克希(Richard Macksey)建议组织一个能把当时主要法国思想家聚到一起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他们的建议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也得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方的支持。于是,一个题为“关于批判的语言和关于人的科学”(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Man)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66年10月18至21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在上百位报告人中,大家最期待的则是法国学术名流巴特、德里达、拉康、伊波里特(Jean Hyppolite)、日拉尔(RenéGirard)、古德曼(Lucien Goldmann)等;德勒兹、雅各布森和热奈特(Girard Genette)因故无法到会,但三人都寄来了论文,大会组织者将他们的论文一一宣读。德里达直到这次会议才第一次见到拉康,并第一次与美国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主要代表保罗·德曼(Paul de Man)相遇。会议结束后,大会组织者在大会论文选集的导言中宣布法国60年代新尼采主义对30年代黑格尔辨证法的胜利,但论文集再版的时候则换了题目,叫做《结构主义争论》。其实,这个题目最能反映当时会议的气氛:与会者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分歧很大,本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了解结构主义,结果最后结构主义本身遭到质疑。德里达成了大会的明星,他的论文成了大会的焦点。他在题为《人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Sign,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的论文中通过尼采、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来批判“在场”、“中心”、“真理”和“中心化结构”(structure centrée,centered structure)等形而上学观点,肯定诠释中的游戏原则。虽然“后结构主义”的概念化和理论化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但是1966年国际研讨会的与会者们实际上已经亲眼目睹了它的诞生。这个大会开创了美国和法国高校及研究机构交流合作的新纪元。就在同一年的秋天,不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而且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①上述三所大学正是所谓的“美国解构主义金三角”。也都开始了与法国进行教师和学生互访的项目。这第三个“历史事件”不仅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的诞生,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当代法国哲学正式登陆美利坚。
二
当代法国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叩开了美利坚的大门,但它马上发现自己跨过的并不是美国哲学系,而是常青藤大学和其他几所精英大学文学系的门槛,而且不久就发觉自己失去了在美国的哲学身份。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福柯、巴特、德里达、德勒兹、拉康、利奥塔(Jean-Fran觭ois Lyotard)和克里斯特娃等人已在美国大学的教学大纲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同样地,在教学大纲里为他们保留位置的仍然不是哲学系,而是比较文学系、法国语言文学系和英美语言文学系。在这些系里,上面所提到的思想理论家被崇拜,他们的名字经常挂在大学教授和研究生的嘴边,成了学术圈里的“时髦”。谈起这些人来神采飞扬的人甚至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而对这些名字感到陌生的人会被人认为无知和落伍。
有这样一个有趣现象:在美国外国语言文学系,搞文学的人比搞语言的人时髦,搞当代文学的人又比搞其他时期文学的人时髦,而能借上面这些法国哲学家的光环来搞当代文学的人最时髦。换句话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的美国大学文学系里,搞时髦理论的人是“精神贵族”。所有理论的重中之重则是“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当代法国哲学在美国的新身份。
当代法国哲学在美国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读者和听众,完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实,完全不同的高教运作体制以及大相径庭的治学方法。怎样才能使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等被长期受实用主义影响的美国人接受,这是那些推崇当代法国哲学的人的当务之急。熟悉美国学术界的人清楚地知道,实用主义在美国占绝对统治地位;任何理论,别说是当代法国哲学,如果不能显示出某种实用价值,它在美国是无法立足的。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终于发现了当代法国哲学的实用价值。以福柯、拉康、巴特、德勒兹和德里达为代表的法国哲学思想被包装成“法国理论”,与80年代的“美国实践”相结合,从而成为当代法国思想文化出口迄今最成功而且规模最大的例子。发明“法国理论”的功劳应该属于常青藤大学及其他名牌大学的文学系。前面已经提到的第三个“历史事件”可以说是“法国理论”的播种之日。
20世纪80年代的法美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现实。当时的美国社会虽然被以里根总统为首的保守势力所控制,但是在相对孤立分散的大学校园内,人们却可以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尽情发表不同的激进言论、大谈弱势群体理论、进行大胆的文本革新。不过这一切对美国公众的影响则微乎其微。恰恰相反,当时的法国社会则被以密特朗总统为首的自由派所主导,但是一直在法国公众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思想学术界却被一群年轻的中间偏左的现代人本主义者占领;他们千方百计对带有左翼和激进倾向的思想家进行普世主义道德恐吓(universalistmoral blackmail)。这群中间偏左的现代人本主义者就是以勒维(Bernard-Henri Lévy)、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以及费希(Luc Ferry)等为代表的“新哲学家”。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曾经力挺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福柯、巴特、德里达和德勒兹等知识精英,并全力以赴排挤他们。①参见Luc Ferry et Alain Renaut,La Pensée 68,Paris:Editions Gallimard,1988。
20世纪80年代初萨特和福柯相继去逝后,德勒兹、利奥塔和鲍德里亚(Jean Beaudrillard)先后离开了政治舞台;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进了精神病院;德里达转向对民主的伦理支持;最后只剩下巴迪欧(Alain Badiou)和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等几个人还在抵抗由“新哲学家”发起的“知识反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激进哲学思想于八九十年代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利坚,被美国人改名换姓,成了前卫的“法国理论”,继续在远离法国的美利坚发挥它应有的社会批判作用。
概括地说,当代法国哲学的美利坚之旅是一个法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论文本向八九十年代的美国系统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出现了三个有趣的现象:(1)法国人眼里的书写/写作问题在美国人那里转换成解读/阅读问题。读者的认同及其内在的多样性成为焦点:比如,读者的性别、种族、年龄、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社会地位、受教育的程度、性取向、健康状况、职业,等等。(2)晚期资本主义的神秘性(mystery)转换成文化认同的谜(enigma)。充分利用“法国理论”的社会批判功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从80年代开始风靡美国。(3)微观政治问题被转换为符号冲突问题。有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结构性的误解”。这里所说的误解并不是指误读、错误或不忠实原文,而是指语词(words)和概念(concepts)从一个特殊的符号市场向另一个符号市场转移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高度生产性。这就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社会条件影响和制约知识的国际流通。①参见Pierre Bourdieu,“Les conditions sociales de la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idées”,in Romanistische ZeitschriftfrLiteraturgeschichte/Cahiersd'histoiredeslittératuresromanes,Vol.XIV,No.1-2,Heidelberg:C. WinterUniversittsverlag,1990,pp.1-10。美国各种复杂的社会条件导致当代法国哲学在美国的新身份是“法国理论”而非“法国哲学”。由于这种新身份的可伸缩性,美国人所说的“法国理论”很快就超越了当代法国哲学的界限,从而涵盖了几乎所有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等。被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影响最大、最深和最广的“法国理论”代表当推以下七大理论明星或“七君子”,他们分别是:福柯、巴特、拉康、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和克里斯特娃。在这七人当中,福柯最出众,学术地位最牢固;德里达最受追捧,最被制度化和偶像化;德勒兹最被误解,特别是被以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为首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误解,经常被他们指责为后现代唯美主义者;拉康、巴特和克里斯特娃三人最受美国哲学以外的人文学科青睐,其中拉康却最被美国精神分析学会所痛恨;利奥塔最走运,在“法国理论”风靡美国之前在法美仍默默无闻的他却因《后现代状况》一书的出版一夜走红。这部基于与哈贝马斯论战的著作俨然成了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圣经。
三
美国人对待“法国理论”的态度与其几十年前对待超现实主义的态度有相似之处。有的把它当成精英文化,有的把它当做时髦,有的对它不屑一顾,也有的把它当做洪水猛兽。“法国理论”在美利坚的深远影响不仅归功于它的朋友,而且它的敌人也功不可没。“法国理论”刚一露面,波士顿大学的一批人本主义者就极力反对和贬低它;社会科学家和分析哲学家一如既往地固守他们对“欧洲大陆哲学”的偏见,认为“法国理论”除了文学,还是文学,没有哲学的影子;科学至上主义者的反应则更加极端。两个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和吉恩·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于1997年合写了一本叫《知识骗子》(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s)的书。这本书的出版正好与英国王妃黛安娜在巴黎丧身于车祸的时间吻合,因而引起了法国以及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该书称“法国理论”的代表们无视事实和逻辑,把科学看成是叙事、神话和社会建构,因此毒性(他们甚至戏称:lacanium,derridium)十足。两人把几乎所有当代法国思想家放进了黑名单。美国文学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批评家、英国文学教授和女权主义者帕丽娅(Camille Paglia)自始至终抵制“法国理论”,声称他们的所有著作里没有一句话能引起她的兴趣,指责后结构主义打碎了词与物之间的联系。她实在按捺不住自己对“法国理论”积压已久的仇恨,公开骂福柯“杂种”。这种低俗的仇恨语言使帕丽娅名噪一时,也使“法国理论”通过大众媒体全面走进美国公众的视野。“法国理论”在美国的影响和地位是它在自己的祖国不曾有过的。也许解构主义理论家德曼对理论的处境看得最透彻。他认为,本来就应该从否定的意义上去理解和定义理论,因为从整体上来讲,它让人犹豫不决,引起人们的抵制,导致人们的厌恶,甚至激发人们的仇恨。
不过“法国理论”的真正影响和传播靠的还是它众多的朋友。它在美国不仅有众多的追随者,而且还有供奉它的三座风格不同的庙宇:比较文学系、法国语言文学/罗马语言文学系和英美语言文学系。最后它还有自己的市场平台,即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及其一年一度的年会。美国20世纪80年代起时兴认同政治,被认为左翼和激进的“法国理论”一下成为各种研究认同问题的专家和学者竞相吸取的理论宝库。无论是种族、性别和社会阶级研究,还是多元文化、宗教包容和全球化研究,他们似乎都能从“法国理论”那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语言(language)和话语(discourse)。“法国理论”最有价值的朋友是下面这样一群美国学术界的明星。他们分别是:萨义德(Edward Said)、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杰姆逊(Frederic Jameson)、费什(Stanley Fish)、斯皮娃克(Gayatri Spivak)和罗蒂(Richard Rorty)。说这些人是“法国理论”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他们把“法国理论”奉为金科玉律,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批判“法国理论”,正是他们对“法国理论”所抱有的持之以恒的批判兴趣使他们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法国理论”在美国的地位和影响离不开他们,而后者的职业前途和学术成就也与“法国理论”息息相关。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红楼梦》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代法国哲学能把美国哲学的大门推开一条缝,美国哲学家若尔缇是最大功臣。他不仅不把当代法国哲学拒之千里,而且主动与其对话。虽然他的这种举动遭到美国哲学同行的非议和排挤,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缩小大西洋两岸两种哲学传统之间的鸿沟的艰苦努力。进入21世纪后,当代法国哲学在美利坚似乎又有了新火炬手,他们当中首推巴迪欧(Alain Badiou)和南希(Jean-Luc Nancy)。当代法国哲学能否在美利坚摘掉“法国理论”的帽子,最终以它本来的身份被美国哲学界接受,人们将拭目以待。希望知识国际流通的速度、规模,以及巨大冲击力能使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各自封闭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成为历史。
(责任编辑:张琳)
杨兆锭,美国文盖特大学(Wingate University)法国语言文学教授。
①本文是由笔者2012年春在清华大学的公开讲座手稿大幅修改而成。主要参考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居塞(Fran觭ois Cusset)所著的French Theory:Foucault,Derrida,Deleuze&Cie et lesmutations de la vie intellectuelle aux Etats-Unis(Paris:魪ditions La Découverte,2003)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