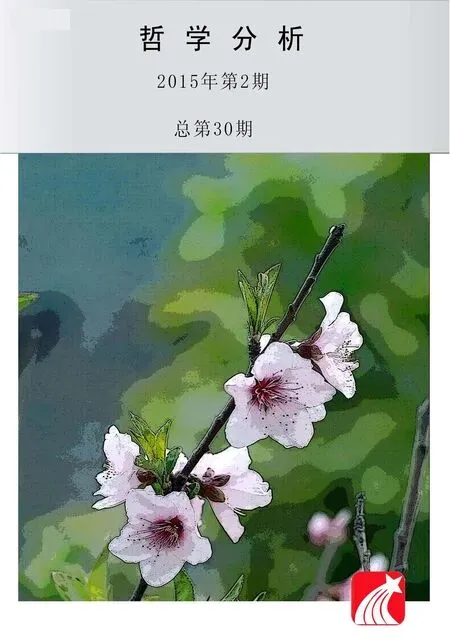儒家仁爱观念的本质及其实现之道
——以基督教的神爱观念为背景
田薇
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
儒家仁爱观念的本质及其实现之道
——以基督教的神爱观念为背景
田薇
基督教的神性爱是全无差异的普遍之爱,儒家的人性爱则是亲疏有别的差等之爱,这是学界中具有广泛性的一种看法。然而,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以及后儒的文本分析显示:儒家仁爱涵盖天、地、人,既是君子人格和政治伦理之基,也是天地大化、生生不已之源,本质上乃是一种具有普遍性、超越性的爱。在实现之道上则讲究由亲到疏、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直至天地万物的次第性之序。然而,这一次第之序既合乎自然人伦,也因合着生生之道的大仁而成为天伦之序。对此,既要看到仁爱具有以爱亲行孝为起点,然后外推的差别性,也要看到仁爱上达天命、下贯万物、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普遍性。在本质上和践行上,仁爱都带有普遍性和超越性与顺序性和差异性的双重性特征。
儒家仁爱;基督教神爱;仁爱的普遍性;仁爱的次第性
基督教的神性爱是全无差异的普遍之爱,儒家的人性爱是亲疏有别的差等之爱,这作为一个“是然”判断似乎成为某种共识,在此基础上又引出某种价值评判,赞扬前者打破了一切世俗界限而塑造了人权平等的现代观念,批评后者缺少这一性格与现代性价值失之交臂而沦陷亲亲藩篱之困。应该承认,这些看法是包含着合理因素的,但若由此否认儒家仁爱的普遍性和超越性则恐怕要归之于只看其一的简单化判断的结果;若要由此不再正视儒家仁爱次第性的合理性,则不免既无视天伦自然的矫情,也无视次第之爱的核准依然是普遍的仁。事实上,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在施行上,儒家仁爱都不缺乏普遍性和超越性的维度,而仁爱的次第之序也因合着生生之道的大仁而成为天伦之序。
从总体来看,儒家仁爱既包含着仁爱是什么的本质看法,也包含着对怎样体现仁爱的方式和路径的理解。就前者言之,仁爱是一个涵盖天地人为一体的带有形而上学、宗教意味的观念。既是人类存在与天地万物的本质,也是个体存在的人格理想;既是指导个人伦理生活的道德原则,也是社会政治秩序的价值目标;既是个体自我修养的美德,也是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既是成就君子和圣人的根本之路,也是天地大化生生不已之源;体现着道德实践的性格、形而上学的性格和天人合一的性格。既有普遍的伦理性,也有超越的宗教性,是贯通儒家思想的核心与灵魂。就后者言之,即在何以践履、何以实现这一仁爱的路径上,儒家采取了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从人到物、直至天地的方式和顺序,我们称这种行诸仁爱有顺序的实践方式为儒家仁爱的次第模式。这里我们既要看到,仁爱具有以爱亲行孝为起点然后外推的差别之序,也要看到,它还是一条上达天命、下贯万物、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的普遍仁爱之道。仁爱在本质上和践行上带有普遍性和超越性与顺序性和差异性的双重性特征。对此,我们将主要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依据并稍及后儒,做出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和阐发。
一、仁者人也与生生谓仁——仁爱在天人之际的普遍性和超越性
作为儒家的核心观念,仁爱的含义是十分广博的,创始人孔子并未给出一个统一的说法,而是在跟弟子问答的各种具体语境中给予过多种说明。在孔子之后的大儒,像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等人对其也是有各具特色的解释。这些解释和说明统合起来看,仁爱指向人性之爱。但是人性之爱并不困于人性,而是延伸到天地万物的生生之仁;也不囿于爱人,而是仁人无不爱。这样的仁爱既是人的一种美德,也是参赞天地化育的天人一体的存在境界和完美人格。对此,我们做出以下几点概括和阐明。
第一,仁乃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守仁为人,失仁丧人。故人性即仁之性。一个真正的人便是一个仁人;有仁,才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没有仁,便失掉了为人的根本。孔子的理想人格“君子”首先就是一个抱仁守仁的人,一个修仁成仁的人。他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①《论语·里仁》。仁的完满境界便是圣人境界。纵观《论语》关于仁的对话,仁更多地体现在成人成德、闻道谋道、知天顺命以及一切言谈举止、生活学习、为人处事活动中。孔子谈仁的方式主要是从成仁抱仁的理想追求切入,也就是从仁的实践方式切入,很少直接给出何谓仁的答案。但是,透过孔子关于成仁之难的各种议论可以发现,仁被视为某种完美无缺的存在状态,在这种观念里深深蕴含着关于仁的本源性、本质性意义的领悟和体认。比如,当弟子几次叙述某人有什么好的行为举止后问道“何如”的时候,他都回以“忠矣”、“清矣”,而面对“仁矣乎”的发问,则每每回答:“未知,焉得仁”或“不知其仁”。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5、76、78、79页。即使是像尧舜这样的古代圣王,孔子认为也不能说就是和仁完全合一了,依然有不到之处。如“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②《论语·雍也》。这表明仁乃某种至高的存在境界,就其形而上的意义而言具有本体论—存在论的意义。
真正从形而上学人性论的高度对仁做出明确阐发的是孟子。他提出了“仁也者,人也”③《孟子·尽心下》。此外,《中庸》里也有“仁者人也”的论断,孟子可能是继承发挥了子思的思想。的论断,确信在人的身上先天存在着“仁”,仁是人性之所在。只是先天的仁性乃是一种潜在的原善,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就是一个仁人君子,而是需要开发之、呈现之、光大之。所以,孟子和孔子一样主张仁人君子是一个不断修身养性的动态过程。但是正因为“仁者人也”即先天仁性的确立,使得仁人君子何以能够修养而成,才获得了内在的可能性依据。而由可能到现实的转化过程则依赖于“仁性”到“仁心”的开显和澄明。所以,孟子又说:“仁者,人心也。”④《孟子·告子上》。潜在的仁性可以显明在心中,真正的仁人君子的道德操持就在于自觉地意识到人的本性在仁,使之朗现于心,并通过心性修养的功夫去守仁固仁,行仁践仁。故有“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⑤《孟子·尽心上》。一说,也是孔子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⑥《论语·颜渊》。之意。这也使得凡人与圣人之间并不存在隔绝的界限,在逻辑上人人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在此,仁既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和本然,又是力图达到的理想和目标。就仁与人的关联来看,在理想和现实、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着距离,在本然和应然、原是和当是之间却是同一的。由前者的距离到后者的同一,便是通过反省内求的自力功夫而实现的道德超越,不同于基督教源于人的罪性之无能而走向外在的神圣救赎。
第二,仁在人性和人心,这仁性和仁心的灵魂与实质就是“爱”,所以“仁”也就是“仁爱”。孟子的“不忍人之心”便是这种最本始的仁爱之端。修养这种不忍人之心,人就能充满仁爱;毁灭这种不忍人之心,人就会流于禽兽。如果说仁爱以人爱为轴心,那么仁爱也以爱人为核心。儒家人文主义最突出的思想特征就是把最大的注意力投注到人和人事上,故而仁爱的中心旨趣就是以人为爱者和被爱者。孔子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在仁中将人和爱统一起来。《论语》中有多处记载孔子和弟子关于仁的对话,例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①《论语·颜渊》。朱熹注释说:“爱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务。”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第131页。人是应该努力关爱和认知的中心,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或者家族、社会、国家、历史在内的全部人生和人事是儒家关注的中心视域。
对于儒家来说,仁爱作为仁之爱是将自然人情和道德觉解集于一身,是一种本然亦当然的天人之合,拒绝和矫正一切偏私之情。所以,按照孔子之见,“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③《论语·里仁》。。只有真正具备仁爱心性的人,才能对人做到恰当的爱和恨、好和恶。这是因为只有安于仁、固于仁的人具备宽厚的品格与中正的尺度,不会私心偏袒,能够正当地爱恨与好恶。在应该的尺度上好应该好的,也在应该的尺度上恶应该恶的。所以朱熹引游氏注曰:“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第69页。在此,仁爱作为人爱和爱人,并不任其困于人之爱的自然限度,而是自觉予以道德理性的调控和规范。这一点将在后面关于亲情之爱的论述中得到进一步阐发。
第三,打通天人之间,将人之爱和天地生生之仁贯通起来,于是,仁爱跳出了人爱的限度,构成一种上至天命,下贯万物的天人合一的存在品性和超越之境,使得人之爱获得了某种本源性的支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从存在论的顺序来看,也就是从超越性的本源来看,人自天而出,人性禀天命而成。《论语》里讲“与命与仁”,《中庸》里言“天命之谓性”,《孟子》里谈“立命存性”都是同一个意思,这奠定了儒家人论的形而上学宗教性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便能够进一步确认,仁爱作为人性也是由天命而来,仁爱是人心乃是回应天心,仁爱是人德则因为是天德,仁爱的最高根据在天。在仁爱里天人一体。《中庸》和《易传》都将天地高远博厚、包容四方、化生万物、悠久无疆看做是一种“大仁”或“大德”,即所谓生生之仁或生生之德,一如《系辞》所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汉儒董仲舒推进了这一思想,明确从天人合一的角度解释仁,他说:“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⑤苏与:《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18页。“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①苏与:《春秋繁露义证》,第61页。天是人和万物的造就者,在其生养人和万物的过程中显示着天的仁爱。仁爱是天的意志,也是天的美德,所以,“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②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仁爱来源于天命而根植于人性。宋儒朱熹也强调仁爱作为人心和天理的统一。在人心中有仁义礼智四端并发展为四德,这可以溯源到天地“生生”之中也有生成、繁荣、推进、稳定四种仁爱之理。在注释孟子“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③《孟子·离娄下》。一句时,强调四德“皆天所与之良贵。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第222页。。仁心是天地生养万物之心,也是人从天地之心得来的宅厚仁心。我们看到,在这个天人一体化的关联中,关联的顺序是从天到人,这是存在论的顺序和方向,意味着仁爱具有超越性的本源(天)。这与基督教的人爱源于神爱具有某种相似性。
另一方面,从修养论的顺序来看,也就是从超越性的路径来看,仁爱乃是由人到天,由下到上,由己及人,由内及外,将个体仁爱的心性延展到天地万物,使人心与天心在仁爱中合一,使人性与天地之性在仁爱中通为一体。这意味着,仁爱乃是人的存在的某种超越性品格和境界、活动和力量。在仁爱里,天地人三者贯通,民胞物与,参天赞地,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广博、深厚与高远,与天地合其德,共其在,也就超越了生命存在的暂时性而跨入了永恒性之境,这也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与命与仁”正是这样一种超越的生命境界。仁在根本上是一种对待终极实在的态度,即敬畏和恭顺天命,相与和赞许天命,而敬畏和相与之道就在于牢牢立足于自身而抱仁守仁、施仁践仁。在这种相与中,仁者爱人,悯人悲天,故而孔子充满仁爱天下的情怀。《中庸》里也说:“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36页。惟有至德,方成至道;惟抵至道,是为圣人之道;圣人之道至大无外,高峻及于天,广博蕴万物。而圣人因至德至道而进抵天地万物,正是大仁之仁,大爱之爱,一种人德合天德、人心合天心、人道合天道的高超境界。故有如此赞叹:“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第39-40页。而在孟子那里,人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此也正是仁爱之心。若每个人都能培养和扩充这颗仁爱之心,而不是追逐个人私利以相害,则彼此之间就可以相安以义,和谐共处;若将爱人之心涵及万物直至天地,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⑦《孟子·尽心上》。,也就达到了天人合一,与万物一体的最高修养境界,此亦为“大人”或“仁人”。仁人无不爱,“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①《孟子·尽心下》。。倘能如此,则“仁者无敌于天下”②同上。。这是一个在仁爱中自我超越的过程,也是一个尽心—知性—知天,或者存心—养性—事天的过程。《大学》所谓“明德,亲民,至善”的大学之道也可以说是一种仁爱天下的修齐治平活动。这些思想在宋明儒学里得到进一步发挥。张载将仁和《易》结合起来,将人的仁心扩展成涵容宇宙的“大心”,在大心中,人和人、人和万物、天地和父母通为一体,这就是民胞物与的观念,也是对孟子“亲亲仁民,仁民爱物”③《孟子·尽心上》。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说:“大心能体天下之物,……视天下无一物非我”,“乾(天)称父,坤(地)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91、493页。程颢将张载的意思更加直接地表述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又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⑤《二程遗书》(卷二上),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赵复三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对于一个仁人来说,宇宙和万物不是身外之物,而是自己的一部分。人心与天地之心是相同的,人类之仁和宇宙之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朱熹说:“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⑥转引自姚新中:《儒教与基督教——仁与爱的比较研究》,赵艳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总之,仁爱既是人性,也是天性;既是人心,也是天心;既是爱人,也是爱物。仁爱立足于人性,上达天命,下贯万物。它既不同于基督教的神性,却也不以人性为束缚。就其本源而言可以溯之上天,天命之谓性;就其作为人的心性和美德来说,则可以通过自我修养自我超越的活动,将仁爱扩充到宇宙万物而实现天人合一。所以,仁爱和基督教的神爱一样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品格。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仁爱观念的超越性品格在肯定天为本源的前提下,更为凸显的是从人爱出发直抵天人之境的超越之路。易言之,仁爱的超越性用力在人之维而非天之维,用力在从人到天、从下而上的境界超越之路,而非从天到人、从上而下的本体超越之路,鲜明体现着儒家宗教性人文主义通过自身修养实现生命超越的功夫论特征。这种超越性诉求不同于基督教从神到人、从上而下、在神爱的救恩里开启的信仰之路。
第四,儒家仁爱存在于天人之际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特征,还通过“诚之道”、“中庸之道”、“忠恕之道”体现出来,这使得仁爱具有非常丰富多维的意涵,更加凸显其形上致思和形下践履不相分离的本色。
先来看“诚”。仁爱的心性是守诚的心性。诚在儒家思想中既是一种存在性—生存性的格位品质,也是一种对待性—处理性的人格态度。就前者而言,诚有真实纯正、原初本然之意,其实这种意义本身就是至仁至爱之意,可谓从形而上学层面上言之,是谓自诚,亦即天诚;就后者而言,诚有不疏不拒、不移不欺之意,这种意思可谓从实践论层面上言之,是谓思诚,亦即人诚。人诚和天诚、思诚和自诚统一不二。故《中庸》里把“诚”视为天人之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朱熹·中庸章句》,第32页。天道至诚,涵养万物出于本性,生生不息殊为专一,至诚即至仁,至仁即至爱。人道以天道为本,故而要怀着真实和真挚的心灵,抱着不二和不疑的态度,以无私和无欺的德行立身处世以致达于万物,这样就可以进抵天道至诚、经纶天下的圣人境界。故《中庸》里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②同上书,第39页。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与天地参。③同上书,第34页。经纶天下之大经,参赞天地之大化,确立天下之大本,此可谓仁爱之至。
再来看中庸。仁爱的人格立身中庸之道。朱子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也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④同上书,第19页。既然不偏不过,恰到好处,不变不易,平常也恒常,那么中庸之道自然是天下的正道和不变的常理。真正仁爱的人格行为无不立身在这条中正适当的道路上,在这方面君子可谓之典范。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⑤同上书,第21页。君子中庸是说君子能够随时做到适中,无过无不及;小人违背中庸是说小人肆无忌惮,专走极端。这样的中庸既是中道,也是美德。透过君子的中庸可以看到一个完美的仁爱人格,这就是“群而不党”⑥《论语·卫灵公》。、“周而不比”⑦《论语·为政》。、“和而不同”⑧《论语·子路》。。在《中庸》里,中庸更在形而上学宇宙观的高度被视为使天地安位、万物滋生、进抵仁爱之至的和谐状态的大本大道。故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20页。可见,中庸不仅是实现人类仁爱生活的人道,也是宇宙仁爱秩序得以生成的天道。在中庸里体现着天人一体的至德,是对孔子“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⑩《论语·雍也》。的诠释。与此相连的是遵礼而行,只有遵守礼仪,才能走上中庸之道,进而把仁爱的心性恰当地表现出来。对孔子来说,礼仪是仁爱的外显,仁爱是礼仪的内化。“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①《论语·卫灵公》。孟子也说:“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②《孟子·离娄下》。
最后来看忠恕之道。仁爱的行为是忠恕之行。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③《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④《论语·卫灵公》。前者言“忠”,后者言“恕”,二者以仁爱为体,统一为“忠恕之道”,也就是伦理实践中的“黄金规则”。可以说,忠是从肯定的、正面的维度施行仁爱,只要是真善美圣的价值,不仅自己为自己努力谋求之,也要为他人努力谋求之。这一层面的仁爱指向了一种最高的行为境界,可称之为“积极自由”之维的仁爱。在孔子看来,这种仁爱的实现是一种完满,即使像古代圣王尧舜之人也有未至之嫌。但为仁由己,应该以“忠道”为终生努力的目标。“恕”是从否定的、反面的维度施行仁爱。如果说忠在动机和行为上蕴含着积极的向外的拓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人做好事,帮助他人实现他们想获取的东西,那么,恕则蕴含着积极的向内的自我收敛,以最大的自我克制去约束自己不要伤害别人,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人;他人有什么难处或者不是,应该努力去体谅之宽容之,可称之为“消极自由”之维的仁爱。
在此,仁爱具备的至诚之品格、中庸之完美、忠恕之德性,无不跳出了人性存在的种种局限和束缚,体现着仁爱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特征。较之基督教的神爱有着明显的异同性,如果说就仁爱的至诚和忠恕而言,与基督教的“虔诚”和“爱人如己”之间有某种相近相通之处,其中都包含着对于真纯笃实的心性和良善宽厚的德行的肯定,那么,其恰到好处的中庸之道,如“以德报德”和“以直报怨”各有正对的适中姿态,便与基督教“以德报怨”或者“爱仇敌”的极至姿态有着颇为不同的性格。但若论爱仇敌体现着神爱的纯粹性和绝对性,恰到好处的中庸体现着仁爱的完善性和无缺性,那么,二者又有着同样的理想性和超越性。
二、亲亲—仁民—爱物:仁爱在施行中的次第性和差异性
儒家的仁爱不仅有着高超的品格和取向,而且有着非常现实的内容和实际施行的顺序,这就是亲亲—仁民—爱物,讲究从亲到疏、由近及远、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的次第性,并且在这一次序中体现出仁爱在行诸不同对象时具有的不同特点,彰显着儒家在处理人间事务和人际关系上十分突出的伦理态度。
前面谈到,仁爱的中心关怀是爱人和人爱。但如何理解人?儒家和基督教是不同的,基督教主张人是以神圣信仰为纽带组成精神团契而共同朝向上帝的人,儒家则强调人是禀受天命处在种种社会人伦关系中的人。这些人伦关系被儒家归纳为“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人的生活不同于禽兽根本就在于人伦关系有道可依:“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①《孟子·滕文公上》。五伦当中有三伦是家庭内部的关系,足见儒家对于家族关系的重视。家族关系是基于血缘亲情的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既承担着人类个体生命的延续,也构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石。君臣代表着社会政治伦理关系,朋友代表着社会人际伦理关系,它们无不建立在父子所代表的家庭伦理关系上。就是说,君臣关系和朋友关系分别是以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为轴心而进一步向外的延伸,是由内部家庭到外部社会的拓展。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②《孟子·离娄上》。。
因此,仁爱是在人伦生活(关系)中展开的,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是家庭伦理生活,以至于在“四书”里谈到仁爱和仁义的时候,都把家庭的孝悌伦理看做是首要的和基本的。《论语》里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③《论语·学而》。《孟子》里则说:“亲亲,仁也。”④《孟子·告子下》。“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⑤《孟子·离娄上》。《中庸》里也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30页。并且,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称为天下之“五达道”,知、仁、勇为“三达德”,而要守持三达德和五达道,都必须以诚事之。朱熹在解释该句的时候将三达德和五达道完全打通,释之为:“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一则诚而已矣。”⑦参见同上。《大学》里同样讲的是人伦关系中的仁爱之实:“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第6页。仁、敬、孝、慈、信都是仁爱本体之用,此之谓君子奉行的“絜矩之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⑨同上书,第10、11页。
正是由于以血缘亲情为核心的家族关系是儒家伦理秩序的基石或轴心,因此,在施行仁爱的顺序上,便以“亲亲”为起点进而向外扩充,这就是由近及远、从亲到疏、推己及人的实践方式。故有孔子之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论语·学而》。这里如何理解“本”字是个关键。如果将句中的“本”理解为“何谓仁爱”这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质”,于是将儒家仁爱的本质归结为“孝悌”或“亲亲”,是不合适的;如果在时间先后的意义上将之理解为“何以行施仁爱”,则更为合适,也更符合儒家在“时中”和“践履”中把握问题的思路。这样的话,孝悌为“本”就意味着仁爱的施为首要在于孝悌,首先要立足于亲亲,先从亲亲孝悌开始,然后再向外拓展。刘宝楠对这句话的注释很恰切:“本,基也。基立而后可大成。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大成。”②刘宝楠:《论语正义》,载《诸子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影印版1986年版,第4页。朱熹也讲,“为仁”说的是“行仁”,如何为仁行仁呢?根本在于“孝弟”,孝弟做好了,仁道也就得以确立了。程子说得更加明确:“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偿有孝弟来。”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第50页。可见,当孔孟将孝悌视为仁爱之本的时候,意思不是指谓仁之为仁的本质在孝悌,而是指谓行施仁爱的根基在孝悌,这个根基就是基点、原点、起点的意思。质言之,对于儒家来说,仁爱为本体,孝悌为发用;若要施行仁爱,需从亲亲开始。
上述可知,若将儒家仁爱的实质归结为亲亲仁爱是不得要旨的,也是一种误解和误读。但是,行施仁爱却是要从亲亲仁爱开始的,因为亲亲基于自然人情,最合乎人性的天然取向。亲亲仁爱是仁爱的基础,没有亲亲仁爱,仁爱如空中楼阁是建立不起来的。在孔子看来,每个人的生命受之于父母的给予,成长受之于父母的教养,世上最大的恩情是父母的养育之恩,因而也需要每个人以终生来回报这份最大的爱的恩情。何以回报?就是要奉行以仁爱为本的“孝道”。孝道基于亲亲之情,又用“礼”来范导和实现亲亲之情,使之成为亲亲仁爱。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④《论语·学而》。父母在世要尊敬顺从而不自专独断,父母不在要恭心敬守三年丧礼。若能三年遵守先父之道而不改之,可称得上孝了。面对宰予质疑三年丧礼太久,孔子批评道:“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⑤《论语·阳货》。
这里我们发现,“孝道”就是亲亲仁爱的实现之道,是将自然的亲亲之情导入伦理仁爱之中。换句话说,亲亲要依礼而行。依礼而行才是孝,孝才是仁爱的实现。否则,不守道德礼仪,仅仅止于亲亲本能,便不是真正的仁爱。所以孔子才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①《论语·为政》。这一说法最能体现儒家亲亲仁爱的伦理品质。仅仅是能够赡养父母远未及孝道,因为连犬马都能做到养育自己的后代,人与禽兽之别不在于“养”而在于“敬”;惟有敬,才能越出自然本能的情感。这便是仁对于爱的引导,使之提升为仁爱。同样,父母育儿也不仅仅是把他们养育长大,还要通过礼仪节文把他们教化成人。若完全听凭自然亲情去溺爱则是不负责任的爱,所以有“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如果说儒家传统是一种典型的德性伦理,那么,通过亲亲仁爱可以得到充分彰显。亲亲仁爱既是一种来源于天然情感的爱,又是一种越出了天然情感而具有伦理意义的爱,是一种将天然亲情之爱与教化伦理之仁结为一体的仁爱。
从自然而然的最为切己的亲亲之情开始将之引向亲亲仁爱,这对于仁爱的实施是首要的和基本的,但仁爱并不因此而局限在家族内部,相反,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向外扩展,由己及人,由亲及疏,展开为始于家族亲亲仁爱又超越家族亲亲仁爱的普遍仁爱,也就是由“亲亲”到“仁民”。从孔子的“仁者爱人”②《论语·颜渊》。到孟子的“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③《孟子·离娄下》。,这里所爱所敬之人绝非仅仅限于家族之内的亲人,而是将敬爱及于所有的人。孔子讲“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④《论语·里仁》。显然是在讲唯有仁者能够爱得无私心,爱得有公正,这种公正又无私的正当之爱不可能是仅仅针对家人的爱。相反,如果在施爱的行为上偏袒偏私自家人,怠慢拒斥其他人,恰恰是仁者所不为的。仁者的爱是将不同的人类个体联结起来的仁爱,也被孟子表述为“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⑤《孟子·尽心下》。和“仁者无不爱也”⑥《孟子·尽心上》。。在无不爱的仁爱里,从个人行为的角度来看,表现为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在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⑦《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以仁爱之心治民的“仁政”,施仁政可以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更进一步,在无不爱里,不仅使人和人,而且使人和物都结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也就是由亲亲仁民直到爱物。董仲舒将之解释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仁?”⑧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转引自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可见,仁爱乃是一种从亲亲到仁民再到爱物的普遍之爱,通过次第性实现普遍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亲亲—仁民—爱物的顺序里,包含着仁爱因对象不同而具有的不同特点。孟子将之概括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①《孟子·尽心上》。儒家的仁爱既是一种最高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普遍之爱,也是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普遍之爱。作为普遍之爱,仁爱遍及一切对象。但是,就伦理层面来讲,对象不同,仁爱的特性也有所不同,可区分为亲、仁、爱。对于父兄而言,仁爱的特点在“亲”,包含的是一种最为密切贴己的情感,虽然亲亲里包含着仁的范导而表现为孝悌伦理;对于他人而言,仁爱的特点在“仁”,突出了人人之间要奉行仁义之德,虽然仁德里边也包含着情意却非亲情;对于外物而言,仁爱的特点在“爱”,意在善加料理万物,善待、善取和善用万物,却既不同于施诸亲人的孝悌之道,也不同于施诸同类的仁义之行。但无论哪种,又都包含着护爱或关爱之意,承担着某种作为人的道义责任,从根本上体现着那个最高的仁爱之本。
仁爱的实施不仅在不同对象上有亲亲、仁民、爱物的差异,即使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由于问题的性质和状况不同,儒家也主张分别对待,不宜一刀切。当孔子面对“以德报怨,何如?”的提问时,回道:“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②《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抱怨和报德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不应混为一谈。人之有德于我,我以德回报;人之有怨于我,我则既不以怨对怨,也不姑息养奸,而是要以直正无私的恰当尺度给予正确的回应,充分反映出儒家在应对社会人事上有着成熟而详致的伦理考量。
可以说,正是由于充分认识到仁爱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对象和内容上的诸多差异,也就使得仁爱的呈现样态有了不同,实现顺序有了先后,我们完全可以把“亲亲—仁民—爱物”的次第模式看做是对于这些丰富的差异性的合理安排。亲人和亲情是最近的,因此,仁爱从亲亲仁爱开始便是最顺乎人性常情的。由此出发,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再将仁爱推展到他人身上,民胞物与,直至天地,乃是最顺当最切实的仁爱秩序。而在这一推己及人、拓展广博仁爱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塑造着个人对自我、对他人、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认知和感受,以致将小我和大我关联在一起,跳出自我与亲亲的限度,在普遍的仁爱里与所有人结为兄弟,构成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当司马牛忧伤“人皆有兄弟,我独亡”的时候,子夏以夫子的教导劝慰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③《论语·颜渊第十二》。在此,兄弟已然不再限于血缘之亲,只要持守仁爱礼义,世人皆可以像兄弟一样,所谓天下一家。对此,现代思想家潘光旦给予了高度肯定:“自亲子之爱,兄弟之爱,推而为戚族之爱,邦人之爱,由近而远,由亲而疏:此同情心发展之自然程序也。……孟子亲亲仁民,仁民爱物二语,实为千古不可磨灭之论。……不能老其老,而欲其老人之老;不能幼其幼,而欲其幼人之幼,天下宁有是理耶?”①《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基于亲亲—仁民—爱物的仁爱思路,孟子反对墨子的“兼爱”观念。对孟墨之争做一检审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儒家仁爱的次第性问题。墨子认为,不应分别人我,而应视人如己。因此,爱者无别,一视同仁。“爱人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②《墨子·小取》。只有“兼爱”一切人,才叫爱人。“兼爱”是为了“交利”,只有兼爱,才能交利。交利则天下利,天下利则天下治。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的相互性原则,正所谓“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③《墨子·兼爱中》。。对于墨子的兼爱观念,孟子将之和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④《孟子·尽心上》。的观念放在一起,激烈抨击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⑤《孟子·滕文公下》。纵观孟子与墨子的冲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墨翟的利他主义和杨朱的利己主义一样,在孟子看来都是走极端,是“恶执一者”,“举一而废百也”。⑥《孟子·尽心上》。孟子强调“执中”,执中也不能恶执,而是要“执中有权”,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变易”。这提醒我们在理解儒家行仁从孝悌始的思想时,不能绝对化和简单化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考虑“孝”字,而是在“行孝”时也要考虑“权”字,以最恰当的方式实现最佳的仁爱状态。比如古人重孝,但禹、稷治水却能三过家门不进而传为佳话;反过来说,“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则与墨子无异”。⑦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第335页。这表明仁爱的施行要讲究中道,拒绝走极端。
第二,墨子的兼爱完全无视人爱的差别,将对父母之爱等同于对他人之爱,违背了人性的自然规律和伦理法则,在实际生活中无法实践。亲亲之爱是天然人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⑧《孟子·尽心上》。。仁爱先从亲亲开始逐渐外展,最为适合人性的伦常秩序。天命之谓性,符合人性的人伦之序也就是天伦之序,天人合一的仁爱之道才是既普遍高超又切实恰当的实践之道。故而孟子有言:“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⑨《孟子·尽心上》。对这段话的理解应该放在孔孟思想的全局下来把握,不宜简单化处理。我们不能将之理解为爱自家人要比爱他人更爱;也不能做出这样的假设:亲人和他人都需要仁爱救助,儒家一定是要救助亲人舍弃他人!这些结论没有必然性,因为孔子还赞许“杀身以成仁”①《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则崇尚“舍生而取义”②《孟子·告子》:“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在成仁取义里也包含着舍去自身和自身所爱之意。因此,“急亲贤”和“急当务”意味着真正的智与仁应在实行过程中分清轻重缓急,务最急的,急最先的,顾最当顾的,然后再依次料理其他,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到最好最成功。其实,对于儒家的观念来说真正想辨明的道理是: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和兄弟都做不到以仁爱待之,更遑论去仁爱地对待他人。这才是儒家强调仁爱从亲亲孝悌开始的理由。
对于这一点,人们习惯称之为“差等之爱”,将其与基督教的无差别之爱相比而否认其普遍性。关于仁爱的普遍性问题,前面已有充分论述,这里不再赘言,只想指出一点,基督教的神性之爱在本体论的秩序中是绝对的、无差别的,但在现实秩序里依然表现出某种“优先性”倾向,只是这种优先性与儒家仁爱的优先性内容不同而已。透过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发现,他最先关注的是那些中心之外的边缘人、残缺人、底层人、遭唾弃的人,是主流之外的弱势群体,而疏离和抨击的则是居于社会中心的主流阶层如有神职的法利赛人、有文化教养的经学家。他多次说道:“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哪,你们有祸了!”③《马太福音》,23:13、15、23、27、29。而优先给予救恩的是“罪人”,就像他说的那样:“我来不是要召义人,而是要召罪人。”因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④《马可福音》,2:17。作为基督上帝,一如耶稣自况:“我是从天上来的;……不属这世界。”⑤《约翰福音》,8:23-24。他的神性之爱完全突破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亲亲之爱,否定和超越自我、家庭、阶级、民族、国家等一切世俗社会的尺规,不仅要求“爱仇敌”,而且要求爱神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⑥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他自己的性命,就不配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26);“爱你们的敌人吧;去让恨你们的敌人快活吧;去为诅咒你们的人祝福吧;去为欺负你们的人祈祷吧;谁打你们的左脸,就把右脸也伸给他。”(《路加福音》,6:27-29)。可以说,耶稣是以否定的、极端的、优先顾爱罪人的方式,要求超越人性的自然限度直抵无差别之爱的神圣境界,这是一条从上到下、从神到人的爱之路。儒家则是以肯定的、中和的、仁爱先从亲亲始的方式,顺着人性的自然倾向而推己及人、由人及物,直抵天人之际的仁爱境界,这是一条从下往上,从人到天的爱之路。二者最终的目标都是要超越人的自身限度,或者达到人与神的和谐,或者达到人与天的合一。只不过神爱从神性出发,人爱从人性出发。这表明,任一传统的核心理念都具有完备性和绝对性,但在现实实践中又都会表现出种种具体性和差异性。就像儒家仁爱急亲贤,基督教神爱则急罪人一样。但无论仁爱还是神爱,其自身都是一种普遍的超越的爱。因此,所谓“差等之爱”并不意味着儒家仁爱是一种不平等的特殊的爱,只是意味着仁爱的有效施行需要有一定的次序而已。
最后,孟子攻击墨子的兼爱,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兼爱与交利相结合,这是一种与儒家仁爱相背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按着墨子的思路,兼爱即是互爱,互爱才能互利。如果爱人而不被人爱,就会发生冲突,天下大乱。相反,儒家主张,仁爱的施为由己不由人,求诸内而非求诸外。孔子说“为仁由己”,孟子说“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如果爱人而不被人爱,则需要反身自省,检查自己是否对人尽到了仁爱。就像孟子说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若“其身正则天下归之”,若“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①引言皆出自《孟子·离娄上》。所以,仁爱观念不能建立在“交互性”和“功利性”的基础上,每个人都应该从纯粹仁爱的动机出发。不仅是个人修为,即便是治国平天下,也需要以仁爱而不是功利为原则。当梁惠王不远千里来向孟子讨教何以利国之道时,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②《孟子·梁惠王上》。他力倡以仁爱为基础的仁政,将仁爱与利相分离,认为仁爱天下并不等于物利天下。仁爱天下讲究的是教化民心,涵养民德,伦常礼教,言行文明,只有这样天下才可长安。显然,这种纯粹理想主义的仁爱观只能是一种普遍的仁爱观。
综上所述,儒家的仁爱一方面出自人性达至天地,反映着从人到天的实践性的普遍而超越的品格;另一方面出自天命,领受在身,存为人性,显诸人心,守之成人,失之丧人,反映着从天到人的存在性的普遍而超越的品格。这使得儒家仁爱兼具人文性和宗教性,与基督教的神爱并非隔绝。但二者的差异无疑是明显的,仁爱凸显人性,以爱人为轴心,顺乎人性的自然倾向,确立的是亲亲—仁民—爱物的次序,由亲及疏、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最终确立的是普遍仁爱;神爱则突显神性,以爱神为根基,突破自然人性的向度,重新安排爱的顺序,这就是由爱神到爱人,爱神胜过爱父母,爱卑贱者优过爱高贵者,最终使不可爱者与可爱者一样都成为可爱的,从而实现普遍的神爱。
(责任编辑:张琳)
B94
A
2095-0047(2015)02-0099-15
田薇,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自力与他力:宗教伦理视域下的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项目编号:09YJA730005)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