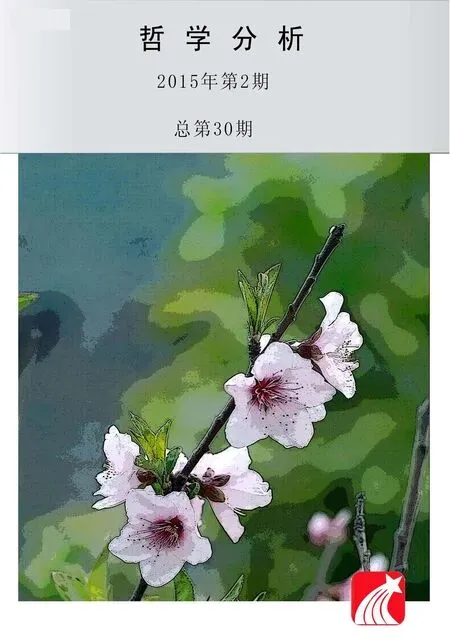自然、人事和伦理:胡适东西语境中的“自然主义”立场
王中江
哲学传统研究
自然、人事和伦理:胡适东西语境中的“自然主义”立场
王中江
在东西文化和思想的语境之下,非常自觉地抵制形而上学的胡适,由于以“自然”为宇宙和万物的存在及其何以如此的最后根据,他实际上又建立了一种形而上学──即“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同样,胡适以“自然”为中心来构建他的科学认知理性(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技术实践理性(改造和利用一切自然),以人的“自然”为中心来建立伦理和道德价值。这些又构成了胡适科学技术上的自然主义和伦理上的自然主义。
胡适;自然主义;科学;技术;伦理
引言
简单回顾一下就可以看出,从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①参见郭颖颐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南京: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90页)、刘青峰编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耿云志编的《胡适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440页)等。、科学主义、实证方法、反传统和西化论等角度对胡适的哲学展开的研究很常见,相应地,人们说到这些东西和符号的时候也往往将它们同胡适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胡适的哲学和思想不应被限制在这些符号上,如果换一个角度的话,胡适自己声称并一直坚持的“自然主义”立场则是非常值得加以关注的。这就是胡适以“自然”概念为中心的“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它是胡适哲学中“最哲学”的部分,是胡适拼命要回避却又无法回避的一种形而上学。①按照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分类,理性的宇宙观是属于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在不十分严格的意义上说,对宇宙和世界作出整体解释和把握的立场,可以说是宇宙观、世界观,也可以说是形而上学。从“描述的形而上学”来看,胡适的哲学就更是一种形而上学。想到胡适拒斥形而上学,想到他抵制思辨性和抽象性,②金岳霖回忆说他弄不清胡适,因为胡适不承认必然和抽象,他的哲学有人生观,而没有什么世界观,但“哲学中本来是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参见金岳霖:《金岳霖的回忆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183页。想到他干脆把哲学定义为“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③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影印版,第1页。不喜欢抽象的胡适,对“根本”这个词后来也产生了反感。在《哲学与人生》中,他把《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定义的“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去找根本的解决”中的后两句话改成了“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他说他这样改是因为“根本两字意义欠明”。胡适:《哲学与人生》,参见《胡适全集》(第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2页。,说他的“自然主义”首先是一种宇宙观、形而上学④有关自然主义这一概念,我们有哲学上的、文学上的不同理解和使用。哲学上的最近的讨论,参见苏珊·哈克:《自然主义视角下的信念──一个认识论者眼中的心灵哲学》,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6期。胡适使用的“自然主义”主要是哲学上的,它是胡适对中国传统立足于“自然”解释世界的一种概括,也可以说又是naturalism的译语。1923年,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明确打出了“自然主义人生观”的旗号,并且展示了他声称的“自然主义人生观”的十个条目,之后他还标榜这是他的“新十诫”。,这会不会是对他的哲学和他的说法的一种公然冒犯呢?我认为不是。
在东西方传统哲学中,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宇宙观和形而上学,在东西方现代哲学中,我们又能看到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各种各样的抵制立场。要是有人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就是这种抵制的立场之一,说步杜威后尘的胡适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大都会不加怀疑地表示赞同。但问题常常有复杂的一面。从一些方面看,杜威对已有的形而上学展开了批判,主张将哲学从各种绝对本体(包括黑格尔的绝对本体)中解放出来,要求哲学摆脱探究万物的终极根源、目的和因果等一类形而上学的问题,这是他“改造哲学”的中心目标和任务。但杜威在这样做的同时,他又乐于探讨诸如相互作用、多样性和变化等存在物的终极的、不可化约的特征,并说这是符合科学思维的一种形而上学:
我不想提出一种形而上学;而只不过指出一种用以设想形而上学研究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专门科学研究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把世界的某些比较终极的特征选做形而上学的题材,使这些特征不致与终极的起源和终极的目的混淆起来,这就是说,使这些特征与那些关于创世论和末世学的问题分离开来。⑤杜威:《形而上学探索的题材》,载《杜威文选》,涂纪亮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由此可见,杜威实际上只是反对某种形而上学,作为替代物他自己又欲建立一种他认为是具有科学性的形而上学。⑥同上书,第184-193页。
胡适的情形如何呢?作为杜威的弟子,他传承着杜威的许多东西。他不仅受到了杜威的方法论和真理观的影响,坚持用实验、实证、科学等观念和方法去思考、处理哲学中的种种问题,而且也受到了杜威批评形而上学和绝对本体的影响,这使他成为现代中国哲学中拒绝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代表性人物。胡适曾将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又称之为“工具主义”和“实际主义”)概括为三个方面——“方法论”、“真理论”和“实在论”。为了避免人们从玄远的形而上学上去理解杜威的实在论,胡适还特意指出杜威的“实在论”是以世界为“实在”(相对于“空虚”)的“实际主义者”所具有的。他这样说:“实在论就是宇宙论,也就是世界观,那是哲学的问题。”①胡适:《谈谈实验主义》,参见姚鹏、范桥编:《胡适讲演》,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胡适的言外之意,方法论和真理论不是“哲学问题”。但按照孔德的实证主义,任何“实在论”的“实在”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它们都是不同形式的形而上学。②参见王中江:《金岳霖与实证主义》,载《哲学研究》,1993年第11期。
进言之,胡适不仅坚持世界和宇宙是实在的“实在论”,而且他还将他的实在论同“自然主义”结合到一起,对“实在”采取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只要坚持一种实在论,只要立足于“自然”的立场去看待世界和解释世界,胡适就无法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他也得不出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的结论。③参见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这是需要我们探讨的胡适的“宇宙自然主义”;除此之外,胡适的自然主义,还包括科学自然主义、技术自然主义和伦理自然主义。反过来说,胡适以“自然”观念为中心而构筑的“自然主义”中的“自然”有不同的层次,它既是胡适用来解释世界和宇宙的最后的依据和信念,又是胡适作为科学认知、技术实践的客体和对象,还是他作为建立人道和伦理的出发点。
一、宇宙、实在和自然
如同上述,我们说胡适以“自然”观念为核心的“自然主义”立场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和形而上学,这主要是基于他运用他的“自然”观念对宇宙和万物作出了整体性和统一性的解释。这种解释由一正一反的两个方面组成。正的方面是胡适从宇宙和世界原本是自己造就自己的“自然”来解释和看待宇宙,认为宇宙及其万物纯粹是宇宙自身活动的“自然”结果;反的方面是胡适拒绝一切超自然的力量,否认宇宙和万物是由最高的“绝对因”特别是“超自然”的力量——“神”主宰的。胡适思想中这种意义和层次上的“自然”,是东西方思想融合的产物。
我们知道,一方面,“自然”是中国思想中的一个古老概念,以它为基础,中国还拥有悠久的自然宇宙观传统;另一方面,在中国,近代以来的“自然”概念又是作为英语nature的译语来使用的,它同时又履行着将西方的“自然”观念移植过来的角色。胡适的自然观念就处在这两种文明的广阔背景之中。由于他的东西方教育背景,他很适合也很自觉地从事了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工作。1926年,他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中这样说道:
西洋近代科学思想输入中国以后,中国固有的自然主义的哲学逐渐回来,这两种东西的结合就产生了今日自然主义的运动。①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载《胡适文存》(第三集),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77页。以下凡引用胡适的著作,除第一次之后皆只注出书名和页码。
这句话完全可以说是胡适的夫子自道或自我注脚。确实,在中国的自然主义运动中,胡适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胡适来说,吴稚晖显然也是这一运动的主角之一,胡适曾无以复加地称赞他。
说起来,胡适对于“自然”这一概念没有作过单独和专门的讨论,也没有至少像他对待“自然法”那样作出过某种概括性说明。②胡适清晰地界定过“自然法”概念。他的“自然法”中的“自然”与他解释宇宙的“自然”有交叉的地方。参见胡适:《中国传统中的自然法》,载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邹小站、尹飞丹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2页。胡适对“自然”的看法和运用,零星地散见于他的一些论著之中,我们也只能通过这些论著中的材料来了解和把握它,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然”同样如此。统而观之,胡适在不同著述中使用的“自然”概念,或者他的自然主义中的自然,主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胡适常常在“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的意义上使用“自然”。这看起来平淡无奇,但胡适就是让这种意义上的“自然”承担起了解释、说明宇宙和万物本性的重任。如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这是胡适最完整地表述他的自然主义立场的地方,同时也是他提出建设性的人生观并竭力为科学作出辩护的地方)这样说:
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③《胡适文存》(第二集),第151页。胡适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中重复了他的这一信条(见《胡适文存》第三集)。
作为“自然的”、“自己如此的”这种意义上的“自然”,从语言属性上说,它是一个形容词。从哲学上说,这种意义上的“自然”,显然不是指“自然界”和“物理客体”,而是指自然界和物理客体(即胡适说的“宇宙”和“万物”)何以如此都内在于它们自身的活动方式。胡适说他对宇宙和万物的这种“自然主义”的解释,是根据“一切科学”得来的认识。但这一说法本身就不够科学,什么是一切科学,它们又如何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二,胡适认为宇宙和万物的变化、运行都有自身的自然法则。如果说上述胡适所说的“自然”是对自然的一种使用,那么这里的“自然”就是胡适对“自然”的第二种使用。这里的“自然”与上述不同,它强调的是客体中的“秩序”,它是“自然界中的自然”。胡适说:
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的大法支配着他。①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胡适文存》(第二集),第152页。
胡适说的“常度”、“自然法则”,具体说就是“因果律”。“因果律”是胡适信奉的科学研究的对象,这是他为科学的基础作出的哲学说明。在胡适那里,科学的因果观念也适合于研究人的生命及其精神现象,因为人本质上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严格地服从于生物学的、生理学的和心理学的各种规律。胡适提出的“新十诫”的人生观,其中两条说的就是这个:“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②同上书,第151页。“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③同上。胡适的这一立场批评的是“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派。在玄学派看来,科学研究的自然是纯粹物质性的东西,而人根本上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但在胡适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研究自然的因果方法,对人类也是适用的。
胡适对“自然”观念的第三种使用,是认为宇宙的空间和时间都是“无限的”,物质的世界是变化的而不是静止的,是活的而不是死的。胡适说,他根据物理学和天文学的知识知道了空间是无穷的,他根据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知识知道了时间是无穷的。我们知道,在传统观念中,空间和时间被认为是无限的。在近代科学中,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也认为时空是无限的;但按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空不是无限的。胡适说时空是无限的,他接受的是牛顿的而不是爱因斯坦的时空观。一般认为,近代机械论的物质观是将物质看成是静止的和死的东西,与之不同,爱因斯坦认为物质首先是一种能量,生命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生命和活的东西。现代中国的生命主义者和反科学主义者往往也以此批评胡适的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胡适说物质不是静止的和死的,大概有同机械自然观划清界限的考虑。胡适是达尔文和赫胥黎生物进化论的坚定拥护者。他接受他们的看法,认为生物是纯粹自然进化和适应的结果,没有任何超自然力量的作用;生物的进化遵循着生存竞争的自然法则,其中也没有任何“自然”的伦理和道德。胡适说:“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残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①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胡适文存》(第二集),第151页。胡适这里说的生物学,就是达尔文创建和赫胥黎竭力传扬的生物进化论,这是胡适一生都信奉的科学之一。在《演化论与存疑主义》中,胡适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用生存竞争、适者生存来解释物种为什么会变化,这打破了类的不变的观念,也打破了上帝造物说,或者其他什么的设计说和规划说。②参见《胡适全集》(第8卷),第35-39页。对胡适来说,生物学还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东西,如,人作为自然的生命都是要死的,没有不朽,没有灵魂不死,当然也没有死后的天堂。但生物学并不讨论不朽、灵魂和天堂问题。
要而言之,胡适用来解释宇宙和万物实在的“自然”,一是指宇宙和万物何以如此的内在原因和机制——“自然而然”;二是指万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和法则;三是指宇宙、万物的广延性、变化。胡适声称,他的这种“自然观”都是依据科学得出的。其实,它是胡适在科学世界观影响下而对宇宙和万物作出的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解释。这种解释,从一方面说,它是“西洋近代科学思想输入中国”在胡适身上的一种产物。一般来说,近代西方在科学影响下的哲学上的“自然”概念,大致有这样几种含义:(1)自然是整个实在和现实的总和,宇宙都是由自然物构成的;(2)世界和宇宙都是“自然”的结果,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没有“超自然”的原因和力量,也无须假定其他终极的实体或根据;(3)“自然”现象具有规则和齐一性,它是可以被认知的,科学的经验方法是认识自然的最有效方式。(4)人类是自然活动的结果和自然世界的一部分,精神和意识是大脑的活动和过程的产物,没有独立的精神实体。以上我们讨论的胡适的“自然”,同这里所说的(2)(3)(4)具有类似性。胡适用自然来指称现实实体、事物和一切现象的全部这一点,是属于他的科学和技术意义上的自然。
胡适的自然主义立场同西方近代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知道了。但胡适说,现代中国的自然主义,又是对中国传统自然主义的复兴。胡适一再强调,对宇宙和万物采取自然主义的立场,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的一个悠久传统。我们知道,在不少方面,胡适都是中国传统的批评者和否定者,以至于他成了全盘性反传统或全盘西化的核心人物。但在自然主义立场上,我们看到了一种相反的情形,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能显示出胡适对中国传统的高度赞美了。现在我们有来自不同地方的自然主义,其中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近代科学产物的自然主义,另一种是近代科学诞生之前的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这两者能够结合吗?对胡适来说这不成问题。他认为,西方近代的自然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古代自然主义的复兴是交互作用的。前者激起了人们对后者的重新关注,后者则为前者提供了土壤。如胡适谈到作为理性主义的自然主义时说:
这种新的理性主义的根本态度是怀疑;他要人疑而后信。他的武器是“拿证据来!”这种理性主义现在虽然只是少数人的信仰,然而他们的势力是不可轻视的。中国民族本是一种薄于宗教心的民族;古代的道家,宋明的理学,都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所以西洋近代的自然主义到了中国便寻着了膏腴之地,将来定能继长增高,开花结果。①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载《胡适文存》(第三集),第577页。
对于中国的自然主义传统,胡适也没有集中性的讨论,他的说法和看法同样散见于他的著述中,如在他的《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等著作中,在他的《先秦诸子进化论》《记郭象的自然主义》《魏晋间人的自然主义的哲学》《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等论文中,我们都能看到胡适有关这方面的言论。根据这些言论,胡适认为中国的自然主义(主要是道家的自然主义)有一个从创立到传承的谱系。他的创立者是老子。老子用“自然”、“无为”的“天道”、“道”取代了早先的意志性和神性之天,用自然的演化取代了神学目的论,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思想。老子之后,《列子》、《庄子》、《淮南子》、《论衡》和郭象的《庄子注》等都以不同方式承继并扩展了老子的自然主义。它们或者像《庄子》和《淮南子》那样,将宇宙和万物看成是道的自然无为的结果,排除了神创论;或者像《列子》、《庄子注》那样,特别强调万物的自生、自化,排除了造物主。对于道家的这种自然宇宙论,胡适评述说:
这个宇宙论的最大长处在于纯粹用自然演变的见解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一切全是万物的自己逐渐演化,自己如此,故说是“自然”。在这个自然演化的过程里,“莫见其为者而功既成矣”,正用不着什么有意志知识的上帝鬼神作主宰。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左派的最大特色。②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载《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68页。
胡适深深为中国古代就有这样一个成熟的自然主义传统所感染。他认为中国中古虽然经历过不幸的宗教化(即佛教化)过程,③他这样说:“我一直认为佛教在全中国‘自东汉到北宋’千年的传播,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巨。”(胡适:《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但幸运的是,道家的自然主义和儒家的人文主义在宋代又再次复兴了,它们把中国人从宗教的非理性中解放了出来:
在那样早的时代(公元前六世纪)发展出来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是一件真正有革命性的大事……这个新的原理叫做“道”,是一个过程,一个周行天地万物之中,又有不变的存在过程。道是自然如此的,万物也是自然如此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是这个自然主义宇宙观的中心观念……然而这个在《老子》书里萌芽,在以后几百年里充分生长起来的自然主义宇宙观,正是经典时代的一份最重要的哲学遗产。自然主义本身最可以代表大胆怀疑和积极假设的精神。自然主义和孔子的人本主义,这两极的历史地位是完全同等重要的。中国每一次陷入非理性、迷信、出世思想,——这在中国很长的历史上有过好几次——总是靠老子和哲学上的道家的自然主义,或者靠孔子的人本主义,或者靠两样合起来,努力把这个民族从昏睡中救醒。①胡适:《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载《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555-556页。
宇宙观上的道家自然主义,对胡适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自然进化观。我们知道,严复曾将《老子》和《庄子》这两部书同进化论联系起来(虽然他同时又批评了两者带有原始主义的消极性),认为这两部著作都有令人惊异的进化观念。胡适同样。在《先秦诸子进化论》中,胡适强调说:“进化论的主要性质在于用天然的、物理的理论来说明万物原始变迁问题,一切无稽之谈,不根之说,须全行抛弃。”②参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575页。对于生物进化论,胡适津津乐道的是,生物之间残酷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打破了慈善上帝的创造说。他说老子早就发现了这一点。老子破除了“天地好生”、“天地有好生之德”的迷信。老子说的“天地不仁,以万物刍狗”,就是认为天地完全是自然而然进行的,没有任何有意的安排。
胡适还从一般性上概括了进化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如天地万物的起源、自古以来天地万物变化的历史、万物变迁的状态和变迁的原因等。由此可知,胡适的进化论不限于生物的进化。胡适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道家思想中发现的进化论,也是如此。深恶探讨万物最终原因的胡适,往往将道家的“道”解释为宇宙的变化、演化的过程(见上述)。胡适说将道作为最高的实在,这是后来人们对老子的误解。③胡适对老子和道家之道的解释,表现了矛盾性的两面:一方面他试图对道作出非绝对实体的解释,这是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另一方面,胡适又认为道家的道只是一个“无从求证”的假设,但道家误认为它就是最高的实在。参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364-365页;《胡适全集》(第5卷),第241-242、578-580页。万物用不着一个先天地生的“道”。从道这个字的本义入手,胡适说道只是自然演变的过程,而不是什么东西:
道即是路,古人用这“道”字本取其“周行”之义。严格说来,这个自然演变的历程才是道。道是这演变的历程的总名,而不是一个什么东西。老子以来,这一系的思想多误认“道”是一个什么东西……道家哲人往往说“造化者”,其实严格的自然主义只能认一个“化”,而不能认有什么“造化者”。①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载《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368-369页。道家的道当然不能只从过程来理解,它先于上帝,先于天地,它是天地和万物之母。
根据以上的讨论,胡适所认知的道家自然主义的“自然”,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指“自然而然”、“自己如此”;二是指“道”的自然无为和宇宙万物变化的历程;三是指生物的自然进化和生存竞争;四是指没有任何造物主、最后之因和神意。按照胡适在《中国传统中的自然法》中对中国古代“自然法”的理解,其中的两项——即“有时求助于天或自然的道(‘道’),即自然法则”、“有时求助于理、道理或天理”,②参见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第202页。同以上的道家的“自然天道”观是一致的。
正如我们在章太炎那里看到的那样,近代中国思想中的“自然主义”尽管对自然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但它都扮演着类似于韦伯所说的“理性化”和“袪魅”的角色。③但在采取的方式和运用的思想资源上,他同章太炎又非常不同。比如,胡适同佛教的观念和信仰格格不入,他将“自然”完全对象化、客体化。在这一方面,胡适也十分有代表性。胡适的“自然主义”既是自然的宇宙观,又是自然合理论(合乎“自然的”就是合理的、理性的),也是批判和否定东西方各种超自然神灵的武器。我们先从胡适对待一起所谓的“闹鬼”事件说起。1922年(民国十一年)3月18日(周六),胡适在日记中记载了一起“闹鬼”事件。这一天胡适受黎邵西之邀,晚上在雨花春饭馆吃饭。受邀客人还有钱玄同、汪怡庵、陆雨庵、卫挺生等。胡适说他们“大谈”了“国语”问题,但他并未记下这方面的内容,他记下的却是陆雨庵家中的“闹鬼”之事。据说,由于各种怪异现象出现在陆家,陆家被迫搬出,而且是限期,不得迟延。在一时找不到合适住处的情况下,陆家只好先住在雨花楼的公寓中。搬出后,陆家雇用了一位穷人住在里面帮助他们看家,但第二天一位泥水匠进入家中时发现,这位穷人已被火烧死。死者跪在地上,上身和头部的肌肉都被烧尽而现出脏俯和筋骨。但室内其他物品并未被烧,只是被子上被烧了一个大洞。④参见胡适:《胡适日记全编(三)》,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85-586页。
胡适是如何看待这桩“闹鬼”事件的呢?按照胡适的自然主义宇宙观,⑤按照胡适的回忆,他从小就受到了范缜神灭论的影响,不相信神佛的存在。(参见胡适:《胡适自传》,第36-38页)他当然不会相信闹鬼之事,也不会相信那位穷人之死真的会有什么神秘的原因。按照他的日记下文的记载,胡适首先肯定这位穷人确实被烧死了,因为他的尸体已被有关官员检查过。但胡适说此事虽然确有“可怪”之处,但陆家闹鬼之事“多”不可信。因为雨庵并未亲眼看见过他所说的怪异现象。雨庵看见的唯一一次,是“鬼”附在一位老妈的身上,她说话的声音变成了男的。但胡适说这仍然可疑。对于穷人被烧死之事,胡适解释为“偶合”。他推测说,那位穷人被烧死一定是一种平常的火,他可能是喝醉了酒而招致了此祸。只是这位穷人是在搬家的次日被烧死的,于是他的死就与“闹鬼”有了一个“因果”关系。
在东西方传统中,上帝、天、鬼神、灵魂不死和因果报应,不仅被认为是实有的,而且也被认为对人类的道德生活是有益的。然而,对于自然主义的胡适来说,这都是不可信、不可取的东西。他说:
古代的人因为想求得感情上的安慰,不惜牺牲理智上的要求,专靠信心(Faith),不问证据,于是信鬼,信神,信上帝,信天堂,信净土,信地狱。近世科学便不能这样专靠信心了。科学并不菲薄感情上的安慰;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要禁得起理智的评判,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①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第5-6页。
从一方面说,胡适的思想同严复具有可比性,比如他们都注重经验科学和实证方法,但从另一方面说,胡适同严复又很不一样。胡适确实是一位科学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而严复则不是。②参见王中江:《从超验领域到道德革新及其古典教化──严复的“宗教观”、“孔教观”和“新民德”》,载《儒林》(第2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胡适和章太炎类似,竭力“祛魅”,竭力要铲除各种超自然世界和力量的存在,但严复则竭力要为“超自然”留下余地。在经验领域里,严复相信和坚持科学的立场,认为一切存在和现象都是可知的。但在此之外,严复又预设了一个超验的、不可知、不可思议的世界;严复还相信各种“超自然”的存在(包括鬼神)。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1917年,严复也还会热心于桐城派人物俞复、陆费逵、丁福保等在上海宣布成立的“上海灵学会”和次年出版的《灵学杂志》,严复还会在致俞复(仲还)和侯疑始的书信中强调“鬼神”的存在,并列举出陈宝琛(弢庵)在光绪甲申丁内艰归里后与一些友人从事的扶乩活动。然而,对于胡适来说,只有一个世界,这就是自然和天的世界,这是完全可以用经验和科学去观察和认知的单纯的“自然”世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没有任何不可知的世界,没有任何“超自然”的神秘领域。如果说严复的思想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是通过科学“祛魅”(特别是宗教世界中的迷信),另一方面他又为巫术、鬼神和迷信留下了空间(“存魅”),那么胡适就没有这种二重性,除了偶然的一时的“皈依”外,胡适是义无反顾地立足于自然主义的“祛魅者”。
二、科学范式中的“自然”
在胡适的自然主义宇宙观中,“自然”这一概念主要是被用以解释宇宙和万物的起源、变迁及其内在根据的,它以自然而然、自己如此这一基本的用法扮演了说明宇宙和万物何以如此的角色,起着解构东西方各种超自然的神及其力量的作用。对胡适来说,这不仅是理智的、科学的立场,也是实际的、现实的需要。除此之外,胡适对自然的使用,主要是将“自然”纳入到“科学”和“技术”的范式之内,使之完全成为科学认知、技术加工的对象和客体。胡适前后一贯地坚持认为,科学和技术是“拷问”自然、解释自然、驾驭自然、利用自然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和方式。这是胡适“自然主义”立场的另外两个方面。在这两方面,胡适都检讨了中国传统的缺陷和缺失。对他来说,人文的、精神性的东西,都要通过对“自然”的科学认知和技术利用中而产生出来,而不是在对自然的茫然、顺从、依附中获得。
在此,如果再次进行一种比较的话,胡适同严复有一致的地方,而同章太炎没有什么共同性。在近代中国自强新政之后,严复竭力主张,中国必须充分发展把握自然奥秘的近代科学和驾驭自然的近代技术,使之成为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途径之一。与此不同,章太炎关心的只是如何将中国和社会从晚清政治和外部帝国的强权中解放出来,而对中国如何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并从中解放出来漠不关心。近代以来的许多中国人认为,这两种解放是有关系的,将传统中国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就是为了获得从列强中解放出来的力量。自强新政是如此,主张广义变法的严复也是如此。到了胡适,这一情况略有变化。对他来说,把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本身就是目的,它不仅是中国人的理智化的需要,也是中国人的幸福所必需的。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胡适的科学范式中的“自然”。
我们知道,胡适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最初选择的专业是农学。按说这是他接触自然的最好的和最直接的方式了。但对苹果进行分类的课程内容,竟然让他不知所措。他不喜欢这样去认识自然,他认为这是浪费时间,甚至是愚蠢的。这是他从学农转到念哲学的原因之一。①参见胡适:《胡适口述自传》,第36-38页。胡适自己不喜欢直接去认识自然,但后来他却成了乐之不疲地教导人们如何去认识自然的启蒙导师。在近代中国将自然对象化、科学化的过程中,胡适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对于自然,至今人类的认知早已无孔不入,无所不在,而且带来了许多问题,但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来说,认识自然和发展中国的科学则是启蒙的主题之一。这是不能忘记的。胡适在这方面展开的启蒙工作是什么呢?
近代以来东西方一直有人在追问中国为什么没有诞生近代科学,①较早的讨论比如冯友兰的《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参见冯友兰的《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稍近的讨论如托比·胡弗的《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周程、于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也有人对当代中国科学发展中的阻力寻根求源,这两种做法都将原因指向了古代。②参见Peng Gong,“Cultural History Holds Back Chinese Research”,Natur e,Vol.481,No.6,2012。胡适对第一个问题的反思,主要就是对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关注“自然”、不将“自然”作为科学认知对象的反思。为了改变这种传统,胡适一方面反思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另一方面是倡导和传播他所理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在胡适看来,中国古代的自然主义宇宙观传统很悠久,它同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相结合,有效地抵制了宗教的狂热和迷信。但是,很遗憾,这两种理性主义传统,都没有促使中国人对自然发生大的兴趣。道家宇宙上的“自然主义”,一开始就具有顺从自然,甚至呼唤回到原始社会的消极主义倾向:
中国古代哲人发现自然的宇宙论最早,在思想解放上有绝大的功效。然而二千五百年的自然主义的哲学所以不能产生自然科学者,只因为崇拜自然太过,信“道”太笃,蔽于天而不知人,妄想无为而可以因任自然,排斥智故,不敢用己而背自然,终于不晓得自然是什么。③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载《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376页。在胡适看来,自然的宇宙论既有纯粹自然演变的意义,也有生物和人类主动去适应和促进演变的意义。④胡适说:“自然的宇宙论含有两种意义:一是纯粹自然的演变,而一切生物只能随顺自然;一是在自然演进的历程上,生物──尤其是人类——可以自动的适应变迁,甚至于促进变迁。”(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374页)但道家只知道遵循纯粹的自然的演变,而不懂得人的主动适应性和能动性。这种自然顺应论导致了人们对认识自然的漠视,也导致了人们对改造自然的忽视。
此外,道家的“道”在抵制和克服自然主宰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人们漠视万物之理和阻碍科学的消极性影响:
然而他们忘了这“道”的观念不过是一个假设,他们把自己的假设认作了有真实的存在,遂以为已寻得了宇宙万物的最后定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的原理,有了这总稽万物之理的原理,便可以不必寻求那各个的理了。故道的观念在哲学史上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其结果也可以阻碍科学的发达。人人自谓知道,而不用求知物物之“理”,这是最大的害处。①参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365页。
可以看出,胡适在强调道家自然主义在中国思想上的革命性贡献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他对这一自然主义产生的因循自然和漠视万物之理这种负面性的检讨。
造成中国人疏远认识自然的另一个原因,在胡适看来是儒家的人文主义传统。同样,胡适一方面肯定这一传统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传统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和《中国的文艺复兴》等著述中,我们都能看到他对这一传统在科学上产生的消极后果的反思。胡适说,中国古代与西方文化一开始就存在的差异,决定了它们后来的不同发展方向。早期的中国构筑了他们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在这方面它同希腊人没有多少差别,但差异在于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对自然物理、数学、几何、力学等也深感兴趣,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陷入伦理与政治理论研究,而希腊学者却在从事动植物、数学与几何学、工具与机械的研究”②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载《中国的文艺复兴》,第55页。。这种程度上的差异性,逐步演变为学术和学问“种类”上的不同。胡适进一步指出,中国一开始的那种倾向性,在中世纪得到了强化,这使中国人更加远离自然:
整个中世纪时期,中国的知识界的生活趋于越来越远离自然对象,而益发深陷于空洞的玄思或纯粹的文学追求。中国的中世纪宗教要人们思考自然、和顺从自然,而不是揭示自然奥秘从而征服自然。而那获取社会声望和公职的唯一通道的科举制度,正有效地把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铸造成一个纯粹追求文字技巧的生活。③同上书,第56页。
对于李约瑟等一些中国科学史研究者来说,这样的结论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中国在科学和技术上的落后,只是最近几个世纪的事。④参见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陈立夫主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但胡适说中国古代注重道德和政治领域的研究,注重文本、文献和文学的研究是不容否定的,科举制度与此恰恰又有因果之关系。
中国的宋明清复兴了儒家的人文主义,有效地抵制了中古时代中国的佛教化和宗教化,但这仍然没有将中国人引向对自然的好奇上,他们继续沉潜于伦理、政治的研究中,沉浸于书本、文学和文献学的研究中。看上去是一个矛盾:胡适对朱熹的“格物穷理”给予了很高的肯定,认为宋代人对它的解释非常符合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但胡适又说,他们的逻辑方法却是没有效果的,其中“最不幸的是把‘物’的意义解释为‘事’”①胡适:《先秦名学史》,先秦名学史翻译组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这是胡适1915年至1917年之间在纽约完成的《先秦名学史》一书中说的话。在这部书中,胡适还进一步说:
朱熹和王阳明都同意把“物”作“事”解释。这一个字的人文主义的解释,决定了近代中国哲学的全部性质与范围。它把哲学限制于人的“事务”和关系的领域。王阳明主张“格物”只能在身心上做。即使宋学探求事事物物之理,也只是研究“诚意”以“正心”。他们对自然客体的研究提不出科学的方法,也把自己局限于伦理与政治哲学的问题之中。因此,在近代中国哲学的这两个伟大时期中,都没有对科学的发展作出任何贡献。②同上书,第6页。
朱子等中国的哲学家真正关心的不是探索“自然”的奥秘,而是探索经典和书本的奥秘,清代的考据学家们更是将这种方法集中运用到历史和文献之中。③胡适在《格致与科学》(1933年)中也解释了中国哲学家为什么在格物上会失败:“他们失败的大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学者向来就没有动手动脚去玩弄自然界实物的遗风。程子的大哥程颢就曾说过‘玩物丧志’的话。他们说要‘即物穷理,其实他们都是长袍大袖的士大夫,从不肯去亲近实物。他们至多能做一点表面的观察和思考,不肯用全部精力去研究自然界的实物’。久而久之,他们也觉得‘物’的范围太广泛了,没有法子应付。所以程子首先把‘物’的范围缩小到三项:(一)读书穷理,(二)尚论古人,(三)应事接物。后来程朱一派都依着这三项的小范围,把那‘凡天下之物’的大范围完全丢了……十七世纪以后的朴学(又叫做‘汉学’),用精密的方法去研究训诂音韵,去校勘古书。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是科学的,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学的。但他们的范围还跳不出‘读书穷理’的小范围,还没有做到那‘即物穷理’的科学大范围。”(《胡适全集》(第8卷),第81-82页)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胡适也说:清代朴学的“方法虽是科学的,材料却始终是文字的。科学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纸堆里大放光明,然而故纸的材料终久限死了科学的方法,故这三百年的学术也只不过文字的学术,三百年的光明也只不过故纸堆的火焰而已”。(参见《胡适文存》(第三集),第94页)相比于对自然的兴趣,中国哲学家更关心的是政治和伦理领域,这同近代科学根本上是面向“自然”和以“自然”为对象形成了明显的不同,这是造成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之一。
胡适还比较了最近三百年东西方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就是西方在科学的许多领域中都开花结果,而中国主要还是沉溺于文字和文献的研究中,没有去倾听自然的声音:
纵观科学发达史,可知东方与西方之学术发展途径,在很古的时代已分道扬镳了。自然科学虽到近三百年中始有长脚[足]的发展,但在希腊、罗马时代,已有自然科学的基础。[例如,Aristotle(亚里士多德)解剖过50种动物]而东方古文化实在太不注重自然界实物的研究,虽有自然哲学而没有自然科学的风气。故其虽有“格物穷理”的理想,终不能产生物理的科学,只能产生一点比较精密的纸上考证学而已。可见研究的对象(材料)又可规定学术的途径与成就。①胡适:《科学概论》,载《胡适全集》(第8卷),第90页。
胡适的这种解释前后是一贯的。1959年,胡适在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三届东西方哲学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大会发言。他不接受一些西方人对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的苛刻批评。他辨析说,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不等于说中国没有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中国古代特别是近世,事实上具有丰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孔子和老子都具有理性、质疑和探索的意识,朱熹的“格物穷理”具有依据事实、证据和归纳的意识。朱子要“格”的“物”十分宽泛,它包罗一切,从天高地厚到一草一木。朱熹对学问的研究和清代的考据学,体现的都是从证据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及方法。问题是,具有如此丰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竟没有产生近代科学:
这种精神和方法并没有造成一个自然科学的时代。顾炎武、戴震、钱大昕、王念孙所代表的精确而不受成见影响的探索的精神并没有引出来中国的一个伽利略、维萨略、牛顿的时代。②胡适:《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载《胡适全集》(第8卷),第511页。
对此,胡适提出的解释依然是之前他强调的东西。他谈到了之前他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的对比,认为阻碍科学在中国出现的主要原因,就是哲学家把“物”限定在“人事”上,没有把“自然”作为学问和研究的对象。
中国人不关心探索“自然”的原因除了上述胡适所说之外,一般认为它还同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科举制度有密切的关系。早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对中国文化有深入认识和感受的利玛窦就发现,中国人普遍感兴趣的是道德哲学,这是因为钻研数学和医学的人不受人尊敬。中国人对道德哲学深感兴趣,是因为学习道德哲学能够通向科举功名,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和荣誉,并达到人生幸福的顶点。①参见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何高济、王遵仲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44页。事隔两个多世纪后,在严复那里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检讨。他批评说,中国古代学问的中心是文字之学,是为官之学,是师心自用之学,这种学问都让人远离自然(虽然严复也认为中国的古典中也包含有科学的方法)。对此,胡适也注意到了。他说科举考试是中国最优秀的人追求的目标,而这种考试完全是测试人们在人文和文字方面的能力。与此不同,西方人比较早地将智力转向了“自然”。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用具体的例子比较了中西在两三百年间的不同选择,并得出结论说:“西洋的学者先从自然界的实物下手,造成了科学文明,工业世界。”②《胡适文存》(第三集),第101页。
虽然胡适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自然”没有被作为科学认知的对象并且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但他相信中国传统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并不会成为中国接受和发展近代科学的障碍,它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也完全可以与现代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结合起来。近代中国的认知转向“自然”,同时也伴随着如何认识自然的方法论自觉。从近代中国墨家和名学的复兴,到西方逻辑学的移植、知识论的建立和科学方法的阐释,可以说都是这种方法论自觉的表现。在这一方面,严复是一个典型(包括他翻译穆勒的《逻辑》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严复之后,胡适是又一个典型。
胡适认识到,如果我们单是转向“自然”而不掌握和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我们照样不能发现自然的奥秘,结不出科学之果——真理,我们在自然面前将一无所获。这是因为自然从不轻易向人敞开它自己的秘密,真理并不容易求得(“理未易察”):
“自然”是不容易认识的,只有用最精细的观察和试验,才可以窥见自然的秘密,发现自然的法则。………自然是个最狡猾的妖魔,最不肯轻易吐露真情。人类必须打的她现出原形来,必须拷的她吐出真情来,才可以用她的秘密来驾御她,才可以用她的法则来“因任”她。③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参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375-376页。
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探讨,他决不会露面。科学的文明教人训练我们的官能智慧,一点一滴地去寻求真理,一丝一毫不放过,一铢一两地积起来。这是求真理的唯一法门。自然(nature)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逼拶可以逼她吐露真情。④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中》,载《胡适文存》(第三集),第4页。王阳明“格竹子”失败的感叹就是一个例子。胡适评论说:王阳明的话“表示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从来没有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虽然有‘格物致知’的理想,终不能实行‘即物穷理’,终不能建立科学”①胡适:《格致与科学》,载《胡适全集》(第8卷),第82页。。
为了使以认知“自然”、探寻“自然”奥秘为中心的科学迅速在中国发展起来,胡适首先回头去挖掘中国传统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如他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去探讨中国的先秦名学,他的目的正是为了复兴中国已有的逻辑和方法;胡适更竭力去宣扬近代以来西方建立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他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对赫胥黎的科学思想的兴趣,更多地是把他们的学说看成是一种通向科学的方法;杜威“实验主义”吸引他的地方,主要也是其中的科学方法。有关这方面我们已有很多的研究。在此,我想强调的是,胡适提出的探索“自然”的科学方法,主要表现在他津津乐道的怀疑、假设、实验、事实、证据等观念中,尤其是表现在他十分得意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信条中:
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②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自序)》,载《胡适文存》(第四集),第463页。对胡适来说,探寻自然的奥秘不仅需要严格的科学方法,还需要高度的耐心和毅力。(参见胡适:《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载《胡适讲演》,第346页)胡适注重科学方法,他对这种方法的运用则仍是历史和国故领域。
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③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载《胡适文存》(第三集),第93页。
但到了最后,胡适的科学方法却变成了养成治学的个人的良好习惯,比如“不懒惰”、“不苟且”、“肯虚心”的习惯。④参见胡适:《科学概论》,载《胡适全集》(第8卷),第90页。不管如何,胡适自己并没有将他倡导的科学方法运用在自然上,他个人的兴趣也不在自然上。自从他告别农学之后,他就同自然分道扬镳了。他的兴趣是在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学和文字上,一句话是在他所说的“整理国故”上,因此,他倡导的科学方法对他而言最后也只能落实在“非自然”的领域中。
三、技术范式中的自然
上面我们讨论的是胡适的东西语境中的“自然”与科学认知的关系,是胡适克服中国旧传统中漠视自然探索、借助于西方新传统将自然对象化、科学化的科学的自然主义。与此密切相联,胡适也渴求将自然高度技术化和工具化,使自然成为人类有待加工和使用的一切物质和材料,通过普遍地利用自然以充分满足人类生存的各种需求。按照胡适的主张,人类对于自然要做的事,就是最大限度地改造、利用它,就是不断地运用新工具和技术从它那里获得可资利用的一切东西。对胡适来说,这也是中国迫切需要“充分世界化”的方面。1926年,胡适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态度》,可谓是他动员中国人接受西方技术文明的一篇“宣言”。之后,在不同的场合,胡适一直在为自然的技术化和工具化而摇旗呐喊(虽然从晚清开始中国人就在辅助的意义上要求输入兴起于西方的控制和利用自然的技术)。这可以说是胡适的“技术自然主义”,或者说是狭义的胡适的“工具理性”。
胡适的技术自然主义包括了一些不同的方面。首先,它是一种对人的精神上的要求。按照这种要求,我们在自然面前要有自己的主动性而不是被动地适应它,我们要成为自然的改造者和利用者而不是它的依附者,我们要相信自身的能力、勇气和冒险精神而不是安于现状和退缩,我们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幸福委之于自己而不是超自然的力量:
从前人类受自然的支配,不能探讨自然界的秘密,没有能力抵抗自然的残酷,所以对于自然常怀着畏惧之心。拜物,拜畜生,怕鬼,敬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都是因为人类不信任自己的能力,不能不依靠一种超自然的势力,现代的人便不同了。人的智力居然征服了自然界的无数质力,上可以飞行无碍,下可以潜行海底,远可以窥算星辰,近可以观察极微。这个两只手一个大脑的动物——人——已成了世界的主人翁,他不能不尊重自己了……这是现代人的宗教。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我们现在不妄想什么天堂天国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建造“人的乐园”。我们不妄想做不死的神仙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活泼健全的人。我们不妄想什么四禅定六神通了,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个有聪明智慧可以戡天缩地的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我们也许不信灵魂的不灭了,我们却信人格的是神圣的,人权是神圣的。这是近世宗教的“人化”。①胡适:《我们对近代西洋文明的态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第6-7页。胡适还引用外国少年一首诗:“我独自奋斗,胜败我独自承担,我用不着谁来放我自由,我用不着什么耶稣基督,妄想他能替我赎罪替我死。”(同上书,第6页)
按照胡适的说法,自主、自尊、进取的精神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新的宗教,人不再相信任何主宰者和救世主,他完全凭借自身的智慧、勇气和力量去面对自然。
第二,从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精神出发,胡适始终主张人类“戡天缩地”,始终主张用人类的智慧和能力最大限度地从自然中获得一切所需要的东西,这里的人类当然首先是指中国人。我们看到,每当胡适谈到人类如何对待“自然”时,他总是喜欢使用诸如“改造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等字眼。现在这些字眼对我们来说已经变得非常刺眼,我们不仅不再轻易地倡导“征服自然”了,而且对科学和技术导致的问题展开了反省,甚至用“敬畏自然”来改变我们对“自然”的冷酷无情。但对于当时的胡适来说,这还不是问题。胡适一生一心所想的只是如何改变中国的贫穷和中国人的贫穷生活,而“自然”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而存在的(这是他的“人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只要能够满足人类生活的需要,人类对于自然可以采取任何他们能够采取的方式。胡适在美国文明中看到了它的典型表现,他称之为“大量生产主义”。它以严格的组织和分工,按一定的程序,源源不断地使原料变成人类所需要的制品。没有比“我们要捶他,煮他,要叫他听我们的指派”这种形象化的说法,更能说明胡适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意识了。这句话出自1930年胡适为纪念中国科学社成立15周年而为中国科学社撰写的社歌中:②后由赵元任谱曲,并于1930年10月25日北平社友庆祝本社十五周年上试唱。有关“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和发展,参见坂出祥伸的『中国の近代思想科と学』,京都:同朋社1983年版,第555-578页。
我们不崇拜自然。他是一个刁钻古怪;
我们要捶他,煮他,要叫他听我们的指派。
我们要他给我们推车;
我们要他给我们送信。
我们要揭穿他的秘密,好叫他服事我们人。
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
明知道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③胡适:《工程师的人生观》,载《胡适讲演》,第400-401页。
1952年,胡适在台湾台南工学院做了《工程师的人生观》的演讲,他说他本来是学农的。为了表示对“工学”的看重,他还说他到六七十岁也许会成为一名工学院的老学生。这足以表明人文主义的胡适,同时又是一个多么浓厚的技术自然主义者。也正是在这次演讲中,胡适提出了一个“工程师的人生观”:
什么叫做工程师呢?工程师的作用,在能够找出自然界的利益,强迫自然世界把它的利益一个一个贡献出来;就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以减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幸福。①胡适:《工程师的人生观》,载《胡适讲演》,第395页。
人与蜘蛛、蜜蜂、珊瑚虫所以不同,是在他充分运用聪明才智,揭发自然的秘密,来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②同上书,第396页。
在演讲的结尾,胡适还特意引用了他20年前为中国科学社所作的社歌,并将它送给了在座的工程师们。胡适提出的“工程师的人生观”表明,相比于他主张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的奥妙来,他更倾心的是人类如何充分地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由此可知,胡适不会接受那种纯粹出于理智好奇去认识自然的看法,这同他的真理观、经验观和环境观也是非常吻合的。如,胡适的主动“适应自然”往往也是指主动地去适应“环境”,他说人类经验就是这种适应的结果:
现在我们受了生物学的教训,就该老实承认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与环境的交互行为,就是思想的作用指挥一切能力,利用环境,征服他,约束他,支配他,使生活的内容外域永远增加,使生活的能力格外自由,使生活的意味格外浓厚。③胡适:《实验主义》,参见《胡适文存》(第一集),第233页。
第三,胡适歌颂近代的技术革命,将新的工具、器具的发明及其运用看成是人类新文明的显要标志,坚信新工具和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最有效手段。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有人抵制这种文明,这包括了了解西方的人。如辜鸿铭感受过英国的技术文明,马一浮感受过美国的工具文明,但他们对此都持抵制的立场,这构成了他们反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与此截然不同,胡适和他的前辈和同时期的人,都坚持认为中国必须接受和发展这种文明。他认为美国的技术和工业文明,造就了美国人丰富的物质生活,也造就了他们的幸福。胡适引用法国科学家柏格生(Bergson)说的“人是制器的动物”、“人是能够制造器具的动物”来证明人优越于其他事物的高明之处。发明家富兰克林当然也表述过类似的(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意思。事实上,生物和动物不同程度上也有使用工具的能力。但胡适说它们的能力太低了,它们无法同人类的制器相提并论。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胡适称道吴稚晖说的人生只不过是两只手和一个大脑在台上做游戏的动物:
这出戏不是容易做的,须充分训练这两只手,充分运用这个大脑,增加能力,提高智慧,制造工具:品物越备,人的能力越大,然后“能以人工补天行,使精神上一切理想的道德无不可由之而达到又达到”。①参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第1184页。
第四,胡适一再强调,改造和利用自然完全是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福祉和幸福的目的,也是发展人类的精神生活所必需的。从晚清开始,中国人主要将发展技术和工业文明看成是寻求富强、实现国家独立和强大的必由之路,与此有所不同,胡适将技术和工业文明首先并主要看成是满足人的物质生活和幸福的需要。如胡适说:
控制自然,为的是什么呢?不是像蜘蛛织网,为的捕虫子来吃;人的控制自然,为的是要减轻人的劳苦,减除人的痛苦,增加人的幸福,使人类的生活格外的丰富,格外有意义。这是“科学与工业的文化”的哲学。②胡适:《工程师的人生观》,载《胡适讲演》,第396页。
在《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中,胡适认为科学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③《胡适全集》(第22卷),第690页。。西方的技术文明一开始就建立在人生的幸福之上,因为它把幸福看成是人生的目的,把贫穷和衰病看成是社会的罪恶:
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④《胡适文存》(第三集),第9-10页。
1956年,在《大宇宙中谈博爱》中,胡适承认一些伟大的宗教都是出于对人类的爱,它们主张爱他、利他而牺牲自己也都是崇高的。但是,胡适同时又指出,用个人有限的能力甚至是不人道的方法去爱人,既非常有限,又非常可笑。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如工程、医学带给人类的不仅是能力,而且是广大的爱。它减少了人类无数的痛苦,大大增加人的幸福:
现在的科学才能放大我们的眼光,促进我们的同情心,增加我们助人的能力。我们需要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博爱——一种实际的爱。①参见《胡适讲演》,第404页。
客观而论,现代技术和工业文明确实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确实推动了人类的精神发展。近代早期的中国人对西方技术的热心主要是出于民族自救、自保的需要,他们希望通过西方的工业技术使中国获得对付西方强权的力量以获得民族的独立和自决,一般称之为“自强”、“富强”。这是一种服务于民族主义需要的技术目标。进一步,中国人对技术文明的热衷,又是出于改善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存状况的需要。他们认为西方通过工业文明使人们获得了物质生活上的富裕和快乐。严复的开明自利主义所主张的就是如此。胡适主张接受西方的技术文明,主要是出于后者。他强烈渴望中国能够步西方工业化和技术化的后尘,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上发生革命性的转变,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条件,使中国人也过上富裕和幸福的生活。在近代中国非常贫穷的情况下,胡适强烈要求推进中国的技术文明是十分自然的,只不过他对技术和工业文明采取了过于乐观主义的立场。
胡适从东西语境中出发建立他的自然主义,同样也体现在他评判中国传统与技术文明的关系上。对此,他有肯定的方面,但主要是批评性的。在肯定的方面,胡适高度赞赏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征服自然的精神。胡适说,荀子一方面用道家的无意志的天去改变儒家的“赏善罚恶”的有意志的天,另一方面又避免了道家因循自然特别是庄子的安命主义,提倡一种征服自然的“戡天主义”。对于荀子在《天论》中说的“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胡适无以复加地称道说:
这是何等伟大的征服自然的战歌!所以荀子明明是针对那崇拜自然的思想作战,明明的宣言:“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这个庄、荀之分,最可注意。②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参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374页。
把自然控制来用,中国思想史上只有荀子才说得这样彻底。从这两句话,也可以看出中国在两千二三百前,就有控制天命——古人所谓天命,就是自然——把天命看作一种东西来用的思想。③胡适:《工程师的人生观》,载《胡适讲演》,第398页。在改造自然的意义上,胡适也有限地赞美了《淮南子》。因为《淮南子》在主张老子“无为”的同时,也主张“有为”。胡适还称赞了中国古代制造工具、利用自然的意识和观念。他以《周易》说的“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为根据,认为人类运用工具控制自然观念是东西方圣人和贤人都具有的。
但摆在胡适面前的问题不只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还有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的技术。对此,胡适主要用道家自然主义宇宙观的副作用来解释。他批评说,道家一味地崇拜自然、顺从自然、因循自然,忽视了人在自然面前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作用:
简单一句话,我们不幸得很,二千五百年以前的时候,已经走上了自然主义的哲学一条路了。像老子、庄子,以及更后的《淮南子》,都是代表自然主义思想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哲学发达的太早,而自然科学与工业发达的太迟:这是中国思想史的大缺点。①胡适:《工程师的人生观》,载《胡适讲演》,第399页。
胡适说,这一缺点从老子开创道家的自然主义时就开始了:“老子因为迷信天道,所以不信人事,因为深信无为,所以不赞成有为。”②胡适:《先秦诸子进化论》,参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578页。之后,庄子、列子和《淮南子》的哲学,进一步加深了老子的这种自然无为的消极观念,陷入到了崇拜自然、随顺自然、因循自然的困境之中。如庄子的生物进化论把生物的进化看成是自生自化,虽然否定了主宰和“最后之因”,但在解释生物为什么能进化上,庄子只看到了生物被动适合的情形,忽略了生物的主动的适合:
近世生物学者说生物所以变迁进化,都由于所处境遇(E nvironment)有种种需要,故不得不变化其形体机能,以求适合于境遇。能适合的,始能生存。不能适合,便须受天然的淘汰,终归于灭亡了。但是这个适合,有两种的分别: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被动的适合,如鱼能游泳,鸟能飞,猿猴能升木,海狗能游泳,皆是。这种适合,大抵全靠天然的偶合,后来那些不能适合的种类都澌灭了,独有这些偶合的种类能繁殖,这便是“天择”了。自动的适合,是本来不适于所处的境遇,全由自己努力变化,战胜天然的境遇。如人类羽毛不如飞鸟,爪牙不如猛兽,鳞甲不如鱼鳖,却能造出种种器物制度,以求生存,便是自动的适合最明显的一例。《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③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参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181页。胡适还举例说,为了避免把“无为”混同于“没有人事”,《淮南子》把无为解释为“合乎自然的行为”,但这样的“因任自然”的“无为”,仍然有“不以人易天”的危险,都有取代“有为”的消极性:
《修务训》里明说,水之用舟,泥之用輴等事,不算是有为,仍算是无为。用心思造舟楫,已是“用己”了;顺水行舟,还算是不易自然;逆水行船,用篙,用纤,这不是“用己而背自然”吗?如果撑船逆流,用篙用纤,都是无为,那么,用蒸汽机行驶轮船,用重于空气的机器行驶飞机,也都是无为了。究竟“自然”与“背自然”的界线画在那一点呢?须知人类所以能生存,所以能创造文明,全靠能用“智故”,改造自然,全靠能“用己而背自然”。①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参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第375页。
《老子》说的“虽有舟车,无所乘之”,特别是《庄子·天地》篇批评汉阴丈人用桔槔汲水、《马蹄》篇反对羁勒驾马,确有胡适说的“不以人易天”的倾向,有明显的减少和降低人类行为的旨趣。但细究起来,道家的自然主义具有复杂的内涵,老子的“无为”主要是反对控制,让事物自身按照自身的愿望去选择和发展。②参见王中江:《道与事物的自然:老子“道法自然”实义考论》,载《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淮南子》的无为也有这样的“高明”之处。庄子批评人为的东西,是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破坏了人类的真实性。但胡适的批评都大而化之地将它们纳入到一个说法之下,那就是“不作为”:
总之,老子、列子、庄子,都把“天行”一方面看得太重了,把“人力”一方面却看得太轻了,所以有许多不好的结果。处世便靠天安命或悲观厌世;遇事便不肯去做,随波逐流,与世浮沉;政治上又主张极端的个人放任主义,要挽救这种种弊病,须注重“人择”、“人事”、“人力”一方面。③胡适:《先秦诸子进化论》,载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588页。
这是近代中国人批评道家的主要方式。除了以上来自道家自然主义的消极倾向外,胡适认为中国传统的迷信、佛教的来世信仰等,也让中国人在自然面前收敛和萎缩起来,失去了对自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东方人在过去的时代,也曾制造器物,做出一点利用厚生的文明。但后世的懒惰子孙得过且过,不肯用手用脑去和物质抗争,并且编出“不以人易天”的懒人哲学,于是不久便被物质战胜了。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①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胡适文存》(第四集),第458-459页。
不管如何,中国人在19世纪自强新政中开始肯定和接受西方的技术文明了。但以技术为中心的“自强新政”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受到了质疑和批评;西方“一战”及其残酷性,不仅使西方人对自身的文明产生了怀疑,也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现代技术文明产生了怀疑。继“中体西用”之后产生的东方文明是精神的、西方文明是物质的这种二元论,是当时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怀疑。1923年中国发生的科玄论战,也是在这种情形下发生的。让胡适一生最不能接受的说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明为“物质文明”、以东方文明为“精神文明”的这种文明二元论;②有关这一方面,参见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对胡适来说,也没有什么比这一论调更站不住脚了。上述胡适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其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反驳这种东西文明二元论。他的文章一开头就用很刺激的话说:“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崇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rual)。”③《胡适文存》第三集,第1页。胡适为了增加他的立论的说服力,他把林语堂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的《机器与精神》作为附录收入到了他的文存[《胡适文存》(第三集)]中。此文是林语堂1929年12月在光华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的讲稿。胡适在林语堂的《机器与精神》一文中找到了知音,他将这篇文章附在他的文后。胡适较早发表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批评了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提出的“科学破产”的观点和把近代西方的人生观归结为“纯物质纯机械”的观点。1953年1月,胡适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的座谈会上作了一个演讲。在演讲之后的提问中,有人就说美国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胡适如何回答可想而知,他还提到了他多年前发表的《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为了不在文明概念上产生歧义并有力地批评东西文明二分论,胡适首先提出了判断文明的标准。他将文明(Civilization)界定为一个民族应对环境的总成绩(文化则是这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按照这一标准,任何文明都一定有两个因子,一个物质的,一个精神的。前者包括种种自然界的势力和质料;后者包括了一个民族的才智、感情和理想。胡适说:
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④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第1-2页。
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运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头是物质;而刳木为舟,构木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①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胡适文存》(第四集),第458页。
按照胡适的这一逻辑,中国不会只有精神文明,它也会有物质文明;西方不会只有物质文明,它也会有精神文明。但这样的结论仍然不会满足胡适的立场。继之,胡适进一步认为,西方不仅具有高度的近代物质文明,而且在此基础上它也产生了高度的近代精神文明。与此相反,东方没有产生出近代的物质文明,相应地它也没有近代的精神文明,它反而更可以说是唯物的。胡适对比说:
知足的东方人自安于简陋的生活,故不求物质享受的提高;自安于愚昧,自安于“不识不知”,故不注意真理的发见与技艺器械的发明;自安于现成的环境与命运,故不想征服自然,只求乐天安命,不想改革制度,只图安分守己,不想革命,只做顺民。
这样受物质环境的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只可以遏抑而决不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
西方人大不然,他们说“不知足是神圣的”(Divine Discontent)。物质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钢铁世界、汽机世界、电力世界。理智上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科学世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知足产生了今日的民权世界、自由政体、男女平权的社会、劳工神圣的喊声、社会主义的运动。神圣的不知足是一切革新一切进化的动力。
这样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制服天行以供人用,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应该能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文明,决不是唯物的文明。②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载《胡适文存》(第三集)第10页。
最后,在胡适那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化的不可分立场,变成了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的信念。人类只有满足了物质生活的需求,他们才有可能去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
我们深信,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提高人类物质上的享受,增加人类物质上的便利与安逸,这都是朝着解放人类的能力方向走,使人们不至于把精力心思全抛在仅仅生存之上,使他们可以有余力去满足他们的精神上的要求。①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第2页。
胡适与东西文明二元论的分歧可以从多方面去分析,其中一个是对西方物质和技术文明有没有必要加以反省的问题(包括残酷的“一战”与这种文明的关系)。胡适强调的是,在近代文明中,中国人的物质条件实在太落后了,中国人的生活实在太艰苦了,只有通过近代的技术和工业文明才能让中国人过上好的物质生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精神生活,否则一切都是好高骛远的空谈。胡适可能知道,西方对近代技术文明的反思在它的发源地早就开始了,比如19世纪欧美的浪漫主义者。但胡适的想法是,谈论科学和技术文明对中国造成的问题还为时尚早,因为这种文明在中国的成长才刚刚开始。最后,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胡适遇到了后来东西方人士对技术文明的反省和批判,遇到了像卡普拉在《新物理的未来──第三版后记》中批判现代人对自然的主宰性立场,②卡普拉批评说:“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认为对自然界的了解意味着男人对自然界的统治。在此我故意用‘男人’这个词,因为我谈到的是科学中机械论的宇宙观与意欲控制一切事物的男性倾向这种家长式的价值观体系之间的重要关系。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把这一关系拟人化了。他在17世纪以激昂的,并且常常是坦率的恶言提出了科学的新经验方法。培根写道,自然界必须‘在她的游荡中被追猎’,‘迫使她服务’,并使她成为‘奴隶’。要将她置于约束之下,而科学家的目的就是‘从自然界拷问出她的秘密’。把自然界看做是一个女性,要将她‘置于约束之下’,不得不借助于机械的设备来从她那儿拷问出她的秘密。”(卡普拉:《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322页)他会作出如何的反应。
四、从人的自然到伦理
在人生和伦理中,胡适的自然主义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胡适认为人类的伦理和道德是不断变化和演化的,就像没有绝对的一成不变的真理那样,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的伦理和道德;与此相联,另一个方面是,胡适认为人类的伦理和道德必须建立在人的自然性(包括人的本能和欲求)的基础之上,压抑人性和人的自然性的伦理和道德,都是不人道和正当的。这两个方面是胡适伦理自然主义的两个信念。上述胡适有关技术文明与人的精神生活和幸福之间的关联已经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
就第一个方面而论,胡适竭力排除伦理道德上的本质论、先验论和神启论。我们知道,道德上的本质论、先验论和神启论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东西方传统中。按照神启论和神正论,神、上帝是人类正义和公正的根源和保证。胡适不承认超自然的神和力量,他像杜威或更有甚之地厌恶本质、先验和神启观念,完全拒绝为伦理和道德寻找神启的解释。胡适诘问说,如果万物都属于上帝的综合的大规划和上帝的安排等,为什么人类实际上充满着不公正,充满着邪恶。胡适对宗教和神灵的批判,除了理智上认为它不可信、不可求证等根据外,他还一直否定神灵对人类的道德作用。如,他在日记中多次留下了他对“预设宗教必要性”的否定。在他看来,按照实验主义的标准,信仰超自然的神对人类没有任何实际的伦理和道德的作用:
我们假使信仰上帝是仁慈的,但何以世界上有这样的大战,可见得信仰是并非完全靠得住,必须把现在的事情实地去考察一番,方才见得这种信仰是否合理。①《胡适讲演》,第327页。
依此标准看来,信神不灭论的固然也有好人,信神灭论的也未必全是坏人,即如司马光、范缜、赫胥黎一类的人,说不信灵魂不灭的话,何尝没有高尚的道德?更进一层说,有些人因为迷信天堂、天国、地狱、末日裁判,方才修德行善,这种修行全是自私自利的,也算不得真正道德。总而言之,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既没有实际的影响,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了。②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载《胡适文存》(第一集),第503页。
胡适信奉的是,最小的实际效果比没有实际效果的伟大的空想更有益。上帝、神是否对人类的伦理和道德发生作用,只能通过它是否能表现出实际的效果来衡量,否则这就是把善的希望寄托在没有现实性的“空头支票”上。③《胡适讲演》,第301页。
不承认伦理和道德的本质论、先验论,与胡适从进化论和适用论去解释伦理和道德的发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道德上的本质论和先验论往往假定,伦理和道德原则是一成不变的,它适用于各个时代。胡适否认能为人类带来美德的神和上帝,也决不接受伦理、道德的不变论。早在1913年,胡适当时还在康乃尔大学学习,他就以“道德观念变迁”为题对道德发表了看法,认为时代变迁,道德也随之变迁,而且它遵循的是进化的法则。1913年10月18日,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列举道德变迁的一些例子后说:
凡此之类,都以示道德是非之变迁。是故道德者,亦循天演公理而演进者也。①《胡适全集》(第27卷),第240-241页。
只是,这时胡适还保留有“真是非真善恶”是永恒不变的信念,说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对它们都无所影响。但之后,进化、实验、历史的观念对胡适的思想越来越具有支配性,从他那里我们常常能听到的就只是伦理、道德的进化和变迁的声音了。1914年11月16日,他抄录了“袁氏的尊孔令”,批评说这一尊孔令共有七种错误,其中有两种错误是:接受政体的革新却断定“礼俗当保守”;以孔子之道为“亘古常新,与天无极”。对于前者,胡适质疑为什么偏偏礼俗不应该革新,对于后者胡适说这是“满口大言,毫无历史观念”②参见同上书,第561-562页。。按照胡适的立场,礼俗和孔子之道都是历史的产物,也都要随着历史而变化和革新。
在胡适那里,伦理、道德的演化和变迁,同时也是它不断增加适应性、适用性的过程。在新文化运动中,这是胡适思想最为活跃之时,胡适提出了当时中国的“新思潮”的概念,认为这一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评判的态度”,它也是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说他的“评判的态度”是遇事都要“重新”去分辨好不好,是不是、适不适。在这一点上胡适也采取了鲜明的立场,他批评调和论和折中论并说:“评判的态度只认得一个是与不是,一个好与不好,一个适与不适。”③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载《胡适文存》(第一集),第527-528页。对胡适来说,伦理道德原则就像技术工具那样,同样是使人类生活方便的工具。中国传统的伦理和道德在过去作为工具是有效的、有用的,但到了现在的中国,到了现在的“时势”和国体,都要求新的伦理和道德原则,不能再固守旧的过时的伦理和道德了。与胡适类似,新文化运动的其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否定孔子的伦理,大都采取了类似的论证方式。
胡适要重估的东西,主要是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更具体地说是儒家的伦理和礼教。他说:“孔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孔教的价值……贞操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贞操的道德在现代社会的价值……礼教的讨论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纲常礼教在今日还有什么价值。”④同上书,第528页。如,“三纲”等,它们不是绝对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对于新的社会来说,它已经不适用了,应该毫不可惜地予以抛弃:
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的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他做“真理”;因为他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譬如“三纲五伦”的话,古人认为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的社会里很有点用处。但是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三纲”便少了君臣一纲,“五伦”便少了君臣一伦。还有“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两条,也不能成立。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有许多守旧的人觉得这是很可痛惜的。其实这有什么可惜?衣服破了,该换新的;这支粉笔写完了,该换一支;这个道理不适用了,该换一个。这是平常的道理,有什么可惜?“天圆地方”说不适用了,我们换上一个“地圆说”,有谁替“天圆地方”说开追悼会吗?①胡适:《实验主义》,载《胡适文存》(第一集),第225-226页。
胡适这里说的“真理”,主要不是指认知意义上的是非、真假,而是指人的一种工具包括传统伦理和道德是否还适用。胡适评判的大旗断定儒家传统的许多伦理和道德原则包括“三纲”在内已经完全不适用现代社会的需要了。
就第二个方面说,胡适的伦理自然主义是主张从人性、从人的自然性出发去建立伦理和道德。胡适始终坚持认为,伦理和道德必须能够满足人的自然欲求,满足人的物质生活要求,并进而满足人格发展的需求。与第一个方面结合起来看,伦理和道德的过时不过时、适不适,究其实质是看它合乎不合乎人性、合乎不合乎人的自然性、合乎不合乎人的个性。传统伦理道德的不人道,不合乎人性,就是因为它不仅压抑了人的自然性,而且也压抑人的精神发展。比如,传统伦理对女性的压抑。对此,胡适和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袖们,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展开讨论和批评。围绕女性的贞操伦理,胡适先后撰写和发表了《贞操问题》(载《新青年》5卷第1号,1918年7月15日)、《美国的妇人》(载《新青年》5卷第3号,1918年9月15日)、《论贞操问题——答蓝志先》(1919年4月作,收入《胡适文存》一集)、《女子解放从那里做起》(1919年7月27日《星期评论》第8号)、《女子问题》(1921年8月4日胡适在安庆青年会暑期讲演会的演讲辞,载《妇女杂志》第8卷第5号,1922年5月1日)。往前追溯,早在1906年,当时胡适在上海学习,他署名“希彊”在《竟业旬报》(第3、4、5期,分别是10月1日、11日、21日)上发表了《敬告中国的女子》。
在这些文章中,胡适对于传统的女性贞操伦理,对于当时仍然为这些伦理进行辩护的人士提出了批评。在胡适看来,传统的贞操伦理首先违背了女性的自然性情,它是对女性人性的摧残。如,对于传统的缠足之习俗,胡适说它首先是摧残了女性的身体和健康,还影响了女性做事的能力,造成了她们的依赖性,它还有害于将来的子孙。让胡适愤怒的是传统的贞操伦理不分青红皂白,片面地要求女性从一而终,强人所难地要求女性守寡和做烈女、烈妇。①让胡适绝对不能接受的还有,为什么贞操的道德约束只是针对女性的,而对男性没有在道德上作出特别的约束。说起来,胡适没有简单地否定女性贞操观念,他强调的是女性贞操观念必须建立在女性自由意志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女性对爱情的追求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但传统的女性贞操观念不是这样,它违背了女性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人生幸福的机会,它压制、压抑了女性对爱情的追求,它形成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它是“不合人情公理的伦理”,是“不近情理的守节”。②胡适:《贞操问题》,载《胡适文存》(第一集),第485页。
胡适说的“人情公理”或“情理”,除了指男女平等、女性自由和精神发展外,它还指夫妇之间的爱情,指两性之间的自然情感和双方彼此精神上和志趣上的相互愉悦。在胡适看来,传统贞操伦常对女性的致命性伤害是,它不关心女性与异性之间是否有爱情就要求她同男性从一而终的结合。在胡适看来,两性之间的爱情是结成夫妻、建立夫妻关系的根本前提。但传统贞操伦理的辩护者蓝志先不接受胡适的这一前提。他质疑胡适说,爱情固然需要,但爱情是容易变化的,夫妇之间还需要道德上的约束。他担心夫妇之间如果只注重爱情,就容易变成肉欲和情欲之爱,也容易失去对人格的尊重。胡适承认夫妇之间要有道德的约束,也不否定“尊重人格”,但他指出,夫妇之间的爱情与道德约束及尊重人格并不是两回事,不是要在爱情之外再加上一个道德约束。所谓道德上的约束,只是“真挚专一的异性恋爱”,人格尊重也只是说“真一的异性恋爱加上一种自觉心”。③同上书,第490页。胡适仍然坚持两性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才是正当的夫妻关系。胡适说:
若在“爱情之外”别寻夫妇间的“道德”,别寻“人格的义务”,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所说的“贞操”即是异性恋爱的真挚专一。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既不是正当的夫妇,更有什么贞操可说?④同上。胡适认为传统通过媒妁之约而确定的婚姻关系,女性对于她的丈夫不会有什么恩爱(其实男性同样),她对他自然也没有什么贞操可言。有趣的是,胡适曾写有《病中得冬秀书》:“我不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我却常念他,这是为什么?岂不因我们,分定常相亲?由分生情谊,所以非路人。海外土生子,生不识故里,终有故乡情,其理亦如此。”据此,两性的亲爱和情谊也有通过“分定”而产生的可能。胡适说的亲爱和情谊如果就是指爱情的话,它因分而结合,这种结合是不是正当。胡适的朋友据此就说他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胡适说,面对他的朋友的质疑,他一时无语。这不仅因为这里的诗句同胡适坚持以自然的爱情来确定贞操不协调,而且它也同胡适的婚姻形成了反差。这确实让胡乱感到难堪。胡适说:
我听了这番驳论,几乎开口不得。想了一想,我才回答道:我那首诗所说名分上发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若没有那种名分上的情意,中国的旧式婚姻决不能存在。……我承认名分可以发生一种情谊,我并且希望一切名分都能发生相当的情谊。但这种理想的情谊,依我看来实在不够发生终身不嫁的贞操,更不够发生杀身殉夫的节烈。①胡适:《贞操问题》,载《胡适文存》(第一集),第486页。
不管如何,胡适坚持认为,男女发自彼此双方的内心的爱情是男女结合和婚姻的正当性基础,也是男女双方的伦理基础。一般将这看成是胡适女性解放观念的一部分,也将这看成是胡适的新文化运动启蒙思想的一部分。
胡适对传统贞操伦理的批评和控诉,广义上属于他对传统伦理禁欲主义的批评。按照胡适的判断,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禁欲主义,部分来自中古的宗教——佛教。胡适以控诉的口吻批判了传统观念特别是佛教对人性的摧残:
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从自欺自慰以至于自残自杀,人生观变成了人死观,都是从一条路上来的:这条路就是轻蔑人类的基本的欲望。朝这条路上走,逆天而拂性,必至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②《胡适文存》(第三集),第2-3页。
这种禁欲伦常被宋明理学所承继。这是胡适批评程朱理学的主要地方,也是他肯定戴震哲学的主要地方。如1928年,胡适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中评价戴震批评理学的意义说:
他认清了理学的病根在于不肯抛弃那反人情性的中古宗教态度,在于尊理而咎形气,存理而去欲。
理学最不近人情之处,在于因袭中古宗教排斥情欲的态度。戴学的大贡献正在于充分指出这一个紧要关键。
戴学的重要正在于明白攻击这种不近人情的中古宗教遗风。例如朱子曾说: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这种人生观把一切人欲都看作反乎天理,故主张去欲、无欲,不顾人的痛苦,做出种种违反人情的行为。①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第1158、1162、1164页。对于戴震批评理学禁欲论,胡适在此前的《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1923年)的短篇文章和《戴东原的哲学》(1925年)的长篇论文中都已作出了肯定。他得出结论说,无视和禁止人的欲望的伦理和道德(“理”)既不正当,也不可取。胡适对戴震的研究和评论,奠定了现代戴震学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也使戴震成为中国近代人性解放的先驱。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这篇论文中,将和他同时代的年长的吴稚晖也列入到了反理学的思想家中并对其进行了无以复加的称赞,认为吴稚晖在《一个新宇宙观》中立足于科学不仅提出了一个新的积极的、主动的人生观,以实际行动回应了“玄学派”,而且建立了以人性、人的自然性为基础的伦理观,在现代扮演了戴震反理学禁欲主义的角色。
结语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知,在胡适的哲学和思想中,相比于“科学”、“实证”、“经验”等概念来,“自然”则是一个前提性的非同寻常的概念。正是以此为基础,胡适建立起了他的“自然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是胡适站在东西文明和哲学的语境中展开的,它的主要内涵和适用范围,一是胡适完全从宇宙和万物自身的内在“自然”上来解释它们,彻底排除任何超自然的存在和原因;二是胡适将“自然”纳入到科学和技术的范式之下使之完全对象化、客体化,将科学看成是解释自然和把握自然的最有效方式,把技术看成是改造和利用自然的最有效方式;三是胡适从自然性出发去建立伦理和道德价值,以克服传统对人性的压抑和禁欲主义。
(责任编辑:肖志珂)
B94
A
2095-0047(2015)02-0055-33
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近现代中国思想中自然与人的观念演变及其当代价值”(项目编号:11JJD77001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