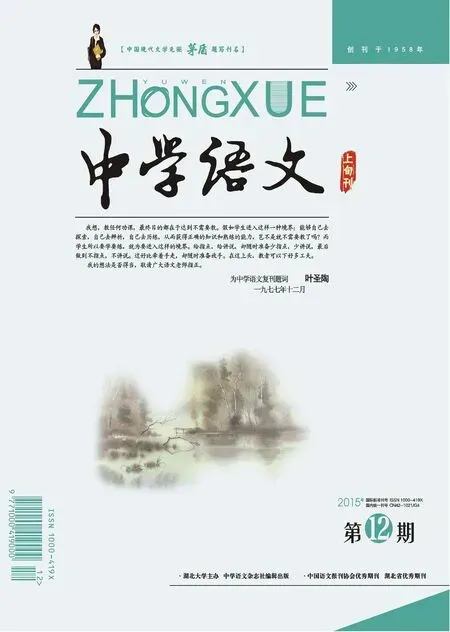王旭明先生推广的“真语文”献疑
杨先武
王旭明先生推广的“真语文”献疑
杨先武
在基础教育领域,语文界堪称“是非”之地,一直未曾停止过论争。继上世纪末那场由圈外人士发起的大讨论之后,近几年,语文界内部又掀起了一股为新课改“纠偏”的浪潮。而在“纠偏”的同时,有人还打出了名称响亮的旗号,其影响最大的当属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先生领衔的“真语文”。王先生在《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羊城晚报》《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发表言论,对课程改革以来出现的“假语文”进行猛烈地抨击,并以其所管辖的语文报刊为阵地,推广他所倡导的“真语文”。
王旭明先生以其特殊身份介入语文教育,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这番炮轰确实击中了要害,而且他所推广的“真语文”乃名副其实,那对于中国语文教育和莘莘学子来说,可谓幸莫大焉。但由于王先生并未完全了解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真实状况(主要靠听公开课、示范课等进行观察),他对语文教育的研究也欠深入,因而所提出的主张也值得商榷。
一、“真语文”抨击的现象的真实性
必须承认,王先生在抨击“假语文”时提到的种种现象均属事实。这些课例充斥着刻意打造的形式,课堂上所突出的“人文”并非新课标所要张扬的人文,而是“冒牌”的人文(有人称之为“泛语文”“非语文”)。对于这种歪曲新课标的做法当然应该纠正,但这些现象只是在少数公开课、示范课中存在,并非是常规语文教学的真实反映。谁都知道,公开课、示范课大都带有表演色彩,有的甚至是在做秀,执教者为了产生“与众不同”的效果,往往采用有别于日常教学的方法和手段,其目的在于吸引听课者的眼球。因此,仅仅根据公开课、示范课之所见而得出的结论是不全面的。近年来,有些语文界人士也是以此为依据下结论,把“泛语文”“非语文”当成了普遍现象。
王先生如果深入实际,以普通人的身份到日常的语文课堂做一番调查,就会看到与之大相径庭的另一番景象:课堂上充斥着为应试服务的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教师为应试而教,学生为应试而学,并且这种状况正随着中、高考竞争的加剧而呈愈演愈烈之势。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是引导学生“披文入情”,通过咀嚼语言文字来理解文本的内涵,并进行具有实际意义的语文能力训练,而是按照考试设题的方式肢解课文,以教给学生答题的方法和技巧。尤其是毕业年级,基本上不再与语文教材打交道,答题训练成了课堂教学的主旋律。这样的语文纯属应试语文,当然不是“真语文”,而是“假语文”。正是这种“假语文”即应试语文干扰了新课改,使语文教学偏离了正确的方向。王先生要打“假”,就必须首先向应试语文发起冲击,而不应该把某些公开课中出现的表面现象看成主流大做文章。当然,对于这些公开课、示范课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如过分强调思想内容甚至漫无边际地扩展、忽视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品味、滥用多媒体等)必须进行反思,但其责任不全在执教者,更应承担责任的是起主导作用的组织者和评判者。显然,王先生向“假语文”发射的炮弹并未击正目标。
二、“真语文”概念不明确
王先生反复强调“真语文”,但并未明确地给“真语文”下定义,我们只是在《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毒舌”王旭明:向假语文宣战》(《中国青年报》,2014年4月19日第3版)中看到一处似属下定义的表述:“真语文就是语文。祖国语言文字的本来含义就是真语文的含义。”从逻辑上讲,这是不符合下定义的规则的,其内涵和外延都不明确。而从“祖国语言文字的本来含义就是真语文的含义”这句话不难看出,王先生所说的“真语文”指的就是语言文字。很显然,他把“真语文”“语文”“语言文字”这三个不同的概念划上了等号,这便造成了逻辑上的混乱。“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名称,和“语言文字”(也可合称为“语文”)是内涵和外延都不相同的概念,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语文课虽然离不开语言文字,但绝不是纯粹的语言文字课,语文教学不等于语言文字教学。语文教学除了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外,还担负着传承优秀文化、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重任。王先生要求语文 “回归到语言文字的本质特征上来”(《这个时代需要真语文》,《光明日报》,2014年5月13日第14版),源于他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语言文字的本质特征等同于语文课程的本质特征。王先生提出的“回归”,实际上是要把语文教学重新拉回课改前那条独尊“工具性”的老路上。
“真语文”这一概念的模糊不清还可以从另一“真语文”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下的结论中看出。该先生说:“真语文,也可以说我个人倡导的‘本色语文’的核心主张是:把语文课上成语文课,用语文的方法教语文。”(《我心中的真语文》)显然,先生在此把“真语文”和他“个人倡导的‘本色语文’”划上了等号。按照先生的说法,“本色语文”就是“真语文”。那么请问:其他的语文派别如生态语文、生命语文、生活语文、绿色语文等等算不算“真语文”?如果不算,那就意味着上述语文都是“假语文”;如果也算,那么先生的说法就站不住脚,而且所谓的“真”未免太宽泛。由此可见,“真语文”是一个连倡导者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
三、无视“文章的思想内涵”的片面性
王旭明先生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国外没有专设思想品德课,所以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传播。而我们国内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专门的思想品德课,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在语文课上挖掘文章的思想内涵。”(《王旭明在“真语文”活动现场推广“真语文”》,《羊城晚报》,2014年11月3日第3版)显而易见,王先生把“文章的思想内涵”和“思想品德”也混为一谈了。“文章的思想内涵”实际上就是渗透在文本中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和思想品德虽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不能等同。人文教育并不局限于思想品德教育,人文精神不单包含思想品德,还涉及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表现为对生命的珍惜,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人的尊严、权利、自由和平等的维护等。语文教材之所以选入大量的文学作品,正是因为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中充溢着人的生命关怀、情感体验、价值取向、审美意趣等。那些经典之作,不仅文字优美,而且以其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以及荣辱得失、美丑善恶的深刻思考,教育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语文教学必须让学生在理解语言文字、学习如何运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去吸吮蕴含在其中的精神营养,这是思想品德课根本无法替代的,也是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因此,“语文课上挖掘文章的思想内涵”,即让学生受到蕴含其中的人文精神的熏陶不是“完全没有必要”,而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种“挖掘”不是无限度的(在必须扎扎实实打好语文基础的小学阶段更应适度),不能脱离语言文字去架空分析。
总之,王旭明先生要推广的“真语文”是只见语言文字、不见思想内涵的语文。虽然王先生也承认语文“关乎人的精神成长”,语文课“一定要培养学生自由、个性的心理品质,一定要培养学生独立创造的人格特征”(《这个时代需要真语文》),但如果摒弃了“文章的思想内涵”,学生的“精神成长”焉能实现?其“自由、个性的心理品质”和“独立创造的人格特征”又何从产生?按照某些“真语文”活动参与者的主张,语文教学要关注的是文章“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课堂教学只应“聚焦于言语表达的形式”。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学生不把“言语表达的内容”即“说什么”弄清楚,不能真正读懂文章(尤其是难度较大的课文),又如何谈得上提高他们的语文水平?很难想象,语文如果剥离了体现在“说什么”中的思想和情感,那会变得多么干瘪;课堂教学如果只盯住“言语表达的形式”,而不能认真领悟其丰富的内涵,更不能为了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而适当地向课外延伸,那将会使语文的天地变得多么狭小,会使学生的视野变得多么逼仄。这样的语文绝不是什么“真语文”,实乃另一种形式的“假语文”。
四、课改的大方向不能改变
新修订的语文课程标准将语文定性为“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同时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尽管两性统一的说法至今仍存在着争议,但它对于纠正课改前片面强调语文的“工具性”而漠视人文精神的倾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语文作为基础教育阶段一门最重要的人文学科,理所当然的要彰显人文性。工具性和人文性绝不是两张皮,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真正的语文是将“说什么”和“怎么说”即言语表达的内容和形式融合在一起的语文。语文教学当然要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为目标,但这绝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根本的目标”。教育是“塑造人的灵魂”的教育,其根本的目标是“立人”,它要培养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而不能局限于认知和技能。正如于漪老师所说:“一个称职的语文教师在组织教学时总是‘缘文释道’‘因道解文’,以文中内在的高尚思想、道德、情操拨动学生的心弦,可以既让学生感受到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又受到文中情与理的潜移默化般的影响。”(《为什么教语文,怎样教语文?》)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相比,语文的人文含量即精神资源最为丰富,理应在“塑造人的灵魂”上担负起比其他学科更大的责任。因此,语文教学既要重视语言
文字运用能力的培养,又要重视人文精神的熏陶。只有二者紧密结合,才称得上“真语文”。这既是新课标对语文教学的要求,也是我们应该尊重的常识。
近年来,语文教学出现了一些混乱状态,这固然与新课标本身的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因受应试教育干扰而对新课标实施不力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因循守旧的思想必然抬头,甚至有人公开主张走回头路即“回归语文的工具性”。这将严重阻碍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笔者在《语文教学不能再走回头路——与钱梦龙、李华平先生商榷》一文(载《中学语文》2015年第9期)中说过,“语文课程标准还存在许多缺陷,还须不断完善,但它所确立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已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正道。”笔者以为,无论新课改还存在哪些不足,但其大方向不能改变。面对当前语文教学所出现的混乱状态,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开历史的倒车,绝不能让语文教学“回归”那条工具化、技术化的老路。
湖北荆州市郢都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