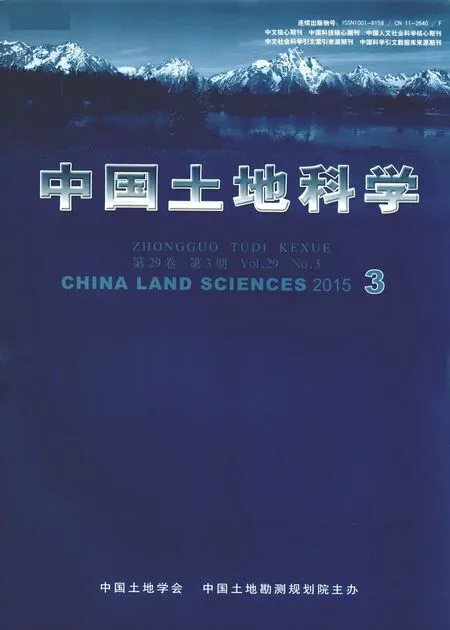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反思
苏方元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2.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反思
苏方元1,2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2.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研究目的:分析中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纠纷仲裁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修法思路。研究方法:逻辑分析和规范分析。研究结果:中国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有着浓厚的行政化、诉讼化的色彩,单方启动、强制管辖、一裁非终局等特点也有悖仲裁法的基本原则。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案件分流功能未能实现。研究结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首先应当明确该制度的法律属性,在此基础上实现去行政化和去诉讼化的改造,实现与民事诉讼的合理对接。
土地法学;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诉讼
2010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以下简称《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对仲裁机构的设置、仲裁程序、仲裁裁决的效力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基本确立了中国的农地纠纷仲裁制度。为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与诉讼的衔接,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9日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农地纠纷适用法律解释》)。该解释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收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就原纠纷提起诉讼。”基于这一规定,本应为独立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以下简称“农地纠纷仲裁程序”)被司法解释以显性的形式明确地推入了“诉讼预演”的境地,丧失了其应有的案件分流功能。那么,农地纠纷仲裁制度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又该如何修法?笔者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以期对农地纠纷仲裁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1 中国现行农地纠纷仲裁制度的基本特点
1.1 仲裁程序启动的单方性
《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和解、调解不成或者不愿和解、调解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同时在第20条规定:“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申请人与纠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二)有明确的被申请人;(三)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据此,农地纠纷仲裁的受理和仲裁程序的启动,并不要求纠纷双方之间事先存在仲裁协议或是事后达成了仲裁协议。任一方当事人均可单方申请而启动农地纠纷仲裁程序,这一点与普通的商事仲裁的协议仲裁制度有着重大差别。可见,启动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不以书面仲裁协议为前提,没有仲裁协议也可申请仲裁这种方式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所特有的[1]。
1.2 仲裁程序启用的可选择性
《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所构建的是“或裁或审,一裁两审”的纠纷解决制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并非诉讼的前置程序,这一点与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仲裁前置显著不同。根据《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条的规定,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发生后,当事人有着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既可以选择和解、调解,也可以选择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还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就是说,对于是启动仲裁程序还是诉讼程序抑或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当事人有着充分的程序选择权。
1.3 仲裁管辖的强制性
虽然当事人对仲裁程序的启用有着充分的程序选择权,但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仲裁管辖却有着浓烈的法律强制的特征。《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书。”根据此规定,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发生之后,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就享有了地域管辖权。这实际上是在仿制诉讼制度,实行强制性的地域管辖,否定了当事人协议选定仲裁委员会的权利。同时,农地纠纷仲裁制度在事务的管辖上也具有强制性。《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5条规定:“被申请人未答辩的,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第35条第2款规定:“被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裁决。”可见,农地纠纷仲裁程序一旦经由一方当事人单方申请启动之后,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就具有了事务的强制管辖权,纵使无仲裁协议、被申请人的答辩,亦无被申请人的到庭,仲裁委员会仍可依照仲裁程序按部就班地行进,并至最终可以缺席裁决。
1.4 仲裁裁决生效的附条件性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实行的是“或裁或审,一裁两审”的制度,与普通的商事仲裁“或裁或审,一裁终局”制度不同。在普通的商事仲裁中,一旦仲裁裁决作出,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法院不予受理。但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裁决书生效的条件,《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却有着不同的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这意味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裁决书的生效是附有一定的条件的,即只有当事人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未向人民法院起诉,裁决书才会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当事人不服裁决并在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将启动诉讼程序,而仲裁裁决则不发生法律效力。
2 农地纠纷仲裁行政化的弊端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情况复杂,且大多涉及人员众多,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若纠纷未能妥善解决,则极易致使矛盾激化,酿成群体事件或上访事件。因此,充分发挥仲裁程序的优势,妥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具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中国《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将农地纠纷仲裁程序定位为行政性仲裁的做法,值得进一步反思。
2.1 行政性的仲裁机构损害了仲裁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2条、第13条、第51条、第52条①《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2 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根据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实际需要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可以在县和不设区的市设立,也可以在设区的市或者其市辖区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设立。”第13 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由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代表、有关人民团体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兼任组成,其中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不得少于组成人员的二分之一。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和委员若干人。主任、副主任由全体组成人员选举产生。”第51 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示范章程,由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共同制定。”第 52 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仲裁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第4条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第4 条规定:“仲裁委员会依法设立,其日常工作由当地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承担。”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设立;仲裁委员会成员应包括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代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规则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示范章程,由国务院农业、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仲裁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由此可见,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参与了农地承包仲裁机构的设置、组成人员选任,以及仲裁规则、仲裁机构章程的制定,而且由当地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农业部门、林业部门)承担仲裁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这种依托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仲裁机构,在某种层面上来说具有了一定的行政职能。仲裁机构的这种“行政”特性对农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解决可能具有一定的便利性,但是,由于无法对仲裁机构利用行政职权“恩威并施”地解决农地承包经营纠纷排除“合理怀疑”,使得仲裁活动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受到极大的质疑。
2.2 行政性的仲裁程序违背了仲裁的本质属性
中国现行农地纠纷仲裁程序本身也有着深深的行政印记。一方面,依据《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农地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是否有书面仲裁协议并非启动仲裁程序的必要条件,只要一方当事人单方面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即可启动农地纠纷仲裁程序。另一方面,双方当事人对仲裁机构不享有选择权,只能向纠纷涉及土地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并接受适用该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和仲裁程序,双方当事人不得协议选择仲裁适用的法律、仲裁规则和仲裁程序。“仲裁的本质在于它的民间性,是当事人出于自愿而将纠纷提交给他们信赖的第三人居中裁决。”[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根本就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而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应当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但是民商事仲裁“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这里不仅没有得到根本性地维系,反而遭受了更为严重地侵害,即是招致了强制性的仲裁管辖。缺失了本质属性的所谓“仲裁”,只能是一种空洞的、形式上的仲裁,并不能起到“停讼止争”的功效。
3 农地纠纷仲裁程序功能的弱化
3.1 农地纠纷仲裁程序案件分流功能失灵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51条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法》第51条规定:“因土地承包经营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 镇) 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和《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3、4条④《农土纠纷调解仲裁法》第3条规定:“发生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第4条规定:“当事人和解、调解不成或者不愿和解、调解的,可以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可以通过和解、人民调解、农地纠纷仲裁、民事诉讼4种途径加以解决。虽然从目前的现实状况来看,解决农地纠纷的重要途径依然是和解和人民调解,但是,伴随农村法律意识的强化及乡土权威的丧失,传统意义之协商和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3]。和解协议和人民调解协议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终极性法律效力,协议的切实履行还需仰仗于道德层面的自我约束。然而,传统的非诉纠纷解决方式赖以存在的基础却因社会变革和乡土权威的退化而逐渐削弱,最终结果必然是更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转而求助于终局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即民事诉讼。随着农地纠纷案件流入诉讼程序的数量增加,人民法院超负荷工作的程度也会随之增大,接踵而来的就是诉讼延迟和案件积压问题。在现代法治社会,民事诉讼虽然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最终和最权威的手段,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纠纷都必须去法院寻求解决[4]。而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恰恰是一种介于人民调解与民事诉讼之间的纠纷解决机制,它体现着人民调解的灵活性,其仲裁裁决又能依程序取得司法意义上之强制性效力[5]。因此,农地纠纷仲裁程序立法的功能定位应当是农地纠纷诉讼案件的程序分流,通过农地纠纷仲裁的途径解决纷争,以减少流入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数量。现行的农地纠纷仲裁程序的诉讼案件分流功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其功用。
根据《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1条①《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1条规定:“仲裁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应当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仲裁程序应当是包含了两道程序设计,即仲裁调解程序和仲裁裁决程序,而且仲裁调解程序是仲裁裁决程序的前置程序,只有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仲裁庭才能作出裁决。仲裁调解程序和仲裁裁决程序在实现中所起的案件分流功能也大相径庭。《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1条第3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第49条规定:“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由于只要双方当事人签收了仲裁调解书,调解书即获得了终局性的程序效果,因此仲裁调解程序事实上实行的是“一调终局”的制度,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案件分流功能,但分流功能作用十分有限。与之相反的是,仲裁裁决并不具有终局性的法律效果,因为《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而与之对接的《农地纠纷适用法律解释》也在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收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仲裁裁决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就原纠纷提起诉讼。”显然,当事人不服调解却能够接受仲裁裁决的情形是难以想象的,毕竟仲裁裁决的作出是以仲裁调解为基础的;如果当事人在调解不成的情状下能够接受仲裁裁决,那么就有理由相信前置的仲裁调解显失公平。于是乎,不服仲裁裁决的农村土地承包地纠纷重新回溯至原点,再以原纠纷形式流向民事诉讼。农地纠纷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则意味着农地纠纷仲裁程序案件分流功能并未发挥作用。
3.2 农地纠纷仲裁程序过程沦落为诉讼预演
中国现行的农地纠纷仲裁制度的构建并没有秉承仲裁的本质属性,而是仿制了诉讼制度,“在案件的受理、仲裁审理的程序及仲裁证据制度等方面无一不是民事审判程序的翻版”[6]。仲裁裁决本身并不具有终局性的法律权威,其生效与否完全假手于当事人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将纠纷诉诸法院。一旦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并按规定以原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那么,原已审理完结的仲裁程序过程则实质性地沦落为当事人之间的诉讼预演。至于农地纠纷诉讼是否成为农地纠纷仲裁的“复盘”,则取决于两者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一致性。
如果农地纠纷仲裁程序过程只是一个单纯的诉讼预演,或许更多的诘问只是停留在其并未起到案件分流功能的层面上,可事实上在仲裁程序过程中往往也会“制造”一些“问题”遗留给法院来收拾“残局”。例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先行裁定”。根据《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2条①《农地纠纷仲裁法》第42条规定:“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纠纷,经当事人申请,仲裁庭可以先行裁定维持现状、恢复农业生产以及停止取土、占地等行为。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先行裁定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农地纠纷适用法律解释》第9条②《农地纠纷适用法律解释》第9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先行裁定后,一方当事人依法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和执行。申请执行先行裁定的,应当提供以下材料:(一)申请执行书;(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先行裁定书;(三)申请执行人的身份证明;(四)申请执行人提供的担保情况;(五)其他应当提供的文件或证件。”之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应当事人申请作出的先行裁定具有法律效力,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先行裁定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和执行。在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并就原纠纷诉诸法院之后,就存在“先行裁定”具有法律效力而最终的仲裁裁决却无法律效力的尴尬局面(仲裁裁决必然包含有先行裁定之内容)。若其后的农地纠纷诉讼仅仅是农地纠纷仲裁的简单“复盘”的话,这或许仍是“不伤大雅”之事;但是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先行裁定”实为错误,那势必要在刚执行完毕之际再执行回转。纵使有着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担保,但对法院的司法公正形象的损伤却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先行裁定书具有法律效力,法院受理和执行先行裁定书时无需就先行裁定之内容做实质性审查。当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之后,法院不以农地纠纷仲裁为基础而必须对所有事实进行重新审理,已执行完毕的农村土地承包委员会的“先行裁定”之内容并未能够有幸成为例外。当然,如果仲裁员与审判员有着相同的法律素养,那么发生“先行裁定”偏差注定只是一个猜想。
4 农地纠纷仲裁制度的修正思想
4.1 民事仲裁制度法律属性的本位回归
《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的立法框架是以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框架和制度设计为“母法”的[7],是依据《仲裁法》第77条③《仲裁法》第77条规定:“劳动争议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之规定所制定的下位法,但在具体的农地纠纷仲裁制度的设计上却偏离了民事仲裁的本位,存在如前文所述的行政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发包方与承包方根据平等、自愿原则订立的民事合同,围绕农村土地承包权发生的权属争议、侵害农村土地承包权以及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争议都是民事权益纠纷,对这类纠纷的仲裁在性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仲裁,而不是行政仲裁[8]。虽然基于法律制度现实意义的追求和农地纠纷仲裁制度本身的特殊性,农地纠纷仲裁制度可以具有与其他民事仲裁制度不同的特征,但是不应当背离民事仲裁的基本原则。因此,对农地纠纷仲裁制度的修正,首当其冲的应当是对该项制度的法律属性的厘清,以明确其民间性、自主性的仲裁本质。
4.2 仲裁程序的“去行政化”和“去诉讼化”改造
明确了农地纠纷仲裁制度之民间性、自主本质,仲裁程序的“去行政化”改造则是顺理成章。农地纠纷仲裁程序的“去行政化”改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仲裁机构的设置“去行政化”,明确仲裁机构的独立性。民间化本身不是目的,确保机构的独立和公正才是目的[9]。因此,农地纠纷仲裁机构应当具有独立性,不能附设于行政机关内部或是与行政机关有着某种业务管理上的关联,避免行政干预,以保障仲裁机构公正裁决。但是,《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以“日常工作由当地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承担”之规定,将农地纠纷仲裁机构与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紧密地捆绑在了一起,丧失了其应有的独立性。故而在修法时可以考虑将《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2条第2款修改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无隶属关系。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其日常工作由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承担。”使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不再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品。同时,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选任也应当“去行政化”,以确保仲裁的公正性。《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包含有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之代表,这一规定在实践中的通常做法就是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担任仲裁委员会主任一职[10],这种“自己做自己的法官”的农地纠纷仲裁的公正性广泛受到质疑。因此,修法时可以考虑删除“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代表”作为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之内容。二是仲裁程序的“去行政化”,确立意思自治原则。农地纠纷仲裁并不是行政处理,程序中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单方启动、强制管辖”的程序设计应予剔除,代之以“仲裁协议”、“意思自治”等民事仲裁的基本程序要求。因此,修法时可将《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0条修改为:“申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有仲裁协议;(二)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三)属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第21条第1款修改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由当事人协议选定。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仲裁申请书可以邮寄或者委托他人代交。仲裁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基本情况,仲裁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和证据来源。”此外,当事人平等地选择仲裁员是仲裁程序形式公正的重要表现[11],但《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却规定在当事人不能选定仲裁员时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这一行政意味浓烈的“指定”不仅有损农地纠纷仲裁程序的形式公正,也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之原则。基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即便是当事人不能选定仲裁员,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也不得“径直”指定仲裁员,而必须是在获得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之后才能予以指定,以维护仲裁程序的公正性。因此,修法时应将《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7条第1款修改为:“仲裁庭由三名仲裁员组成,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共同委托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其他二名仲裁员由当事人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将第27条第2款修改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以由一名仲裁员仲裁。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另外,盲目学习法院诉讼模式,导致仲裁诉讼化并试图把土地仲裁建设成另一个法院的做法,不但有悖仲裁的本质,而且背离了建立土地仲裁纠纷机制的初衷[6]。既然农地纠纷仲裁程序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并列而成为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应当有着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不同的特点,即程序简便、高效,从而避免仲裁成为诉讼的“预演”、诉讼成为仲裁的“复盘”。农地纠纷仲裁程序的“去诉讼化”改造,就是要让农地纠纷仲裁程序走出法定程序化的误区,重新回到《仲裁法》所制定的程序框架之中,充分发挥农地纠纷仲裁程序的灵活性、及时性。鉴于农地纠纷仲裁程序完全仿制于诉讼程序,其“去诉讼化”改造必然是要大幅度地删减、修改《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有关程序的诸多条文,并按照民商事仲裁的基本原则来重新设计程序。例如,《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第30条第3款规定:“开庭应当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以及当事人约定不公开的除外。”这明显是仿制了诉讼“公开审理为原则、不公开审理为例外”的模式。这使得开庭仲裁至少受着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必须在开庭前先期公布案由、当事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二是必须有着适合公开开庭的场所,而这两个因素无疑对农地纠纷仲裁的便捷性和灵活性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牵制。因此,建议修改为:“仲裁不公开进行。当事人协议公开的,可以公开进行,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
4.3 “一裁终局”原则的确立
一裁终局原则是世界各国普遍确认的仲裁法基本原则,确认该原则有助于维护仲裁裁决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提高解决民商事纠纷的效率,有助于使仲裁较于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长处得到更充分的发挥[12]。前述的农地纠纷仲裁程序之修正,也为中国改变现行农地纠纷仲裁的“或裁或审,一裁两审”制度,实行“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的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法理依据。“一裁终局”原则的确立才能树立农地纠纷仲裁的法律权威,实现农地纠纷仲裁程序对纠纷案件的分流功能。
4.4 农地纠纷仲裁与诉讼的对接:司法监督
《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为农地纠纷仲裁与纠纷诉讼留下了一个对接口,即在第48条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起诉的,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但这个对接应该说是一个并不成功的对接。原因在于:一是否定了仲裁“一裁终局”的原则。依照“一裁终局”原则,仲裁庭一旦作出了裁决,该仲裁裁决当即就具有了法律效力,但在当下的《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下,仲裁裁决却有着一个“生效犹豫期”,只有在当事人期满且未诉诸法院时才能产生法律效力。二是虽然规定了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诉之内容却不明确。由于《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撤销仲裁裁决,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也只能是以“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应“就原纠纷提起诉讼”来与之对接。从形式上看,农地纠纷仲裁和诉讼实现了对接,但实质上却是农地纠纷仲裁遭到了否定,至少是遭受了漠视。即使是在诉讼中人民法院并不对仲裁决议进行任何评断,但农地纠纷仲裁的权威也因仲裁裁决的无法律效力而受损。
农地纠纷仲裁与诉讼的对接不应当是将农地纠纷仲裁搁置一旁而重新审理原纠纷,而应当是在确立“一裁终局”原则的基础上赋予人民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的权力,实行司法监督。当然,前提条件必须是如《仲裁法》第58条①《仲裁法》第58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决有前款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第63条②《仲裁法》第63条规定:“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一般,在《农地纠纷调解仲裁法》中明确可以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应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经审理后认为并不具有法律所规定的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情形之时,就应当驳回起诉或申请,维护农地纠纷仲裁裁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于法院依法撤销仲裁裁决的案件,当事人可以依法重新申请农地纠纷仲裁,或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
[1] 孙仲玲.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律制度的思考[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9(4):120 -124.
[2] 郝飞.关于我国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的探讨[A] . 仲裁研究(第15辑)[C]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6 - 64.
[3] 冯怀江.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实务手册[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0.
[4] 江伟.民事诉讼法专论[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9.
[5] 丁宝同.农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调解程序探析——以功能定位与法理定性为中心[J] .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15(2):74 - 82.
[6] 徐晓波.我国农村土地仲裁制度之反思与重构——兼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 [J] . 皖西学院学报,2010,26(1):69 - 72.
[7] 孙仲玲.涉农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探讨[J] .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7(4):108 - 111.
[8] 杨官程,阎君梅.试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制度的法律属性[J]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90 -91.
[9] 陈福勇.模糊化还是明确化——也谈仲裁机构的性质问题[A] .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第62辑)[C] .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86 - 97.
[10] 刘昕.浅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行政化 [J] . 中外企业家,2011,(11):58 - 61.
[11] 汪祖兴.当事人程序参与及其对仲裁程序公正性的影响[J] . 中国司法,2006,(5):22 - 25.
[12] 蔡虹,刘加良,邓晓静.仲裁法学[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5.
(本文责编:仲济香)
The Introspection of the Arbitration System on Rural Land Contract Disputes in China
SU Fang-yuan1,2
(1. Law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2. Law School,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some problems of the arbitration system on rural land contract disputes and to bring forward proposals for perfecting it in China. Methods employed include logical analysis and normative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arbitration system on rural land contract disputes has degenerates into the administrative arbitration system, and the arbitration procedure has been designed as the same as the litigation procedure. Furthermore, the arbitration system on rural land contract disputes runs without the arbitration agreement, the principle of party autonomy, and the final ruling system. Meanwhile, the function of the arbitration system on rural land contract disputes that is used to shunt the cases has failed.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nature of the arbitration system on rural land contract disputes should be confirmed at firstly, and then reforms this arbitration system to docking with the civil litigation.
the science of land law; land contract disputes; arbitration system; litigation
F301.1
A
1001-8158(2015)03-0032-07
10.13708/j.cnki.cn11-2640.2015.03.004
2014-03-24
2015-02-02
苏方元(1970-),男,广西桂林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诉讼法学、司法制度。E-mail: suman16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