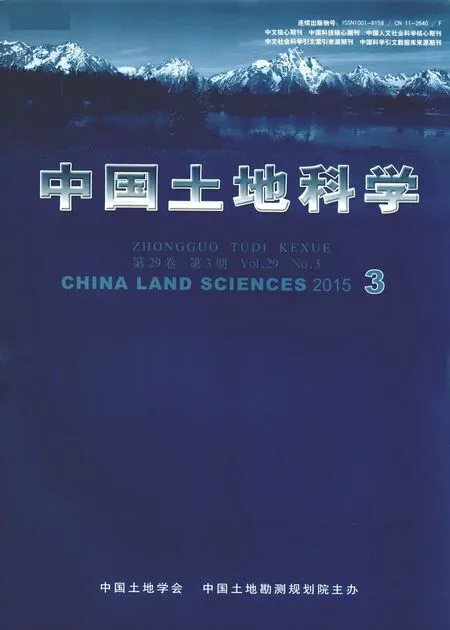论城乡一体化视域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走向
陶钟太朗
(1. 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2. 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纽约 10023)
论城乡一体化视域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走向
陶钟太朗1,2
(1. 四川大学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2. 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纽约 10023)
研究目的:在对城乡一体化实现之后的社会图景进行基本把握的前提下,确认集体土地所有权存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演进的应然形式。研究方法:演绎法,归谬法。研究结果:在城乡一体化目标视域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得以存在的身份基础将丧失,其制度功能亦将失效,故集体土地所有权必将消亡。另一方面,以私人所有权替代集体所有权亦不可取。研究结论:在构建完备的农村土地用益物权体系基础上,以国家所有权概括承继集体所有权方是正途。既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相符,同时亦保持了城乡法制统一,并真正能够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配置。
土地法学;土地经济;集体土地所有权;城乡一体化;走向
长期以来学者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走向问题的研究大多立足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从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上讲,这种讨论具有合理性,但却普遍缺乏全局性和整体性视野。笔者认为,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走向的研究,除立足于现实国情外,还应充分把握城乡一体化实现之后的基本社会形态。以未来必然产生的社会事实作前提,进行制度发展趋势的预判,指引制度改革,才能保障目标与过程的统一,才能得出科学性的结论。对城乡一体化目标的整体把握,是进行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长期以来的讨论能够大致描绘出城乡一体化实现之后的社会图景:首先,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将会消亡,人口流动将不受特定身份的限制;其次,生产要素配置将破除城乡壁垒,在全域范围内自由流通;再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会建立,全民均等性地享受国家福利。本文讨论将围绕着这一基本认识展开。
1 城乡一体化实现后集体土地所有权存续困境论
1.1 困境一:集体成员资格从封闭性到开放性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丧失存在的根基
权利由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三要素构成,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某一权利的权利主体不复存在,那该权利也就消亡了。根据现行法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是农民集体①《宪法》第10条、《民法通则》第74条、《土地管理法》第10条和《物权法》第60条。。《物权法》第59条进一步明确了农民集体的内涵,即“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对于“本集体成员”这个概念,通过明确本集体成员资格的判断实质上可以达到“本集体成员”这个概念的明确化[1],目前对集体成员的身份认定,原则上以户籍为标准。集体成员的身份是以农村户口为基础的,如果取得城市户口,则不可能享有成员资格[2]。在此基础之上,以地域作为不同集体成员资格划分的依据,即不同村民小组、不同的行政村或者乡镇,形成不同的集体成员资格②《物权法》 60条: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三)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现有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体系,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权利主体,首先是排斥具有城市户口的居民成为“本集体成员”,其次是排斥户籍不在本村民小组(本行政村、本乡镇)的农民成为“本集体成员”③第一种排斥是一种绝对排斥,即城市居民绝对不能成为“集体成员”;第二种排斥存在例外,由于搬迁(需要搬入地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婚嫁、收养等原因,甲集体成员可以成为乙集体成员,同时其丧失甲集体成员的身份。。
在城乡一体化目标视域下,现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农民身份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城乡统一的中国居民身份。为应对这种改变,有学者尝试设计一种新的权利主体,“宪法及法律指定的国有以外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当地全体居民共同所有”[3],即原属“农民集体”所有的集体土地,演进为属于“当地全体居民”共同所有,对成员身份的确定以“当地全体居民”为条件,能成为“当地居民”的当然以居住地为条件[4],即只要以该地作为居住地的人就应为“当地居民”。由于居民不受限制的迁居自由是城乡一体化目标的应有之意,任何人均可成为某特定地域的“当地居民”。集体成员资格由封闭变为开放,特定人享有的身份利益变为任何人均可享有的利益。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赖以存在的特殊身份——农民身份和特定地域性身份将不复存在。故城乡一体化实现后,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将丧失其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权利主体消灭,则集体土地所有权也无法存续。
1.2 困境二:充分城镇化后的极限可能
准确地讲,这种困境并非出现在城乡一体化实现之后,而是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乡一体化进程必将伴随着蓬勃的城镇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④城镇化率(城镇化水平)通常用市人口和镇驻地聚集区人口占全部人口(人口数据均用常住人口而非户籍人口)的百分比来表示,用于反映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和聚集程度。是53.7%,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城市蓝皮书》,按照市民化的标准,中国的完全城镇化率仅42.2%⑤现在中国的市民化标准主要以户籍为依据,即户口为城市户口即是城市居民,而现有很大部分居住在城市的居民并未拥有城市户口,因此会出现以户口为标准和居住地为标准的城镇化率的偏差。,即有超过10%的农村户口居民居住在城镇。中国未来的城镇化率目标,大致是75%—80%,意味着约33%—38%的农村居民将伴随城镇化的进程逐渐成为城市人口。而从现有的农村人口结构来看,主要以老年人居多。据考察,中国自改革开发以后,农村人口流动呈现这样一种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常居人口是“38”、“99”、“61”,即妇女、老人和儿童,至20世纪90年代初,妇女逐渐随着丈夫外出务工。到21世纪初,农村儿童逐渐随父母迁居城镇,农村的主要常居人口就是老年人了。当外出务工人员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老年人逐渐死亡,以该村民小组为户籍所在地的人将越来越少。
因此,随着城镇化的逐渐深入,这样一种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即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将呈现出不断萎缩的趋势,从数以百计的农民集体逐渐萎缩至以十位计的农民集体,甚至缩减到以个位计的农民集体,并且还有一种极限可能性:以某一特定的“农民集体”为考察对象,“农民集体”中的多数由于城镇化带动成为城市居民,同时由于死亡和婚嫁的原因,原有的集体成员逐渐缩减至“零”。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一种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趋势。当集体成员数量不断的缩减,所谓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就有演化成一种私人所有权的可能,即当集体成员仅为十数人或者数人甚至一人时,集体所有权所意蕴的“集体”利益将不复存在,更准确地讲是私人土地所有权而代表私人利益了。这种极限可能必然会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存续提出挑战。
2 集体土地所有权功能考察——兼评城乡一体化实现后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必要性
2.1 集体土地所有权功能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体土地所有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制度功能,其存在的必要性毋庸置疑。但是这样的制度功能在城乡一体化目标视域下是否有存在必要,则需进一步考察。通过归纳,集体土地所有权曾存在以下几种制度功能:
人员固定功能。建国之初,人们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流动是自由的。但是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驱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5],造成了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基本生活资料供应不足,而农村又流失大量劳动力,农业生产荒废的困境。于是,何以固民于农村,成为当时亟需解决的问题。户籍制度能够将农民限制于农村,而由于农民对特定集体的身份归属性,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更能将农民束缚于特点的空间点。
资源摄取功能。国家通过建构集体所有权而否定私人所有权,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国家对农村进行资源摄取的权力通道[6]。一方面,将资源摄取对象由个人转换为了集体,大幅度降低了谈判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农村集体的领导层受政府任命,其对征收的执行力度不容置疑。并且,在集体土地所有权最终确立阶段,集体成员退出权丧失,集体成员只能依附于集体方能生存,又极大降低了单个农户的对抗性。事实上,集体化经济绝不是农村社区内农户之间基于私人产权的合作关系,就其实质来说,它是国家控制农村经济权利的一种形式[7]。迄今,根据摄取的资源的不同,分别存在过对“农村产出”的摄取(1949—2006年)和对农村土地价值的摄取(1982年至今)①1982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1999年《土地管理法》、2001年《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土地管理的决定》、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政策逐步建立健全了政府垄断城市土地一级市场的机制。。
社会保障功能。随着中国城镇化步伐加快,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土地所蕴含的高额价值逐渐显现,土地价格飙升。在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订之前②1982年《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第18条,1986年《土地管理法》第41条。,城镇非农居民有权利申请农村宅基地建房[8],也没有禁止城市居民到农村购房的法律规定。由于资本趋利性的存在,使得城市的资金逐渐向农村渗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和信息差别有让农民利益受损的可能性。采取何种方式能够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存在以及其身份属性,能够有效地将农民与非农民、本集体成员和非本集体成员区分,以此为依托,禁止城市居民和非本集体居民到本集体建房而居或买房而居③1998年《土地管理法》第43条;1999年《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通知》第2条第2款;2004年《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有效地保障了农民的基本生存利益不受侵害④以此方式保障农民基本生存利益的同时,却使宅基地使用权的财富功能大打折扣,是否合理,在中国进行了长期的论战,现在仍无定论。但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为依托维护农民的基本生存利益,这一制度功能却是现实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社会保障功能逐渐被挖掘并确立起来。进入21世纪,经济危机频发,农民工在城市失业返乡的现象频繁发生,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有效的隔离了外来资本的入侵,使得返乡农民仍有房可居,有地可种。其社会保障功能凸显,有学者更是将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本制度依托的农村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9]。
2.2未来和城乡一体化实现后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功能样态——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存续的必要性考察
资源摄取功能、社会保障功能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但是否就能以此为理由将集体土地所有权改良作为制度改革的方向。对此,作者持否定意见。析言之,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功能存在现实必要性并不表示未来仍有必要,需要明确的是未来社会形态(城乡一体化目标视域下)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功能的必要性问题。人员固定功能早已因其所依存的社会背景消失而消亡;需要考量的即是资源摄取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首先,就资源摄取功能而论,对农业产出的资源摄取早在2006年农业税取消时即已消灭。对集体土地价值剥夺的资源摄取功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还会继续存续,但却必然是一个弱化的过程。在城乡一体化实现后,再以剥夺城市周边土地价值的收益去进行不发达地区经济的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不成其为正当理由,曾经的一个长时期的剥夺过程已经完成了上述目标,因此,集体土地的资源摄取功能亦无存在价值;其次,就社会保障功能而言,城乡一体化的应有之意是社会保障体系在全民范围内确立起来,也许那时会存在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但却不应有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异。因此,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于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功能已经属于不必要。
3 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化改革合理性之证成
可得出如下结论,在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得以依存的身份土壤(可能性),亦有存在的制度功能(必要性)。但是,在城乡一体化实现后,其存在的前提——农民身份将会消亡,其存在的必要性——制度功能丧失作用。集体土地所有权还能否存在,答案已经浮出水面,即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城乡一体化目标视域下是不能存在的。有了这一结论,在实现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如何进行制度选择就有了方向性指引。事实上,学界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讨论由来已久,在土地所有权上采何种道路众说纷纭[10],但均可以纳入私有化、国有化和在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改良3种基本观点。笔者认为,就保留集体所有权而对其进行改良的观点而论[11-12],由于“农民集体”在城乡一体化实现后将整体消亡,集体土地所有权必然成为空中楼阁瞬间崩塌,其不合理性不言自明。而且,继续保留土地所有权的二元结构,人为地造成土地权利的身份差别,并不符合城乡资源一体流通的应有之意,有碍完整成熟的土地市场形成[13]。因此,对集体所有制进行改良,积极重塑集体所有权主体和权能以做“实”集体所有权的观点[14]断不可取。剩下的两种选择:对集体土地进行私有化处理[15-16]或者是国有化处理[17-18]。笔者认为,私有化处理不符合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样也会出现新的土地二元结构,即部分土地归国有(原城市土地),部分土地私有(原农村土地),这必然导致新的制度混论,此种改革思路亦不可取。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国有化改革,是惟一可依赖的改革路径,具体理由如下。
3.1 统一居民身份要求土地所有权一元化
城乡居民身份上的差别是国家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二元结构存在的前提,但这样一种二元结构的存在,在逻辑上却不能自洽。土地的国家所有从最终归属的角度属于全体国民所有,其中包括城市居民,亦包括农村居民,因此,国家土地所有权存在最终所有者身份的无差别性。但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从最终归属的角度属于本集体全体成员所有,即当然排斥城市居民成为权利主体,亦排斥其他集体成员成为权利主体,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最终所有者的身份专属性,这种身份专属性权利是不能永续性存在的。目前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城乡尚未一体而需要予农民以倾斜的权利保障,但城乡一体后,统一居民身份的民众在社会保障层面已经没有城乡差别,因此,上述理由即不成立。而且,统一居民身份,不同的土地权利,将造成新一轮的权利身份差异,城乡一体化将沦为空谈,故而,统一的居民身份必然要求一元的土地所有权。透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种一元的土地所有权只能是国家土地所有权,而不能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私人土地所有权。
3.2 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化改革的现实可能性
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国家所有之路,具有现实可能性。首先,符合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地位,一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尽管集体土地所有权可以被认定为是公有资产,但是,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国有化塑造,将进一步增强其公有资产属性,而更多地摒除掉其私有资产性质,符合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地位这一要求;另一方面,将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国有化改革,亦有利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若采用土地私有化改革思路或者土地集体所有化改良思路,则有可能出现土地——这一最重要的资源,大规模地集中于私有经济当中,这无疑会有碍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其次,在统一的城乡居民身份这一预设前提下,不能存在以特定身份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权,但是却可存在不以身份为要求的抽象的国家所有权。详言之,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化改革的结果,是形成一种抽象的国家所有权,与现在城市地区的土地国家所有权一样,它并不隶属于特定区域的全体城市居民所有,而是抽象地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所有,这符合城乡一体化后城乡居民身份的无差别性。
再次,城乡一体化的应有之意包括土地资源在全域范围内自由流通,抽象的国家所有权取代以身份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将有力地消除土地资源自由流转的身份障碍,促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和流通。现有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相关的土地使用权体系,其获得需要有集体身份,其流转亦受集体身份限制,以国家所有权取代集体所有权,则身份限制自然消解,相关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不受权利主体身份限制自由流转。
可以发现,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改革是城乡一体化目标所蕴含的应有之意,具有必然性和不可逆性。应关注城乡一体化过程视域下如何进行制度构建,以按部就班地实现土地全国范围内的国有化。
4 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化改革路径
改革的目标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元的土地国家所有权,现有的城市土地权利体系是农村土地权利体系演进方向的蓝本,即形成土地的国家所有再辅以相应的用益物权制度。因此,制度演进路径就是塑造完整的农村土地用益物权体系,并逐渐弱化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制度功能,为国家土地所有权概括取代集体土地所有权创造条件。
首先,应逐步建立农村用益物权的权利表达机制,根据现行法律,土地征收法律关系主体是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这样的主体安排完全漠视了征收法律关系中另一类利益主体,即农村土地用益物权人。这是造成当下因土地征收而屡屡引起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国家(政府)对土地价值的摄取应逐渐弱化,而土地增值收益应逐渐回归至农民手中。如何实现,这就需要建立农村用益物权权利表达机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征收过程中农村土地物权人的参与权,包括知情权、异议权等;一是在征收补偿费用安排的最终决定权,这都将有效降低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现象和代理人成本,缓解农户、集体经济组织、政府三方尖锐的矛盾,并弱化农村土地用益物权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依赖。
其次,破冰之旅是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改革。农村土地用益物权体系的去集体化是一个渐次过程,而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将是打破集体土地权利身份要求的突破口,现在时机已成熟。一方面,双向城镇化呼声日高,城镇居民有到农村居住创业的诉求[19]。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又有实现宅基地使用权财富功能的强烈愿望。并且,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的制度设计只需做一个技术化处理,即将宅基地使用权作空间权设置,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迎刃而解[8]。流转问题一旦解决,将极大地增加农民财富,建设需求同样增加,新型城镇化将蓬勃发展。
第三,核心问题是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建构。宅基地使用权空间权塑造这一技术改革路径可以实现居住利益保障和资源的物尽其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又如何进行制度构建既能实现其社会保障功能,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实现物尽其用。习总书记最近关于农村问题的讲话给出了答案,即“我们要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促使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20]。在这样的思路下,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而言,作为物权的承包权能够给他以足够的保障,一方面,它能够有效对抗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侵入,另一方面,其剥离“经营权”加以流通,也更易在其不从事农业生产时实现土地收益,因为以“土地经营权”保障受让人的利益,将有更多的有意资本投资农业,必然形成更完善的议价机制,土地流转价格对农民更为有利。而农民进城后不愿耕作的土地,能够有效流转至生产专业户和家庭农场手中,提升农村生产效率,保障粮食生产。
以上述制度建设为依托,形成完备的农村土地用益物权体系,并逐步建立全域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而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概括国有化,既符合国家社会主义性质,亦建立一元化的土地所有权。
5 结论
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走向能够在未来的社会蓝图中寻找,通过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基础和功能作用进行梳理,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城乡一体化目标视域下丧失了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化改革有其历史必然性,夯实农村土地用益物权体系则是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国有化的必由之路。
(
):
[1] 张先贵.集体土地所有权改革的法理思辨[J] . 中国土地科学,2013,27(10):31 - 36.
[2] 王利明,周友军.论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J] . 中国法学,2006,(1):45 - 54.
[3]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9.
[4] 王菊英.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之关系论析[J] .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6 - 41.
[5] 喻文莉,陈利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嬗变的历史考察[J] . 中国土地科学,2009,23(8):46 - 50.
[6] 李凤章.通过“空权利”来“反权利”: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本质及其变革[J] .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5):16 - 28.
[7]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J] . 管理世界,1995,(3):178 - 189,219 - 220.
[8] 陶钟太朗,杨遂全.论宅基地使用权的空间权塑造[J] . 中国土地科学,2014,28(6):16 - 22.
[9] 贺雪峰.农村:中国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EB/OL] .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630.html, 2011-05-10/2014-10-12.
[10] 王静.城镇化中土地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中国近10年研究成果综述[J] .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4):55 - 61.
[11] 孟勤国.中国农村土地法律政策的三个前置性问题[J] .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7):96 - 100.
[12] 陈小君.后农业税时代农地权利体系与运行机理研究纶纲[J] . 法律科学,2010,(1):82 - 97.
[13] 蔡继明.中国现代化、城市化与农地制度改革探析[J] . 经济前沿,2005,(1):7 - 10.
[14] 张先贵.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有所为与有所不为[J]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4):14 - 19.
[15] 陈志武.农村土地私有化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N] . 财经时报,2005 - 10 - 08.
[16] 杨小凯.土地私有制和宪政共和的关系[EB/OL] . http://www.lawtime.cn/info/lunwen/xianfa/2006102644247.html, 2006-10-26/2014-10-13.
[17] 刘俊.中国集体土地所有权法律制度改革——方向与出路[A] .刘云山.中国不动产法研究(第五卷)[M]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32 - 233.
[18] 吴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从“既成事实”到法定转变[J] .土地科学动态,2014,(3):1 - 4.
[19] 厉以宁.论城乡一体化[J] . 中国流通经济,2010,(11):7 - 10.
[20] 习近平.深化农村土地改革不能搞强迫命令[EB/OL] . http://news.sina.com.cn/c/2014-09-29/194930934641.shtml, 2014-09-29/2014-10-14.
(本文责编:陈美景)
Trend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TAO Zhong-tailang1,2
(1. Law School,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2. Law School, Fordham University, New York 10023, US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exist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regard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Methods used include deductive method and reduction to absurd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basis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will be lost in the future and also the funct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will be lost according to the goal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ventually,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will disappear. Additionally, it is not a solution to use the private ownership to substitute rural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ng the rural usufructuary right system, using the state ownership to replace the rural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will be the positive solution. It wi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sic economy system, keeping the uniformity of land law and really achieving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land resources allocation.
land law; land economy;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rend
D923,F301.1
A
1001-8158(2015)03-0062-06
10.13708/j.cnki.cn11-2640.2015.03.008
2014-11-03
2015-02-05
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农村房地产权城乡间流转与遗产继承研究”(13AJY013)。
陶钟太朗(1981-),男,四川简阳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E-mail: 7673949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