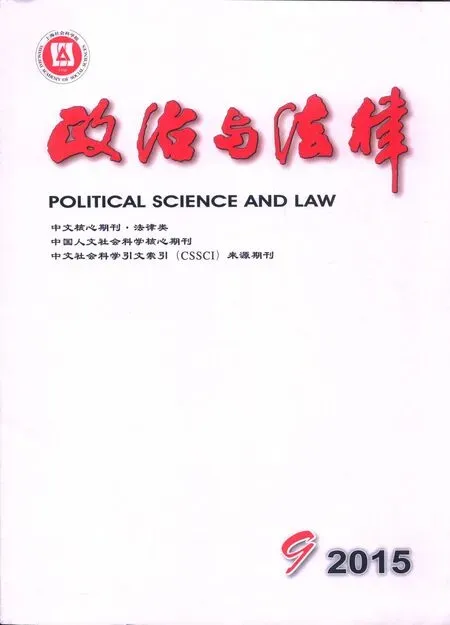正当防卫回归公众认同的路径*
——“混合主观”的肯认和“独立双重过当”的提倡
储陈城(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正当防卫回归公众认同的路径*
——“混合主观”的肯认和“独立双重过当”的提倡
储陈城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我国正当防卫的司法裁判已经逐步脱离了公众的认同。司法机关往往会通过认定防卫人的主观意思不唯一和防卫结果的过当来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和适当。脱离公众法感情的正当防卫裁判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事实上,任何防卫人的主观都必然包含着“保护”和“伤害”两种意思,混合的主观意思并不一定排斥正当防卫的成立。防卫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关键要看两种意思在主观中所占据的地位。实践中以“整体过当论”为理论依据推演防卫过当容易异化为单纯以“结果是否过当”来判断正当防卫是否过当。而采纳“独立双重过当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其会强调在判断“手段是否过当”的基础上辅助考量防卫结果以最终认定是否构成防卫过当。
正当防卫;防卫意思;侵害意思;防卫过当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司法机关往往不能准确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常将很多典型的正当防卫认定为相互斗殴或防卫过当,进而认定为故意伤害罪。如果正当防卫的案件中出现了死亡结果,就更难认定为正当防卫,可以说,司法机关对于正当防卫的裁判已经开始脱离公众对于正当防卫正当性的判断。笔者从全国各级法院公示的正当防卫的案件中调取了224份判决书,并从中筛选出能够反映整个案情全貌的判决样本以及被《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和《人民法院刑事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等权威书目收录的判决样本100份。这些判决书样本共涉及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以总数的80%为标准,则数量排在前列的分别是河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自治区、海南省、上海市、北京市、安徽省和新疆自治区。上海、广东可以作为东部发达地区的代表;河南、湖南、安徽则可以作为中部地区的代表、而广西、海南和新疆则可以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代表。在笔者统计的样本中,不构成正当防卫的判决书最多,为58件;认定防卫人防卫过当的判决书数量居次,为36件;判决构成正当防卫的最少,仅为6件。换言之,以正当防卫作为出罪事由的判决比率仅为6%。虽然这个出罪比率已然远高于我国无罪判决率的总体水平,①据统计,2008年至2012年,全国法院共判处各类刑事案件被告人5239739人,其中宣告无罪5196人,无罪判决率为0.10%。参见马剑:《人民法院审理宣告无罪案件的分析报告——关于人民法院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证分析》,《法制资讯》2014年第1期。但是这一出罪率和它作为我国实定法之中仅承认的两个违法阻却性事由之一的地位颇为不符。
这94份认定被告人构成相关犯罪的判决书主要涉及以下四个罪名:故意伤害罪(74件)、故意杀人罪(14件)、聚众斗殴罪(5件)和寻衅滋事罪(1件)。
这94份有罪判决书中,除了36份因为被告人防卫过当而获罪之外,其他58份判决书则分别因以下原因而被法院认定为不构成正当防卫:一是防卫意志瑕疵(41份);二是不存在现实不法侵害(9份);三是防卫不适时(5份);四是针对第三人的防卫(3份)。
审理正当防卫的案件时,法官会按照正当防卫的条件和案情进行一一对比,以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的要件。是否存在现实不法的侵害、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以及防卫的对象是否是侵害人本人的判断均属于客观判断,对于客观情状的判断比较容易把握,在司法实践中也较少出现争议。而防卫人的防卫意思属于主观层面的判断,需要通过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以及其他客观证据来综合推理,这便增加了司法机关作出误判的可能,加上理论上对于防卫意志的争论,使得司法机关往往对于防卫意思从严把握,从而限缩了正当防卫的成立可能。另外,防卫是否过当虽然也属于客观事实的判断,但是由于对既有规范把握不准,使得司法机关往往陷入单纯进行法益价值衡量的误区,使得很多正当防卫的案件被误判为防卫过当。
二、问题的分析:正当防卫裁判脱离公众认同的解释轨迹
(一)司法过度追求防卫意志的唯一性
对于正当防卫的成立,防卫意思是否必要早就在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的论辩中展开了争议。违法性的本质,如果采取行为无价值论的观点,则违法性的判断必须包含主观要素,因此主张防卫意思必要说。但是如果采纳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在违法性判断上则不要求含有主观要素,因此主张防卫意思排除说。防卫意思排除说的一个经典的案例是:“一个单纯为了满足英雄的感觉而为他人正当防卫,不能因为其不符合正当防卫的主观要求,而变成有犯罪的故意。”②黄荣坚:《刑罚的极限》,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04页。但是基于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相统一的原则,我国通说的理论认为正当防卫必须具有防卫意识,防卫意识又分为防卫认识和防卫意思。所谓防卫认识是指防卫人意识到有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防卫意思是指防卫人进行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侵害。
在我国,实施正当防卫不仅须要有防卫意思,还必须在主观上有祛除侵害的意思,即在实施正当防卫的时候,防卫人不能有故意伤害侵害人的意图,如果防卫人在防卫时存在故意伤害侵害人的意图,则正当防卫难以成立。比如对偶然防卫的经典案例进行进一步的改动:某甲正在追杀某乙,被某丙发现,某丙与某甲有世仇,早就想致某甲死亡,既为了报复某甲,客观上也为了保护某乙,所以开枪杀死某甲。在该案中,防卫人丙既有借防卫之名行报私仇之意思,也有保护他人合法权益的意图,同时在客观上也满足正当防卫的其他要求,那么某丙是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正当防卫呢?当这种主观上的故意伤害或者杀人的犯罪意图与防卫意图产生混合,司法实践的通常观点认为,此时防卫人在主观上就只有犯罪意思,而没有防卫意思。因此也往往会认定行为人不构成正当防卫。这种结论并不是脱离刑事司法操作的假想和臆断。比如在杨坤属故意杀人案中,就是如此。该案的案情如下:被告人杨坤属之翁父王兴友(本案被害人)多次纠缠杨坤属欲与其发生性关系。某日,王又趁机欲与杨发生性关系,而杨不从,双方遂发生推拉抓扯,王不慎摔倒在地,在无亮光的情形下,被告人杨摸着狗槽砸向王,后又拾起半块狗槽再次向王砸去,均砸在王的头部。该案的检察机关控诉认为,被告人举起狗槽砸王兴友头部的行为证明被告人有故意杀害受害人的意图,因此以被告人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③四川省泸县人民检察院以泸检诉字(2000)第103号起诉书。而一审法院则认为虽然缺乏证据证明被告人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但是被告人在无光亮的环境条件下,为教训王兴友而实施的伤害行为,故应以故意伤害罪定性。④四川省泸县人民法院(2000)泸刑初字第120号判决书。该案的被告人长期受到受害人的性侵犯,在主观上对受害人已经产生仇恨情绪。在再一次受到受害人性侵犯的时候,该案的被告人首要考虑的是通过拿起较重的狗槽向人的头部砸,来达到阻止侵害人继续侵害,使得自身法益得以保护的目的。同时,作为一个成年公民,被告人必然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肯定会导致被害人身体的损伤,甚至是死亡。基于被告人因长期受到被害人性侵害而感到的屈辱和仇恨感,其对被害人的伤亡结果是持放任甚至是追求的态度,也就是间接故意甚或直接故意。也正因如此,检察机关和一审法院最终均认定被告人不构成正当防卫。
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防卫人主观意思唯一性的苛求,有时候甚至达到“洁癖”的地步,他们会将行为无价值论的防卫意图进一步伦理化和前置化;只要起因存在瑕疵,就断定防卫人主观上肯定不会再有防卫意思。比如江苏省常熟发生的何强、曾勇等人聚众斗殴案就是一个典型。徐某与曾某因赌债发生纠纷,某日,徐指派的何强与曾指派的杨佳就债务偿还问题谈判未果,后何与杨、曾互通电话,双方在言语上互有挑衅。在判断双方将发生进一步冲突的情况下,何随即打电话给张某,让其纠集人至徐的公司准备菜刀等工具。何又再次拨打曾勇电话,再次产生矛盾。当日中午,曾纠集多人持刀赶至徐的公司,与何强等6人展开持械斗殴,致3人轻微伤,公司内部分物品毁损。⑤参见江苏常熟市人民法院(2011)熟刑初字第0785号判决书。对于该案的解析,陈兴良教授和赵秉志教授都认为该案的被告人之所以不构成正当防卫的重要原因是事情的起因是赌债这一非法因素,起因就不合法。⑥参见陈兴良:《聚众斗殴抑或正当防卫:本案定性与界限区分》,《人民法院报》2012年4月13日第3版。赵秉志:《关于何强等“菜刀队”案件定性的基本观点》,http://www.dffy.com/fayanguancha/sd/201204/28284.html,2014年6月2日访问。将防卫意图提前到案件发生的起因阶段,并加入赌博这一伦理因素,显然不能令人信服。事实上,正当防卫的起因和正当防卫最终是否成立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和防卫意图也没有任何关联。比如某甲到洗浴中心欲要求店家提供卖淫服务,最终因为价格未谈拢而发生争吵,店主气急败坏,突然持利刃向某甲的要害部位猛刺,某甲拿椅子抵挡,并击中店主,致店主轻伤。该案也存在起因上存在伦理不法,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某甲的防卫意思和正当防卫。⑦参见李勇:《结果无价值论的实践性展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页。
司法实务中,因为被告人在起因阶段的不法而认定防卫人缺乏防卫意思并被判不构成正当防卫的案件不乏其例。比如钟长注故意杀人案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证。被告人褚某的制毒窝点被警方查获后,持枪与同伙苏某驾车逃窜。为躲避追捕,褚打电话给被告人钟长注,要求钟协助其逃离。钟在明知褚持有枪支的情况下仍然帮助其藏匿和逃离。在逃窜过程中禇和苏怀疑钟是举报人,遂用手铐将钟铐在车上,苏持手枪击中钟的腹部。为防卫自己,钟挣脱手铐,在与苏搏斗中,持枪朝苏开枪,击中苏胸部,致苏死亡。⑧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泉刑初字第5号判决书。该案就涉及防卫的起因具有伦理上的非法性和刑法上的非难性,因此一审就认为被告人钟长注明知同案人褚某等2人是犯罪的人而为其藏匿作案工具、带路,帮助其逃匿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争吵并相互开枪射击,均属不法行为,钟长注持手枪击中苏某胸部,致其当场死亡,其行为已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和窝藏罪。
(二)司法过度强调防卫过当的结果衡量
除了特殊正当防卫之外,正当防卫需要满足限度的要求。“正当防卫只有控制在必要限度内才是正当的,因此防卫限度是正当防卫理论的核心。”⑨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50页。超过防卫的限度就是防卫过当,在日本也被称之为“过剩防卫”。日本刑法对正当防卫要求比较严格,在日本的刑法规范中不存在我国的特殊正当防卫的情形,因此所有的正当防卫都必须满足相当性,即必须维持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范围内。⑩参见[日]松宫孝明:《刑法总论讲义》,钱叶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日本刑法第36条第2款规定:“超出防卫限度的行为,可以根据情节减轻或者免除刑罚。”①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其防卫过当可以区分为质的防卫过当和量的防卫过当。所谓质的防卫过当是指在防卫的时候手段超过了必要限度的正当防卫。比如本可以用拳头击打就可以阻止侵害人的侵害,却使用尖刀进行防卫。所谓量的防卫过当是指防卫的手段并不过当,但是在量上超过了限度。比如用刺一刀就可以让侵害人停止侵害,却连续刺了数十刀。根据日本刑法的规定以及理论界对过当防卫的分类可以看出,在理论学说上,虽然日本刑法对于防卫过当的判断也注重法益的权衡,但更注重对防卫手段是否过当进行精致的分析。②参见[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4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6-267页。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4-336页。日本的判例也基本采取这一立场,在判断防卫是否过当时,重要的是判断防卫手段是否具有相当性,“故纵然因反击行为所生法益侵害结果偶尔大于将被侵害之法益,亦可成立正当防卫之行为”。③余振华:《刑法违法性理论》(第二版),台北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30-131页。
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对于防卫过当的规定也比较简洁,其第23条后段规定“防卫过当者,得减轻或免除其刑”。但是通说对于防卫过当的理解,仍然重点考察行为人的防卫手段。比如林钰雄教授就认为防卫过当是行为人出于防卫意思,且客观上具有防卫的事由,只不过使用了超过必要性的手段的防卫行为。④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43页。而林东茂教授对于防卫过当的解释则更是一语中的:“所谓防卫过当,通常指手段上显然超越必要程度。”⑤林东茂:《刑法综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4页。因为正当防卫是针对不正的行为,侵害者应当承担被反击后遭到更大侵害的风险,因此没有必要过度关注结果法益的比较。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日本抑或是我国台湾地区,对于防卫过当的判断更注重防卫手段的判断,而对于防卫结果的权衡不太重视。
我国刑法关于防卫过当的规定要比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更全面和清晰,因为我国刑法上防卫过当的判断要平衡考量行为过当和严重的危害后果两方面,不会有所偏颇。现笔者以金峰故意伤害案加以分析。该案被害人蒋某、黄某和张某共同徒手殴打被告人金峰,金在反抗过程中使用水果刀向蒋某连捅数刀,致其重伤。⑥具体案情可参见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09)青刑初字第248号判决书。对于该案防卫是否过当的判断,首先要看防卫人的防卫手段。对于侵害人一般性的殴打行为,其采取的防卫手段,即用水果刀捅侵害人,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反言之,其可以被期待采取“水果刀捅”以外的侵害性更低的方式来作为防卫手段。其次,判断行为人的防卫结果是否过当,相对于侵害人所侵害的一般性身体法益,防卫人的防卫造成侵害人重度身体法益的侵害,因此防卫结果也过当。因此通过独立的手段和结果的判断,该案的行为人最终被认定为防卫过当。这是符合我国刑法规范的判断防卫过当应然的司法裁判程序。
然而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认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造成重大损害’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具体表现。①高蕴嶙:《论防卫过当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福建法学》2012年第3期。那么其推理的逻辑就是:“防卫手段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必然造成重大损害”,以及“造成重大损害”、“防卫手段必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种观点有着张明楷教授的整体过当说的痕迹,张明楷教授认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结果之间密不可分,“不存在所谓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换言之,只是在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才存在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问题;不存在所谓‘手段过当’而‘结果不过当’或者‘结果过当’而‘手段不过当’的现象”。②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整体过当说本质上并没有错误,它在形式上同样认为防卫过当就是“手段”和“结果”同时过当。它是这样定义的:如果防卫人的一般防卫不构成防卫过当,则即便造成了侵害人的重伤或者死亡,也不能认为“结果过当”,而“手段也必然不过当”。同样,如果防卫人的一般防卫不构成防卫过当,则即便使用的防卫手段具有极大的致死伤可能性,也不能认为“手段过当”,而“结果也必然不过当”。
首先,整体过当说的这种循环论证导致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推演逻辑是倒置的,在演绎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误导:防卫手段是否明显过当?回答这个问题要看防卫结果是否过当,结果是否过当要看行为人是否是防卫过当。从正面推理则变为如下逻辑:行为人构成防卫过当,则结果必然是过当的,则手段也必然是过当的。其次,“作为极端彻底的结果无价值论的持有者,其内容是,违法性的本质……与行为人的主观要素无关”,“亦即否定主观要素具有违法要素的性质”。③刘艳红:《主观要素在阶层犯罪论体系的位阶》,《法学》2014年第2期。而防卫手段是否过当并非完全的客观事实的判断,必须结合防卫人在面对侵害时的复杂主观心态,因此也需要进行主观判断。所以笔者推论认为,虽然张明楷教授在形式上并不否认防卫过当需要考虑防卫手段,但是实际上通过整体过当论的循环论证弱化了对防卫手段是否过当的判断。再次,在实务中,“防卫手段是否超过必要限度”并非都能如前述蒋某故意伤害案那么明晰而容易地判断,实践中更多存在的是,由于案件发生的环境复杂,判断防卫手段是否适当需要复杂的法律分析,所以实务部门往往选择更为简单的判断,即判断防卫的结果是否过当,进而通过“造成重大损害”来类推“防卫手段必然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因此,这种整体过当论极易导致和促使司法部门在判断是否防卫过当时,误入唯结果论——以防卫结果作为认定防卫是否过当的唯一标准的雷区。
因此我国司法实务在认定防卫过当上,走上了一个极端,即以防卫结果作为认定防卫是否过当最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这也使得我国司法部门将防卫过当的评判简易化为防卫所造成的结果的判断,简言之就是法益价值的简单衡量。比如赵泉华故意伤害案就是如此。该案中被告人赵某与王某、周某素不相识,双方因琐事发生争执。事后,王、周等人多次至赵家进行挑衅,均因赵避让而未果。某日晚,王、周再次至赵家,采取暴力强行踢开赵家上锁的房门,闯入赵家,赵为制止不法侵害,持械朝王、周挥击,致王某头、面部挫裂伤,属轻伤;致周头皮裂伤、左前臂软组织挫裂伤,属轻微伤。④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2000)闸刑初字第628号判决书。一审法院简单对比防卫人所受侵害程度和防卫行为对侵害人造成的伤害后果之后,认为后者受损权益价值高于前者,就认定被告人防卫过当,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构成故意伤害罪。
三、回归的路径:“混合主观”的肯认和“独立双重过当”的提倡
(一)防卫人主观混合意思形态及处置
防卫意思是判断防卫人主观意思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核心,通说认为诸如相互斗殴以及偶然防卫都不仅缺乏防卫意志,还具有故意侵害他人权利的意思,所以不成立正当防卫,甚至可能构成犯罪。①参见张明楷:《刑法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87-190页。众所周知,偶然防卫的主观意志是缺乏防卫意思且只有侵害意思,但是互殴行为并非没有防卫意思。事实上包括正当防卫在内的任何一种防卫行为,行为人主观上都既有保护的意思也有侵害的意思,正如黎宏教授所言:“即便是在正当防卫的场合,行为人不是出于防卫意图,而是出于愤怒或激动而反击对方的情形完全有可能存在;同时,在伴随有报复加害对方意图的正当防卫的场合,行为人在防卫之外,同时也存在攻击、伤害对方的意图。”②黎宏:《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法商研究》2007年第2期。如果认为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不能含有侵害的意思,则成立正当防卫的唯一可能就是防卫人不对侵害人进行任何反击,而是积极逃避。因为只有这样,防卫人在主观上才会纯净到只有防卫意思而没有也不可能有侵害意思。相互斗殴的行为人在主观意志上是复杂的,他们既有侵害对方的意思,也有保护自己的权利免受侵害的意志。基于理性人的基本思维,绝大多数理性人都不可能在不保护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去侵害他人的权利。在斗殴的情况下,任何一方的斗殴行为都可以分解为侵害对方的攻击和保护自己的防御两种行为。来自于对方的侵害性攻击就是“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己方的保护性防御也正是为了使自己的人身免受对方的侵害性攻击。总而言之,互殴行为在主观上是含有防卫意思的,在客观上也符合正当防卫的其他要件。既然如此,为什么相互斗殴行为致人伤亡还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岂不与正当防卫的要件相矛盾?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因为目前理论和实务界曲解了正当防卫与否在主观上的关键性区别。这种关键性区别不应是防卫人是否除了防卫意思外还有故意伤害的意思(即防卫人主观上是否“唯一”),而应是防卫意思和伤害意思在行为人主观中所占据的地位如何。
目前对于防卫意思的内容有目的说与认识说两种观点。防卫意思目的说认为,防卫人在进行正当防卫的时候,主观上必须且只能有保护自身、他人、公共或者国家的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侵害之目的和动机。如果在防卫的时候不仅有防卫的目的,还有因激愤或者有攻击的意图的时候,就不能认为防卫人有防卫的意志,也即不能成立正当防卫。这就是我国目前理论和实务界对正当防卫人主观所持有的主流立场。而防卫意思认识说则认为,防卫人在进行正当防卫时,主观上只要具有防卫的目的和动机就已经足够,即便行为人在防卫时还具有因激愤或者有攻击的意思,仍不能否定其正当防卫的意图。③参见甘添贵、谢庭晃:《捷径刑法总论》,2006年作者自版,第154-155页。正如大谷实教授所言,防卫时“由于亢奋、狼狈、激愤、气愤而没有积极的防卫意识,或者攻击意识与防卫意思并存,也不应当马上否认其防卫意识”。④[日]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成文堂2009年版,第289-290页。日本的相关裁判也认为,“防卫意识与攻击意识完全可能并存,防卫意识并不被攻击意识抵消,故不能因为行为人具有攻击意识就否认其具有防卫意识”。⑤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1985年9月12日判决,日本5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6第39卷第6号,第275页。这也支撑了笔者前文所言的观点,即防卫者在防卫时的主观意思不可能是单纯的为了保护法益,必然还包含有其他意思——即伤害侵害人的身体等权益。因为认识说承认了任何防卫行为的防卫人在主观上都具有混合意思,所以防卫意思认识说要比目的说更为合理。但是这种观点并非完美,因为防卫人的主观意思混合之后如何才能判断防卫人是否满足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分类处理。笔者认为防卫人混合的主观意思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一般型。其要求对法益的保护是积极追求和对侵害人身体等权益的伤害持放任态度,但不积极追求,是间接故意的两个条件。
由于保护法益的主观意思是积极追求的,而伤害侵害人的权益的主观意思是放任的,也即持间接故意的态度,所以,显而易见防卫人的前一种主观心态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一般典型意义上的正当防卫的防卫人在防卫时主观意思的体现。那么如何判断防卫人的主观意思是属于一般型的呢?综合案情,如果具备以下要素的两个以上者,可以判断为防卫人的主观是属于一般型的。第一,防卫人在遇到侵害人的侵害之前,与侵害人之间没有矛盾,对侵害人不存在进行侵害的基础。第二,侵害人的侵害并没有激起防卫人的愤怒,防卫人面对侵害选择的首先是积极退让,迫不得已时才还击,或者虽然没有积极退让,但是选择的是侵害程度最低或者较低的手段进行防卫。第三,在制止了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之后,防卫人及时停止防卫行为。第四,防卫行为造成侵害人伤亡的结果,防卫人积极寻求救助。下面笔者以王占财故意伤害案为例加以说明。王健、王家伍2人因琐事与被告人王占财发生纠纷。二十分钟后,王健邀约王帅等5人欲殴打王占财。王帅持菜刀砍王占财。王占财立即起身逃避,王帅追砍,王占财被砍中几刀,退进自己店内,拿起两个啤酒瓶抵挡王帅,打中王帅的面部,致其倒地,伤及头部,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①新疆石河子市人民法院(1992)石市法刑一字第179号附民字第02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该案的防卫人在防卫时主观上即属于典型的一般型。首先,其与被害人之间素不相识,不存在提前产生侵害意思的基础;其次,其在面对被害人的侵害时,首先选择的是逃避,只是在逃避也无法摆脱侵害时,才选择还击;再次,综合当时的案情,在赤手空拳无法实现自身保护目的的情况下,防卫人并没有选择更具伤害性的刀具,而是啤酒瓶,防卫手段的侵害程度相对较低;最后,其在将侵害人击倒在地后,没有继续殴打侵害人。
第二种是愤恨型。其要求对法益的保护是积极追求和对侵害人身体等权益的伤害由于愤恨等情绪也是积极追求,是直接故意的两个条件。
基于对侵害人的愤恨,防卫人在防卫的时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由于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使防卫人产生激愤、仇恨等情绪,而使得防卫人对于侵害人的身体等权利的损害持积极追求的态度,也就是直接故意。如果防卫人在防卫时,前一种主观意思占据主导地位,则理应成立正当防卫。综合案情,如果防卫人符合以下情形,则主观上极可能属于愤恨型。第一,防卫人与侵害人在防卫进行之前素来不和,有较大的矛盾。在面对侵害人紧迫的侵害时,防卫人很有可能产生“一石二鸟”的想法。但是这种主观意思是在侵害产生的前提下产生的,如果没有侵害人侵害的情况下,防卫人则没有伤害侵害人的意思和打算。第二,侵害人屡次挑衅防卫人,或者其侵害行为极易激发防卫人的愤怒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防卫人的主观也极可能会产生积极伤害的意思。第三,从客观上来判断,防卫人选择的防卫手段具有较高的侵害性,也可以判断出防卫人的主观属于愤恨性。比如,面对他人的拳脚殴打侵害,选择锋利的刀具予以防卫。
以下笔者以叶永朝故意伤害罪案为例来分析。王为友等人在被告人叶永朝开设的饭店吃饭后未付钱。后多次纠集多人到叶的饭店滋事,并发生冲突。某日王纠集郑伟国等多人再次前来闹事,王抽出东洋刀向叶的手臂和头部各砍一刀。双方扭打相互砍刺,叶持尖刀刺中王胸口。郑见状拿方凳砸叶头部,叶转身刺中郑的胸口,又和王继续扭打。最终王和郑经抢救无效死亡,叶也多处受伤。经法医鉴定,王为友全身有八处刀伤。②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7)台法刑抗字第13号刑事裁定书。
该案的起因是被害人王为友吃饭后拒不付款,还多次借此对被告人寻衅报复滋事,并持东洋刀向被告人砍了两刀,致被告人头部和手臂受伤。通过案情可知,被告人拔出自备尖刀向被害人刺去主要是为了防止被害人继续侵害自己人身安全。同时刑法对于事实的判断不能偏离常识、常情和常理,③参见马荣春:《论刑法的常识、常情、常理化》,《清华法学》2010年第1期。基于常识、常情和常理的考量,被告人在受到被害人的侮辱、挑衅和伤害之后,自然心生愤怒之情绪,人们无法期待其主观上完全排除借正当防卫之机来伤害被害人以泄心头之恨的想法。另外从被害人全身有八处刀伤也可以看出被告人在进行正当防卫时是对被害人带有极大的仇恨情绪的。也正因如此,该案的控诉机关才会控诉被告人为故意杀人罪。但是这种侵害意思的产生是在防卫意思的支配下的附属产物,如果没有防卫意思,也就很难有机会产生侵害意思。因为即便被告人在防卫时有伤害攻击者的意图,法律也要迁就被告人的这种主观,不得苛责。其依据乃是被告人的这种有意伤害侵害人的意图正是因为侵害人的侵害行为引起的。
如果出现行为人在防卫时,法益保护的意思和积极伤害侵害人权益的意思等同或者无法区分孰轻孰重的情形,那么行为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呢?比如某甲正在追杀某乙,被某丙发现,某丙与某甲素来有仇,早就想致某甲死亡,既为了报复某甲,又为了保护某乙,所以开枪杀死某甲。但是某丙积极杀死某甲的意思和保护某乙生命的意思哪一个占据主导地位又难以区分,该如何处理分歧不断,需要认真分析。如前文所言,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对此早已争论不休。依照行为无价值论的观点,某丙防卫意思不纯,有故意杀人的意思,应当认定为故意杀人罪;而结果无价值论则必然会认为只要有客观的防卫效果存在就可以认定正当防卫的成立。如果支持前一种观点,则仍然在压缩正当防卫的存在空间,而如果支持后一种观点,则在当下又无法在司法实践中推行。张明楷教授则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应认定为事实不明的情形,必须适用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①同前注⑮,林东茂书,第83页。如果单纯是基于存疑有利于被告的目的,则这种观点恐会遭到行为无价值论者的反对。笔者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应各退一步,法益保护的意思和积极伤害侵害人权益的意思等同或者无法区分孰轻孰重时,只要具备正当防卫的其他要件,即可以认定正当防卫成立,也就是让结果无价值论占据这种情形的理论制高点,而行为无价值论将完全控制下文所论述的“放任型”主观混合意思状态下的正当防卫成立与否的判断。
第三种是放任型。其要求对法益的保护是持放任态度和对侵害人身体等权益的伤害积极追求,是直接故意的两个条件。
可能有人会质疑在“愤恨型”的主观混合意思形态中,为什么没有法益保护的意思明显低于积极伤害侵害人权益的意思的情况分析呢?一般来说,如果防卫人对于侵害人权益的伤害意思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其对于法益保护的意思也就不再是积极追求,而只可能是持放任态度。这也就是笔者所称的“放任型”主观混合意思形态。相互斗殴的行为人主观上即属此种样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于坚持结果无价值论,可能会在司法实践中碰壁。首先,会使得司法在面对互殴行为时无法做出合理的判断,正如前文所言,互殴行为的行为人也有保护自己法益免受侵害的防卫意思,但是由于行为人选择参与互殴,则对于自己法益的保护不再是积极追求的态度,反言之,如果行为人对自己法益的保护是持积极追求的态度,则其应该选择不参加斗殴。所以互殴行为人对自己法益的保护是持放任的态度。显然互殴行为是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其次,可能会使得防卫人在防卫时往往选择最具攻击性和杀害性的手段来伤害侵害人。比如某甲正在追杀某乙,被某丙发现,某丙与某甲有世仇,早就想致某甲死亡,他也知道对甲开枪就可以保护到乙,其原本可以开枪射击甲的腿部就可以使得甲停止侵害,但是其选择开枪射击甲的要害部位,使甲死亡。因为正当防卫需要满足必要性原则,即在防卫人有可选择的空间和时间的情况下,“其应当尽量选择最为温和、造成最小损害的手段为之”。②同前注⑭,林钰雄书,第236页。同时基于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考量,为了避免将司法置于现实的尴尬境地,对于这种情形,考虑我国当下的理论和实务态度,认定防卫人不构成正当防卫比较适宜。
(二)防卫过当的手段和后果独立双重过当之提倡
司法实务中认定防卫过当以防卫结果的法益价值进行简单衡量的倾向完全偏离了正当防卫的设置理念。因为正当防卫中的侵害者应当承担被反击后遭到更大侵害的风险。基本上,防卫者所保护的利益,其价值无须大于反击后所破坏的利益。也就是说,正当防卫不要求防卫人在防卫时做两种法益的利益权衡。对于正当防卫是否成立,其决定性的要素并不是等价或者不等价的权利或者法益之间的冲突,而是权利和不法之间的冲突。防卫人和侵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采取有利于防卫人的原则进行处理的。也就是说防卫者受到侵犯的法益,原则上优先于必要情况下对违法者所侵害的法益,即使是防卫者所要保护的法益比违法侵害人的法益要低。因为,当为了保护权利而对抗不法的时候,利益的相当性考量就没有适用的空间,这里所隐藏的基本法理是,“权利绝对没有理由退让不法”。正当防卫权的行使,不必过分重视所欲防卫的法益和防卫行为所侵害的法益是否相对称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强求被攻击者承担因为防卫行为不充分而造成其权利或者法益受害的风险。如果违法侵害非常急迫,只要防卫手段上具有客观的必要性,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即便是使得侵害人遭受更大法益的损害,仍然肯定正当防卫的成立。①高金桂:《利益衡量与刑法之犯罪判断》,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19-120页。在正当防卫中,相当性原则之考察,是针对进攻与防御,而非针对所受侵害或危险之法益位阶及防卫行为所侵害之法益位阶加以对比。②林山田:《刑法通论》(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我国刑法上的防卫过当中,“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结果”之间应该是并列关系,只有同时具备的时候,才能认定为超过了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也就是说,防卫过当必须是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且因此造成了重大损害。反言之,如果防卫行为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但是造成了重大损害结果,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同样,如果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但是没有造成重大损害结果的,必然也不能认定为防卫过当。笔者将这种把手段过当和结果过当分离考量的观点归纳为独立双重过当论。③同样观点还可参见陈正云:《论准确认定和把握防卫过当的标准》,《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1期;王政勋:《刑法的正当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页。虽然独立双重过当论和前文所述的整体过当论都认为防卫过当必须是“手段”和“结果”都要过当,但是,不管是司法实务中的通常做法还是张明楷教授整体过当论的观点,都认为“防卫手段明显过当”和“造成严重损害后果”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是需要循环论证的,且一般是通过“结果是否过当”来定义“手段是否过当”。而独立双重过当论则认为“手段过当”和“结果过当”是分开的两个独立个体,不能相互循环论证。也就是说,承认既存在“防卫手段明显过当”但是没有“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防卫,也存在“防卫手段适当”但“造成严重损害后果”的防卫。比如某甲用拳殴打某乙,其击打力度和部位至多造成某乙轻微伤,但某乙拔出手枪朝某甲的头部射击,不过因射术不精,子弹打偏,擦着某甲的发梢飞出,并未造成某甲的任何损伤,某甲惊吓停止侵害。此案便属于“手段明显过当”但“结果不过当”的情形,因为这种防卫不符合两者都过当的要件,不能被视为防卫过当。再比如某甲是矮小瘦弱的女性,在夜间被陌生男子某乙尾随,某乙试图对某甲进行强制猥亵,突然走到某甲身后强行拉某甲的衣服并实施猥亵行为,某甲惊吓过度,误以为某乙要实施强奸行为,在混乱中摸起一块石头砸向某乙的头部,造成某乙死亡。这种案件和典型的基于强奸案件而进行无过当防卫有所不同,因为如果站在防卫人的角度来看,其基于恐惧而认为侵害人存在强奸的意图和行为,进而进行无过当的正当防卫是可以进行解释的。但是在实践中,如果司法机关站在客观事实的角度来分析,则会认为,因为侵害人并没有实施强奸的意图和行为,亦即客观上侵害行为并非是强奸行为,则防卫人不能实施无过当的正当防卫。那么如何解释防卫人的行为不是无过当防卫但是又不构成防卫过当呢?唯一的解决路径就是该案是属于“结果明显过当”而“手段不过当”的情形,因为基于综合案情的考量,人们无法期待防卫人在当时的情况还能选择其他更为合理的手段进行防卫,因此防卫人构成正当防卫。
独立双重过当论的推演逻辑是:首先综合全案的案情,站在案发时的立场,看防卫人除了选择当时的防卫工具、防卫力度、打击部位等等之外,是否还能期待其选择其他侵害性更小的防卫手段,以判断行为人防卫手段是否适当。如果司法机关的论证结论是无法合理期待防卫人选择更为合理的防卫手段,则直接可以认定不构成防卫过当。如果认为行为人的防卫手段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再继续通过法益权衡的分析,看防卫行为是否造成了重大损害结果,即结果是否过当。最后再作出是否防卫过当的最终结论。因为防卫结果是否过当的判断完全是通过法益权衡来进行的,比较简单,而防卫手段的判断则需要结合案件发生时的种种情况综合考究,最为复杂,因此是防卫过当判断的核心。所以笔者主张在判断防卫过当的时候,要摒弃“以结果是否过当的判断为主体,以手段是否过当的判断为辅”的错误做法。防卫过当必须要以防卫手段是否过当为主体进行考察。这也正是前文所述的日本防卫过当判断的精华所在。因此如何判断“手段不过当”便成为了亟需解答的问题。实际上,对于防卫手段是否过当的评判,学术界并没有也无法提出更为具体的判断标准。即便是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也无法解答“正当防卫在何种具体情况之下,方能解为是符合‘相当性’原则”。①同前注⑬,余振华书,第145页。因此如何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来构建和细化防卫手段的判断标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笔者只能在此提出如下建议以供参考。
在考虑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时,首先要把侵害者与防卫者双方置于案发当时的特定环境中,根据案件的起因、时间、地点、环境、侵害的情状、侵害的密集程度、侵害行为的手段和危险性、强度、后果等因素,以及着重考量防卫者在当时所可能选择和适用的防卫手段,进行整体、全面、客观的分析判断,一般来说,防卫手段的适当性要从客观、事前加以判断。②同前注㉜,林山田书,第205页。另外,对于防卫手段是否适当的考量,还要从客观的第三者的立场,立于被侵害人的地位进行判断。③参见柯耀程:《刑法问题评析》,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8-20页。如果以事后理性的目光来审视侵害发生时,处于理性认识受困状态下的防卫人所采取的防卫行为,则不具有合理性。因此,还需要利用期待可能性思想来论证防卫手段的适当性。虽然通说认为它是有责性判断的理论,但在违法性判断上,其也有发挥作用的空间。构成防卫过当的前提必须要求行为人有实施较小侵害性的防卫手段的可能性但没有实施,行为人的防卫行为才值得评价为超过必要限度。期待可能性必须“在行为人的主观精神能力之外还与客观环境联系起来,充分考虑客观环境条件对人的相对自由意志的限制作用”。④刘艳红:《调节性刑罚恕免事由: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功能定位》,《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在此,笔者以谭某被控故意伤害罪案为例加以说明。植某和植某航无故对谭某滋事。植某踢打谭某的腹部,谭某即拿起拖把欲抵抗,植某和植某航就抢去拖把并对其进行殴打。在打斗过程中,谭某被推倒在地,并被一摩托车压住左腿,身旁的玻璃门被撞碎,但植某和植某航仍继续殴打谭某的背部。谭某便从地上抓起一块玻璃向后划去,划伤植某颈部、植某航鼻梁、左上臂。植某被划伤后倒在地上,后经送医院救治无效死亡。⑤《遭殴打刺伤施暴者致死法院判决正当防卫无罪》,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7/id/1025169.shtml,2014年9月17日访问。该案的公诉机关认为谭某的防卫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的危害后果,因此构成防卫过当。但是综合案情来看,谭某被植某和植某航2人无故围殴,其唯一的防卫工具——拖把被植某抢走,并被打倒面朝地背朝天俯卧在地,其左腿也被一辆被推倒的摩托车压住。但是此时,植某和植某航2人并没有放弃侵害行为,继续俯身弯腰殴打其背部并致轻微伤,不法侵害始终没有停止。此时的防卫人基于愤怒、慌张和恐惧的心理,且手无寸铁,对于所遭受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意图的危险程度一时难以分辨,在没有办法选择一种恰当的防卫行为的情况下,为避免继续遭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出于防卫本能,只能随手抓起地上的碎玻璃条朝背后乱划。虽然本案的结果法益的对比是保护身体法益而侵害了生命法益,从结果上来看存在失衡的状况,但是从案发当时的实际角度来分析,防卫人当时只能选择两种防卫手段,一是在倒地背身的情况下,赤手空拳来还击;二是捡起地上的碎玻璃予以还击。而防卫人谭某当时的情况是无法通过赤手空拳的打斗来促使植某等2人停止侵害以防卫自身法益的,因此无法期待防卫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坚持选择第一种防卫手段。
另外,考量正当防卫的手段是否超过必要限度还要根据防卫人当时面对侵害时的精神状态。德国刑法第33条规定,因迷惘、恐惧或者惊愕而超过正当防卫界限时,对行为人不处罚。这里“不处罚”是指免责。①[德]耶塞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588-589页。因为在处于迷惘、恐惧或者惊愕的状态下,行为人往往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其选择的防卫手段的限度可能在当时无意识地超越了必要的界限。在德国,根据其刑法第33条的规定,考虑到被攻击者的精神状态,这种错误的判断无法避免,即便最后造成的损害后果和要保护的法益失衡,也不能对防卫人定罪。受到男性侵害的女性防卫者以及对于防卫能力相对弱小的人面临强力侵害或者突然性侵害时,通常都会产生迷惘、恐惧或者惊愕。人一旦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往往难以被期待能冷静地推断侵害的方式、力度和结果以及采取何种理性的防卫手段以应对。因此事后司法机关理性的判断不能取代当时防卫人处于紧张状态的选择,事后理性看来“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防卫手段”在当时则并没有超过“防卫手段的限度”。吴金艳故意杀人案便是此类典型的案例,笔者对其加以分析。孙金刚、李光辉、张金强三人为报复尹小红,密谋强行将尹带到山下旅馆关押几天。某日凌晨3时许,三人破门而入,强行闯入尹的宿舍(该宿舍位于深山)。孙直接走到尹的床头,李则站在被告人吴金艳(尹的室友)床边,张站在宿舍门口。孙掀开尹的被子欲强行带走,遭拒绝后,便殴打尹并撕扯其睡衣,致尹胸部裸露。吴见状劝阻。孙转身殴打吴,并扯开吴的睡衣并踢打吴。吴顺手摸起一把水果刀将孙划伤。李见状拿起一把铁挂锁欲砸吴,吴持刀将李刺倒在地,致其死亡。②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4)海法刑初字第696号判决书。对于该案,检察机关认为本案的受害人没有实施达到严重危及吴金艳等人人身安全的程度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还没有产生。被告人在面对侵害人的侵害时,当时有很多求助选择,却使用了过当的防卫手段,因此认为被告人应当构成故意伤害罪。
对于侵害人的侵害行为是否已经达到足以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不应当以侵害人本来的侵害计划为依据,而应当以侵害发生时防卫人所处的环境、力量对比、精神状态等因素综合考量,即“根据相当性理论,行为通常性的判断要考虑行为发生的时空环境,同时应当以一定社会范围内一般人的观念为判断的实质标准。该案的发生时间是凌晨,夜深人静,而且深处山里的饭店宿舍。地点则是被告狭小的宿舍。侵害人是三个身强力壮的年轻男性,而被告人只是两名弱不禁风的年轻女子。侵害人破门而入,强行掀被子,殴打,撕扯睡衣,持铁锁砸等等一系列动作均会让防卫人产生恐惧,三个侵害人到底是要实施伤害、绑架、杀人抑或是强奸,从防卫人认识的角度来说都有潜在的可能。防卫人在受到侵害、惊吓,精神上处于高度恐慌的状态之下,看到受害人持铁锁向其砸去,只能以手中的刀予以还击。在综合考量整个案情之时,必须要考虑女性受到侵害时心理产生的恐慌程度。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还要求被告人选择其他的求助防卫或者依赖、等待援助,则过于苛刻了。
(责任编辑:杜小丽)
D F611
A
1005-9512(2015)09-0027-11
——以美国为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