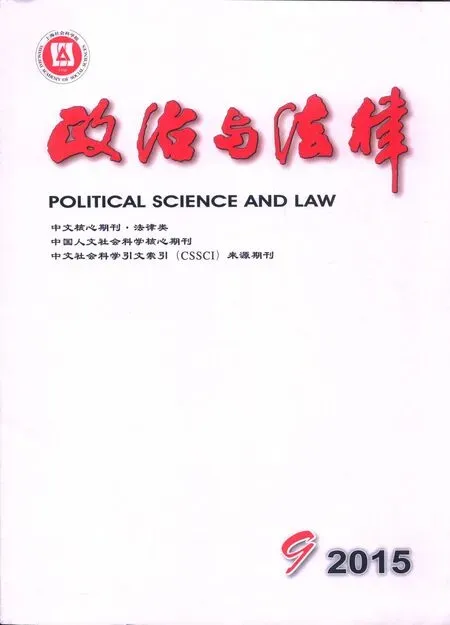论当代民族自决权内涵的更新*
张磊(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200042)
论当代民族自决权内涵的更新*
张磊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上海200042)
民族自决权的演进轨迹反映出的历史规律是每当民族自决权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它的内涵都会发生一次重大的更新,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以适应当时国际社会的历史环境。在今天,民族自决权存在理论上的瓶颈与实践上的混乱,应当再次更新其内涵。作为其内涵更新的重要方面,当代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应当更明确自决权的主体资格与行使条件,更强调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障,更重视内部自决权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民族自决权;内涵;民族;国家主权;内部自决权
民族自决权主要是指“受外国奴役和殖民统治的被压迫民族摆脱殖民统治和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权利,也泛指各国人民都有不受外族统治和干涉、自由决定和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利”。①王家福主编:《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页。在冷战结束之后,民族自决权在具体适用中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包括导致国家分裂与地区动荡。考察民族自决权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它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演化的。因此,民族自决权在晚近的国际实践中引发种种争议与冲突之后,人们有必要思考其内涵是否应当再次更新。
一、适时更新民族自决权的内涵符合历史规律
从民族自决权的发展历程来看,根据时代特点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其适时地更新自身的内涵,是得以逐渐演进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民族自决权的产生和传播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相辅相成
民族自决权在哲学意义上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德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康德的思想。根据康德的理论,“国家是由许多人依据法律组织起来的联合体”。②[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商务出版社1986年版,第139页。于是,他认为每个社会都有自己进行统治的权利。尽管康德当时没有使用“自决权”这个措辞,但是他的观点显然是对自决权思想的阐释。③See Frank Przetacznik,The Basic Collective Human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 and Nations as a Prerequisite for Peace,Vol.8,New York Schoo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p.56.之后,另一位德国著名思想家黑格尔明确提出:“独立自主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荣誉。”④[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39页。此外,德国学者费希特认为由许多人组成的团体与单独的个人是一样自由的。⑤参见[德]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载梁志学主编:《费希特著作选集(卷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5-417页。由此可见,早期的政治思想家们所倡导的个人和团体的自由成为民族自决权的思想萌芽。
1577年,法国学者让·博丹(Jean Bodin)在《论共和国》一书中首次提出国家主权的概念。当时,博丹认为主权在君。之后,1762年,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提出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于是,主权在民的思想开始取代主权在君的主张。主权概念的提出与进化给民族自决权的早期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和领域。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明确地提出一个民族去统治另一个民族是不合理的。⑥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62-172页。在此基础上,英国学者约翰·洛克进一步提出,统治者的权力只能来自于他与其国民之间的社会契约,人民的同意是政府建立的合法性基础。如果一个政府是征服者强加于被征服者的,被征服者的后裔就有权摆脱这个政府。⑦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60页。于是,在这样的思想引导下,民族自决权的早期思想从追求抽象意义上的自由开始逐渐转变为追求具体意义上的主权。
在民族自决权的产生与传播过程中,近代民族国家开始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率先在西欧建立起来。发生在1565年的“尼德兰革命”可以被认为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开端。在赶走西班牙军队之后,尼德兰北方七省宣布成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即今天的荷兰。⑧参见秦海波:《世界上第一个“民族国家”荷兰的诞生》,《中国民族报》2007年4月27日第5版。之后,发生在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为推动民族自决权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独立宣言》中尽管没有直接使用“自决权”这个词汇,但是它所宣示的民族自决权是不言而喻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所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则明确地将民族自决权作为政治口号之一。⑨参见董云虎、刘武萍编著:《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296页。此后,民族国家在西欧得以相继建立。到19世纪末,西欧的政治版图上基本都是民族国家了。
(二)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使民族自决权理论获得国际公认
在20世纪之前,民族自决权的适用范围基本局限于西欧和美国。因此,当时的民族自决权尚未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公认。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在西方国家中第一个主张将民族自决权适用于所有民族。这一点首先落实在美国对菲律宾独立的态度上。在1913年,美国宣布自己对菲律宾采取的新政策,即支持菲律宾通过行使民族自决权的方式寻求独立。当时,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哈里森(Harrison)宣布:“我们作为受托者,不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而是为了菲律宾人民的利益。我们要采取的任何步骤都将是为了菲律宾群岛的最终独立和为这一目的所做的准备。”⑩Ray S.Baker and William E.Dodd ed.,The New Democracy Presidential Messages,Addresses and other Paper(1913-1917), Vol.1,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1926,p.53.更重要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的1918年1月8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美国国会提出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该文件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任何民族都有权决定由谁来代表和统治他们”。①这对“一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同时期,另一位详细论述民族自决权的重要人物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1902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首次承认民族自决权。1903年,列宁写了《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宣言》,重申“国内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这一基本原则,并同时强调,要求承认每个民族具有自决权“仅仅说明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永远无条件地反对任何用暴力或非正义手段从外部影响人民自决的企图”。②《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0页。1913年,列宁在《民族问题提纲》中对民族自决权给出初步的明确定义:“我们纲领中关于民族自决的那一条,除了从政治自决,即从分离和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个意义上来解释以外,我们决不能作别的解释。”③《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9页。在此基础上,列宁于1914年发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理论。他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当时主要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要使世界无产阶级紧密团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这两方面的历史使命都必然要求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④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1页。
威尔逊和列宁的论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点,即任何构成民族的团体都有权利组建自己的国家,包括民族政治分离权。换言之,“威尔逊提出的民族有决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和选择自己发展道路自由的思想隐含有对民族政治分离权的承认。这已非常接近列宁的‘民族自决权就是民族政治分离权’的观点”。⑤张澜:《伍德罗·威尔逊的民族自决思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他们的主张在东西方都得到广泛的支持,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世界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国际社会主流意见对民族自决权的理解是比较绝对的,尤其是承认所有民族都拥有政治分离权。不过,应当澄清的是,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是针对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民族压迫政策,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民主手段提出来的。因此,尽管列宁承认民族政治分离权,但他的初衷并不是鼓励所有民族都要实际行使该权利,而是希望各民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能够联合起来。
威尔逊和列宁的思想使民族自决权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公认。这种公认之所以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源于当时世界范围内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开始进入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已经被西方列强瓜分完毕。伴随殖民高潮而来的是殖民者的民族压迫和被殖民者的民族觉醒。于是,伊朗的立宪革命、印度的自主自产运动以及苏丹马赫迪大起义等一系列反帝斗争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也在欧洲主要国家兴起,其中最突出的是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法国的复仇主义、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等。因此,无论是欧洲,还是亚非拉,整个世界都面对空前高涨的民族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威尔逊的主张,还是列宁的理论,都能够符合当时世界的需要。
(三)非殖民化运动使民族自决权开始正式成为国际习惯法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1945年联合国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世界秩序开始走向法治。《联合国宪章》第1条将“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作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同时,《联合国宪章》第55条进一步规定:“为造成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和平友好关系所必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起见,联合国应促进:第一,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业,及经济与社会进展。第二,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之解决;国际间文化及教育合作。第三,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于是,民族自决权开始正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
联合国成立时,全球有7.5亿人生活在殖民地国家中。也就是说,当时全世界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遭受殖民统治。⑥参见陈建樾:《联合国与非殖民化》,《世界民族》2002年第6期。于是,联合国在成立伊始就将非殖民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之一。
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是世界非殖民化运动最蓬勃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联合国大会相继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文件,确认和提倡民族自决权在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及其行使。
195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民族与国族自决权》的决议,承认和提倡各国管理下非自治领土及托管领土各民族的自决权利。⑦参见《民族与国族自决权》,A/RES/637(VII),联合国大会1952年12月16日通过。
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该文件第2条规定:“所有民族均有自决权,且凭此权利自由决定其政治地位,自由从事其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⑧《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A/RES/1514(XV),联合国大会1960年12月14日通过。同时,其第6条进一步规定:“凡以局部破坏或全部破坏国家统一及领土完整为目的之企图,均与联合国宪章之宗旨及原则不相容。”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A/RES/1514(XV),联合国大会1960年12月14日通过。
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公约都对民族自决权进行了规定。前者第1条第1款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⑩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United Nations,Treaty Series,Vol.999,p.171.该条规定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后者的第1条第1款。①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United Nations,Treaty Series,Vol.993,p.5.
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以下简称:《国际法原则宣言》)。根据该文件,“各人民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之原则”属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这个原则之下,“所有人民都有权自由地决定建立自主独立国家,与某一独立国家自由结合或合并,或采取任何其他政治地位,均属该人民实施自决权之方式”。②《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A/RES/2625(XXV),联合国大会1970年10月24日通过。不过,该宣言同时规定:“以上各项不得解释与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坏在行为上符合上述各人民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原则并因之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同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之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每一国均不得采取目的在局部或全部破坏另一国国内统一及领土完整之任何行动。”③《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A/RES/2625(XXV),联合国大会1970年10月24日通过。
在联合国建立前,民族自决权还不是正式的国际习惯法。所谓国际习惯法,是指“国家出于法律义务感而不是善意、礼让或者方便的考虑而采取的行为”。④Valerie Epps,International Law,Boston: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09,p.5.“国际习惯法只有在各国实践具有普遍性,且各国承认有义务这样做的条件下,方可成为法律。”⑤张乃根:《国际法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页。于是,国际习惯法要成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需要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形成各国一体遵守的普遍做法,即通例;各国明确表示其之所以遵守该通例是因为法律义务感,即法律确信。民族自决权在联合国建立前已成为各国一体遵守的通例,但还没有较多的全球性条约或者国际法文件对其进行确认。然而,在联合国建立后,上述的一系列全球性的国际法文件都对民族自决权进行了明确的肯定和提倡。因此,法律确信在此间期间得到了显而易见的确立。从这个角度看,民族自决权在联合国建立前更多地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权利,而在1945年后开始正式成为国际习惯法,成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
上述文件中,除了1952年《民族与国族自决权》的决议只是确认“非自治领土及托管领土”上的民族享有自决权之外,其他文件都认为“所有民族”皆享有民族自决权。即使是1952年《民族与国族自决权》的决议,它也没有明确排除其他民族拥有自决权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因此,从文义解释的角度看,联合国大会不是要将民族自决权的范围局限在殖民地、托管地或者非自治领土上的民族,而是希望确认民族自决权适用于所有民族。这基本体现了威尔逊和列宁所持的观点。
不过,联合国大会在确认民族自决权具有普遍性的同时,也非常强调该权利的行使不能威胁国家主权。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和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都明确规定了这一点。这说明国际社会在当时已经意识到该权利对国家主权可能产生的严重威胁。然而,上述规定更多地只是一种政治表态,没有具体的预防和解决办法。之所以没有具体的预防和解决办法,一方面是缘于该问题本身固有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种威胁在当时并不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在非殖民化运动中,民族自决权主要被应用于殖民地、托管地或者非自治领土上的民族,而这些民族脱离宗主国或者托管国宣布独立,不会被认为对任何国家的主权产生威胁或者损害。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对这一点的认识几乎是统一的。在上世纪后半叶殖民地的独立过程中,国际社会罕有关于损害宗主国或托管国国家主权的指责。于是,在冷战结束之前,或者说在非殖民化运动接近尾声之前,民族自决权对国家主权的威胁或者损害并没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四)冷战之后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开始成为焦点
应当承认的是,非殖民化运动至今尚未完全结束。不过,当人类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殖民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与此同时,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世界上许多地区曾经被长期掩盖或压制的民族矛盾骤然变得尖锐。其中,很多地区都以民族自决权作为依据要求行使民族政治分离权,而这些地区中的绝大多数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托管地或者非自治领土。换言之,冷战结束之后,民族自决权在当代的主要适用对象已经超出了非殖民化的范畴。
在超出非殖民化范畴之后,民族自决权仍然被频繁地运用在各种国际实践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当今世界不断出现以民族自决权为法律依据的“独立公投”,如2006年南奥塞梯脱离格鲁吉亚、2008年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2011年南苏丹脱离苏丹、2014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以及1995年加拿大魁北克“独立公投”和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等等。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当时民族自决权主要被适用于非殖民化运动。东西方都不认为殖民地、托管地或者非自治领土的独立是对宗主国或托管国国家主权的威胁或损害。然而,当民族自决权走出非殖民化范畴之后,上述共识就被严重的分歧所取代。
尽管在当代厘清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是异常困难的,但回顾民族自决权的发展历程就可以看出以下一个历史规律,从而能够为解决今天的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这个历史规律是,每当民族自决权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它的内涵都会发生一次重大的更新,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以适应当时国际社会的历史环境。
从冷战结束到今天,民族自决权需要在完成非殖民化的历史使命之后进一步发展,尤其是解决如何协调它与国家主权之间关系这个在当代非常突出的问题。因此,根据上述历史规律,民族自决权的内涵在当代应得到及时的更新,以符合国际社会的需要。
二、应当更明确自决权的主体资格与行使条件
(一)“民族”与“人民”的辨析及其当代主要特征
《联合国宪章》第1条和第55条都使用了“人民(people)”这个词,而不是“民族(nation)”。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文件中也有类似情况。1952年《民族与国族自决权》的决议要求“支持一切人民和民族的自决权”;1960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采用“人民”这个措辞。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确认“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规定的是“各人民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之原则”。由此可见,无论是《联合国宪章》,还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重要文件,主要使用“人民”这个词,而不是“民族”。
然而,在联合国成立之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都更多使用“民族”这个词。这也是“民族自决权”这个法律术语的由来。例如作为详细论述民族自决权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权威人物之一,列宁在190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就使用“民族”一词,并且始终如此,包括后来1914年的《论民族自决权》和1916年的《论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
之所以会有“民族”与“人民”两种对自决权主体不同的理解,是因为自决权在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正如列宁所说:“在西欧大陆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所包括的是一段相当确定的时期,大致是从1789年到1871年。这个时代恰恰是民族运动以及民族国家建立的时代。这个时代结束后,西欧便形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体系,这些国家通常都是单一民族国家。”⑥《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4页。因此,在民族自决权从学说变成实践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区分“民族”与“人民”。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多民族统一国家开始越来越多。尤其在殖民体系之下,原来的民族观念被打破和重构。于是,殖民地上的民族在觉醒之后所形成的“民族”可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以语言、文化、宗教或者种族为纽带的“民族”,而可能是以反对宗主国或侵略国的压迫为纽带而团结起来的崭新“民族”。因此,当多民族地区摆脱外国统治,寻求独立时,就有必要在特定历史阶段内区分“民族”与“人民”。
不过,在今天,当谈及自决权时,实际上“民族”和“人民”都是可以使用的,因为在21世纪,绝大多数的主权国家不再以所谓“民族的纯洁性”来标榜自己的正统,而是承认和倡导多民族的融合与共生。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民族”和“人民”开始打破18世纪到20世纪那种泾渭分明的区分,而出现了可以互通的语意。换言之,“民族”一方面可以保持传统意义上的狭义概念,例如汉族、斯拉夫民族等,另一方面也可以泛指构成某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例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
应当强调的是,在当代,无论是使用“民族”还是“人民”,其必须具有一定的特征才能拥有自决权。199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进一步研究人民权利的概念之国际专家会议最后报告和意见》对此做出了比较好的诠释:“为了寻求国际法上的权利,包括自决权,构成人民的团体应当具有以下特征:(a)该团体具有以下一个或多个共同的特征:(i)共同的历史传统;(ii)种族或人种的身份;(iii)文化上的共同性;(iv)语言上的统一;(v)宗教或者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vi)领土上相邻;(vii)共同的经济生活;(b)该团体的人数不用很多,但不能仅仅只是某个国家内部一些个人的联合而已;(c)该团体作为整体愿意被认定为人民,或者具有成为人民的自觉意识,但仅仅具有前述特征本身并不代表具有这样的意愿或者意识;(d)该团体必须具有相应的机构或者方式来展现或表达他们共同的特征和身份认同的意愿。”⑦Final 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of an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Experts on Further Study of The Concept of The Right of People for UNESCO,SNS-89/CONF.602/7,22 February,1990.
(二)民族自决权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才能被实际行使
具备上述特征的民族只是拥有行使民族自决权的资格,并非当然地可以行使该权利。除了包括宪法在内的国内法的合理制约外,还需要满足国际法上的某些条件,该民族才能实际行使自决权。
受到殖民统治或者外国占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在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内部,某个地区的人民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行使国际法上的自决权?对这个问题,国际法上目前是有争议的。在诸多意见中,值得注意是,将民族自决权区分为内部自决权和外部自决权的学说在西方有较大影响力。所谓外部自决权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政治分离权。同时,如果一个民族愿意与其他国家联合或者并入其他主权国家,那么它可以在该国家里行使内部自决权,即各种形式和程度的自治。考虑到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的必要性,一个民族的外部自决权应当受到限制。⑧Antonio Cassese,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73-74.在限制外部自决权的考虑下,所谓“救济性分离权”就成为一种妥协的方案。根据该理论,当且仅当一部分群体受到一定程度的不公正待遇时,那么作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种救济方法,民族自决权所产生的国家分裂权将会是最后手段。⑨See Allen Buchanan,Theories of Secession,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26,No.10,1997,p.31.
对于是否存在“救济性分离权”的问题,国际法院在2010年做出的《关于科索沃独立问题的咨询意见》中以超出联合国大会所提出的问题为由不予回答。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在“各人民享有平等权利与自决权之原则”下有这样的规定:“以上各项不得解释与授权或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局部或全部破坏在行为上符合上述各人民享有平等权及自决权原则并因之具有代表领土内不同种族、信仰或肤色之全体人民之政府之独立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冷战结束后,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了上述规定。著名国际法学者安东尼奥·卡塞斯将上述规定反过来理解,即“如果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是‘代表’其全部人口的,就是说他允许任何群体平等地参与政治决策进程和政治机构,特别是它不以种族、宗教或肤色为由拒绝任何群体参加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就是尊重自决原则的。其结果是,只有当政府以种族、宗教或肤色为由拒绝任何群体参政时,这些群体才有权主张(外部)自决权”。⑩Antonio Cassese,Self-determination of peoples:A legal Reapprais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112.尽管“国际法尚未肯定也未否定救济性分离权”,①赵建文:《人民自决权与国家领土完整的关系》,《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但用救济性分离权来限制外部分离权的滥用可以成为更新民族自决权的发展方向之一,尤其是当某地区的人民被拒绝参与国家治理,甚至遭遇严重人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换言之,这可以成为民族自决权能被实际行使的重要条件之一。
三、应当更强调对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保障
(一)单方面的武力行为应当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
在非殖民化运动中,作为国际习惯法的民族自决权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对于殖民地、托管地和非自治领土上的民族如何行使自决权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但除此之外的“所有民族”,几乎只是确认它们有自决权而已。
具体来讲,《联合国宪章》第11章“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第12章“国际托管制度”以及第13章“托管理事会”对于托管地和非自治领土上的民族如何行使自决权做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
更重要的是,殖民地人民既可以通过和平方式争取独立建国,也可以通过武力方式达到该目的。换言之,“联大的多项决议、联合国实践和非殖民化进程中的国家实践都确认了殖民地人民或解放运动使用武力的合法性”。②王忠宝:《论国际法上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7页。例如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1974年《侵略定义》和1987年《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等一系列国际文件都做出了相关规定。不过,殖民地人民“使用武力的条件是他们要求自决的行为遭到有关国家‘强制行动’为措施的阻挠”。③参见黄瑶:《正义战争论对现代国际法及国际实践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然而,一旦脱离非殖民化的范畴,由于国际法的相关规定捉襟见肘,是否可以单方面使用武力寻求独立就成为比较模糊的问题。毫无疑问,单方面使用武力寻求独立是对国家主权的直接威胁之一。
联合国之所以允许殖民地人民使用武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国际关系,因此不属于宗主国的内政问题。既然是一种国际关系,那么可以直接受到国际法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从联合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非殖民化运动的巨大影响力,尤其是一大批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在当时的背景下,允许殖民地人民使用武力寻求独立是特殊的历史遗迹。
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不同,多民族国家的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国内关系而非国际关系。因此,解决两者冲突的法律依据应当首先是包括宪法在内的国内法,然后在特定情况下才是相关国际法。在处理国内关系上,国际法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的——除了不干涉内政之外,也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冷战结束之后,多次以自决权作为依据的武装分离冲突中,联合国都要求禁止使用武力。例如在格鲁吉亚冲突中,联合国安理会在1993年通过第876号决议,要求各方停止使用武力;④See UNSC Res.876(19 October 1993),UN Doc.S/RES/876.又如,在前南斯拉夫地区,联合国安理会在1994年通过第959号决议,要求冲突各方和相关其他方面,尤其是塞族武装分子停止采取任何敌对行动;⑤See UNSC Res.959(19 November 1994),UN Doc.S/RES/1203.再如,在科索沃问题上,安理会在1998年通过第1203号决议,要求科索沃地区的各派力量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⑥See UNSC Res.1203(24 October 1998),UN Doc.S/RES/1203.事实上,在非殖民化运动以外,联合国几乎没有直接允许或间接鼓励某个地区或者民族在处理国内关系上使用武力。因此,作为更新民族自决权内涵的重要方面,单方面的武力行为应当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即只在对迫在眉睫的实际侵害进行自卫、爆发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等极为少数和极端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武力。
(二)现代国际集体安全机制需要同步改革和完善
在严格限制具有自决权的民族单方面使用武力的同时,必须改革和完善现代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只有国际集体安全制度足以有效和及时地避免或制止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等现实和严重的威胁,民族自决权的行使和解决才能真正进入到和平的轨道。
众所周知,现代国际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是联合国。然而,在冷战结束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除了可能包庇常任理事国或受其支持的国家逃避国际制裁外,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冷战后的迅速凸显使大国一致原则出现了新的弊端——它严重迟滞了安理会应对危机的效率。这种弊端所导致的灾难肇始于卢旺达大屠杀。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专机坠毁引发的仇恨导致卢旺达两大种族(图西族与胡图族)之间的杀戮。在大屠杀后期的1994年6月22日,安理会才以10票对零票(5票弃权)通过第929号决议,授权法国组建维和部队进入卢旺达。然而,此时已有上百万人丧生。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新世纪后,西方开始推行所谓“保护的责任”理论。2001年,加拿大“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保护的责任》的报告,首次提出该理论。根据该报告,所谓“保护的责任”是指主权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人民免遭可以避免的灾难——大规模屠杀、强奸和饥饿。当该国陷于瘫痪且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这样的责任时,为了预防和制止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势,应由国际社会承担该责任。引人注目的是,该报告认为,如果预防措施不能解决或遏制相关局势,国际社会在极端情况下可以进行军事干预。在需要进行军事干预时,应首先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进行。在安理会不能形成决议时,应由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一致共策和平”方式或者由区域组织利用“区域办法”进行干预。在上述办法均未能实施时,则可由个别国家或者临时性国家联盟进行军事干预。⑦Se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at http://www.responsibilitytoprotect.org,16 June,2015.。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第6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这份文件对“保护的责任”进行了重大修正。它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军事干预必须得到安理会授权,即只能在在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第二,军事干预的理由只有四个——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此外,《世界首脑会议成果》还明确规定,无论是军事干预还是非军事干预,主导权在联合国,而非区域性国际组织或个别国家。
在经历了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危机等地区性动摇情势之后,人们认识到《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上述主张是正确的和积极的。于是,问题的焦点又回到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上,因为只有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危机,才能真正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避免以美国和北约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性国际组织擅自实施军事干预。更重要的是,也只有依靠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保障,才能实现民族自决权的和平行使与对国家主权进行合理监督之间的平衡。
四、应当更重视内部自决权在当代的重要意义
(一)外部自决权与内部自决权在当代重要性的调整
尽管《联合国宪章》第1条和第55条确认自决权的存在,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让所有的民族都脱离自己的母国,建立民族国家,而是希望各民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而这种“友好关系”更多地应当落实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上。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民族自决权的内涵不限于政治独立,而是有更加广泛和综合的内容。只不过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由于非殖民化运动的历史特殊性,政治独立被作为那个时代民族自决权的主要方面。因此,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应当将内部自决权提高到更重要的层面来看待。正如艾伦·布坎南教授所说的那样:“更加明确和可能有结果的做法是将精力集中在各种不同的途径上,即当地的团体通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政治自治来实现自决。”⑧Allen E.Buchanan,The Right to Self-Determination:Analytical and Moral Foundations,Arizo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Vol.8,No.2,p.50.
无论是限制外部自决权的滥用,还是保障内部自决权的实施,遵循法治原则都是一个有效和合理的途径。在这方面,应当注意联合国大会2007年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其第3条规定:“土著人民享有自决权。基于这一权利,他们可自由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谋求自身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其第46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1、本《宣言》的任何内容都不得解释为暗指任何国家、民族、团体或个人有权从事任何违背《联合国宪章》的活动或行为,也不得理解为认可或鼓励任何全部或局部分割或损害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的行动;2、在行使本《宣言》所宣示的权利时,应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本《宣言》所列各种权利的行使,应只受限于由法律规定的限制,并应符合国际人权义务。任何此种限制不应带有歧视性,而且绝对是必需的,完全是为了确保其他人的权利与自由得到应有的承认与尊重,满足民主社会公正和最紧要的需要。”
显而易见,上述第46条第1款是对第3条的限制即土著人行使自决权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不得对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构成威胁或造成损害。这实际上就是限制外部自决权,也就是民族政治分离权。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第46条第2款要求民族自决权的行使必须受限于由法律规定的限制。换言之,应当强调民族自决权的“依法行使”。
在民族自决权的晚近实践中可以看到,如果强调国内法治,包括宪法的崇高地位,那么民族自决权的行使就能在和平有序的轨道内运行。魁北克分别于1980年和1995年举行的“独立公投”以及苏格兰在2014年的“独立公投”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当然,有效的国际监督也是必要的。然而,以法治以外的方式单方面要求行使民族自决权可能会对国家稳定和人民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二)应当进一步推动民族区别的淡化和区域一体化
在吸取历史教训之后,人类开始认识到民族平等对于世界和平的极端重要性。于是,联合国在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第2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并且不得因一人所属的国家或领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国际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他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从20世纪中叶至今,国际社会在消除各种歧视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尽管不同形式和程度的民族歧视至今仍然存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区别的淡化对于推动民族融合和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正在和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也为内部自决权的落实和完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此外,在冷战结束之后,人类迎来了区域一体化的新趋势。区域一体化既是淡化或消除民族区别的“良药”,又是强化内部自决权、避免民族政治分离权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欧盟无疑堪称典范。
1993年11月1日,《欧洲联盟条约》正式生效,宣告欧盟从此建立。根据该条约第G条第C款,原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增加了第8条。新增的第8条规定,“特此建立欧盟公民身份。具有成员国国籍的每一个人都是联盟的公民”。由此可见,通过建立“欧盟公民”的新身份,欧盟试图从身份认同上消除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区别。这一点非常重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高涨的基础之一是被过分强化的民族身份认同。反过来,假如能够构建一个不以民族区别作为依据的身份认同,那么这对民族主义无疑是釜底抽薪。尽管国家可以通过民主宪法构建起“公民”的身份,但由于各国国情不一,“公民”之间也有可能被区别化。例如,“在1981年《英国国籍法案》颁布之后,英国仍然有6类地位不同的公民:英国公民、英国属土公民、英国海外公民、英国臣民、英国海外国民和受英国保护人士”。⑨Rieko Karatani,Defining British Citizenship:Empire,Commonwealth and Modern Britain?,Routledge,2003,p.180.很显然,在区域一体化中,欧盟公民的新身份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上述区别所带来的分歧。实际上,区域一体化的过程就是打破原来以族群认同感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我们”,用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我们”取而代之。换言之,近现代的民族主义者就是通过族群认同感将人民区分为“我们”和“他们”,从而达到民族区分、民族对立,甚至引起民族仇恨的目的。尽管这是当初民族主义者所使用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却同样可以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身份认同。
除了身份认同之外,在区域一体化的宏观背景下,西欧国家还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和挑战。这既包括来自国内地方自治要求的压力,也包括来自国家之上的超国家管治的压力。超国家层面上的欧盟和次国家层面上的各种区域性地方性制度主体在不断侵蚀着原属于民族国家权能的同时,政治活动日趋活跃。⑩参见翟金秀:《欧洲一体化背景下的当代西欧民族主义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2页。就此而言,人们完全可以说,西欧已经迈入了一个后民族国家时代,或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所指称的“后民族格局”时代。①参见[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于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民族国家的诞生地欧洲又率先成为国家之间民族融合的先行者。无论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是广泛的民族融合,还是更多的民族藩篱,它都会使民族自决权朝着更加强调内部自决权的方向发展,因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动因就是寻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三)内部自决权应当充分重视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
在内部自决权的制度构建中,还应当充分重视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这是因为多数民族的意见可能压制少数民族。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例如在1995年魁北克“独立公投”之前,魁北克的印第安人先期举行了一次投票,结果是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决定:即使魁北克独立,他们也要留在加拿大。面对印第安人的公投结果,独立派领袖马上指责印第安人的公投结果是非法的,因为那片土地属于魁北克。然而,倘若对地区少数派的不同意见置若罔闻,那么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波黑主要有三个族群,即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克族和穆族要求波黑脱离南斯拉夫宣布独立,塞族则反对波黑独立。1992年,穆、克两族举行关于独立的公投,而塞族不同意,并且宣布塞族控制区从波黑分裂出去,波黑内战由此爆发。魁北克印第安人和波黑塞族的例子都说明,如果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和诉求,那么内部自决权就无法真正落实,并且可能会导致少数民族不得不转而寻求外部自决权。
值得指出的是,强调内部自决权的重要性,并不是意味着就可以完全剥夺少数民族在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寻求外部自决的权利。这是因为如果少数民族被牢牢地封锁在内部自决权中,那么多数民族就不会再有任何动力去与少数民族开展有关自决权或者重新分配权力的对话了。②See Anna Moltchanova,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and Justice in Multinational States,Springer,2009,p.147.因此,保留和尊重符合国际法的外部自决权本身实际上是对内部自决权的监督与促进。
五、结语
民族自决权的发展历经了不同的阶段。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叶,西方思想家将抽象的民族自由逐渐转化为对主权的追求。于是,民族国家在西欧率先建立起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空前高涨,民族自决权开始适用于所有民族。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随着非殖民化运动进入高潮,民族自决权被主要应用于殖民地、托管地和非自治领土上的民族。然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非殖民化运动进入尾声,民族自决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开始成为焦点。因此,为了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当代,民族自决权的内涵应当及时更新。
作为内涵更新的主要内容之一,有自决权的“民族”应当在自身特征和权利行使条件上受到更多和更明确的限制。同时,当今的时代主题已经变为和平与发展,因此,应当更加强调和落实对国家主权的保障。为此,在严格限制单方面使用武力的同时,必须同时改革和完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代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同样,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在当代既要限制外部自决权,也要将内部自决权提高到更重要的层面看待。遵循法治原则、淡化民族区别、促进区域一体化以及重视少数民族的利益诉求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
(责任编辑:闻海)
D F94
A
1005-9512(2015)09-0132-11
张磊,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东政法大学人权与人道主义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当代民族自决权的流变与中国的外交立场研究”(课题编号:2014BFX 006)和中国法学会研究课题“冷战后民族自决权与当代民族矛盾的内在联系研究”(课题编号:CLS(2014)D 1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