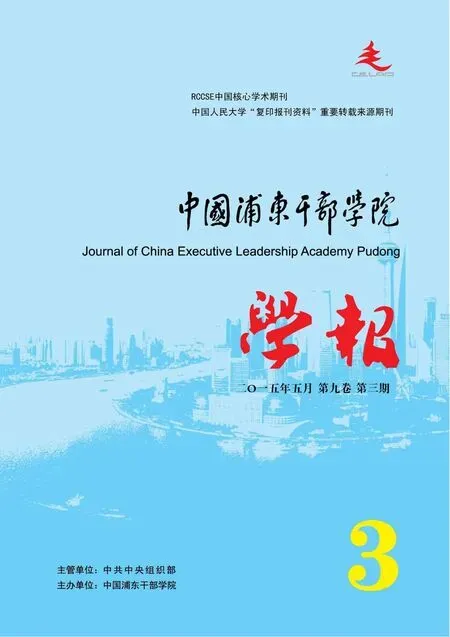略论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分野
刘志伟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9)
略论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分野
刘志伟
(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北京100089)
从权利主体、权利结构、权利目标和权利归属等方面,可以区别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分野。在权利主体方面,分别以“人与物关系”和“人与人关系”为基础;在权利结构方面,分别体现主体之间“平等”和“不平等”关系;在权利目标方面,分别以“均衡”和“非均衡”为追求目标;在权利归属方面,分别以“个人本位”和“集体本位”为归属。
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法治建设
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是人类社会两种显性权利。厘清二者分野,对于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掌控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为人类福祉服务,对于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社会经济与政治改革,建立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社会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权利主体:“人与物关系”和“人与人关系”分野
(一)经济行为主体存在的基础是人与物之间的权利关系
众所周知,经济权利中最核心的是“产权”,而人与物的权利关系则是产权存在的基础。产权包含一组权利束,即“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处置权)等的集合,这些基本权利都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基础上。产权的内涵,也就是产权主体可以通过自己对物的自由支配权利而获得自己与之相关的经济利益。因此,产权在现代经济学体系中就是研究由于人对物的这种权力和利益,以及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由于对物的不同配置,进一步所导致的人与人的关系。产权对于现代经济发展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产权具有使外部性内部化作用。“外部性”即一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其他经济主体带来无偿收益,或给别的经济主体造成无需赔偿的损失。外部性能够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尤其是在“负外部性”情况下,侵害主体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其他成本则为社会所承担,特别是由直接被侵害方所承担。从产权角度看,外部性是一个新权利的出现,在原有的产权格局下,产权主体的行为却产生了新的权利(责任),如果对这种新的权利设置了产权,那么就既不是“外部性负效应”,也不是“外部性正效应”,而是“外部性内部化”。
第二,产权具有激励和约束作用。产权如果界定清楚,产权主体的努力就会得到明确的收益,而且这种收益具有明确的可预期性。产权提供的激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促使个人努力的内在机制。产权使个人努力和资源产出最大化一致起来。同时,产权激励不仅对产权主体来说是有利的,对产权主体所拥有的资源效应最大化也是有利的。因此,产权促使了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产权激励还促进了产权主体对自身行为的有效约束,因为产权主体不适当地使用产权会使产权的价值受损,从而产权主体得不到产权的利益。产权既决定了产权主体能够做什么,又决定了产权主体不能做什么,产权的这种约束从而也刺激产权主体尽最大努力去优化资源配置。
第三,产权具有降低不确定性作用。经济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人类社会复杂的各种经济活动,任何人的知识能力和判断能力都是有限的。市场价格是供求双方均衡的结果,供求双方竞争的过程充满了各种非人力所能统计的变量,从而导致结局难以明确预期。供求双方各自都只掌握非常有限的知识和信息,做出的决策也不可能完全正确。同时,相对于人的主观偏好而言,商品世界又是不确定的。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易是个人权利的交换,以权利的交换获取自己的利益,而不同主体对权利的评价也都是不同的,在人们交换过程中也就充满了大量不确定性。而产权的界定,就不仅使得产权主体知道自己权利的边界,并可以预测自己产权的总体承担能力,而且使得产权主体可以明确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能获得的收益,从而对自己的收益具有了明确的预期。
(二)政治行为主体存在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人是在与他人的社会联系和合作过程中,即“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体现人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P2)人的这种社会性本质属性意味着人并不是孤立的人,而总是生活在与他人特定联系之中。一切政治行为主体存在的基础都是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权利体系。
从权利发生学角度分析,政治权利是人与人之间权利关系的产物。回顾人类社会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在脱离动物界以后的原始社会初期,生活于社会原始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由于生存需要、调解纠纷需要,从而必然促使他们中一些人,或者成为原始群体中拥有指挥权、分配权的领导者,或者成为原始群体中受指挥、受分配的被领导者。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2](P218)
政权是人类社会政治权利的集中体现。从政权客观和主观构成要素来看,政治权利本质属性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
第一,政权的客观构成要素是人与人之间权利关系的产物。众所周知,政权形成的基础是人们的利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形形色色的利益,然而,利益的实现和维护并不是一个自发过程,而是利益主体自觉和能动的活动过程。人们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权利主体必然尽可能地调动各种有效资源,并且把这些资源凝聚成权利主体借以展开谋取自身利益的实际力量。那么,这种外在于权利主体的力量就成为其客观构成要素。从力量对比关系来看,显然“群体”这一具有社会性属性的力量较之“个体”具有天然优势,即所谓“人多势众”。因此,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基于利益的需要而自觉与不自觉地形成立场、目标、价值取向相对一致的社会利益集团,这些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基本政治格局,如阶级、政党、利益集团等等,正是这些社会利益集团构成了一切社会政治权利的客观要素。
第二,政权的主观构成要素也是人与人之间权利关系的产物。政权的主观构成要素主要包括法规制度、思想观点、政策策略、理论范式和政治领导者能力素质等等。仅以“能力素质”这一主观构成要素而言,由于权利主体有个体和群体之分,因而权利主体的能力素质也有“个体能力素质”与“群体能力素质”之别。“个体能力素质”主要体现在权力主体的知识水平、品德修养、经验阅历、性格意志、分析判断能力、领导决策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革新创造能力等方面,而“群体能力素质”则除了包括组成群体的各个个体的能力素质之外,更多地体现在群体立场的统一、群体目标的协调、群体价值取向的认同等方面。显而易见,无论是个体能力素质,还是群体能力素质,二者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们都是在人与人交往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积累和不断提高的,也都是人与人之间权利关系的产物。
二、权力结构:“平等”与“不平等”分野
(一)市场经济行为主体之间是“平等关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也就从社会身份、所有权和行为自主权等三个方面,内在规定了人与人之间主客体关系表现为一种相互平等的社会关系。
第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与人之间在市场交易活动过程中互为主客体,他们都是平等的交易者。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生产方式,在这一经济活动过程中,每个商品交换者所关注的焦点,在于被交换商品的自然特性和个人自身对于商品的自然需要,而并不关注交换者本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商品交换者相互之间都视为平等交换者,都承认对方为被交换商品的所有者,都是自愿出让被交换商品,从而满足各自对不同商品的需求。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外在于这一交换行为的其他社会身份和地位都是不存在的,人们在这一交换过程只存在一种社会关系,那就是“平等的交易者”。马克思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3](P197)
第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与人之间在市场交易活动过程中都是各自所需交换商品的完全平等的所有者,他们都平等地拥有支配自己所需交换商品的权利。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经济制度、运行机制或运行方式,而这一配置过程又是通过市场交易活动的方式实现的。任何资源如要介入到这一交易过程之中,从而在商品的相互交换中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首先就要求每一个交易的参与者必须拥有资源或商品的所有权。从表面上看,市场经济的运行表现为商品相互交换的过程,但是从深层次上看,这一商品交换过程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被交换商品所有权的交换过程,是人们对被交换商品所有权的丧失和获得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深刻指出的:“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他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4](P102)因此,没有了被交换商品的所有权,也就没有了商品交换的活动。
第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与人相互之间拥有平等的、完全的自由支配自己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利。在市场经济过程中,这一权利表现为人有权利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生产要素包括自身知识、智慧等广义人力资本,按照自己真实意愿投入到他认为能够给自己带来利润回报的某些生产领域。这一权利不仅保证了人们所具有的生产要素的最大发挥,而且也使人有可能自由发展和完善自身。人类社会一切经济活动都围绕“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三大基本问题展开。生产者追求的是自身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需求满足,从而各自表现为一定的供给决策和需求决策。经济主体拥有平等地、完全地自由支配自己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这一权利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没有人们平等的、完全的自由支配自己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权利,也就没有各种资源的不断流动,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存在。因此,恩格斯指出:“只有能够自由地支配自身、行动和财产并且彼此处于平等地位的人们才能缔结契约。”[5](P76)
(二)社会政治行为主体之间是“不平等关系”
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曾经指出:“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体的文化体制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把统治他人的权力赋予某些人(他们被称为‘权威’),并强迫被统治者必须服从后者。”[6](P116)美国政治学学者汉斯·格斯和怀特·米尔斯更直截了当指出:“如果人人平等就不会有政治,因为政治本身就包含着上下级。”[7](P193)
第一,从微观层面看,人与人相互之间在社会权利结构体系中所处具体位置的不同,即社会角色的等级性,决定了他们相互之间不平等的关系。政治权利是一种相对严密、有序的社会系统结构。一种政治权利,总是由若干部门、层级和岗位构成的统一体系,各个部门之间、各个层级和各个岗位之间形成纵横交错的权利依存关系。在这种权利的等级序列中,上级总是以下级构成自身存在的基础,权利主体总是以权利客体作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如此一来,居于不同权利等级的人们便有了职务等级之别和权利大小之分,这就客观地、外在地决定了人与人相互之间形成了制约与被制约的不平等关系。上级具有指挥、支配下级的权利,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指示,即政治主体是制约者而政治客体成为被制约者,从而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呈现出自上而下运行的流程。
第二,从宏观层面看,以国家权利为核心的政治权利所具有的特殊强制性,决定了社会政治行为主体相互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任何权利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否则也就构不成社会政治行为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关系。但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不同类型的权利,其强制的形式和手段却是各不相同的。在此,所谓“特殊强制性”就是指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权利主体可以通过系统地、有组织地使用暴力对政治客体进行强制,即运用法律、法规等制度化的暴力工具,通过剥夺人们的荣誉、财产、自由乃至生命等强制性手段来推行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相对于以掌握暴力工具为支持的政治行为主体——“国家机器”,那些没有掌握暴力工具的政治行为主体显然就处在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之中。
三、权利目标:“均衡”与“非均衡”分野
(一)经济行为主体以追求“市场均衡”为目标
所谓“市场均衡”,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的解释是:“在每一时刻,都有无数的因素影响着经济活动。……然而,在所有这些混乱之中,市场正在不断地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当市场平衡了所有影响经济的力量时,市场就达到了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所谓市场均衡,代表了所有不同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种平衡。居民户和企业愿意购买或出售的数量取决于价格。市场找到了正好平衡买者和卖者愿望的均衡价格。价格过高意味着产量太多的物品供过于求,价格太低引起物品的供不应求和短缺。在某一价格下,买者愿意购买的数量正好等于卖者愿意出售的数量,这一价格就产生了供给和需求的均衡。”[8](P66-67)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均衡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萨伊的“萨伊定律”,再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过程。这一观点认为,市场机制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每一个行为人(消费者和生产者)去追求各自最大的利益,在市场价格灵活而迅速的调节下,各个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总能正好相等,即所谓“市场出清”。
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理论”,把市场均衡的概念落实在一组明确而严密的数学方程上,从而发展成为一套日趋缜密完善的理论体系。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又与萨伊定律密切相关。萨伊定律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所概括总结的。他认为,经济主体能够预见市场的发展和情况,从而提出了供给创造需求、产品是以产品购买的原理,即“萨伊定律”。萨伊指出:“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在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将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9](P144)在萨伊看来,卖必然引起买,卖与买是平衡的,供求总是自动地趋向一致,因而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存在的。
瓦尔拉斯正是在萨伊定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这一理论主要运用近代数学方法,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上,分析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进而建立起了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第一个一般均衡分析经济模型。一般均衡分析经济模型以人们既定收入分配方式为前提条件,它设定在一个以利己动机驱使下从事经济活动的社会中,商品消费者力图在收入的限制下取得最大效用,商品生产者力图从经营中得到最大利润,资源所有者则力图用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换取最多回报。面对着这样一个社会,瓦尔拉斯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关于均衡价格和数量问题,即在包括产品和资源的各种市场上,是否存在着一系列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使每个消费者、生产者和资源所有者都能实现他们的目的。二是关于均衡价格和数量稳定性问题,即如果均衡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果然存在,那么这种均衡是否具有稳定性。瓦尔拉斯进而以四个联立方程组解答了这两个问题。第一组方程表示,每一种资源的所有者所提供的资源数量取决于一切资源和商品的价格。第二组方程表示,对每一组商品的需求量取决于一切资源和商品的价格。第三组方程表示,每一种劳务的供给量等于生产全部商品所需要的消耗量。第四组方程表示,每一种商品价格等于它的成本。瓦尔拉斯认为,不但上述方程式具有均衡解,而且方程所决定的均衡也是稳定均衡。这就意味着,一旦经济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市场力量就会自动对经济制度进行修复,使之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因此,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到萨伊的“萨伊定律”,再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市场均衡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危机不断爆发,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出现持久、全面经济危机,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市场均衡理论开始产生质疑。1936年,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从如下三个方面质疑:一是在劳动市场上存在非自愿失业,这就表明至少有一个市场是处于供求不相等的非均衡状态;二是市场调节不仅通过价格来进行,货币调节也同样重要;三是社会行为主体不仅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也对诸如收入水平等数量信号做出反应。1937年,凯恩斯又发表《就业的一般理论》,进一步批驳了市场均衡理论有关货币的职能仅仅是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观点,再次指出货币除了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充当储藏财富的手段。他强调,货币储藏财富的职能是通过利率的形式而对投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就业、产出和国民收入。他在此基础上认为,仅靠“价格调整”只能使社会经济处于完全未出清的状态,即有效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实现的生产能力小于潜在的生产能力。凯恩斯主张,只有依靠“收入-支出”的方法进行调整以扩大有效需求,从而使有效需求逐步调整到与总供给相一致的程度。因此,社会经济中出现非均衡的矛盾现象是一种通例,市场均衡才是一种特例,人们应当面对社会经济中非均衡的现实,努力分析情况以寻找应对之策。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学界逐步在凯恩斯非均衡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非均衡学派”,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曾经使用“非均衡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均衡”等多个概念称呼自己的理论,其代表作是1982年出版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贝纳西接受了凯恩斯的“市场未出清”的观点,但又并不认为市场经济处于“完全未出清”状态。与凯恩斯不同的是,他认为市场未出清状态只是就市场经济某些局部区域而言的,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有些区域可能同时处于出清状态。[10]
现代经济学市场均衡理论虽然受到巨大挑战,然而,如果认为市场均衡理论就此被推翻则大谬不然。一方面,应承认市场均衡理论的确存在一些明显不足,例如,这一理论把“物物交换”完全等同于“商品交换”,否认了由于货币参加流通使买与卖在时空上都可以发生分离,从而具有产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应认识到,市场均衡理论仅仅是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理想状态的一种描述,即它运用“应然分析”方法对市场经济的内在约束机制进行描述,而非均衡学派则运用“实然分析”方法,对市场经济动态运行中的实际状态进行描述,并努力寻求达到市场均衡理想状态的种种对策。两个学派各自立足于不同角度对市场经济运行状态进行描述,因而不应简单地彼此否定。贝纳西一再强调:“我们应注意,非瓦尔拉斯方法并不是‘反瓦尔拉斯’,相反,它只是在更为一般的假设下应用那些在瓦尔拉斯理论中一直很成功的方法。”因为,“我们需要一种如瓦尔拉斯方法一样的一般性方法,它能兼容各种现实的价格机制和预期机制”。[11](P338)所以,市场均衡学派与市场非均衡学派并不存在根本观点的矛盾对立,两个学派在追求市场经济体系均衡运行的目标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二)政治行为主体以追求“权力非均衡”为目标
与经济行为主体追求实现市场交易活动的“均衡”状态为目标截然不同的是,政治行为主体则以实现政治权力活动的“非均衡”状态为目标。政治权利“非均衡”现象的产生,来源于政治权利主体同时并存着“权力”与“权威”这样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影响力。权力是权威得以成立的基础,没有权力这个前提,权威就无从谈起。然而,权力又不等同于权威。就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的关系而言,权力是指权利主体支配、控制权利客体的行为能力,权威则反映的是权利客体对于来自权利主体的支配和控制合法性的认同程度。权力与权威虽然都是权利主体所拥有的一种影响力,但是权力反映的是权利主体自身的一种能力,它表现为权利主体外在的、强制性的影响力;权威则是权利主体的能力在权利客体上的反映,它表现为权利主体内在的、非强制性的影响力。
权力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它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权力“有限性”是其社会属性的基本规定性。相反,权威反映的是权利客体对于来自权利主体支配和控制合法性的认同程度,也就决定了权威具有“无限性”这一本质特征。换言之,就权利客体对于权利主体的服从程度而言,在坚决反对、拒不服从到心悦诚服、坚决服从,乃至献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辞地服从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无限发展的广阔空间。权力有限性与权威无限性,即权力与权威非均衡现象,成为人类社会政治行为中客观必然现象。
四、权利归属:“个人本位”与“集体本位”分野
(一)经济行为主体以“个人本位”作为权利归属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在社会经济个体活动的微观基础之上,在其经济结构内,每一种经济资源、每一项经济活动、每一个经济区域,都无可避免地要融入统一市场体系之中,而活跃在这一市场体系中两大经济行为主体:一个是企业,一个是个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企业,还是家庭,或者个人,人们经济活动都是以“个体”为基本单位,即使是一个员工众多的企业,它在参与社会经济交易活动过程中,也必须以个体方式,即单一“企业法人”的方式进行。企业、家庭和个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都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独立拥有财产。拥有“独立财产”是市场主体参与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前提,只有独立拥有财产,市场主体才能独立承担各种相应的社会经济责任,才能得到其他市场主体的信任,才能获得或者购买各种经济资源,才能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也只有“拥有独立财产”,所谓“市场主体”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才不至于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完全受制于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也必须接受法人制度的约束,以其接受委托进行生产经营的财产,独立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第二,独立做出决策。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一切经济决策,都必须由经营者独立自主地做出。在社会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习俗惯例所认可范围内,企业可以独立进行筹资、投资、生产、销售和利润分配,个人或家庭可以独立决定是否参加社会经济活动,从事什么样的生产经营项目,在自己营业收入中多少用于储蓄,多少用于投资,多少用于消费,以及消费什么和如何消费等等。
第三,独立承担风险。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营者独立做出经济决策,相应也就意味着一切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经营者必须自负盈亏,即独立承担一切生产经营风险。决策正确,企业、家庭和个人都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增加自己的财富和资产。若决策失误,市场主体就会因此蒙受损失,企业可能因此破产,进而退出市场竞争,个人或家庭可能因此而丧失部分甚至全部财产,只能靠社会救济度日,市场主体必须为自己独立决策承担责任。
总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行为主体是千千万万企业、家庭和个人,他们以个体方式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有关生产经营的决策都由他们各自独立地做出选择,同时,也就相应地由他们各自独立地承担一切有关生产经营决策所带来的风险。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正是由于以上三个基本特征,也就内在必然地决定了经济行为主体以追求“个人本位”利益作为权利归属。
(二)政治行为主体以“集体本位”作为权利归属
在社会政治行为主体内在必然地以“集体本位”作为权利归属,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治行为主体的政治权力来源于社会公众。从政治管理的角度而言,所谓政治也就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行为主体所拥有的权利,来源于政治行为客体——社会公众的授予和认同。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与企业、个人或家庭以个体方式独立拥有财产权完全不同,政治权利的所有权归属于社会公众,“社会公共性”是政治权利的本质属性。政治权利的社会公共性本质属性,内在必然地要求政治权利必须为社会公众服务。政治行为主体谋取和运用权利的过程,一方面固然表现为政治行为主体主观、能动的行为过程;另一方面,这一行为过程既要受到政治权利的社会公共性这一本质属性的客观制约,还要受到政治行为客体社会评价与合法性认同的客观制约。
第二,政治决策以“多数通过”为基本原则。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一切社会经济行为都是行为主体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的结果,因而经济行为主客体的关系是双向、平等和自愿的;然而,人们在社会政治活动过程中,凡属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政治决策,即社会公共性决策,通常都是以多数通过的方式决定的,一旦某一政治决策通过之后,即使对这一政治决策持反对意见的少数也必须执行,因而政治行为主客体关系是单向、不平等和强制性的。
第三,政治决策的风险是由社会公众共同承担的。在人们社会政治生活中,任何一定区域内社会公共性决策风险,实际上都是由这一区域内全部居民所承担。以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为例,一旦多数社会公民做出了和平或是战争的政治决策,也就意味着这一国家内全体公民相应选择了和平或是战争的决定,进而也就意味着这一国家内全体公民都要相应接受其全部后果。
综上所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以及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一伟大实践进程中,我们就应明确经济权利主体与政治权利主体的分野,从而在社会经济改革和法治建设中,高度重视以产权保护为核心,有效发挥产权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对于经济主体行为的激励与约束作用,有效降低市场经济风险与不确定性;在社会政治改革和法治建设中,高度重视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与政治领导者的能力建设。我们就应明确经济权利结构和目标与政治权利结构和目标的分野,从而在社会经济改革和法治建设中,高度重视经济行为主体之间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确保公平竞争,防止市场垄断,确保经济全过程平稳运行;在社会政治改革和法治建设中,高度重视对社会公共权力的有效控制和约束,坚决将社会公共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我们就应明确经济权利归属与政治权利归属的分野,从而在社会经济改革和法治建设中,厘清经济行为主体的责任、权利与义务,有效建立经济行为激励与惩罚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在社会政治改革和法治建设中,厘清政治行为主体的责任、权利与义务,有效建立政治行为激励与惩罚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M].杨祖功,王大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7]Hans Gerth and Wright·C.Mills,Character and Social Structure,New York:Harcourt and Brace,1953.
[8][美]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4版)[M].胡代光,余斌,张军扩,等,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6.
[9][法]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法]让·帕斯卡尔·贝纳西.市场非均衡经济学[M].袁志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11]方兴起.市场经济宏观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李冲锋]
A Discussion on the Divide of Economic Rights and Political Rights
LIU Zhi-wei
(China Leadership Science Research Center,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Beijing 100089,China)
The divide of economic rights and political rights can b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aspect of rights subject,rights structure, rights objective and rights ownership.In terms of rights subject,th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rights is“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 and thing”but political rights is“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 and person”.In terms of rights structur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equality”and“inequality”is embodied differently.In terms of rights objective,economic rights emphasis“equilibrium”but political rights emphasis“disequilibrium”.In terms of rights ownership,economic rights emphasis“individual standard”but political rights emphasis“collective standard”.
economic rights;political rights;economic reform;political reform;legal construction
D034.5
A
1674-0955(2015)03-0094-08
2015-01-06
刘志伟(1957-),河南罗山人,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