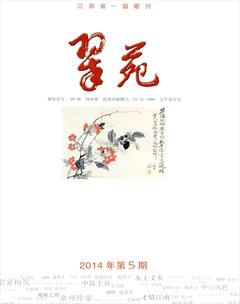路过人间(五章)
眺望的房子
我和他约好在旺角朗豪坊见面。
他是香港的著名诗人,也是我的朋友,偶尔赴港,我总不免惊动他。
我们要去观塘,本来从旺角搭乘地铁颇为便捷,不知为何他竟带我改乘中巴。我说出了我的疑惑。
“你这个大人物来访香港,熟悉了东九龙,也该看看西九龙。”他用不怎么流利的普通话说。
大人物是他对我这个小人物的戏称,我们之间,常常以这种方式相互戏谑。
中巴一路疾驶。窗外掠过一座座巍峨的楼群,也掠过一个个陌生的地名。终于在绕过一座山岭后,我们在兰田下车。忽然他改变主意,提出到他的寓所坐坐。从这里搭地铁也算顺路,我当然不好拒绝。
在去地铁站的路上,忽然看见一个巨大无比的鬼佬胖汉,从人群中巍巍然夺路而来。我从未见过如此伟岸的肥佬,如一座移动的大山。这肥佬若长居于此,一定可以成为此处的地标。以后我若前来拜访诗人的寓所,在此只消远远看见他岿然屹立的身影,就必定不会迷路了。
尽管无数次来港,将军澳我还是首次造访。从车站出来,将军澳这个新开发的社区,虽和香港别处一样人潮涌动,却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安静和疏朗。
我跟随他,穿过叮当作响的斑马线,走向一座叫君傲湾的大厦。
用智能卡开门,穿过长长的走廊,再接受穿制服女管理员的盘问,方才坐上电梯。我说,拜见特首,恐怕也无需如此繁琐和复杂。
他住在9楼。当他掏出钥匙,打开其中的一间,我不免吃了一惊。虽然对香港寸土寸金的住房空间早有所闻,但落实到眼前这个典型的中产阶级身上,仍然出乎我的想象。就像列车车厢的一小节,或是一间屋子被劈成的一半,面前的空间,形成一个长条形,站了两个人,已显逼仄和局促。靠里面是一个双人沙发,对面是一个电视柜,门口则立着一个书柜,整齐地摆满了书。这已是这个空间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布局了。
“没有你住的宽敞。”他打趣道。可是我知道如果栖身香港,恐怕连一间小小的洗手间也供不起。
其实房间里最吸引人的还是他养的那只小花猫,我们一进来,它就迫不及待地扑了上来。我对这只小花猫“久仰”了,我曾无数次听他谈起,每逢外出他总要先为它准备充足的猫粮。一旦外出久了,来不及赶回,他就十分焦急,赶忙让他的妹妹,穿越大半个城,专程去照顾它。
我还没见过如此顽皮的猫,它瘦骨嶙峋,有着尖尖的耳朵、长长的脖子,敏捷得如同一头小豹。它一点也不惧生,我想逗一逗它,它不是扬起爪子向我示威,就是扑过来轻轻咬我的手指。它还一次次将大半个脑袋伸向我放在门口的袋中……
房间虽小,却五脏俱全,卧室、厨房、洗手间一样都不少。他打开厨房的门,里面密密麻麻堆放着各种瓶子。“我从不开伙。”他递了一杯热茶在我手上,语气中透着落寞。
和众多的现代人一样,这些年他的感情之路也一直走得跌跌撞撞,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港产电视剧,他先是和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结发妻子仳离,又和一位写诗的女教师走在了一起。我们都熟识这位女诗人,她衣着入时,身材颀长,他们常常出双入对,一同过境,出现在各种场合。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和他如此登对的女诗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分离。于是,他又恢复了单身,回到了旧有的生活轨道。
这些年,始终未曾与他仳离的是缪斯女神。纵观他漫长的写诗生涯,他的诗风其实一直未曾大变,那些感伤、柔美、敏感的诗句仍然时时从他的心底涌出。
“熟悉的车站总有吹冷的身影”。这是我喜欢的他众多诗作中的句子,也是他为某个咖啡馆的题诗。这难说不是他生动传神的自况。也许诗人注定是孤独的,在这间小小的居所写完一首诗,或者未及孵化出一个梦,他又会出发,奔向车站。车站里,与一个个陌生而又模糊的身影擦肩而过,也难说不会陷入更大的孤独之中。
然而,他又是乐观的,他生性中不乏乐天知命的成分。什么时候,我看见小花猫已经躺在了他的臂弯,这一刻,小花猫很温柔,他也很温柔。
“到阳台看看吧。”阳台狭小,却有极广阔的视野。从这里可以鸟瞰广角的将军澳全景。然而,煞风景的是,一幢拔地而起的高楼,如凌空降落的飞来峰,挡住了视线。
“不过,”我打趣道,“你可以更加近距离地观察香港现实的人生百态了。如果有一个望远镜,观察就更加细致了。”
“我要买那种高倍的。”从阳台上可以看见一侧的人家的厨房,一个主妇正在忙碌。他赶忙声明,“不过,一定要放里面一点。”他就是这样,血液里总是流淌着某种达观、幽默的因子。
很快,我们要赶往北角与他的一位朋友共进晚餐。临走,他送了我一本新世界译本的《圣经》,黑漆软皮的封面书脊上,分别被他贴上了俏皮的卡通人物,其中一个还握着长长的单筒望远镜。
陨石坠落
阔别多年后,在那个夏日的晚上,我们终于又回到了故乡。我和姐姐异常兴奋,顾不上洗脸,也不等妈妈将饭做好,更不去理会爸爸的警告,就各自披上衣服出门了——这多像小时候的情景。可以想象,我们一旦出门,不等到妈妈一遍遍在矿区大院喊哑了嗓子,我们是绝不会回家的。
其实,此刻我们这么急着出门,也不知要去哪里。夜色一点点浓起来,矿区大院也早已亮起一簇簇灯火。我该说,这么多年,矿区可是一点未变,从矿井上来的矿工穿着大雨鞋,依然一身乌黑,从远处就可以感觉他们灼灼闪亮的目光。还有那些早已下班的矿工又攒足了力气,在宿舍门前嬉笑、吆喝,莫非哪个工友的媳妇来探亲了,大家正好借此闹一闹。
矿区在重重大山的夹击之下,形成一个狭长的地形,矿区里的房屋主要就集中在这个狭长地形的尾巴上。不消多时,我们就在矿区里转了大半圈。
姐姐问我,还想去哪里?
我想不起来。
姐姐就说,我们回去吧。
我附和道,好的。
忽然,姐姐叫了一声,伸出手指向夜空。
抬头望,漆黑一片的天幕上,正有一颗颗流星,拖曳着长长的尾巴,急速掠过。间或有掉队的一颗,蓦地一闪,又赶忙向远山追去。
我们呆立着,出神地望着天上的奇景。没有想到,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我们。
随着一声声响亮的呼啸,一颗颗发光物坠落下来。有的在天边,有的在不远处,有的我们即使不知道在何时落下,也能看到远处发出的光亮。这会是什么?对着脚下的光亮,蹲下身来,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陨石,是陨石。这些陨石起初很是灼热,不一会就冷却下来,用手抚摸,竟有光滑、温润的感觉。
我们现在置身于石墙的最东头,矿区的边缘。正是这面高高的石墙,把矿区与外面漆黑的乡村和无边的山野隔开。这里以前有一个开水灶,矿上人们天天前来打开水,家属也常常提了大木盆聚集这里洗衣服,将水花和吵闹声溅得到处都是。不过,可以看出,现在这个开水灶已遭废弃,因处在矿区的一个死角,白日里这里也许还有人走过,此刻则完全被黑夜覆盖,阒无一人。
这时抬起头,夜空已没有刚才那般热闹,恢复了惯常的平静。间或还有一颗星蓦地一闪,拖着一条细细的光线,不知将坠向何方?我们在夜空下伫立很久,开始搜集散落的陨石。
这些陨石有的大如婴儿拳头,小如山间野枣,只一小会,我们就拾到不少,堆积在开水灶一角,竟有小山似的一堆,在眼前发出幽幽光亮,像是黑暗中一簇在燃烧的篝火。
世界愈加黑暗,也愈加沉寂。贪心的我们,并不满足,还想发现更大的陨石、更多的陨石。我们分明记得,刚才夜空灿烂、群星汇集,有无数颗陨石掉了下来,在等待着我们去捡拾呢。
于是,我们忘了爸爸妈妈揪心的等待。不知不觉间,我们走出矿区,渐行渐远。我们听到了水流“哗哗”的流淌声,听到了蛙鼓高一声低一声的鸣叫。小河边、树丛下、草地上,甚至矸石旁,我们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可能疏忽遗漏的地方,可是,没有,一颗也没有,哪怕是小拇指般大小的陨石也没有一颗。有时,我们被远处的一点光亮所吸引,凑近了看,却是不知从何处灯光的反光。走到一条大路上,忽然看到一个刚从井下归来的矿工,我们赶忙跑上去询问,看到陨石了吗?就是能发光的石头。他摇着头,一脸愕然。
于是,我们又回到矿区。至少我们还收集藏匿了一堆陨石。我们穿过一片矿区宿舍,来到石墙边被废弃的开水灶,眼前却是空无一物。我们顿时傻眼了,我们左找右找,也不见那堆我们垒起来的陨石。我们分明是藏匿在了开水灶的背后,这里漆黑一片,是不会被让注意到的。我们不死心,围着开水灶,翻遍这里的东西,甚至一堆煤也不放过,可就是没有。
终于,疲倦已极,我们回到了家里。
星空的微笑
很久很久以前,我家住在西北一个偏僻的矿区,矿区坐落在一个凹进去的山坳里,四面环绕着重重叠叠的青山,头顶却有一方别处见不到的晴朗而纯净的天空……这是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很少有人知晓它的存在,它有着被世界遗忘的宁静。
常常夜幕落下,我溜出家门,跑到空旷的矿区大院,举起头来,仰望星空。可笑的是,我如此迷恋星空,对天文学却是一窍不通,星星的名字根本叫不出几个。许是受了很多传说的影响,我总幼稚地以为,天上也和地上一样都住满了人,星星是他们手中提着的灯笼。可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整夜整夜地举着灯笼,在散步,还是在找着他们丢失的心爱的宝贝?这些问题一直在折磨着我小小的脑袋。还有当我长久地打量一颗星星,便会发现她其实也和我一样,在做着各种各样诡异的表情,我朝她挤眼睛,她也朝我挤眼睛,我朝她笑,她也朝我笑,可她的笑却更加动人,更加神秘……夜空下的我,一站就是大半天,最后脖子也直不起来。矿区大院里有一株开满白色小花的苹果树,白色小花常常不知不觉落了一地,我往往带着一身花瓣回家。
夜深了,妈妈却不入睡,还在家里等着我。爸爸自然是上夜班去了矿井的深处,妈妈坐在灯下的缝纫机旁为我们赶做着来年的新衣裳。不管我多么晚回家,她都不会责备,而是马上起身为我张罗宵夜。香喷喷的小米粥和烤得脆脆的馒头便很快变戏法似地出现在面前。每当看着我大口大口吃得香甜的样子,笑意,便在妈妈的脸上流淌。
不知我在夜空下漫游了多少个日子,某个冬天的晚上,奇迹终于显现。一颗星星,正变成一只硕大的灯笼,径直朝我飞来,它一直飞到我的头顶,然后擦过树梢缓缓飞去。它比我见到过的所有灯笼都要大,都要亮,我甚至还能看到上面影影绰绰的轮廓。我追赶着,追赶着,直到它渐渐消失在天边。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UFO,只是觉得新奇。在矿区的大道上一路小跑,我抑制不住激烈的心跳,急忙将刚才的奇遇告诉了几个刚从井下上来的矿工,他们没人相信,反倒笑我眼睛花了。于是我气喘吁吁地回到家中,讲给正在等着我的妈妈听,妈妈却表现出和我一样的激动之情。现在我仍记得她眼中含着的晶亮的光:“那是天上的宝船,看见的人一生都会幸运。”
这一生是否幸运,我不知道,但妈妈的话我一直记得。岁月如矿区大院里那棵苹果树上的花儿,总是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我早已走出了那个四面环山的小小矿区,也不知不觉长大成人。在他乡异地,在长路漫漫的旅途,我仍旧会像从前那样,常常会仰起头,面对深邃的星空出神。我见过很多只有在明信片上才有的迷人风景,也对星空的奥秘有了更多的了解,可是,星空中的微笑虽然迷人却转瞬即逝,那从树梢旁缓缓擦过的宝船,从此再也没有在我的视野中出现过。
有一年的冬天比任何一年都要寒冷,在阔别数年之久,我又回到了那个安卧在群山怀抱之中的小小矿区。接连好几个晚上,我在寒夜的星空下盘桓,温习儿时的内容。一样的星星还在朝我眨着眼睛,朝我发出神秘迷人的微笑。可是在我站立的脚下,原本空旷开阔的矿区大院,平地长出几幢高大的楼房,使得视野变得异常逼仄和狭小,曾经花儿开得那么灿烂的苹果树也忽然不见了踪影。更使我心中作痛的是,我家那间熟悉的老屋,再也不会见到闪烁的灯火和灯火下等着我的亲爱的妈妈了。妈妈是在这一年辞别这个世界的,身在他乡的我甚至没能及时赶回与她见上最后一面……伫立在老屋的门前,我不知妈妈去了哪个遥远的地方?一颗很大的星,忽地一闪,莫非妈妈已坐上从星空中飞来的宝船,到了天空深处某个遥远的地方了。长久地凝视着头顶深邃的星空,在稠密的星群中间,我仿佛看见那一树开得热烈而灿烂的花儿在苹果树旁,妈妈正含笑将我凝望……
让歹徒来找我
我的同事李耀,浑身有蛮力,自称来自湖南某个武术之乡,从小习武。他时不时就会挺胸向我们展示一番他的小肌肉,并摆出一个夸张的功夫造型。他也风趣,常常习惯性地眯缝起眼睛,未及开口,就先自惹人发笑。可他却天生胆小,面对股票略一下跌撒腿就跑,遇见单位领导也会舌头打滑,骤然说不出话来。
讲讲他的一个轶事。那年我与他同去东北开会,中间会务组安排去长白山旅游。归来途中,停留于一个叫安图的小城。晚上饭毕,无处可去,我和他,还有南京来的严浩,在我们下榻的宾馆门前溜达。忽然看见旁边一家歌舞厅敞着门,就走了进去。看见我们,里面的几个男女纷纷围拢来,有个男人还要带我们上楼。我们见大厅内无一顾客,加上几个男女神情诡异,就想赶快闪人。再说我们本来就只是随便看看,并不想深入。为顺利“出逃”,我还谎称我们再去叫几个人一起来。
出了舞厅,我们漫无目的,来到宾馆外。夜幕降临,因为不见路灯放光,已难辨行人的面孔。我们站在路旁一棵小树下,闲聊,看街上人来人往,忽然李耀压低声音,悄悄说,我们赶快回去。我们不解,问为何。他告诉我们,他发现不远处有三个人一直在鬼鬼祟祟跟踪我们,他已经认出了那三个人是舞厅的,他们一直偷偷监视我们。
我向远处扫视一番,并无发现什么可疑人等。我问李耀,在哪儿啊?我怎么就看不见?他指指不远处的路边。那里的确站着几个人,可到处都是人,凭什么就断定他们是舞厅里的人,而且就在跟踪我们?另外,奇怪了,他的小眼睛近视——顺便一提的是,他的近视眼镜高达1000度,通常辨认物体不是靠看,而是靠闻。他的目光突然之间怎么会变得如此有穿透力?
拗不过他,我们只好快速回到宾馆。进了房间,心想这下该天下太平了,不料李耀却做出一个叫我们颇感吃惊的举动。只见他慌里慌张把房门反锁了,还大动干戈搬了桌子将门顶住。接着他一脸肃穆,大声宣布今晚他决定不脱衣服和衣而眠。还有,他说马上他还要上街去买一把菜刀回来,压在枕头底下。
“相信我,今晚他们一定会来找我们。”他肯定地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预料那几个舞厅的人一定会来。既然我们已被他们盯上,就无法轻易逃脱。
我问他们为何就一定要盯上我们,我们又没有招惹他们?再说我们也只是在舞厅逛逛,又没有消费,更没有赖账。话说回来,即使有事,我们这次一下子来了二三十人,人多力量大,怕个鸟。
尽管李耀比我年幼几岁,他却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相当有把握地告诉我们,这方面他有经验,因为我们是外乡人。
我和严浩都认为他在鬼扯,就一遍遍轮番劝说他,却都不奏效,我怕一个晚上被他闹腾个半死,无法睡觉,毕竟明天还要坐一整天汽车呢。就只好无奈又郑重地向他宣布:
“这样好了,那几个人如果晚上非来不可,到时候我就这样对他们讲,一切与你无关,他们直接找我好了。”
我这样一说,才终于堵住了李耀的嘴,乖乖去睡了。那一夜,就像我预料的相安无事,那几个被他“惦记”的歹徒并无叩门突然来访。
翌日明媚的阳光下,我们在这座小城游览,走在街上,充分领略了小城的安宁和祥和。李耀那小子一路蹦蹦跳跳,早已将昨夜的插曲忘得一干二净。
遇蛇记
蛇应该是人们眼中最为恐怖和丑陋的动物之一了,瞧它竖起扁扁长长的脑袋,吐露火焰一般跳跃的蛇信子,小小的眼睛闪着诡异而狡黠的光,那细长的身体即使弯曲着,也如一根坚韧的鞭子。每每在电视中看到这一幕,我往往会闭上眼睛,或者转过身去,心中则会涌出说不出的恐惧和恶心。
大概人对蛇的恐惧和厌恶由来已久。这不仅仅因为蛇能分泌令人致命的毒液,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恐怕还是蛇那极端丑陋的外表。老虎素有大虫之称,虽也能致人于死地,但因为其威风凛凛,人们往往对其生出景仰之心。即使是包含致命毒液的其他动物,人们对其恐惧的程度也远不及毒蛇。面对蛇,我们在惊叹万物奇妙的同时,便会充满疑惑,造物主为何造出了一个形象如此委琐和怪异的家伙?
后来在阅读《圣经》时,我找到了答案,原来蛇是魔鬼的化身,即蛇是魔鬼撒旦变身而成。蛇因引诱夏娃偷吃善恶树上的禁果,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蛇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旧约》中如此描述:“神对蛇说:‘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也就是说蛇之所以有今天的面貌,实在是罪有应得的结果。至于魔鬼究竟应该呈现何种形象,人们有“画鬼容易画虎难”一说,描绘起来不难,因为谁也不曾见过魔鬼,便可胡乱想象,任意臆测,但这往往很不可信,也极易造成混乱,而把魔鬼的形象统一为毒蛇,不但极妥贴地凸现出其邪恶的本性,也将一个原本十分混乱的物象清晰化了。
对蛇的认识,我们当然不会忘了著名的《农夫与蛇》所产生的影响。人们总是因为自己的愚行和轻信,付出昂贵的代价。伊索这个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再明白不过地告诉我们蛇之所以为蛇的原因,不管在什么情形下,我们都不要忘了蛇的名字前有一个“毒”字。
在不算长的半生中,我个人也曾有过与蛇“狭路相逢”的遭遇。那一幕可追溯至儿时,一个夏日,我和姐姐结束了学校的一天,奔走在回家路上。时近黄昏,砂石路已变得模糊不清,我走得昏昏沉沉,突然眼尖的姐姐一把抓住了我,并大叫了一声“蛇”。我定睛了看,原来脚下盘曲着一条蠕动的蛇。要命的是我当时穿着短裤,裸露着双腿,假如不小心一脚踩下,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吓得面无人色,只顾没命地跑,生怕它会突然追了上来。跑着跑着,以致在路上碰上了校长大人,我们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敬意,只含混不清地告诉他碰上了蛇,便飞快逃走了。
这是我唯一一次与蛇的邂逅,事隔多年,我现在想起,仍会有一丝恐惧掠过。后来,我也常常在山中盘桓,却再未与蛇遭遇过。倒是偶尔在山道上见到过透明而美丽的蛇皮,那是冬眠后苏醒的蛇蜕化后留在山道的。但那已不含恐惧的成份了。
虽然人人对蛇怀有莫名的恐惧和仇恨,但似乎并不影响对蛇某种程度的亲近,这足以反映出人与蛇之间存有一种极其复杂微妙的关系。人们常常在媒体上看到蛇与女明星亲密接触的艺术摄影,以体味其中所制造的奇异效果,人们甚至在报纸上读到少女与蛇同眠的消息,也有先睹为快的冲动。但人们对蛇的征服,最能得到体现的还是餐桌上。蛇肉成为一道极受欢迎的盘中物,多年来都未有衰落的迹象。很多人都能通过蛇肉,享受到美食的乐趣。但也许是受《圣经》的影响,我本人一直视蛇肉为不洁之物,每每在酒桌上见到大盘堆起的蛇肉,便不忍下箸。
不管人们抱着何种心态,可以肯定的是,蛇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我指的是那种真正游弋藏匿在山间草丛中的蛇。即使你怀有猎奇之心,无性命之虞,在野外也未必能遇到了,更不要说是那种难得一见的眼镜王蛇了。
作者简介:
张樯,来自苏州,写作多年,有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等作品散见于各地报刊。现任深圳特区报副刊编辑,主编“前海”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