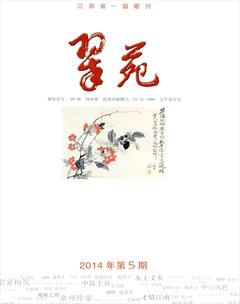亲人们
一、媳妇
男人电话回来说,生意亏本,京城的饭不好吃。男人在电话里气短心慌的,他说这几天准备回家,可能要住两天。
莫不是出了啥大事?出再大的事宋大爷也不管,管不动了。宋大爷八十多了,老伴去世二十几年,嫁出去的闺女也已经有五年没回来了,去京城做生意的儿子更离谱,先跑出去五年,五年里没给自己一点信息,后来回来一趟,住了几天,又跑出去五年没有音信。忽然电话说要回家,爱回不回吧,不怕家里老人臭,多住几天也行。
男人回家,虽然手上拎着脑白金脑黄金的,但嘴上气势汹汹,跟宋大爷说话,不待宋大爷把话慢慢讲完,就加塞说自己的事,工地上死了两个人,这些年在外没个人帮衬,累死累活的,挣的卖命钱全栽进去了。那口气,好像自己活得这么辛苦,宋大爷和命运一起有份捉弄他。
媳妇香兰更胖了,不知吃啥好的喝啥贵的,胸围腰围直往外呼,看见男人她有点不好意思,头一低,贴着床沿从男人面前过去,把一把药片放在宋大爷手心里,一只手伸到宋大爷背后,托宋大爷坐起来,靠在床背上。然后又腿擦着床沿,从男人面前撤回厨房端水。
宋大爷有点尿失禁,女人要给宋大爷擦身换裤子。男人起身四处看了看,房子两室一厅,收拾得挺干净。香兰和宋大爷各人一个房间,宋大爷房间里还留了张老伴的黑白照片。男人踱到阳台上,阳台角落里堆着卖钱用的纸盒子空罐子,晾衣绳上挂着宋大爷和女人的内衣裤,女人从前喜欢穿大裤衩的,现在比以前更胖了,倒穿起了紧身小短裤。男人看着旗子一样的布片,深吸一口烟,烟头扔地上踩扁了,转身去宋大爷房里。
男人想让宋大爷把房子过户给他,爹你也这把年纪了,我就你一个儿子,这房子早晚得给我,如果不是人命关天,我也不会为这房子大老远赶回来。宋大爷脑子不糊涂,说亏你说得出口,为了房子才回来,都跑出去多少年了,怎么才晓得房子?你甭想!
父子俩吵得厉害,男人犟不过宋大爷,别把老头子给急得气憋过去了喽。过两天,男人的姐姐回来了,她嫁去外省日子过得穷,大约为了省钱,一连很多年没回家了,这次倒被弟弟请回来了。爹,你不看看自己多大年纪了,现在不把房子安排好,将来有个万一,啥啥啥都是不方便。说到可怕又邪恶的“啥啥啥”,姐姐顿了下,斜眼看看房门外站着的香兰。万一闹起来都是祸害,你现在过户给弟弟,不但将来的事清楚,现在也是救人命,好多人感谢你呢,爹!女儿把宋大爷说成救人性命的活菩萨。
姐姐好说歹说,说到去世的妈,这个头发花白的女人一下子伤感得特别厉害,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恨不得给犟老头子下跪。宋大爷也哭,是啊,你妈多好一个女人啊,给我留了两个种,我活成啥样也不管,我还没死就谋我的房子,要把我赶到路边去。
姐姐缓缓收声后,拉弟弟到门外,问道,那女人肯定给咱爹说什么话了,咱爹不该是这样的,连妈的面子都不给,不能呀!
男人五年前从北京回来,办了一件重要的事,和媳妇香兰离婚。离婚第二天他又赶回北京,他在北京有了新的媳妇,还有了一个新儿子,会喊他爹了,怕时间耽搁了新媳妇生气。没及时打扫战场,留下了个祸害,香兰没从家里搬走,竟然和宋大爷凑一块了,还领了结婚证。日防夜防,家贼难防,真没想到香兰长得憨憨傻傻的样子,心底有这么深的计谋。老头子也不是个东西,和香兰结婚!这不是老子打儿子的脸吗?男人想来想去不服气,就冲这一点,老头子也该把房子让出来,让嚼舌根的人看看,儿子还是儿子,再说房子别叫外人占去了。
爷俩这一气斗的,亲亲眷眷都被男人请来,劝宋大爷给儿子一条活路。
宋大爷卧床不起有两年了,可脑子好使着呢,他看情形不对,再闹下去别委屈了无辜的人,摊牌了。说房子已经过户给自己的媳妇香兰了。香兰站在床沿上,两只胖手互相握着,脸红彤彤的,不说话。
男人傻眼了。这么大事儿,你咋不跟我吱一声儿,你脑子糊涂了!你干的都是啥事儿,尽丢我的脸,妈在天上看着呢!男人气得发抖,香兰没给他生孩子,凭啥得房子。
宋大爷是教书先生退休,脑子好使嘴也能说。他说,我中风了给你打电话,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吱一声儿就挂了?你糊涂了!你妈也在天上看着呢!
男人张嘴要辩,但话没底气,又闭上了。
趁着房间里族里老长辈们都在,宋大爷说,我病了这么多年,一儿一女没人顾得上瞥我一眼,鬼门关去过几趟了,每回拉我回来的都是这女人。他眼睛望着香兰说。我算想清楚了,谁待我好,谁就是我儿女;谁心疼我,谁就可以是我老伴。宋峰你十年前去北京,把媳妇留在家里,你媳妇流多少眼泪我全看到了。五年前你回来,和香兰离婚,你媳妇没拖你一点后腿,她嘴笨说不过你,眼睛见识也没你广。我这个老头子心疼啊,你媳妇在家等你,想有一个周全的家,你却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对她没个交代!你媳妇在家代你尽孝,全心全意照顾我,我们宋家能就给她这结果?
长辈们都不说话了,都是七老八十的“老不死”们的了,哪个不盼望享儿孙福啊?哪个不盼个老来伴?又有几个舒舒坦坦、没半点烦恼地过着?长辈们齐齐看着男人,等男人回话,给个让人服帖的说法。男人也觉没趣,脸上被打了耳刮子一样火辣辣的,没想到那个女人不蠢,还有点手段,把老头子收拾得服服帖帖。
男人回北京后一个星期,又打电话回来了。他在电话里对宋大爷说,我问过律师了,那房子是妈留给你、我和姐三个人的,你可以把你的份送给香兰,我和姐的份你得归还,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按份算下来,你得给我和姐50万元。宋大爷“啪”挂了电话,孽种!
再过了一个星期,男人又打电话回来。这次他在电话里气急败坏地吼:老畜生,房子六年前你就过户给她了,那时我还没离婚呢,我要告你破坏我们的婚姻!
宋大爷喘着气也对着电话吼:畜生,你告去!
二、姐夫
楚云飞放暑假了。姐姐打电话让她过去。楚云飞很高兴,姐姐家在省城,她正想去省城逛逛。而且姐姐自小霸道惯了,让去不去,要挨骂的!
姐夫来车站接楚云飞的。这姐夫,她四年前见过几次,那时候她还在上初中,不懂得他好在哪里,对他的长相完全没概念,只晓得姐姐经常在她耳朵边上提,研究生啦,知识分子啦,在大学里做老师啦,楚云飞的感觉就是这个姐夫才学丰富,高不可攀。最近一次看见他,是他和姐姐结婚的时候。一晃一年又过去了,楚云飞现在已经是一家幼儿园的老师了。
楚云飞出了车站,被一个穿红色t恤衫的男人跟上了,她扭转身子背对着他,目光冷冷地看着远处,谁知他不识相,又转到前面来盯着她。这种目光楚云飞见多了,馋嘴都馋到眼睛里了。她斜眼偷瞥了他一下,戴个黑墨镜,穿个红T恤,蓝色牛仔短裤,底下穿双咖啡色皮鞋,没品位的乱搭,一看就不正经。男人见她看自己,凑上来说,你是云飞吗?
楚云飞脸立刻红了,没想到这是姐夫。
都是姐姐害的,姐姐说姐夫现在是博士了,是讲师了。楚云飞印象中的博士穿着黑衣服、戴着黑色方帽子,满眼睛的学问。跟姐夫上了打的车,楚云飞害羞起来,觉得自己刚才太傲慢了,人家是博士,是高级知识分子,给你拎包拎箱子,你怎么连个“谢”字都说不出口?楚云飞小时候成绩不好,见老师就心慌脚软,对高学历有种天然的敬畏,如今姐夫却是高学历加大学老师。这样的姐夫跟她并排坐在车后座上,她简直如坐针毡,姐夫问一句她才答一句。
姐姐收拾了一个柜子给她放东西,楚云飞把自己的东西一理好,算是在姐姐这儿暂时安顿下来了。
楚云飞怀着敬佩之情看姐姐和姐夫说话,这么厉害的男人,姐姐也就是中专毕业,在姐夫面前不犯半点怵,不仅不犯怵还指挥姐夫做这做那。姐姐的性格还和在家里做姑娘一样,到姐姐家当晚,姐姐就指挥楚云飞洗碗刷锅了。姐夫呢,别看是个博士,和别家男人一样,听老婆的话,姐姐让他倒垃圾,他就乖乖进厨房收拾垃圾袋。楚云飞看见他细长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把垃圾袋拎手拢起来,两根小手指始终翘着,楚云飞看得忍不住笑起来。姐夫你去看电视吧,垃圾放这儿,我洗好了碗会收拾的,你只要告诉我垃圾站在哪里就行。
姐姐还没买房子,租住在一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子里。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转身都费劲,只有卧室大一点。晚上睡觉的时候,姐姐安排楚云飞睡地上,这个地就紧挨着他们俩的床。
半夜里她被床震动的声音吵醒,听到姐姐、姐夫在扭打:薄毯子像被撑空了在风中抖动,沉重的肉搏声,还有近乎于无的耳语。楚云飞已经20岁了,工作后在老家谈了一个男朋友。她知道姐姐、姐夫在干什么,卧室门和窗帘的遮光效果很好,伸手不见五指。楚云飞悄悄翻个身,背对着床。
第二天一大早,姐姐喊醒楚云飞,告诉她三餐安排。早饭去菜场买包子、油条,午饭楚云飞自己烧自己吃,晚饭楚云飞烧大家吃。姐姐本来有个正式工作,赚的钱全用来给姐夫读研究生、博士了。姐夫大学的工作进编落实后,姐姐嫌原来的工作不称心,辞了重找。可是称心的工作难找,这两年,姐姐这里做做,那里做做。最近姐姐的工作是在一家饰品店做导购员,时薪制,姐姐一般工作八小时就准时回家。姐姐说这两年也不想换工作了,反正万一怀孕了也不能做什么一本正经的工作。
做家务,楚云飞不怕。中午弄了一个小点心后,楚云飞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微信给男朋友看。取名叫:色香味俱全。男朋友很快回了一个流口水的脸,楚云飞这才美美地开始享用点心。姐姐姐夫在家的时候,她不跟男朋友联系,怕姐姐笑话,她一定会说:看你这点出息,一个小公交车司机就把你迷得这样?
姐姐、姐夫当着妹妹的面调情,他们为对方有一句话说得不妥追来追去,追到沙发上,然后摁倒对方,打屁股、掐脸蛋,到最后是搂着一记亲吻,那吻简直把两个人吸在一块儿了。开始楚云飞觉得眼睛没地方放,姐姐的热辣性子就是这样的,不遮不掩,可是这样同一个男人亲热,她是第一次看见。姐夫呢,更加让她吃惊,她是怀着敬佩一个博士的心情来看他的,然而他俗之又俗,小小的租房里一个书桌都没有,楚云飞只见过一本搁在马桶水箱盖上的《量子力学及其新进展》,才能勉强确定他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他同姐姐调情,也全然没有半点遮掩。
两个星期后,就在她要把姐夫当成一个完全的俗人时,姐夫又把她拉了回来。那天晚饭姐夫没回来吃,姐夫的一个课题研讨会在学校召开。晚上10点多姐夫回来,拎了一大包资料,他的论文,研究成果,会议材料等,原来他的书都全看在脑子里了。他兴趣盎然,拉着姐姐和楚云飞聊,虽然已经简而言之,但复杂介质啦、电磁场啦、电磁波啦……楚云飞和姐姐还是完全听不懂,只知道会议开得很成功。楚云飞从姐夫资料袋里拿出一本书,是姐夫的论文,厚厚的书,两三百页呢。
姐姐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三个人一人倒了一杯,说祝贺老公步步高升。姐夫很高兴,摆手说,什么步步高升,祝我终于出了一口气,这个论文憋我两年了,终于出版了,大家对它的评价都很高……下面就要开始着手评副教授了。姐夫仰望着天花板,为自己计划未来。
楚云飞羞涩地举杯,敬姐夫,祝贺姐夫终于出了一口气。姐夫又回到了那个戴博士帽的形象上,而且还和教授联系上了。姐姐确实有眼光。
那天晚上,他们照例在床上折腾了很久才睡觉。
后半夜,天上的星星都睡着了。楚云飞穿着棉布睡衣,两朵乳房分摊在胸两旁,棉布睡衣外面还盖了一条薄毯子。梦里的楚云飞胸口有点痒,翻个身子,手臂垂到胸前。有个黑影迅速缩回了手。楚云飞一下醒了,睁开眼睛,伸手不见五指,但她分明看见一个人影爬回了床上。再细细往前推,那胸口的痒……是了!有双手伸进毛毯,放在她两朵乳房上,轻轻地捏。她身子不动,两条胳膊把胸护好了。做梦吗?肯定不是!帮她盖毯子不小心蹭到的吗?碰和捏的感觉太不相同。楚云飞再也睡不着。
第二天是周末,姐姐昨晚的开心还在,说云飞来两个星期了,带她出去玩玩。楚云飞完全没有精神,不想去,但没有足够的借口推脱。站在景点上,脑子里全是半夜那双手。他跟她说话,她不回他,也不正眼看他。装得跟没事人一样,还博士呢,教授呢,哼!
姐夫跟姐姐说,云飞摆脸色呢!姐姐不高兴了,把楚云飞拉到角落里说,姐夫好容易抽空陪你,你别给脸不要脸。楚云飞眼里迅速洇上泪水。今早出门,因为少带一个保温茶杯,姐夫说她记性不好,脑子有问题。他还没对她说过重话,为这种小事这样说,恰恰确定了楚云飞心中的猜疑。他故意惹她哭,她哭了,他才有理由掩盖;她的不开心才有合理的解释。你看现在,姐姐就以为她还在生早上因茶杯挨骂的气。他猜中她不敢对姐姐说出事实。按姐姐的脾气,如果她知道了事情,一定是护着自己的男人,说楚云飞的不是。没有十足的证据,怎么敢说?
爬山的时候,姐夫伸手拉她上一个大台阶,那只手无心得很,若说有心那便是他递给她的一根橄榄枝。姐姐在旁看见了说,姐夫向你道歉呢。楚云飞被姐夫拉着,很不情愿,身子有意往后仰,姐夫笑嘻嘻地,脸上还是昨晚研讨会成功的开心。他坦荡荡地,她别别扭扭地。
第二天楚云飞找了个学校的理由,整理东西回老家了。姐夫这个人她实在看不透,也害怕看了。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她姐姐才能搞得懂,搞得定。她还是喜欢她的小公交车司机。
三、后妈
女人嫁过来的时候,韩月只有6岁。
父母亲分开已经有一年,她还不清楚离婚的概念,只知道有时她住母亲那边,有时她住父亲那边。当父亲突然让她喊这个陌生女人“妈妈”的时候,她很惊讶,怎么还有一个妈妈?
女人很时髦,会打扮,在小城里是一道风景。她待韩月还不错,带她去游乐园玩,给她买新衣服,帮她洗澡、梳好看的辫子,给她做好吃的,像妈妈一样用软软的声音跟她说话。她听爸爸的话,喊她“妈妈”。
回到母亲住的地方,母亲告诉她“后妈们”的故事。沙基镇上一个后妈给孩子灌白酒,灌醉了,用火钳把孩子活活打死,可怜孩子醉得连疼都不知道;夯基镇上那个残疾小乞丐,常年拖着鼻涕,光屁股趴在地上,男不男女不女的,据说是他后妈把他丢出来的——他爸爸娶了后妈就全听她的,对待自己亲儿心肠硬得像铁。她第一次听到白雪公主的故事,母亲着重讲了后妈怎样处心积虑想害死白雪公主,善良的公主吃了后妈给的红苹果,韩月的心“通通通”地跳着,跟着故事里的白雪公主一起死去。后来她在幼儿园又听到了灰姑娘的故事,当孩子们为王子终于找到心中的公主欢呼,她忧心忡忡于另一个细节:后妈让灰姑娘独自在家干活,自己却带着她亲生的女儿们去参加王子的盛宴。
韩月知道了亲妈和后妈的概念,她开始对女人产生怀疑,她粉红色的笑脸下藏着险恶的心,这青面獠牙的女鬼!她不再叫她“妈妈”、接受她的礼物,也不再给她微笑。
第二年女人生了一个弟弟。亲妈说,你看好了,以后东西也不会给你买了,她有自己的儿子呢。
女人依然常常给韩月穿的吃的,直到弟弟6岁时,她终于露出了狐狸尾巴。给韩月买新衣服的频率慢了,那年冬天,她只给她买了两件新衣服,弟弟则有三件。她仔细观察,心里冷笑,亲妈说得对。
比这个更可恨的是,父亲竟然要夺回亲妈对她的抚养权,还让她少去亲妈那里。你别不识好歹,你那个妈的话有几句真为你好?父亲教训她。她讨厌他把亲妈说得那么遥远,她回答他:你那个女人的话又有几句是真为我好?她料定是后妈在父亲耳朵边上说了诽谤她们亲娘俩的话,父亲才会变得和传说中的一样。
通过再次协议,父母亲商定好,韩月的抚养权还是归母亲,但平时她得住父亲这边,周末一天住母亲那边。
母亲的日子过得不好,离婚后又一次被男人骗了,那个男人带着她生的男孩消失了。母亲租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屋子里,半夜娘俩挤在一米二宽的小床上,韩月搂着亲妈那温暖结实、毫无防备的身体——和后妈在一起,肌肤接触只能让彼此更尴尬。母亲跟她讲自己跟父亲恋爱的故事,他们是中学同学,他文采斐然,她是校花,他们反抗父母,自由恋爱。讲着讲着,母亲哭了,她帮母亲擦眼泪,自己的泪却止不住地流。她快上初中了,已经有了懵懂的关于爱情的向往,她恨透了父亲那边的女人,她抢走了自己的父亲,挤走了自己的母亲。如果不是她,母亲怎么会沦落到这地步?她给她买这买那,那些东西难道本来不就是她韩月的?
弟弟韩冬已经能说会道了,跟前跟后地叫韩月姐姐。这个弟弟她倒不陌生,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她心情好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喜欢他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十分讨厌他。有一次,她从亲妈处回来,因为刚流过泪,心上的盐还在蜇她。她跑进厨房把奶奶杀鸡时溅在地上的血沾到弟弟的面包片上,再裹上蕃茄酱,骗弟弟吃下去。
爷爷奶奶都偏心,鱼肚子上的肉夹给弟弟,鱼背上的肉才给她;大虾给弟弟,小虾给她。他们明显是在拍女人的马屁,狗屎的亲情,连演都不会演。韩月心里诅咒他们,筷子故意一歪,碗里的半盆菜被弄到了桌上。她的目光冷冽,没有笑容。奶奶忙收拾油腻的桌子,唠唠叨叨批评她:丫头,你的手怎么这么没数,你看,油弄到冬冬身上了。
韩月只管吃自己的,眼里的冷箭射到弟弟身上,再射到女人身上,再射到爷爷奶奶身上。老不死的,吃死你们,吃穷你们!
女人也说话了,韩月你多大孩子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女人知道她是故意的,她已经不像嫁过来时那么爱笑了,常在大家面前说钱不够用,那难看的脸色想来就是摆给韩月看的。
上高中了,路远,要买电瓶车。韩月想买一辆粉红色的,跟女人早就讲好的。女人带她逛街,末了说逛一天了,实在找不到粉红色的,明天还要上班,我看红色的还更好看呢,价钱也不便宜。女人也不管韩月的意见就买下了。韩月车都没拿,一甩手就回家了,心想,如果是你亲女儿,你能这么敷衍?
她哭着把这件事告诉亲妈。亲妈闹上门来,骂女人臭婊子,不要脸的骚货,不是东西,虐待她的女儿。楼洞里挤了好多来看热闹的人,交头接耳地说话,很多人原本并不晓得这是一对继母女。事情的发展偏离了买车的源头,亲妈隔着防盗门和后妈对骂,后妈竟然也回骂韩月亲妈婊子,急得韩月直跺脚,她站在屋里,帮防盗门外的亲妈,她大声骂屋里头的后妈臭婊子臭婊子臭婊子。后妈一吃惊,乱了阵脚,失了劲头,对骂的话成了没有箭头的稻杆。门外头的人议论纷纷,更热闹了。
那次她们亲娘俩大功告成,后妈生气了——大人还生小孩的气,可见的确不真心亲她。从那以后她和后妈开始了多年的冷战——在韩月看来,女人的热情明显有假,她的那些兄弟姐妹们也虚晃晃的,对着韩月称女人为“你妈你妈”,明知不是一根筋上来的,你妈个头啊?
17岁那年,父亲车祸去世了。后妈带着她和弟弟韩冬,披麻戴孝;弟弟小,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和后妈被人搀扶着,哭得昏过去几次。父亲活着的时候,忙着处理她和后妈的关系,因为韩月一直怀疑父亲中了女人的毒,不再爱自己,所以没跟父亲好好说过几次话。而这次,韩月终于把父亲紧紧抱在了怀里——一百七八十斤的男人变成一捧骨灰。
众人散去后的屋子空荡荡的,父亲被挂到了墙上。后妈对她说,你和弟弟都姓韩,都是爸爸的孩子,我会把你们带好。这次,她有点相信后妈的话了。父亲只一个星期,她和后妈都迅速瘦了许多,她们俩一个是寡妇,一个是孤儿,都是姓韩的男人抛下的可怜人,瞬间失了共同的依靠;而此刻后妈脸上的泪珠、黑眼圈、疲惫是真实的,眼睛也不回避她的直视——韩月冰凉直视的目光已经成为一种表情。
然而亲妈说,后妈总归是后妈。
此时,亲妈的日子过得更差了,在宾馆做保洁,临时工,一个月才千把块钱。韩月想既然父亲不在了,自己干脆跟亲妈走,但亲妈只是低头落泪。她到底心疼亲妈,还是跟后妈住着,吃用都是后妈的。亲妈算过了,后妈手里有父亲去世的赔偿金,里面有韩月的份。
又过了两年,韩月大学毕业了。后妈在商场工作,做品牌服饰的导购员,曲里拐弯地也认识几个有钱人。她找朋友的老公帮忙,陪笑脸说好话,帮韩月谋了个工作。工作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差,每个月两三千块钱收入,韩月独立了。
再过些年,韩月结婚了,嫁了一个卖汽车的。后妈出于做妈的立场,也给她置办了嫁妆,不算太少也不算太多,反正在韩月看来不给自己丢脸,也不给自己长脸。她得给儿子留着呢,韩月想。她从后妈家里搬出来后,就把亲妈接到自己身边。从她知道亲妈就是肚子流血、眼里流泪,忍痛生下自己的那个人开始,就盼望有一天能让亲妈跟自己过上好日子。亲妈无家可归的时候,她心疼极了。
韩月怀孕了,生了个男孩。丈夫待她不错,孩子管韩月亲妈也叫奶奶,就像亲妈生了孙子似的,亲妈乐得合不拢嘴。韩月听过白雪公主的故事后,十多年没有喊后妈“妈妈”了,冷战的几年里,她压根不喊后妈,父亲去世后,她喊她阿姨。阿姨快五十了,又嫁了个男人,因为韩月与她本来没有什么话说,加之心下总觉得后妈改嫁等于背叛了父亲,对她后嫁的男人也颇不喜欢,所以除了逢年过节,平时基本不回家。
韩月已经是一个妇人了,在俗世里翻滚过,有些事情,族人们、邻人们也不再背着她嘀咕。一点点地,玻璃碎片聚合成块,她看到了事情的另一些影子。
当年,自己亲妈嫌父亲没有出息,在外面找了个做大生意的男人,然后毅然和父亲离婚。亲妈离婚后和大老板生了个男孩,但大老板已有家室,不想离婚,有一天趁亲妈外出,大老板带着男孩消失了。亲妈竹篮打水一场空,知道父亲脾气好、耳根子软,且听说父亲新置了房子,就回头来找父亲,想说些好话让他回心转意,谁知父亲告诉她已经和女人订了婚,新房子就是用来结婚的。亲妈上门找女人吵架,骂她是勾引她男人的狐狸精,拆散他们原配夫妻。她们俩的怨恨,在韩月正式认识后妈之前就已经有了。
而后的故事,就有了韩月的存在——她像一把开刃的匕首推动故事朝流血的方向前进。
亲妈说的那个爱情故事,只是故事开始的前半段,父母亲年少时懵懂友好的部分罢了。
而更为可疑的部分,亲妈从来没有说过。据一些并不可靠的流言说,韩月不是父亲的孩子——在这件事上父亲对后妈说,既然叫我爸爸,我就养她这个女儿。当然这些外人的议论,韩月是不信的,唯一知道真相的亲妈,韩月不愿意去问。她和女人争夺了这么多年的父亲,她不愿相信他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碎片的整合,花了她几年的时间。此时,孩子上幼儿园了,她按着自己内心的计划走,要给儿子最快乐最简单的童年。而这些年渐次到来的信息,和人生的轨迹,让她开始走上与亲妈后妈们重叠的路,爱情啊婚姻啊都是一些瞬间多变的复杂东西,难明其里,让人患得患失。这些年,每得到一个新的碎片,她心里就先替亲妈辩驳,辩不过了,就退一步解说:谁不想活着舒服一点,任性一点,自由一点?谁又能活得那么周全?她有时候看着跟在自己身边的儿子,觉得他好像当年跟在自己身边的弟弟,她后悔自己当初给弟弟看了太多不好看的脸色。大人的事,自己懂多少?
亲妈已经是个头发半白的大妈,体态臃肿,全无当年校花的影子。她嘴上叼着烟——说老了,改不了了,不改了;两腿架开了,坐在板凳上择菜,不时说出那句曾让韩月深感欣慰的话:还是女儿贴心,拉屎拉血生出来的,跑得了人跑不了心。亲妈毫无防备的笨拙身体里,藏着简单的构思和强大的能量,让她安心地把女儿养在别人身边,而不惧丢失。这么多年来,她只要不时地给韩月讲讲后妈们的传说,韩月就成了落难的公主。
但是,一个每天都要吃高血压药、糖尿病药的中年妇女,如果以前没有恨过她,以后也犯不着恨她了。更何况,自己的确一直爱她。韩月想。
后妈还是住在那个家——后妈再嫁时,韩月跟她大吵过,不许她在父亲眼皮底下玷污这块干净地。屋子重新装修过,父亲的照片被收到了箱子里——这是爷爷奶奶的意思。爷爷奶奶还跟后妈住着。韩月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看着,眼里都是从前:六岁她刚刚进这家,后妈帮她洗澡梳头穿衣服;后来这里有了弟弟,她和他吵架,偷偷打他,作业故意教错他;再后来她骂后妈婊子,她和爸爸爷爷奶奶所有人吵架;后来父亲去世了,她和后妈、弟弟居于同一屋檐下……女人待她——如今自己做了母亲,想想有些教育的细节、经济的盘算——还是付出了很多,也怀了极大的耐心,而且即便是亲生母亲,也就是这样了。
后妈房间墙上还挂着父亲去世前一年她拍的艺术照,泛黄的美人笑在过去,后妈是爱美极了的人。当年为她爱打扮,为她拍这套艺术照,韩月和她计较过,日子过得这么紧,凭什么做女儿的没有化妆品,不拍艺术照,做妈的老女人倒要浪费这些钱,摆得这么妖媚还想勾引谁?
女人的故事韩月不甚明了,据说是受过爱情的伤。总之,她28岁遇上父亲,做了韩月的后妈——人们说,怎么挑的,挑来挑去挑个让自己做后的,老话怎么说来着,宁坐茅坑板,不做前后晚啊?
算起来,后妈今年也该50岁了,比亲妈小两岁。她正在厨房忙着烧吃的,一会儿她就要端着菜,出来招待韩月一家三口了。
后妈一向不太说话,韩月想这次应该自己先开口。第一句叫她什么好呢?韩月看着厨房里忙得热火朝天的女人背影,腰越发细瘦了,但头发还是做得一丝不苟,她跟亲妈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父亲不在这么多年,韩月第一次为叫女人什么感到为难,感到叫什么都挺不好意思的。也第一次觉得,自己大概也算是这个女人的女儿。
然而故事的发展,只到韩月出嫁后难得回家为止。生活这本书并不厚爱任何人,它既没有对韩月翻开亲妈那本书,也没有翻开后妈的任何一页。韩月静止在她对现下生活的爱里,丈夫、孩子、亲妈一家团圆,日子越来越好;也静止在对童年、少年、青春这三个特殊时期的恨里,狐狸精、骨灰、作为对手的弟弟、以及老不死的爷爷奶奶们,他们与她越来越远。她只在自己的那本书里前进,女童、少女、少妇、母亲……她在不同时期的每个阶段里,用自己调制出来的画笔,不断修正自己的情绪、身份、故事和人生的方向,有逐渐复杂的色彩和阴影。她可能永远没有机会接近任何一个真实的她们——立体的、身上有深浅不同的颜色。
故事后两段关于亲妈、后妈的揭晓,她们三个的融合,不过是好事者善意的想象,她旁观她们,知道一些不方便对当事人说的东西。但,她知道的也只是片段,况且道听途说的,谁负责真假呢,只适合敷衍成文,私下里读读,臆想这世界还有透明的可能罢了。
作者简介:
白小云,2002年开始,陆续在《钟山》《青春》《雨花》《芳草》《上海文学》《延河》等发表纯文学作品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