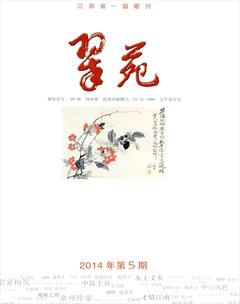四十而惑(外三章)
如果从10岁识一千个汉字开始算,成本的书我读了三十年了;如果从踏上工作岗位算起,社会这本书,我也读了二十年了。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惭愧啊,三十岁的时候我一事无成,四十岁啦,成本的书看不懂了,社会这本书更看不懂了。
躲在阳台一角,看着灰色楼宇间一小块长方形的灰色天空,想象着高山流水谢知音的琴声,想象着触手可及的竹林七贤的酒罐,真想忘乎所以地狂啸几声、痛痛快快地大醉一场!
从我懂人事起,我的家乡不停地变,承包、搞活、改革、开放。把这书面语翻译成乡村生活,就是:从集体种田到各家各户自己种,从“双抢”到“一熟”,从一两家人家不种麦到大家不种麦,如今好,连稻也不种了,只种树苗,整个乡镇的田都变成了园艺场。祖祖辈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农耕方式和犁、水车、石碾等传统农具一起结束了田间地头晒场二千五百年的“操劳”,“光荣退休”走进了它们的养老院——博物馆。我们的后代不用面朝泥土背朝天、不用戴着斗笠卷着裤管去扶犁去赶牛,不用弯着腰割麦插禾,不用养猪肥田不用囤粮果腹。他们将由老师领着观赏一下那些好玩的、木制的、石制的、铁制的农具,读一读“汗滴禾下土”,然后完成一篇作文,就“经历”了稻的一辈子、麦的一辈子、农民的一辈子。
上世纪80年代,村里家家做童装、绣被套,树荫下的老婆婆不停地搓着皮筋;90年代,镇上办起了兽药厂、农机厂、汽修厂,大姑娘小媳妇都高高兴兴地到社办厂去上班啦。如今,满街的设计院、满街的汽车、满街的经理。
长长舒一口气,我叹息的是:我父亲出生的村庄,看不见油菜黄,闻不到稻花香,处处是郁郁葱葱的大树和小树,大树都是从别处移来的,最早来“落户”的大树在安徽生活了百来年,是邻居大叔把两瓶廉价的烧酒送进村长家后、用20吨的大卡车运回来的,小树则基本上来自浙江。江南风光依旧旖旎,但水乡的大河小港彻底失去了“欢声笑语”,不是被堵就是被黑。水乡少年与水为伴的快乐与自豪消失啦,我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我的孩子只能在都市游泳馆里以小时计算着与水相亲的欢娱。
我读书时,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农家子弟一年又一年地复读,为了考上大学转户口安排工作。那时的农村青年,不握锄头就是出人头地,出人头地无非两条路,除了读书读出头,就是当兵入党转干。
我相信条条道路通罗马,凭借城镇户口安排工作的“人上人”政策,我进了工厂当了工人。可工人阶级的光荣消失得让工人们猝不及防,下岗、买断工龄;车间被租、工厂被转;再后来,工厂的围墙拆了,房地产商进来了。一个分厂遍布四十多个乡镇的龙头企业,一个曾经享誉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明星企业,一个有着数千职工的大型企业,像沙漠上的春天还未完全盛放就已枯萎。
待业、失业、再就业;工作、家庭、孩子;房子、车子、票子,我的这二十年啊,哭着笑着走过来了。工作的累生活的苦,都无所谓,咬咬牙就过去了,我怕就怕中国的人际关系。总说,师傅教徒弟留一手,有师傅压着,咱就没有出头之日。可师傅毕竟是从上世纪50年代走过来的人,虽然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他们遵守传统道德。而我周围比我略年长、与我年岁相仿或比我还小的年轻同志们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公务人员”理直气壮的“优越感”,掩耳盗铃的“聪明相”,自相矛盾的“勇气”,夜郎自大的“才气”,让我汗颜,中国道德的“马其诺防线”彻底失守——我真是不明白啊,是这世界变化太快,还是世道人心变得太坏。
我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也不可能改变别人——我明白。所以,我只想也只能安静地读书,工作,活着,仅此而已。
悄悄告诉您一声,我没脾气。
两位王老师和师母们
两位王老师的故事,我早已烂熟于胸,以前,外公说过,父亲也说过。如今外公和父亲都不在了,孤独的母亲每每回忆三十年前在新疆的点点滴滴时,总会提到王老师们,其实,那是两对夫妻不弃不离、两个家庭两代人的故事。
在新疆时我太小,我对王老师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那时两位王老师家都在水工团,离我家四五十公里,我没去过那儿。父亲母亲和他们成为朋友是因为韩老师,我外公救过韩老师的命,孤身一人在新疆的韩老师就把自己当成了外公的儿子,我父母自然就是他的妹妹妹夫了。水工团约等于监狱,都是不许外出的“犯错误”的人,他们唯一与犯人不同的是:拖家带口,一月有25元工资。韩老师与两位王老师一样来自首都北京,都是著名大学(不是同一所)才华横溢的年轻助教,不同的是韩老师没结婚,那两位王老师有老婆。水工团的头“文革”期间害了不少人,乱整人还拷打,“文革”结束后,冤者家属找到水工团,那头不承认,水工团的难友们就和家属一起去沙包挖。老天有眼啊,大伙凭着记忆居然从流沙里找到了屈死者的尸首,干了,捆绑的痕迹拷打的痕迹都在,被打断了一条腿还割掉了一只耳朵。那头后来被判了刑。
新疆最苦的活是修渠,水工团就干这个。没粮没手套,零下几十度还在挖渠,韩老师病得奄奄一息,水工团撤走了,竟把他留在了一个破帐蓬里。老王老师拼了性命从汽车上跳了下来,遇上了我外公,用马把韩老师拖外公家了。外公是傅作义的兵,那时日子也不好过,可外公是苦孩子出身,身上有革命的枪眼刀疤且大字不识一筐,所以在四十五团,外公还是团长。其实,外公和水工团在一个工地修渠,也刚撤下来不久,天越来越冷,地冻得比石头还硬,又连着下雪,外公心里急,水工团怎么还不下来,他天天骑着马到沙梁子后边去转圈,还就撞上老王了。韩老师还有一口气,外婆管打针吃药,外公用脸盆盛了雪帮韩老师擦身降温,折腾了两三天韩老师才醒。外公叫上政委一起送韩老师王老师回水工团(证明他们没有外逃),老王老师的老婆已经披麻戴孝哭了几天了。外公没文化但他敬重知识分子,水工团苦啊,外公仗义,每年冬天都打些野兔弄些酒,让我爹妈送去。
为救韩老师跳车的行为被定性为擅自离队,老王老师被罚去戈壁滩放羊,工资停发。老王老师赶着一群羊,他老婆用拉拉车拉着铺盖、锅和他们第一个孩子,走进了没有人烟的大漠深处。母亲说老王老师的老婆和老王是大学同学,一个学金融一个学外语;大学毕业,一个分配在银行一个留校教书;老王在北京的监狱关了三年,他老婆给送了三年饭。老王出来了被发配新疆,他老婆不肯跟他离婚被银行开除了,两人告别父母就到了新疆。老王老婆除了那次以为老王死了,哭了几天外,从来都是笑弯着眉说话的,一开口就是我老公我老公的,我老公傻么,自己掏钱印了传单到天安门去发,自个思考成反革命的。老王老师的羊一放就是六七年啊,六七年间,他老婆在我外公家住过三次,他们的老二老三老四都是我外婆给接生的。没工资没布票没油,老王和他老婆和四个孩子在戈壁滩上自给自足,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老王老师会两门外语,我父亲一直帮他订着外语杂志。
春天的阳光照进水工团已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老王老师和我父亲一起调进奎屯教师进修学院,老王教英语,修渠放羊荒了十年,老王一拾就起,大伙开玩笑,老王的羊只听得懂英语口令。老王两儿两女,第四个孩子叫二丫,我妈做过她的班主任,小小的个子,天天和同学斗嘴,唾沫星子乱飞,成绩好得一塌糊涂。老王的四个孩子都上了大学,都学的外语专业。老王老婆落实政策本可以回北京,原来的工作单位还派了人来,可老王老婆见老王太忙(一个学校就老王一个外语老师),竟决定不工作了,就在家帮老王。他老婆用补发工资买了一台当时最高级的缝纫机,偶尔空了,她就上街买一大卷布回来,做小衣服小裤子,然后拿去卖。在戈壁滩上生存了十年,什么能难倒老王老婆啊。老王老婆老公孩子全管,还管刻钢板印讲义,挣的钱还不比老王少。奎屯的商店一有录音机卖,老王老婆就买了一台,她和老王一起录英语磁带,男女对话,老王上课就放这。后来,进修学院并到石河子大学,老王干到65岁才退休,老俩口现在跟二丫住在广州,老王老婆瘫痪几年了,二丫请了两个保姆伺候着。
小王老师的故事简单些,他老婆和他是穷山坳里一对竹马青梅的金童玉女。小王老师到北京上大学,他老婆就在乡间小学代课供他兼照料他妈。小王老师在大学当老师了,婆婆也走了,小王老师的老婆就进了北京。小王老师在监狱关了一年,他老婆被学校赶了出来,没工作没地住还是犯人家属,小王老婆当保姆捡菜叶加工鞋底,好不容易把小王老师等了出来。发配新疆还不给路费,俩人一路扒火车睡车站,走了半年才到水工团,他们有三个孩子,一家五口只发一个人的口粮加25块钱。小王老师的老婆不知用什么办法从老家弄来了一副石磨,自己偷偷磨豆腐,没日没夜地磨,一家人这才活下来。属兔的小王老师老婆因为长年累月欠觉,两只眼睛红红的,小王老师叫她小白兔,他老婆管同样属兔的小王老师叫灰毛兔(小王老师不满30岁头发就灰白了)。小王老师学的是中文,跟我爸同专业,俩人都好看书写诗,小王老师最感激的是我爸送他蜡烛。小王老师每次挨斗,他老婆不用人点名自个就站到小王老师身边去了。我爸说,领导一不注意,小王老师就亲他老婆一口。我爸还说,这个是人给编的,不可能。小王老师爱耍宝,一高兴就大声朗诵:“啊,老婆,我要大声为你喝彩!我孩子的妈,我的好老婆!”再后来,小王老师一挨斗,他老婆他三个儿子一起上台站着,像一截楼梯。落实政策,小王老师不愿回到北京那伤心地,就联系了成都的一所大学,车都装好了,明天就要走了,当晚,小王老师喝了点酒,第二天没醒。小王老师永远留在了水工团,他老婆带着仨儿子去了成都。他老婆在成都磨豆腐卖豆腐供出了三个儿子,香港回归的那年,小王老师的老婆死了,我爸和韩老师赶去成都。现在,小王老师的三个儿子有两个在国外,一个在他父亲当过助教的大学当副教授。
笑 容
采风——两天游三地,感觉蛮好:
千灯为昆曲发源地之一,我却在深藏于小镇弄堂里的昆曲博物馆里听到一段苏州评弹《枫桥夜泊》,倒也饶有风趣。因为叫“千灯”,所以造了一座灯博物馆,从古到今的几千盏灯陈列其中,不知这世间是否有“画蛇添足灯”。
锦溪很有点舅婆家的味道,我在那买了两对开店女子自己编的中国结,以前买过各式各样的中国结,但都不敌这对实在,很结实的线,很粗的穗子。我还看到了“床前明月光”里的“床”,吃到了海棠饼。
三山岛的环岛公路慢跑一圈需一小时。长天共秋水,芦苇伴残荷。伸手摘黄桔,低头忆童年。
——写在前面
采风回来,朋友们纷纷把我的照片从QQ上传了过来。
我看到了立在不同风景里的我,每一张我都笑着,我看见了我的笑容。柔和的眼睛,淡淡的皱纹,齐耳的短发,整齐的牙齿,我对自己的笑容很满意:笑靥如花,温润如玉,是一个42岁的女人应有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到自己的笑容了,不是笑得少了,而是刻意回避,每每外出,只拍风景不拍人。风景多美啊,白的云、绿的草;巍然的石头、流动的溪水。人,又老又胖的,煞风景。
其实,拍照的心态折射生活的态度——不想笑是不想打开心扉了。
少年时想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流浪,风吹过耳,雨透衣衫,一日十里,十日百里,我就不信走不完那“三百六十五里路”。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不再年轻。我在狭隘的回忆中回忆着走过的“三百六十五里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掰着手指头算过,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时,我正好30岁。而立之年赶上那样好的时代,我一定会很了不起的,“有鸟于阜,三年不鸣,一鸣惊人;有鸟于阜,三年不飞,一飞冲天”这个美好的想法令我热血沸腾了许多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是我从小到大作文里常写常新的人生奋斗目标。20岁之前,我的笑声回荡在校园里,我和我的同学们谈论理想,谈论费翔,我们把“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行囊”唱得意气风发。30岁之前,读书工作生活,看电影谈恋爱结婚生子,日子忙碌杂乱,像田边的野草,还没长顺呢就枯了;刚适应了蔫头蔫脑,又被春风拽着不知所措地绿了。过日子的心情随口袋里人民币的厚度而波动,没钱就沮丧,一发工资,又财大气粗忘乎所以起来。那双“红舞鞋”有些磨脚,但我每天仍无比勇敢地傻笑着穿着它舞蹈,我热爱我那一地鸡毛的生活。
从30岁到40岁,祖国长高了、强壮了,我的家庭物质财富也日益增长,一切是那样地欣欣向荣。但我的“洁癖”日益严重: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中国的腐败、中国的种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让不惑之年的我困惑不已。而这些“不合理不合法”已经影响到我生存的小环境,最可怕的是身边的朋友也渐渐失去了善良与真诚,他们似乎热衷于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不幸之上,然后还能振振有词地“指责”别人的“不道德”。我累了,我的身体和笑容都出现了“亚健康”。
如果一切都是体制之过,那么,构建这体制的人到哪里去了?英国某家报纸给读者出了个讨论题:这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结果最简短的,是作家切斯特顿平静的回答——“亲爱的先生们:在我。”假如每个生活在这个体制内的人都意识到问题“在我”,那么这个社会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这是我在常州籍作家赵翼如的书中读到的一段话,是啊,如果我更善良更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是不是能发现更多的善良与真诚呢?党的十八大召开了,我衷心希望我的祖国健康我的同胞快乐。
同事中年岁最长的作家老金说:再过一两年,我就吃素了。到了那个年纪,只需要最少的需要啦。一句随口说说的话,我却记住了。我曾对闺蜜说过:十年不买衣服也年年有衣服穿,十年不买内衣也不会紧张黄梅天。就物质而言,除了每天最简单的三餐茶饭,已经不需要“需要”了。
同事中最年少的诗人羊羊在文章中写道:“如今的人都去云南了,留几张影像,所谓‘丽江时光,一张纸片真能留住时光?而这已然为一个舒缓、柔软、优雅的专用名词了。我身边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一生不停地旅行,走过太多好像一定要去的地方,只为获得短暂的精神归宿。归途时,却发现丢了自己的故园,丢了自己的江南时光。”——感谢老弟,一语惊醒梦中人,是该停下来了。坐在自家的庭院里,喝口茶发会呆,扫扫鸡屎。然后,去田野里走走,一如爷爷吸着烟“巡视”他的土地。
好友平儿皈依了,身边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了宗教世界,也许他们和我一样迷茫,但他们找到了寄托,每每和他们纯粹的目光接触,每每看到他们宁静的笑容,我都很感动,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懂得幸福,所以微笑。
找爸爸
电影《巴山夜雨》我看过不少于十遍了,每次看,我都流泪。电影的主人公秋实与我是两个时代的人,我们没有相似的人生经历,我原本没有哭泣的理由,没有共鸣啊。但看到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那个小女孩,那个唱着爸爸的诗寻找爸爸的小女孩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写诗。
又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又一次看《巴山夜雨》。
船要起航了——
我又看见了杏花,泪流满面的杏花依依不舍地与老父、恋人作别——今夜,我注定又将跟着杏花哭一路……
我又看见挽着竹篮的老大娘,今夜,我又将望着老大娘坚强的脸流泪,我的心将随那篮红枣一起卷进一个个黑色的漩涡……
抄过秋实家的小伙子告诉秋实——“诗丢不了”时,我哭了。
终于,又看见那个小女孩了。小女孩在找寻未曾见过面的爸爸,小女孩在船舱里走着、唱着妈妈临终前教她的歌: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 飘荡/小伞儿带着我飞翔 飞翔 飞翔
这是小女孩爸爸写的诗。小女孩也许还不明白妈妈的深意,但她水灵灵的眼眸里充盈着渴望,渴望找到爸爸。她轻轻地站在可能是她爸爸的每个人的身旁,唱着那歌。
我终于为眼泪找到了一个流淌的理由:诗,还可以找寻爸爸。
《巴山夜雨》的片尾,小女孩找到了爸爸,老船长在终点前的一个山脚下停了船,当诗人抱着女儿走上山岗时,老船长拉响了汽笛。
我的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来到新疆,战天斗地,教书育人,我知道他从未后悔过。新疆是个好地方,其实好地方在南疆,我出生在北疆的最北边,那儿就不是个好地方,缺水缺菜、缺医少药,小小的我因为缺钙因为高烧,抽成了斗鸡眼,父亲不愿我陪着他在边疆喝苦碱水,父亲不忍我落下残疾,于是,父亲把我送回了他的故乡——风柔水秀鱼肥米香的江南,可这物质、自然条件的改善是以我和父母长时间远距离的分离为代价的。只有十岁的我开始了与父母天各一方的生活,在我最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却承受着孤独,然而父亲的一封封来信填充着我的寂寞无助,父亲的信里总有一首写给小豆豆(我的乳名)的小诗,那些年,我读着爸爸的诗想着远方的爸爸。如今,父亲不在了,我也早已忘记了父亲写给小豆豆的那些小诗了。
我是一颗蒲公英的种子
谁也不知道我的快乐和悲伤
爸爸妈妈给我一把小伞
让我在广阔的天地间飘荡 飘荡
小伞儿带着我飞翔 飞翔 飞翔
当影片中小女孩唱起爸爸的诗时,我的快乐和悲伤一起袭上心头:小时候,我是蒲公英,离开了爸爸妈妈的怀抱;如今,我想给满头银发的父母一个温暖的拥抱,可父亲不在了,天空中飞翔的是我的眼泪:我怎么就忘记了父亲写给我的诗了呢……
作者简介:
张咏梅,笔名墨雪。生于新疆,长在江南。当过工人、编辑,现供职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文学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书写、记录,在《雨花》《青春》《扬子江诗刊》《小小说选刊》《经典美文》等刊物发表作品数十万字。有散文集《新疆没有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