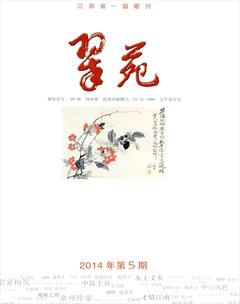张戬炜的诗
张戬炜
青山的屈辱与诗人的愤怒
——浙东:一种无趣的对话
青 山
我跌进了屈辱的深谷,
我阅尽沧桑,
从没低下高贵的头颅。
陶渊明因我而懂得悠然,
李太白因我而飘洒忘物,
可我却跌进了屈辱的深谷。
瓯江还在美丽地流淌,
美丽得像一段将被剪裁的绸布,
我像一个丑陋的陪衬人,
我的身躯上长满了
癞疮——那斑斑点点的可怖的坟墓。
陶渊明李太白的后代呵,
等你的子孙来看望我时,
整个浙东恐怕已经变成
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公墓,
我 甚至 已经不会 哭。
诗 人
我无法听完你的诉说,
尽管诗人最能理解痛苦。
我曾经为无数个诉说呐喊,
每一声呐喊都在
曲曲折折的铅字缝中死去。
诗人不过是精神病人的一种,
习惯为汉字的排列方式欢呼,
总以为手中之笔,
是足以开天辟地的巨斧,
在前一分钟,我才真正
明白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错误
我可以为你身上的癞疮
——那令人憎恶的椅子坟
感到莫名其妙的愤怒,
但我的笔不能签署红头文件,
诗人的愤怒,
不过是精神病人的愤怒!
青 山
我不懂得精神病患者,
我只是需要愤怒!
三岁的孩子已经在我身上
造好他的豪华而恶俗的坟,
可我的脚下,还有
七十老妪住着漏雨的屋。
在我们这个连每片树叶
都有两个诗人在歌颂的国度,
假如每个诗人都愤怒,
就足以让活着的人知道,
世界上没有不朽的事物,
秦始皇在我身上缀过癞疮,
汉高祖在我身上缀过癞疮,
慈禧在我身上缀过癞疮,
如今他们自认不朽的冥府,
不是任凭烟蒂浓痰四处密布?
诗 人
活了无数岁的你呵,
比三岁时的我更糊涂,
并不是每个诗人都会愤怒,
且愤怒据说已不再是诗的任务。
诗人都在关心自己的职称,
耗心耗力,从荆冠向桂冠过渡。
在你说的这个诗的国度,
批判修正主义的口号,
最终结果只是不准穿喇叭裤。
阿Q革命的目的,是
夺取那张漂亮的宁式床,
且秦始皇有墓、汉高祖有墓,
社会主义的公民岂能无墓!
朽不朽都是身后事,
西太后的坟没修进颐和园
《人民日报》告诉我,
国家主人的墓已修进西子湖。
那七十老妪虽然住破屋,
但她肯定愿意,
给三岁孙儿铺平阴间路……
庸俗吗?庸俗。
痛苦吗?痛苦。
令人痛苦的庸俗,
令人庸俗的痛苦。
青 山
被强奸者的屈辱,
可以替换为庄严的公诉,
面对强加于我的屈辱,
却只能默默无语。
诗人呵,折断你的笔吧,
江河污染,青山受辱,
你居然处变不惊,依然如故……
诗 人
你以为屈辱仅仅在几座坟吗?
我告诉你——不!
大兴安岭得意忘形的火苗,
巫婆的舌头一样舔尽了绿树,
武夷山伐木者手中的钢锯,
魔鬼的牙齿一般啮秃了沃土,
有人呐喊:“伐木者,醒来!”
殊不知“伐木者原来不读书”
面对二亿文盲二亿准文盲,
醒来的诗人又有何法术。
呵,你的屈辱,我的愤怒,
只能像珠蚌一样,
深藏心底,磨成珍珠……
1988年9~12月
纪念碑
一、
无数清醒的死者扭曲的
身躯,以及紫褐色的血
既然无法选择生
不妨选择怎样死
死亡如季节般
不可回避
人生成为沉重的负荷
诗开始有了永恒的主题
纪念碑 诞生
二、
我们没有自己
我们只拥有历史
热带雨林一样深远
热带雨林一样潮湿
热带雨林一样鲜活
热带雨林一样沉闷
无数棵树掠夺土地
许多大树挂满阳光的金币
一些树只好死去
雨林仍在麻木地发育
三、
我看见星星般浩瀚的死者
为了一个美丽的许诺
发黄的线装书像苍老的门
吱吱嘎嘎地翻动
为什么成为生者
竟然是五千年的谜
一千个答案的脚下
蜷曲着一千零一个死者
四、
走向死神黑色的唇齿
确实是别无选择
于是有了许多纪念碑
甚至辨不出重量
骄横的龙在碑的额头上
与凤交媾
淋淋漓漓地扭动
确信能生产不朽的东西
自由抽象地吹动它们
像吹动一片秋天的叶子
五、
选择怎样死去
是没有大理石相伴的
大理石只属于
对死亡极度恐惧的人
选择死亡的死者
有一面会唱歌的旗帜
旗帜不懂得死亡
在寒冷的天气里
旗帜会变成石头
坚硬地飘动
变成另一种碑
六、
五千年的土地
七十年的道路
无数清醒的死者的眼睛
透过血色蛛网
指点如何选择死亡
使生变成红玛瑙
生本来并无意义
只有死亡
才能给生留下定义
七、
真的纪念碑不是石头的
有时甚至只是一种感觉
清醒地选择死亡
给生者留下血和旗帜
生命如太阳花一样
短暂的灿烂
永久的记忆
这样的纪念碑
分子结构
是每一个幸福的生者
1989年7月断续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