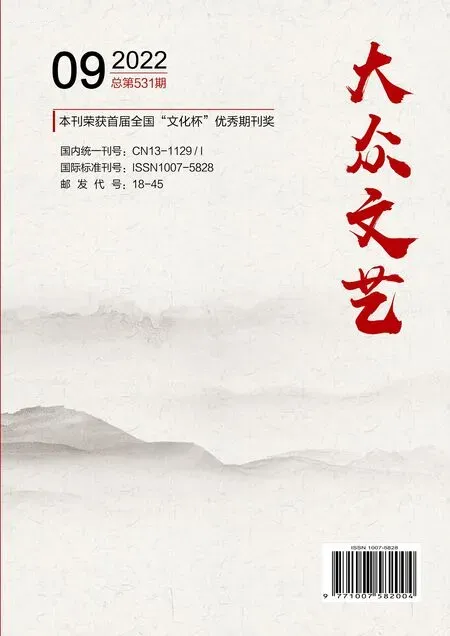从《广艺舟双楫》看康有为碑学审美观
王育育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570228)
从《广艺舟双楫》看康有为碑学审美观
王育育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570228)
康有为系碑学的集大成者,其《广艺舟双楫》可谓是书论史上的一大里程碑。于书法发展的折转期,康氏通过该书,在“变易”这一核心书学思想下提出“尊碑抑贴”、“尊魏卑唐”的主张,壮大了碑学声势,拓展了碑学影响。在“气象”此一审美范畴的统领下,康有为极力推崇“雄强茂密”的阳刚之美,受儒家思想影响,亦兼尚“阴柔”与“中和”之美,体现出其思想的复杂性。在其碑学审美观的指引下,康氏开一代书法新风,创成独具一格的“康体”书法,使后世学书者受益。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碑学;审美观
康有为(1858~1927)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及思想解放的先驱,其一生除游历求学、教学、组织变革活动外,潜心学术,著作颇丰,其中,文艺类的属《广艺舟双楫》影响最为深远。
康氏集碑学之大成,继包世臣《艺舟双楫》之论而“广”说之,著成《广艺舟双楫》,以通变的史学眼光审视书法流变,评论碑品,讲述学书经验与技巧;体例彰明,征引广博,论证严谨;集中体现了康有为的书论见解。因其作于康氏向皇帝上书不达,变革大计受攻责,心中苦闷而键户读碑之际,故多受其革新思想影响。书中激越之词与变古立异之说为时人所责,然恰是此不溺旧说、另辟蹊径之学说促使康有为专注于碑学研究并最终使碑学兼具实践与理论系统。该书成为岭南书学乃至中国书学研究的经典著作。
一、尊崇“雄强茂密”之美
嘉庆、道光以后,帖学盛极而衰,向来以“清朗俊逸”、“妍妙秀媚”为审美旨趣的传统帖学在时世危艰之际已无法满足时人表达其炽热的情感和困顿的人生之需。康氏认为当适时注入遒劲舒放的风格,方可振拔其生气,遂极力推崇“雄强茂密”的审美理想。这是康有为在书法艺术上主张变革并着眼于书法形体表现特征的一大贡献。
(一)推崇“雄强茂密”
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在阮元(公元1764~1849年)、包世臣(公元1775~1855年)首倡重视碑学以救帖学之弊后于大量出土碑版的充裕客观条件的支持下,进一步明确提出“尊碑抑贴”这一核心书学思想,从中便可窥见其尊尚雄强之风。康氏尊碑一方面是由于书帖日久老化,频繁翻用而受损,另一方面,则为碑版书法的五点特征所折服,言曰:
“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这段话集中体现了康有为重碑轻帖、尊魏卑唐的书学观点及原由。所列前四点从书体的角度论六朝碑之优点:魏碑不但因书法字体齐备、笔画完好而易于临摹,而且还具有史料价值和承上启下之用,可以考证隶楷之流变与后世各变体之源流;第五点则从风格上作论,当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舒长而刻入的笔法与雄奇之势使其达到唐宋书法所未能达的独特境界,这是康有为在其书中首次流露出对雄强之气的推崇。由此观之,其所谓“尊碑”,从审美上而言,尊的是碑版书法所展现出来的内在气势,即有似于曾国藩(1811~1872)以乾坤二卦论作字造形时所言之“乾道”。曾氏认为具此卦象的书法内主于神气而脉络舒通,与从形质出发而要求结构合乎法度的“坤道”迥然相异。[2]88康氏论书不拘泥于法度,这恰与其激进的变法革新精神及其自身刚强性格特征形成对应关系。由此便不难理解其为何如此极力推崇“雄强茂密”之风。
除此,康有为尊尚雄强之气、推崇茂密之体格亦可散见于其论述书体源流、品评碑品等相关书论篇目中。卷二《体变第四》虽是论述书法艺术自先秦至清代、从籀篆到隶楷之发展情况,然其在梳理书体流变并强调学书者研究书法艺术当观古论时之际多有论及此一审美风尚:秦分是最先从钟鼎及籀字演变而来的字体,康有为因秦书《琅琊》“茂密苍深”而以其为极则;汉末书体演变为真书,康氏观三国钟繇书帖与该时期的其它碑版以其“茂密雄强”为美。《宝南第九》一篇中认为南朝碑数量绝少,只字片石,最可宝贵,其源溯于吴,吴碑中被康有为推为篆、隶、真、楷之极的四碑亦是或浑劲无伦,或奇伟惊世。然而自宋、齐之后,碑版书法体势日渐纤弱,至于梁及陈朝已变为娟媚柔好,再无雄强之气,幸至北魏碑版书法体态庄茂且不乏飞宕俊逸之气,魄力犹存,尽显茂密,评论至此,康有为言辞间流露出激赏之意。由此观之,康氏尽购南北朝碑而又专尊魏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碑版在态势形质上所体现的阳刚美正中其审美旨趣。另有《取隋第十一》称隋碑深得洞达之意故足取之,却又因部分碑版气势薄弱,行笔间尚乏雄强茂密之气象,康氏不得不对其稍加贬抑。
(二)“雄强茂密”的具体指涉
康有为以“十美”为总概,道出尊崇魏晋南北朝碑的审美旨趣及其具体所指:
“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
“十美”中“魄力雄强”居首,可见其地位之着重。细作品思,此处康有为所谓的“雄强”已然成为一种具有概括作用的审美范畴,统摄书法艺术生成的其他诸种因素。从书法的精神品格上出发,提出“魄力”“气象”“意态”“精神”“兴趣”,在整体上给审美主体产生“壮”“大”之感。所谓“笔法”“点画”“骨法”“结构”“血肉”,则从运笔和结构形式上强调力度感。康有为在谈及魏碑时,认为其尽是佳品,无不可学者,并时时褒赏其“骨血峻宕”之特征,此处,“骨”与“血”的关系亦是强调用笔所透之力。给人以壮美的“大”以及富有生命感的“力”恰是“雄强茂密”表现出的书法形质意味。
“雄强”体现为熔铸于书法中创作主体的精神人格,属内在意蕴,“茂密”则表现为书法创作的外在形质,是内在力度的显现。真正的阳刚之美当由此二者相互融合而成。提倡“雄强”之美非以康氏为首,前代之人已有相关论述。包世臣在《艺舟双揖》中对“雄强茂密”作过具体阐释:“雄则全气勃勃,故能茂;强则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强也。”包氏虽然强调雄强与茂密二者紧密结合,但他认为书法若达“茂密”之态,则“雄强”已备,此乃视“雄强”为达成“茂密”之条件,强调的是“茂密”。
康有为继承包氏提倡“雄强茂密”,但综观其文论,其对于二者间的关系则有了新解。在他看来,二者并无所谓孰重孰轻,且非包含条件关系,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没有“雄强”难言“茂密”,没有“茂密”,“雄强”亦无复存在。如上文所述,康有为用南北碑刻的“十美”来作具体分析。显然,他并不效仿包氏就“茂密”而言“雄强”的做法,而将这一审美理想同书法艺术生成的精神品格、运笔结体等诸因素结合起来,构成包含有其他诸多审美趣味的范畴群。这种对前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在拓充“雄强茂密”这一审美理想的内涵之余还使得其更具独特意味。
二、兼尚“阴柔”、“中和”之美
作为碑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的碑学思想虽多有激越之词,但在审美形态观上,除上文论证的推尊“雄强茂密”之美外,还兼尚“阴柔”“中和”之美。
(一)“阴柔”之美
陈永正评论康有为的审美观曰:“康氏在肯定书法艺术‘阳刚’之美的同时,却否定了它的对立面‘阴柔’之美,未免偏激”,笔者认为此评说有失偏颇。康有为确实反对过于“妍媚”“靡弱”的书风,亦有激越之词,但在其思想深处仍兼尚“阴柔”之美。
康氏兼尚“阴柔”这一审美旨趣仍可见诸《广艺舟双楫》一书。卷六《榜书第二十四》中,康有为指出榜书的习写有临仿难周、笔毫难精、运管不习、执笔不同、立身骤变之“五难”,推荐学书者取法并临摹古人所写的大且精之字。其中,北魏素有“书法北圣”的郑道昭(455~516)所书《云峰山刻石》深受康氏青睐,被列为“妙品上”,且评论该碑曰:“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郑道昭下笔多为正锋,方圆并用,给人以结体宽博之感,又体气高逸,特别是在章法上做到密致而又通理,使整体趋于和谐,呈现出迥异于阳刚气的阴柔美。
此外,康有为虽不提倡干禄体,但在《干禄第二十六》中又因《裴镜民碑》和《樊府君碑》具有阴柔之美而大赞之。在他看来,《裴镜民碑》整朗方润、字画丰满,虚和娟妙,清秀有如出水之莲花与开天之明月,当奉为干禄书体中的无上上品,他认为有此二碑,学榜书几乎无需再取法其它碑版。
综上所述,康氏对书法的阴柔之美确有崇尚之意。在《广艺舟双楫》中,描述具有“阴柔”之美的碑版多用“媚丽”“娟好”“妍美”“虚和”“圆静”“平整”“端和”“匀净”“精秀”“清朗”“疏朗”“逸韵”等词语。由此观之,“静逸”与“和谐”是康有为所兼尚的阴柔美中的主要类别,以形式的统一、完整,韵味逸永为主要特征。据统计,《广艺舟双楫》中约120处涉及“阴柔”气象[3]134。实际上,“阴柔气象”包含为康氏所诟病的“靡弱”与“妍媚”,本文所讲的“阴柔之美”是建立在剔除该类气象的基础上,探讨康有为审美旨趣中所尚赏的阴柔美。与推崇阳刚之美的内在气韵不同,康有为兼尚“阴柔”之美的核心思想是指向书法表现形式的和谐,有类于曾国藩论书之“坤道”,言其“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2]88。康氏对后者的品评言辞虽未若品评前者般将其尊崇之意推到极致,但我们仍不可否认其在审美上对“阴柔”之美的追求这一客观事实。
从康有为品评《三公山碑碑额》《樊敏碑》《司马升墓志》等碑石中可见具有阴柔美的书法内在表现为生命力较小,外在体现为整体形式的和谐与匀整。这与阳刚美所体现出的雄强旺盛之生命气息以及茂密之结体截然不同。
(二)“中和”之美
康有为一生在政治及学术上的思想尤为复杂,至于其碑学审美观更是如此。介于阳刚与阴柔之间,还存在一种“中和”气象。康氏碑学审美观中也包含对书法“中和”气象的向往。
在《榜书第二十四》一文中,康有为列具有“中和”之美的《淇园白驹谷》《泰山经石峪》《太祖文皇帝石阙》为佳碑,还因尖山、冈山、铁山摩崖之书皆浑穆简静而称其高绝。《泰山经石峪》用笔为圆,《淇园白驹谷》用笔为方。康有为更倾心于前者,列其为榜书第一,原因便在于其具有草书的风情之余还散发出篆书之雅韵,整体上尽显雄浑古穆。康有为本最为尊尚书法结体之茂密,但当论及榜书鉴赏时则持相反态度。他再次以宽绰有余的《泰山经石峪》为例,论证榜书的作法异于其他书法形式,笔墨讲求雍容之态,神态力主安静简穆,避免雄肆之气带来的突兀与视觉冲击,一改阴柔美生命力较小之状态,使其趋于中和,且特别强调作榜书若有意写就气势雄强者属粗野之人或不能书之人,是可鄙的。贬斥之余,康氏不忘回味《泰山经石峪》和《太祖文皇帝石阙》给人以“中和”之美的享受:“若有道之士,微妙圆通……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气韵穆穆,低眉合掌,自然高绝”。用“有道之士”“冰雪”“处子”这些处于生命本然状态的事物作比喻,更显露出康有为对碑版书法之“中和”气象的神往。
由此观之,康有为所兼尚的“中和”之美表现在具体作品上是指结体与章法由内而外散发出浑朴、深沉之气且内中富含意蕴,其最根本的特点在于“浑穆”。明朝项穆(1550~1600)认为“道统出源,匪不相通”,即人之伦理道德与书法之精神品格有相通之处。因而其尊评仲尼曰:“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气质浑然,中和气象也”,且认为书法之美善者亦当如此。所谓“中”即“无过不及”,所谓“和”则“无乖无戾”。具有“中和”之美的书法,介于阳刚美与阴柔美之间,在神态上趋于本然,体态上静中含动,虽没能如“雄强茂密”一般能以其磅礴气势而易于夺人眼球,亦无娟娟雅好之碑所特有的能扣人心弦之高逸气韵,但却散发出质朴淳和之气,令人愈品愈觉醇香。
《广艺舟双楫》中与“中和”气象相关的描述多用“淳古”“雍容”“浑穆”“静穆”“安简”“虚和”“自然”“古朴”“和雅”,等等。书中约有138处文字谈及对该类气象的描述。其中,“淳古”“雍容”“静穆”“端美”“凝重”是“中和”之美的几种代表类型。康有为在品评《三公山碑》《是吾碑》《东海庙碑》等碑版时多有论及此些特征。从中可观知,“中和”之美的内在状态可理解为生命力的深藏不露,而其外在形式即是这种生命力以自然之态显现出来的感性表现。
三、审美观之“矛盾”的原因探析
综上所述,康有为的书法审美观中存在兼尚“阴柔”、“中和”之美的旨趣已成事实,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观点尚未达成共识。笔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康有为在言辞上将“雄强茂密”之美推崇至极,主观意向上对其的关注程度深于另外二者,自然导致研究者的疏忽;另一方面则由于对康有为书法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就书法论书法的境地中,而未能从康氏的人生经历以及心理学等角度探寻形成其审美观上存在此种“矛盾”的内在原因。
追本溯源,康有为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审美观根源于其思想的复杂性。而其思想雏形的形成与其自小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康父早逝,康有为孩提时所受的教育均来自祖父康赞修,冠年之时又拜朱次琦为导师。康赞修是一醇儒,笃守程朱之学;而被世人尊称为“九江先生”的朱次琦(1807~1881)则是晚清经学家,亦主张程朱理学,且兼采陆王心学,治经则归宗孔子。在二者的影响下,康有为一生中最初的思想启蒙完全来自儒学,于接受能力最强的青年时段更是立志做圣贤之人,决心读遍圣贤书,儒家思想在康有为的意识中早已根深蒂固。
康有为曾自称“至乙酉之年而学已大定”。乙酉之年为1885年,既然“学已大定”,那末此时其思想胚胎早已形成,而《广艺舟双楫》成书于己丑之腊,即1889年,从时间上看来,该书的写作是在康氏思想雏形已定之后,自然受溶浸于其思想深处的儒家温婉之气所影响,这体现在书法审美上便是上文论及的兼尚“阴柔”之美。
基于儒家思想,康有为作《大同书》,在西方现代化大生产的前提下,展现了一副以人道主义、天赋人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社会理想,构建乌托邦,表达其大同思想。这种追求至善至美、和谐的大同理想折射在康有为的书法审美旨趣上恰是对“中和”之美的向往。康氏将中国富强与世界大同视为其生平的素志与理想,此二者出自同一人的思想蓝图,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因其层次分属不同且所处阶段各异。那么,康有为在书法审美旨趣上既推崇“雄强茂密”之美又兼尚“阴柔”、“中和”之美这一现象实则亦无矛盾可言,因其分别强调的是对书法内在气韵、表现形式、整体风貌等诸因素所呈现出的不同状态的界定与评说。
化解矛盾的前提是承认它的存在。探讨康有为的碑学审美观,只有在认识并承认他对“雄强茂密”“阴柔”“中和”之美存在不同程度的尚赏,才能在原因探寻中化解此种“矛盾”,经此客观而全面地透视康氏碑学审美观。
虽然康有为碑学审美观兼尚“雄强茂密”“阴柔”“中和”之美,但其主要贡献仍体现在前者的影响上,不仅乘帖学之坏兴碑学,扭转“靡弱”书风,开一代“雄强”之气,丰富中国书法艺术流派,还促成“康体”书法,对后世学书者,如梁启超、徐悲鸿、刘海栗、萧娴等皆有指导意义。
[1]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注[M].崔尔平.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
[2]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
[3]参见刘兆彬.康有为书法美学思想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
[4]陈永正.岭南书法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194.
[5]项穆.书法雅言[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5.
[6]康有为.康有为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