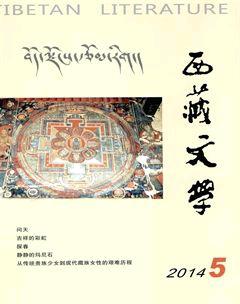向生命作证
唐翰存
我对散文诗的最初印象,来自于鲁迅的《野草》。那种幽微之美,那种陌生化表现,那种语词的精粹,使它成为我的枕边之书,常读常新。魅力不减。《野草》是很内向的文字,以“独语”的方式,隐现了作者的生命哲学。作为中国散文诗这一文体的开创者,鲁迅给后来者以诸多启发,可惜至今无有超越者。鲁迅本人在散文诗方面的成就,也超越了他在新诗上的成就。他的新诗,语多拗口,有时打油的意味重,与同时期一些优秀诗人相比,艺术上不很成熟。可是,一旦他转化形式,将散文的因素引进诗歌里,就生质变,让人仰慕不已。这个现象,是值得研究的。
当代散文诗里也许不乏佳作,可惜甚少,大多平庸泛泛。曾经有一个时期,我喜欢翻阅印刷精美的《散文诗》杂志,后来再也不看了。原因在于,那上面发表的作品,大多华而不实,唯美则唯美,可那种唯美的语言背后,实则没有什么内容,实则是苍白和空洞。可以不客气地说,散文诗在当代,已经完全沦落为一种“花瓶”。偶尔赏玩一下,觉得愉悦,看的时间长了,难免心生厌烦。
就在这个花瓶即将在我心目中破碎的时候,真是无独有偶,甘南青年诗人王小忠寄来几本新出的书,其中有他的两本诗集,还有一本,是他们合出的散文诗集《六个人的青藏》。这本绿皮小书,在我书桌上辗转了近一年,有时也徘徊到床边,睡前翻读一二。尽管看了这本书我心生欢喜,可我懒散,还时常不忘提醒自己,要冷静、低调,我不能因为这么一本书,就轻易改变我对当今散文诗的看法。我必须延宕一下。就这样,延宕到了上个月参加省文代会。这本书的作者之一、藏族诗人扎西才让也来与会,晚上大家在宾馆的房间聚会。扎西陪我出去买酒,在小卖部抢着付钱时他把房卡弄丢了,后来偷偷去找,满头大汗地回来。那是一张标准的藏族汉子的脸,黝黑的脸廓上眼睛放光,诚实而又不安。他将房卡找到了,就像将诗歌找到了。后来他发短信,说他们的书登上中国散文诗排行榜了。
我重新翻阅这《六个人的青藏》,发现这六个人——牧风、扎西才让、王小忠、瘦水、花盛、陈拓,都是清一色的藏人,可他们的作品,并非清一色的“散文诗”。他们的作品里,诗的成分多,散文的成分少。或者说,在散文诗里,他们主要以诗取胜,而非散文。诗歌重表现,散文重写实;诗歌重意象,散文重叙述;诗歌重留白,散文重铺陈。所谓散文诗,是将诗歌的因素与散文的因素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质变了的文体效果。从这个标准上看,他们有些作品,并不是严格的散文诗。不是散文诗,却不妨碍它们是“诗”,甚至是好诗。这没什么关系。散文诗既然已成了花瓶,我们厌倦之余,瞧瞧从花瓶里开出的几朵花,也挺好的。
它们可不是插在花瓶里的百合之类,它们是草原上的格桑花,是绿簇里的狼毒花,长在天地间,被鹰追踪。得到阿尼玛卿山雪水的浇灌,因此就野生,耐高寒,热烈,旷味十足,当然也孤寂。在此之前,我还从未读过如此集中抒写甘南自然地理的诗歌。那青藏高原的东北角,我先后去过两次,在黑措,在桑科草原,在大夏河,在拉卜楞寺,流连忘返,感慨无限。那是一片适合生长诗歌和栖息灵魂的土地,每当经轮转动,羚羊奔跑,草木繁殖,河水安息,一切都显得那样神奇和自足。六位藏族诗人从小生活在那里,他们的祖先生活在那里,他们的血液里不仅流淌着民族的传统,也汲取着天人合一的气脉。很容易看出,他们与天地自然是如此亲近,他们的作品里有一千八百个意象,就有一千八百种自然的踪迹,其身心,简直可以外化为草木,内结为寒露,凿骨为笛,升腾成鹰。“一切美好犹如它的流逝,带着雪山的寒意和植物的馨香。”“如果我睡着了,我就要让我的文字醒着,不然那些深浅不一的青草,会打断石头飞翔的翅膀。”对自然的敬畏、热爱以及忘我的想象,是人性健康的一个标志,也是现代人审美的一个盲点。我们习惯了愈来愈强硬的人造环境,已经对自然疏远了、麻木了,读着那些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文字,反而有点不适应了。
几年以前,在一次甘南诗歌峰会上,我曾经放言,甘南作为一个藏族聚居区,有其特殊的自然地理、民族生活以及宗教方式,在文学和诗歌创作中,非常有利于产生一种自足的、完整的、集中的民族形式。这种民族形式在甘肃其它地方不太可能形成。历史上曾经有,那就是敦煌。现在,这本书的出版,正是六位藏族诗人奉献出了他们的“民族形式”。他们对天地自然的歌唱,渗透着他们的生活习俗,民族独有的审美,还有信仰。我们知道藏民族很久以来就生活在青藏高原,他们之所以能在那么高海拔的地方活下去,离不开精神信仰的支撑。苯教,以及后来的藏传佛教,已经内化到藏族人的生命里,形成本民族独特的自然观和生命观。正因为有信仰,才有了他们心目中的神山、神湖、神水,才有了“和睦四瑞图”,才有万物平等,生命轮回,空无自性。“此时,女人不怕被打开,信仰也在呼吸着的土壤里,扎下了它的根须。”一切都合乎天性,合于自然,止于道。“她坐在那里,一个人静静地呆着。或许想到转世,投胎。或许什么也不想,只那么坐着,让我伤心,让我孤单。……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干完一周的工作,在周末闲暇的时候,我还是徒步上了山。∥在余辉里,在那棵红柏和那棵白桦下,像母亲当年那样,静静地坐在树桩上,坐成一截少言寡语的流泪的树桩。”母亲坐过的那个树桩,是有佛性的,而“我”之所以能够“坐忘”,变成一截树桩,一定是因为生命之间有相互含摄、可以移情的东西存在。
在《六个人的青藏》一书里,除了看到自然、信仰,我们还看到藏民族的文化、历史形象。作为建筑的文化,寺院和村寨,出现的较为频繁。因为在藏区,这两种物象具有标志性意义。“合作有寺院,院内有经筒。/在九层佛阁转经筒,院外花朵正开,墙头花朵正红,心灵花朵正白。/金顶深处,红墙内外,时间在一片红色里游走。”寺院是安置信仰的地方,藏传佛教的寺院从构造到形貌色彩,尤其庄严独特,与酥油的膻香和诵经的声浪浑然一体。与寺院相比,村寨是安置生活的地方,“孤独的天空。泥土悄悄地流泪。/村庄和油灯渐渐消失,大地一片沉寂。牛和犁业已老去,孤烟和房屋业已老去。”这是在描写现代文明背景中,村庄和农事的某种萧条、落败,令人感伤。可是,真正的荣耀在什么地方呢?似乎只能向过去寻找。在格萨尔王的时代,村庄和部落里诞生着英雄,也流传着史诗。如今,只剩下一些传说和废墟了。藏民族是一个怀旧的民族。在这本书里,我们不时看到诗人对历史遗迹所感发的那种幽古情绪,从西天部落到吐谷浑,从牛头城遗址到阿尼玛卿山下的生死纷争。“此时安坐在城堞上,我依稀看到时光里北方的吐谷浑从西晋的战火里一头撞进甘肃南部,垒土为城,饮血踏歌。”“抱起你,阿尼玛卿;抱起你,神的白羊;抱起你,山神的儿子——父亲;抱起你,我刻骨铭心的卓玛,走上高高的天葬台,走向一个归宿。”这些抒情文字的背后,往往隐现着某个故事,闪烁之间,一种叙事感拉开。对于散文诗来说,这种叙事感是必要的,甚至可以更明朗、清晰一些,让故事跳出来。因为有了故事,散文诗也就有了纵深度,有了某种厚实的质地。
书名叫“六个人的青藏”,表面看,体现了诗人们的自信,实则是一种虔诚。面对青藏,唯有虔诚,唯有生命的投入,唯有深入骨髓的熟稔,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六个人的青藏,就是六个人的故乡,是六个人的生死场。这些年来,他们偏安于高原一隅,在那里生活,繁育,隐忍,感念。他们的写作,有意无意,受到时代话语热潮的某种隔离。没有多少人关注他们在做什么,就像没有多少人关注我们在做什么一样。可他们有青藏,有雪域的献辞。他们的爱和痛,像草木一样,为那片土地隐隐传递着风声。因此,看见的和看不见的,听到的和听不到的,都会被时空之手接纳,变成为万物立心的一部分。
2014年3月18日,兰州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