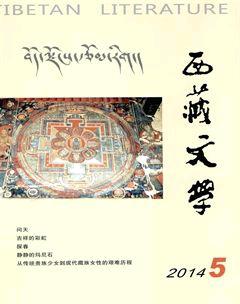吉祥的彩虹
一九五一年夏天,进藏部队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以无坚不摧之势,迅速向拉萨挺进。如何使大部队在大雪封山之前跨过怒江天险,成了当时最关键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高志诚率领十几名战士来到扎青宗建立兵站,为大部队渡江作准备。
他们来到怒江边,渡口上空无一人。高志诚和战士们站在江边的巨大岩石上瞭望,只见江两岸怪石狰狞,巉岩兀立。汹涌的江水,像受惊的野马嘶叫奔腾。兵站的同志们不约而同地同声赞叹,真是怒江天险,名不虚传。
对岸,座落在山脚下的喇嘛寺,鎏金的小顶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寺庙和村庄之间,有座用青石块砌的高大建筑,像一座城堡,也像一座监狱,那是宗政府。宗政府近旁,有座规模不大却十分讲究的两层楼房院落。围墙和楼房全是雪白色,看样子是宗本(县长)的住宅。在这三座突出的高大建筑物四周,散乱而拥挤地排列着一座座低矮的平顶土房和破烂帐篷。
高志诚想,马上就要和那些高大建筑物里的主人打交道了,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将对进藏大军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时近黄昏,欲渡无船。高志诚和战士们在河边靠崖搭起了帐篷。
第二天中午,有两只牛皮船向江这边划来。他们上岸,见解放军站在路上,马上装出降边嘉措一副笑脸,迎了过来。
这是宗政府秘书隆珠,奉宗本旺扎之命,率人前来迎接兵站同志。
高志诚面带笑容,迈着稳重的步伐,向前走了两步。隆珠赶紧跨上一大步,托着哈达的双手微微向上一抬,头和身子一起向下倾:“本布啦(长官)辛苦了!我代表旺扎宗本前来欢迎贵军。”
高志诚侧过身子,从洛桑手里拿过哈达,轻轻一抖,将一条崭新的哈达托在双手上,向前一伸,搭在隆珠手上,同时接过了隆珠的哈达。高志诚和蔼地说:“谢谢宗本的好意。”
高志诚请隆珠到帐篷里坐。隆珠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以后,接着说:“听说贵军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我们上至宗本,下至僧俗百姓,都非常高兴。没有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连住的地方也没有准备好,让你们露宿野外,真是抱歉,抱歉!”
高志诚客气地说:“这没有什么,我们一路行军,住惯了帐篷。隆珠啦,我们是不是现在就过江去见宗本?”
“这不行,不行。”隆珠赶紧说,“这几天河水猛涨,牛皮船颠簸得很厉害。旺扎宗本害怕失礼,才命令我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见本布啦。俗话说:皇帝的心思,夏季的天气最难捉摸。这些天,气候变幻无常,不看准天色,千万不能开船。出了事,我们担待不起呀。此刻,怕又要起风,就请贵军在这边委屈一夜,明天再说。”
高志诚考虑是初次见面,不好过于勉强,要乘牛皮船过江,确实也有困难,只好再住一夜。
俗话说:“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月学狗爬。”就是说在康藏高原上,只有七八九三个月的气候比较好。但是,隆珠并不像高志诚那样着急,过了一天又往后推延一天。三天过去了,在兵站同志的一再催促下,他才带着兵站的同志过江。
牛皮船很小,全部人员要分三批过江,隆珠很客气地请高志诚先上船。那只船上,有两个船工,一个四十多岁,另一个有二十七、八岁,身体很壮实。见他们走过来,年长的船工立即放下绾在头上的辫子,跳下船,吐着舌头,躬着腰,然后用力拉住绳子请客人上船。那个年轻人却一动不动,挺立船边,右手拿着浆,插进水里。他没有理隆珠,用冷漠、不满,甚至带有敌意的目光,看着这些陌生人。
高志诚和战士们亲切地向年轻人点头,问好,年轻人依旧昂然挺立,就像船上没有来人一样。
船在江中颠簸前进。这年轻船工引起了高志诚的注意。他裸露着上身,藏袍的两个袖子系在腰上,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体格健壮,相貌英俊,像是一座古铜雕像。只是上嘴唇显得过短,一排洁白的上牙异样地露在外面,尽管留着胡子也掩盖不住。
上岸了。高志诚和其他同志向两位船工连声说:“土吉其(谢谢)!土吉其!”那位年长的船工跳下船,躬着身子,伸开双手,吐舌头,表示敬意。年轻人依旧站在船上,看着他们。高志诚亲切地问:“卓波(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吉村。”
高志诚再次向他们表示感谢,然后在隆珠的陪同下,走上岸去。
旺扎带着宗政府的一些僧俗官员前来迎接。他是五品官,是这个宗里官衔最高的一级。今天,他穿着清朝的官服,在一群身穿藏装和袈裟的人里面特别显眼。小宋和其他同志好奇地看着他。
在宗本的客厅里,主人和客人分两边坐在铺有藏毯的垫子上。高志诚把一份公函交给旺扎:“宗本拉,这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给您的信。我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根据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进军西藏,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希望宗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完成自己的光荣历史使命。”
旺扎表现出一副诚心诚意的样子说:“我坚决拥护十七条协议,衷心欢迎解放大军到西藏。愿为大军效劳!”
“宗本啦,请问渡江的船只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们一接到解委会的指示,立即着手准备,该修的修,该补的补。”旺扎神色十分自得地说。
“现在有多少船只?”
旺扎迟疑了一会儿,说:“三、四只。”
“别的船呢?”
“就这么几只,我们不像内地,穷的很。”
“啊!”高志诚注视着旺扎的神情。又问:“那些船只什么时候能修好?”
旺扎吸了下鼻烟,打了个喷嚏,然后慢悠悠地说:“我们尽量抓紧修吧。”他向隆珠递了个眼色,隆珠会意,站起来,殷勤地说:“宗本啦,高站长他们今天刚到这里,山高路险,长途跋涉,是不是先请他们休息休息,让我领着去看看房子?”
旺扎马上站起来:“那好,那好!你就代表我好好招待!”
藏族战士洛桑见旺扎和那些官员们虚假应付的样子,正要说什么,高志诚却站起来说:“好吧,渡江的事咱们明天再商量。”高志诚觉察这里的气氛不大对头,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决定进一步摸清情况。再作决策。
隆珠把兵站的同志带到了隔壁一座二层楼房里。楼下是宗政府的卫队,兵站同志外出时,隆珠破例给士兵们大量的酒肉,让他们大吃大喝,然后像发疯一样狂舞乱叫,有时把上身脱得精光,披着长发,在楼梯口挥舞长剑,说是在练剑术。兵站同志无法接近群众,更没有办法去找船。
第二天,吃过早饭,楼下的几个人又喝得醉醺醺的,来喊洛桑,要同他比剑术。洛桑和高志诚商量一会,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带剑,要是愿意,可以比枪法。”
一会儿,隆珠出现了:“高站长,刚才洛桑说要同我们比枪法,是真的吗?”
高志诚说:“看来秘书对此兴趣很高,我们愿意试一试。”
不久前,旺扎和方达活佛一起,在朗杰寺大念《咒经》,散布谣言,把“红汉人”解放军说得非常可怕。不准藏民同汉兵来往,强迫他们躲到山里去。今天又一反常态,说是宗本的命令,要老百姓来看比武。旺扎盘算的是借比舞抖抖自己的威风,想方设法让解放军在乡亲面前出丑;乡亲们却也乐意来看,看这些新来的汉兵究竟是什么样子。
兵站同志看到来了不少群众,心里很高兴,昨天挨门挨户去访问,也找不到几个人,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正是和群众接触的好机会。
隆珠把老百姓都召集到县城西面的一个草坪上,然后让人在一百步外插上十支箭:五支一组,每组是四角摆四支,中间插一支。旺扎和高志诚一起来观看。隆珠对高志诚说:“我们一边出一个人,每人五发子弹,看谁能把五支箭头都打断。”
高志诚说:“好!你们先打吧!”
隆珠向后面使了一个眼色,一个彪形大汉跳出来,拿枝英式步枪趴在地上。叭!叭!五声枪响,五支箭头都断了。士兵们狂呼乱叫,又吹口哨,又跺脚。那彪形大汉神气十足地站起来。旺扎赏给那个大汉一条哈达,他把哈达缠在抢筒上,高高地举起来,绕场走一圈,又引起士兵们一阵狂叫。旺扎看着高志诚,得意地笑了笑,说:“这下该看解放军的了。”
高志诚对一个射击能手打了个招呼,那个战士正在上前。站在高志诚后面的通讯员小宋,早已憋不住了,说了声:“看我的。”提着卡宾枪一个箭步冲上去,摆开射击姿式。
乡亲们看见一个小解放军出来比赛,都感到惊讶,纷纷议论:“这小汉兵能行吗?”
隆珠问高志诚:“他算数吗?”
“当然算数。”
隆珠又张开巴掌:“本布啦,只能打五发啊!”
“用不了五发。”高志诚大声地说,即是对隆珠的回答,更是对小宋的鼓励。小宋从小参军,年龄虽然不大,但参加过淮海战役和大西南进军,经历过许多次激烈的战斗,练得一手好枪法。
在大家的议论喊叫声中,小宋不慌不忙地看好角度,做好射击准备,等隆珠说了声:“开始。”他扣动扳机,从左边斜穿过去,第一枪打断了三支箭头。人声沸腾,称赞不已,第二枪打断了二支。乡亲们热烈地议论开来,称赞解放军的好枪法。
隆珠感到难堪了。他怕宗本怪罪于他,于是灵机一动,又生一计,对高志诚说:“我们西藏人喜欢跑马射箭,这里草坪小,今天我们就不跑马,比赛射箭好不好?”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大,让周围的人都听得见。
高志诚以探询的目光看了看藏族战士洛桑。洛桑点了点头,高志诚对隆珠说:“拿弓箭来吧!”
这回答,使隆珠感到意外。他估计汉人不会射箭,说比赛,只是要将他们一军,挽回面子也好向旺扎交差。这下他只好让佣人取来弓箭,然后让人在五十步外摆两个瓶子,瓶子上各放一个鸡蛋。他对高志诚说:“一箭要把鸡蛋射掉,但瓶子不能倒。”
高志诚说:“还是你们先射吧!”
隆珠让一个士兵出来,那人拉满弓,一箭射去,把鸡蛋射落在地,因为羽毛擦着瓶子,晃了两下,但没有倒。那些士兵拍手叫好,高喊:“让汉兵来射!”“这下要看汉人的啦!”
洛桑从士兵手中接过了箭,嗖地一声,弦响处,蛋已落地,瓶子纹丝不动,干净利索。
隆珠暗暗佩服洛桑的好箭法,但他不死心,说:“两个人都射中了,分不了胜负。放远一点,一百步,怎么样?”
洛桑点了点头,好像在说:随你便吧!
这次还是那个人先射,一箭把鸡蛋射了下来。
该洛桑射了。
旺扎说:“唱歌要嗓子,拉弓要膀子,这是一百步啊,臂力不好可不行!”
洛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摆开架式,用劲开满弓。本来可以射了,但看着那些人嚣张的气焰,他肚子里有股气,想射得更猛些,憋足气,使狠劲拉了一下,“咔嚓”一声,箭未出手,弓却断成了两截。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一个孩子情不自禁地拍手欢呼:“金珠玛米力气大!”“金珠玛米赢啦!”他看得太高兴,竟忘了豺狼般的老爷就在身旁。
连输了两场。隆珠狼狈不堪。一肚子的火正没地方出,听见那孩子叫,扭头一看是宗本家的佣人小次登。他猛扑过去,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住衣领,狠狠朝前一推,把小次登摔倒在地,又从背后抽出皮鞭,往他头上叭、叭就是几下。这时,突然一个年轻人从人群中冲出来,一把夺过皮鞭,折成两节,愤怒地摔在地上。隆珠恼羞成怒,挥拳就打,大声喊:“给我抓起来!”几个士兵如狼似虎地冲了上去。洛桑大吼一声:“不许抓人!”一个箭步冲上去,挡住了士兵。隆珠怒火未消。一挥手,又有几个士兵冲上去。高志诚忙走到隆珠面前,态度平静而语调坚定地说:“秘书,这样不好吧!”
面对着高志诚从容大方,坚定沉着的神气,隆珠内心恐慌,呆呆地站立在那里。
高志诚转过身对旺扎和那些官员们说:“藏族同胞喜欢跑马射箭,比赛枪法,像过节一样,大家高高兴兴,热热闹闹,这是件好事。今天我们应邀来比赛,也是为了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增强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和友谊,并不是为了比输赢。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随便抓人、打人,多扫兴呢。”旺扎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他看见高志诚的目光里含有温和和不妥协的神色,只得从嗓子眼里挤出一个字:“是。”
隆珠耷拉着脑袋,悻悻地走开了。
高志诚转过身去看,从那炯炯有神的大眼和由于上嘴唇短了些,露着牙齿的嘴,他一下子认出这敢于冲出来的年轻人,就是那天送他们过江来的船工吉村。高志诚忙上前要和他说话,吉村却走开了。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看高志诚和战士们,仿佛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汉兵。
洛桑走近小次登,紧紧搂着他的肩膀,亲切地抚摸着他脸上带血的鞭痕。这个倔强的孩子放声痛哭起来。
现在,楼下的那伙士兵老实多了,再也不来挑衅,也不借口保护,明目张胆地尾随解放军了。
兵站党支部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组织大家向广大群众和上层人士广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十七条协议,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高志诚了解到,吉村的阿妈有病,前几天到寺庙去点酥油灯,腿又被狗咬伤。他便派卫生员小周去为老人医治。那个和吉村一起送他们的年长船工叫邓珠,是个阅历丰富的人。经常去支乌拉,高志诚决定先到邓珠家里去看看。
这天高志诚刚走进邓珠家不久,就见有一个人影在窗外晃了一下。邓珠朝他使个眼色,又朝窗外努努嘴,低声说:“不许我们随便和汉人说话,谁不听话就割舌头,抽脚筋,剜膝盖骨。”高志诚听着,浓眉一皱,回想这几天的情形,原来是明里不跟,暗里跟得更紧了,怪不得乡亲们还是不敢讲话。为了不使邓珠为难,他随便聊了几句就回去了。
由于害怕被偷听,邓珠没有和金珠玛米多说话,但是他知道金珠玛米的心意,他为金珠玛米找不到船着急。他知道宗本把所有的船都藏起来了,但是他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他的邻居吉村知道,他决定偷偷地为大军做吉村的工作。
经过几天的访问摸底,高志诚发现这里的很多群众还不知道有个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这样重大的事情缺乏了解。旺扎指派人跟踪、监视解放军的行为,更是违反协议规定的。于是他要求旺扎宗本把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公布给广大僧俗人民,做到家喻户晓,老幼皆知。
“这个……”旺扎面有难色,随即眼珠一转,灵机一动,马上取出那本红色精装的藏文版协议在他们面前晃了晃,“我照这个讲过了,可是我们这里的老百姓和你们汉民不同,天生的愚笨,再好的道理他们也听不明白,白费唇舌。”
高志诚说:“百姓并不愚笨,应该经常给他们讲,还应该贴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就这么一本,怎么贴呀?”
洛桑马上说:“这里印得有一些,请宗本向僧俗百姓散发。”洛桑不等他回答,从皮包里取出一叠铅印的宣传品交给他。旺扎用颤抖的手,像接一个火团似的勉强接收下来。
高志诚把口气放缓和一些,说:“宗本啦,不仅要宣传,更重要的是要照着协议的规定去做。这样不仅对广大群众有利,对您自己也是有好处的。只要您同人民站在一起,真心为人民办事情,像您这样的上层人士,也是有光明前途的。协饶活佛和曲扎头人不是和我们合作的很好吗?”
旺扎肚里气得冒火,鼻子里却不冒一点烟,还装出诚心诚意的样子:“这个我明白。我明白。”他心里却想着,藏民不会听汉人的话,只要你找不着船和船工,哼,过怒江天险,进西藏,妄想!还得派人加紧暗中监视高志诚他们,甚至放冷枪,投恐吓信。
回到兵站,同志们在一起又商量了怎样发动群众,自己造船的事。
洛桑说:“现在造船材料已准备好了,协饶活佛和曲扎头人也答应派人帮助我们。”
“邓珠大伯说,他也要找一些人来帮助我们。”小宋说。
高志诚对洛桑说:“我们要继续做好吉村的工作,一方面把他们藏的船弄到手,还要动员逃到山里的船工和乡亲们早点回来。”
正在这时,卫生员小周和一个战士急匆匆地走进来,向高志诚报告:“站长,巴桑卓嘎阿妈不让我们给她看病了。”
“为什么?”
“她说隆珠给了巧莎(用活佛的尿拌着黄土制成的‘药),把我们上的药和纱布扔在了门口。”
高志诚觉得这不是一般的迷信思想,肯定和宗本他们破坏我们找船,造船的工作有关。他对洛桑说:“你和小周再去一趟,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好给吉村做做工作。”
洛桑和小周到吉村家时,正好邓珠也在那里。
洛桑关切地问:“阿妈,好一点了吗?”
邓珠代她回答:“她说这两天痛得更厉害了。”
邓珠生气地说:“隆珠不让她找解放军医病,把你们上的药扯下来扔了,吃的药也拿走了。”
这时吉村从渡口回来,见他们来看阿妈,向邓珠大伯尊敬地点了点头,又看看洛桑和小周没有说话。
洛桑主动向他打招呼:“又上渡口了?我们来看看阿妈的病。”
吉村盯着他,欲言又止,他的脑子像水磨石一样飞速转动,老是想着一个问题:金珠玛米究竟是什么人?他们到西藏来干什么?一年前“送鬼”的那天,喇嘛寺堂悬挂的红汉人图像至今仍搅扰得他心神不宁:散乱的头发拖在地上,鼻孔里冒着烈焰,张开血盆大口,随时准备把人吞下肚去。眼睛里闪射着鬼火,那双毛茸茸、血淋淋的手伸向正在念经的老喇嘛。这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穷达活佛还讲了好多从前汉人杀藏民、烧寺庙、抢东西的事。他对旺扎和穷达活佛讲的那些话产生了怀疑,他迷迷茫茫,觉得那只毛茸茸、血淋淋的黑手不是长在红汉人身上,而是长在隆珠身上,长在旺扎身上,正是那些被他们说成是魔鬼转世的金珠玛米,却在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穷苦百姓。这时,他脑子里像塞了一团羊毛,乱糟糟的,理不出个头绪来。他心绪不宁地走灶边,添了一根柴。
小周见吉村和过去一样,不和他们说话,又对巴桑卓嘎说:“不上药怎么行,伤口会感染化脓的。”
巴桑卓嘎吃力地说:“管家给了巧莎,涂上就会好的。”
小周摇摇头,心想,那东西越擦越坏,越吃越糟。
洛桑心里着急。又不好勉强,诚恳地说:“您信不过我们的医生也没有关系。我也是受苦的农奴,跟你们说句实话,阿妈啦本来就有病,这次狗咬得又很厉害,巧莎是治不好的,赶紧想办法擦一点麝香,要不整条腿都会烂掉。”这几句话说得很朴实,很真挚。深深打动了吉村的心。他猛地站起来,走到洛桑身边,抓住他的肩膀问:“你真是受苦的农奴?”
洛桑用左手抚摸着吉村搭在自己肩膀上的粗大手,满含悲痛地说:“不仅是受苦的农奴,而且是‘犯了罪的农奴的孩子。”
“什么?‘犯了罪的农奴的孩子?”吉村从身后跳到前面,两手紧紧抓住他的肩头,好像他会跑掉似的。
洛桑指着自己额头上的伤疤:“你看这个。”
“烙过‘狗字的伤疤!”吉村急切地问:“谁给你烙的?为什么?”
洛桑拍了拍吉村的肩头:“你坐下,听我慢慢给你讲。”洛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好像是要让自己激愤的心情平静下来,然后用深沉有力的声音,叙述着:“二十多年前,爷爷因为还不起高利贷,日子没法过,带着阿爸、阿妈逃出了庄园。但是,他们没跑多远,就被领主抓了回来,剜掉了爷爷的膝盖骨,扔进蝎子洞,活活地被蜇死了。他们还说我阿爸和阿妈是犯了罪的逃亡农奴的孩子,在阿爸阿妈的额头上烙了‘狗字。我刚落地,他们就说我也是有‘罪的人,不久额头上也被烙了一个‘狗字,说我们犯了罪的农奴跟狗一样下贱。”说到这里,洛桑摇摇头说不下去了。
“后来呢?”吉村睁大双眼,一动不动地看着洛桑。
“农奴还有什么好下场?”洛桑接着说下去,“后来阿爸被捆在铜马上活活烧死了。阿妈也被迫跳进了金沙江。只剩下我一个孤儿,被一个好心的爷爷带到江东,到处流浪,靠要饭过日子。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金珠玛米像神鹰一样飞到了西藏,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我才当上了金珠玛米,走上了光明幸福的道路。”
雪山上的青松根连着根,受苦的农奴心连着心。洛桑一家三代人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吉村对自己苦难身世的联想,也激起了他对旺扎满腔的仇恨。他抓住洛桑的手,激动地说:“洛桑兄弟,我也是‘犯了罪的农奴的孩子。”他指着自己嘴唇,又指着阿妈的嘴唇:“你们看。”还没有等吉村说完,巴桑卓嘎双手捂住脸,“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洛桑走到跟前,亲切地说:“阿妈啦,您不要难过。”等巴桑卓嘎稍微平静下来,他对吉村说:“雪山上的青松过一年会增加一道年纹,农奴的孩子长一岁会积一层恨。卓波,这些仇和恨使我们聪明了起来。”
吉村也满怀悲愤地诉说着:“我阿爸也是船工。阿爸为了偷偷地把三个年轻的牧民送过江,被旺扎抓住,说他违抗了宗本的命令,犯了死罪,第二天就用湿牛皮包着身子扔到怒江里了。”说到这里,吉村紧紧咬着牙,眼睛里射出一道愤怒的光,一会儿又猛地抬起头,指指自己的嘴唇说:“因为我是犯了罪的农奴的儿子,把我和阿妈的嘴唇割了。幸亏那天割嘴唇的士兵也是一个穷人的孩子,他下不了狠心,闭着眼,只割了一半。不然整个嘴唇都会割掉的。”
吉村说:“旺扎把阿妈我俩的嘴唇用绳子穿起来,在江边的大树上吊挂了七天七夜,说要给不听话的农奴作个样子。”
吉村两代人的血泪仇,激起了洛桑对他的深切同情,觉得的心和吉村的心贴得更紧了,他怀着真挚的感情对吉村说:“卓波。我们都是皮鞭下长大的,你为什么相信那些黑心肠人的话,把亲人金珠玛米当仇人?”
吉村再也憋不住,把心中的疑团告诉了自己的朋友:“卓波,请您告诉我,金珠玛米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过去的汉人有什么不同?”
洛桑告诉他:“汉藏人民都是兄弟,过去欺负我们西藏人民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各族人民把国民党反动派赶出了大陆,如今又派来金珠玛米,帮助我们西藏人民过好日子。这是我们真正的亲人啊!”
吉村又问:“他们说,红汉人是浮云,老爷是蓝天,云走蓝天在;红汉人是流水,老爷是岩石,水流岩石在,汉人终究是靠不住的。”
洛桑回答说:“金珠玛米像雪山上的青松,要永远扎根在西藏高原上,他们要世世代代同西藏人民在一起,共同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
吉村用激动而欢快的声调说:“沙子和金子混在一起,用水一淘就会被冲走,留下的是真金;真理和谎言混在一起,用事实一对照,谎言就会被揭穿,真理的光辉能把人们的心儿照亮。感谢你,我的好朋友,你用金子一样纯洁的心,擦亮了我被风沙迷住的眼睛。请您告诉我,我能为亲人金珠玛米做些什么?”
洛桑直接了当地说:“翻山要有路,过河要有桥,没有桥就要船。解放大军就要渡过怒江,进军拉萨。卓波,请你告诉我们,他们把船藏在什么地方?”
吉村说:“他们把船藏在……”
“阿加巴桑,您的病好一点了吗?”隆珠推开门闯进来,故作亲热,打断了吉村的话。他后面跟着三个士兵,和过去不同的是都没有背长枪。
屋里的人用惊奇的目光看着他们,没有人答理。隆珠笑嘻嘻地说:“洛桑啦也在这里!”
他把一口袋糌粑和用羊肚子包着的酥油,放到巴桑卓嘎跟前:“宗本说,这几天你别来干活,好好在家养病。宗本怕你家里没有吃的,让我送一点糌粑和酥油来”。
巴桑卓嘎和吉村都没有理他,他也不管别人理不理。继续说:“吉村,宗本说有重要事要过江,你要辛苦一趟。”
吉村拍了拍身上的灰,冷冷地说:“找别人去吧,我刚回来。”
隆珠伸出大拇指说:“谁不知道你是扎青渡口最能干的船工,船开得稳,开得好。坐别人的船,宗本还不放心呢。”
吉村不知道宗本是不是真要过江,不愿去。巴桑卓嘎虽然不相信宗本会发善心,但害怕他们下毒手,对儿子说:“孩子,你就去一趟吧!”
隆珠赶紧说:“对,快去快回。回来好照顾阿妈。”说着连拉带推把吉村带走了。到了门口,吉村回过头,看着洛桑要说什么,隆珠却抢先说:“洛桑啦,你们坐,我们先走一步。吉村很快就会回来。”说着硬把吉村带走了。
看着隆珠不同寻常的举动,洛桑警惕地说:“旺扎真的要过江?”
邓珠走到门口,一种不祥的预感掠过心头,他说:“野兽的花纹在外头,人的计谋在里头。谁知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
当天,吉村没有回家。第二天上午,吉村还没有回家。
同志们都为吉村的安全担心,正在想办法要弄清他的下落时,小次登急急忙忙跑了进来,他到高志诚跟前,扑通一声跪在跟前,带着哭声说:“高站长,请你们快去救吉村哥。”
高志诚和同志们赶紧把他扶起来,连忙问:“吉村在哪里?”
小次登急得话不成句,断续地说:“昨晚半夜我听见有人走动,又听见用皮鞭抽打声,可是没有听见有人喊痛,连哼也没有哼一声。过了一会儿,几个士兵抬着一个长东西,好像是人,送到土牢里关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是吉村?”高志诚想把情况弄确实一些。
小次登说:“今天一早,我去找隆珠,听见宗本在他房子里说话,我悄悄地站在外面,听到宗本说:‘先把他关好,等汉人一走,和他爸爸一样,扔到河里喂鱼去。”
洛桑气愤地说:“真比毒蛇还要狠。”
小次登央求说:“高站长,吉村哥哥可是好人,请你们赶快去救他吧……”说着又要下跪。
经过一番周折,当高志诚和洛桑找到吉村时,他正在黑暗的牢房里。高志诚用手电横扫了一下,从黑暗的角落里突然发出一个粗犷沉闷的声音:“谁?”他们一下就听出是吉村的声音,高志诚和洛桑同时高兴地回答:“吉村,是我们。”吉村也听出是高志诚和洛桑啦。“我在这里。”他猛然站起来,可是啊哟一声,又沉重地倒了下去。原来,旺扎把吉村当成要犯,把他一人关在铁桶一样的牢房里还不放心,又给脚上了沉重的大木枷,使吉村连站都站不起来。他俩看见吉村的藏袍被撕成碎片,打得遍体伤痕,血肉模糊,又心痛,又气愤,扑过去,抱着他,亲切地说,“吉村,你受苦了。”
吉村万万没有想到金珠玛米会来这个地方。他就像被激流冲走,快要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遇到救生船一般,吉村紧紧抱住高志诚,含着泪花,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高志诚命令旺扎的小管家打开大木枷,和洛桑一起搀扶着吉村出来。
他们刚走出牢房,邓珠,小宋,小周,小次登和乡亲们都迎了上来,大家热情地向他问好,关切地询问他的伤势。看着这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听着这一声声感人肺腑的话语,吉村心里无比激动,泪水模糊了他的双眼,他好像经历了两个世界。
吉村怀着感激的心情,看着像慈父一样关心自己的邓珠大伯,又看着大家,然后用嘶哑而深沉的声音,用力地说:“我要带着金珠玛米去找船,帮助大军过江。”他那带血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微笑,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射出一道从未有过的光芒。
“对,大家都去帮助金珠玛米找船,造船,让大军早一点到拉萨!”人群中发出了一阵山洪暴发般的巨大声音。
一直在窗口偷看的旺扎,听见这声音,感到心惊肉跳,他怀着恐惧而阴暗的心理,赶紧把窗户关上。
正是“七八九正好走”的季节。这天,高志诚陪着部队首长来察看过江的情形。江边是一派繁忙而欢快的景象。兵站同志新造了几十只牛皮船,被旺扎藏匿的船只也全部找了回来,逃到山里的船工和群众,也陆继回家了,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做好,大部队到达扎青后,便不失时机地开始渡江。此刻,他们看见身穿长袍,身上裸露的藏族船工和身着草绿色军装的解放军战士,在一只只牛皮船上齐心协力,奋臂摇浆,牛皮船在波涛汹涌的怒江之上,劈波斩浪,随着澎湃的江水,一起一伏,向西飞驰。高志诚高兴地对首长说:“藏族同胞为我们架设了一条通向拉萨的吉祥彩虹。”
这时,洛桑和吉村他们划的那只大牛皮船,满载着战士靠岸了。吉村高兴地举起浆,向首长们挥舞致意,并用他那雄浑豪放的声音,唱起了一首新编的藏族民歌:
哈达不要太多,
雪白纯洁就好;
朋友不要太多,
结识金珠玛米就好:
我的心呀,
就像盛开的格桑花。
其他船上的船工和岸上的人们,也跟着唱了起来。这歌声越来越雄壮,越来越高亢,压倒了怒江的波涛声,在峡谷中久久回荡,回荡!……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
——搜救转移400多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