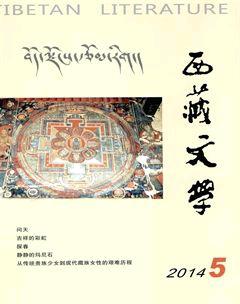探春(外五篇)
南泽仁
我时常从睡梦中醒来后赤脚走出家门,走出院门,站在平牛板上方闭眼冥想:我打开了一对深藏已久的翅膀,朝着天光轻盈飞翔。我看到所有的森林、云朵都朝着一个方向赶赴;我看到了白天和夜晚,太阳和月亮都有头有脸。后来,我又看到了一座荒芜、寥落的小城,城中有处静谧院落,坐北朝南围了一层楼的平顶房。院坝一半用作晒太阳和种指甲花,另一半栏了篱笆,分成了无数小块,供给院内的人当作菜园。它们暴露在从早到晚的阳光下。
它是九龙县文化馆的院落,我与奶奶随父亲的调入搬来这里,我们栖居在北面的两间套房里。东面的房屋紧挨后山,因为潮湿,平顶房上又加筑了一层新楼房。尔叔背着吉他,牵住他远道而来的订了娃娃亲的新娘,第一户入住到了二楼左边第一套房内。每晚,他都会在昏暗的白炽灯底下弹一些零碎、忧伤的曲子,他拨动琴弦的手指白皙而修长。左边第二套是我父亲的卧房,外面一间摆放了两张藤椅和一张实木书桌,其余部分立满了书架,架上挤满了各类书籍。里面一间只放了一张床,每天中午他都要午睡,且睡得很沉,我会潜入外面一间,找薄本书籍来阅读。原本找着就要悄悄离开的,可很多时候读得入神就蹲身坐在了书丛中,忘记上课。时间成了一枚蜘蛛,在书柜与房顶间结满细密的往事。楼梯右边的第一间是翁扎家,他有一脸毛茸茸的络腮胡子,喜欢打猎,家中时常只剩他的妻子和一对女儿。妻子叫三咪,皮肤白净,细眉大眼,一条又黑又粗的发辫盘绕头顶。她身体瘦弱,时常咳嗽,像黛玉。从门口经过。总能闻到从屋子里弥散出来的中草药味。一对女儿喜欢来我家玩耍,我们会展开一块毛巾,把一个布娃娃包裹起来,悉心喂养。每次尽兴之时,三咪都会站在二楼顶,朝坝子中间喊:哦——纳措!她们就会瞬间消失在我面前。
翁扎家的隔壁由警察阿萨借住。他着装讲究,每次见他,他的白衬衫都会陪衬一条整洁的领带,深红的、暗红的、浅红的。他在外地读大学时带回来一位回族新娘,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她高挑,文静,在县广播局当播音员。她一来,广播里的预报就跟电视节目里的普通话很好地衔接住了,大家觉得文化生活很有质量。不久他们就添了一个女儿,接着一位回族婆婆就来到了她们的生活中。婆婆会弄各种面食,锅盔、面块、面条,他们的生活过得很滋润。再后来,这院坝内又来了十几位回族男子,他们驾驶东风汽车,在县城周边运载木料或是在矿山运输矿石。他们集体住宿在文化馆隔壁的国营食堂。他们不吃猪肉,每隔一、两个月,就会买回一只草羊栓住在院内的苹果树下,宰杀,开膛破肚。苹果树上挂着那只羊头,整个院落装盛在它惊惶的蓝色眼球里,寂静而安详。回族婆婆背上背着小孙女,帮着他们烹饪羊肉,忙前忙后。他们个个吃得有滋有味,我们却不习惯闻到那浓重的膻味。没有运输的时候,他们会在院落的长凳子上闲散地坐成一排,晒太阳,细碎地说着自己的方言。我放学归来,在他们整齐的注目下回到家中,接着我会趴在窗前看着他们的背影,他们都戴着白布帽子,干干净净的样子。
那时,秀英小姑在读县中,她每个周末都会来我家洗衣服。她把天蓝色的毛线编在发辫里,垂在胸前,纯净且好看。那些回族人中有一位叫小马的长得眉清目秀,他会在我经过院坝的时候向我问起关于秀英小姑的事情。于是,在一个酸梅花盛放的寒假里,我和秀英小姑瞒着奶奶和父亲坐上了小马的汽车,去了乃渠之外的洋桥沟口。一路上酸梅花开得红艳,小马就会停下车来,与我们一起欢喜地在山坳里攀岩,折枝,直到整个驾驶室花香扑鼻。秀英小姑嗓子很好,小马请她唱支歌曲,她就婉转地唱了《泉水叮咚》、《牧羊女》、《草原之夜。》小马笑了,脸红得比我手捧的那束酸梅花还要透彻。秀英小姑一路上显得比原本还要矜持,秀气。我坐在靠车窗的位置,看着满山的翠竹和酸梅花想,他们这是在恋爱了吧!恋爱原来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一个月过去了,桃花也开了,开在春天里。小马和那些回族人都回青海去了,因为阿萨和他的回族新娘离异了。
重绿
叶脉是季节的掌纹,一棵接着一棵蓬勃年轻的柳树,撑开我一路到头的安宁。
我听到一颗心距离我越来越近时,河水宏大的歌唱瞬时远逝。这时节,除了纤弱的指甲花,所有的柳树仿佛遭遇了一场婚礼,凌乱无序地等待着凋零亦或孕育。一场大雪降临后。这个小城突发奇想的为每一棵光秃的柳枝垂挂了无数在暗夜里也会闪耀的塑料彩球,直到柳树开始舒展嫩芽,它们才会被华丽褪去。遗失一颗,落入路人孤零零的心情,在无风的枝条上轻轻地飘来荡去,无从碰触。
每天我都要穿过柳丛,到达这个院内。阳光时有时无,忽然间觉得它原本的安静,像梦境。数年前,我在这里居住过的,我曾为了一条鱼蓄了一池子的清水,鱼没有进人水池就从我手中滑落,不知去向了。我一直在找,每看见一个水池我都会凑近去找,我能够认出,它与所有的鱼都不一样,它不喜欢水。这个院内几株樱花开的时候,最让人内心繁盛了,所有的事物都像石头一样好端端的存在。零落时也是如此盛大,迷茫的白。我时常会立在二楼的窗前望去,院中央,六棵硕大的白杨树生生的把一另栋楼隔离开来,隐秘处似有似无,很多情况下,它并不存在,除非从树下走出一位穿红衣裳的_人来。仰望最远处的天空下。一匹青山上橘红的缆车像数颗迷惑在秋天里的果子,串起来来回回地穿梭,时间不具意义。二楼的门外是向上、向下的楼梯,还有一处长长的回廊。没有人经过的时候,我会打开十指,其间穿梭,微风从指缝间滑过,心灵就会长出一对轻盈的翅膀,飞向很远的方向……
入夜,我听着自己的呼吸,打开你的诗集。每一个字迹,都是由一根银丝线串起的一颗颗绿松石,它的绿像是一只孔雀看着另一只孔雀清澈的眼神。
问路
一出门我就会迷路,不过我会问路。
我还是去了燃灯寺北街,单位的办事处就设立在那里。这条街道嘈杂得很,街道两旁的人做着各种营生,有麻抄手,午后就会关门闭户了;有酸奶厂,从早到晚的开着;有一店子没有名字,只在晚上开,里面亮着粉红暗淡的光线,显得清闲;还有一个店门口一直挂着一只花圈,晚上关门也不收回去,任其从早到晚地开着越来越陈旧的白花。
那时,我的父亲就住在蓉城,我问路,穿过眼前这条街道就到达了父亲的居所,叩开他的家门,他看到我,笑得那么好,好像经历了一场不紧不慢的绵雨,在开门那会儿雨忽然就住了。父亲的居所极其简朴,最朝阳的窗户前放置了一张偌大的红木写字台,台上放着一叠稿纸,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蓝墨水字。我们的谈话总是不多,偶然停住,又轻轻接起。我想要传递一些关于我母亲和妹妹的讯息给他,可是,说着说着我就看到了窗外的阳光照白了他的两鬓,于是我又开始轻描淡写地为自己的话圆场:妹妹家牧场上的牦牛已经上百头了。她们说今年还要买十几头,冬天当做菜牛卖了。父亲皱眉说,牲畜不要养得太多,有命债;我说,妹妹家的四眼藏獒下了六只小藏獒,有人出高价买,她们就卖了两只,换回一辆摩托。父亲又说,卖狗不好的。俗语说:这世卖狗,下世讨口。你回去要让她送人吧,太多了自己也养不了,就送给那些温和的人家,也会善待它们;我想说说母亲,但终是没有开口,都过去了……
我只在门卫处停留了片刻,无意走进院内,门卫胖姨明显瘦了,见我,那笑容极浅。那时候我们进出都会相互欢喜地点头,父亲时常让他们来家取些牛肉或是瓜果。父亲人胖,走路回来,经过门卫处,胖姨和他的爱人总会麻利地给父亲端出凳子,让父亲歇息片刻,他们夫妻俩就站在父亲左右两旁,等父亲讲几句笑话,然后开怀大笑。胖姨的眼睛很小,一笑就只剩下一线缝。父亲起身,胖姨会拿回凳子,若是见到父亲手中提有物件会接过,送父亲上楼。如此和谐。
胖姨用手擦了门口放置的破旧沙发让我落座,之后她与我同坐。我们说着一些不相干的话题,胖姨每看我一眼都会把眼神收回去,又重新放在我的肩上或是手臂上,到最后,我们都没有话说,一道沉默。离开时,我与胖姨道别,她眼眸好亮,只是一低头一线泪就垂下了,落在这样一个尘世。
晚间,我寻得一处距离燃灯寺北街的很远的地方寄宿,我想要沉实地睡上一觉。入眠,父亲就来了我的梦里,他牵住我的手,那么温热,我们走了好长的路,到了一个拐角处便停步了。只见几位僧人搀扶着一位年长的僧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父亲让我与他一起叩拜,年长的僧人伸出手,把掌心放在我的额头上加持。
我想要问父亲抑或僧人,接下来的路。梦却在这样一个清冷的异地醒了过来。
过年
布的记忆里从未有过与阿普、奶奶、父亲、母亲一起聚守过年的景象。记忆存放在他们各自的东西南北中。
冬日的太阳总是那么朗照着,偶然会有风从麦垛上掠过,传出一串干燥的窸窣声响。山岩上的酸梅树结满了花苞,画眉鸟在枝头飞来又飞去,花苞就打开了,显露淡黄清浅的蕊。春,这般来到。茨易的十二户人家在除夕这天都各自备足了菜肴,相互宴请。布的父亲还没有归来,家里只有奶奶跟布两个人。清早,奶奶去屋后的水岩边采摘一围裙的白花回来,用它洗尘。院落寂静安宁,奶奶褪去包裹布一身的皮袄,将她放入木桶内。盛来热水,细流地将水顺从布的脊背往木桶内渗。热水没过布的下巴时,奶奶开始搓揉那些白花,直到泛出淡绿的泡沫,泡沫映照无数朵太阳。奶奶把它们涂抹在布的周身为布洗尘,布欢喜地用指尖去碰碎那朵朵太阳。洁净后又为布穿上那身皮袄,还从怀中取出一朵她精心用各色篙子染成的牛毛花扎在布的头顶上,作为送给布的新年礼物。布有多么好看,奶奶的笑容就有多么灿然。
等布不再带那朵牛毛花时,继母来了。她是美丽的。她的手腕和腰带上缀了红红绿绿的小珠子。她行走起落像一场小雨落在叶片上一样好听,清新。她的左眼下有一颗豆大的红痣。夜里看它像一颗泪滴。她带给布一件黄底绿碎花的衬衫,布穿上它,陪衬长长发辫,茨易的人们都说布长得像她继母。布的衬衫越穿越短,发辫越蓄越长。妹妹出生了。布背着妹妹,发辫垂在胸前,那花衬衫就显露出布的肚脐,布不住的往下拉它。冬日的太阳很快就走过了天空的一半多,那时是饥饿的。除夕。父亲还没有归来。继母在公社的伙食堂蒸熟了一笼又一笼的白馒头,揭盖时,蒸笼的雾气缭绕着继母和馒头。等蒸笼里剩下最后一个馒头时,继母终于把它偷偷地递给布。馒头那么烫,衬衫又那么短促,布不知到要把它藏在那里才好。那是公社的馒头。布记忆不起是怎么把馒头吃了。只是布如此深刻地想念着她们。
布能供养奶奶时,依旧只有奶奶和布两个人一起过年。布觉得自己把日子过成了一条河,又薄又凉且无休无止。布很犹豫,为奶奶着想的时候布把筷子拿得很短,不然就近嫁了还带着奶奶一起生活。布为自己着想的时候,又把手移到了筷子的最上头。希望有个人能把自己带走,远远地,最好在深山里头。他领着布回去过年,他的父母一看见布就会牵住她的手,不停地摩挲、摩挲,仿佛等了布已是许久、许久。他还会带着布去爬屋后的那片山林,回来时拾捡些柴火。入夜,一家人围坐火塘听他讲许多许多布从未曾听过的故事。他那么睿智,笑容展露整齐洁白的牙齿,他看布的每一眼都会看到心里去。因为总是想象,所以现在布竟不会拿捏筷子而上不了席面了。(有俗话:筷子逮得短,嫁人就近;筷子逮得远,嫁人就远。)
今又逢过年,布如此追忆,想要找回,愿用所有的时光倒退。
八月
八月。
十五,月亮如期而至,只是被暗沉的云层遮挡住了,我们没能会面。一年一度的中秋,凭此珍贵。
十六,带了雍贝去朝拜观音阁,还是要穿过那个窄巷子,沿108步石梯往上走。石梯两旁的房屋还是那么陈旧,门户安然紧闭。门口随处可见一小堆崭新的瓦砾,时间仿佛刚刚从这里经过,不曾妨碍通途。石梯笔直向上。仰望处,阳光泼洒下来,睁眼,异常难受,情绪仿佛困倦已久,想要垂泪亦或沉睡。一个修长的影子跌入石梯,一位满身沾染了白浆的工人,手提半桶白浆从上至下,在我们面前经过后就径直去开启石梯边上的一间屋门,接着又随手关闭了门户。门上贴着一张字条。写道:出门记得关灯,进门记得上锁。阳光下,无声无息。
等到登上最后一步石梯,就是这座小城的后山公路了。一路有来往汽车疾驰掠过,一股热风从地面卷起迎面扑来,雍贝用手护住眼睛,我用手护住额上刘海。观音阁的脚下有两、三处摊点卖香火。走向最近距离的香火店,方寸间,大娘手捻佛珠,安然静坐。见我们凑近,起身相迎。我说买香火,她微笑,语言柔和,逐一指出每一小捆香火的名字:心想事成、长命百岁……随意买了,沿一路的风马经幡朝庙宇走去。借一处破旧碗盏中燃动的灯火,引燃香火,随手插入院中一个巨大的铜制香炉中,就去朝拜菩萨。庙宇因地势略显促狭,进入殿门,抬头就觐见了菩萨立在一盏莲上,眉目慈善,温暖。与雍贝在殿堂朝拜菩萨,起身,一位阿珂喇嘛微笑走来,送与我们一人一根婉转着两个小结的被加持过的红丝线。谢过阿珂,走出大殿转向右侧紧挨着的另一个小殿,殿中供奉有几尊金刚罗汉佛,神色各异,逐一望去,内心就历经了一场春秋,一场雪,整个冬,放晴。
逆风,漫步回归,经幡招展。回望观音阁,紧依山势而建,简洁、安宁、祥和。听说,曾有一块巨石从观音阁的后山顶上滚落,险些就要砸到观音阁时,却忽然转向观音阁不远处滚落,观音阁安然无恙。路的边上,卖香火的大娘与我们亲热道别。另外两位稍微年长的老婆婆各自安坐两处,面前摆放的香火、酥油在阳光下默然审视着尘缘。
天,晴朗。心情,像微笑一样。一生一世的恬淡,凭此珍贵。
时光静止
总会在一场淋漓的夜雨声中醒来又睡去,雨城的冬日,像暮年和归处。
日渐陈旧的楼房、街道身陷碧水青山而云遮雾绕。太阳一出,就被青衣江面的锯齿山峰割伤。天,终日落泪,用所有的湛蓝和明丽为太阳疗伤,一次次听风说起,青衣江是个胸襟宽广的女子。
接连数日小雨,等不到放晴。姑姐撑开三把雨伞,一片晴天就在我和雍贝头顶上方盛开。这趟,我们要去登距离雨城不远处的一座青山,传说她林木葱茏、四季青碧。在旅游车站搭乘开往景区的白色商务专车,半小时,我们就抵达了。因为是雨天,又过完了年假,游客稀少,宽敞的观景车只载了我们三人就往山上驶去。公路两旁用铁丝网围栏隔着密匝的阔叶林、竹林。车窗玻璃外层沾满雨水珠子,不时滑落成线。导游是位年轻的女子,一直埋头玩微信,她自说自话:“凉山那方发生火灾了,说是一个疯子放的火,禽兽!”迎面,一道高大紧闭的铁门,随景观车临近分别朝左右两边自动打开。导游依旧埋头说话:“车已进入猛兽区,不要拍打车窗玻璃,以免惊吓猛兽。”我们屏住呼吸,随一道道自动打开的铁门,看着车窗外密林中缓慢掠过的老虎、狮子、棕熊、野狼。它们体态轻盈,不急不躁,在林间走动,站立,抑或蹲身歇息,早已习惯了头顶飘渺的细雨及车窗内注视的目光。
进入可行走观赏的动物园林区,我们便下车步行,由一路的指示牌导航前行。
一处假山环保的土院中,几只驼羊和一匹小马驹站立雨中,见有人来,驼羊就围拢上来。淋湿的驼毛光滑柔顺,如卷发,一缕一缕垂下。一位管理人员手拿几个小纸袋阔步朝我们走来,说是卖饲料,十元一袋,买下可喂食它们,驼羊的嘴唇就已经凑到了我们手上。饲料是用水浸泡过的饱满的玉米籽,放几粒在掌心,一只驼羊就热爱的食用起来,其它几只便知趣地走开了。小马驹则躲到不远处机警、敏锐地观望。
斜坡,拾级往下。眼前出现了一头白牦牛,仿佛电影《转山》中的一场梦境。一位五十开外的男人,手牵住从牦牛鼻孔穿出的麻绳,见到我们,便立马祈福通白般地念叨:“观音的坐骑,牛魔的妹妹,路过的神仙要不要骑上去留影。”它来自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相比黑牦牛,实属珍稀。它秉性豪迈不羁,此刻却温顺,眉目低垂。一对角上扎满了红红绿绿的绸子,通体的白毛被梳理得丝丝缕缕。经他耳畔这么念叨,白牦牛似乎早已淡忘了自己原本是谁,身在何处。
山路起伏,转折,通向一个宽阔平台。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迎面袭来,接着两峰高伟的骆驼就立在前方了,一峰见着有人靠近就朝空旷的平台边沿走去,身影孤独。另一峰,不停地来回走动,地上的稀泥合着它的粪便,不时散发令人作呕的气味。游客从旁路经过,脚步匆促,掩鼻而过。我走近它,它那么孤傲,一座山一样的冷峻。我们是第一次相见,它目空一切。我却暗自纳罕它突兀的驼峰和仰望的高度。
门口,一块糊满稀泥的小牌写着猜谜语:骆驼的驼峰用来储存什么?我想,是水。答案就在背面,写着:脂肪。骆驼的眼、鼻、耳,睫毛、平足等所有一切都是为沙漠和远行生长的。不是所有的屈膝,都会有大风袭来,这是骆驼的本能。
离开骆驼,一条小径,逶迤穿竹林过去,偶然一只五彩鸟雀从路上扑哧飞过。一只深红羽毛的鸟儿在小径中央走走停停,也不飞离。路人经过,要为它的美丽轻轻绕行。静静凝听林中各种鸟雀鸣唱,陌生而聒噪,这一路并非偶遇。此中,手机来电的蝉鸣也跟着响起,一只蓝色孔雀从身后的一棵树上忽然忒地,接着拖着长长的金翠没于密林深处。电话那头是一位守护卡瓦格博的诗人,他说去探春了。走完林中,通过一方人工岩洞,洞口设置了一处木雕长椅,椅子的左右把手上分别停落着两只蓝色孔雀,他们一动也不动。拍照要付钱,与孔雀合影要加双倍的价格。姑姐说,你那么喜爱孔雀,去合影吧,不然遗憾了。爱孔雀是因为它洁净的品质,与它靠近,希望是三只孔雀的相遇。只是,我忽然到来,那么仓促,没来得及整理好蓝色的羽毛。
时值正午,我们观赏到了动物的行为表演。
在一处绿色雨棚遮风挡雨的小型表演场地,一群鸟儿分别栖落于几位管理人员臂弯,整齐登场。一只被称作公主的白色鹦鹉尤其出色,爪子和嘴壳并用,随不断变幻的音乐缓缓升起彩旗;有节奏地滚动小球;展开翅膀轻轻舞蹈;识别游客递来的钞票额度。其它鸟儿安静等待,主持人报出它们名字时,它们别离枝头一般拖着脚抓部系住的长长细铁链,从管理人员臂弯依次纷纷飞出。
等到鸟儿们退场,两头庞大黑熊分别挽着两位驯兽师的手,摇摆登场。它们骑单车、翻筋斗、跳恰恰。模样憨态可掬。每次完成一项表演,它们都会卯足全劲地奔走到驯兽师面前索要食物,吃完继续尽其所能。那些食物是一种强盛欲望的佳食,为此,它们险些想要开口讲人话了。
七八只小猴登场时场面最凌乱而热闹。它们表演走钢丝,双手举着花束、头顶小球,也顶碗,动作伶俐。一只小猴在走钢丝途中拒绝走完最后一程,就翻身下去了。管理人员用力一拉套牢在它颈上的绳子,小猴被迫滚到了他面前。他发怒朝小猴的腹部猛踢一脚,脸就红了。小猴双手抱头护着,我心就痛了。那刻,我站起来了,后来又坐下了。我无力为小猴做点什么。管理人员接着又一拉套牢在小猴颈上的绳子,小猴便顺从地爬上钢丝继续表演,极其认真。表演完毕,其它小猴都站立钢丝上将手中的花束和小球巧妙地抛向管理人员手中。而那只被踢的小猴却伸长了手臂,亲自把花束和球递到管理人员手中。它还幼小,却要学会忍耐和讨巧。小猴的经历触到了我的记忆。原来,我是个胸襟不宽的女子。
主持人报节目,猛兽表演。在另外一个通道口,一群老虎和两头狮子带着自身的英武和威猛傲然上场。相似于一些人与生俱来的秉性,隐忍以及伟大。它们登梯,瞬间越过时空一样的距离,越过驯兽师设置高空中的一道独木桥及桥上紧密的梅花桩。我心随它们穿行,它们偶然会张大嘴露出锋利的牙齿面朝观众,完成一次意味深长的喘息。它们已被驯服,与所有登场的动物一样。我想,那驯服的过程不是靠近它们说些感心动耳的话,也不是用手抚摸它们的毛皮,一定不是。
一曲葫芦丝《月光下的凤尾竹》,一头庞然大物就登场了。主持人说,它是来自缅甸的大象姑娘。它怀念家乡,只要听到葫芦丝的乐曲,它就会翩翩起舞。果真,大象随曲子登上了不足三米宽窄的一个方凳上,一起一落,体态笨拙而富有节奏地为大家展示舞蹈。背井离乡,这个词汇用在此处,如此相投,也如此心酸。表演结束,主持人说,大象每天要耗尽大量食物,有爱心的观众可买下管理人员手中的苹果亲自喂食它。我与雍贝买了好几袋以示犒赏大象姑娘,大象见到苹果就把长长的鼻子温柔地伸向我们,展开杯盏大小的鼻翼,吸住苹果后放进嘴巴,接着又伸来索要。
表演是在几声零落的鼓掌中结束的,雨还在落。
这一路到头,我行走,沉思,自省,仿佛自己是一只与山林失散许久的禽兽那样无措。登上山顶就是出口了,漫天瞬间飞舞轻清雪花,回望眼下青山,一派飘渺迷茫。时光静止,你在听吗?
责任编辑:次仁罗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