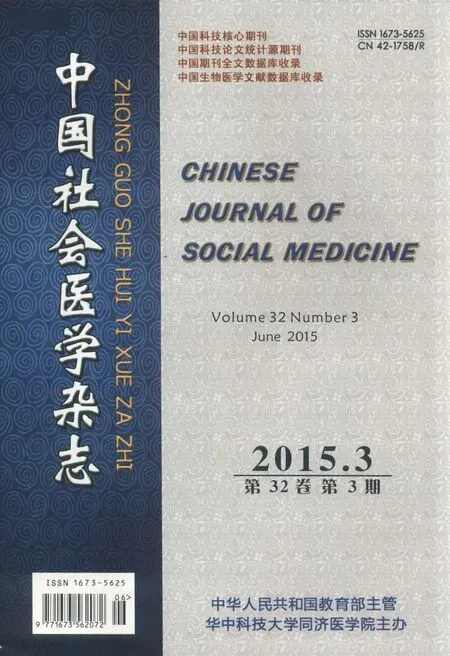关于加强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初级卫生保健的探讨
程怀志, 郭斌
2009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新的医疗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呼吁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以及建立一个更强大的公共卫生与初级卫生保健体系。社区卫生服务是以初级卫生保健为重点,融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功能等为一体的,向人们提供基层医疗服务。新医改后,我国把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的初级卫生保健提上了议事日程,对于控制慢性病、急性传染病的预防等意义非凡。
1 初级卫生保健的重要性
1.1 初级卫生保健是实现卫生服务公平与效率的关键
2009年的新医改,我国政府再次强调了基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初级保健的重要性[1],即人们享有基本医疗保健的权利,而不应因经济困难、交通不便、时间原因等因素导致的应就诊却未就诊或应住院却未住院的情况出现。但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居民卫生服务需要无法及时转变成有效的卫生服务需求的问题,与此同时,还有部分人群过度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以致出现了卫生服务利用不公平。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卫生服务系统的公平性在191个国家中排名第188,位居倒数第4。究其原因,我国专家一致认为,公平性较差主要由于初级卫生保健及预防较为薄弱。而研究表明,一个有效的初级卫生保健体系能够调整其他健康决定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减少可预防的死亡,并且改善与提高卫生服务系统的协调性与持续性,初级卫生保健是实现卫生服务公平与效率的关键[2]。
1.2 初级卫生保健能够加强并促进预防服务
《2008年世界卫生报告》强调,应该更加重视预防,强化初级保健,而不是依赖专家护理或生物医学干预。2004年美国国家卫生保健差异报告指出,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服务的居民要比一般人群接受更多的预防服务。所以初级卫生保健能够促进获得预防服务,减少可避免的住院,改善整体卫生状况,减少人们之间的健康差距。数据表明,初级卫生保健的提供可以保障出生时较高的期望寿命与较低的婴儿死亡率,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率降低、特定疾病死亡率降低、可避免的死亡率降低、可避免的住院情况减少以及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提高[3-4]。当然,初级卫生保健人均医生拥有量也能够减少负面影响,如关于全死因死亡率的收入不公平、心脏病死亡率以及癌症死亡率[5]。2003年SARS危机的暴发就暴露了我国卫生保健系统的缺陷,警示我国不仅仅需要关注对公共卫生设施的投资力度,而且还要关注初级卫生保健以及社区中的预防服务。
2 我国初级卫生保健演变过程
自1949年以来,我国卫生保健系统经历了3个时期:①以公平为导向的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9年);②以效率为重点的市场经济时期(1979-2003年);③致力于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新医疗体制改革时期(2003年SARS之后)。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公共卫生以及初级卫生保健都取得了一些进步,仅3%的GDP健康支出就满足了国家的基本医疗需求,健康状况迅速改善,因此,中国“赤脚医生”模式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
但自从市场经济引入我国以后,由于政府过度依赖市场机制,因而减少了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投资,即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50%下降到了2002年的42%。这种剧变导致基层医疗机构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同时也进一步削弱其提供具有社会效益的公共物品的意愿及能力,如预防、免疫等。为将其利益最大化,基层医疗机构不得不把重心放在增加盈利上,而不是更普遍地满足卫生保健系统的目标。在这种体制下,许多基层医疗机构不得不破产倒闭,仅存的基层医院也转向提供盈利性的卫生服务,而不是强调初级卫生保健及预防服务。1997-2001年期间,卫生保健系统瞄准的是高级医疗机构的增加,重点强调专科服务以及高端技术服务,基本上忽略了初级卫生保健的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成为卫生保健系统中最不发达和最脆弱的部分。
由于这些变化,基层医疗机构成为了低质量服务的象征,与大医院相比,基层机构中提供服务的医生被认为是缺少竞争力或者是不专业的。2003年SARS灾难性暴发凸显了卫生部门的失职,同时,也暴露了现有公共卫生及其卫生系统的薄弱点。此后,我国政府再次确定了初级卫生保健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尽管困难重重,但初级卫生保健重新确立以及政府的支持似乎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数据表明,与2009年相比,2010年以社区为基础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就诊患者增加了28%,2011年增加了16%,2012年又增加了14%[6]。
3 存在的问题
3.1 基于社区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资金不足
尽管我国政府一直强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便利性,但却忽略了由于其资金不足所致机构设备陈旧、资源缺乏、药品不全、卫生人员技术水平不高及其学历普遍低下等问题,从而导致人们对其信任度不高[7],因此出现大医院就诊人满为患的失衡状况,2012年大医院的就诊量是社区初级卫生保健机构的3倍[6]。我国医学专家和卫生政策专家都有这样强烈的共识,他们认为多数患者能够在初级卫生保健机构获取更适宜的治疗,事实也的确如此[8]。2009年颁布的卫生服务报告阐述了对以社区为基础的初级卫生保健的兴趣,但是新医改并没有对其卫生人力进行重大投资,也没有对其机构公共资金增加投入。正是因为这些都没有变化,所以想要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初级卫生保健系统一直是缓慢发展的。
3.2 全科医生收入普遍不高,发展受限
我国大部分医学生在毕业后都努力争取进入大医院工作,因为那里的医生不仅能获得更高的薪水,而且也能够享有较好的声誉和良好的职业发展,但我国大多数的全科医生自医学院校毕业后都缺少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机会。同时,由于政府对卫生服务机构投入有限,这些机构,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不得不通过获取其他收入以维持生存,比如极度依赖医药收入,数据表明,2007年以社区为基础的初级卫生保健70%~80%的收入都是源于药品提成[9]。但自从2009年我国实施基层医疗机构“零差价”政策后,社区医生的收入进一步受到了限制。
3.3 基层医生技术水平有限,竞争力较弱
全科医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具有学生数量有限且教育经验不足等特点。全科医生并不具备专科医生所拥有的更专业的医疗技术;同时,大医院高学历医务人员所占的比例远远要高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6]。所以一般情况下,人们认为愿意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医生都是教育水平较低、不能在大医院胜任的人员,而这种认知模式已经破坏了患者对这些机构以及在此工作医生的信任。这样也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社区医生的水平不高而减少了愿意在这些机构接受卫生服务的患者数量,反过来又降低了有能力的医生在社区工作的意愿。
3.4 缺乏完善的双向转诊制度
我国这些以社区为基础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并不是作为医疗保健系统中相辅相成的组成部分,而是与大型医院之间存在共同竞争的提供者(医生)和消费者(患者)。遗憾的是,由于基层医院长期提供低水平服务而很难吸引患者来此就诊,卫生保健机构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也加剧其财政问题,并进一步抑制了政府对公共卫生和初级保健的投资。所以,多数居民患病后依然信赖大型综合医院来寻求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也就是他们认知的高质量的卫生服务。至今,这种局面仍未得到扭转。
3.5 基本药物目录的局限性
2009年基层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零差价”药品政策有效地降低了患者的现金卫生支出。但是由于基于社区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存在基本药物品种短缺、部分药品采购不到以及部分患者的用药并不属于基本药物目录范围等问题,从而导致患者如果想要获取这些药品,还需去大型医疗机构。正是由于在以社区为基础的背景下,药物的可得性受到了约束与限制,一些患者对于使用这种常规性卫生服务资源望而却步。这也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想法,认为以社区为基础的初级卫生保健提供的是低质量的卫生服务。
3.6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过于重视医疗而忽略了其他功能
尽管新医改方案提高了基层医疗机构的地位,但是无法保证为其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所以这些努力所获得的短暂成功从长远来看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资金有限,大多数基于社区的初级卫生保健仍不愿意提供“非营利”的公共卫生服务,他们更愿意提供具有直接经济效益的医疗服务,而忽略其他诸如预防、保健、康复等服务功能。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消失不见了。多数以社区为基础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仍然像是小型医院,而不是作为社区健康的守门人来提供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4 对策及建议
4.1 加强对初级卫生保健的投资
投资不足在我国公共卫生以及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中仍持续存在。对此,政府应该在肯定基于社区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重要地位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政策支持和增加资金投入,并监督落实到位以及随时追踪资金的流向,同时也要保证这些资金投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4.2 发展我国全科医学,提升人们的信任度
要想改变全科医学不如专科服务的观点,关键就是给全科医生提供继续教育与培训的机会,提高其竞争力,加强职业发展规划,并提高其工资待遇;同时,建立一个有关全科医生的专业协会[10],即制定专业及规范其行为的标准,这样的独立性不但有利于全科医学的发展,培养高素质的全科医生,还有利于提升人们对其信任度。
4.3 扩大社会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尽管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强社会医疗保险的实用性,并且增加对基于社区的初级卫生保健的报销范围及报销比例,但迄今为止这些努力仍是不够的。政府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补偿比例并扩大报销范围,尤其是预防服务,并进一步修订基本药物目录,以适应居民多样化的卫生需求。
4.4 建立双向转诊制度
政府应鼓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大医院之间的患者进行双向转诊,这样将有助于提高整个卫生系统的绩效。争取做到小病去社区,大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同时,政府需要制定相应的法规或财政奖励来建立双方合作关系,明确他们之间不应是竞争关系,而应为互补关系,二者之间并没有利益冲突与刺激。
4.5 医患双方信息透明化
尽管我国政府作了许多努力来恢复患者对基于社区的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以及全科医生的信任,但效果欠佳,而建立一个透明的医疗信息机制将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时,多给患者提供参与其中的机会,比如,让患者有机会秉承公正公平的原则来评估全科医生的绩效,并且有权利给医疗机构提供信息反馈等。
综上所述,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的初级卫生保健对居民就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发展与完善任重而道远,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J].中国劳动保障,2009,(5):48-53.
[2] Jonas S.An introduction to the U.S.health care system[M].NY:Springer Publishing,2003.
[3] Shi L,Macinko J,Starfield B,et a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mary care,income inequality,and mortality in US States,1980-1995[J].J Am Board Fam Pract,2003,16(5):412-422.
[4] Weisz D,Gusmano MK,Rodwin VG,et al.Population health and the health system: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voidable mortality in three nations and their world cities[J].Eur J Public Health,2008,18(2):166-172.
[5] Starfield B,Shi L,Macinko J.Contribution of primary care to health systems and health[J].Milbank Q,2005,83(3):457-502.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3.
[7] Hung LM,Rane S,Tsai J,et al.Advancing primary care to promote equitable health:implications for China[J].Int J Equity Health,2012,(11):2.
[8] 张雪,田文华.家庭医生制度的“守门人”作用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3,30(2):115-117.
[9] Karen E,Winnie Y.Hospital competition under regulated prices:application to urban health sector reforms in China[J].Int J Health Care Finance Econ,2004,4(4):343-368.
[10] Wang H,Gusmano MK,Cao Q.An evaluation of the policy on community health organizations in China:will the priority of new healthcare reform in China be a success?[J].Health Policy,2011,99(1):3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