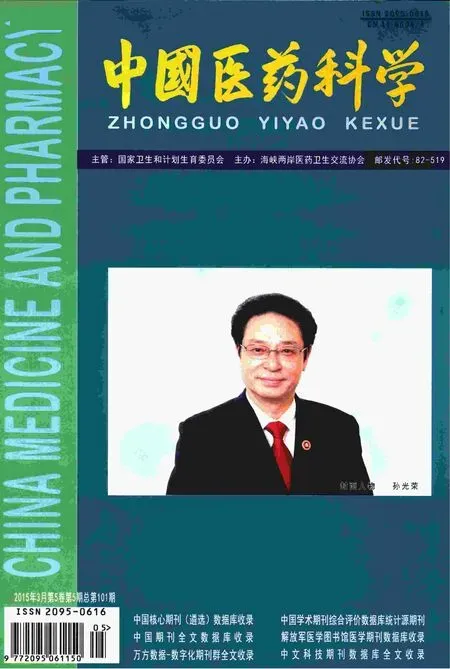浆细胞性乳腺炎62例临床诊疗分析
常志坤
辽宁省铁岭市中心医院乳腺科,辽宁铁岭 112000
浆细胞性乳腺炎(plasma cell mastitis,PCM)是一种非细菌性乳腺炎性病变[1],是以乳腺导管扩张、浆细胞浸润及管周纤维化为特征的病理改变,多发生于中青年妇女,偶见于男性及儿童[2]。临床表现多样,常见乳房肿块、乳房红肿、乳头凹陷、乳头溢液、乳瘘等。临床极易误诊为恶性肿瘤,因此对不同类型的浆细胞性乳腺炎进行临床、影像学分析是提高术前诊断正确性的关键,从而对各型患者采取个体化的手术方式,提高治愈率,并避免对患者造成过度损伤。现将我院乳腺科2010年6月~2013年5月收治的浆细胞性乳腺炎患者进行临床分析,并探讨不同类型手术方式和时机的选择,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均为女性,年龄16~62岁,中位年龄37.6岁。未孕8例,有生育史54例,其中8例生产后未哺乳。左乳32例,右乳26例,双乳4例,病程约4d ~ 3年。单发病灶50例,多发病灶12例。根据临床表现可分为:(1)乳管扩张型:5例,不能触及肿块,为超声、钼靶检查发现乳管扩张,乳晕区异常回声,乳头后方结构紊乱等,其中3例伴有乳头溢液,2例为淡黄色液,1例为脓性。(2)非炎性肿块型:22例,乳晕区肿块13例,乳晕外肿块5例,混合肿块4例,其中6例为多发灶。(2)炎性肿块型:18例,有明显包块,局部皮肤发红而无脓肿形成,3例有乳头溢液。(4)脓肿型:13例,皮肤红肿范围较广,其内部有波动感,6例有乳头溢液,2例为淡黄色液,4例为脓性。(5)窦道型:4例,3例为脓肿切开术后形成,1例为脓肿破溃形成。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手术治疗,肿块型行术中冰冻病理检查及常规病理检查,脓肿型行切开引流,切下周边少许组织送常规病理检查,均经病理确诊为浆细胞性乳腺炎。手术方式:病变较小者行局部麻醉,大者行全身麻醉,脓肿切开引流10例,肿块切除、象限切除43例,单纯性乳房切除7例,皮下乳房全切并行假体植入2例。
2 结果
2.1 乳腺超声
所有患者均行超声检查,可见导管扩张、低回声包块、液性暗区,回声不均质,有的见散在强回声点,形态不规则,边界不清晰,多见血流信号丰富。
2.2 钼靶检查
行钼靶检查31例,表现为肿块或腺体密度增高、成片絮状影,边界不清晰,伴颗粒状圆形钙化影,散在粗大、细颗粒状钙化,乳头凹陷,乳房皮肤增厚。
2.3 MRI检查
行MRI检查8例,表现为斑片状、结节状病灶,单发或多发,边缘模糊,乳头凹陷,乳房肿大,局部皮肤水肿增厚。
2.4 血象检查
均行白细胞计数,其中6例患者白细胞增多。
2.5 细胞学检查
乳头溢液细胞学检查12例,可见炎细胞、脱落上皮细胞,均未找到瘤细胞。
2.6 病理检查
肿物穿刺病理检查15例,见炎细胞浸润,乳腺导管扩张,3例诊断为浆细胞性乳腺炎。
2.7 随访结果
经过1~4年的随访,其中9例复发,其中10例行切开引流术,复发3例,复发率30%;43例行肿块切除或象限切除复发6例,复发率14%;7例行单纯性乳房切除及2例皮下乳房全切并行假体植入患者均未复发。
3 讨论
PCM的病因迄今仍不明确,目前多认为PCM的发病可能与乳腺导管退行性变及受到异常激素刺激导致乳腺导管分泌功能异常、乳头先天畸形引起乳管闭塞、细菌感染及自身免疫等有关。Ming J等[3]认为先天性乳头内陷可能是PCM的主要原因。在治疗上目前仍认为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方法[4]。
PCM的病理特点复杂,大多表现为导管上皮不规则增生,导管扩张,管腔扩大,管腔内有大量上皮细胞碎屑及含脂质的分泌物积聚,导管周围组织纤维化,并伴有淋巴细胞浸润,后期病变可见导管壁增厚、纤维化,导管周围出现小灶性脂肪坏死,周围可有大量组织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5]。根据其不同病理过程将其分为不同的期别[6]:导管扩张期、炎块期、脓肿期和瘘管期。本病晚期阶段,由于扩张导管中刺激物可溢出管外引起管周以浆细胞浸润为主的炎性反应,故称为浆细胞性乳腺炎[7-8]。
PCM临床症状复杂多样,主要表现为乳房急性炎症、乳房肿块、乳头内陷、乳头溢液等,发病早期往往无明显症状。本研究依据疾病临床表现不同,将PCM分为五种类型:(1)乳管扩张型:病变早期,临床多无明显症状,不能触及肿块,无炎性改变,可有乳头凹陷、乳头溢液,超声显示乳腺导管扩张,内含低或极低回声区。(2)非炎性肿块型:乳房肿块形成,但无炎性表现。(3)炎性肿块型:有明显包块,局部皮肤发红、皮温可升高,无脓肿形成。(4)脓肿型:皮肤红肿范围较广,其内部有波动感。(5)窦道型:PCM病程后期,脓肿切开或脓肿破溃后脓液流出,久治不愈而形成瘘管。各种类型PCM在诊断、鉴别诊断、治疗、预后等方面各不相同,现分别予以分析。
乳管扩张型患者多无临床症状,仅表现为乳头凹陷、导管扩张、管壁增厚,有时合并乳头溢液,此时肿块还没形成,诊断多需依赖超声、钼靶及乳管镜及脱落细胞行病理检查,治疗上提倡早期干预,果断手术的原则,可清洁乳头,保持乳头乳晕区洁净,给予内陷乳头手法复位,乳头溢液较多的患者可以轻柔手法挤出分泌物,有条件可进行乳管的清洗,以防止疾病进展,但当出现明确肿块难以控制时,要果断进行手术治疗,把病变导管连同所属腺叶作锥形切除,手术同时矫正乳头畸形,保持术后乳房外形美观,此型治愈率高,本研究手术切除5例患者,随访未见复发患者。
非炎性肿块型PCM的主要临床症状是乳房肿块,无红肿,此类型极易被误诊,常常与乳腺癌混淆[9],主要可以从以下几点鉴别:浆细胞性乳腺炎肿块的位置多数处于乳晕下方和乳头乳晕附近,肿块多呈片块状,其长轴多与乳腺导管走行一致,且常与皮肤粘连,乳头溢液多为淡黄色、浆液性或脓性,乳腺癌患者的乳头溢液多数为血性,血性溢液在浆细胞性乳腺炎性反应状中较少见,有国外文献报道,乳头溢液患者中33%为PCM[10]。早期即可出现同侧腋淋巴结肿大,质软,压痛明显,随病程缓解可逐渐缩小或消退。超声检查肿块横径往往大于纵径,形态不规则,边界模糊,无明显包膜,呈不均质低回声,病灶内部多有扩张乳管,并可见部分液性暗区向周围腺体渗入,与乳腺癌“蟹足样”改变有所不同。本研究非炎性肿块型PCM共22例,术中经冰冻快速病理检查除外恶性病变后,将病变乳管、肿块连同周围部分正常腺体、脂肪组织局部扩大切除、象限切除15例,单纯性乳房切除5例,皮下乳房全切并行假体植入2例。两例肿块切除术后复发,行单纯乳房切除。由于切除范围大,创腔多放置引流管并加压包扎,若病变切除不彻底容易复发,引起切口处破溃,形成难以愈合的慢性瘘管,需要再次手术切除残留的病变,本研究两例复发患者考虑可能因肿块较大,为追求术后外形美观,手术切除不彻底有关。
炎性肿块型多为急性期PCM,类似急性乳腺炎表现,乳房肿胀疼痛,触之疼痛加剧,但皮肤微红或暗红,白细胞计数一般正常或稍高,有文献报道PCM可能伴有厌氧菌感染[11]。此类型诊断一般不难,但需与急性乳腺炎及炎性乳癌鉴别,急性乳腺炎多发于孕期或哺乳期妇女,起病急,多伴有高热,白细胞计数常增高。炎性乳癌皮肤颜色多呈紫红色,皮肤呈橘皮样改变,斑片状水肿,红肿面积占乳房1/3以上,边界清楚。急性期PCM肿块较大,治疗上多以手术治疗为主,可辅以理疗、中药等治疗[12],手术一般自乳头根部切除所累及乳管及病变乳管所在的整个腺叶。如果合并细菌性感染,应先行抗感染治疗,局部硫酸镁外敷等,肿块缩小或皮肤肿胀消退后行手术治疗,2例患者经抗感染治疗后仍形成脓肿,最终行脓肿切开引流术。此类型复发率较高,本研究炎性肿块型行肿块切除、象限切除16例,4例复发,复发率25%,但均早期发现,脓腔范围小,或仅为窦道形成,追加二期病变导管及肿块扩大切除,1例复发者行单纯性乳房切除。
脓肿型患者脓肿一般位于乳晕区,单发或多发,如果脓液不多,可按炎性肿块型处理原则行手术扩大切除,如果脓液多、脓腔大、波动感明显,此时脓液中常夹有粉刺样物,此类型需与非哺乳期慢性乳腺脓肿及乳房结核相鉴别,乳腺结核可见潜行性边缘及苍白肉芽肿,豆渣样分泌物,脓液涂片可找到抗酸杆菌,对这类患者术中均应切除部分组织行病理检查明确诊断。此期患者需行脓肿切开引流术,每1 ~ 2日换药一次,早期脓腔以甲硝唑冲洗,待伤口愈合,周围炎症消退后再行病灶彻底切除病变的乳管及周围的炎性肉芽肿组织。13例患者行肿块切除、象限切除3例,单纯性乳房切除2例,脓肿切开引流8例,其中脓肿切开引流术患者有3例复发。
窦道型PCM属病程后期,脓肿切开或脓肿破溃后久治不愈形成瘘管,Hanavadi等[13]认为术后感染为瘘复发的主要因素。手术切除瘘管及病变组织是主要的治疗手段,术中经瘘管口注入甲蓝以明确瘘道的走行方向及范围,手术切除范围包括瘘口周围皮肤、肿块及部分正常腺体组织。本研究4例窦道型患者,3例为脓肿切开术后复发形成,1例为脓肿自行破溃形成,经手术切除后,均治愈,随访未见复发患者。
PCM各类型并非完全独立,同一患者往往伴有多种症状同时出现,或随疾病进展可相互转换,因此要根据不同病期采取不同的个性化治疗方案,正确选择手术时机及彻底切除病灶是治疗成功及决定愈后的关键。
[1] 耿翠芝,吴祥德.浆细胞性乳腺炎的诊断与治疗[J].中华乳腺病杂志(电子版),2008,2(1):20-23.
[2] Rahal RM,De Freitas-Junior R,Paulinelli RR. Risk factors for duct ectasia[J].Breast J,2005,11:262-265.
[3] Ming J,Meng G,Yuan Q,et al.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rgical modality of plasma cell mastitis:analysis of 91 cases[J].Am Surg,2013,79(1):54-60.
[4] 李琳,卞卫和.温阳托毒法治疗浆细胞性乳腺炎体会[J].实用中医药杂志,2008,24(11):738-739.
[5] 唐文,何山,郑轲,等.浆细胞性乳腺炎的临床研究[J].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2008,22(11):810-811.
[6] 马榕.乳腺导管扩张症临床病理特征与治疗对策[J].中国实用外科杂志,2009,29(3):215-217.
[7] 左文述.现代乳腺肿瘤学[M].第二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395.
[8] 吴意赟,梁定,殷立平,等.彩色多普勒超声对浆细胞性乳腺炎的诊断价值[J].解放军医药杂志,2014,26(9):82-84.
[9] 陈佩详,崔国忠,王德斌,等.浆细胞性乳腺炎误诊为乳腺癌21例分析[J].中国医师进修杂志,2011,34(2):58-59.
[10] Vargas HI,Vargas MP,Eldrageely K,et al.Outcomes of clinical and surgical assessment of women with pathological nipple discharge[J].Am Surg,2006,72(2):124-128.
[11] Dixon J M,Ravisekar O,Chetty U,et a1.Periductal mastitis and duct ectasia:diferent conditions with diferent aetiologies[J].Br J Surg,1996,83(6):820.
[12] 崔进军,宗林,陈松,等.辨证分型结合理疗治疗浆细胞性乳腺炎35例[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9(4):689-690.
[13] Hanavadi S,Pereira G,Mansel RE.How mammillary fistulas should be managed[J].Breast J,2005,11(2):108-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