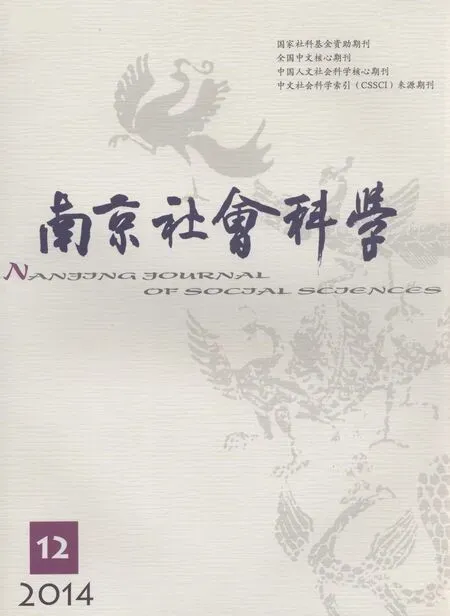从超越到圆融:论华严宗对印度大乘佛学的几处误读*
吴学国 王斯斯
从超越到圆融:论华严宗对印度大乘佛学的几处误读*
吴学国 王斯斯
印度大乘佛教的精神是超越的,它否定一切现实存在的自为真理性,坚持色空、性相的本体论区分;反之,华夏精神是自然的,把体验当下现实中万物的圆满具足、互生互容、融通无滞的整体性当成最高智慧。华严的几个最基本的观念,如三性一际、理事圆融、事事圆融,分别来自对大乘唯识的三性说和般若的色空不二、诸法平等思想的独特解读。通过这种解读,华严以理事的融通一如弥合了大乘对色空、性相的本体论区分,以诸法现存的圆满具足消融了大乘对现实存在的否定,从而使华严思想实现了从超越到圆融的转移,也就是脱离印度大乘佛教本来的精神而向华夏自然精神传统靠拢,因而这是一种根本的误读。这种误读,由于华严思想本身是在华夏精神传统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应视为华严受后者影响的结果。
般若;三性一际;理事圆融;事事无碍
印顺法师曾指出中国佛学的最大特点是圆融①。华严、天台和晚期禅宗皆以圆教相标榜,而其中以华严论圆融最彻底。这种圆融的思维,旨在消融现象与本体、此岸与彼岸、心与物的本体论差别,解构实体的自为存在,从而返回到当下存在(即自然)的圆满自足、流通无碍,即消解精神的超越,回归自然思维。圆融思维的一切存在皆现成圆满且互具互入、互相转化、流通无滞的观念,尽管被当作极高的智慧,但其实只具有自然的、宇宙论的意义。
圆融思维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传统存在根本矛盾,却与华夏传统的自然思维具有本质的一致性。大乘佛教旨在通过性空思想否定一切现实存在,并确立那绝对超现实的空性、法界为存在的真理,因此它的精神是超越的。这种超越性表现为色与空、性与相、真与俗的本体论区分。大乘的般若智慧不仅否定现实存在,而且否定超越的空性真如——如果空性被当作一种现存实体的话——所以是空亦复空。大乘以色与空、性与相、真与俗二边皆毕竟空、不可取不可受故,强调其为不二、平等,这是双非双遣。它试图由此打破精神可以依赖的一切当下、现存的存在,以实现精神的绝对超越,这就是大乘所谓“无住无得”之境。般若就是精神无限地否定其当下此处,而迈向绝对自由的空境的运动②。总之,大乘佛教的精神是超越而非圆融的。反之,与印、欧传统相比,华夏精神以注重现实、崇尚自然、缺乏超越性为最大特点③。它以最直接、朴素的自然为存在的真理,以回归最原初的自然、守住存在的当下此处为生命的理想。因此它的思想始终属于自然思维范畴,没有经历对于自然的否定,未曾领会过印、欧思想那种彼岸和此岸、现象与本体的分离(本体论区分),因而它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包含、相互贯通、相互转化的,世界是一圆满、流通的整体。华夏传统思想坚持形质、体用、本末的一元无间、相即融通关系,未尝有过佛教那种色空、性相的分剖。比如道家就相信道与物是相摄相入的:道既覆载万物,又内在于事物之中,甚至施及瓦甓、屎溺(《知北遊》)。道家还标榜道通为一、齐物玄同,甚至物我同一(《齐物论》),要求在道的同一性体验中,冥契万物的融通一如。华夏思想也没有产生过印、欧那种超越时空、因果的实体观念,因而认为一切存在物都是相互贯通、互摄互入的。比如阴阳、五行就是相互包含、相互生成、相互转化的;它们都不是有确定自性的实体,而是构成一个融贯、流通的整体。总之,与印、欧思想的超越和分裂相反,华夏传统思想就是自然、融通的,本质上与华严的圆融思维一致。中国佛教在华夏传统思想背景下展开,其实是印度大乘佛教与华夏文化这两大精神传统对话的产物。但是强调存在之自然、融通的华夏传统,当然很难接受大乘佛教的超越思维,它自然会努力淡化这种超越,融通后者带来的分裂的世界观,圆融的思想即由此形成。
本文以下要阐明的是,华严宗一些最基本的思想,如三性一际、理事圆融、事事圆融等,尽管皆可回溯到印度大乘佛学,但与后者的精神实质是根本矛盾的,却与以自然、融通为特色的中土自然思维更一致;它们的形成正是由于华严宗在华夏自然思维传统的影响下对大乘佛学的诸法平等、色空不二等教义的理解产生了严重偏差,这使得大乘原先的性相隔别、色空双遣、万法皆空的超越立场,被性相一如、理事无碍、事事圆融的自然、现成思维代替,使印度大乘毕竟空的绝对超越蜕变成现前具足的圆融智慧。
一、从“三性各别”到“三性一际”
首先,三性一际的思想,作为华严宗的最基本教义之一,就是通过华严对唯识三自性说的独特解读形成的。我们将表明通过这种解读,三性说原有的超越思维被圆融思维替代,因而三性说完全丧失了原先的旨趣,故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严重误读。
唯识的三性或三自性说,即以为世间一切存在,皆包含三方面的存在意义,即遍计所执自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三自性的核心是依他起性,此即依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因,借其他诸种助缘而生的一切法,即是诸识。遍计所执性谓凡夫于此诸识作虚妄分别而生的实我、实法等境相。圆成实性即于依他起性上断除遍计所执而显现的诸法实性,亦称法性、真如。如世亲释云:
谓若说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诸如是等永无异门,依遍计所执自性而说。若说诸法如幻、阳炎、梦相、光影、影像、谷向、水月、变化,诸如是等虚妄异门,依依他起自性而说。若说诸法真如、实际、无相、胜义、法界、空性,诸如是等真实异门,依圆成实自性而说(玄奘译,《摄大乘论世亲释》卷六)。
这就是说遍计是实无的妄有,依他是如幻的假有,圆成是如理的真有。可见唯识三性说,强调的是三性各别。同理,《摄大乘论》亦云:“若由异门依他起自性有三自性,云何三自性不成无差别?若由异门成依他起,不即由此成遍计所执及圆成实;若由异门成遍计所执,不即由此成依他起及圆成实;若由异门成圆成实,不即由此成依他起及遍计所执。”(玄奘译《摄大乘论本》卷二)。另外《成唯识论》亦云:“此三为异为不异耶?应说俱非,无别体故,妄执、缘起、真义别故。”(《成唯识论》卷八)这就是说,三性寓于同一识体,故非异,而有妄执、缘起、真义之差别,故非不异。唯识还提出识有虚妄(遍计)与真实(圆成)、世俗(依他)与胜义(圆成)之别(同上,卷九)。这些都是要明判三性的本体论区别。至于唯识持三性各别的原因,世亲释云:“若依他起与圆成实是一性者,此依他起应如圆成实是清净境。”(玄奘译《摄大乘论世亲释》卷四)盖唯识立三性说,服务于宗教的目的,其宗旨在于断除遍计所执、净化依他起、证得圆成实,因而要求严判三性差别;根据世亲的说法,如果以为三性同一,那么存在的妄执、缘起、真实三义便无从区分,大乘的去妄存实、破俗显真的修证就无从立足。唯识强调三性各别,宗旨即是要在修道中依次超越遍计、依他,即主观和客观的现实,证入一种超现实的真理,即圆成实性,从而实现一种绝对的精神超越。因此唯识三自性说的宗旨是超越的。这种超越性来自对般若空思想的继承。唯识三性说乃是从般若中观的二谛说发展出来的④。后者将事物的存在意义区分为真(胜义)谛和俗谛两种,其基本宗旨是真空俗有。全部现实性都属世俗有,皆是虚妄分别的产物;唯绝对超现实的空性才是胜义有,离虚妄分别。在此意义上,真俗或性相的分剖体现了精神对于现实的绝对超越。唯识三性说继承了这种精神超越。其以为圆成实性即胜义有,遍计所执是虚妄分别产生的影像,即中观所谓世俗有;而虚妄分别就是依他起的诸识,唯识亦称之为世俗有。在这里,尽管唯识把般若避免给予肯定性表述的虚妄分别明确规定为实有,但至少在早期仍以为在证得胜义有时,不仅遍计所执应当断除,导致遍计所执的虚妄分别即依他起也应当伏灭。这同样是否定一切现实性以证入绝对超越的空性真如,与般若学的宗旨是一致的。总之唯识强调三性各别,体现了大乘佛教原有的精神超越。
反之,华严宗论三性,旨在说明其一乘无尽缘起的三性真妄交彻,强调的是三性同一。对此法藏开示说:
三性各有二义:真中二义者,一不变义,二随缘义。依他二义者,一似有义,二无性义。所执中二义者,一情有义,二理无义。由真中不变、依他无性、所执理无,由此三义,故三性一际,同无异也。此则不坏末,而常本也,经云:‘众生即涅槃,不复更灭也’。又约真如随缘、依他似有、所执情有,由此三义亦无异也。此则不动本,而常末也,经云:‘法身流转五道,名曰众生也即。’……是故真该妄末,妄彻真源,性相通融,无障无碍(《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
在这里,法藏借用了《大乘起信论》的真如具不变与随缘二义的说法。他认为圆成实性就是真如、如来藏心,具有不变、随缘二义。一方面,真如一味,而随缘显现为依他似有、所执情有,故真如即诸法,此谓不动本而常末;另一方面在此随缘显现中,真如体性不变,而依他无性、所执理无,皆以真如为实质,故诸法即真如,此谓不坏末而常本。
然而与《起信》不同的是,华严的三性同一,乃是立足于性相圆融,认为既然诸法皆是真如(圆成实性)的显现,故真妄相彻、性相通融;妄与真、性与相都是互摄互入、相贯相容、一体流通、无滞无碍的。在这里,真妄、性相的本体论区分完全被打破,这是与《起信》完全不同的。在法藏看来,三性之间皆是互融互贯、相摄相入的。如他说:“此上三一一各融不二为一性故。总者所执是无。圆成是有。依他是俱。以真妄该摄二相尽故无二也。”(《华严探玄记》卷四)故于三性中,随举其一,即含容余二者。其中关键的是:(一)圆成与依他的圆融。如法藏说:“圆成虽复随缘成于染净,而恒不失自性清净。由不失自性清净故,能随缘成染净也。”(《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真如随缘转化为具染净的阿赖耶识,即依他起。在这里,华严强调的是真如与赖耶互容互摄、融然一味。正是立足于这种性相圆融,法藏对玄奘法相宗的性相各别进行了批评:“若依始教,于阿赖耶识,但得一分生灭之义。以于真理未能融通,但说凝然不作诸法,故就缘起生灭事中建立赖耶。”(同上,卷二)这是说在玄奘学中,性与相,或真如与生灭法不能融通,因而其宗义不够究竟。其实在这里,玄奘的持论才是真正符合印度唯识学本旨的。在这种性相圆融基础上,华严宗乃将生死与涅槃打成一片。其云依他起由分别一分成生死,由真实一分成涅槃,故非生死非涅槃,是故不可定说一分,“若见一分余分性不异,是故不见生死,亦不见涅槃”(同上,卷四)。因此华严圆融哲学的图景,是真妄交彻、性相互融、生死涅槃一际无异。(二)依他与遍计的圆融。《分齐章》说:“依他似有等,岂同所执是情有耶?答:由二义故,故无异也。一、以彼所执,执似为实,故无异法。二、若离所执,似无起故。”(同上,卷四)一方面,遍计是执识为境,由依他转化而成,其实质即是依他而无别体;另一方面,识依境起,真如唯因转化为遍计故,成为依他起。故此二性互为因果,且由同一圆成实性转化而成,所以是一际无异的。正如学者指出,主张依他和遍计的圆融一如,违背了唯识三自性说的原意,也是造成法藏与玄奘唯识冲突的重要原因⑤。另外,三性的有、无二义,也都是各自同一无异的。如圆成的不变与随缘,为同一真如故、不离不异故,是以二义全体相收、一性无二;依他的似有(缘生)与无性(真如),也同样是一体二面且无差别,故圆融不二;同理,遍计的横计(妄有)与理无(真如),亦是无二唯一性(同上)。法藏在此强调说:“非直二义性不相违,亦乃全体相收毕竟无二也。”(同上)也就是说二性是相互包含、相互贯通、融然一味。因此三性一际,举一全收,真妄互融,性无障碍(同上)。
总之,华严对唯识三性说的理解,是从三性各别转移到三性同一。正是这种读解决定了它与忠实于唯识本旨的玄奘学的冲突。华严的读解之所以是一种误读,就在于三性一际思想消融了三性说本来强调的真妄、性相、染净以及生死、涅槃的区分,也解除了大乘佛教实现绝对超越的努力,因此消解了三性说包含的精神超越,使三性说失去了原有的精神价值。这种误读使三性说的旨趣从超越转移到圆融。华严这种旨趣的转移,其实是脱离印度佛教传统而向华夏的自然思维传统逐渐靠拢。考虑到华严宗学是在华夏传统思维背景下展开的,这种转移应被认为是华严宗受后者影响的结果。
二、从“色空不二”到“理事圆融”
华严宗圆融思想的核心是理事圆融和事事圆融。所谓三性一际即旨在说明理事圆融。此外,华严宗还通过理事无碍法界观表明理事圆融的宗旨。华严初袓杜顺以十门开示此观,谓理遍于事门、事遍于理门、依理成事门、事能显理门、以理夺事门、事能隐理门、真理即事门、事法即理门、真理非事门、事法非理门(参见宗密《注华严法界观门》)。此即从十个不同方面观理事圆融,领会理由事显、事揽理成、理事互融无碍,乃至平等与差别一际无异,由此悟入法界无尽缘起的道理。其中最基本的是理遍于事和事遍于理二门。法藏释此二门义云:“理遍于事门,谓能遍之理性无分限,所遍之事分位差别,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何以故?以彼真理不可分故,是故一一纤尘皆摄无边真理,无不圆足。二事遍于理门,谓能遍之事是有分限,所遍之理要无分限,此有分限之事于无分限之理全同非分同。何以故?以事无体还如理故。”(《华严发菩提心章》)在这里,事是个别的事物,理则是普遍的实质;理与事互容相摄、互相圆具。其他诸门也是从不同角度阐明这种关系。华严宗还以水波喻和金狮子喻形容理事圆融的关系。如杜顺云理事如水与波:“高下相形是波,湿性平等是水。波无异水之波,即波以明水。水无异波之水,即水以成波。波水一而不碍殊,水波殊而不碍一。不碍一故处水即住波。不碍殊故住波而恒居水。何以故?水之与波别而不别故。”(《华严五教止观》)法藏云理与事如金与金所铸之狮子:“谓金无自性,喻真理不变也,随工巧匠缘,遂有师子相起。喻真理随缘成诸事法也。起但是缘,故名缘起。”(《华严金师子章注》)这些比喻清楚表明理与事不是形而上学的本体与现象的关系,而是一种宇宙论的质料和形器关系。理如水、金一样,是无差别的质料;事相如波、狮子,是理体随缘转变而成的形物。法藏还以金狮子喻表明理事是体用一元、本末无间的关系:“即此师子情尽体露之法浑成一块,喻师子相尽真金现前。繁兴大用起必全真,喻师子功用事事皆金。万像纷纭参而不杂,虽四像迁移,各住自位。一切即一皆同无性。摄末归本,不碍末也。一即一切因果历然。依本起末,不碍本也。力用相收卷舒自在。力显性起圆融法门无碍。故名一乘圆教。”(同上)这种体用、本末关系同样只具有宇宙论意义,它们只说明了自然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因此华严对理事关系的理解使理事、性相的本体论区别完全被抹杀。在这里,印度大乘佛教领会的那种空性真如对于现实存在的绝对超越,被华严的圆融智慧模糊化以至完全遮蔽了,所以理事圆融意味着佛教原有的精神超越之丧失。
尽管如此,华严的理事圆融思想仍是以印度佛学为根据,实际上它就来自华严宗对般若的色空、性相平等不二义的独特解读。如杜顺云:“心真如门者是理,心生灭者是事,即谓空有二见,自在圆融,隐显不同,竟无障碍。言无二者,缘起之法似有即空,空即不空,复还成有,有空无二,一际圆融,二见斯亡,空有无碍。”(《华严五教止观》)这清楚表明理事圆融观来自华严宗对般若色空不二平等思想的解读。我们将表明这种解读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完全背离了般若不二论的绝对超越旨趣,而逐渐融入力求冥契存在整体之圆满、融贯和一味性的华夏传统智慧。
般若学讲色与空、性与相、真与俗乃至世间与涅槃平等不二,其宗旨在于开示空有二边双非双遣的中道,由此表明大乘不取二边、无住无得的绝对超越或自由。如《心经》云:“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般若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亦云:“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离色亦无空,离受想行识亦无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一)色泛指一切现实存在、世间。空或空性则是超越现实的存在真理、彼岸。所谓“色即是空”,是说一切现实存在是性空如幻的,故不可住、不可得;“空即是色”,是说空就是色等的实性,而非离色别有自体,因而也是不可住、不可得的。《般若经》说菩萨依般若空智,观色空不异,从而达到彻底的无住、无得之境,得以“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同上)。因此,般若说即色即空、色空不二,立场是双非双遣,旨在开显真空不住空有、非有非无。真空不仅是色空,而且是空亦复空,甚至是非色非空亦空,“离四句绝百非”,不取二边,甚至不取不二边。故般若空智,就是精神的无限超越或否定运动。精神由此打碎一切枷锁、偶像,了无牵挂,实现了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而空性就是通过这种绝对否定运动呈现出来的存在真理,它就是存在的不可住、不可得性。
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承认华严宗对于般若色空不二平等义的理解非常独特。如法藏说:
色揽空成,如动波之收水;事含理就,似金器此随形。色依空立,空约色明。互夺则二义必亡,互成则两门俱现。现时即隐,故观色而常空;空时即显,故观空而恒色。色既非色,空亦非空。互有力而互无,互相成而互夺,故无生之义遂彰。由相成,故缘起之门乃现。色无自性,举体全空;空无自体,举空全色。色空无二,圆通一际,更使一通一碍,溥在相而未融;或隐或显,解在性而方中(《华严策林·九达色空》)
水波、金器之喻表明在这里,般若的色与空被理解为一种宇宙论的形质、体用、因果关系,这首先使这二者都成为实有的,于是般若的“色空双遣”就被转化成“理事俱如”。其次,在这里,般若的色空不二的中道,被理解成体用一元、本末相即、形质无间的圆融关系。法藏以金狮子喻表明色与空的体用相即、本末贯通、圆融无间图景,并把对后者的领会当作“一乘圆教”的究极境界(《华严金师子章注》)。杜顺亦以波水一如表明有空不二、一际圆融;二见斯亡,空有无碍;真妄交映、全体赅彻的道理(《华严五教止观》事理圆融观)。这些都旨在把色空不二理解为理事的一际无异。法藏还以色空相望各有四义,进一步阐明色空圆融之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疏》)。如空望于色,有此四义:一、显他自尽。谓以空即是色故,色现空隐。二、自显隐他。以色是空故,色尽空显。三、空有俱存。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隐显无二、互不相碍,故二俱存。四、空有俱泯。此谓空与有举体相即、一际无异,绝二边故,故二俱泯也。色望于空,准此应知。如此则色与空隐显自在,相即无阂,合为一味,圆通无寄。
总之,华严宗用体用、本末、形质的一元无间理解般若的色、空范畴,泯灭了二者的本体论区别,并在此基础上彻底消融二者的差异、隔阂,使二者成为实质同一的。它立足于这种抽象同一来理解般若色空不二,认为色与空是一际无异、显隐无间、相摄相入、圆融无碍、流通无滞的。于是色空不二成为理事圆融。华严还将这种圆融推到极致,认为理事的不异与异、二与不二本来也是一际无异的(《华严五教止观》事理圆融观)。
对比般若对色空不二的阐释,应当承认华严的理解是一种严重误读。因为般若说不二,并非旨在确立一种绝对同一或统一性,更不是要对两边进行折衷,而是对两边的真理性都进行否定,即空有双遣,由此领会空性、真如不可住、不可得的实相。然而华严理事圆融则把不二理解为两种现存、实在之物的相互同一和贯通的关系,这种理解完全丧失了般若不二论原有的双非双遣、不取不受的旨趣,以及对空性、真如的不可住、不可得性的本源领会,所以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导致的负面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不二”转化成“一元”、“空有双非”转化成“理事俱如”、色空俱遣(不取不受)转化为理事俱存,于是般若的无住、无得的绝对超越完全被抛弃了。另一方面,它使理事、色空的本体论区别完全被抹杀,空性真如对于现实的超越性被遮蔽,而且理事一如必然使修道论上所谓生死与涅槃、真与俗、染与净也都随之成为圆融一际的,这意味着佛教原有的超越理想之丧失。因此理事圆融意味着佛教原有的精神超越的沦丧。
华严宗对般若思想的这种误读,使它完全偏离了大乘佛教原有的精神,而逐渐靠拢甚至将自身融入了强调体悟存在之为融贯、流通、圆满的整体性的华夏传统。由于华严宗学本身是在华夏传统背景下展开的,因而这种圆融思想应当被认为是华严受到后者影响的结果。华夏固守当下的自然思维与般若的绝对超越思维的巨大反差,决定华夏精神在面对般若佛教时,首先必然努力将后者那无限地否定当下、迈向无住无得之绝对自由的思想重新拉回此处,亦即变“无住”为“有住”。这使得中国主流的佛学皆是依如来藏心性一如思想理解般若,因为如来藏思想把空性理解为实有的真如心,故毕竟还有所取、有所得,比原味的般若更能适应华夏精神传统。这种读解导致般若的绝对超越思维的沦丧。华严以《起信》等的如来藏思想为重要资源,自然接受了这种资源。其次,这种反差也决定华夏思维很容易对大乘的不二论产生误读。华夏自然思维传统没有经历印、欧传统的精神超越导致的现象与实体的分离,而是以体验万物的融通一如为智慧,因此很难接受印度大乘佛教理事、性相隔别的立场。当它试图用这种融通的智慧来领会大乘性相、真俗不二平等的教义时,就很自然地会把后者理解为万物的融通一如。
在华夏文化传统中展开的中国佛学,很自然会受到这种融通智慧的影响。我们以上分析表明了华严就是用中土传统的体用、本末、形质的一元思想理解般若不二法门,故华严对般若的理解就是站在华夏自然融通思维立场上的。正是这种融通思维促使华严思想进一步消解如来藏的色空、心法的隔阂,从而彻底消融了大乘佛教中理事、性相的本体论区别,从而导致事理一如思想的形成。总之,华严宗就是在华夏自然思维传统影响下,把般若的有无俱非、真俗双遣转化成圆融一味、理事皆如,这是一种根本的误读。
三、从“诸法平等”到“事事圆融”
所谓事事圆融或事事无碍法界,乃是华严圆融智慧之究竟。其说概言之,即谓以事理圆融一如故,一切事法皆互相涵容、互为因果、互融互贯、法法无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宗开此义为十玄门:一、同时具足相应门,谓一切诸法同时相互具足圆满、互为缘起、无碍无杂;二、广狭自在无碍门,谓一切诸法随其广大、狭小,皆相摄互容、任运俱现、各不相妨、自在无碍;三、一多相容不同门,谓一法与多法力用交彻,一能含多、多能含一,然一多历然可别;四、诸法相即自在门,谓诸法不但功用相入无碍,其体亦互容互即、融通无碍,一法即一切法,一切法即一法;五、隐密显了俱成门,谓一切诸法互即互摄、隐显同时、并存无碍;六、微细相容安立门,谓随一法能含一切法,且于中诸法各住自位、同时显现,如是相即相入、重重无尽;七、因陀罗网法界门,谓一切诸法相入相即、交互映现、重重无尽,如因陀罗网的无数宝珠;八、托事显法生解门,谓一即一切故,随托一事便显一切无尽之法;九、十世隔法异成门,谓处在不同时间点的诸法亦皆相即相入而不失先后长短等差别;十、主伴圆明具德门,谓诸法互为主伴、相依相属而不坏自相(《华严经探玄记》卷一)。此即所谓十玄无碍。华严以为一切诸法皆全具此十门,相即相入、无碍自在,层层缘起无穷。有学者对此评价道:“依法界缘起的思想,任何一法虽有自己独立的性相和特点,但这一法中也具足了任何其它法的性相。从这一思想出发,对任何一法的考量和分析只在在它与诸法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才能得到正确的把握。”⑥事事圆融其实就是一切事物皆相互包含、互为因果。这种关系只属于自然、宇宙论的领域。因此事事圆融思想已完全蜕变为一种自然思维。它与大乘佛教原有的精神超越已经失去任何实质的关联,而是向中土强调融通、圆满的自然精神靠拢。
华严对事事圆融思想的解释,一方面表明这种思想乃以般若的一切诸法平等无碍思想为依据。般若以一切法空、不可得故说一切法皆平等一味:“空即是平等。”(《大智度论》卷一百)“以一切作法皆是虚妄不实,如梦如幻,诸法平等,是为真实。”(同上,卷十六)“平等即是毕竟空、无所得。因无所得破有所得事既办,亦舍无所得。如是菩萨于有所得无所得平等般若中应学。”(同上,卷八十三)同样因一切诸法毕竟空故,说诸法各各无碍:“一切法无所依止,无所依止故无障无碍”(同上,卷五十三),“如来如相无有碍处,一切法如相亦无碍处”(同上,卷七十二)。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关于华严事事圆融的说法拿来对照。如杜顺说:“然此法者即全以无性性为其法也,是故此法即无性而不碍相存也。若不无性,缘起不成。……既全收性尽,性即无为不可分别,随其大小性无不圆。一切亦即全性为身,是故全彼为此。即性不碍幻相,所以一具众多。既彼此全体相收,不碍彼此差别也。是故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华严五教止观》)其中所谓无性性就是空,一切诸法以性空故,不碍相存,且平等、无差别。这与般若说平等、无碍具有相同理路。在更多情况下,华严宗是以理、事说空、有,因而以差别事相皆全摄一味理体作为诸法平等、无碍的依据。如云:“‘如此华藏世界海中,无问若山若河乃至树林尘毛等处,一一无不皆是称真如法界,具无边德。’依此义故,当知一尘即理即事,即人即法,即彼即此,即依即正,即染即净,即因即果,即同即异,即一即多,即广即狭,即情即非情,即三身即十身。何以故?理事无碍,事事无碍。”(《修华严奥旨妄尽还源观》)“今则理事融通,具斯无碍,谓不异理之事具摄性理时,令彼不异理之多事,随彼所依理,皆于一中现”,故一一尘中见一切法界(《华严经旨归》)。总之,华严的事事圆融思想,最基本的内容仍是诸法的平等、无碍,且同样以诸法性空为根据,在这方面它与般若说诸法平等无碍完全一致,表明它无疑是以后者为根据,是对后者的重新解读。
另一方面,从华严的上述读解,也可以明显看出它与般若的原旨有根本区别。这在于:一、空、有皆被实在化,空有关系被转换成理事的体用、本末、形质关系。在此基础上,华严把诸法平等理解为不同事相分享同一理性实质,把法法无碍理解为体用的一元性及实质的融通。这种读解,使般若的诸法平等无碍,完全丧失毕竟空的宗旨,蜕变为一种自然的同一、相即和融通关系,因而是一种误读。二、在事理的实在相摄关系基础上,般若的法法无碍思想,被理解为一种万物圆满互具、相融相贯、流通无滞的宇宙论图景。后者在印度佛教传统中根本不存在,而只属于强调事物的相互转化、流通、圆具关系的华夏自然思维传统。在这里,华严的解读全失般若毕竟空的宗旨,故亦是一种误读。然而在实在论立场上体验万物的合融一如、相互包含、流通无滞,不属于印度佛教传统,而属于华夏自然思维传统。因此华严的误读,就表现出脱离印度佛教的精神,而向华夏思维传统靠拢的趋势。这一趋势,由于华严思想本来就是在华夏精神传统的背景下展开的,故应视为中国佛学受后者影响的结果。
总之,华严宗的三性一际、理事圆融和事事无碍思想,分别来自对大乘唯识的三自性说和般若的色空不二、诸法平等思想的误读。这种误读以理事的融通一如弥合了大乘的性相分剖,以诸法现存的圆满具足消融了大乘对现实存在的否定。它意味着华严的立场从超越转移到圆融,因而使华严思想偏离了大乘佛教的本旨,而向旨在体验万物当下现存的圆满互具、相即相生、融贯一如、流通无滞的华夏自然思维传统靠拢。可以说这种误读决定了华严宗基本的形上学图景。由于华严的思想本身是在华夏传统背景下展开的,因而它的这种误读,应视为受后者影响的结果。当然,华严宗在这里也可能受到天台宗学的影响,但这并不违背我们的结论,因为一方面,天台的圆融思想(尤其是法界互具思想)也不属于印度大乘佛学,而肯定来自华夏传统影响,所以华严即使沿袭天台之学,也是通过后者间接受华夏传统影响;另一方面这种沿袭本身也是在华夏传统背景之下进行,因而也离不开这种背景的影响。
注:
①印顺:《印度之佛教》,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
②参见穆提《中观哲学》,华宇出版社1984年版,第360页。
③吴学国:《关于中国哲学的生命性》,《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④高崎直道等:《唯识思想》,华宇出版社1985年版,第310—316页。
⑤上田义文:《瑜伽行派的根本真理》,《谛观》第55期,谛观杂志社1988年版,第69页。
⑥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1年版,第116—117页。
〔责任编辑:金宁〕
FromTranscendencetoYuanyong:OnSomeMisinterpretationsofHuanyanSchoolofIndianMahayanBuddhistTeachings
WuXueguo&WangSisi
The spirit of Indian Mahayan Buddhism is transcendent, whereas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is naturalistic. Some fundemental concepts of Huanyan school, such as Non-difference of tri-svabhava, Lishi Yuanyong and Shishi Yuanyong were produced by mis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Buddhism of Indian Mahayan Buddhist Teachings, e.g. Tri-svabhava theory, Advait(non-two) of rupa and sunya, Sama(equalness) of all dharmas(beings). Those misinterpretations developed under influence of Chinese tradition of natural thought. They introduced the shift of Huanyan thought from transcendence to Yuanyong.
wisdom; Non-difference of tvi-svabhava; Lishi Yuanyong; Shishi Yanyong
*本文是中央基础研究专项基金项目“华梵之间:古印度吠檀多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研究”(NKZXTD1105)的阶段性成果。
吴学国,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天津 300071;王斯斯,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天津 300071
B946.4
A
1001-8263(2014)12-0037-08
——从体、相、用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