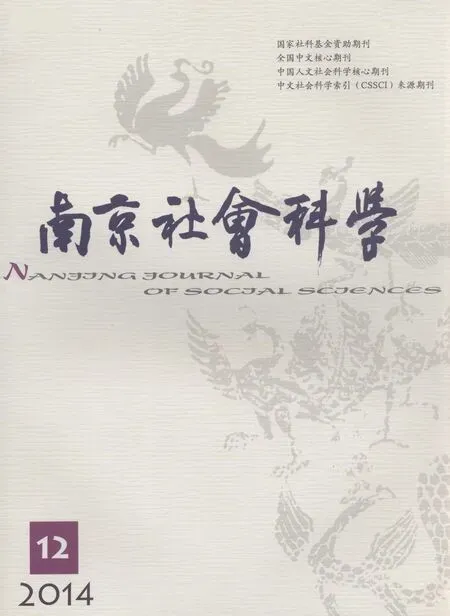论新型城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童 星
论新型城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
童 星
路径相同、功能一致、千城“一面孔”、管理“一刀切”一直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顽症。当前全国范围内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必须正确处理好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从城市发展机制理论来看,有“需求指向”型与“供给基础”型;从城市发展功能定位来看,有“综合全能型”与“人居人文型”;从城市与人口供养关系来看,有“人养型”与“养人型”;从城市发展路径来看,有“土地扩张型”与“人口吸纳型”;从城市人口规模来看,有“建制镇和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与“特大城市”。上述各类城市均有自身的长短优劣以及适合自身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各地应当因地制宜地选择城镇化发展道路,最后殊途同归: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
新型城镇化;城市发展机制;城市功能定位;城市与人口供养关系;城市发展路径;城市人口规模
近年来,路径相同、功能一致、千城“一面孔”、管理“一刀切”一直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顽症。许多城市都在“摊大饼”式地扩张,都以“国际化大都市”和“最佳人居城市”为发展目标;许多城市的产业结构高度趋同,功能定位极其一致,发展套路相当雷同,导致“城市的比较优势不突出,同构竞争现象频发,影响了差异互补功能的发挥”;①许多城市在征地、拆迁、城管中都出现了野蛮执法甚至暴力冲突。在当前全国范围内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形势下,正确处理好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至关重要。
一、“需求指向”与“供给基础”:两种城市发展机制理论
一般说来,关于城市发展机制的理论分为两大类:一是强调发展的动力在于外部需求的“需求指向”理论,二是认为推动城市成长的力量主要在于内部供给状况的“供给基础”理论。在计划经济年代,各地都按照“需求指向”理论来建设城市特别是新兴工矿城市。该理论认为城市中只有两大部门或两大产业,即基础产业和服务产业。基础产业是为城市外的需要服务的,比如工矿城市就是为城市外对工矿业品的需求服务的;而服务产业则是专门为城市内的需要服务的,比如工矿城市也要有一系列的服务部门来满足工矿企业职工的生活需求。显然,这种理论把基础产业看成是整个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命根”,因为外界对城市输出的产品需求越大,城市中的基础产业部门人数就越多,相应地,作为基础产业后勤的服务产业部门人数也可以得到增加,整个城市于是得到发展。在“需求指向”理论的指导下,长期以来我们在城市建设中重基础部门、轻服务部门,重第二产业、轻第三产业,重生产建设、轻社会配套。于是,不仅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项目“欠账”太多,吸纳劳动力的数量也非常有限,而且一旦当地自然资源的开采减少或枯竭,此类新兴工矿城市将面临严峻的可持续发展“瓶颈”。
城市发展的“供给基础”理论则认为,当工业城市发展到当地资源接近于充分利用时,城市的增长就取决于它聚集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能力。当一个城市在早期依靠自然资源的开采而扩大规模时,其基础设施、资金积累、技术也一定有了相当的规模和较高的发展程度,从而也就具有了从周围吸纳新的生产要素的能力来促进城市继续发展,即“城市的转型发展”。根据这一理论,甚至有的城市可以一开始就走主要从外部吸纳资金、技术、劳动力来发展自己的道路,当然这就必须首先搞好交通、通讯、房地产、水电气以及服务等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的硬件和软件。②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浦东新区、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和发展,浙江义乌、山东临沂的崛起,以及许多城市的新城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建设,都是如此。“供给基础”型城市具有交通、通迅、服务、基础设施、政策环境、金融体系、人才与劳动力、管理机制等方面的良好条件,使经营者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其价值,因而迅速发展成为经济中心。
当然,“需求指向”理论并非完全失效,该模式仍具有合理性。工业生产职能对于现阶段中国大多数城市来说仍是基本的职能之一,相当长时期内工业产值在城市经济总量中仍会保持较大比重,一个发展时间久、体系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对于城市发展也并不全是负担。但是,资源型工矿业城市的区位条件大多不十分理想,智力、信息、管理等资源缺乏,其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决定了它们难以成为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小城镇往往凭借历史传统和本地特有的自然、人文资源,走“一镇一品”之路,以特色产品拥有相当高的市场占有率,既满足了外部的需求,也发展壮大了自身。这也显现出“需求指向”理论的生命力。
同理,“供给基础”理论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并非万能,“供给基础”型城市建设道路也并非一定成功。特别是当全国各地城市都走“招商引资”、“筑巢引凤”、“跑部上项目”、“房地产开发领先”之路以后,产能过剩,“供”远远大于“求”,甚至造就出一些“鬼城”。这更加证明了凡事不能“一窝蜂”,必须因地制宜,实事求是。
二、“综合全能型”与“人居人文型”:两种城市发展的功能定位
“综合全能型”源于“生产全能型”,其城市定位产生于如下的背景:国家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各地都尽可能建立本地区相对独立和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尤其是工业经济体系,追求“大而全”、“小而全”。这种自成体系局面的形成和发展,是通过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体制来实现的,因而造成各地行政分割和彼此封闭。
从城市的政府机构设置上来看,不论城市的规模、人口,省里套中央的、市里套省里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体育、信息等领域都设立相应的部门单位,城市有驻京办事处、驻省府办事处,除了外交部之外,国家所有的机构部门都能在各级城市中找到它的“具体而微”者,所不同的只是级别高低、规模大小的区别。幼儿园、学校、工厂、医院、饭店、娱乐场所等等应有尽有。各城市的生产部门也是“大而全”、“小而全”,根据规划建厂生产,不考虑当地的自然、社会条件是否许可,为了计划指标的完成而立项。城市规模再小也是“五脏俱全”。
由此,政府是“全能政府”,城市是“全能城市”。正是由于其“全能”性,城市相对的独立性比较强,缺少与外界的交流和合作,只有城市领导人相互之间在完成计划指标或政绩上的竞争。自身传统的优势产业、优势项目得不到有效的发挥,而一些“水土不服”的项目由于政府的庇佑却得以保留。乍一看各行各业门类齐全,齐头并进,其实各行业间良莠不齐,优不能胜,劣不能汰。各个城市一定程度上能够自给自足,而这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经济结构严重影响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更遑论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当然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生产全能”有了一定的改观,但并未绝迹,因为全能的政府所主导的“综合全能”仍在不同程度上“重塑”或“再造”“生产全能”。
如果说“综合全能型”的城市定位关注单个城市“全面”发展的话,与其对应的“人居人文型”的城市定位则立足于人——满足人的需要,强调文化历史的存续,在此基础上发展城市,彰显城市个性与特色。人的需要是城市发展的直接目标,城市自身的规划由此应运而生。当代世界新发展战略与传统发展战略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将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作为基础与出发点。人是城市的主体,城市的发展不能忽视人在城市中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这一基本问题。
“人居人文型”的城市定位源于人本主义或曰人文主义的思想理念。人本主义(humanism)是西方人实现现代化的主导思想之一。它始于文艺复兴时期,更与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思想有密切的渊源关系。自18世纪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过程中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构成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哲学基础。③人本主义是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力的思想,其意在着力呼唤城市中一度迷失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核心的人际结合以及将社会生活引入到人们所创造的空间是其基本主题。④早在1933年,《雅典宪章》就提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居住、工作、交通和游憩,并强调了“人”在城市中的地位,指明了城市规划“以人为本”的方向。1977年发表的《马丘比丘宣言》对其进行了发展和修改,强调了自然环境与生活环境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并将理解和贯彻这一关系视为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1997年的《21世纪城市规划宣言》提出,当代城市规划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以人本主义精神规划设计和建设城市”。⑤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成为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它是自觉为人着想的开端,是经济发展型社会转向人文发展型社会的前奏。⑥我国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开始在城市发展中得到了重视。
“综合全能型”和“人居人文型”城市的并存,导致“国际化大都市”和“最佳人居城市”的并存,也为“城市群”或“城市带”的构建提供了依据。国际化大都市通常都是“综合全能型”的,最佳人居城市则必然是“人居人文型”的。老实说,一个城市要想同时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和最佳人居城市,几乎是不可能的。国际化大都市和最佳人居城市的结合,要通过“城市群(带)”的形成来实现。因此,各个城市应当在所处的“城市群(带)”中,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同一“城市群(带)”中的各城市则应依据经济与区域发展的客观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的藩篱,分工协作、功能互补,发展城际快捷交通,推进一系列同城化政策,实现整个“城市群(带)”的协调发展。
三、“人养型”与“养人型”:两种城市与人口的供养关系
就城市与居民的关系而言,除了彼此相互依存之外,还有深层的供养关系。笼统地说有两种:一种是城市和更多的周边地区的居民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维系着城市的正常运转与进一步发展——“人养市”;另一种是城市本身的现有条件,如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社会人文条件、经济产业结构等有利于城市和更多的周边地区的居民满足其生产生活需要——“市养人”。从这个角度可以把城市划分为“人养型”与“养人型”。
“人养型”城市中直接从事生产的居民的产出除了维系自身的家庭生活之外,还有部分被用于供养非必需的非生产者的开支,即一部分人的劳动在养活自己的同时还供养着另一部分人,甚至有时城市内部供养关系不能平衡,还需要这个城市以外的城乡居民(纳税人)来供养。这里所谓的供养关系,并非马克思所指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是指再分配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供养关系。典型的例证就是政府机关或其他非生产部门机构过度膨胀、冗员过多。这些“吃皇粮”的富余人员并不从事生产活动,也不直接创造价值,却要享受国家财政的分配,消耗资源和财富,无形中给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居民(纳税人)带来沉重的负担。这类城市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就需要越多的人来供养它们。
“养人型”城市则是指,现有的城市条件更有利于城市居民的创造性活动,有利于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有利于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城市良好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适合人居,合理的产业结构能够提供充分的劳动就业岗位,并且还能进一步吸纳一定规模的外来劳动力来充实本城市的发展需要。这类城市数量越多、规模越大,就越能供养更多的人口。显然,城市化就是要鼓励“养人型”城市的发展,抑制“人养型”城市的扩张。
可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沿海省份的各省会城市其城市综合实力或发展态势大多弱于省内另一个大城市,如广东的广州不如深圳,福建的福州不如厦门,浙江的杭州不如宁波,江苏的南京不如苏州,山东的济南不如青岛,河北的石家庄不如唐山,辽宁的沈阳不如大连。内地省份也常出现类似的情况与趋势。
省会城市在省内其各种便利条件是得天独厚的,原先的城市规模、经济基础都是省内首屈一指的。为什么发展会落后于那些原本基础条件不太好的后起之秀呢?其实,省会城市是政治型城市,有两级政府,除了本身的市政府外还有省政府。且不论省政府对省会城市管理的直接干预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必须看到政府不是生产部门,它是需要纳税人供养的。政府从扩大自身的政治影响出发来考虑进人,能够进来的都是进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系列的,随行迁入的配偶家属也多是“吃财政饭”的,都需要纳税人供养,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这样的群体规模越大越无积极意义。省会城市较之省内其他城市,需要供养更多的吃“皇粮”的人口。这类城市庞大的被供养群体不仅需要巨额财政拨款的支撑,还需要农民工的流入,凭借农民工来弥补城市中许多脏、苦、累及其他职业声望低的岗位的空缺。虽然这些岗位是不可或缺的,但充实这些岗位的农民工往往不被认为是当地人,城市居民不认可他们的市民身份,不给他们应有的权益和地位。较之其他非政治型城市,省会城市农民工的身份地位问题和城市融入问题更加明显。
那些非省会城市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定位,但是它们的发展多是基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借助先前按照供给基础方式规划建设城市,其间积聚了一定的生产要素,如较为充足的资金、成熟的专业技术、各行各业的人力资本等,加上本地区较好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城市自身的软硬件条件,较之省会那些政治型城市还少了过多的供养消耗。其城市本身在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还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籍此供养更多的人。
此外,城市的产业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与居民的供养关系。不同的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比较大,而第二产业的机器化大生产则在一定程度上排斥劳动力。一个城市能够提供的劳动岗位越多,也就能够供养越多的居民。城市产业选择在符合城市功能定位要求的前提下,还必须符合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当今社会,城市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第三产业正在兴起。城市集中了大量的人口和众多的生产企业,必然产生大量的、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行业,以交通运输、通讯信息、科学教育、商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得到蓬勃发展,第二、三产业共同构成现代城市的经济基础。对于城市发展而言,交通运输、通讯信息加强了社会交流与沟通,科学教育为社会发展积累了知识储备,商业服务业则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四、“土地扩张”与“人口吸纳”:两种城市化的发展路径
许多地方“城市化增长路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具体表现在政府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如撤县(市)改区、县区合并、建立开发区、大学园等来实现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导致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中等城市少不了内环、外环,大城市则有一环、二环、三环,城市越大,环路也越多,“人口城市化低于土地城市化”。⑦
其实,城市化更重要的是人口的城市化,它要通过吸纳农村人口的途径来实现。现在正在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就是要解决3个1亿人的问题,即1亿进城农民工转变为市民,1亿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居住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1亿中西部地区农民就近城镇化。显然,这3个1亿人问题的解决途径是不一样的。
首先看1亿进城农民工转变为市民。农民市民化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间的发展往往体现出阶段性,而非简单地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就能完成的。首先是进城农民(无论是主动性的外来流动人口、还是被动性的本地失地农民,下同)的就业生机要得到解决,即赋予他们城里人的经济权利,这可称为A阶段;其次是要享有公共服务,即赋予他们城里人的社会权利,这可称为B阶段;最后是能够自主管理、参政议政,即赋予他们城里人的政治权利,这可称为C阶段。而且每个阶段还可细分为“有部分权利”(下标1)和“与城里人平权”(下标2)两个亚阶段。改革开放迎来了A1阶段的开启,尽管在1990年前后的治理整顿期间和2009年前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许多进城农民工因找不到工作不得不暂时回乡,但很快便得到了恢复;然而由于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并存,至今许多城市、许多产业领域都尚未进入A2阶段。近些年来,许多城市开始注重向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提供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医疗救治、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甚至公租房、廉租屋等基本公共服务,即进入了B1阶段;但由于长期以来实施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城市一直视农民工为“外来”“流动”人口,公共资源基本依据城市户籍人口规模予以配置,因而距离B2阶段还相当遥远。少数城市已经通过“新市民之家”等形式尝试外来人口自我管理,但还不能被视为已经进入C阶段。所以,各个城市应当根据自身所处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进城农民市民化的策略,循着经济赋权、社会赋权、政治赋权的步骤依次稳步递进;通过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等形式推进A1阶段向A2阶段演进,通过“积分制”等形式推进B1阶段向B2阶段演进。
其次看1亿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居住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各地城市在以往“摊大饼”式的扩张和发展过程中,村、镇整建制地转为社区、街道,失地农民变成了市民;在国企改制、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过程中,许多工人集体下岗,原有的工作单位也不存在了。但他们的生活方式未变,交往圈子未变,许多人仍没有融入城市职业分工体系,原有的管理体制机制解体,新的管理体制机制或尚未建立、或虽建立但运行状况不佳,区域功能没有分化,公共空间没有形成,其发展也往往没有纳入城镇领导者的视野和城市规划的范畴。这些就是当今许多城市的城中村、棚户区的来源。“城中村”、“棚户区”不仅成为城市安全的隐患、社会治理的难点,而且成为城市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对于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起来极为棘手。国内外许多城市的管理者都有这样的共识:与其搞旧城区改造,不如重建一个新城。面对各个城市极不相同的历史变迁、现实矛盾、经济基础、财政实力、资源约束和社会条件,不可能给出“一刀切”的行动指令和管理细则,国家只能给出一个宏观目标和基本原则,在法治的大框架下,放权让各个城市从实际出发,自力更生,群策群力,自主进行城中村、棚户区的改造,既提升整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也促进以当年失地农民和下岗工人为主体的城中村、棚户区居民融入现代化的城市职业体系和生活方式之中,共建共享城市的现代化。
最后看中西部地区1亿农民就近城镇化。当年,费孝通先生曾写过脍炙人口的《小城镇,大问题》,系统总结了长三角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实践经验,勾画了农民就地城镇化的美好图景。当前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就近城镇化,也只能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途径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之初长三角地区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经验并没有过时。另一方面,如今的宏观经济社会形势又与改革开放之初有了很大的不同,中西部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也不能照抄照搬长三角地区当年的经验,如要从做好功能区规划入手,企业入园区,转移人口进集镇,防止“乡乡点火、村村冒烟”,防止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要注意同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重振“丝绸之路”战略相衔接,同东部地区和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相衔接,同本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衔接;还要创新管理,出台吸引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回乡创业的政策,并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
在处理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关系方面,不能不提及户籍制度的改革。长期以来的城乡分治,国家赋予了城镇户口过多的“含金量”,只要拥有了城镇户口,就拥有了就业保障、住房福利、粮油副食品价格补贴以及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保障。“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在城市居民中先后破除了普遍就业制度、均等工资制度、粮油副食品价格补贴制度、福利分房制度,实行了教育成本分担以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的改革,城镇户口中的‘含金量’大大缩水,但仍然远远没有降至为零。”⑧而且不同等级、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之间,户口中的“含金量”差别也很大。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采用各类事项与户籍脱钩的办法,进一步剥离附着在户口上的各种额外的权利;另一方面,鉴于各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同,其面临的“城市病”和发展“瓶颈”也不同,因此也就需要区别对待,“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⑨
在处理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关系方面,也不能不提及“土地财政”的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称,目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10.6万元,全国平均为13.1万元/人。3亿人的市民化就需要40万亿元。面对这一天文数字,只能在土地上做文章。目前的“土地财政”广受诟病,但垫付总量高达40万亿元的新型城镇化成本,又不能不依赖“土地财政”。其实,目前“土地财政”的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收取方面,而是出在如何支出方面,只要确保其真正用在推进城镇化事业上,确保上述3亿人能够获利,确保失地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增值的权益,依靠“土地财政”来支撑新型城镇化,就是必要且可行的。
总而言之,我们的结论就是:新型城镇化必须因地制宜,从而殊途同归——“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⑩
注:
①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区域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2页。
②童星:《世纪末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8—149页。
③⑤邓平、周波:《在人居环境建设中对“人本主义”思想的探索》,《四川建筑》2003年第3期。
④周素红、蓝运超:《人本思想综述及其在城市规划中的体现》,《现代城市研究》2001年第2期。
⑥曲凌雁:《城市人文主义的兴起、发展、衰落和复兴》,《城市问题》2002年第4期。
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区域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1页。
⑧童星、马西恒:《“敦睦他者”与“化整为零”——城市新移民的社区融合》,《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1期。
⑨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责任编辑:秦川〕
OnDiversityandUnityoftheNewUrbanization
TongXing
Same development path, same city function, all cities with a same face and same management type has been being the chronic disease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urrently countrywide promoting new urbanization, we must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ty and unity. From view point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eory, there are “demand point” type and “supply base” type; From view point of urban development functional orientation, there are “comprehensive versatile” and “habitat humanistic” type; From view poi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population, there are “people raise type” and “ raise people type”; From view point of urban development path, there are “land expansion type” and “population absorb type”; From view point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size, there are “ towns and small cities ”, “medium-sized cities”, “big city” and “megacity”. All kinds of the city type above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s well as the preconditions for their own development. Therefore, all should select accordant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path, and finally get to the same end: promote big city, medium-sized city and small city and town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dustries and citie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new urbanization; urb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ity function orientation; urban and population dependent relationship; urban development path; urban population
童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3
C912.2
A
1001-8263(2014)12-0051-06
*本文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作者和董华于2006年合作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理论的再认识》一文,该文被收入《中国城市评论》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