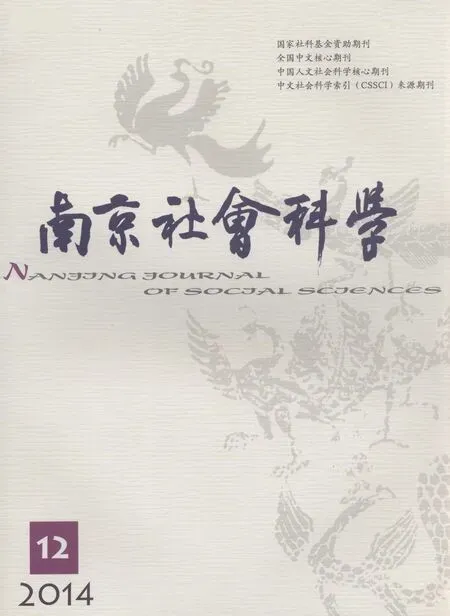文化工业理论再认知:本雅明与阿多诺的大众文化之争
胡翼青
文化工业理论再认知:本雅明与阿多诺的大众文化之争
胡翼青
文化研究的学者率先建构了本雅明和阿多诺在大众文化上二元对立的观点。他们认为二者在三个方面有较大分歧:其一,本雅明看到了大众文化中所蕴含的公众反抗的积极潜能,但阿多诺则完全无视这一点。其二,本雅明看到了媒介技术积极的向面而阿多诺则不承认这一点,后者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者和悲观论者。其三,本雅明的政治立场更接近布莱希特而非阿多诺,前者倡导艺术的政治化来反对法西斯的政治美学化,而后者则认为必须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否则艺术将无法摆脱政治宣传的下场。然而,回到历史的语境,这三个论点都站不住脚。相反,多个证据表明,本雅明是文化工业理论的开创者,阿多诺等学者只是在不断地顺着本雅明的思路拓展这一理论。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阴暗基调,只是因为对纳粹和反犹的过度敏感,导致其夸大了进步主义时代之后美国的大众社会与文化的极权特征。
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本雅明;阿多诺
本雅明与阿多诺关于大众文化的争论似乎已经成为论及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结构时不能回避的问题。不过,对这一论争的理论阐释,似乎还远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阶段。原因是多数学者所使用的阐释二者论争的方法,即抽离历史背景的文本的结构性比较分析,无法最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社会与历史语境,这种解读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偏颇的。站在去语境角度的解读和从整个学术史入手来思考这一问题,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景象。本文便试图站在更长的学术史时段来透视这场争论,以期指出以往研究存在的欠缺。而如果要这样做,我们恐怕首先要从费斯克说起。
一、从费斯克谈起
受到霍尔和葛兰西的影响,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是受众对具有话语霸权的文化商品或文本的再创造。他指出:“大众文化是由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为了从那些资源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这些资源也为支配者的经济利益服务。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①这一表述集中体现了费斯克对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阿多诺的不满。因为他所反驳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就是阿多诺。阿多诺曾公开宣称说:“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②阿多诺坚定地认为,强加于受众的大众文化表面上可以归咎于传媒技术,其实应当归咎于支配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所以他确实认为大众文化构成公众的外部环境并且是由支配性力量强加于公众的。对此,有人评价说:“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对大众文化批判最为激烈,影响也最为深广的是阿多诺。‘文化工业’是阿多诺用得最多的术语。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它基本上是大众文化的代名词。理由上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种大杂烩,它是自上而下强加给大众,所以是一种文化工业。”③
费斯克是整个伯明翰学派中最具民粹主义色彩的学者,这从他对大众文化的定义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承认大众文化所依赖的某些资源如媒介在某种意义上被统治者所掌握,因此统治者确实具有文化霸权。但他又指出,霸权不能脱离抵抗而单独存在:“霸权之所以必要,或者甚至是可能,仅仅因为抵制的存在。”④按他的这个逻辑,霸权是以抵抗为前提的,所以有霸权就有公众的反抗,哪怕这是游击队对占领军的反抗。费斯克不能忍受那种无视受众抵抗甚至无视受众主体性的理论。因此,当他在20世纪70年代接触到《启蒙辩证法》一书时,他被阿多诺的理论彻底震惊了。他指责说:“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字典里,根本没有‘抵抗’和‘规避’这样的字眼。”⑤
其实,甚至包括大卫·莫利在内的许多学者都不是太认同费斯克的极端化和乐观主义。然而,在人文学科具有高度贵族化的英国,伯明翰学派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英国人文学科平民化的开端。所以从雷蒙·威廉斯和霍加特开始,这些非贵族家庭出身的学者就一直倾向于强调文化是公众的日常生活,反对将文化看作是精英艺术。所以,相比于费斯克,他们更不喜欢阿多诺的精英主义,不喜欢他的傲慢与偏见。而同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本雅明显然更接近文化研究的口味。本雅明所指称的机械复制技术可能带来的革命的潜能,以及他所提到的密谋者、游荡者和拾荒者都被看作是对文化研究民粹主义观点的一种支持。因为本雅明不仅宣称大众文化的民主潜力,而且也提到现代性所造就的个体如游荡者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公众的反抗。在文化研究看来,无论是本雅明的理论还是身份,用本雅明来反对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实在是很合适。于是,文化研究几乎以一己之力,在20世纪80年代建构了本雅明与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观点的不同和论争。其中史蒂芬森和刘易斯在文化研究的两部代表性教科书中的表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史蒂芬斯指出:“不顾阿多诺的抗议,本雅明辩证地评价原作韵味的下降。尤其是通过新媒介的艺术品复制的技术手段,为文化生产和文化接受的各种更加民主和有更多大众参与的形式提供了前景。……本雅明与布雷赫特持同样的观点,却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的观点相左。”⑥而刘易斯则认为:“本雅明不像阿多诺那样,对新技术及其传播模式如广播、电影、电话、留声机等全盘否定。事实上,本雅明颠倒了阿多诺的看法,认为新技术将艺术从资产阶级的占有和控制中解放出来。”⑦
但本雅明的大众文化观是否就倾向于民粹主义,与阿多诺的思想是否真有本质的不同,文化研究却没有加以认真的论证。他们只是选取了那些有利于民粹主义的只言片语来说明这一点。许多学者认为,本雅明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不仅超越其同时代的人,也确实超越了文化研究学者的视野与境界。
无独有偶的是,相当数量的美国学者可能比英国学者更不喜欢阿多诺,如果让他们选择,他们也更倾向于推崇本雅明。本雅明在美国的大热固然与汉娜·阿伦特的大力推荐不无关系,但美国学术环境本身的选择也不能无视。在托克维尔时代就被观察到的平等主义盛行的美国,被看作精英主义的阿多诺肯定是不受欢迎的。美国人与英国人一样,是由他们的立场而不是他们的学术理性决定了他们的倾向。
在众多反对阿多诺的美国学者中,马克·波斯特是急先锋之一。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媒介的判断毫无锐气,沦落为攻击和漫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绕开了文化层面,站到技术决定论一边。在他们的分析中,工人阶级或民众群体被构型为消极被动并且毫无生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并没有摆脱现代理论的逻各斯中心主体,因此他们就不能把电台的大众化受众看成非他律性的,故而将这一奴役归咎于技术。”⑧在贬低阿多诺的同时,他又极度地抬高本雅明:“首先,虽然本雅明与杜亚美、阿多诺以及其他人一样是在相同的现代主义艺术传统下接受教育,但他却尽量不对电子媒介所散播的文化产品表现出蔑视的态度。其次,尽管启蒙规划的马克思主义式描述使他大受鼓舞,他对历史辩证法中文化介入的方式也兴趣盎然,但本雅明在解释林林总总的历史条件时并没有带着对普通平民的反感。第三,他也没有将主体的逻各斯中心观带到他对媒介的理解中。……第四,他对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的处理总的说来是成功的,没有陷入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在他看来,本雅明完美无缺:“本雅明没有让杜亚美和阿多诺的精英主义及人文主义假设充斥他的头脑,所以他对第一媒介时代的阐释比他们专业得多:他把媒介带来的自由潜能放在当前局面下各种力量的运作这个语境中加以考察。他既不把媒介作为资产阶级残渣而弃之不理,也不把媒介的到来作为乌托邦的肇始而大唱赞歌。”⑨就这样,波斯特把本雅明和阿多诺完全对立起来,而且立场非常鲜明。但波斯特对本雅明的评价似乎与我们的常识完全相悖,因为本雅明从没有将媒介的自由潜能放到任何社会语境中去加以考察,而只是在理论上探讨了它的可能性与潜力,而阿多诺却要现实得多。仅就这一点便可以判断,波斯特对本雅明的推崇缺乏理性,显得过于情感化。关于这一点,我们下文还将进一步讨论。
从英美学界的态度大致可以看出,在推崇民粹主义的知识界中,用本雅明的民粹主义来指责阿多诺的精英主义大众文化观,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假思索的传统。抛弃其中的阶级立场、意识形态取向和政治因素,将两人的理论对立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几点:
其一,本雅明看到了大众文化中所蕴含的公众反抗的积极潜能,但阿多诺则完全无视这一点。其二,本雅明看到了媒介技术积极的面向而阿多诺则不承认这一点,后者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者和悲观论者。其三,本雅明的政治立场更接近布莱希特而非阿多诺,前者倡导艺术的政治化来反对法西斯的政治美学化,而后者则认为必须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否则艺术将无法摆脱政治宣传的下场。
然而,这些所谓的差别是否能够成立,是表象的差别还是深层的差别,提出这些差别的方法是什么,证据是否充足,这都是值得追问的。阿多诺的观点确实与文化研究大相径庭,但是否如文化研究所说的那样与本雅明也大相径庭呢?
二、莫须有的二元对立
其实,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思想史研究界存在着与文化研究完全不同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似乎能够列举的证据更为充足,对本雅明与阿多诺的解读似乎也更加深刻。魏格豪斯对这一段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既来自于文本,又来自于学派成员之间的交往与行动。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通过发表在《社会研究学刊》上的文章,本雅明体现了他与阿多诺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关系模式,即一方面他们之间有紧密无间的团结,另一方面他们共同对抗作为意识形态批评家的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这是两个阵营的对峙,一个是根据美学的现代性经验建立起来的历史哲学阵营,另一个则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使用古典唯心主义艺术观的阵营。”⑩
即使是一个学派的成员,学者之间由于学科背景不同,学术成长经历不同,所处环境不同,自然会有观点上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到底是根本上的差异或范畴上的不同,还仅仅只是强调的侧面不同。前者肯定是二元对立,后者则可能是辩证统一。事实上,认为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理论具有根本对立的理由几乎每一条都是不成立的。
我们重点来看第一点,本雅明是否完全无视大众文化的消极潜能,阿多诺是否完全无视大众文化的积极潜能。
本雅明有一句名言:“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如果说本雅明对大众文化有什么积极的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一定是建立在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态之上的。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篇最能反映本雅明积极态度的文章中,作者既没有否定灵韵对于艺术品和受众的积极意义,也没有简单到完全无视复制的消极作用:“总而言之,复制技术把所复制的东西从传统领域中解脱了出来。由于它制作了许许多多的复制品,因而它就用众多的复制物取代了独一无二的存在;由于它使复制品能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加以欣赏,因而它就赋予了所复制的对象以现实的活力。……其最有影响的代理人就是电影。电影的社会意义即使在它最具建设性的形态中——恰恰在此中并不排除其破坏性、宣泄性的一面,即扫荡文化遗产的传统价值的一面也是可以想见的。”所以,有学者总结说:“本雅明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本雅明总是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具有同样的想法,认为富有韵味的艺术为超验提供了可能性,如果能为己用,那么这就包含了未来幸福的希望。”本雅明在技术方面的观点也同样如此的两可,他的一个中心观点是:“技术要么在人民大众手中变成总体世界欣快经验的客观工具,否则即将来临的便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可怕的大灾难。”所以,他强调共产主义要用艺术的政治化去对付纳粹的政治审美化:“人类,现在成了为自己本身而存在的人,他的自我异化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人们把自我否定作为第一流的审美享受去体验。法西斯主义谋求的政治审美化就是如此,而共产主义的政治化对法西斯主义的做法做出了反应。”
而阿多诺,即使是20世纪40年代年轻气盛的阿多诺,也没有无知到完全无视大众文化给公众带来的机会。在《启蒙辩证法》1944年内部刊行版的前言中有两句话:“我们早已完成更详尽的论述,请静候最终版本。另外,我们还将讨论大众文化有哪些积极方面。”据说在英语世界正式出版时,这两句话被删除了。所以有学者评价说:“《文化工业》既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被工具理性操纵的反乌托邦图景,又同时辩证地证明了大众文化可以为人类带来源源不断快感。所以说《文化工业》将两种思路‘打包’递送给读者:一边是对权力统治的批判,另一边则是对自由的向往与期冀。”在此之后,阿多诺似乎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影响有了更多的论述。在1947年对电影音乐、1954年关于电视以及1966年关于电影的研究中,阿多诺都开始努力挖掘大众文化积极的一面,他相信文化工业的解毒剂就是文化工业本身,在他看来,电影在教育年轻人对抗主流意识形态。“很多人不相信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居然认为大众文化还有积极的方面,但事实证明二人的确有‘本雅明’的一面。”
所以,像本雅明和阿多诺这样伟大的学者,也都饱受德国思辨哲学的训练,不可能像某些英美文化研究学者那样具有非黑即白的逻辑。当然,从文本来看,两人显然在不同的侧重上各自用力,因此给读者以错觉,其实当事人自己心如明镜。比如本雅明在给阿多诺的信中就曾经写道:“在我的研究中我追求阐发肯定的因素,而你显然是提示否定的东西,在你的研究中看到的一种力量,它正是我的弱处所在。”由此可见,二人的研究范式与逻辑完全是一致的,只是关注的侧重点不太一样。
至于第二点差异,波斯特的概括一点道理都没有。美国传播学者的通病在于,总是在无端指责他人为技术决定论时,自身却扮演着真正技术决定论的角色,因为他们总是围绕着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或效果展开他们的研究思路。波斯特本人关于互联网的著作《第二媒介时代》就很有技术决定论之嫌。在波斯特的逻辑中,凡是说媒介效用强大的一概都是媒介技术决定论。然而,按照他指责阿多诺的逻辑,本雅明也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因为只要本雅明认定复制技术必然带来社会变迁,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那么在波斯特的意义上,本雅明都应当是技术决定论。尽管值得商榷,但沃林认为,本雅明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倾向:“本雅明显示出布莱希特式的非批判地、直接地把‘技术’力量拜物教化,致使地忽视了这一技术在现实操纵性的社会运用。”相比于本雅明对技术潜能的纯粹推测,阿多诺倒更不像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如果波斯特仔细阅读过阿多诺的著作,那么他应该明白,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的论述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阿多诺不断地提醒我们,技术的那些潜能说阿多诺有强大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还勉强可以成立,但若说他是个技术决定论者,那只能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然,本雅明也不能被看作是技术决定论者,因为他同样关心的是使用技术的人或者说技术掌握在谁的手中,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
关于第三点差异,认为本雅明的政治立场更接近于布莱希特,这也并非没有争议。本雅明确实深受布莱希特的影响,他关于艺术政治化的观点与布莱希特的创作实践确实有相当接近的地方。但显然本雅明未必在心底里完全赞同布莱希特的主张,并努力地抵抗布莱的政治主张对他的影响。尤其是在他流亡法国期间,他还是更愿意接近远在美国的研究所。“本雅明对布莱希特在充满敬意之中也有对此友谊的警惕,他拒绝永远离开巴黎和布莱希特流亡到丹麦。”在内心底里,本雅明始终高度重视远在美国的研究所,以及他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友谊。为此,他甚至同意研究所修改他的论文和研究计划并强烈地希望离开法国到美国与研究所会合。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本雅明与阿多诺的所谓二元对立,均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相反,通过我们的分析,证明二者在很多方面有着强烈的一致性。“尽管阿多诺并没有完全理解本雅明所有的想法,但他确实比朔勒姆,或是布莱希特,或是其他人理解得更多,正是他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进入了本雅明的思想之中,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多地吸收了本雅明的思想。本雅明在谈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之前,特别强调了两者之间深刻的一致性。”
三、重新评价文化工业的缘起
我准备进一步论证本雅明与阿多诺不仅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且在思想上共同构成了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他们之间有着明确的思想承接关系,而且是本雅明率先形成了文化工业理论的思想理路。
文化工业理论的发明权一直都被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账上。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他们集中地阐释了文化工业的观点。文化与艺术已经成为了一种工业生产行为,由少数的生产中心通过标准化的生产方式去满足大量分散的消费者的需求。而这种生产行为的背后,是支配社会的强大政治经济权力。政治经济权力通过这种文化生产组织和管理着社会成员并支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工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整合控制了整个文化与艺术领域,进而控制了所有受众。让他们在感觉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失去主体性,让他们在感觉自身个性张扬的前提下失去个性,让他们在文化的启蒙中失去解放的可能。文化工业的出现,是经济垄断向文化领域渗透的必然结果。阿多诺后来还专门就为什么给大众文化命名为文化工业做了解释:“在我们的草稿里,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倡导者认为,它是这样一种文化,仿佛从大众本身产生出来似的,是流行艺术的当代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文化工业’代替了它。”
然而,如果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文化工业理论尤其是其内涵的发明权恐怕并不来自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而是来自本雅明。是本雅明先关注到了文化工业的问题,并率先做出了自己的表述。早在1935年之前,本雅明就在《讲故事的人》一文中看到了文化工业的端倪,小说和新闻媒体取代了讲故事的人而成为文化的主要消费形式。而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通过对于摄影与电影的研究,本雅明看到了某种艺术的潜能。可以复制的艺术代表着文化市场化的可能,因此公众可以更多地接近艺术作品。然而,本雅明的批判思维也就此生成:艺术原有的独一无二性——灵韵的消失使真正的艺术消失了,艺术变成了大众消费品。“19世纪的这一发展使创造的形式从艺术中解放出来。……这种新奇的创作实用地将自己准备成商业艺术。”当艺术变成了满足大众消费需求的产品时,艺术生产的逻辑就变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业社会商品生产的逻辑,而艺术本身,即具有灵韵的艺术则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生产的逻辑等同于商品生产的逻辑或受商品生产逻辑的左右,这是本雅明的伟大发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学说的一大贡献。“从他作为一名左派知识分子的经验和担负的工作来看,本雅明实际上应当比阿多诺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理论。”
我们需要来玩味本雅明形容大众文化的重要关键词,比如“大众”、“消费”和“接近”。这些词都在说明在本雅明的眼中,公众被分割和异化为孤独的原子式的个体,他们从表面到内心都是整齐划一的。艺术再也不能被真正理解,而只能在形式上被感知,被消费,成为一种彻底的快感文化。而这种快感文化又在娱乐大众的同时支配着大众的行为。“娱乐业通过把他们提高到商品的水平而使他们较容易获得这种满足。在享受自身异化和他人的异化时,他们听凭娱乐业的摆布。”艺术与公众均被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物化了。本雅明绝望地宣称:“生产力的发展将前一个世纪的象征变成碎石断片。……资产阶级的丰碑在坍塌之前就是一片废墟了。”我们会发现,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此后的研究只是对这一主题的进一步拓展和明确,他们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对文化工业生成的社会机理进行了更理性的探究以及对公众如何被文化的产品所物化进行了深入分析。而这一切都是1944年以后的事了。
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走得更远的是,本雅明还认真讨论了艺术创作主体是如何被纳入文化工业浪潮的。在拱廊街的研究计划中(阿多诺反对这个计划的第一稿,但对其第二稿大加赞赏,并促成研究所对这一计划的立项),他传神地描述了作家是如何被纳入现代传媒大众文化生产的:“一个社会就以这种方式在大马路上将生活在其中的文人吸收进来。在街头,他必须使自己准备好应付下一个突然事件,下一个机智的警语,或下一个谣言。在这里,他展开了他与同事及城市人之间全部的联系网,他依赖他们的成果就好像妓女依赖乔装打扮。”本雅明虽然没有认真研究像大仲马这样成功迎合了大众文化的弄潮儿,但他通过展示波德莱尔的尴尬境地向我们展示了文化工业来临后文人的处境:“波德莱尔明白文人的真实处境: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一样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却是想找个买主。”本雅明笔下的波德莱尔仍有传统文人的清高。波德莱尔注定是那个时代的游荡者,他不愿意与市场化的文学合流,他可以嘲笑拉马丁、大仲马等文人,但他注定要被大众文化消灭。这其中蕴含的绝望情绪只能用“只因没有希望,希望才给予我们”来言说。本雅明所谓的机制复制的积极影响,只能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所以,文化工业理论其实是由本雅明提出的,尽管他本人的悲惨命运使他没有能最终完成他的宏大研究计划。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只是发展了其中的某些主张,并更多地强调了其中消极的一面,并反对“艺术政治化”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本雅明的死在很大程度上触动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让他们意识到本雅明这条理论路径的重要价值。所以有学者评价说:“《启蒙辩证法》的两位作者既是卢卡奇的信徒,又是本雅明的拥虿。”当然,该理论的冠名权并不属于本雅明。
四、文化工业理论的美国经验
再次重申彼德斯对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理解:“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比较阿多诺和本雅明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立场,但阿多诺绝不是一个对大众持轻视态度的人,本雅明也并非时时欢呼着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现象。阿多诺终其一身深受本雅明影响。”这可以作为我们上述讨论的一个总结。不过仍然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认为本雅明和阿多诺二元对立,既有学术意识形态的立场差异,也有方法层面的问题。将两人文本脱离其社会历史语境,将两人文本置于对立关系的结构性对比框架中进行对比,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所以,既要忠实于文本,又要还原文本的历史语境,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种思想。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文本的去语境化解读。然而一旦放回真实的社会和历史语境,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德国人本雅明的法国版文化工业理论和德国人阿多诺的美国版文化工业理论。这只是同一理论体系在不同社会经验语境中的两个变种,它们所具有的只是表象上的差异。身处不同文化环境,这即使不是导致阿多诺和本雅明文化工业理论表象差异的最根本原因,恐怕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而这一点,至今没有专门的文献加以讨论。
本雅明始终呆在法国,在那里,希特勒的阴影挥之不去。他之所以主张用艺术的政治化来反对法西斯的政治美学化,与他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压力息息相关。可以说,生活在极权社会形态中的本雅明仍然对文化的民主形态有一点幻想。另外,市场化的大众文化在当时的法国还没有形成什么气候,本雅明所能观察到的法国的文化生产者,无论是文人,电影导演还是艺术家,都与美国的大众文化生产完全不同。他对文化工业繁荣到顶端的景象没有体验。直到今天,法国和德国仍然是抵制美国大众文化入侵的最主要国家,本雅明无法从上述两个国家真正看到机械复制的文化消费时代,人性是怎样被彻底物化的。这也是为什么本雅明的观点如此缺乏社会现实支撑的重要原因。观察法国的现代文化工业,恐怕需要等到居伊·德波、鲍德里亚人到中年的那个时代。然而阿多诺看到的,是进步主义时代之后的美国大众文化。
进步主义时代到目前为止还是美国史上一段谁也说不清的时代,甚至连它的起止时间都没有统一的看法。准确地描述这一时代的特征,只可能是挂一漏万。然而,如果我们从这个时代结束之后美国的变化来反观这一时代,也许会更有收获。在经历了进步主义时代以后:美国从一个农业大国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大国;从一个分权的政治联合体变成了一个高效的中央集权政体;从一个地区性大国变成了国际性的霸权国家;从自然形成的多个传统社区走向了一个整体性的社会;从一个众声喧哗的社会变成一个舆论一律的社会……所以,进步主义时代是一个美国全社会学习现代社会管理的动荡时代。在应对诸如移民、犯罪、贫富差距、职业道德沦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各种观点、对策通过交锋和实验渐渐形成了一套社会管理的科学方法和一种美国式的科层体制,并由此重建了现代社会秩序。而与之伴随的,是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意识形态控制的无处不在。
1937年,当阿多诺受拉扎斯菲尔德之邀踏上美国大地时,美国已经具备了欧洲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娱乐生活。广播每天都在放着各种流行音乐和广告,信息的轰炸几乎无处不在;电影院川流不息,梦工厂正在不断地炮制白日梦;电视正快速登上历史舞台,把美国人变成一个个“沙发上的土豆”。美国人的娱乐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使有着良好家庭教育背景的阿多诺感觉自己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商业化了的大众文化,给当时在美国搞电台项目的阿多诺以很大的打击。它大大超出了他在20年代里在老欧洲所记得的天真幼稚的范围。他现在看到的无处不在的广告在欧洲没有相应的例子……”然而作为旁观者,阿多诺敏锐地感觉到,在这一系列根本性的转型中,少数精英掌握的国家权力通过运用各种技术手段最终形成了对多数民众进行有效有序的科学管理体制。其中就包括通过现代大众传播和文化工业的方式主导意识形态,控制舆论,垄断思想,从而终结个体的主体性和人的全面解放。这就是美丽新世界娱乐文化的本质。阿多诺在华纳公司的电影产品中看到了批量复制技术的同一性原则,它们终结了人的个性:“从根本上说,克莱斯勒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好奇心不同的孩子们所产生的幻觉而已。……华纳兄弟公司和迈尔公司的产品也属于同样的情况。”他也在唐老鸭身上看到了文化工业对观众潜移默化的规训:“卡通片里的唐老鸭,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倒霉蛋,总会不断遭到重创,这样,观众也就学会了怎样经受惩罚的考验。”这一切都表明,阿多诺所遭遇的美国式的大众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他思想的基调。
然而,对美国文化的悲观并不仅仅只有只有这一原因。阿多诺和整个研究所都与普通的流亡者不一样,他们是德国犹太人。交战国公民的身份和犹太民族的身份让整个学派的成员对美国社会与美国文化缺乏认同感。学派的成员在美国像文化孤岛一样存在,其社会身份极度边缘。与此同时,对纳粹和反犹的警觉和过敏,使他们对美国大众文化背后的极权问题强调过度,而对其蕴含的反对力量着力不够。而对美国民主社会的预期和随之而来的失望,则扼杀了他们对于文化民主形态的最后一点幻想。所以,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多少有一些强调阴暗的成分,并使之背离了辩证法的初衷。这是阿多诺理论的欠缺之处。关于这一点,回到联邦德国之后的阿多诺也有反思。
我想阿多诺在给本雅明的信中不断地提醒后者缺乏辩证的思想,其表达的语境就是他在美国亲眼目睹的一切:复制技术是不可能掌握在公众个体手中并发挥民主的潜能的,因为权力对技术的掌握和垄断要比公众容易得多。当然,心存幻想的本雅明并不真正了解阿多诺的语境,而想象破灭的阿多诺也并不了解本雅明的语境。如果本雅明能够跨越大西洋到达美国与研究所汇合,结局可能就完全不同。当然,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
结 语
时势造英雄。30年后,到费斯克和德塞托等人去讨论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抗时,竟是如此没有英雄气概。在他们看来,怠工是抵抗,换台是抵抗,关电视机也叫抵抗。现代性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所说的抵抗是一种权力框架中的抵抗,是一种顺从前提之下的抵抗,也就是阿多诺所说的:“人格所能表示的,不过是龇龇牙、放放屁和煞煞气的自由。在文化工业中广告已经取得了胜利:即便消费者已经看穿了它们,也不得不去购买和使用它们所推销的产品”。与30年前的德国理论家相比,费斯克们的抵抗理论显得非常可笑,也许资产阶级的权力精英所希望的就是这种抵抗。即使通过扭曲本雅明理论的原意来论证他们看法的合法性也是枉然。我喜欢彼德斯的那句精彩的评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为强调大众文化的解放性潜力而严厉指责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人类的能力过分苛刻,其实极不明智地走上了他们所反对的道路:过分执迷于建设乌托邦而全然抛弃了必需的清醒头脑。”
注:
①④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③④陆毅、王扬:《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0页。
⑦杰夫·刘易斯:《文化研究基础理论》,郭镇之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7页。
⑧⑨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0、16—18页。
〔责任编辑:御风〕
ThroughtheMistoftheCultureIndustryTheory:Re-ontheMassCultureWarsofWalterBenjaminandAdorno
HuYiqing
It’s cultural studies scholars who first built the Benjamin-Adorno dual antinomy in th field of mass culture. They think that the two have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Walter Benjamin saw the public’s positive protest potential in mass culture, while Adorno ignored this point. Second, Walter Benjamin found the positive side of media technology, but Adorno did not concede it. The third is that Walter Benjamin made his political stand more closer to Brecht than Adorno, the former initiated politicized-art to against the aestheticized-politics, while the latter advocated the belief “art for art’s sake” or “self-to-art”, otherwise, art will not be able to get rid of political propaganda. However, back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three arguments are untenable. On the contrary, more evidence prove that Walter Benjamin was the pioneer i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industry, Adorno and the other scholars just follow his ideas and continue to expand this theory. The dark tone of Adorno’s culture industry theory, just because of his overly sensitive to Nazi and anti Semitism, which leads to his exagge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otalitarianism in American mass society and culture after the progressive era.
culture industry; mass culture; Benjamin; Adorno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3
G0
A
1001-8263(2014)12-0121-07
———阿多诺艺术批评观念研究》评介
——论《贝多芬:阿多诺音乐哲学的遗稿断章》的未竞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