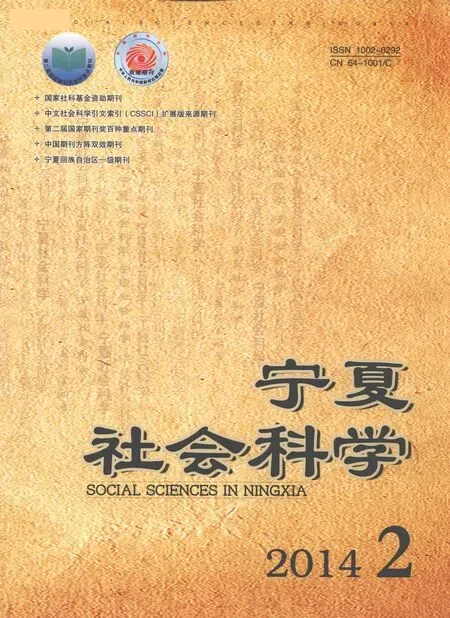宗教与死亡的文学对话——论石舒清小说创作中的死亡书写
张 静
(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死亡是指机体生命活动的终了,死亡往往与悲剧联姻,成为文学的最高审美形式。因此死亡犹如一曲哀伤的旋律,被中外文学大家反复吟咏、百唱不厌。宁夏回族作家石舒清也不例外。石舒清在自觉不自觉间以文学的方式所进行的死亡言说,所完成的对生命个体的死亡体验与死亡意识的书写,呈现了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
在石舒清小说创作中,涉及的死亡书写对象是比较丰富的。梳理其作品,笔者发现,石舒清笔下死亡书写最多的是成人,这些成人大都是极平常、极普通的穆斯林民众,他们没有壮烈的事件,没有英雄的色彩,有的只是令人叹息的人生际遇和生活境况。比如《疙瘩山》中的“小姚”,在落榜、辍学、流浪、被歧视、被侮辱之后的超凡脱俗,到最后静躺在尸床上。石舒清笔下的死亡书写还有一些是孩子,这些孩子全部因病或意外事故自然死亡,而且几乎全部用的是经名,既折射出西部地区儿童的现实生存境况,又具有鲜明的回族特色。比如《牺牲》中12岁的舍巴,为避免两村的械斗,父亲用石块将其击倒身亡。此外,石舒清笔下的死亡书写主体还涉及了动物,这些动物多为奉献于宗教的牛和羊,通过书写动物之死,着意表现了回族民众的宗教情怀与精神追求。石舒清的代表作《清水里的刀子》里为举念宰杀的那头牛,或《羊的故事》中那只不谙世事的早夭的羔羊。他们生命的身份可能不一样,但是生命的尊严却是一样的。他们生前活着有些无奈、有些不明白甚至还贯穿着生不如死的意味,但他们的死却都是干净的。所以死者洁净、脱俗、清秀、美丽、清癯黄亮的面颜,才有资格成为“世人的最后一面镜子”。石舒清的“死”是另一种形式的“生”,所以他的死者具有内涵丰富的表情,这种表情有着饱满的象征性和有力的暗示[1]。
在石舒清的小说创作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对死亡关联的场所、景物与用物进行了描述。在这些外物的烘托下,死亡书写有了别一种意义。在石舒清笔下,坟、坟院这样一些直接承载死亡的场所,全无阴森恐怖之感,相反,却成为一个“亲切的所在”、“我”的“向往之地”、“马子善”老人真正的“家”。这种对坟的理解与认知完全迥异于汉族,在汉文化里,是谈坟色变的。而在穆斯林文化中,死并不意味是灾难,而是一种精神的皈依。那么,坟也就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场所。因此,在回族人眼里,坟及其坟院也就毫无阴森恐怖之感。在书写死亡主体所处的环境时,多描写风、太阳、月亮、云、雪等这样一些与死亡关联的景物,着重突出风的迅急、阳光的明亮、落日与月亮的神秘莫测、云和雪的洁白轻淡,具有明显的西北物候特点。这些丰富的意象,在伊斯兰文化里有着丰富的寓意,尤其是对“月”的描写,在回族的心中,月亮被视为民族心像的载体,历来被回族当作冰清玉洁的象征。另外,在对亡人的服饰书写中,最突出的是对白布的描述。对祭奠者的服饰书写中,最多的是对白帽与盖头的描写,也具有鲜明的回族特色。在回族心中,白色既是母族历史特征的一种概括,也是母族生存价值的一种评说。回族借助白色通往了一个隐形的世界,其核心就是宗教文化。宗教仪式及其情感的内化使得这些外物的描写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外物在宗教氛围的浸染下,成为石舒清死亡书写这一创作特征有力的组成部分。
石舒清对死亡书写对象的表现手法是多样的。有详细叙写死亡过程的,如“在火里舞之蹈之,并且发着奇怪的声音。她在火里面跑着,成了大火的中心,但她突然被什么绊倒了,她企图爬起来,却没有成功,渐渐地就看到她在大火里缩成一团……”[2]。有详细描写死后情态的,如:“脸上有一行干了的泪痕。脸很枯焦,像一片萎了很久的秋叶。眼睛、嘴唇紧紧地忍受着什么痛苦一般闭着。有血!一绺儿血,沿着嘴角淌到地上。脸上地上的血都己凝着了。”[3]有简洁叙述死亡的情节,如“大姨娘、大姨父深夜从县医院抱着盼舍回来了,盼舍已经无常了。”[4]有通过他人陈述来写死亡的,如:“早起起来说晕的,喝了点白糖水,笑着说:‘我怕没事了。’一阵阵儿就主啊主啊地喊着口唤了。”[5]石舒清对死亡的淡化处理,不同于先锋小说中的“零度情感”,对生命的终结,石舒清总是赋予了丰富的精神内涵,说到底,这种艺术处理,还是源于回族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悲悯的情怀让他不仅停留在对苦难的观照和世俗人生本质的揭示上,而是超越了这种苦难,使得石舒清对死亡的审视具有终极关怀的高度。
同陈继明、季栋梁、张学东等其他宁夏作家相比,石舒清的死亡书写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同样是书写触目惊心的杀人场景,陈继明是“冷峻地写实”,比较真实地“再现”了死亡的过程,直面死亡的血腥。如:“他举起菜刀,准确地朝新教师的头部砍去,新教师的整个身体猛地弹了一下。……新教师的头被剖切成均匀的两瓣,浸泡在血和脑浆里。”[6]而石舒清写得比较节制,似乎有意避开杀人的残酷,甚至在具体的杀人描述中甚至没有提及到“血”,例如:“王有生想都没想,就抡起斧头向刚站起来乱举着双手的刘俊霞来了一下子。被削去半个面孔的刘俊霞突兀地站了站,猛地向王有生倒过来,王有生神经质地跳开在一边。”[7]同样是书写死后情状,季栋梁多用“长长地”、“白森森地”、“红的”、“白的”等形容词,力求直观。而石舒清则采用比喻等修辞,仅求形象,例如:“她的脸,发紧着,青得像一块石头。那被专意修过的眉毛也像荒风吹掠过的野草。”[8]即使是通过他人转述死亡,张学东对死后情态进行直观描述,如“那个疯女人,半年前跳楼自杀了,死得很惨,脑浆都摔出一大摊。”[9]而石舒清仅叙说死亡过程,如“男人就哄她说有个话说,哄到背后弯弯儿里,面袋里的斧头就拿出来了,把婆姨剁成了碎碴碴。”[10]总之,石舒清的死亡书写比较“写意”,读来多了一份凄婉、悲凉,少了一份血腥。究其原因,还是与石舒清所信奉的伊斯兰教崇尚“清真”、追求“清洁”的精神相契合。
石舒清的死亡书写不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在这些密切交织着宗教教义和宗教情感的有关死亡书写的艺术文本中,作者以鲜明的民族个性表现了回回民族特有的生活风貌、独有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素质,以及在传统文化熏染下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和生活趣味,突出弘扬了宗教正面的精神与教义。具体来讲:
第一,回族对死亡有着宗教情味极浓的深刻理解。死亡,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消亡,更是精神上的皈依,是“归真”,是一个与灵魂相关的问题。死亡,是离别,更是归去。所以,对马子善(《清水里的刀子》)老人来说,死亡并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是顺从自然的。当他听见冥冥之中“那苍老而稳妥的声音”轻轻召唤时,没有恐惧,却是“诚恳”地点头。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耳子(《沉重的季节》)、小姚(《疙瘩山》)、姨奶奶(《逝水》)、刘老太太(《背景》)他们面对死亡时的那种平静达观、宁静安然的态度。即使是动物死亡,回族也讲究“不要让非死不可的生命自行死掉,而是以真主的名义把它宰掉,让它死后归落到端庄的路道上”[11]。
第二,回族对宗教的信仰与情感己内化为一种为人处世的准则。在岁月长河的积淀里,宗教与日常生活、生存环境融为一体,深深浸入回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生活的过程就是信仰的过程,人们在信仰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坚守自己的生命。石舒清笔下的姨奶奶(《逝水》)、小掌柜(《出行》)、环环媳妇(《节日》)、小姚(《疙瘩山》)等回族民众,都是把宗教信仰变成为支撑生命的精神信念,在孤寂清贫的生活中,构筑一方灵魂的圣地,甚至不惜以死守护,从而获得至高无上的精神享受。他们将宗教情感内化为承受苦难的人格力量,在苦难与死亡的面前,怀着坚定的信念,隐忍地生,坚强地活,有尊严地死,张扬了生命承受苦难的坚忍和高贵。透过他们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及富于尊严而节制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看到了回族民众对“善”“洁”精神的追求,看到了穆斯林民族极力倡扬坚忍、敬畏、苦其心志、磨其心力的人格精神,强调为人的血性和刚气,并以此忍领“苦难”,拒斥“怜悯”,坚守宗教信念的虔诚。
第三,回族的宗教仪式已成为一种价值制衡,规范着回族民众的日常言行。回族有一种仪式,老人病重了,“孝顺的儿女们,到床头去讨‘口唤’,不孝顺的后代却讨不着‘口唤’。讨不着老人‘口唤’的人,那不但要负疚终生,还要受千夫所指的犬刑呢”[12]。“讨口唤”的仪式实则提出了做人最基本的准则——孝敬父母。回族还有一个习俗,有人亡了,“前来送葬的人都要去瞻仰一下亡者的遗容,以此遗容来参想自己的生死”[13]。无论是瞻仰亡者的遗容,还是参想自己的生死,实则都是在以“清真”的精神,评判他人,约束自己。再者,亡人在下葬前,他的子女都要专门询问亡人生前有没有欠别人的账。因为“在穆斯林中间,账是个大问题。一个欠别人账的穆斯林,是带着一团巨大的阴影入土的,而且这阴影,还在蔓延在他的家里,令他的子孙后代,寝食不安”[12]。“老人无常后,遗留的账债由后辈偿还。”这样,才能“干干净净轻轻松松回去”[14]。甚至,如果给老人许乜贴的鸡、羊死了,也会被视为“心不诚”。这样的一种仪式、习惯实则都是一种道德规范,要求穆斯林民众要有责任,讲担当,重诚信。
第四,回族的宗教教义已内化为一种道德准则,不断矫正着被世俗生活遮蔽了的心灵。马保义(《月光下的村子》)在金钱的诱惑下,拾取了不应获取的三百块银元,参与了偷盗公粮活动,最后因患严重的心脏病“口唤”(殁)了。马耳子(《沉重的季节》)在金钱的诱惑下,由一个颇有正义感的农民沦为替权势者看家护院的打手,以至成为杀人犯,付出死的沉重代价后,才获得灵魂的寄托。在穆斯林民众看来,活着要“干什么呢?尽量做些口唤时让灵魂安宁的事情”[12]。因此,目盲而不得已以招魂谋生的柳术增(《招魂》),歉疚一生,舍散一生。宗教教义也成为作者笔下人物形象归宿的评判尺度,尔斯玛乃与尔里媳妇(《赶山》)两人因违背了本民族教义,最后落得妻死已疯的下场。三爷(《三爷》)恶德恶行,最后被暴尸荒野,胡乱埋葬。
[1]牛学智.石舒清短篇小说论[J].扬子江评论,2009(3).
[2]石舒清.阴阳.[J].新疆回族文学,1998(5):18.
[3]石舒清.赶山[J].朔方,1993(4):16.
[4]石舒清.残月[J].新疆回族文学,2001(5):11.
[5]石舒清.逝水[J].朔方.1993(4):31.
[6]陈继明.邪恶一次[J].朔方,1994(4):18-19.
[7]石舒清.一半是阳光[J].新疆回族文学,2001(1):19.
[8]季栋梁.死人的事情[J].黄河文学,1997(1):22.
[9]张学东.给蝌蚪想象一种表情[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315.
[10]石舒清.旱年.开花的院子[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7.
[11]石舒清.羊的故事·伏天[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291.
[12]石舒清.月光下的村子[J].新疆回族文学,1996,4:23.
[13]石舒清.疙瘩山·伏天[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5.
[14]石舒清.红花绿叶·开花的院子[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203,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