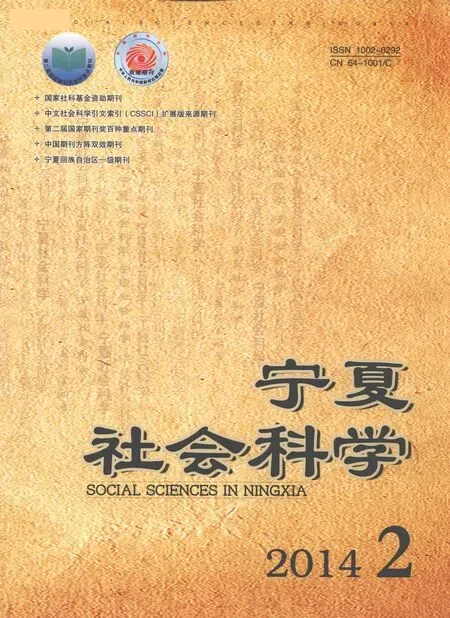沈定一的“是”与“非”——基于萧邦奇《血路》一书的再判断
毕文锐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一、基于“网络”的判断
沈定一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理论上通过他所处的社会网络应当可作一大致的判断,然而我们却遗憾地发现,他的网络关系实在是如同他本人一样复杂,以致难以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基于《血路》,我们可知沈定一大致从属过五个网络:一师网络、省议会网络、上海小组网络、亲族网络和朋党网络。我们将逐一对其展开分析。
1.一师网络。一师网络是沈定一身处的最辉煌最革命最富战斗力,也是伤害他最深的一个网络。这一网络的主要成员杨之华、宣中华、俞秀松、徐白民、唐公宪、施存统、王贯三、安体诚、倪忧天无一不是沈定一的忠实信徒和行动追随者,沈的思想曾经给他们以鼓舞和指导,而他们也带来了沈极为喜欢的青春活力与昂扬斗志。但是在国共分裂时期,这个沈定一亲手打造、倾心呵护的网络毫不留情地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并在清党运动中遭受了灭顶之灾,几乎一半的成员成了革命烈士,与沈定一存身右翼阵营的选择形成了鲜明对比。
2.省议会网络。省议会网络是1916~1917年沈定一担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并发起抵制北洋军阀入浙运动时形成的一个广泛同盟,核心成员许祖谦、任风冈、褚辅成、查人伟等均为沈任命的省议会负责人,他们也同沈一样,至少是誉满省内的名流,在维护宪政体系和抵制军阀入浙的行动中坚决拥护沈定一,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并在之后十年的历次议会决议中无一例外地站在沈定一一方。然而,这支纯粹由名流,或者说是由文弱书生组建的网络,在军阀和政客相互勾结又彼此倾轧的年代是毫无实质战斗力可言的,因而他们所能为沈定一提供的也只是一种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尤其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当国共分裂,整个社会也陷入左右对立状态时,这一网络的成员又几乎成为了浙江省内非共产党的左派主力,且许多人遭到了沈定一从属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逮捕。这一事实无疑对沈定一的评价又泼上了一盆脏水。
3.上海小组网络。1919年,沈定一避居上海后,与戴季陶创办了《星期评论》,并与记者邵力子、叶楚伧等交好,他们的活跃大力推进了上海地区的思想启蒙。沈成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重要领导人,《星期评论》的办公室也成为“青年学生着迷般争赴上海会见沈定一和戴季陶的圣地”[1]59。在这一系列会见或者“朝圣”的过程中,前述的一师网络也逐渐形成。终于在1920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时,《星期评论》和一师两个网络的主力成员们加上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茅盾、张东荪等短暂结成了一个新的网络。他们为期不长的合作显然是有助于唤醒民众和组织青年的,并对一年后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立有着毫无疑问的重要影响。但是,“对一个主要是自诩颇高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且人人在个人利益上不愿做轻易让步,更兼有那么几个毫无疑问爱出风头的人在内的团体来讲,工作中的配合和强度问题,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所导致的冲突,有时会使个人恩怨和意识形态倾向互相掺和,从而导致社会连接纽带的破裂”[1]88。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这一网络中相当一部分成员,尤其是才学出众而本身也自视甚高的沈定一、陈独秀、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人之间的关系是好不到哪里去的。同时,由于这一网络的大部分成员要么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要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然享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和大学者,甚至还有几位革命烈士,这就把沈定一这个早早就与中共分道扬镳并参与了臭名昭著的清党工作的“大叛徒”形象反衬得愈加鲜明刺目。
4.亲族与朋党网络。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后,国共合作潜藏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已经是一名纯粹的国民党员的沈定一开始着手于控制省党部的工作,在这一阶段,由于他多年的追随者和生力军——一师网络全员站在共产党一方,并不断向沈的权力发出挑战,沈定一只得退守衙前,并以他的亲族(沈肃文、沈尔乔)和他新的坚定信徒(王讷言、陈博敦、徐攀云、孔雪雄、石博侯)为基础形成了新的网络,我们权且称之为亲族—朋党网络,这一网络的成员出于血缘和信仰的原因,对沈定一个人极为忠诚,并成为其沈系省党部和衙前自治协会的主力。与之前的网络相比,这一网络的成员在知名度和影响力上明显不足,很可能仅仅局限在萧山附近。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除却与宣中华等争夺省党部控制权外就只剩下在浙东(主要是衙前)搞一点虽为先驱却不切实际的农业乌托邦,且在沈定一去世之后,他们连维系这最后一点点幻想的实力也不复存在,可见组建这一网络是沈定一后期的无奈之举,其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沈定一最后的十二年生命在1925年前后存在一个明显的断层,在这之前他以激进的形象面世,宣扬的是自由、民主、启蒙、平等、法制的思想,并吸引和赢得了大批社会名流和青年学子的支持与崇拜,但在这之后,几乎仅仅是因为支持国民党右翼这一项举动就使得所有昔日的门生旧友与他反目成仇,以致他不得不依靠亲族、乡党这样的封建纽带去维系自己日渐式微的影响力了(而不任用乡党是他在议长时代的显著风格之一)。按照“一个人越是与他所属的群体和社会认同,越是表现为道德上的高尚”[2]267的逻辑,不得不说,仅就网络结构而言,沈定一是很难得到一个正面评价的。而且综观各个网络,其中的大多数人都算得上是沈定一的学生和信徒,即便是平辈的同事和亲友,也大都明显年轻于他,因而往往愿意从属于沈这个相对“长者”。但值得一提的是,古往今来,学生反对老师的事情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极少发生的,纵然偶尔也会出现诸如亚里士多德“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佳话,但终属罕见个例。像沈定一这样遭致自家弟子集体“背叛”的可谓是旷古奇闻。在这种情况下,历史的天平真的很难再袒护老师,而只能倒向学生一方了。正如宣中华所言:“我为革命与沈玄庐合作,沈玄庐能劝我加入共产党,但绝不能拉我退出共产党。他敢于反革命,我就同他干到底。”[1]168显然,在这群学生眼里,不是他们造次,分明是老师自己反水在先,那也就怨不得他们“更爱真理”了。
二、基于“身份”的判断
如果仅仅是从网络出发,我们只能粗略地认为沈定一不过是个“坏人”,尽管他曾经也做过一点“好事”。但若沈定一完全就是一个起先投机革命,后来又背叛革命的极右派政客,那么我党的干部还有必要怀疑他是否是个坏人么?于是我们便需要从“身份”的角度再去重新审视沈定一的形象。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手术效果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住院的总天数、引流管留置时间优于对照组,P<0.05;手术后观察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格拉斯哥晕迷分值、血肿水平、FIM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脑水肿少于对照组,P<0.05。
沈定一的一生被冠以了行行色色的身份,这些身份大都风马牛不相及,甚至有一些还是相互矛盾的,于是我们便不得不认真地甄别关乎沈定一的每一种身份,同时又必须加以区别对待,重点探究他的一种或为数不多的几种核心身份。
《血路》中提及的沈的身份多达二十余种,有表示阶级成分的地主和土豪劣绅,有表示职业的诗人、记者、学者、县令、政客、留学生、革命领导人等,有反映政治倾向的激进主义者、社会经济现状的强烈批判者、国民党忠实信徒、西山会议派、极右派、中间派等,有记录事迹的农民抗租改革运动的倡导、鼓动和组织者以及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等,有表示人物性格的我行我素者、个人英雄主义者、游侠骑士等,还有他自我定位的青年导师,等等。在所有这些身份认定中,有四个身份对他的人物定位和历史评价应当起决定作用,即地主、个人英雄主义者、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和国民党忠实信徒,前两个身份决定了他的个人特质,后两个身份决定了他的悲剧人生。
1.地主。评判一个人的好坏,首先要确认他的成分和出身,要确定他的阶级立场,这一套路已经沿用了几十年,至今仍在各种登记表上留有残迹。我们在这里优先举出“地主”这一身份,既不是要对沈定一这个明显不够革命的阶级出身展开批判,也并非要为他超越自身落后阶级属性的行为大唱赞歌,而是想要说明,地主这一身份对于沈定一的人物养成是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的。
地主虽然同资本家一样作为剥削阶级,并且是比资本家要更为落后的剥削阶级,但是地主推行的那种剥削往往要更为仁慈和光明正大一些,也即地主同佃农的关系与资本家同工人的关系是不完全一致的(地主与佃农的关系绝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绝大多数地主本身也不过就是农民,虽然他们远比一般农民富裕,虽然他们已经不再需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可是他们依然亲近土地而鲜有投机分子。且地主多半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勤劳并富于实干精神,这是使得他们从农民群体中脱颖而出的初始因素;二是具有不俗的文化修养,因为在科举废除以前,有功名的人是全家免除赋税和徭役的,这一政策是大部分地主得以完成资本积累的保证。沈定一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主,他才华横溢且极具行动力,他亲近农民也了解农村,他天生是开展农民运动的不二人选。当对立阵营的人们要攻击他的出身时,往往觉得“地主”这个称呼尚不够解气,因而要在前面冠以修饰称之为“大地主”,这倒也不错,沈家的确要比一般的地主家庭更为殷实,可我们也不能够忽视他散尽家财,毁家纾难这一点。至于还有更激烈的谴责,将其划为“土豪劣绅”,这便是只能暴露自身狭小器量的无端生事了。
2.个人英雄主义者。个人英雄主义者其实先天包含了我行我素者的含义和游侠骑士的形象,所以即使如我们这些从未见过这位沈三先生的人们也可以透过这个身份认定获得一种相当立体的直观感受。但凡是个人英雄主义者,一定具有如下特质:清高、孤傲、无畏、自以为是、理想主义、强烈的控制欲、推崇权威也自诩为权威。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消除两点对个人英雄主义者的偏见。第一,个人英雄主义不等于单干主义,尽管过分相信自身实力而不刻意寻求团队的支持,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喜欢单枪匹马的厮杀,这一类人并非不能容身于集体,而是他本人必须是这一集体毫无争议的领袖和绝对权威,如果满足了这一点,一切个人英雄主义者都首先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因为他们需要那种被追随的满足感。第二,个人英雄主义者也不同于唯我独尊者,并非叫嚣老子天下第一的才叫个人英雄主义,他们同样有可能折服于某一强大权威并对其宣誓效忠,他们推崇这种权威的同时也期待着向其他人树立自己的权威。
沈定一正是一位符合上述一切特质的个人英雄主义者。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知县时,就有胆量刑责做巡抚的父亲,在北洋军阀入浙以后,他仍然敢于冲进办公室里怒斥督军,在上海他对来访的学生侃侃而谈,自觉充当他们的精神导师和保护者,在衙前他亲自深入到农民当中去宣传演讲,发动轰轰烈烈的抗租运动,当一师网络集体反对他并组建新的省党部时,他凭借个人威望召开衙前会议重建自己的派系。而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在遇到了孙中山以后,却坚定不移地追随其脚步,甚至在其死后仍然矢志不渝。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在历史上非常有人缘的个性,但是在其所处的时代,可以确信他不会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这样的一类人,西方有堂·吉诃德和拿破仑,东方有项羽和木曾义仲,无论其人生何等辉煌,无论后人怎样敬仰,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他们都是失败者,而且往往是众叛亲离的失败者。因此,哪怕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同样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沈定一也应该用一次惨痛的失败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可是潜藏的敌人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但是以我们现有的常识去判断,衙前农民协会这种农业生产力条件下的乌托邦实验难道还会有第二种结局吗?而一手策划和开展这种极端理想化实验的行为本身也再次佐证了沈定一是一彻底的个人英雄主义者。
3.共产党发起人之一。沈定一作为共产党发起人和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之一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而关于这一方面的史料在此也无须赘述。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的是,这一身份对沈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又为他带来了些什么。
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统治阶级(无论是军阀还是官僚资本家)来说,共产主义无疑是激进的代名词,至于这一主义究竟指代的是什么,追求的又是什么,守旧势力并没有心情去了解。一些最早的共产党人自身也未必明晰这诸多主义中的一种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只因着听闻它是革命的或是受了哪位先生的引导便加入了进来,即便是那些相对明白一些的党员在具体的方针上也分歧极大,有主张激进革命的,也有主张渐进改良的,有要求暴力夺权的,也有寻求合法宪政的,这样一个党派是松散、多疑、摇摆不定而又纪律涣散的,它对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掌握是之后十几二十年的成熟过程中逐步实现的。在它最初的组织里,简单分来无非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外加一小撮投机主义者。所以,共产党的发起人这一身份除了充分肯定沈定一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果决的行动力以外,实在是证明不了更多的东西,而他在1924年的脱党行为更直接表明了他的思想同共产主义思想根本无法求同存异。其实可以说,尽管有着解放农民和实现社会平等的思想,沈定一仍然从来就不是个共产主义者,在精神层面上,我们恐怕很难指责他的“背叛”,他本人的信仰应该是一以贯之的,并且是更接近三民主义的,同共产党相比,他还远远算不上是激进。
但是,沈定一自己也感叹道:“中国人究竟名重于实啊!”共产党发起人这一身份对他产生的影响远非它实际意味着的那一点点。在共产党方面,发起人这一独特身份放大了他背叛组织的罪恶,从而燃起对他的熊熊怒火,使得他的一切行为变得不可原谅;而在国民党方面,一个身贴极端势力标签的人实难取得确实的信任,因而只能遭受有色眼镜背后一道道阴冷目光的打量,并在一次次权力斗争中随时准备着被清洗出局。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份,使得沈定一里外不是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似乎都不愿意承认他是一个“好人”,而这又正好反过来成全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吧。
4.国民党忠实信徒。如果说早期共产党是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那么同期的国民党则为之更甚。从历史的角度讲,国民党一开始就是一个各派势力妥协的产物,除了辛亥革命的元勋们和陆续加入的广义上的革命者,党内还充斥着军阀、旧官僚、大商贾和帮会成员,他们一没有牢靠的组织架构,二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与其称之为一个政党,倒不如称之为辛亥以来对现状不满者的一面旗帜。如果没有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一大,孙中山恐怕至死都无力组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中枢。即使是重新改组之后的国民党也依然有着三处软肋,而共产党又偏偏直戳其上,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可避免的破裂。首先,国民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地方上的组织建设极其薄弱,县一级及以下的党组织基本上是依靠共产党员建立并负责维持运转的,因而国民党事实上没有多少基层组织;其次,国民党中大批当权派和军事将领都是大地主出身,在农村拥有庞大的利益范围,而共产党组织的农会以及镇压地主的行为深深触动了这些利益(同理,沈定一也遭党内这一部分人嫉恨);再次,由于国民党员先天的复杂成分,以致党内派系林立,内斗不断,而其中很大的一项分歧正在于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因此,当作为最高仲裁者的孙中山去世后,国共之间就只剩下了猜忌和防范。不掌握军事力量和革命主动权的共产党深感来自国民党的威胁,而曾经被袁世凯窃夺了革命果实的国民党对于掌控着几乎全部基层组织的共产党也怀有莫大的恐惧,于是兄弟俩反目成仇,并互相指控对方背叛革命。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革命”呢?
至少在沈定一眼里,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只有跟着孙中山才是干革命。与其说他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倒不如说他是孙中山的得意门生来得妥当。沈定一根本不曾认同过共产党的纲领,从他自身的思想和行动来看,他要建立的绝非是赤色的中国。同情农民,同情工人,主张平等,重视教育,这只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左翼的政治理想,甚至还掺杂了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在里面,经受了血雨腥风的无产阶级革命始终不在沈的考虑范畴之内。要知道,虽然他组织了看似相当激进的抗租运动,可那也不过是带领农民以尽量合法的方式(考虑到他为此而在省议会奔走,他本意应当是采用完全合法的方式)寻求减租而已,这与共产党动辄没收财产甚至处以极刑的镇压土豪劣绅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因此,作为忠实的国民党信徒,即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沈在清党前后的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但也同样因为他事实上是忠于孙中山个人,或者说孙中山个人的主义,因而他不可能与国民党内的实权人物(这些人物在利益和权力面前是不讲什么主义的)开展合作,也就只能识趣地退出领导层,回到衙前去搞他的乌托邦。而他这种罔顾现实,单纯追随孙中山的理想化态度已经足以为他埋下杀身之祸了。
如前所言,是地主和个人英雄主义者这两个身份塑造了沈定一的性格特质和世界观,决定了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而共产党发起人和国民党忠实信徒的矛盾身份则使他深陷各派势力相互倾轧的漩涡并最终伴随着他不切实际的理想被现实无情地粉碎。通过基于其身份认定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沈定一“背叛革命”的行为和“刻薄寡恩”的形象其实是可以找到合理化解释的,也即他的一些争议性言行放到历史宏观中去考察时应当被视作是超善恶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与我们的观点不同,立场相左就称其为十恶不赦,这样的指责总是缺乏足够信服力的。
三、基于“场所”的判断
经过了基于“身份”的判断,我们已知沈定一算不上是个大恶人,纵然有些相对负面的言行,也是基本可以给予理解和宽容的。那么我们就将再透过《血路》的视角,基于“场所”范畴对沈定一进行再审视,以得出更为全面的结论。在本书中,沈定一的“场所”线索并不复杂,总共只有上海、杭州和衙前三处,下面我们试作一一分析。
1.上海。上海,是沈定一的辉煌之地。早在辛亥年,动辄“拔刀”的沈三先生就在这里组织了“中华民国学生团”,参加了收复上海的武装起义,并受到过孙中山的嘉奖。等到1919年他避居来沪,又很快以《星期评论》为阵地,“活泼泼地”为获取光明而奋斗,并成为了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担负起充当“青年精神导师和保护者”的责任。随即,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在他居沪期间,青年学子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求得他的指导,由他号召的,甚至可能是直接参与了的罢工和游行也取得了成功,这是他人生中的一段辉煌时期。他同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一起,他的主张得到积极的拥护与追随,他的实践行动引发热烈反响并达成预期目标,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他的人生再也不曾如此顺遂,他的威望也再未如此时一般扶摇直上,不遭贬损。而反过来讲,沈定一在上海从事的活动无论怎么看也都是彻头彻尾的好事,他取得与之相对应的美名和赞誉也是理所应当的。
2.杭州。杭州之于沈定一,唯有一词可以概括——抗争。1917年,他为了抵制北洋军阀进入浙江而发动议会和社会各界请愿抗争;1921年,他为了农民抗租运动的合法性而呼吁抗争;1925年,他又为了同宣中华等争夺省党部的控制权而奋起抗争。浙江的省会对于这位省内风云人物来说似乎从来就是一片战场,他在这里同北洋军阀、同政客官僚、同他的同事和昔日弟子们都展开过激烈的争斗,虽然就台面上看败多胜少,可他依旧斗志昂扬,乐此不疲。在这片战场或者舞台上,他有时赢得了威望,有时也输掉了声誉,支持和反对他的力量也此消彼长甚至互换场地。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省内的政治格局已经悄然改变,革命的形势也早已不复当年,而沈定一却始终还是当年的那个沈定一。就政治立场而言,他不同意共产党激进的革命主张,也明显不愿意与国民党中的极右势力同流合污,故而左派将他当作右派来抨击,右派把他当作左派去防范,结果是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究其根源,是他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性格使之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去适应大趋势的改变,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伍固然要吃亏,但若根本不站队还想要分一杯羹,那当然就连命都保不住了。
3.衙前。衙前可以称作是沈定一的理想之地,也可以管它叫乌有之乡。1921年,他在这里组织建立了衙前农民协会,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租运动,虽然最终以惨败收场,甚至牺牲掉了农民领袖李成虎,但是沈定一依然在当地深孚人望,老百姓对他“救农民于水火之中的努力深为感激”[1]120。1927年,在右派确定即将完全掌权的形势下,沈定一再度退回衙前并开始了他矢志不渝的关于农村自治的实验。尽管在经费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少困难,但总体效果明显是令他满意的。尽管这种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桃花源”在动乱的现实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但他却因为一串罪恶的子弹而免于亲眼看到自己一手营建的乌托邦的覆灭。而魂归故里对于一个还保有传统意识的革命者来说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透过对“场所”的考察,我们发现沈定一是不谋私利的,尽管他也会追求个人的声望,也会表现出对组织的控制欲和一定的权欲,但是总的来讲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利益,即便是牵涉到他自己,也是为了达成他的崇高理想,而非为了满足他的某项私欲,就此而言,至少他无愧于一名革命者的称号。纵览他十余年的足迹,每一次的斗争或实践都是为了捍卫他信奉的主义,或是为了构建他理想中的国家。对于他的行为评价应当放到一个建设“理想国”的层面上去,如果仅仅视其为一个宪政主义者、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农民同情者或者上述种种身份的机械组合体就未免太低估他的水准了。
四、关于是非的综合判断
在经历了一长串分析之后,我们重新回过头来思考开篇的问题,沈定一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也许此时我们再引入沈定一对自我的身份认知会有助于对他的是非判断,那就是“青年的精神导师”。正如毛泽东晚年说他只要一个teacher就够了一样,沈定一在他的诸多身份里也仅仅只承认自己是个teacher。他把教育视作开启民智的不二法门,他一心想继续孙中山未竟大业,准备着手对人民开展“训政”的过程与他本身试图在中国推行启蒙运动的过程是大略一致的。“启蒙”放在西语环境里更为直观(法语里启蒙是 lumières,光是 lumière,英语里启蒙是 enlightement,光是 light),就是带来光明,因为这之前的世界一片黑暗,这种可怕的黑暗不是感受自人们的眼睛,而是心灵,不是因世间缺少火光,而是缺少知识。正如沈定一诗中所写“藏身处,不知道是天是海,只是光明”,他是渴望“从黑暗中杀开一条血路”[1]79,为中国探得光明的。但是,同所有他的同类型人物一样(比方说大家熟知的项羽),他的性格、他的能力和他所采取的方式是无法实现他的理想的,这便是一种典型的悲剧英雄的宿命。尽管也有数十年的从政经历,但是沈定一供职的不是有名无实的议会,就是理论重于实践的党部,他从来就不曾是一个行政官僚,更不要说以投机钻营谋生的政客了。在那个黑暗动荡的年代里,他根本毫无政治斗争的经验可言,那点演讲和示威的小把戏在统治阶级眼里简直可以不屑一顾。这就好比一只刚刚断奶的小老虎怯声怯语地询问一头黑熊说:“请问我可以吃你么?”这样的人生是悲壮而令人惋惜的。故而,关于对沈定一的评价,就像对项羽等人的评价一样,我们明显不能按照样板戏里那样鲜明的善恶形象简单粗暴地将其定性为好人或坏人,而只能是就事论事地客观评析他的功与过。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认为,价值评价主要不是一个真理性问题,而是一个合理性问题。而合理性在根本上是一种历史的合理性,是主体的历史和理性问题[2]277。不同的个体、不同的阶级都信奉各自不同的价值,但是只有与历史发展方向一致的无产阶级价值才具有更大的历史合理性和最强大的生命力,对于历史人物的价值评价应主要依据其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的表现而定。在此立场上,一方面,沈定一所抱持的乌托邦主义和精英政治主张自然是与广大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当家作主的历史意愿相悖的,因而注定要为时代的洪流所抛弃。但从另一方面看,社会总是在破旧与创新中发展,在摸索与求证中前进,在开放与交往中强大的[3]53。在那个宇宙混沌、天光未开的年代里,沈定一同所有新文化的旗手、五四运动的先驱一样,为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养其蒙使正者、圣人之功也”,作为20世纪初颇具影响力的革命家、启蒙思想家和实践探索者,沈定一是注定不应为历史所遗忘的。
[1][美]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M].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马俊峰.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徐飞.智与愚[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