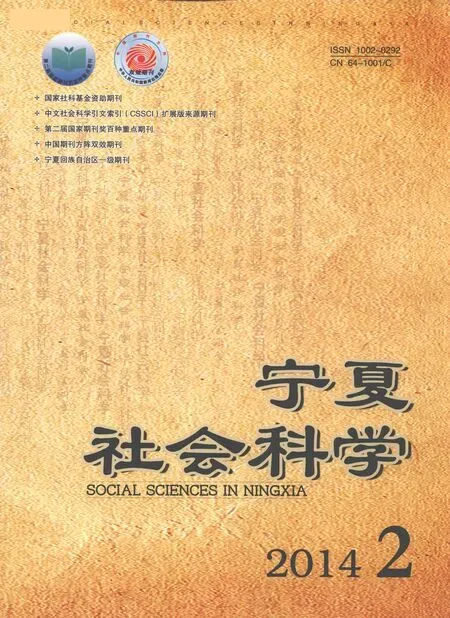亚述历次迁都比较研究
陈飞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1)
迁都即都城的变换、迁移,但关于亚述的“都城”,有一点须说明,即亚述的“都城”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首都”,因为在古代亚述人的语言中,并没有一个可与现今所说的“首都”完全匹配的词[1]。在亚述王铭中,亚述国王在提到亚述都城时多称之为“我的城”(URU-ia)或“我的统治之城”(URU be-lu-ti-ia),大体上可理解为“统治中心”,包含两层意义:一为亚述国王所居王宫所在地,二为亚述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这也正是本文所谓亚述“都城”的含义。迁都固然司空见惯,亦非亚述独有;但亚述迁都往往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对亚述迁都过程及原因的分析有助于把握亚述迁都的基本规律及其所反映的亚述历史发展的特点。
一
亚述迁都涉及多座都城间的依次更替。自公元前3000年代至公元前7世纪末亚述帝国灭亡为止,亚述先后出现六座都城:阿淑尔(Ashur)①、舒巴特—恩利尔(Shubat-Enlil)②、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Kar-Tukulti-Ninurta)③、卡尔胡(Kalhu)④、萨尔贡堡(Dur-Sharrukin)⑤和尼尼微(Nineveh)⑥。
1.从阿淑尔到舒巴特—恩利尔。阿淑尔是亚述最古老、也是历时最长的都城。除作为城名之外,“阿淑尔”也是亚述人的主神阿淑尔神的神名,“亚述”(Assyria)一词便来源于“阿淑尔”[2]。亚述人最早于何时定居于阿淑尔已不可考,而在沙姆—阿达德一世(Shamshi-Adad I;约公元前1726—前1694年)之前的古亚述时期⑦,亚述大致是一个以阿淑尔为中心的城邦国家。阿淑尔能够成为亚述最早的政治中心主要缘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其地依山麓地带和河流交汇处,扼守交通要冲,承接南、北平原,既可作为定居生活的依托,又是天然的军事要塞。此外,在古亚述时期,阿淑尔也是亚述与安纳托利亚高原之间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
公元前19世纪后半期,阿摩利(Amorite)某部族领袖沙姆什—阿达德一世征服阿淑尔,废黜原亚述国王埃里舒姆二世(Erishum II)而袭亚述王位,随即将亚述都城由阿淑尔迁至舍那(Shehna),并将其更名为舒巴特—恩利尔(意为“恩利尔神之王座”)。沙姆什—阿达德迁都于舒巴特—恩利尔的原因不难理解。首先,沙姆什—阿达德是异族统治者⑧,将都城迁离阿淑尔可远离亚述本土反对势力,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其次,舒巴特—恩利尔位于雨量丰沛、农业发达的哈布尔平原中心地带,在此建都便于控制此地农业丰产区。同时,舒巴特—恩利尔连接底格里斯河流域与叙利亚、安纳托利亚地区,是重要的贸易中转站[3]。再者,以舒巴特—恩利尔为都城也可便于沙姆什—阿达德着手处理叙利亚事务,尤其是应对带有离心倾向的地方势力和不断侵扰农业区的游牧民族[4]。
2.从阿淑尔到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沙姆什—阿达德一世死后,其王国迅速倾塌,舒巴特—恩利尔也随之衰落,在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挤压下,亚述辖地重又退回到阿淑尔、尼尼微、埃布拉(Arbela)等地,亚述都城也重回阿淑尔。中亚述时期,亚述再度崛起,在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统治时期(Tukulti-Ninurta I;约公元前1242—前1206年),亚述扩张达于巅峰。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将亚述都城由阿淑尔迁至新建的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意为“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之港”)。
依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在其王铭中所言,他修建该城系遵循阿淑尔神的神谕:阿淑尔神令其在正对阿淑尔的底格里斯河对岸新建一处崇拜中心。根据古代两河流域的传统,为神灵修建神庙是国王基本职责之一,因此,图库尔提—尼努尔塔的上述托词并不能解释其迁都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将都城迁离阿淑尔或许出于某种内在的政治原因。在中亚述时期,亚述不再是一个城邦国家,而成为一个区域性国家,亚述疆域的扩展必然使亚述国王的王权急剧上升,而王权的上升势必冲破以前城邦制下国王与贵族相互制衡的机制。因此,为缓解扩大的王权与传统的贵族权力的矛盾,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可借迁都以规避贵族势力的敌对并构建新的中央权力内核。此外,作为战功卓著的征服者,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也可能会期望通过在处女地上建起一座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新都以求彰显功绩、名垂青史。
3.从阿淑尔到卡尔胡。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世死后,新都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旋即被弃,亚述都城再次回到阿淑尔。自此直到新亚述时期,亚述都城一直都是阿淑尔。新亚述国王阿淑尔那塞尔帕尔二世(Ashurnasirpal II;公元前883—前859年)后将都城由阿淑尔迁至卡尔胡。
阿淑尔那塞尔帕尔二世迁都于卡尔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系倚重其地理位置。卡尔胡位于亚述中心地区,地处大扎布河与底格里斯河交汇的三角洲地带,交通便利,例如在萨尔贡二世(Sargon II;公元前721~前705年)时期,卡尔胡是亚述军队出征前的重要集结地之一[5]。其次,从当时亚述用兵的方向来看,亚述西部和北部边陲应是国防重点;由于卡尔胡比阿淑尔更靠近北方,故迁都于卡尔胡更有利于巩固西、北边防。此外,鉴于阿淑尔那塞尔帕尔二世时期亚述扩张更趋猛烈,亚述由区域性国家向帝国的过渡业已开始,王权的进一步扩大或许更需摆脱原有政治模式的桎梏,因此将亚述都城迁离阿淑尔便显得尤为必要。
4.从卡尔胡到萨尔贡堡。卡尔胡作为亚述都城历时一个多世纪,萨尔贡二世即位后,将都城由卡尔胡迁至萨尔贡堡。同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一样,萨尔贡堡也建于一块处女地上。约公元前717年,萨尔贡二世开始营建萨尔贡堡,约公元前706年,萨尔贡二世正式将都城迁往此地。然而,直至萨尔贡二世战死时,该城尚未完全建成。
萨尔贡二世迁都于萨尔贡堡的原因可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当时亚述的劲敌乌拉尔图人可经陶鲁斯山口轻易进入尼尼微平原,而萨尔贡堡位于尼尼微与陶鲁斯山麓之间,故进可攻、退可守,从而起到前言哨口的作用。其次,萨尔贡二世是一个篡位者,他推翻沙尔马那塞尔五世而争得王位,但卡尔胡作为亚述都城历时已久,旧政治势力的积淀必然厚重,故萨尔贡二世或意在避开旧都潜在的反对势力而另择新都[6]。
5.从萨尔贡堡到尼尼微。萨尔贡二世之子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公元前704—前681年)继位后,尚在建的萨尔贡堡被弃,亚述都城迁至尼尼微。自此直至亚述帝国灭亡(以公元前612年尼尼微陷落为标志),尼尼微成为亚述最后的都城⑨。
辛那赫里布迁都至尼尼微的最初动因可能系萨尔贡堡引水不便,而相比之下尼尼微则具显著优势:其地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多条通商路线的交汇处。此外,萨尔贡二世横死战场可能在心理上对辛那赫里布造成极大触动,亚述国王虽素有亲征的传统,但国王战死疆场且尸首无存在当时亦属罕见,辛那赫里布或将此惨剧视为其父萨尔贡二世遭到的诅咒[7],本能的惶惧促使其离开萨尔贡堡的不祥之地。
二
通过以上可知,亚述迁都并非亚述史上一个孤立的、偶发的历史现象,其规律和特点可归纳如下。
1.从时间分布上看,亚述在古亚述时期迁都一次(从阿淑尔到舒巴特—恩利尔),在中亚述时期迁都一次(从阿淑尔城到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在新亚述时期迁都三次(从阿淑尔城到卡尔胡、从卡尔胡到萨尔贡堡、从萨尔贡堡到尼尼微)。亚述迁都的频率在前期较小,而在后期较大。
2.从空间转移上看,除却舒巴特—恩利尔,亚述都城多集中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且都城的迁移基本遵循由南到北的方向:阿淑尔相对位于最南端,由此向北依次是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卡尔胡、尼尼微和萨尔贡堡。其中,阿淑尔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其余则位于东岸。另外,在古亚述和中亚述时期的两次迁都中,亚述都城先后回到阿淑尔,而在新亚述时期的历次迁都中,亚述都城自迁至卡尔胡后再未重返阿淑尔。然而,即便不再是都城,阿淑尔作为亚述主神的神座所在地仍是亚述最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中心,亚述国王的登基仪式在阿淑尔神庙举行,许多亚述国王死后也葬在阿淑尔。在某种意义上,作为阿淑尔神的“神权之都”,阿淑尔城构成连接天堂、人间和地狱的“竖轴”;而作为亚述国王的“俗权之都”,亚述都城、即世俗的“统治中心”则构成世界的“横轴”[8]。
3.从各都城的历史来看,阿淑尔、舒巴特—恩利尔和尼尼微是历史悠久的古城;卡尔胡是在旧城基础上扩建而成;卡尔—图库尔提—尼努尔塔和萨尔贡堡则建在处女地上,且无独有偶,也只有这两座都城系以建城者的名字而命名。另外,每迁至一新都时,亚述国王一般会从其他地方调集人口来此居住以扩充新都的规模。
三
亚述迁都的原因大同小异,大致可归为如下几类。
1.新都的战略位置重要,或交通便利(如卡尔胡、尼尼微),或农业繁荣(如舒巴特—恩利尔、尼尼微),或有利于巩固国防(如卡尔胡)。
2.迁都系为适应政治形势变化的需要。首先,亚述征服规模和统治疆域的扩大所带来的王权的集中可能会与阿淑尔城邦时代遗留下的贵族政治势力产生冲突,为摆脱传统政治框架和顽固保守派的束缚,亚述国王或会通过迁都以为王权开拓新的权力空间。这一趋势可能肇始于古亚述时期(沙姆什—阿达德一世时代),发展于中亚述时期,而到新亚述时期则更为显著:一则新亚述时期迁都更为频繁,二则迁至卡尔胡后亚述都城便永远离开阿淑尔。王权的上升是亚述由城邦国家向区域性国家和帝国不断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9]。其次,特殊的历史和政治背景,如王位争夺所引发的政变等也会成为迁都的直接原因,因为新当权者可借此规避旧都原有的反对势力而培植新的政治力量[10]。例如,作为异族征服者,沙姆什—阿达德一世定都于舒巴特—恩利尔;作为篡位者,萨尔贡二世迁都于萨尔贡堡。
3.在某种程度上,亚述国王的个人雄心和喜好可能也是促成迁都的另一个因素。纵观亚述迁都史,亚述都城的历次迁移几乎无不发生于某位强悍国王统治下的兴盛时期,征服战争的胜利、统治版图的拓展所带来的荣耀感或会促使这些国王通过建设新的都城以求彪炳史册。
四
亚述迁都带来多方面的影响。首先,迁都使亚述能够适应特定历史背景下王权集中的需要,而王权的集中及其所带来的政治稳定和国家职能的强化也反过来使亚述战争机器的运转效率得以提高,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古代近东地区在亚述主导下走向统一。同时,伴随迁都而来的大量人口的调配与集中也令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汇加速进行。最后,新都的营建也会直接刺激亚述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的发展。
另外,亚述迁都之频与南方的巴比伦尼亚形成鲜明对照。巴比伦尼亚人通常对于国王在巴比伦以外的某地建都(城)甚为反感,从阿卡德王国的萨尔贡(Sargon;约公元前2334—前2279年)和纳拉姆辛(Naram-Sin;约公元前2190—前2154年)到新巴比伦王朝的那波尼德(Nabonidus;公元前556—前539年),他们在巴比伦之外的建城活动都曾受到指责;相反,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rezzar;公元前634—前562年)却因自己未在巴比伦之外另建城市和行宫而引以为荣[11]。与巴比伦尼亚人的狭隘和保守相比,亚述人的政治胸怀似乎更为开放和务实,或许这也体现在亚述的宗教政策上:他们对异教崇拜持宽容态度,也从未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于任何一个被征服民族。
注释:
①阿淑尔地处底格里斯河与小扎布河交汇处以北的底格里斯河西岸,遗址即今伊拉克北部的卡拉特—舍尔卡特(Qal’at Sherqat),位于摩苏尔以南约100公里处。
②遗址即今拉兰(Tell Leilan),地处喀布尔河支流瓦蒂—亚拉河(Wadi Jarrah)左岸,位于今叙利亚哈塞克省(Al-Hasakah)境内。见H.Weiss,“Excavations at Tell Leilan and the Origins of North Mesopotamian cities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Paléorient 9/2(1983),39-52.
③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阿淑尔城以北约3公里处,遗址即摩苏尔以南约100公里处的图鲁尔—阿卡尔(Tulul al-‘Aqar)。
④遗址即今尼姆鲁德,位于摩苏尔以南约30公里处。据阿淑尔那塞尔帕尔二世所称,卡尔胡最先为中亚述国王沙尔马那塞尔一世(Shalmaneser I;公元前1272—前1243年)所建。
⑤遗址即今豪尔萨巴德,位于摩苏尔东北约15公里处。
⑥遗址即今伊拉克境内的库雍基克及其以南1公里处的那比—于努斯(Nabī Yūnus),位于底格里斯河东岸,与摩苏尔隔河相对。
⑦基于可利用的文献资源和各时期的语言特点,亚述历史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古亚述时期(公元前15世纪以前)、中亚述时期(公元前14—前11世纪)和新亚述时期(公元前10—前7世纪)。
⑧根据一篇铭文,一个名为普祖尔辛(Puzur-Sin)的亚述人后推翻沙姆什—阿达德之孙阿西努(Asinu)的统治并斥责沙姆什—阿达德是“外国的瘟疫,并非阿淑尔城的人”。见A.K.Grayson,Royal Inscriptions of Mesopotamia,Assyrian Periods(I),Toronto,Buffalo,London(1987),78.
⑨尼尼微陷落后,亚述末王阿淑尔—乌巴里特二世(Ashur-uballi?II;公元前611—前608年)在哈兰(Harran)即位,三年之后,陪都哈兰为新巴比伦军队攻陷。
[1]A.K.Grayson,“Assyria:Ashur-dan II to Ashur-Nirari V(934-745 B.C.)”,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III/2),Cambridge(1991),204.
[2]M.Novák,“From Ashur to Nineveh:The Assyrian Town-Planning Programme”,Iraq 66(2004),177.
[3]P.Villard,“Shamshi-Adad and Sons:The Rise and Fall of an Upper Mesopotamian Empire”,J.M.Sasson,Civilizations of Ancient Near East,New York(1995),874.
[4]H.Weiss,“Rediscovering:Tell Leilan on the Habur Plains of Syria”,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48/1(1985),27.
[5]J.N.Postgate-J.E.Reade,“Kalhu”,D.O.Edzard,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der Vorderasiatischen Archaelogie (V),Berlin/New York:1976-1980,321.
[6]H.W.F.Saggs,The Might That Was Assyria,London(1984),97-98.
[7]A.K.Grayson,“Assyria:Tiglath-pileser III to Sargon II(744-705 B.C.)”,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III/2),Cambridge(1991),117.
[8]S.Maul,“Die altorientalische Hauptstadt:Nabel und Abbild der Wel”,G.Wilhelm,Die orientalische Stadt:Kontinuitat,Wandel,Bruch(Colloquien der Deutschen Orient-Gesellschaft 1),109-124.
[9]M.T.Larsen,The Old Assyrian City-State and its Colonies,Copenhagen(1976),215.
[10]A.H.Joffe,“Disembedded Capitals in Western Asian Perspectiv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40/ 3(1998),567.
[11]H.Lewy,“Assyria,c.2600-1816 B.C.”,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I/2),Cambridge(1971),737.
——希利尔的三本书读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