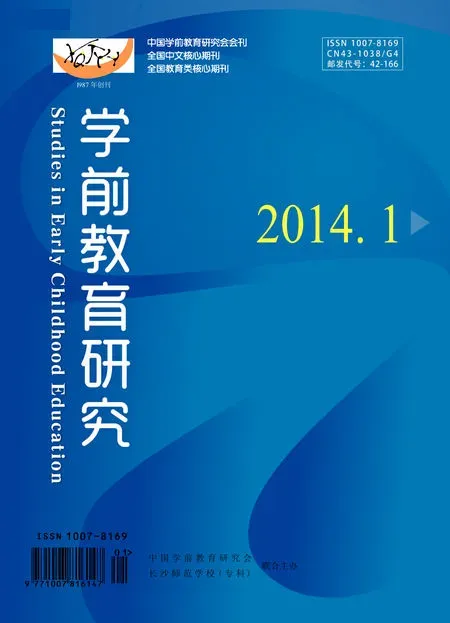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中的身体问题*
——五论进化、发展与儿童早期教育
杨 宁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过去二十年来,西方哲学和思想领域经历着一场“身体”转向,其标志之一是语言学家拉科夫(Lakoff)和心理学家约翰生(Johnson)1999年共同出版的著作《肉身中的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在书中,拉科夫和约翰生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三个基本命题: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无意识性、抽象概念的隐喻性。[1]这也是第二代认知科学即具身认知科学(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的三个主要发现,预示着以符号的、计算的、离身(disembodiment)的信息加工隐喻为核心的第一代认知科学转向强调身体的、情境的、实时的第二代认知科学。后者强调身体对心智或认知的塑造,关注脑、身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代认知科学关注身体在个体早期发展中的作用,重视心智的感觉—运动过程(sensori-motor processes)及其协调在高水平认知和抽象思维形成中的作用,强调身体、大脑和环境的耦合关系,这对儿童早期教育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的意义,并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何谓身体问题?
从思想史角度来看,身体问题在东西方都是由来已久的重要问题,但只是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开始急剧地转向探讨社会生活中的身体,从而理解我们特殊的历史连接的复杂性。”[2]身体问题涉及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和机器人研究等诸多学科领域,一大批学者如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詹姆斯、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吉布生(Gibson)、瓦雷拉(Varela)、拉科夫、约翰生、克拉克(Clark)、布鲁克斯(Brooks)、西伦(Thelen)、德雷佛斯兄弟(Dreyfus&Dreyfus)等都或多或少地思考着这一问题。鉴于文章篇幅和我们关注的焦点,在本文中我们基本不涉及具身哲学思想的演变,并尽量把对身体问题的讨论限定在认知科学范围内。
(一)具身或具身性
“从古希腊哲学最早的残片开始,人类就被区别于‘无理性的’动物和所有的低等生物,依据是人类具有独一无二的抽象的概念形成和推理能力。根据这种观点,人类的理性使我们形成抽象的心理表征成为可能,心理表征代表并指向外部的或目前不在我们经验中的(如,是过去的或将来的)事物的状态。”[3]这种逻辑从柏拉图经由笛卡尔等人深深影响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由此引发的情形是,人类往往有意或无意忘记自己是一种生物,忘记自己的身体,忘记自己的生物学属性。比如我们都耳熟能详这些判断:“人是有意识的动物”“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人是游戏的动物”“人是符号的动物”等,但往往忽略了每一判断中宾词的涵义,即归根结底,人是动物,有着漫长的进化史,与生物界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越来越丰富的生物学、习性学和遗传学研究成果表明,人类并未超越生物界而飞升,我们是整个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与所处环境或小生境息息相关。“我们人类是活的生物。当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也在行动,或许我们没有与环境保持一致协调,但是我们的思想从未离开过它。通过我们在环境中的身体意义形成了我们的思维,通过我们与世界的具身接触,形成了我们大部分的抽象推理。”[4]这也就是“Embodiment”或身体问题的基本涵义。
“Embodiment”一词目前有多种译法,如“涉身”“寓身”“融身”“体验”等,可以说都各有理据,我们这里采用了李恒威等人的译法,即“具身”或“具身性”,指我们的心智或认知深深植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以及我们与外部世界的交互体验中。瓦雷拉等人在阐述他们的认知和具身行为理论时对“具身”概念作了澄清:“通过使用具身这一术语,我们试图强调两点:第一,认知取决于经验的种类,这些经验来自于具有多种感知运动能力的身体;第二,这些个体的感知运动能力植根于或内嵌于一个更大的生物、心理和文化背景中。”[5]
具身概念与认知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传统认知科学(或称第一代认知科学)集中在抽象的、离身的符号推理和计算,对身体和心智受外部世界影响并反过来影响外部世界的种种方式很少予以关注。毋庸置疑,生物和神经具身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大脑是在心智与身体之间最明显的联结,理解心智必定要理解认知的神经生理学机制。”[6]当然,仅仅关注大脑还是远远不够的。从神经科学上看,“身体是一个弥散着神经系统的有形之物。正是因为这个神经系统在自然演化中的发展,使生物体从一个单纯的如客观物体一样的外在的躯体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的心智世界的活的身体。所有的哺乳动物(以及更高级的灵长类生物)的神经系统都由集中于脑部的中枢神经系统和弥散于躯体的外周神经系统组成。因此,智能体的身体可以分为两个相对明显的部分:中枢神经系统的脑和弥散于外周神经系统的身躯。人类从行为到言语思维的智力都是通过神经系统的内部调节状态的中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神经存在(neural being)……没有脑神经系统和弥散的外周神经系统的紧密联系,心智的具身性是不可能的。”[7]同时,正如著名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所言,“正是我们的有机体而不是其他什么绝对外部现实成为我们构建周围世界的基本参照,成为那个时刻存在的、构建自我经验主要部分的主观感的参照;我们最周密的想法和最明智的行动、我们最大的喜悦和最深的伤痛,都是以身体作为衡量标准”。[8]在达马西奥看来,身体为心理或者说为脑的表征提供了基本背景、基本参照和基本主题。如果没有具身性,心理可能是无法被观察到的。
当然,讨论身体问题离不开生物学基础,这一点有两个层面,其一是种系发生层面,比如有些研究者主张,只有根据认知器官在其身体的种系发生中所起的生物机能和作用,才能恰当了解自然认知系统。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了解身体的自然史,同样要了解身体进化的小生境(evolutionary niches)。[9]毫无疑问,作为肉身,人类身体与动物身体一样是漫长的自然进化过程的产物。其二是个体发生层面,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人也是动物,个体的身体是活的身体(lived body),而活的身体既是发展的过程,也是发展的产物。
(二)具身认知
在认知科学以及心理学领域,对具身问题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对“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的研究来实现的。尽管具身认知已成为一种明确的认知研究进路、纲领和范式,但人们对“具身认知”的确切含义仍没有一致观点,不同的取向和学科领域有不同的界定。总的来看,可以这样理解“具身认知”: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身体及其与环境的交互为基础的。“认知是根植于自然中的有机体适应自然环境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能力,它经历一个连续的复杂进化发展过程,它最初是在具有神经系统(脑)的身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动力过程中生成的,并发展为高级的、基于语义符号的认知能力;就情境的方面而言,认知是一个系统的事件,而不是个体的独立的事件,因为认知不是排除了身体、世界和活动(action)而专属于个体的心智(大脑)并由它独立完成的事件。”[10]
具身认知观或多或少地涉及以下特征:第一,承认身体及其感觉运动过程在认知中所起的作用。在传统认知观中,身体及其部分被仅仅看作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或执行装置,而具身认知观则认为身体及其部分是关键成分。“基于不同学科的实验证据,许多(即使不是全部)高级的认知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以身体为基础的,它们利用(部分的)模仿或者感觉运动过程的仿真,通过对神经回路的再激活也激活了身体上的感知和行动。”[11]第二,在生物(特别是进化的)机能的背景下理解认知,认知的机能是支持身体活动和运动,正如神经学家沃尔普(Wolpert)所言,为什么植物没有大脑,因为植物不需要运动。[12]第三,认知是实时的、情境化的活动,通常与知觉和行动不可分割。实际上,在具身认知科学看来,认知与知觉和行动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
此外,来自不同学科的许多学者都讨论了“具身认知”的内涵和特点,如威尔逊(Wilson)进一步评价了其六个显著的主张:第一,认知是情境的(Cognition is situated)。[13]认知活动发生在一个真实世界环境的情境中,并且内在地涉及知觉和行动。威尔逊对这一主张提出批评,她认为我们的认知并非都是情境认知,也存在离线认知活动,诸如计划、记忆和白日梦等。人类认知活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它能在任何时候与当前环境交互作用的去耦(decouple)。[14]不过就儿童早期,特别是感觉运动阶段来说,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这一阶段儿童的认知基本上是在线(on-line)的、情境的,必须依靠“个体和环境之间真正的动态耦合”。[15]第二,认知是具有时间压力的 (Cognition is time-pressured)。我们是“活着的心智”(mind on the hoof),必须根据在与环境实时相互的压力下认知如何发挥功能来对其进行理解。第三,个体把认知任务卸载到环境中(We off-load cognitive work onto the environment)。由于人类信息加工能力的限制(例如注意和工作记忆的限制),个体需要利用环境来减少其认知负荷,他们可以利用环境来保存甚至操作信息,而只是在需要时才提取那些信息。第四,环境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The environment is part of the cognitive system)。对研究认知系统本质的科学家来讲,信息在心智和环境间的流动非常密集,川流不息,所以孤立地研究心智是没有意义的。第五,认知是行动导向的(Cognition is for action)。心智的功能是为了指导行动,对知觉和记忆这样的认知机制必须根据它们对情境适当的行为所起的作用来评价。第六,离线认知是基于身体的(Off-line cognition is body-based)。即使脱离开环境,心智的活动也是基于进化而来的,基于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即感觉加工和运动控制的机制。不难看出,这六大主张实质都确认了人是在世存在的(being in the world),即人是活生生的肉身存在,人最初的活动是和环境浑然一体、不可分离的,因此在认知发展过程中,知觉和身体活动始终居于首要地位。
尽管还存在许多争论,具身认知的范式在认知科学领域逐渐取得认可,认知或心智不再被看作是一组逻辑或抽象的机能,“而是一个植根于身体经验,植根于与身体动作的相互连结,植根于与其他个体相互作用的生物系统。从这种观点看,动作和表征不再根据经典的心—物二元来理解,而是相互密切联系的。在环境中的行动,与其中的物体和个体相互作用,表征环境、感知环境、分类环境和理解环境的重要性,也许不过是关系连接的不同水平,这些连接存在于有机体和他们操作、思考、生活的局部环境之间。”[16]
二、婴幼儿的心智是一种具身心智
(一)婴幼儿心智天然的具身性
从发生学角度看,婴幼儿的心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身心智,或者说,婴幼儿心智天然地具有具身性。首先,婴幼儿的存在首先不是作为意识主体,也不是社会主体,而是作为身体主体。儿童来到这个世界,他们与世界的关系是“非二元的”、主客体混沌不分的,即婴幼儿最初的活动是和环境浑然一体的。从个体心理发生来看,儿童与世界的分离首先是身体与世界的分离,然后才是心理与世界的分离。“自我首先是身体自我。我们在婴幼儿期间形成的自我区分是基于与其他物体不同的我们的身体的感觉运动经验。”[17]因此,从认识论角度而言,“真正的认知主体绝不是笛卡尔认识论意义上与自然分化的纯粹精神性的主体,而是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主体(body-subject)。”[18]这种主客体非二元性自发地为认知主体与其所处环境提供了一种朴素的、非结构性的耦合(unstructural coupling)关系。
其次,从个体认知发生来看,最初的心智和认知是无疑是基于身体的,身体构成了婴幼儿自我的核心。达马西奥指出,“早期身体信号,无论是在进化还是发育过程中,都有助于形成自我的基本概念。”[19]有充分的理据表明,“从发生和起源的观点看,心智和认知必然以一个在环境中的具体的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因此最初的心智和认知是基于身体和涉及身体的,心智始终是具(体)身(体)的心智,而最初的认知则始终与具(体)身(体)结构和活动图式内在关联。”[20]实际上,婴幼儿认知乃至整个心理活动都是建立在身体运动提供的感觉刺激和原始信息供大脑处理的基础上的。
第三,感觉运动活动或协调在婴幼儿认知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感觉运动协调是从婴儿到成人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作用程序之一,它构成了许多种学习的基础。”[21]感觉运动协调的根本作用在于它能够为儿童在真实世界中进行复杂的分类提供基础,实际上婴儿的抓、握、拿、咬等动作在吉布生的可供性(affordance)意义上已经就是对外部世界的最初分类。史密斯和加瑟(Smith&Gasser)更是提出:不需要外部任务或教师,“仅仅通过在环境中的知觉和行动,多重重叠和锁时(time-locked)的感觉系统使发展中的系统能够‘教育’自身。”[22]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也反复表达了这样的看法。皮亚杰认为,活动(必然是主体的身体活动)既是感知的源泉,又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基础。在感知运动阶段,通过感知和动作及其协调,儿童建构起复杂的动作图式或格式。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动作的内化,儿童形成更加高级的思维和运算。在“具身性假设背后的中心观点是:心智或智慧是在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中涌现出来的,是感觉运动活动的结果”。[23]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婴幼儿的认知是实时的,是一种在线认知(on-line cognition)、情境认知。总之,婴幼儿生活在一个具体的、真实的物理世界中,这个世界“充满了丰富的对知觉、行为乃至思维起组织作用的种种规则。”[24]婴幼儿的心智不仅存在于他们自身,同时也分布于他们与物理世界、文化环境(包括语言和人工制品)的互动和经验之中。从根本上讲,身体或具身及其与环境的耦合关系不仅涉及婴幼儿认知发展的核心机制,也构成了高水平认知或抽象思维的基础。
(二)具身认知的理据与证据
1.发展心理学研究的支持。
发展心理学家提供了支持具身认知假设的关键证据与理据。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特别是皮亚杰始终认为认知技能是在感觉运动能力的基础上涌现出来的,他把“成人认知如何在感觉运动能力的基础上形成看作发展心理学的核心问题”,[25]认为高级认知是在感觉运动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26]从而对认知如何由非认知过程产生提供了一种整合的观点。在皮亚杰看来,儿童认知发展的最早阶段在很大程度上由感觉运动能力构成,不妨看一下他对二级循环反应(secondary circular reaction)的描述:4个月和4个半月的婴儿“抓住挂在他的摇篮顶部的一根细绳,拉动绳子,使挂在摇篮上面的拨浪鼓摇晃起来。婴儿很快又多次重复这个动作,每次动作有趣的结果又会促使他再次重复。这构成了鲍德温(Baldwin)意义上的‘循环反应’,或者是在初生状态下的新习惯,这里获得的结果和手段还没有分化。稍后,你只需要在摇篮顶部挂一个新玩具,让儿童寻找绳子,就开始构成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分化”,而这正是智慧的萌芽。[27]幼小婴儿对手眼的控制还缺乏组织,他们与玩具的互动不过短短几分钟,但他们的活动就变得非常有组织并且明显是目标导向的。皮亚杰确信这种活动模式涉及多通道知觉—动作环(multimodal perception-actions loops),是理解智力起源的关键所在。[28]显然,感觉运动的各个成分在不同任务、不同方式中的结合使其并不像我们通常想象的那么简单,感觉运动各成分间的协调、耦合和重叠,为婴幼儿的心智提供了大量的雍余性和复杂性。巴萨娄(Barsalou,L.W.)等人就认为有理由相信感觉运动中这些重叠的协调(overlapping coordinations)是认知发展的动力,能够创造高水平的抽象。[29]
另一位关注感觉运动能力研究的大师是发展心理学家西伦,她以婴儿动作研究著名,对婴儿的学步(walking)、够物(reaching)等行为作了大量研究。西伦提出高水平认知的发展并不要克服或抛弃儿童早期获得的感觉运动能力,而是将其整合到高水平认知,并使其更加灵活。[30]西伦和史密斯等人的研究还进一步证实了身体记忆在皮亚杰经典任务(A非B错误)中的作用。[31]结果表明,当婴儿在够物任务中够到几次目标物后,他们会对目标以及手臂的感觉及姿势定势建立起位置记忆,接下来这些记忆会影响婴儿进一步够物的决策。这清晰地证明,运动与作为“认知”过程的记忆和决策是不可分离的。
2.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支持。
上面已提到,拉科夫和约翰生关于认知科学的三个基本命题:心智的体验性;思维的无意识性;抽象概念的隐喻性。第三个基本命题也可以看作是具身认知的语言学证据。拉科夫和约翰生反复强调,“我们绝大多数正式的概念系统是用隐喻构造的”,[32]“我们的绝大部分日常的概念系统本质上是隐喻的”。[33]而大量的隐喻来自身体及其关联行为与特性,抽象概念、范畴和推理并不是对外部现实客观的、镜像的反映,而是由身体经验形成的,特别是由感觉运动系统形成的,是具体概念特别是身体概念的隐喻扩展。在拉科夫和约翰生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他们列举了大量身体隐喻的实例,即各民族语言中大量存在的以身体器官、身体动作、身体感觉为基础的隐喻以及以身体为参照的空间隐喻。拉科夫和约翰生还进一步指出:“推理,甚至就其最抽象的形式而言,都利用了而非独立于我们的动物本性(animal nature)”。[34]也就是说,对概念包括抽象概念的运用和推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身体中的感觉运动系统,依赖于以我们与外部世界的空间关系和我们身体部位为基础的隐喻,所以身体是直接参与到认知过程中的。
3.镜像神经元:具身认知之根。
所谓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是指一类特殊神经元,它们能在主体没有直接的外显动作的情况下,仅仅看到别人进行相同动作时也会被激活。20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帕尔马大学里佐拉蒂(Rizzolatti)教授带领下的研究小组在研究猴脑运动皮质(motor cortex)时偶然发现,当猴子有目的地做出某个动作时,猴脑中的某些神经元就会处于激活状态。让研究人员更为吃惊的是,当被研究的猴子看到同伴做出同样的动作时,这些神经元也会被激活。这类神经细胞似乎就像一面镜子,能直接在观察主体的大脑中映射被观察对象的动作,所以研究者将这类神经元称为镜像神经元。随后,研究者在人类大脑的相应区域也发现了镜像神经元。镜像神经元对个体社会认知,如行为理解、模仿学习、手势交流、移情、语言和心理理论等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35]
总之,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如吉布生在知觉生态学领域的开拓性工作,特别是其提出的可供性(affordance)概念,代表了具身认知范式的先驱。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在这里无法展开。这些证据背后其实是身体的进化史和自然史,是身体进化的小生境(niche),只有根据认知器官在身体的种系发生上具有的生物机能和功用,才能最充分地理解自然的、具身的和实时的认知系统。“实际上,任一心理现象(包括认知活动)只是不断发生着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动态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片断,而且这动态演化还有历史进化的一面。所谓‘认知即认知发展’这一说法就深刻地表达了这一思想。”[36]实际上,“大多数具身认知文献背后都隐含着进化的论据……具身认知取向试图提供生命短暂的简单生物和现代人之间的认知上的连续性”。[37]这里我们再一次回到了“进化、发展与儿童早期教育”这一主题。
三、具身认知科学对儿童早期发展与教育研究及实践的意义
(一)当代儿童早期教育中被遮蔽的身体
在当前儿童早期教育领域,人们关注的焦点往往是语言、计算等领域,身体及其相关问题很少进入理论研究视野,在实践中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似乎相对于心智与知识而言,身体是不重要的、低水平的,感觉和运动教育也是无足轻重的。西方学者布莱恩·特纳对社会理论的批评用在这里非常贴切:“社会理论在理解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行为的过程中实际上忽视了人体的重要性。人体的特性,虽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无论是在社会研究还是社会理论中都不重要。结果,身体在社会思想中奇怪地遗失了或缺席了。”[38]无独有偶,著名美学理论家迪萨纳亚克也批评道:“实际上,2000多年以来,即使不总是在实践上也是在理论上,身体和感官一直被看作心灵和理性的对立面,并且在任何有关人类特征的讨论中都被降到次要的位置”。[39]如果说身体在社会研究还是社会理论中还可以说是一种遗憾的话,身体在教育特别是儿童早期教育中的缺失就是不折不扣的悲剧了。
(二)身体及其活动应是儿童早期教育的出发点
具身及具身认知研究对儿童早期教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具有重大意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将身体及其活动当作儿童早期教育的出发点,也有充分必要承认感觉运动及其耦合的特定价值,承认儿童与客体、与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交互的重要性。
首先,活生生的、整体意义上的身体活动是儿童早期教育的出发点。具身认知研究告诉我们,儿童早期(特别是感觉运动期)的认知是实时的、在线的和整体的,是通过活生生的身体在具体环境中的行动来实现的。“心理首先必须是与身体相关联的,只有在身体持续提供的基本参考基础上,心理才有可能与其他很多真实或想象的事物有关联”。[40]正如加德纳所指出的那样,“儿童不存在思维引领动作或者通过动作形成思维等问题,他们思维与动作融为一体……一个听音乐和听故事的儿童,他是利用自己的身体在听的。他也许入迷地、静心地在听,或者晃着身体,保持节拍地在听,或者这两种心态交替着出现。但不管哪种情况,他对这种艺术对象的反应都是一种身体反应,这种反应弥漫着身体感觉。”[41]
第二,应关注感觉—运动活动在儿童早期发展中的重要性。具身认知研究表明,婴幼儿的认知是感觉—运动性质的,他们的认知无法与感觉—运动割裂开来,感知和动作也是根本不可分离的,同时他们的感觉—运动系统又是与环境高度交互的。
第三,儿童与物理现实的交互、与环境的交互、与他人或社会的交互是紧密联系、高度统一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许多研究表明,儿童与物理现实的交互、与环境的交互、与他人或社会的交互两者之间紧密依存,不可或缺。“感觉—运动协调需要由社会性交互来补充,看上去感觉—运动加工与社会性交互的结合会给发展提供最强大的动力”。[42]诸多证据支持早期动作发展和感觉运动经验不仅有助于婴幼儿认知发展,也有助于他们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动作技能的延迟或受损,如在自闭症等情况下,对婴幼儿的社会互动和发展有负面影响。[43]这充分说明早期动作发展非常重要,因为早期动作发展必然带来感觉的发展以及经验的扩展,教师应尽可能鼓励儿童主动探索,不但与物理现实、外部环境积极互动,同时也要积极与他人或社会互动。
四、结语
史密斯和西雅(Smith&Sheya)提出,“有充分理由表明主流认知科学长期以来不能有效解释认知发展,主要是因为它基于去身或无身(disembodied)的观点。”[44]毫无疑问,新的认知科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解释认知发展,包括具身认知的发展。认知科学的研究离不开认知发展的研究。具身认知研究无疑将大大推动儿童认知发展研究和儿童认知发展理论的建构。同时,也要看到对于具身认知发展的研究还刚刚起步,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从激进具身观(radical-embodiment)到温和具身立场,具身理论也呈现极为复杂、多元的趋势,远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同时,具身认知还需要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
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指出:“长期对身体缺乏社会学式的理解,对于医学社会学、对大量的其他社会领域,诸如情绪、性、体育、激情和衰老等,都会有一些关键性的影响。正是在这些领域(健康、体育、休闲、性和消费主义)中,身体、社会和文化的互动是社会实践的关键特征,也是在这里,我们才死活需要一个有关‘活生生的身体’的精巧复杂的社会学……对许多实际领域来说,身体社会学至关重要。”[45]然而在当前发展心理学中,“关于发展的纯粹的认知观点倾向于把身体看作评价儿童真实认知能力的一种障碍物。身体不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妨碍揭示儿童真正能力的障碍。”[46]同样,对儿童早期教育研究与实践而言,长期对身体缺乏理解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现实,并严重影响到了儿童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的实践。儿童早期教育研究与实践需要关注身体问题,当然仅仅依靠身体社会学或心理学都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更加广阔的理论背景上构建一门新的、科学的儿童身体教育学,或者说儿童教育学很大程度上可以是身体教育学。
注释:
①对“embodiment”的关注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大量的个体发展问题(如皮亚杰、维果斯基)、运动和动作问题(如E.Thelen等),同时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发展的”,即对个体而言,认知不是一开始就处于言语思维的高级认知水平,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见李恒威,黄华新.“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观[J].哲学研究,2006,(6))。
参考文献:
[1][34]Lakoff,G.&Johnson,M.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3,4.
[2][38][45][英]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A].汪民安,陈永国编.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9,19,19.
[3][4]Johnson,Mark,&Tim Rohrer.We are Live Creatures:Embodiment,American Pragmatism and the Cognitive Organism[A].In Tom Ziemke,Jordan Zlatev&Roslyn M.Frank(eds.).Body,Language,and Mind[C].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7.
[5]Varela,F.J.,Thompson,E.,&Rosch,E.The embodied mind: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M].Boston:MIT Press,1991:172-173.
[6]Chrisley,R.,Ziemke,T.“Embodiment”[R].the Macmillan Encyclopedia of Cognitive Science,2002.
[7][10][18][36]李恒威,黄华新.表征与认知发展[J].中国社会科学,2006,(2):34-44.
[8][19][40][美]达马西奥.笛卡尔的错误:情绪、推理和人脑[M].毛彩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4,185,5.
[9]Sloman,A.Evolvable Biologically Plausible Visual Architectures[A].In Tim Cootes,T.and Taylor,C.(eds.).The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Machine Vision Conference[C].Manchester:BMVC Press,2001:313-322.
[11]Svensson,H.,Lindblom,J.&Ziemke,T.Making Sense of Embodied Cognition:Simulation Theories of Shared Neural Mechanisms for Sensorimotor and Cognitive Processes[A].In Ziemke,Zlatev&Frank(eds.).Body,Language and Mind[C].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7:241-269.
[12][21][42][瑞士]Rolf Pfeifer等.身体的智能——智能科学新视角[M].俞文伟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18,87,129.
[13][14]Wilson,M.Six views of embodied cognition[J].Psychonomic Bulletin and Review,2002,(9):625-636.
[15]Fernando Almeida e Costa,Luis Mateus Rocha.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Embodied and Situated Cognition[J].Artificial Life,2005,11(1-2):5-11.
[16]Garbarini,F.,Adenzato,M.At the root of embodied cognition:Cognitive science meets neurophysiology[J].Brain and Cognition,2004,56:100-106.
[17]李恒威,黄华新.“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观[J].哲学研究,2006,(6):92-99.
[20]李恒威,盛晓明.认知的具身化[J].科学学研究,2006,(2):184-190.
[22][23][24]Smith,L.B.&Gasser,M.The development of embodied cognition:Six lessons from babies[J].Artificial Life,2005,(11):13-30.
[25]http://www.readperiodicals.com/201112/2562297911.html,2013-7-1.
[26]Thelen,E.Motor development as foundation and future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2000,24(4):385-397.
[27]Piaget,J.,&Inhelder,B.The psychology of the child[M].New York:Basic Books,1969:10.
[28][44]Smith,L.B.&Sheya,A.Is Cognition Enough to Explain Cognitive Development?[J]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2010,(1):1-11.
[29]Barsalou,Simmons,W.K.,Barbey,A.K.,&Wilson,C.D.Grounding conceptual knowledge in modality-specific systems[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2003,(7):84-91.
[30]Thelen,E.Grounded in the world: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the embodied mind[J].Infancy,2000,(1):3-28.
[31]Smith,L.B.,Thelen,E.,Titzer,R.,&McLin,D.Knowing in the context of acting:The task dynamics of the A-not-B error[J].Psychological Review,1999,106:235-260.
[32][33]Lakoff,G.&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56,4.
[35]Rizzolatti G&Craighero L.The Mirror-Neuron System[J].Annu Rev Neurosci,2004,27:169-192.
[37]Wilson,M.How did we get from there to here?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on embodied cognition[A].In P.Calvo&T.Gomila(Eds.).Directions for an Embodied Cognitive Science:Towards an Integrated Approach[C].Elsevier,2008.
[39][美]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艺术来自何处及原因何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5.
[41][美]加德纳.艺术与人的发展[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119.
[43]Motor Experiences and Social Skills:A new way to think about development[EB/OL].http://speech-language-pathology-audiology.advanceweb.com/Archives/Article-Archives/Motor-Experiences-and-Social-Skills.aspx,2013-7-1.
[46]Needham,A.,&Libertus,K.Embodiment in Early Development[J].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Cognitive Science,2011,(2):117-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