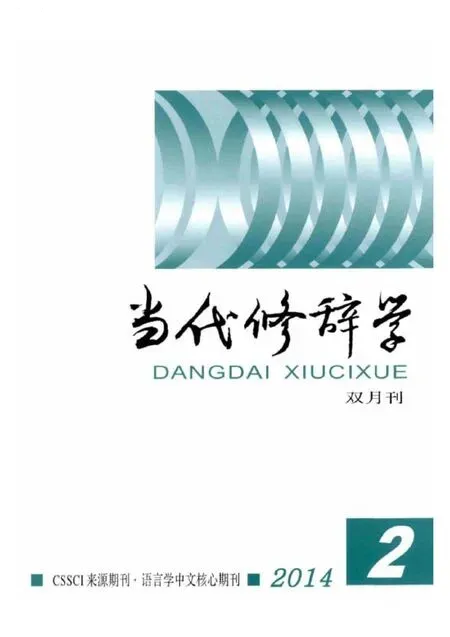“招聘”和“求职”:构式压制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
施春宏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北京100083)
提 要 本文在对构式压制的内涵做出重新定位的基础上,讨论了构式压制的范围,并从构式对组构成分的“招聘”和组构成分向构式的“求职”这两个角度刻画了构式压制过程中存在的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借此讨论构式压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文章最后论及了构式研究中出现的构式崇拜问题。
一、构式语法兴起及其所面对的构式压制现象
构式语法的兴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动因。一是对一般语法研究或主流语法研究中不怎么重视的边缘现象的关注,特别是对习语性构式(如熟语、成语、固定或半固定格式等)形义关系特异性的分析,如 Fillmore,Kay&O’Connor(1988)关于“let alone”、Kay&Fillmore(1999)关于 WXDY 构式(“What’s X doing Y?”)的规则性和习语性(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的研究;二是对主流句法理论不好处理的非常规句法现象的探讨,如对论元增容或减容之类的所谓的构式压制(construction coercion)现象的研究,特别关注句式性构式构造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殊形义关系。对非常规现象、边缘现象的关注及其句法化描写和解释,推动了构式观念的深入发展和构式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例如下面是可资比较的“经典”现象:
(1)He put the napkin on the table.(他把餐巾纸放到了桌子上面。)
(2)He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他打喷嚏把餐巾纸打到了桌子下面。)
从论元结构上看,这两个句子都是表示使移(caused-motion)关系的三元构式,每个构式中都含有三个论元,其配位方式是:施事+动词+受事+处所。然而,“put”是“天然的”三元动词,进入三元构式中,是一种自然的功能呈现。而“sneeze”是“天然的”一元动词,现在却能出现于三元构式中,这便出现了所谓的论元增容(argument augmentation)现象。这就出现了问题:作为一元动词的“sneeze”为什么能出现在三元构式中?构式语法的解释策略(如Goldberg1995)是,假设构式本身具有论元结构或曰配价结构,具体动词进入构式中体现为一个例示(instantiate)的过程,它的论元角色跟构式的论元角色发生融合(fusion)。如此一来,必然的推论就是:如果一个动词的论元结构及其所支配的所有论元角色跟构式所提供的论元结构及其角色属性完全一致的话,该动词就能很自然地例示构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然而,如果一个动词的论元结构及其所支配的论元角色跟构式所提供的论元结构及其角色属性有所出入的话,构式就要对那些有所背离的论元结构及其角色属性进行“修整”,从而制造出合格的成品。具体到例(2),就是三元构式将该构式的论元结构及其相关论元角色派送给sneeze,使其实现三元结构化,从而进入该构式之中。这种对动词论元结构(属于句法理论中的语义结构)“修整”的过程,即经过施压而制作成功的过程,就是一般所言的“构式压制”。
显然,就此论断而言,构式压制就是自上而下的“加压”过程。然而,这里面似乎有一些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思考。其中最关键的是,是否只要施加构式的压力,就可以迫使非三元动词实现三元结构化?语言事实告诉我们,并非如此。那么,对一个非三元动词而言,如何知道它是否可以实现三元结构化?具体条件是什么?其运作方式如何?这恐怕是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再来看两个例子。有人用构式压制来解释程度副词修饰名词(下文径作“副+名”或副名组合)的现象,如“很阳光、非常淑女”等,认为其中的名词经过构式压制后形容词化了或非范畴化了,从而能够进入这个构式中。然而,并非所有的名词都能进入副名组合中,如不能说“很茶杯、很天花板”等;而且这样的说明也不好解释为什么“很香港、很山东”的可接受程度大大高于“很西宁、很山西”。任何一个理论,既要能够说明合式的表达,也要能够说明不合式的表达,还要能够说明不同现象之间合式程度的差异。又如近些年出现了“被自杀”类的新“被”字式,有人基于构式压制的观念认为其中的不及物动词“自杀”经过构式压制后及物动词化了。然而这并不好说明新“被”字式“被”后的成分也可以出现及物动词的情况,如某人没有抄袭别人的作品但被传为抄袭了,因此可以构成新“被”字式“被抄袭”。①
由此可见,构式压制从根本上说,只是一种基于非常规现象、边缘现象生成方式的概括,而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解释。当然,这种概括是很重要的概括,它揭示了非常规现象、边缘现象的语言价值(language value),使人们认识到这些非常规现象是交际系统中早已存在的重要现象,而且有时还是推动语言现象发展演变的重要现象。同时它还揭示了非常规现象、边缘现象的语言学价值(linguistic value),使人们认识到通过对非常规现象、边缘现象的分析,能够更深入地认识常规现象、核心现象的本质和整个语言系统的存在状态,从而推进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更新。②
关于构式压制的内涵及其生成机制,构式理论研究已经做了相当深入的讨论(如Goldberg1995,De Swart1998,Panther& Thornburg1999,Michaelis2003a、2003b、2004、2005,Lin&Liu2005,Traugott2007,Ziegeler2007,Bergs&Diewald2008,等)。汉语学界在引入相关认识的同时将它运用到汉语研究的实践中,关注的问题如关于构式压制的转喻机制以及更为具体的凸显、抑制、增加、剪裁等识解机制(如李勇忠2004a、2004b,袁野2010,杨勇飞等2011,崔雅丽2012,董成如2012等)、副名组合的语义压制问题(黄洁,2009a;王寅,2009)、体压制(袁野,2011),以及存现句(董成如等,2009;董成如,2011)、双及物句(黄洁,2009b)、非常规单宾构式(许萌等,2011)、中动句(李炎燕,2011)、被动句(袁佳玲,2008;李勇忠,2004a)和“被自杀”类新被字式(冷慧等,2011)、祈使句(吴淑琼等,2011)等构式生成中的压制现象。王寅(2011)在介绍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词汇压制等若干新的压制现象。施春宏(2012)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拓展,本文在此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探讨,试图对构式压制的内涵和机制的本质问题提出新的认识。基于我们的理解,本文借用“招聘”和“求职”这两个概念来隐喻性地描写和解释构式压制乃至构式生成过程中存在的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
二、构式压制的内涵及范围
要分析构式压制的机制,首先需要对构式压制的内涵及范围做出明确的说明。而目前学界对这两方面的认识都需要进一步调整。
1.构式压制内涵的再认识
关于构式压制的理解,目前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共识。但我们通过对被学界视为构式压制的现象和过程的具体分析,觉得有必要对构式压制的内涵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概而言之,目前学界一般将构式压制理解为构式将压力自上而下地施加到进入构式的不合常规的组构成分之上,使之满足构式意义上的要求。如Goldberg(1995:238)认为“构式对词项施压使其产生跟系统相关联的意义”,Michaelis(2004:25)认为“如果一个词项在语义上跟其所出现的形态句法环境不相容,那么该词项的意义就应当适应包含着它的结构的意义”,王寅(2011:322)认为“当动词义与构式义不完全一致或相冲突时,构式常会迫使动词改变其论元结构(增加或减少动词的论元数量)和语义特征”。③
显然,这些认识的共同之处都是将构式压制理解成为解决整体和部分的语义冲突而采取的语言机制。然而,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我们很难说例(2)中的“sneeze”在三元构式中语义发生了变化。既然这是个三元构式,那么自身所提供的论元结构和论元角色就未必需要其组构成分来负担。而且这种认识还容易引发一个显著的理论悖论:提出句式性构式具有论元结构是为了反对词汇中心论(Lexicalism)在解决相关问题时所采取的核心投射策略;而如果认为构式将其论元结构派送给其组构成分,从而使“sneeze”成了三元动词,这便又陷入词汇中心论的逻辑之中。基于这样的分析,施春宏(2012)对构式压制的内涵做出了重新定位:“所谓构式压制,指的是这样的现象:在词项进入构式的过程中,如果词项的功能及意义跟构式的原型功能及意义不相吻合,那么构式就会通过调整词项所能凸显的侧面来使构式和词项两相契合。”这种认识对构式压制的内涵做出了更一般的理解,它不但强调了意义的压制,还突出了功能的压制,更重要的是指出构式压制的机制是一个认知凸显的过程,其目标是“使构式和词项两相契合”,而不只是使词项“臣服”于构式。正如Ziegeler(2007)所探问的那样:既然词项与构式有冲突,那么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就是:压制究竟如何在自然语言的上下文中被认为是合理的。施春宏(2012)的“契合论”正是试图对此做出的回答。本文则进一步指出,这种契合机制是通过构式的“招聘”机制和组构成分的“求职”机制的互动关系而发挥作用的,在这种互动机制中,“招聘”机制起着主导作用,“求职”机制起着主体作用。如果这种认识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构式压制的内涵则可以进一步调整为:“所谓构式压制,指的是这样的现象:在组构成分进入构式的过程中,构式向组构成分提出需要满足的准入条件,如果组构成分的功能、意义及形式跟构式的常规功能、意义及形式不完全吻合,则通过调整其功能和意义结构及形式结构中的某些侧面以满足该准入条件,若两相契合,则构式压制成功;若不能两相契合,则构式压制无效。”根据这样的理解,构式压制过程中的互动机制不仅发生在功能及意义之间,同样可以发生在形式之间,更重要的是发生在不同语言层面的交界面。这就牵涉我们对构式压制范围的理解。
2.构式压制的范围
由于构式本身是普遍存在的④,而所有的构式都存在从典型成员到次典型成员到边缘成员这样的范畴原型效应(prototypical effect),这样在语言交际的在线生成过程中,构式压制现象也必然是无所不在的(pervasive)。既然如此,对构式压制的理论分析自然可以涉及语言系统、语言交际的各个层面。基于这种认识,相对于目前主要关注来自构式对词项的(意义上的)压制,我们将构式压制的内涵做了更为宽泛的理解,使其不仅局限于功能及意义层面的压制,进一步拓展到形式层面的压制;不仅局限于构式和词项之间的压制,进一步拓展到任何构式及其组构成分之间的压制。也就是说,构式压制可以有宽窄不同的理解,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狭义的构式压制、广义的构式压制和宽泛意义上的构式压制。
狭义的构式压制指句法层面上出现的构式压制现象。目前讨论的构式压制现象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基于这种理解,尤其是关于句式和体(aspect)与其组构成分之间存在的压制现象。修辞层面的“超常”搭配现象本质上也应该看作构式压制(施春宏,2012),例如由“瘸了腿”而在特定语境中构造出“瘸了手”甚至“瘸了心”。
广义的构式压制指语法层面上出现的构式压制现象,除句法层面外还包括词法层面的构式压制。如“形+化”,其中的“形”(形容词性成分)具有变化后的描述性特征(如“自由化、丑化”);如果其他成分进入其中,必须能凸显其中的描述性特征(如“电子化、国际化、民营化”)。
从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念来看,句法结构、词法结构的生成基础受到概念结构/语义结构的促动,因此句法层面和词法层面的构式压制往往都伴随着概念结构/语义结构的调整,即跟概念结构/语义结构中结构成分的凸显与潜隐等调整机制有关。
上面的构式压制现象都牵涉到形式和意义之间关系的调整和适应。然而,如果对构式压制做出更为宽泛的理解的话,形式之间也存在构式压制现象。北京话中的儿化现象,就可以看作一种构式压制现象,如“guan(罐)+er→guar(罐儿)”,儿化的操作使“罐儿”的读音变得跟“褂儿”基本一样了。韵律对句法的制约作用,从句法结构生成的角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形式上的构式压制现象。如“关严了窗户”可以说,是因为“关严”构成了一个韵律词;而“关严实了窗户”(“实”为音足调实的音节时)不能说,因为“关严实”不能构成一个韵律词,因此不能带宾语;若要维持“动补式结构+宾语”的句法格局,就需要对“关严实”的韵律结构进行压制,从而形成“关严·实”(“实”读轻声),基本满足了动补结构带宾语的韵律要求。(冯胜利,2000)当然,压制的成功与双音节补语第二个音节能够轻声化有关;如果不能实现轻声化,便不能实现有效的压制而生成合法的表达。
基于宽泛意义上的理解,需要将构式压制理解为常规构式与非常规组构成分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简单地理解成构式和词项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哪种范围的理解,其本质都是一致的,就是构式整体和部分之间、部分和部分之间在功能、意义及形式上如何化解冲突、如何实现和谐的问题⑤。显然,构式压制理论所要研究的关键问题就是(特定)条件和(特殊)现象之间的关系及其运作机制。这实际上也是所有语言研究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
三、构式压制的作用机制
基于上文对构式压制内涵的重新定位,我们认为,构式压制效应的发挥是构式和组构成分互动式作用的结果,构式提供了需要满足的基本要求,组构成分提供了能够满足的基本条件,两者相互选择、相互配合,“在构式和组构成分的特征契合中实现构式压制”(施春宏,2012),从而实现了有效的表达。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进一步将构式压制过程中的这两个方面分别用“招聘”和“求职”来隐喻说明。下面先分而述之,然后综合讨论。
1.构式对组构成分的“招聘”机制
构式作为一个形义配对体⑥,对语言系统中的各类语言成分提供形式和意义/功能上的准入条件,满足了准入条件就能成为构式成员集里的合格的成分,否则就无法进入构式集中。这有些类似于生成语法中的特征核查(feature-checking)。如果一个组构成分满足了构式形式和意义/功能上的所有要求,自然就能完全通过特征核查。这种具体用例便是该构式的典型样本。如果一个成分只满足了其中的部分要求,但这些要求在整个构式的构造中具有关键作用,因而能够接纳那些虽不具备充分条件但已具备必要特征的成分,从而也能实现合法的表达形式。这便是构式压制。换个说法就是,构式压制的基本体现就是使进入其中的组构成分满足构式的形式和意义/功能上的关键性特征要求。这实际上跟现实生活中的“招聘”情况比较相似。如果将一个岗位比作一个构式的话,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的时候会根据自身需要明确岗位性质,设定岗位要求,从而(理论上)面向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招聘。也许有人完全满足招聘的条件,也许有人仅满足招聘的部分条件,但关键条件已经具备,他们都可以成为该岗位的人选;否则就没有进入岗位的可能。举例来说,下面是三种类型的“把”字句:
(3)张三把苍蝇打死了。 (张三打苍蝇+苍蝇死了)
(4)孩子把妈妈哭醒了。 (孩子哭+妈妈醒了)
(5)(唱)这首歌把嗓子唱哑了。 ([某人]唱这首歌+嗓子哑了)
例(3)例示了现代汉语句法系统中“把”字句的原型形义关系:施事+把+受事+及物性动作+结果。其中施事“张三”发出及物性动作“打”,受事“苍蝇”在及物性动作直接作用下产生某种结果“死了”。然而,“把”字句的构式形义关系是可以拓展的,拓展的基本条件是“把”字句所表达的事件结构包括使因事件和使果事件两个方面,而且需要凸显使果事件主体所产生的结果。这样,即便是非及物动词,如果满足了这样的条件,也可以进入“把”字句。如例(4),其中的“哭”是不及物动词,但这个句子满足了这里提及的“把”字句的基本条件。从“把”字句原型形义关系来说,“哭”进入其中显然存在着构式压制的情况。当然,如果我们将“把”字句的形义关系概括为“致事+把+役事+致使行为+结果”,那么“把”字句的语法意义则是“通过某种方式,凸显致事对役事施加致使性影响的结果”(施春宏,2010a)。若此,例(4)就不再经历构式压制了,而是例示了其扩展了的构式。尤其是例(5),从原型构式来看,这个句子生成过程则更为复杂(参见施春宏2007)。虽然“唱”是施事发出的及物性动作,但这个动作跟受事/役事“嗓子”没有直接的句法语义联系,“唱”的宾论元“这首歌”提升为役事是转喻的结果,转指“某人唱这首歌”,属于实体转指事件;同样,若将“唱这首歌”提升为役事,也是转喻的结果。这两种转喻都是部分转喻整体。转喻机制在整个句式的生成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有时某个现象是否看作构式压制,还跟我们对构式形义关系的概括有关。如果就例(3)所例示的原型形义关系而言,例(4)和(5)存在构式压制现象。如果将“把”字句的形义关系抽象为“致事+把+役事+致使行为+结果”,则三个例子从不同角度例示了这个构式,形成三种不同的下位类型。一般研究构式压制现象的文献容易将例(5)看作词项和构式之间的形义“误配”(mismatch),然而,如果我们的分析成立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误配并不存在。可见,“招聘”的条件有时基于不同的识解(construal)角度。这就启发我们要对相关现象进一步做出一致性概括、跨构式概括(generalization across constructions),从而对所谓的构式压制现象的“招聘”机制做出更具涵盖力的分析。
2.组构成分向构式的“求职”机制
根据构式理论的基本观念,任何语言单位都是构式。这样说来,进入构式的组构成分实际上也是构式,都有自己的形式和意义/功能方面的特征。它们在交际中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寻找合适的结构,有了合适的位置通过了特征核查就能够整合到上位构式中去。这有些类似于生成语法的句法结构生成过程中的“并合”(merge)机制,也跟现实生活中的“求职”情况比较相似。这些组构成分以自身具备的某些形式和意义/功能特征,在语言交际系统中寻找机会,展示自身条件(素质),通过寻找合适的位置而进入某些构式中使自己的某些特征凸显出来。
这也就意味着,处于求职状态中的组构成分并非必然只适合于某一种构式。如“sneeze”,除了例(2)的用法外,还可以出现于下面这样的构式中:
(6)He sneezed.
(7)He couldn’t stop sneezing.
(8)He stopped to sneeze.
这三种用法一般看作是“sneeze”的常规功能,而例(2)中的“sneeze”则被视为非常规功能、边缘用法,经过了构式压制。又如“阳光”在“一束阳光、金色的阳光、在阳光下、阳光灿烂、吸收阳光”之中,被视为常规功能,而在“很阳光”中,则被视为非常规功能、边缘用法,受到了压制。
显然,“sneeze”和“阳光”能适应很多职位,只不过有的职位的要求跟其所具有的特征契合度高,其典型特征本身就处于凸显的状态;有的契合度稍低,组构成分中适合于构式的某些特征需要通过构式压制才能得到凸显;有的在关键特征上并不契合,因此“求职”自然不能成功。当我们说“sneeze”在例(2)中和“阳光”在“很阳光”中存在误配现象时,都是从常规构式的角度来识解的,如果从“求职”机制着眼,这些用法实际上都折射出它们的潜在交际能力。由此可见,具体的组构成分在“求职”过程中,构式压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化隐为显,有时还要变显为隐。也就是说,具体组构成分已经在语言交际中练就了一身本领,因此并非只有在特定构式中才能显示出来(虽然常常在某个特定构式中显示出来),它的能量释放方式常常有很多种。
3.构式和组构成分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
由上文通过“招聘”和“求职”两个隐喻来说明构式及其组构成分的整合过程可知,无论是常规构式、核心构式的生成过程,还是非常规构式、边缘构式的生成过程,都是构式和组构成分双向互动合力作用的结果。
就此而言,“压制”这个术语并非最合适的表达,对组构成分而言,它体现的是一种完全被动的机制,而且似乎预示着,某个组构成分本来是不具备构式的准入特征的,经过一番压制之后而变得具备了该特征。⑦根据我们对构式生成过程的认识,我们认为构式压制过程中,组构成分实际上也实现为寻找、选择这样比较主动的机制。所谓的构式压制,更准确地理解,应该是“招聘”和“求职”同时发生的双向互动过程,是在相互的条件不完全契合时寻找关键契合点的过程。招聘,提出入职条件,吸引参与者;求职,展示所能从事职业的素质,释放自己的潜能。只有两相结合,才能生成合格的构式。⑧因此,构式压制是“招聘”机制的主导作用和“求职”机制的主体作用同时运作的结果。当然,相对而言,构式压制的关键在于被压制者自身的可塑性。因此研究构式压制现象的关键在于对被压制对象“可塑”特征及其呈现机制的分析,从而实现现象条件的具体化和生成机制的规则化。正如陆俭明(2006)在分析句法语义接口问题时指出的那样,“重视词语的句法、语义的特征的研究与描写,将是解决好句法语义接口问题的重要一步。”
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所谓的转类、去范畴化、转喻等在构式压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无非就是凸显构式所要求和组构成分所拥有的关键特征(“神似”),调整其他特征,从而跟构式的典型成员在形式上相合(“形似”)。就此而言,我们不怎么同意这样的隐喻性说法:“词汇与语法构式之间的关系,犹如液体和容器之间的关系,我们把液体装在某一特定形状的容器中时,液体就被‘压制’成容器的形状。”(王寅,2011:70)因为在灌装的过程中,液体的性质并没有调整,而且液体对容器没有选择性;可是词汇对构式具有选择性。语言表达都是构式及其组构成分受限合作的结果,体现为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
由此可见构式压制表象之下的实质。从“招聘”和“求职”相契合的过程来看构式的生成过程及“超常”组合中所呈现的构式压制现象,在构式压制过程中,构式和组构成分之间呈现的“异”只是一种表象,而其实质则是两者在关键特征上的“同”。构式压制就是构式和组构成分在互动过程中显其同,隐其异,求大同,存小异。如果不能实现这样的显隐机制,就不能通过构式压制而生成合法的表达。
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构式和组构成分合力作用的语言层面。近年来界面(interface,或曰接口)研究成为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而引发构式压制的语言现象大多属于不同语言层面的界面/接口现象。论元增容和论元减容现象就是句法和语义的界面现象,“副+名”现象则是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界面现象,“关严·实窗户”涉及韵律、句法乃至语音层面,而儿化往往涉及音系和形态、语义、语用的相互作用。对界面问题的重视成为新的语言学理论的生长点。如韵律语言学(韵律词法学和韵律句法学)就是近年来界面研究的重要收获,如果依照主流语言学的分析路径,其中涉及的很多现象都可以看作存在构式压制的情况。由此可见,构式压制现象是探索界面/接口问题的一个重要而又便捷的窗口。对构式压制中界面现象的研究,有可能引导我们构造新的理论框架,而这需要对合力机制的系统分析。
四、构式压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就上文的分析而言,构式压制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尚未被充分关注或激活的功能,从而拓展既有能力的适用空间。它像一架探测器,探测组构成分的适应能力;又像一台挖掘机,挖掘构式的拓展空间。因此,对构式压制过程中双向互动的合力机制的认识可以深化我们对语言交际中可能性和现实性关系的认识。这里我们继续使用“招聘”和“求职”这两个隐喻来说明问题。
从“招聘”这一视角来看,构式压制更多地体现为以常规现象、核心现象为参照,为组构成分进入构式提供了准入的条件;而从“求职”这一视角来看,构式压制更多地体现为实现“超常”组合的现实性。有效的特征核查则化可能为现实。
就构式压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而言,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构式压制现象的出现既受到特定交际场景的制约,又受到既有特定语言系统的制约。组构成分的可塑性,是在既有系统中成形、在交际中塑身的。例如:
(9)枇杷具四时之气:秋结菩蕾,冬花,春实,夏熟。才熟后,又结菩蕾。(南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四)
就做谓语的能力而言,动词性成分“结菩蕾”实现的是常规用法,而名词“花、实”经过压制进入到该构式之中。当然,这些名词之所以能够进入与其自身的特征有关,它们在情境中能够激活其概念结构中隐含着的概念内容“开(花)”和“结(实)”。而且,在当时的语言系统中,实体成分表达事件性内容(表现为语言形式就是NP代表VP)虽较先秦时期有所降低,但仍有相当的可能性(据此,“秋结菩蕾”说成“秋菩蕾”也未尝不可)。在现代汉语系统中,这种可能性则大大降低,因为现代汉语系统已经是一种动词型语言(刘丹青,2011),而先秦汉语虽未必是充分的名词型语言,但名词的活跃能力远比现代汉语强,《朱子语类》时期则仍在转变的过程中。因此,构式压制现象是历时过程中的共时表现。
构式压制现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还体现出语言系统的类型特征。现代英语句法系统中,sneeze之所以能进入使移构式之中,首先与使移结构所提供的形义关系有关。使移构式的基本概念结构是:使因事件使某个对象产生某种结果。其基本语义内容是:X CAUSES Y to MOVE Z(Goldberg,1995:3);基本句法配置是:X V-ed Y PP,其中Y 既是 X 的受事 /役事,也是PP的位移主体。例(1)典型地例示了其中的形义关系。然而,在现代英语句法系统中,当sneeze可以代表整个使因事件时,便同样可以进入这一构式,但调整了Y与X之间的语义关系(两者之间不再出现于同一个动词的论元结构中),其基本语义内容是:“He sneezed”caused“the napkin”move“off the table”,从而被包装进入“X V-ed Y PP”的结构中,形成例(2)这样的表达。显然,这样的构式压制是在现代英语系统之中实现的。
认识构式压制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还可以从该机制所产生的效应来考虑。构式压制的结果有两种。一是“压服”,组构成分临时性进入,实现的是临时工的角色,离开构式后自身并未发生改变,如“很中国”的“中国”。二是“压成”,在构式压制的作用下,组构成分的语义/功能、句法、音系最终发生了变化,临时工变成正式工,如“很科学、很规则”中的“科学、规则”就成了兼类词,形容词用法也成了它们的常规功能。⑨而这些不同结果的出现,往往也与组构成分自身的潜质有很大关系,只有与构式形义关系契合度高的成分才更容易被压制出新的身份。这便是内因的主体作用。没有这些内因,怎么压也压不成;内因不充分,压制过程中的难度就比较大。压制通过转喻手段就是凸显(profiling)和消显(deprofiling)、增加和裁剪这些认知过程协同作用的结果(De Swart,1998;Michaelis,2003a;Ziegeler,2007;许萌、王文斌,2011),而非简单地施压、压迫。其实,在某个具体的构式压制之前,某个组构成分所具有的特征只是隐而不显罢了,实际上它是早已存在的或在语境中能够有效建构起来的。⑩例如某些名词所具有的描述性特征,并非只有在副名组合中才能呈现出来。以“平民”为例,以词法形式对描述性语义特征的显现方式如“名词 +‘主义’”(平民主义)、“名词 +‘气 /味’”(平民气)、“名词 +‘化’”(平民化)、“名词+‘式’”(平民式)等;以句法形式对描述性语义特征的显现方式如“‘越来越’+名词”(越来越平民)、“‘比’+ 名词 +‘还 /更’”+“名词(比平民还平民)”、“‘像’+ 名词 +‘一样’+形容词”(像平民一样朴实)、“名词 +‘了’”(都平民了,还摆什么贵族的架子)、“X+‘(不)是’+名词”(他又不是平民,凭什么也来领救济)、“名词+‘似的/一般’”(平民似的、平民一般)、同语式(平民是平民,贵族是贵族)等。(施春宏,2001)其中有些现象就被一般研究看作构式压制现象,如“‘比’+名词+‘还/更’+名词”和“名词+‘了’”等。因此,一个组构成分是否进入某个特定的构式中,其可能性受到构式和自身条件的制约,其现实性则是在具体交际场景中的实现。压制都是压制那些表面上冲突,实际上关键之处相一致的对象,如果真正地发生冲突,谁还能成功地压制谁?
五、余论:边缘现象的理论中心化和构式崇拜问题
构式语法的兴起源于对非常规现象、边缘现象的重视,或者说是将非常规现象、边缘现象由理论体系的边缘拉到了理论体系的核心,认为它们和常规现象、核心现象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试图通过对非常规现象、边缘现象的说明来对整个语言做出全面的说明。构式语法对“构式”内涵的重新定位正是这种观念的体现。这是语言研究观念的重大调整。对构式压制现象的分析推动了构式语法这种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借助于“招聘”和“求职”这两个隐喻来说明构式及其组构成分的整合过程,同时认为它们在本质上跟生成语法对句子生成过程的认识比较一致。构式向语言系统中所有成员开放,但不是所有成员都能进入其中,只有通过构式特征核查的成分才能获准入内;而具体成分实际上具有很多组构能力,常常能够满足多种构式的特征核查,只不过在特征核查过程中,有的特征不能直接地完全吻合,因此需要借助凸显和压制机制,在“招聘”和“求职”的互动过程中经过磨合而实现构式及其组构成分的融合。构式压制现象为语言交际提供了丰富而复杂的语言成分及其关系,对构式压制现象的分析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语言学价值,这种认识从一个新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课题,调整了很多新认识,引发了很多新思考。
然而,当前的构式语法研究有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就是似乎出现了“构式崇拜”,认为所有的语言问题都是构式问题,构式理论能解释所有现象,所有的其他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构式理论也都能解决,构式语法几乎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语法理论。(施春宏,2013b)这种认识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终极真理”观。且不说这种认识的逻辑困境和现实偏离,仅就研究的本身而言,有不少构式语法研究其实只是将球踢到了构式的框中,贴标签、换马甲的现象特别普遍。很多构式压制分析只是指出了某个特殊现象是不是存在构式压制,而对其“招聘”的要求和“求职”的素质、对构式压制的概念基础及其配位限制并未作深入的挖掘。这是构式压制研究乃至构式语法研究都必须重视的地方。
另外,现有的构式压制观一直强调对立、冲突,然而我们觉得构式压制成功的真正动力来自于构式整体形义关系和组构成分形义关系的有机契合,在凸显和抑制、增强和减弱的过程中实现了构式和组构成分的整合。基于此,构式压制甚至可以不叫“构式压制”,干脆叫“构式整合”。当然,作为界面现象/接口问题,构式压制的动因和机制则是特别值得关注、值得特别关注的语言现象,尚需我们做出系统的本体论研究和方法论归纳。
注 释
①实际上,新被字式“被”后成分是个极其开放的类,如可以是数字等形式(“教育部称67%公众赞成汉字调整网友调侃被67%”)。这与新被字式的生成机制有关。具体分析参见施春宏(2013a)。
②关于语言现象的语言价值和语言学价值,施春宏(2010b)曾通过对网络语言现象的分析对此做了初步的探讨。语言价值关涉语言生活为作为交际系统的语言提供特定的语言成分,形成特定的结构关系,实现特定的功能;语言学价值关涉语言生活、语言现象启发、推动人们做出有意义的语言学概括。
③学界对构式压制的一般理解,参见施春宏(2012)的概括,这里只列出几则主要文献中的说明。
④根据构式语法对构式内涵的经典理解(如Goldberg1995、2003、2006),可以将构式理解为形义关系的特定结合体,这样,从语素,到词,到短语,到句子,直至篇章,甚至语体、文体,都可以看作构式。由于语素以及某些单语素构成的词没有一般理解中的“构”(结构),因此Goldberg后来又将构式限定于有结构的语言单位了(Goldberg,2009)。
⑤陆俭明(2010)以积极修辞中的比喻和消极修辞中的句式选择为例提出并说明“语义和谐律”是修辞的基础,同时指出“语义和谐律”在修辞层面具体如何体现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就构式压制理论所分析的基本现象来看,也许它是探索其中机制的一条重要途径。
⑥为说明问题的方便,下面对构式的理解基本上按常规认识来理解,暂不考虑“纯”形式构式。
⑦就我们对范畴化的原型效应的认知而言,运用这个概念还是有些便捷之处的,它揭示了非常规现象、边缘现象的生成和拓展的过程和机制。
⑧正如德国谚语所说:“任何比喻都是跛脚的。”用隐喻的方式来说明问题,只能就其所关联的成分和关系而言,而不涉及喻体的其他方面做无限拓展,如偶然因素(如招聘者那天的心情)、意外情况造成招聘—求职成功或失败的情况。这里是用常规的“招聘—求职”框架来做隐喻性理解。
⑨例(2)中的sneeze,一般认为是临时的压服,但有人指出,它的及物用法已经规约化了(陈和敏,2011)。若此,则已经经历了从压服到压成的过程。
⑩如果基于我们上文对使移构式语义结构关系的分析,sneeze在例(2)中的用法没有发生转喻,不存在凸显和消显之类的识解过程,因此本质上并不属于构式压制现象,而是使移结构的一种例示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