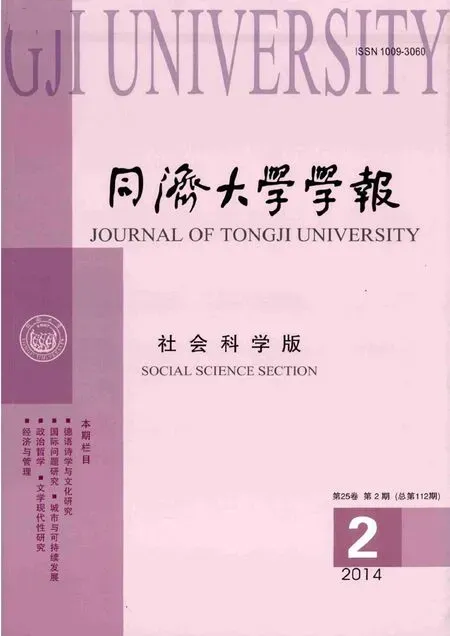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与社会融合
胡晓江,南 方,郭元凯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100875)
一、提出研究问题
2013年11月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查”数据①该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中国城镇化调研数据。该调查报告的部分内容载于《大流动的社会:农民工融入城镇社会的困境》,凤凰网2013年11月15日发布,链接地址为:http://politics.gmw.cn/2013-11/15/content_9502613.htm,2014年1月22日访问。显示,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流动打工主体,超过九成的80后农民工不打算回乡就业,而是倾向于选择大中型城市定居。这个庞大群体在社会融合中面临的挑战,直接影响着他们城市化的步伐。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受外部和自身多重因素的影响。从城市环境看,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由此衍生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等,均阻碍了他们的社会融合。[1-2]从农民工自身来看,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特征,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等人力资本,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和留城意愿等社会资本,以及他们的日常办事能力和休闲娱乐方式等文化资本均会影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3-5]
无论是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角度还是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来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资本”视角决定了研究重点是已经拥有的、可以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的个体资源,换言之,“资本”体现了农民工在不同维度上与社会互动的效果。然而,对于农民工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所依赖的基础技能和社会动机,无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或是文化资本的视角都无法系统地描述。因此,尽管诸多研究发现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融合有重要影响[6],但对于如何提升农民工的人力和社会等资本,除了认为应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投入和创造更适合于他们融合的社会环境外,并未提出更具体的干预措施。
从社会能力的视角来看,个人与社会互动的效果,以及在互动过程中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技能、社交地位和社会关系均是一个人“社会能力”(social competence)的外在表现。[7]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过程正是其个人与城市社会互动的过程,社会融合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功能性结果。
有一些国内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部分能力对其社会融合的结果产生了影响,比如工作技能水平、工作搜寻能力、适应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确实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进程中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8]这些发现为我们以社会能力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提供了启发。但国内目前并未有研究深入讨论社会能力的体系,也缺乏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现状的研究。在社会能力与社会融合的相关关系分析上,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有专门研究以外[8],对其他方面能力与社会融合关系的研究少之又少。
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其职业发展的早期,这一时期正是他们逐步认同新的职业身份、适应城市生活、模仿城市生活范式、为未来社会融合打基础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能力培养对未来的社会融合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首先尝试描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基本状况,通过对社会能力与社会融合的相关性分析,识别出对社会融合有积极促进作用的社会能力。这一研究发现将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技术培训和社区服务在内容设计上提供更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建议,从“赋能”新生代农民工的角度,为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合做出贡献。本文所探讨的基于发展心理学的社会能力框架,也可以为社会融合提供新的跨学科视角。
二、文献综述
1.社会能力的理论框架
对社会能力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属于研究儿童及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程度、衡量社会互动有效性的发展心理学领域。近年来,国内儿童发展心理学领域也兴起了针对社会能力的研究。在大多数研究中,社会能力的核心内容均被定义为社会互动的效果[7][9],然而不同的研究对社会能力的指标和内涵又有不同的界定,其中有三类研究取向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一是通过考察个人的技能和行为来研究其社 会 能 力 的 社 会 技 能 取 向 (social skills approach)。这类研究认为社会能力是一整套适当的技能 和 行 为[10-11],Aderson 和 Messick 归 纳 出包括社交、意识、情感、认知取向以及自我归属感等共29种指标[12]。这一研究方法能够快速识别出那些对社会互动有促进作用的技能和行为,并能为下一步评估和干预社会能力提供指南。[7]这一研究路径最大的挑战便是该研究方法并未提供识别这些行为和技能的理论体系,从而导致指标选取上的不一致。另外,这一研究路径过于关注个人行为和技能本身,可能会忽视个人所处的环境对能力的影响。[13]
二是通过考查同伴之间的社交地位研究社会能力的取向(peer status approaches)。[14]这种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同伴对与研究对象互动效果的评价,进而发现行为对社会能力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的优势在于,同伴关系与当下和未来的社会地位均有相关关系,因此对于社会能力的效果有比较好的预测性。[15]该方法可以很好地识别哪些社会能力不足,但是无法解释这些社会能力缺乏的缘由[14],也无法为提升社会能力提出有效的干预方案[13]。
三是通过行为的功能性结果来研究社会能力的结果取向(functional approach)。那些达成个人的社会目标、获得良好发展结果的个体被认为是有社会能力的。如Ford和Chen等认为,社会能力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通过恰当的方式,实现社会目标并产生对个体发展有积极意义的结果的能力。[16-17]国内研究者张晓等也认为社会能力是“个体恰当、适宜地应对社会情境、实现社会目标的能力,常被作为衡量个体发展的重要指标”。[18]结果取向用于解释社会能力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对于某些行为社会效果成败的判断,缺乏统一的方法论和相对清晰的标准。[7]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不同流派的争鸣,McFall提出了一个综合维度的定义:社会能力是指“对个体在某一情境下的行为进行的有效性判断”[19],这一概念既包括个体在情境下的行为结果(他人对行为有效性的判断),又包括实现有效性的前提条件(行为技能),同时还将情境变量加入概念中。[20]
Rose-Krasnor基于综合维度取向,搭建了社会能力“金字塔模型”(图1)。[7]在“金字塔”的顶端,是社会能力研究的指导理论,指明了社会能力并非单一的指标或某几个技能,而是受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处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以及系统行为的社会效果。因此,社会能力有一整套结构,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与特定的社会目的相关。“金字塔”的中部是社会能力的一系列指标,具体包括自我和他人两个领域,这代表了从自我和他人两种角度来看待个体行为的有效性。在自我方面包括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等,在他人方面包括友谊质量、同伴地位、社会支持系统等。
“金字塔”的基础,则是一系列社会技能和行为动机,以实现中间层指标。这一层面的社会技能包括表达和沟通、同理心、情感自我调节、应对挑战以及换位思考等。

图1 社会能力“金字塔模型”① 该模型的英文原版出自 Rose-Krasnor L.,“The Nature of Social Competence:A Theoretical Review,”in:Social Development,1997(6),pp.111-135.中文翻译版转引自张静、田录梅、张文新:《社会能力:概念分析与模型建构》,载《心理科学进展》,2012年第12期,第1991-2000页。
2.本文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社会能力“金字塔模型”建构的立体路径,为研究社会能力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具体的分析框架。基于“金字塔模型”的理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则具体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环境中,伴随着认同职业身份、适应城市生活、寻求个人发展的过程,所使用的一系列社会技能以及这些行为的社会效果。本研究关注的社会融合状况,可以看成是这一系列社会技能与外界环境互动的社会效果,因而无法在同一个量表中既描述技能和行为本身又衡量这些技能和行为的效果。因此,本研究将使用“金字塔模型”的社会技能层面为理论框架(图2),进行研究设计。

图2 本文建构的理论框架
参照Aderson和Messick开发的包括自我意识、主观能动性、照顾自己的习惯、自我价值感、人际交往中的觉察能力、与他人建立积极关系的意愿、使用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控制、好奇心、学习意愿、灵活地获取信息、语言能力以及常识等社会能力指标[12],本研究设计了一个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量表。为更好地帮助研究对象理解这些指标,将量表的问题转化为“为人处世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学习新东西的能力”、“城市生活的能力”、“表达和沟通能力”、“心理素质”。
Aderson和Messick的指标体系是为衡量儿童的社会能力而开发,用来衡量已经进入职业阶段的青少年时,有必要加上就业有关的社会能力。本文参考了Ronald等人提出的“广义就业能力”(a broad model of employability),该框架的个人就业能力维度不但包含了上述的基本社会能力,也涵盖了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和工作经验以及社交网络等指标[21],这些指标在量表中被表达为“工作有关的专业技能”、“行业知识”、“人脉”。Ronald特别强调了基本读写和计算能力、面试时的表达能力的作用,因此量表也采取了这些指标,表达为“基础文化知识”、“法律知识”、“普通话”。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社会融合问题研究”。该数据为横截面数据,通过2012-2013年在河南、安徽、福建、广东和江苏五省对4588名80后农村户籍的新生代农民工开展的调查问卷获取。

表1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N=4588)
2.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状况。国内学界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研究集中在对社会融合理论和维度的讨论,以及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现状的描述和影响分析上。“社会融合”被认为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22]在这个过程中,新移民在居住、就业、价值观念等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融入城市社会、向城市居民转变,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减。[3][23]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研究均认识到社会融合的多重维度,并进行了丰富的理论探索,梳理了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重社会融合维度[5][23-25],但多位国际和国内学者都意识到,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维度存在着一定的递进关系,特别强调社会融合始于经济融合,经过文化接纳和行为适应,最终达到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26-28]本文将社区融合和心理融合作为因变量,重点分析社会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社区融合和心理融合的影响,同时将经济层面的融合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
社区和社会关系融合主要通过“认识社区很多居民”、“和邻居经常来往”、“会为邻居主动提供帮助”、“帮助过其他居民”、“我的孩子和本地孩子一起玩”以及“我的父母与社区里其他老人一起聊天”6个题目组成的5点里克特社区融合量表进行测量,量表内容包括从“非常符合”(1)至“非常不符合”(5),得分越低说明社区融合状况越好。
心理融合主要包括归属感和社会距离2个指标。本研究借鉴Bollen和Holy提出的主观社会融合量表(perceived cohesion scale)来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融合[29],共有6项题目。每个题目都采用5点里克特量表,从“完全同意”(1)到“完全不同意”(5),得分越低说明心理融合程度越高。社会距离是由7个题目组成的5点里克特量表构成的。这是一个逆向计分的题目,得分越低说明社会距离越大,在使用时进行了反向计分。
我们将社区和社会关系融合量表得分,以及归属感和社会距离量表得分相加取均值,作为一个连续变量代入模型。
(2)自变量
课题组在开展大规模问卷调研之前,曾在浙江、江苏和福建等地进行前期调研,与新生代农民工就这些能力进行讨论和澄清,最终在问卷中设计了一个由12个题目组成的5点里克特社会能力量表,从“很好”(5)至“很差”(1),得分越高说明该能力越强。表2显示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的基本特征,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与社会交往相关的能力评价普遍比较低,仅有“法律知识”整体得分值达到“一般”,而其他各项能力均自认为“不太好”,特别是“生活自理能力”很差。法律知识好于其他能力,说明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非常关注法律知识的普及,而且已经表现出了效果。

表2 新生代农民工自评社会能力量表得分
在对社会能力自评量表进行Bartlett球形检验后,发现量表很适合做因素分析(表3)。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素时限定特征根大于1者,采用最大变异法来进行正交转轴,经过反复比较,萃取了对总变异解释率最高的3个因素(解释率达到71.107%),将其作为社会能力的3个维度,即职业发展能力、城市适应能力和常识了解能力(表4)。

表3 KMO值及Bartlett检验结果

表4 转轴后因子负荷矩阵
经过因素分析后发现,生活自理能力、城市生活的能力、心理素质、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为人处世的能力与表达和沟通能力可被划分为一组,我们将这组命名为“城市适应能力”;行业知识、工作有关的专业技能和人脉划分为一组,命名为“职业发展能力”;法律知识、基础文化知识和普通话划分为一组,命名为“常识了解能力”。
(3)控制变量
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水平以及是否有子女在已往研究中已被证明对农民工社会融合有显著的影响[2][3][5][30],因此本研究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代入模型。另外,如前文所述,本文还将职业阶层、居住类型和社会保险等经济融合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代入模型,以控制社会融合不同维度间接影响的混杂因素。
在模型中,主要选取职业阶层、住房类型和社会保险3个指标进行测量。职业阶层的赋值方法为:普通员工1分,技术工人2分,自雇及其他3分,管理人员(包括基层和中高层管理人员)4分。住房类型主要是指在务工地是否已经有了自己的房产。在赋值中,“居住在自己或父母的房子”赋值1,其他情况赋值0;社会保险主要是指在务工地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情况,如果三种都参加则赋值3,参加其中两种赋值2,参加其中一种赋值1,都没参加的赋值0。
3.研究假设
基于前文所述,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个体间在社会融合上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生代农民工策略性运用各种社会技能与城市环境互动的结果。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为:社会能力与社会融合呈正相关关系,即社会能力越强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社会融合状况越好。具体来讲,根据自变量选择情况(见变量测量部分),上述假设包括如下三个分假设:
(1)城市适应能力越强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社会融合状况越好;
(2)职业发展能力越强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社会融合状况越好;
(3)常识了解能力越强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社会融合状况越好。
上述假设关系,如图3所示:

图3 研究假设
四、数据分析和结果
根据上文的研究设计及思路,我们首先建立了社会能力与社会融合之间的关系,来探寻社会能力对社会融合的影响程度。

表5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能力与社会融合的相关分析
从表5中可以看出,社会能力与社会融合之间具有显著性相关。其中职业发展能力与社会融合的相关度最大,相关系数为0.241,其次是城市适应能力、常识了解能力。整体的社会能力与社会融合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64,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越强,该群体的社会融合情况越好。
为了进一步厘清社会能力中哪种因素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最大,我们采用OLS回归分析方法,考察社会能力的不同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情况以及经济融合等控制变量后,将前面因子分析后形成的三个能力因子即城市适应能力、职业发展能力、常识了解能力依次放入到模型之中,来探寻三者对社会融合的贡献率,得出了最终模型,表6呈现了这四个模型的数据摘要。

表6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与社会能力回归模型摘要

续表6
模型1中放入了主要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有无子女、年龄、住房类型、职业阶层、社会保险;模型2增加了职业发展能力变量;模型3则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城市适应能力变量;模型4加入了常识了解能力变量。所有模型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随着变量的增加,模型的调整拟合优度也在增长。
模型1显示,有无子女、性别、住房类型、职业阶层、社会保险等对社会融合均有显著影响,这与前述文献研究的结果一致。年龄和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影响不显著,这与其他研究发现的未婚农民工比已婚农民工留城意愿更加明显这一结论[31]不符。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我们的样本大部分是22至30岁之间的农民工,他们大部分没有结婚,数据差异性不大。
在住房类型上,拥有自己房产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没有房产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情况要好。也就是说,在流入地是否拥有自己的住房对社会融合具有正向影响。拥有较多的社会保险项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社会保险项目是一种制度化背后的社会福利,拥有越多的社会保险项目,也就意味着自己今后的生活有了更好的保障,在这座城市就有了立足的基础。从职业阶层来看,阶层越高,社会融合情况越好。这可能是因为职业阶层较高的人在工作条件、社会交往机会等方面存在着优势,更容易适应城市的要求,可以更好地融入城市。这验证了刘传江等人提出的观点:“农民工的劳动强度越大,该群体可能越不愿留在城市,社会融合情况越差”[32],也证明了经济层面的社会融合对最终的心理融合有重要的影响。
在增加职业发展能力变量之后,相比模型1,模型2的拟合优度增益了83%,解释力大幅提升至12%,说明职业发展能力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在模型2中,职业阶层对社会融合的影响力开始下降,也意味着职业发展能力与其所处的职业阶层有相关性。
模型3中加入了城市适应能力,模型的拟合优度增益为6%,解释力进一步提升,模型结果显示了城市适应能力与社会融合显著相关,职业阶层变量的影响力进一步减弱。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常识了解能力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增益为2%,模型的解释力略有提升。加入常识了解能力变量后,职业阶层已经没有了显著性影响,这也进一步说明,社会能力与其所处的职业阶层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性。
五、讨论与思考
上述模型分析结果验证了我们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设,城市适应能力、职业发展能力以及常识了解能力均与社会融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社会能力越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状况越好。
本研究发现,工作有关的技能、行业知识和人脉等职业发展技能不但能帮助农民工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这些技能也是实现职业阶层上升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稳定的工作和更高的职业阶层,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扎根的前提条件。这一发现更进一步证明,社会融合的不同维度之间存在递进关系,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融合会显著影响社区融合和心理融合。
城市适应能力则更直接地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进展和质量。良好的为人处世和表达、沟通能力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建立稳定的社交网络、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有重要作用,学习能力和城市生活的能力则帮助他们更快地适应城市文化。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生活自理能力,会让他们更积极乐观地面对城市生活压力和困难。这些技能的恰当使用,会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质量,进而增强他们的社会融合程度。
常识了解能力,包括普通话、基础的法律和文化知识等,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外界环境互动时的背景知识体系,会在他们找寻工作、面试、交朋友等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对于常识的判断和掌握,也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对于和自己有关的事件的反应和态度。比如当他们的劳动权益受到伤害时,他们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知道可能获得帮助的渠道,用比较清晰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处境和观点,这些能力均对他们克服社会融合的不利因素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然而,从本研究呈现的数据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各项社会能力偏低,几乎都在一般水平以下,这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很差。应试教育强调文化知识和考试成绩而忽视对综合素质的培养,对于人力资源的片面追逐,使得各级政府和职业教育学校更重视学历、证书和那些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技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学习社会能力的机会。然而,从社会能力的视角反观则发现,社会能力包含的技能和动机,往往是获得人力资本的基础,而这些至关重要的技能,却无法从目前的正式教育系统里获取,需要通过与家庭和周围人的互动来体验。而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都曾经是留守儿童的经历,使得他们也缺乏从父母和家庭成员之间习得这些能力的机会。
另外,本研究使用的社会能力量表为自评量表,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能力的评价如此之低,也表现出他们偏低的自我效能感。低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他们对自己未来发展的打算,也会降低他们与周围环境互动时的期待,进而会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带来消极的影响。[33]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建议在职业教育阶段和农民工在职培训中,充分重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能力,专门设计出符合青少年心理发育阶段的能力提升课程,重点对他们的社会交往、表达沟通、换位思考、解决问题、积极乐观等能力进行培养和支持,通过改善他们的社会能力来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合效果。
最后,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能力仅从社会技能层面进行探讨,而更为系统的社会能力指标体系还有待深化与完善;其次,研究发现,职业阶层对社会融合的影响随着社会能力变量的加入而不再显著,说明职业阶层与社会能力存在相关关系,限于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并未对这一发现进行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值得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