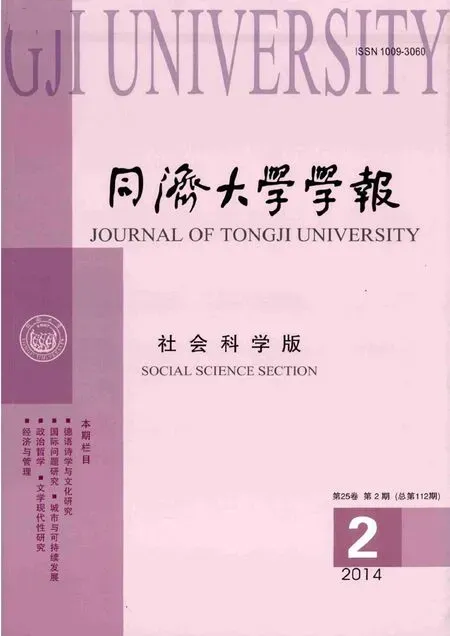论约翰·阿什贝里诗歌创作中的后现代诗学风格
汪小玲
(上海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部,上海200083)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评论家、纽约派重要诗人约翰·阿什贝里(John Ashbery,1927-)早年即在诗歌、绘画、音乐等方面彰显天赋。1956年,诗集《一些树》(Some Trees)的出版奠定了他在美国诗歌界的地位,1975年出版的《凸镜中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荣 获全国图书奖、普利策奖以及全国图书评论奖。2001年,阿什贝里被命名为“纽约州诗人”,以此表彰他对美国尤其对纽约诗坛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和持久的影响力。当他同时期的纽约派核心诗人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1926-1966)、詹姆斯·舒亦勒(James Schuyler,1923-1991)等都已作古,阿什贝里却还是“先锋”,成为英语诗歌的中心人物和其他诗人纷纷效尤的对象。如今,阿什贝里已成为全球英语诗歌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后现代诗学风格,强调中心意义的消解以及对传统技法的分离,重视诗歌创作的实验性,在荒诞不经的表象下形成了内在的和谐与契合,呈现出另类的诗学美感。研究表明,阿什贝里的诗是他玄思状态下意识的自由流动,其后现代诗学理念与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中心消解与诗意悬置;消解逻辑因果关系;强调诗歌的即兴式写作。本文旨在通过对阿什贝里诗作的文本解读与研究,从三个层面揭示阿什贝里诗歌创作的特色,论证诗人在创新求变的诗歌实践中所构建的后现代诗学观以及由此而取得的杰出诗歌艺术成就。
一、中心消解与诗意悬置
中心消解是阿什贝里诗歌作品彰显后现代风格的重要特征之一。“它趋向一种多元开放、玩世不恭、暂定、离散、不确定的形式,一种反讽和断片的话语,一种匮乏和破碎的‘苍白意识形态’。”①蒋孔阳、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1页。所谓“苍白的意识形态”指的就是中心意义的消解。它打破了美与丑、文学与非文学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从而给实验与创新留下了巨大的空间。阿什贝里显然把握了这样的诗学理念并将之化作自己的创作风格,从实验性的模仿走向富有独创性的诗歌艺术之路。
阿什贝里早期诗歌鲜明的实验效果代表了纽约派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纽约派诗人们并没有制定任何共同的纲领或行为准则,也没有公开发表什么宣言以昭告天下。他们是一群志趣相投、目标相近的实验主义者”①唐根金:《20世纪美国诗歌大观》,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3页。。现代主义作家否定了上帝及客观规律的存在,宣称“上帝死了”。②叶秀山:《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3-170页。后现代诗人则更推进一步:不仅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主体也死了,一切都被消解了③曾艳兵:《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7页。。这正是阿什贝里诗作所体现的实质内容,它打破了权利话语的结构,是对当时统治美国诗坛的“新象征主义”诗派所框定的文雅、高贵、理性等正统规范的修正。阿什贝里诗学理论中的“主体的破碎”,即那些看似源于诗人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回顾,却在每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被分解得支离破碎,与纽约派鼎盛时期的20世纪中叶普遍认同的宏大叙述已是不可为的想法不谋而合。宏大叙述本意是一种“完整的叙事”,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过分追求历史规律,忽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述的摒弃以及主张的“碎片化”趋势,就是中心意义的消解与诗意的多维性和不确定性。在《什么是诗》(What Is Poetry)中,阿什贝里写道:
设法避开思想,就如同这首诗?
但我们回归它们,像回到妻子身边,
而将热望的情人留在一边?
……
在学校里,所有的想法都被梳理而出,
留下的如同一片苍茫大地。
闭上眼睛,你能感觉它遥遥数里。④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9页。
在诗的开篇,阿什贝里就刻意强调诗歌创作就是要“设法避开思想”。在学校里,我们被灌输了许许多多的观点,被旧有的意识形态所束缚,所以冲破所谓“思想”的羁绊,获得意识的自由驰骋、无拘无束,方才是诗歌创作的本质。在阿什贝里看来,在诗歌中要想找到诗人所表达思想的意图是虚妄荒唐的,诗歌创作重在过程而非作品自身,也许找到的是“妻子”,失去的却是心中念念不忘的“情人”。诗人运笔时记录的是大脑中的种种思绪,而并非一定要予人以教义或深刻的思想意义。学校教会我们认识世界的能力,然而,这种能力实在有限,我们往往看出了小小的局部,却遗漏了整个苍茫大地,我们又何处去寻找所谓的中心思想、理论、观点?对此,我们往往相距甚远,遥不可及。诗歌很难说在表现什么,打动人心的有时是纯净如水的文字,有时是引人入胜的意境,有时是音乐般铿锵悦耳的旋律。既然连思想也谈不上,又何来中心意义,因此中心消解在所难免。它消解了一点,却使得诗歌走向了朦胧多维、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赋予诗歌更广阔的创作领域。
一首诗没有了人们普遍认同的主题思想,它的意义也就很难界定了。因此,中心消解必然会导致诗意悬置的现象,它们相辅相成,将诗歌引向多极化,这便是阿什贝里又一重要的后现代诗学理念。诚如美国后现代文艺理论家威廉·斯潘诺斯所言,后现代主义“摧毁了封闭性”,它消解了任何已成定局而朝“未然”敞开,它旨在通过语言而揭示人的存在之维,并“在读者和文本间激起无止境的对话”⑤[美]斯潘诺斯:《结构与后现代文学问题:走向一种定义》,载《平等关系》,1979年第2期,第115页。。因此,诗意悬置于不确定性打破了现代主义的僵化、封闭、窒息人性、遮蔽存在的状况而朝开放、多元、敞亮存在的方向迈进。在这方面阿什贝里堪称表率。他的诗往往在诗意悬置的状况下触动人心,在诗意的不确定性中制造出缤纷而又迷离的特殊感受,如《一些钱》(Some Money):
我说我是笨拙的。
我说我们愚弄了我们的生活
为了一点小钱和一件外套。
大树,一旦长成。即告消失。
我说你可以赶上所有古怪的活动。
这时候孩子在干扰你。
你从未被要求和狗一起回来
钓鱼竿斜靠在台阶上。
为什么所有的窗户都黑了?
为什么月桂在天空中燃烧它烟一般的形象?
女王的客厅里一切都金光闪闪。①[美]约翰·阿什贝里:《约翰·阿什贝里诗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
在该诗的上半段中,诗人呈现给读者的是一连串相互之间没有关联、杂乱无章甚至有些怪异的事物名称。按照正常的思维方式,一点小钱、一件外套、孩子、狗、钓鱼竿、窗户、月桂、女王的客厅,似乎没有任何的联系,将它们作为意象并置在一起似乎也无多大意义。然而,它们给读者所造成的视觉、感官上的冲击力却不可小觑。无论是迎风招展的大树还是恋家的小狗,无论是烟笼寒月的景致还是富丽堂皇的皇宫,都给予读者连绵的思绪与想象。诗意悬置是该诗最明显的特征,它所造成的开放性使得多种阐释成为可能:一个笨拙的人会把大家的生活弄得一团糟,我们不正是为了一点小事情,如一点钱、一件外套常常闹得不可开交吗?大树成才了恰好是被人看中和伐倒之时;你可以依着自己的兴致参加各种派对,可如有了孩子,这些都免谈。你和狗一样的来去自由;你钓鱼归来,斜靠在台阶上的钓竿和你一样的惬意。可转瞬间,窗外风云突变,窗户黑漆漆的,就连原本皎洁的月亮也被云烟笼罩,燃烧着冒出黑色的雾气。一切好似被黑暗吞噬,只有女王的客厅依旧金光闪闪,绚丽无比。当然,我们还会有其他多种释意,但真正重要的是诗人在记载其大脑中真实思想时所带给我们的触动与震撼。诗句中,静态的事物与动态的天空风云巨变互为铺垫;色彩的变更,如洁白的月亮、黑色的烟雾以及金色的大厅给予读者视觉的冲击与享受,所有这一切均赋予诗歌自身的“内在性”。它不再对精神、真理、美善之类超越价值的事物感兴趣;它诱使读者在琐碎的环境里沉醉于形而下的卑微愉悦之中。因此,这首看似“心猿意马”、不知所云的小诗却颇具张力、活力与创造力,成为阿什贝里最具诗意悬置的代表诗作之一。
综上所说,阿什贝里诗歌创作中所呈现的中心消解与诗意悬置的现象充分彰显其后现代诗学风格,同时也表明后现代诗歌的主体性随着中心意义的消解与诗意的不确定性而零散成碎片,形成多元性与开放性。正如诗人所言:“诗的意思就是诗行上写的话,以及某一片段内含的任何东西,但没有观点。我没有想要告诉世界的特别的东西,诗中仅仅是我写作时的所思所想。”②李顺春:《美国现代诗歌鉴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165页。这样的所思所想大大拓展了一首诗所能涵盖的时间与空间,赋予诗歌作品多维的朦胧性和内在意蕴。
二、逻辑消解
既然中心消解、诗意悬置,那么诗歌必然会呈现零散化与非逻辑化。因此,阿什贝里后现代诗学的另一原则便是在诗歌创作中继消解中心后又进而摒弃了诗意中的逻辑性,导致了诗歌写作中的逻辑消解。后现代诗歌“远不是‘整体性’的,而是紧张的、破碎的、与自身分裂的”③Ian Gregson,Contemporary Poetry and Postmodernism,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6,p209.。昔日以诗人为中心的视点已被打破,诗歌创作成了一堆破碎的东西,碎片与碎片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对此,阿什贝里大胆打破传统的标点符号和语法定规,运用一些具有分离性的句法和大量的散文化长句。他还从音乐、绘画、戏剧、电影等其他门类的艺术中汲取灵感与技法,将不和谐音、杂乱无章的节奏、通感、蒙太奇等引入诗句中,产生支离破碎、不合逻辑但却缤纷迷离的效应。他的最负盛名的代表诗作——《凸镜中的自画像》便是这一诗学风格的集中体现。
全诗长达552行,分六个诗节表达了相互联系又循环往复的主题:艺术总是歪曲事实。因此,阿什贝里在揭示艺术荒诞性的同时首先消解的是诗歌创作的逻辑性,因为无论是在绘画中还是在诗歌中,真正完整地反映现实始终难上加难。恰如凸镜中的自画像是被扭曲的一样,诗歌内容也往往似是而非,不合逻辑:
如帕明吉尼亚所做的,右手
比头还大,插向观察者
并轻松地偏斜,仿佛要去保护
它宣告的一切。①译文见http://www.douban.com/note/38019939/.
显然,人的手不可能比头大,画家夸张的笔法自然是对观察者视觉与判断力的挑战,而它要去保护的无非就是被视觉歪曲却又像手一样真实存在的事物。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手与头孰大孰小,从而认为凸镜里的画像是荒诞不经的,所以诗歌艺术本身就缺失寻常意义上的逻辑性。
虽然不合情理,但被扭曲的自画像在程度上却更具有真实性,更接近人之灵魂深处的本真,因为只有灵魂了解被曲解背后的原因。在此,因果关系显然被颠倒了,诗意中逻辑的消解也就意味着其因果关系也不复存在:
灵魂不得不停在它的所在之处,
即使不安地,倾听着窗上的雨滴,
被风鞭打的秋叶的叹息,
渴望,外面的自由,它也必须
在这儿摆着姿势。它必须尽可能少地
移动。这就是自画像所讲的。
然而在那凝视中混合了
敏感,愉悦和懊悔,在它的克制中
那么有力,以致一个人不能看得过久。②② 译文见http://www.douban.com/note/38019939/.
诗人分明在告诉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事物往往是表面的、肤浅的,而灵魂则不然。灵魂是有感知的,叹息、渴望、敏感、愉悦、懊悔不一而足。但灵魂又是晦涩深奥的,它深藏不露,与表征相互作用。人对于现实的认知好似锯齿形的碎片,世界存在多种表现手法,现实不只有一个版本,且一切都在变化发展,即使是最强有力的现实也有可能会被不加验证地忽视。因此,阿什贝里抛弃了传统诗人对现实强调的理性要求,认识到镜子的虚幻性和现实的不可捉摸性,进而彻底否定了诗歌作品中的因果关系,产生了一种疏离感,从而对现实存在的真实表达性与如何表达疑虑重重:
弗朗西斯科,你的手大得足以
毁坏这球,太大了,
一个人会想到,挥舞柔软的网
只是主张它更长地拖延。
(大,却并不粗糙,在另一种尺度中
几乎像海底一条假寐的鲸
和水面自大的小船
相关联。)可你的眼睛宣告
一切都是表象。表象是那里的一切
除了那里的一切其他都不存在。③③ 译文见http://www.douban.com/note/38019939/.
人的手不可能大得如同一张网、一条假寐的鲸,可见表象终究不是事实本身,可表象却围绕在我们的周围。所以,诗人最后想传达给读者的信息是艺术歪曲现实是一种惯例,人们对艺术的追求是无望的,现实是不可能被准确完整地表现出来的,现实的组成部分只是偶然的片段的发生。因此,根本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和因果联系。
阿什贝里在消解诗歌创作中的逻辑、因果关系后转而将创作的重心引向诗歌自身的技巧,这也是后现代诗人惯常的做法,因此,《凸镜中的自画像》的极大成功还缘于阿什贝里精湛的语言艺术。缺少逻辑关联的枝节、转移、分岔、异域语境和标点符号的任意应用证明,如表现主义者宣称绘画应该表现抽象和平实一样,诗歌也应如此。因此,后现代诗歌鼓励解读的多种可能性,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效果和其构成的富有魅力的形象,呈现后现代主义多元化的特征,从而将对语言的认识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如果说现代主义是以“自我”为中心,后现代主义则是以“语言”为中心,“谁拥有了语言,谁就‘拥有’世界”④[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88页。。后现代诗人创作的意图不是表现世界,也不是抒发内心情感,揭示内心世界的隐秘,而是要用语言来制造一个新的世界,从而极大地淡化甚至消解了诗歌反映生活、描绘现实的基本功能,所以作品内涵中自然也就缺失了逻辑因果的联系。
总之,《凸镜中的自画像》将后现代主义诗歌的零散化与非逻辑化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是对尼采“世界是我的表象,世界的本质是非理性的意志,真正的艺术必须摒弃理性”①曾艳兵:《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9页。之观点诗意的解读与印证,并最终使得文字游戏、“无聊话”、非逻辑性的表达都变成了后现代诗歌。这些诗歌“把对生活的阐释转化为语言,语言又转化为生活”,因此虽然他的诗里缺少寻常的情节和传达体验的一致性、逻辑性,但即使是最挑剔的评论家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诗句常常出奇制胜”②张子清:《二十世纪美国诗歌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59页。,这也是阿什贝里后现代诗学的特色与内涵。
三、即兴写作
即兴写作是阿什贝里后现代诗学风格的又一呈现,也是彰显中心消解、诗意悬置和逻辑消解最佳的表现手法,它使得诗歌创作走向了真正的自由与不羁。后现代诗学观认为,创作要追随多变的想象力的流动,在没有预定设想的情况下自发地随机运笔,即强调一种偶然的、随意的发挥和行动。阿什贝里的创作往往不分时间和场合,笔随心想、天马行空多属于即兴而为的率性之作。他喜欢将产生创作激情的环境和自己的心理活动直接写入诗中,写作时有人打扰,他会把这一特定的场景、场景下的对话甚至只言片语融入自己的诗歌创作,正如诗人所说:“我最好的作品是在我被别人打扰了的时候写出来的,人们给我打电话或是让我完成必需的差事的时候。就我的情况而言,那些事情似乎有助于创造过程。”③王家新:《二十世纪外国诗人如是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56页。如此的形式自由、主题松散的即兴写作给人的感受首先体现出意象飘忽、跳跃、断裂、含混和不完整的诗歌内在表征。如《一些钱》的后半首:
而在外面的猪圈里仍是冬天
一阵接一阵的头痛
通向被摧毁的灌木
上面钉着一顶毡帽
更靠近你的形象,什么感觉。
狗们准时到来不是为了幸运。
龙虾叫喊那是多久之前
没有比这更大的钢笔了,对象说
仿佛好躲开一步
在狭窄的走廊里亲吻我的心肝
在它之前是战争年代,寒冷终止在
那个音符上。④[美]约翰·阿什贝里:《约翰·阿什贝里诗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8页。
显然,所截取的诗行是诗人在玄思状态下的率性之作。不以为然的评论者认为,这些即兴而为的诗句都是连篇累牍的废话;认同者则认为阿什贝里擅长于从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去探求原始的或是高尚的意义。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大家一致认可的,那就是阿什贝里即兴创作的诗往往曲高和寡,对读者要求很高。仔细研读,我们会发现,跳跃和断裂充斥在字里行间:从猪一跃而至狗再到龙虾;从头痛至灌木上的毡帽再到硕大的钢笔;从冬天一跃而至寒冷的战争年代,其间的不连贯以及彻底的断裂一目了然。这样的跳跃和断裂自然就构成了诗歌内容的含混和不完整,如龙虾怎可发出叫喊、谁在狭窄的过道里亲吻我的心肝?抑或这些都是暗喻,是飘忽的意象?虽然在结尾处诗人刻意强调“寒冷终止在那个音符上”,可整首诗依旧没有完整和戛然而止的感觉,读者也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解读这样的实验性的诗作:一个曾在残酷的战争中受过伤的老兵,在隆冬时节旧伤复发,头痛难耐,于是,他回想起曾经伏击守候的灌木丛,想起阔野中狂吠的犬,想起戴着毡帽的生死与共的亲密的战友。记忆是深埋在心之深处的蓓蕾,她绽放在人的脑海,比再大的钢笔也要管用,因此,她所带来的温情融化了冬日的冰雪,使寒冷在回忆的旋律中烟消云散。当然,十个读者就可以有十种解读,使得这首看似不经意间创作的小诗极具张力和多维朦胧的指向,其开放性与互动性无疑给当时过分强调理性与高雅、墨守成规、脱离大众的美国诗坛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也使诗歌艺术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
阿什贝里即兴写作之现实意义还表现在他大胆突破传统的尺度,强调世间万物皆可入诗的新理念。他用现代口语叙述,不押韵,好似随口交谈,打破了诗歌语言和非诗歌语言的界限,还诗歌一个更为辽阔的新天地。许多在普通人脑海里一闪而过的事物、人物,到了他的笔下,就变成了自然流泻、颇具诗情画意的美妙的诗行,如他的名篇《一些树》(Some Trees):
这真令人惊讶的每一棵树
都与另一棵相连,像言语
行为静止不变。
纯属偶然。①李顺春:《美国现代诗歌鉴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164、165页。
诗人以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树木为主题,却在告诉我们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树树相连,以沉默为语言,然则彼此相通,互相守候,人与人如此该是多么的美妙。于是,徜徉在树木丛中的诗人又写道:
这个清晨我们相遇
远离尘世,仿佛
心有灵犀,你和我
突然成了这些树想
告诉我们的那样:
它们彼此相连
蕴含深意;不久
我们也能相交相知相怜。②李顺春:《美国现代诗歌鉴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164、165页。
树分明以榜样的姿态教导人类也要彼此珍惜血肉相连的缘分,如果诗意往下延伸不啻是自然美好的,这正是传统诗人所津津乐道的,然而,阿什贝里笔锋一转,却又说:
所幸的是我们并未创造出
这样的场合,我们周围是:
一片充满喧嚣的宁静,
画布上呈现
一个个微笑,一个冬日的清晨。
在令人目眩的光线中,晃动,
我们的日子看似如此的缄默。
这些似乎就是它们的自我防线。③李顺春:《美国现代诗歌鉴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164、165页。
在一片充盈着喧嚣的宁静中,微笑和冬日的清晨在炫目的光线中被定格在画布上。这幅油画是把握整个诗境的“指南”。在油画上,有树与树之间无言的沟通,有树给予你我的启迪;有沉默,有喧嚣,有行动,有感动;又或者什么都没有,一切只是好像、似乎;一切都是作者的想象而非真正看到,听到的——当然,即使看到听到的也未必是真。一切都在画布上,又都在画之外。一切都在言语中,又都在不言之中。抽象与具象结合,不同的语言和思绪交替,句法上与主题上的逻辑发展缺失,前后出现明显的断层,诗意倒置,诗歌陷入模糊晦涩中。于是,我们彼此并不相连,我们用日复一日的缄默来铸就自我的防线,在互相伤害的严酷社会现实里祈求安宁。这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写照,这正是诗人汩汩流动的思绪想要告白于天下的。
由此可见,阿什贝里即兴写作的创作风格与技法充分体现出他对诗歌艺术的经验和审美等玄思,只有拨开了诗人设置的重重迷雾,读者方能了解诗的内在意蕴,诗人在创作作品的同时也创造了读者。于是,“艺术与人生的关系已被艺术与它自身的技巧的关系所替代了”。④[英]阿兰·罗德威:《展望后现代主义》,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518页。阿什贝里刻意求新的精神不仅深化了诗歌创作的不确定性与随意性,而且打破了传统的规范,使诗歌走向多元化的发展轨迹。
综上所述,阿什贝里的诗歌创作充分彰显其自成体系的后现代诗学风格。通过中心消解与诗意悬置、通过消解逻辑因果关系与即兴写作等后现代诗歌理念与写作技法在其作品中的贯彻与运用,他在创作中摒弃“中心”,蔑视权威,解除了等级制度,让读者在互文性、相对性、流动性与创造性的过程中随遇而安。因此,读阿什贝里的诗,读者可以顺着读,倒着读,也可以在任意的地方开始读,从而产生了一种自适与愉悦,“保持一种嬉戏的多元角度,转换观众心中的意义场”⑤Ihab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Ea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Ohio: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p168.,如同其他纽约派代表诗人一样,阿什贝里的诗作打破了纽约派形成之前把持美国诗坛的“高贵”、“文雅”、“不触动理性誓不罢休”的诗歌传统,修正了由艾略特框定的所谓正统规范,将附庸风雅、严肃庄重、精英意识等僵化的教条加以消融,从而确立纽约派别样的诗学理念与风格。环顾整个美国诗坛,纽约派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余音未绝,可以说,没有纽约派的实验性创作和后现代诗学探索,就没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纽约诗坛的百花齐放,更不会有如今美国乃至全球后现代诗歌多元化蓬勃发展的新格局,对此,阿什贝里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