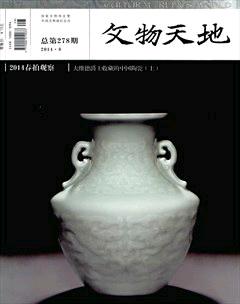人物画断想
赵晨


中国画史在晋唐以前,基本上是人物画的历史。但在晋唐以降,人物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至宋以后则全面退隐,让位给山水、花鸟画。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社会的全面下坡造成人的精神的隐退,即当对外在的反抗力不从心或经邦济世的前途渺茫时,人们转而追求内在的精神自由和人格完美,画者也就自然地“疏于人事”,将晋唐以来宏丽恣肆、华贵雍容的人物画让位给文静典雅、蕴藉恬淡的山水、花鸟画。另一方面,晋唐人物画的高度成熟,使后继的画家在宁述不创的继承中展示的只是“程式”所带来的样式,而非“程式”所产生的过程。因而,陈陈相依所带来的只是面目的概念化与雷同化。至此,疏略了“师造化”的传统内涵,人物画成了一个概念的样式和“不求形似”的墨戏了。
正如古人所言,“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人物画总离不开人的具体形象与具体造型,因而关注形象,关注人的存在成为人物画家的主要任务。至任伯年、徐悲鸿后,写实手段的融入和对社会人生的关注造成了人物画的空前发展,但“笔墨”这一抽象的审美概念被诉诸人物画后,却始终在艰难中行进。因为造型的规定,人物画家始终很难如山水、花鸟画家那样“出笔便如急管繁弦,声情并集”。笔墨语言的抽象性和提炼性使它无法也不会像西画那样去诠释一个直观的真实。它的抽象性体现为它不是如西画那样去表现一个明暗深浅、三维立体的直观的真实,而是在主观界定之后达到一个合理的逻辑的真实,它只是一个合理的抽象;它的提炼性体现为它需要我们用眼睛去想、去找,而不是直观地看和记录,它是一个由看到提炼的过程,由“看不见”到“看得见”的过程,尖头的毛笔不同于平头的油画刷,它高度的敏锐性使它更接近感觉,更靠近心灵。它需要在笔笔生发之际彻底地放松,将理性的判断让位给肌肉的记忆,而成竹在胸和高度熟练是它的保障。所谓“尽精微”是指处理的精微而不是描绘的精微,它往往是意会所带来的不尽之味。正所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
如上,迅速的造型能力和熟练的笔墨技术及二者的有机结合,都是一个人物画家所应具备的。而时下技术的磨练却被疏离,言必提“形似为末”或“气韵为先”,“道为上而技为下”,全不顾这其中的因果关系,“道”不过是“技”的高级显现,即使气格超逸也终是“技”的得心应手之后的相忘所致。而现代人物画需要近距离地表现与审视人与人的存在,因而“形”的问题自然成为了人物画的首要问题。古人所说的“形竞增而意竞生”或“真境逼而神境现”讲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