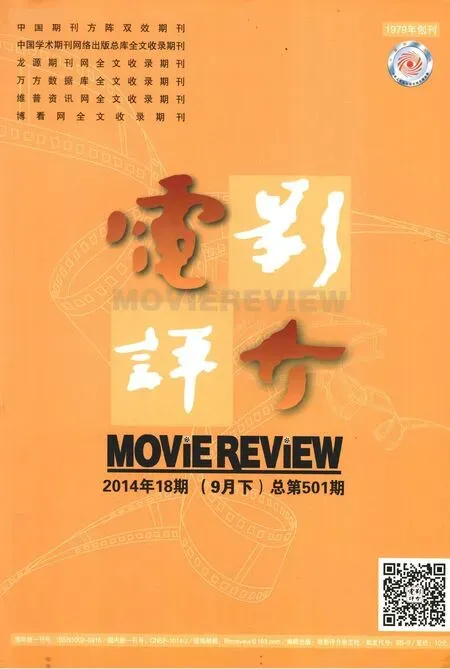《归来》:悲剧的反悲剧叙事
王 侠
凭借着与严歌苓合作的《金陵十三钗》的成功经验,张艺谋再度抽取了其小说《陆犯焉识》的片段,成功地将其搬上银幕。有了《我的父亲母亲》历史积淀,《山楂树之恋》的纯情捕捉,《归来》在对那段特定年代回瞻的视域中,完成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重述。“较之于现实的话语,历史的叙事始终丰满、凝重,充满了细腻的层次和无限繁复的情感。”[1]亲历反右派斗争、文革,且有着知青体验的张艺谋,似乎有着对那段历史难以拂去的梦魇,《活着》中对文革所造成的凤霞流血而死的惨烈呈现,《我的父亲母亲》中对父亲因右派身份出走对母亲所造成伤害的展示,《山楂树之恋》中对生活在文革阴影下人物的生离死别的讲述,无不是酷烈跌宕的人生悲剧的复演。同样是对文革事件的复述,《归来》的经典之处在于它既没有呈现文革的苦痛岁月,也没有指向文革后陆冯夫妻二人的苦尽甘来的生活。而是以丈夫看着失忆的妻子等待自己作为影片叙事的机制,这样的处理方法,一方面有意于将人物与文革那段苦痛的岁月拉开距离,呈现出温情脉脉的生活细节,另一方面,他又不自已地将魔咒般缠绕在自己脑海中关于文革的记忆诉诸影片,在看似消解悲剧、消解文革的创伤记忆中又将人物推向了更深一层的悲剧中。
一、悲剧与反悲剧:悲剧的温情化表达
有人曾评论,《归来》是反思文革的“伤痕”电影的“归来”[2],也有人评论“《归来》不控诉、不撕裂,温情回归。”[3]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但又不完全正确,“伤痕”与“温情”不是对立的矛盾体,而是此消彼长,显性与隐性的关系。影片以一种温情化的方式,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痛人生轻描淡写,着意于展示温馨浪漫的诗意化场景。
影片故事的真正展开是文革后,摘掉了右派帽子陆焉识的归来,实体归来,丈夫的身份却没有归来,妻子冯婉瑜的期盼也没有归来,但他以极大的耐心和包容心使得文革浓重的阴影淡化。归来后,本该是笑脸相迎的妻子,对他却投以木然、冷冰的神情,为了找回妻子曾有的记忆,他想尽各种办法,再次从火车站走出,到朋友家寻找他的照片,修琴、弹琴、将未寄出的信重新翻出来,读给妻子听,当他所作的这些努力都白费时,他黯然伤神,“真成了那个念信的了”的身份让他几近绝望,女儿的一句话提醒了他“想了那么多办法,不就是为了接近她能照顾她吗?”于是他不再想着怎么找回自己的存在,而是想方设法接近妻子,以“念信同志”的身份照顾妻子的生活,也照顾妻子反复无常的记忆。这是在承认悲剧的立场上对悲剧进行反抗,是在以退为进。在文革时期的折磨和囚禁中,对归来的盼望,对无可抗拒的灾难的接受和承认,在悲剧中寻找点滴安慰已经成了陆焉识度过灾难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这在陆焉识给妻子念的信中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念信在影片中不仅成为陆焉识接近妻子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且也是影片对他在文革期间生存状态的一种巧妙回视,这些信件显示了他在困境中充满希望与喜悦的精神状态,在曾经本该给妻子也给自己的安慰中再次找到了缓解现实残酷的止痛片。始终怀揣着美好的希望,始终不向悲剧低头,但由于悲剧命运似的无可抗拒,所以又只能在承认和接纳悲剧现实的前提下,与悲剧进行迂回战术,甚至试图爱上悲剧本身,让这种极无奈极可悲的爱内化为一种心理习惯,使悲剧可爱起来,温情起来。
陆焉识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痛丝毫不亚于妻子,但是文革的阴影却让妻子精神恍惚,造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记忆缺失。这种阴影在陆焉识身上却没有丝毫的表现,作为一个男人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担当使得他不仅值得妻子去爱、女儿去爱,也值得让曾经是帮凶的居委会去爱。他身上所显示的人性魅力和无私精神轻易就驱散了文革的阴影,轻易就抹去了女儿的罪过,然后一步步照亮妻子被浓重阴影遮蔽的心灵,即使不能打开她的记忆之门,也能够透过这扇门所有的细小孔隙,装点她的心房。
影片中最温情的一幕体现在陆焉识为冯婉瑜弹钢琴的那段情节。在陆焉识抚摸久违的琴键、重弹过往的幸福生活之时,冯婉瑜也在琴声中渐渐找到了记忆迷雾覆盖的回归之路。陆焉识借着琴声所扇起的驱雾的清风,在妻子面前伸出一只指引的手,妻子也若有所悟似的牵住了这只手,接受着小心翼翼的牵引。正在大功将要告成之时,幸福的眼泪同时从重逢的夫妻眼中流溢出来,可能几乎所有观众都会误以为陆焉识真的归来了。但是很快冯婉瑜的眼神又开始迷茫起来,疯魔似的退回到凌晨的迷雾和昨夜的阴影中,继续着对5号的等待。这一道立即被掐灭的转机之光,使得悲剧的温情达到了近乎诗意的程度,转瞬即逝的希望带来了恒久的寻找最终幸福的动力。
二、等待与反等待:迎接幸福的逃避性策略
影片取名为“归来”,其着眼点不在“归来”上,而在对“归来”的等待上,“等待归来”因此成为影片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在张艺谋的电影中,一直有着等待、归来的主题,也有着等待后的喜悦与等待后的绝望二者悖论的情况,《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对父亲数年的等待,换来的是“从那以后,父亲再也没离开过母亲半步”的幸福人生,而《山楂树之恋》中静秋对老三的期盼,最终却以老三生命垂危的方式重逢,宣告了等待的虚无与绝望。到了《归来》这里,张艺谋将等待的幸福与等待的虚无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不同于《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每天在那条路上对父亲的翘首期盼,也不同于《山楂树之恋》中最后已逝的老三对静秋乌托邦式的告慰:“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了,我不能等你到25岁了,但我会等你一辈子。”《归来》中的冯婉瑜的等待显得荒诞滑稽,因为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回来了,可是冯婉瑜却因为患上“心因性失忆”症,记忆的时针永远停留在了4号和5号之间。
冯婉瑜一方面渴望丈夫归来,这是她生活的唯一动力,一方面又害怕丈夫归来,因为失贞。影片中一直未露面却如影随形的方师傅,是她的另一个男人。从陆焉识给她盖被子,她惊恐地叫起来“方师傅,你不能再这样了”,以及丹丹说见过方师傅用饭勺打过母亲的头,两个情节就能看出来,方师傅与冯婉瑜的不正当关系维持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而方师傅之所以能长期霸占冯婉瑜,也是因为他手中握有的迫害陆焉识的权力。但是由于他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丈夫的缺位,不能不说冯婉瑜也在某种程度上接纳了他,尽管这种接纳是极为屈辱的。冯婉瑜的失忆症就是在这样巨大的撕裂和矛盾中造成的,爱与恨、期盼与害怕让这样一个贤妻良母的精神世界崩塌了。一方面,等待丈夫归来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化,甚至成为生活本身,她做的任何事情、忍受的所有屈辱都是为了丈夫能够归来、夫妻能够团聚。另一方面,她为了丈夫归来甚至出卖了妻子的贞操,同时就失去了做妻子的权力,导致了身份的迷失。这种困局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的心理负荷,导致了“心因性失忆”。所以她才会屡次错把丈夫当成方师傅,只有把他推出去冯婉瑜才能继续等待丈夫,同时推迟了丈夫归来的进程,也造成了已经归来的陆焉识丈夫身份的丢失。这样就使得等待本身成为了最坦然和最幸福的事情,这是一种追求幸福的逃避性策略。
陆焉识正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才拼命要唤醒妻子刻意埋葬的记忆。在弹奏钢琴的情节里,唤醒妻子记忆的努力眼看就要大功告成,如果不是冯婉瑜潜意识中对丈夫真正归来的恐惧和拒斥,陆焉识是完全能够实现丈夫身份的复归的。接着陆焉识又想到了念信的妙招,才获得了长期登门拜访的资格。弹琴所带来的震撼是冯婉瑜不能接受的,因为这琴声在她记忆中是真实存在的;而念信所带来的慰藉正是她所需要的,因为这些信件从来没有寄出过,不在她的记忆之内,它们所传达的正是她所不知道的远方丈夫的消息,得到一种隔着时间和空间的幻想的满足感。
而从陆焉识这方面来说,他不断充当着“念信同志”的角色,不断在“5号”早晨陪着妻子到火车站等候自己身份的归来,因为意识到妻子心灵的创伤永远不能治愈,记忆永远不能被唤醒,他也只有凭借远方的另外一个虚拟的自己给妻子幸福,进而从妻子那里获得幸福。这无疑也是一种追求幸福的逃避性策略。等待和归来在冯婉瑜的潜意识里、在陆焉识的意识里都已经被虚置,成为一种象征,其根源乃在于尽管妻子和丈夫的身份互相缺失,却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爱情维系其中,让双方相濡以沫、相扶到老。
三、觉醒与反觉醒: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丧失
文革十年动乱是一场大浩劫,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尤为严重。影片中陆焉识一家是个知识分子家庭,陆焉识是大学教授,懂法语、会弹琴,冯婉瑜也是中学教师。正是因为这种身份,陆焉识才被打成右派、流放到西北做苦力。那个反知识的时代以及陆焉识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是他们夫妻二人悲剧的源头。但是我们看影片中男女主人公没有说一句反思文革、控诉文革的话,他们只是默默地接受着审判、惩罚、折磨。因为冯婉瑜的不觉醒,才使得女儿丹丹深中文革之毒,只因为要抓住跳《红色娘子军》主角的机会,就轻而易举地出卖了父亲,成为扼杀父母爱情和家庭幸福的帮凶。后来丹丹一直为出卖父亲而愧疚不安,这种愧疚里恐怕还夹杂着当年虽然出卖父亲、依然未能出演主角的悔恨,如果当初丹丹因为“大义灭亲”而达到了目的,那么她对父母的愧疚恐怕也没有那么强烈。而尤为使人震惊的是,当丹丹终于鼓足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时,陆焉识竟然轻描淡写地就过去了。这固然可以表现陆的宽宏大量,但同时可见他对残害自己以及妻子的文革是非常麻木的。陆焉识一如冯婉瑜,只是希望家人能够早日团聚,他从西北牧场逃跑也只是为了见见妻子,而非忍受不了自己所遭受的压制和迫害。以此而言,陆焉识与妻子的知识分子身份并没有得到凸显,在他们身上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觉醒,如果把他们换成任何其他身份,对情节开展和主题表现也不会造成什么妨碍。
《山楂树之恋》中的主人公们也都是知识分子,但是文革时代背景的设置,却是产生并见证纯洁爱情的基本前提,使整部电影都吹着一股含有淡淡香味的小清新之风。里面每个主人公对文革都是默默接受的,默默服从的,从来就没有说过半个“不”字。甚至老三在谈到自己母亲的自杀时,也只是一笑而过而已。
文革可以在人性的慢慢流露中变得温情脉脉,社会和自然的大灾大难也可以在爱情亲情的娓娓道来中变得楚楚动人,甚至一切伤害、冤屈都可以经过时间的过滤只留下美好的成分。但是作为五四精神中觉醒的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在政治高压下选择沉默,是一种集体的有意识的反觉醒。他们都像患了冯婉瑜的“失忆症”一样,不再认识自己、家人甚至整个社会,他们缩回到一己的哀乐当中,只要夫妻能够团聚、父母能够健康、儿女能够平安,就是最大的福祉和慰藉,只要能像冯婉瑜一样轻轻松松地打开门迎接暴风骤雨中归来的丈夫就足够了。即使连这些基本愿望都实现不了,他们也可以像丹丹和静秋一样在舞台上唱着嘹亮的歌曲、跳着铿锵的舞步,赞美着压制和欺骗他们的时代。
结语
张艺谋在《归来》中采用的是一种悲剧的反悲剧叙事策略。通过陆焉识人格力量中的担当和包容,使我们看不到曾遭受过的迫害在他身上留下的创伤,只看到他作为丈夫拯救妻子、作为父亲原谅女儿,无论妻子有没有认出他,他本人的归来绝对是对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挽救,我们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了悲剧温情化的一面。人实体的归来与身份的无法归来,满含期待的等待与等待的自我消解架构起了这场悲剧,但是夫妻双双由真正归来一起退回到虚幻的等待中,用逃避现实的策略完成了对幸福的寻求,找到了一种新的扶持和默契,这又使得悲剧逆转为反悲剧。同时,知识分子本身的觉醒性和影片中知识分子家庭集体的反觉醒也使得影片在背景的构建上,呈现出悲剧的反悲剧效果,诚如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的那样:“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4]
[1]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18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310.
[2]李弢.归来!归来?归不来……[EB/OL].(2014-05-24)[2014-09-15]http://blog.sina.com.cn/s/blog_8f372bcd0101l2y4.html.
[3]郑娜.《归来》不控诉不撕裂,温情回归[EB/OL].(2014-05-23)[2014-09-15]http://www.ce.cn/culture/gd/201405/23/t20140523_2860962.shtml.
[4]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66.
——论严歌苓长篇小说《陆犯焉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