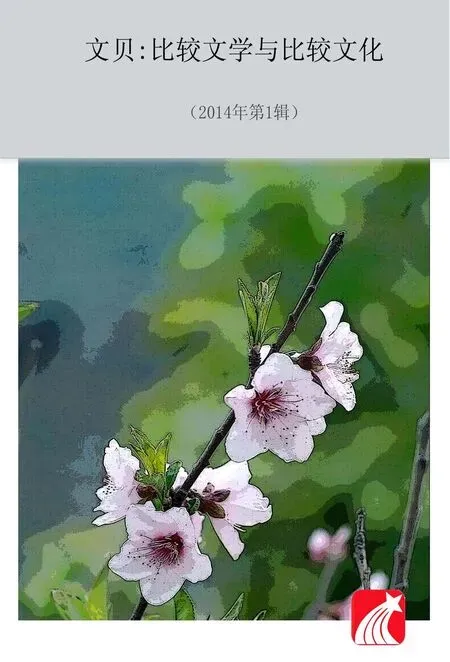从中国视角透视《树枝不会折断》中的意象呈现
闫 昱 刘 燕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作为20世纪50年代初出现的美国“深度意象派”(Deep Imagism/Deep Image School)的代表诗人之一,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1927—1980)以其简洁明快而意境深邃的抒情诗闻名诗坛。相对于以庞德(Ezra Pound)为代表的前期意象派和以艾略特(T.S.Eliot,1888—1965)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深度意象派”旨在“通过对无意识的开掘,使得想象的跳跃和比喻的转换成为可能,使意象从心灵深层跃起”,是“对50年代新批评派智性诗或新形式主义诗的一种逆反”。而这一后现代诗歌流派的出现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的影响不无关联。“深度意象派”的主将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认为“深层意象”的源头就是中国的道家美学,美国当代诗歌应以“道”为方向,才能达到“阴阳之平衡”;而赖特乃是“诗取道以求阴阳平衡”原则的杰出践行者。与布莱、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肯尼斯·雷克斯洛思(Kenneth Rexroth,自称“王红公”)等一样,赖特也是一位对中国文化和儒道思想极为推崇的诗人,他既喜欢陶渊明、王维的纵情山水,闲适恬静;也倾心于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的淡泊名利、坚韧超脱的精神,并在其诗歌书写中进行穿越古今、跨越中西的心灵对话。尤其是1963年出版的抒情诗集《树枝不会折断》(The
Branch
Will
Not Break
)奠定了赖特作为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诗人的基础,它与 W·S·默温(Merwin)、S·普拉斯(Sylvia Plath)以及 G·金内尔(Galway Kinnell)的诗作一起,标识着美国后现代诗歌朝着一种带有实验性质的自由诗的转变,“不像任何当时的美国诗”,是“赖特创作生涯的真正分水岭”。莱斯丽·厄尔曼则认为:“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Georg Trakl)的表现主义诗歌、中国古典诗歌和西班牙超现实主义诗歌是构成赖特这本诗集特点的三大来源。”本文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的视角透视《树枝不会折断》中的中国元素,考察赖特笔下的文化意象(中国诗人)、景物意象(树、月亮)、动物意象(昆虫、马、蝴蝶)与女性意象(水)的呈现方式及其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联之处,这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反思中国古典文学在跨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他者”之激发与启示意义。一、《树枝不会折断》中的文化意象
“意象”作为一个审美范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上溯到古代《周易·系辞》的“圣人立象以尽意”,古义是“表意之象”,是“指用来表达某种抽象的观念和哲理的艺术形象”。意象是一种蕴含了个人审美情趣和文化倾向的表现符号。美国理论家韦勒克、沃伦认为:“在心理学中,‘意象’一词意味着对过去的感觉或直觉经验的精神重现或回忆,而并不完全诉诸视觉。”也即,人物、动物、植物等视觉形象可以成为诗歌的主要意象,触觉、听觉、通感、回忆、无意识中的幻象同样也可以成为意象。20世纪初意象派诗歌运动的推动者庞德把“意象”定义为“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它的“呈现给人以突然解放的感觉: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的感觉,一种在我们在面对最伟大的艺术品时经受到的突然成长的感觉”。可见,如何选取“意象”,选取哪些“意象”以及用何种方式呈现不同语境中的意象,给读者以突然解放的自由感和顿悟,成为20世纪美国诗歌得以变革、创新的重要途径。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庞德在1915年发表了根据美国东方学者E·费诺罗萨(Eanest F.Fenolosa,1853—1908)的遗稿而整理的中国古诗英译本《华夏集》(Cathay
),收入了他翻译的李白、陶渊明、汉乐府等中国古诗19首。庞德善于领会中国古诗的精华,对汉语象形字、意象、含蓄、暗示、跳跃、浓缩、蒙太奇等艺术特征有独具匠心的把握,他用“化简诗学”(reductionist poetics)这个术语来概括中国古典诗歌的简约风格,即用“超越比喻的语言”(language beyond metaphor)而非各种比喻的修辞手法,直接、简朴地描写日常事物,写出现代诗人的现代感受和现代体验。以庞德的《地铁车站》为例,“第一次有意识地实验了句法单元上的并置结构(juxtaposition/parataxis)这种现代诗的重要的句式特征”。正如蒙罗所总结的:“中国诗那种新的表现法,那种出奇的现代性,使它们完全有资格在一本20世纪诗选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布莱、赖特为代表的深度意象派诗人们继承并发展了庞德所开拓的美国新诗的意象传统,但与其前辈美国诗人不同的是,他们对中国古诗和中国文化的汲取不再停留在追新逐异、形式变革和东方情调上,而是更深入地领悟了中国诗歌和中国文人所蕴含的精神境界,尤其是诗人的内在灵魂、精神品格、人生境界与中国文人息息相通。这一点在赖特的创作中尤为明显,以《绿色长城》(The
Green
Wall
,1957)、《圣犹大》(Saint
Judas
,1959)为代表的早期诗歌较为遵循传统英诗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恪守节奏、韵律、诗节和善用比喻的规律,语言密集,逻辑严谨,形式拘谨,笔调晦暗而沉重;而在这部赞美自然和生命的《树枝不会折断》中,赖特创造出了一种充满力度(power)和能量(energy)、更加透明(clarity)和凝练(terse)的意象语言(imagistic language)和随意开放的自由诗体(free verse),诗人追求幸福、安宁和心灵的慰藉,流露着积极乐观的情绪和宁静悠远的意境。毫无疑问,赖特在人生态度、精神向度和诗体风格方面的突然转变同他在20世纪60年代与布莱的相识相知密不可分。布莱是一位致力于延伸诗歌语言边界的诗人,为美国诗坛译介了西班牙、拉美诗歌和中国诗歌,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当代诗人通过对欧洲主流文学之外处于边缘、他者地位的诗歌范式的吸纳,突破传统英诗刻板的规则和过度高雅的主旨。布莱本人的创作“受益于中国诗,尤其是在景色中隐藏深远意境”。“他诗歌的力量完全建立在平凡环境里强烈的主观情绪上。”当赖特早期的创作模式走进死胡同并对人生感到绝望痛苦之际,是布莱引导他关注中国、西班牙、拉美、奥地利、北欧等国家的诗歌,深入了解王维、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等中国古诗和洛尔卡、聂鲁达、特拉克尔为代表的非英语诗歌传统,放弃过于理性的逻辑结构,追随一种自发性的、本能的、直觉性的思考方式和潜意识里自由涌现的深度意象。谈到布莱对自己的巨大影响,赖特满怀感激:“他让我明白了一点,并非只有一种那类试图让我掌握、带我走进死胡同的诗歌传统。他提醒我诗歌是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即使所有的诗歌都是有规范的,那么也有很多种规范,正如同感受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同样,理解赖特的文学知音也莫过于布莱本人,他在《詹姆斯·赖特的作品》(The
Work
of
James
Wright
)中评价其诗充满着一种“善待自我”(friendliness toward yourself)的感情,即无论情况多糟,总要抱有美好的愿景,关照自己,自珍自爱。布莱认为这才是伟大艺术中应该蕴含的基本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美国诗歌中罕见,因为美国人更善于自我怀疑,总是“以一种自怨自艾的敌对态度度过一生”(live all their lives with a vigorous hatred of themselves)。然而,赖特“在最好的中国诗歌中,几乎每一首诗里都有表现”。杜甫、白居易等中国诗人的形象开始出现在许多美国当代诗人的写作景观中,如王红公和布莱都很崇尚杜诗忧国忧民的仁爱情怀和“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态度。赖特在《在百货商店的收款窗口前》(Before a
Cashier's
Window
in
a
Department
Store
)的第四节引用了杜甫的乱世经历和诗歌意象:杜甫在一片战场中战栗着醒来
曾经,在万籁俱寂的夜晚,辨认
血肉模糊的女人们,清理
那憔悴的吊眼梢。
月亮升起来。
(笔者自译)
这节诗呼应了杜甫的名篇《北征》:“鸱鸮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杜甫描绘了沿途所见长年战乱导致民不聊生、触目惊心的现实,其中一次月下战场白骨遍布的恐怖景象令人毛骨悚然,锦绣田园已然变成鬼蜮世界。赖特在象征物欲、贪婪的收款窗口前,忍受饥饿与歧视。杜诗中战争摧毁了美好的生活,而赖特诗里繁华的商业都市也破坏了人与人的情感联系。赖特借杜甫忧生悲悯的感慨表达自己对现代文明的怀疑与痛斥。
不过,赖特最喜爱的中国诗人当属白居易。他对这位性情温和、风格朴素、接近大众的诗人充满崇敬之情,对他的身世和坎坷人生产生共鸣。《树枝不会折断》的第一首《冬末,越过泥潭,我想起了中国的一个地方官》(As I Step over A Puddle at the End of Winter,I Think of an Ancient Chinese Governor,以下简称《冬末》),正是赖特读了韦利(Arthur Waley)翻 译 的 白 居 易 《初 入 峡 有 感》(“Alarm at First Entering the Yangtze Gorges”)后有感而发。此诗“从白原诗的景色自然地转入美国的景色,然后是对中西古今诗人灵魂的回应”。白居易的原诗《初入峡有感》作于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记录了诗人改任忠州刺史,沿长江经三峡赴任的一路艰辛。在《冬末》一诗中,赖特站在波涛汹涌的密西西比河岸边,遥想古代中国的白居易沿江逆流而上赴任的情景,三峡的风貌和白居易的形象在诗人脑中浮现,他不禁对白居易仕途坎坷,忧心忧国、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无法实现的际遇境况发出喟叹,诉说衷肠:
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写于公元819年
白居易,两鬓稀疏的老政客,
有何用?
我想起你,
忐忑不安地进入长江三峡,
当你逆流而上
奔向忠州
赴任官职或是别的
你抵达时,我猜,
已暮色苍茫。
但现在是1960年,又是春色萌动,
明尼阿波利斯城的巨石
为我建造属于自己的沉沉暮色
在纤绳和激流之间。
元稹在哪里,你挚爱的好友?
那曾经解开中西部的全部寂寞的大海
在哪里?明尼阿波利斯又在哪里?我一无所见
除了那棵随冬而黑的可怕的大橡树。
你在山后找到孤独者的城市了吗?
还是你紧握着破败纤绳的一头
用了一千年?
(笔者自译)
And how can I,born in evil days
And fresh from failure,ask a kindness of Fate? ——Written A.D.819
Po ChuI,balding old politician,
What's the use?
I think of you,
Uneasily entering the gorges of the YangTze,
When you were being towed up the rapids
Toward some political job or other
In the city of Chungshou.
You made it,I guess,
By dark.
But in 1960,it is almost spring again,
And the tall rocks of Minneapolis
Build me my own black twilight
Of bamboo ropes and waters.
Where is Yuan Chen,the friend you loved?
Where is the sea,that once solved the whole loneliness
Of the Midwest?Where is Minneapolis?I can see nothing
But the great terrible oak tree darkening with winter.
Did you find the city of isolated men beyond mountains?
Or have you been holding the end of a frayed rope
For a thousand years?
这首诗的标题点名了主旨,以白居易诗句“况吾时与命,蹇舛不足恃”(韦利英译)作为题词,引入《初入峡有感》的语境。赖特描绘白发鬓鬓的白居易逆着激流奔波赴任,到达忠州时已是暮色苍茫,孤零寂寞。诗中问道:“你挚爱的好友元稹在哪里?”白居易曾写过多首思念元稹的诗,赖特对元稹与白居易之间的深厚友谊很熟悉。忠州乃山中蛮荒之地,孤独的白居易与元稹只有在梦中相见。白居易尚有挚友聊表慰藉,而诗人却一无所有。赖特把长江三峡湍急的激流与明尼阿波利斯市边奔腾的密西西比河并置在一起,古今对照。面对着命运多舛的前途,他求教于白居易,是否有一个收留孤独者的城市能给予他暂时的解脱;他似乎看见白居易如同逆水的纤夫一般,紧握着那条破败了的纤绳的一头,一千年都不曾放手。“纤绳”象征着诗人同现实生活的紧张联系,暗示着诗人在逆境中执著坚韧的精神。一个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诗人就是这样穿越时空和文化的距离,与9世纪初的中国诗人进行心灵对话,在绝望无助的困境中从中国古代诗人那里叩求“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信念。不难体会出,美国当代诗人的人文关怀与中国诗人所追求的“普通人性”深深契合,试图以中国式的“简朴的人性”对抗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对人心的侵扰与污染。
在诗歌手法上,赖特“不仅在自己的诗作中保留了东方古国的异国情调,还成功地运用了‘陌生化’技巧”。他把白居易原诗中的若干意象化用在诗中。如“the tall rocks”是“上有万仞山”的呈现;“Build me my own black twilight”和“But the great terrible oak tree darkening with winter”是对“未夜黑岩昏”的挪置;“bamboo ropes”、“a frayed rope”来源于原诗中的“竹篾”、“苒蒻”意象。诗人通过借用、改写白居易的诗歌意象和场景,展开了跨文化、跨时代、跨空间的心灵对话。比起庞德仅仅停留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改写与引用上,赖特在心灵上、意境上更接近中国古典诗歌的精髓,他没有停留在表面的形式与意象的借用等外在方面,而是在当下的困境中展开了中美诗人的心灵交流、叩问与解答。这使得他能够成为杜甫、白居易的异国知音,让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平原刮起了中国的汉唐风。
二、《树枝不会折断》中的景物意象
美国学者鲁宾(Larry Rubin)评价“赖特和三千年的中国诗歌一样拒绝‘去展示关联’”;“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所描述的事物赋予意义的工作,并且正在尝试只描绘事物本身,就像绘画艺术里的一种方式”。赖特继承了庞德开创的美国新诗传统,从汉诗中学到了远离传统英诗严格逻辑的自由跳跃的句法结构,尤其是的意象并置/叠加的蒙太奇手法。如《春天的意象》(Spring Images):
Two athletes
Are dancing in the cathedral
Of the wind.
A butterfly
lights on the branch
Of your green voice.
Small antelopes
Fall asleep in the ashes
Of the moon.
两个运动员
正跳舞在风的
教堂内。
一只蝴蝶
飞落在你绿色话声的
枝头上。
几匹小羚羊
熟睡在月亮的
灰烬里。
(张子清译)
此诗的三节是有关春天的三组意象的并置:“风的教堂”、“绿色话声的枝头”和“月亮的灰烬”。赖特展现了三个相继切换的画面;三组名词的并置结构冲淡了词与词、句与句之间的时间或因果关系,彼此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语词对应关系之上的和谐:相同的名词、对仗的句子、一致的内在结构。这首诗由最简洁的语言和意象构成,具有古典汉语那种经济和含混相结合的 “脱体性”(bodilessness)特点:“它既是简朴的又是复杂的;既是静态的又是动态的;既是时间性的又是空间性的;既是音乐性的又是雕塑式的。”在《春天的意象》中,诗人用气势宏大庄严的“教堂”描绘无所不在的无形的“风”,体现了空间性;用“绿色话声”形容绿意盎然的“枝头”,视觉与听觉相互转换;“月亮”之“灰烬”的形容,给意象注入了一种能量。此时,作为观察者的诗人完全隐退,而是让意象自身涌现,留下解释的空白,形成多义性与模糊性的开放式诗歌风格。这种以物观物、“意”在“象”中,且超出“象”外的呈现方式不涉及任何抽象概念,但却是最高意义的还原和敞开,趋近中国诗学主张的“得意忘言”之境界。但不同于中国古诗或者意象派所追求的客观意象,深度意象派诗人们笔下的意象更多受到无意识的引导,往往是源自非理性感觉的主观意象和自由联想。
中国山水田园诗对于风花雪月、树木河川等自然景观的细腻观察和情感寄托,引发了美国当代诗人们的热衷与契合。赖特不仅善于捕捉大自然景色中最有意义的细节,而且赋予自然景色以深层意识的暗示,从而唤起现代人超脱现实返回大自然的愿望。《树枝不会折断》的书名来源于其中的一首诗《两次宿醉》(Two Hangovers)中的最后一句“That the branch will not break”。在中国古诗中“树”往往象征着积极向上、坚忍顽强的生命力。赖特使用“树枝”这个自然意象,暗示了一种富有韧性的不屈不挠的人生信念:大自然永远是人类的精神支柱和艺术灵感的源泉。人也需要学习这种永不折断的“树枝”精神,经受人生的暴风雨和各种挫折,毫不妥协,傲立风霜。又如,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月亮”成就了中国千百年来无数的咏月佳作。赖特也是爱月爱夜之人,对于事物的阴柔、空旷、虚静之面尤其敏感。如《开始》(Beginning):
The moon drops one or two feathers into the field.
The dark wheat listens.
Be still.
Now.
There they are,the moon's young,trying
Their wings.
Between trees,a slender woman lifts up the lovely shadow
Of her face,and now she steps into the air,now she is gone
Wholly,into the air.
I stand alone by an elder tree,I do not dare breathe
Or move.
I listen.
The wheat leans back toward its own darkness,
And I lean toward mine.
月儿投到田里一两片羽毛。
黑森森的麦苗凝神谛听。
此时,
万籁无声。
那儿,月儿的幼雏正试
它们的羽翼。
林间,一位苗条的女子抬起她可爱的
面影,轻盈地步入空中,轻盈地升上去了。
我独自站在一株老树旁,不敢呼吸
也不敢动弹。
我屏息倾听。
麦苗向它自己的黑暗处倾身。
而我也倾身于我的黑暗之中。
(张子清译)
在万籁无声的夜晚,月亮竟然像鸟儿身上坠落的羽毛。这个比喻让静态的画面顿生动感;月光轻盈地飘逸四散,惹得麦苗“凝神谛听”。“Be still./Now”,语言简单之极,几近中国古诗的凝练与禅意。诗人发现月光下有“一位苗条的女子”好像梦境一般地轻盈地升入天空,这是诗人在无意识世界里出现的幻象。最后两句诗,麦苗倾入“自己的黑暗”,我也倾身于“我的黑暗”,“我”与自然各得其性、物我相忘。在此诗中,赖特把客观意象“月”与主观意象“羽毛”、“少女”关联起来,体现了深度意象派对于无意识幻象的挖掘和梦幻性,使得诗歌意象之间的跳跃性更为突兀。
月亮在大多数夜晚带给诗人安宁与恬静,但有时也带来愁绪与孤寂。在《1960年圣诞,失去儿子后的我面对月亮的残骸》(Having Lost My Sons,I Confront the Wreckage of the Moon:Christmas,1960)中正是如此,诗中的前两节这样描绘月亮:
After dark
Near the South Dakota border,
The moon is out hunting,everywhere,
Delivering fire,
And walking down hallways
Of a diamond.
Behind a tree,
It lights on the ruins Of a white city:
Frost,frost.
天黑后,
靠近南达科塔州边界的地方,
月亮正在四处狩猎,
承载着火,
从钻石的走廊上
走下来。
它在一棵树后,
照亮一座白色城市的
废墟上空:
霜,都是霜。
(笔者自译)
诗人把月亮比作狩猎者(hunting),在树后照耀着城市的废墟;而月“霜”(frost)的比喻令人联想到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在中国古诗中,冰霜既是险恶环境的象征,也暗示着人生易老和人生坎途。此诗中的月亮失去了往昔的宁静美好,失去爱子的诗人无法排解的伤悲在最后两节中愈显黯淡凄凉:
This cold winter
Moon spills the inhuman fire
Of jewels
Into my hands.
Dead riches,dead hands,the moon
Darkens,
And I am lost in the beautiful white ruins
Of America.
这个寒冷的冬天,
月亮溢出宝石的
残酷火焰,
落在我手中。
死去的财富,死去的双手,月亮
暗沉,
我迷失在美国
美丽的白色废墟中。
(笔者自译)
诗人笔下的月光是尖锐刺眼的“残酷火焰”,是“白色废墟”;城市如同被烈焰燃烧过后的灰烬,诗人迷失其中。虽说“千里共婵娟”,但受到各自文化传统和不同时代背景的影响,中西诗人笔下的月亮寓意相差甚大。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月亮”是细腻情感或感伤情绪的化身,常与江河、湖泊、花草等柔性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其情感表达含蓄而婉约,如《春江花月夜》中诗人描绘清幽的月夜,感叹人生无常却哀而不伤。但在希腊神话中,充满能量的太阳被誉为“阿波罗神”,与征服者有关;“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是其孪生妹妹,与“狩猎者”和庇护者相关;“月亮”意象往往与星辰、大海、天空等浩瀚壮观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如华兹华斯(W.Wordsworth)在《在坎伯兰海岸,面对海滨之月》(To the Moon Composed by the Seaside,— on the Coast of Cumberland)中把海上的月亮比作航海者的朋友,它统治夜空,是精神崇拜的象征。赖特在诗中把月亮比作轻盈的鸟儿,把月影比作燃烧后的灰烬,把月亮视为狩猎者;其笔下的月亮充满着动态感,承接了希腊文化的神话意味,是具有生命力的能量之源。由此亦可见中美诗歌内在深处的文化差异。
三、《树枝不会折断》中的动物意象
评论家彼得·施迪(Peter Stitt)认为《树枝不会折断》“这部诗集的主题正是探索和追求,赖特由城市转向乡村,由社会转向自然,由人类转向动物,由对死亡的恐惧到永恒的信仰”。不同于浪漫主义在描写自然时以“我”(人类)为中心的理想化与浪漫化,赖特往往从动物本身的换位视角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导致的对动物的杀戮与灭迹,体现了动物解放/动物权力的生态伦理思想。在《一本劣诗集令我沮丧,我走向一片未开垦的牧场,邀请昆虫来陪伴》(Depressed by a Book of Bad Poetry,I Walk toward an Unused Pasture and Invite the Insects to Join Me)里,赖特宁愿听着草蜢和蟋蟀的叫声,也不愿听蹩脚诗人的喧闹声。
释怀了,我把书丢在一块石头后面。
我爬上一个长满青草的小山岗。
我不愿打扰蚂蚁,
他们正一个一个地顺着篱笆柱子向上爬,
运送着白色的小花瓣,
留下了单薄的影子,几乎透明。
我闭了一会眼,聆听。
几只年老的蚱蜢
累了,使劲跳着,
它们的腿真是沉重。
我好想听听它们清亮的嗓音。
然后甜美悠远的歌声传来,一只黑色的蟋蟀
先开唱了,在枫树林里。
(笔者自译)
此诗以一个完整的陈述句作诗题。长题目在英文诗里并不多见,在中国古诗中却不足为奇。其句式往往包含了一个完整的信息,吸引读者一探究竟。在赖特看来,一本劣诗集很可能是那种模仿性的、了无新意的诗,而真正的诗人将它不屑地抛在一边,走向“长满青草的小山岗”,置身于昆虫之间。诗人对小昆虫的描写极具画面感:小蚂蚁运载着白色小花瓣,投下的影子虽然微弱,却充满生命力;蚱蜢上了年纪,疲倦吃力地跳着,不愿意低头认输;蟋蟀唱起歌,其天籁之音如庄子所言:“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法国生态伦理学家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指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包括那些从人的立场来看显得低级的生命也是如此。”赖特从世俗的烦闷中解脱出来,从小昆虫身上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与力量,在他眼中,一切生命都是神圣而值得赞美的。《祝福》(A Blessing)是诗人与马的对话,表达了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的平等、亲密关系:
就在通往明尼斯达罗彻斯特的高速路边,
暮色轻柔地在草地上向前跳。
两头印第安小马的眼睛,
乌黑又饱含善意。
他们高兴地走出柳树林
来欢迎我和我的朋友。
我们越过铁丝网进入牧场,
在那里两头小马吃了一天的草,好静寂,
他们紧张地颤动,抑制不住喜悦,
因为我们来了。
他们如湿漉漉的天鹅羞怯地低着头。彼此相爱。
……
突然我觉得
如果我能走出躯体,就会
如花盛开。
(笔者自译)
暮色笼罩下芳草萋萋的牧场和公路汽车填满的大都市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诗人在公路旁走下车问候草地上正凝望着他们的两匹小马,它们静寂地吃了一天草,终于看见了朋友,喜悦万分,宛如两只弄湿羽毛的天鹅。诗人眼中小马已经和人一样,感情充沛,温情脉脉。动物之间尚且“彼此相爱”,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更应多些关爱和信任。传统英诗主客界限分明,“我”常凌驾于客观对象之上,而中国古诗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经常模糊,在写景后往往以个人感受作结,追求天人合一、万物无差的境界。如李白《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人与山之间像朋友一般,主客一体,亲密无间。赖特这首诗的结尾句也是意味深长:“我突然觉得/如果我能走出躯体,就会/如花盛开”,这似乎与前面的描写没有关联,其实是主客体的融合。诗人在与马的密切交流中,感到自己和马一样,是大自然的一个生命,甚至可以像花儿一样,敞开胸怀自由绽放。在《恐惧给了我活力》(Fear is What Quickens Me)中,诗人甚至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受到捕杀而惊恐不安的动物,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恐惧感:
1.
在美洲被我们父辈杀害的许多动物
都有着敏捷的眼睛。
它们四处惊望,
当月色渐浓。
新月落入南方城市的
货场里,
月亮消失在芝加哥的黑手中;
对北方田野里的鹿来说,
不足为奇。
2.
那位高个女人在做什么
那儿,在树林中?
我能听见兔子和悲哀的鸽子窃窃私语
在幽暗的草丛,那儿
在树下。
3.
我环视四周。
(笔者自译)
诗中的父辈代表着捕杀动物的残酷历史。南方的田园风光不再,“月亮”成为市场上堆积的“货场”;北方的工业城市芝加哥烟囱冒出的滚滚黑烟好像黑手,侵蚀着原本美好的生态环境。小鹿知道自己终将和历史上被人类捕杀的动物一样,在劫难逃。第二节中的“高个女人”神秘莫测,最灵敏的野兔和鸽子窃窃私语,预示大难临头。第三节只有一行,“我环视四周”,这里的叙述者“我”是一只担惊受怕的小动物,以防受到人类的攻击。赖特试图让人体悟到动物对人的恐惧感,以此警告人们要以史为鉴,不再像祖辈那样捕杀动物,掠夺自然。毫无疑问,在赖特、施奈德等为代表的美国诗人身上体现的万物齐同、敬畏自然的生态意识与老庄的齐物论相呼应,或者说,中国古老的道家哲学与后现代的环保主义思想异曲同工,在人与万物可以相互转化的意识上尤为契合。蝴蝶是中国古诗中典型的意象,从庄周梦蝶开始,蝴蝶就像梦中的精灵,无拘无束,遁入大化,被赋予了自由、梦幻、虚境等象征意味。在《明尼苏达的松岛:躺在威廉·杜弗农场上的吊床上》(Lying in a Hammock at William Duffy's Farm in Pine Island,Minnesota)一诗中,赖特如此写道:
头上方,我看到古铜色的蝴蝶,
沉睡在黑色的树干上,
在绿荫中叶子般被风吹动。
山谷下,空屋后,
牛铃一声声
传进午后的深处。
我右边,
两株松树之间洒满阳光的地里,
去年的马粪堆
闪闪发光地变成了金黄的石头,
我仰身向后,当暝色四合,
一只雏鹰滑过,向家飞去。
我虚度了一生。
(张子清译)
诗中充满了道家式的空虚意象:沉睡的蝴蝶、空屋、牛铃,午后的深处,甚至诗人自己也悬在空中,清静无为。而在虚虚实实之中有着动静之分和远近之别。山谷、空屋、松树静寂地伫立着,牛铃回荡,以动衬静;蝴蝶的近景与松树的远景交错;变为“金黄的石头”的马粪享受自然的恩泽,又回馈自然;雏鹰在暮色中急速回家。这是一个人与自然、意义与物象自动涌现、圆融和谐、相互敞亮的神秘时刻。这种神秘体验在本质上是因坐忘而导致心斋的道家审美之境。不过,此诗的最后一句“我虚度了一生”显得非常突兀,这是赖特式的画龙点睛之笔,也是诗人对自己曾经与大自然处于隔离状态的一种反思与觉悟,好似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尾句。通过它来产生一种轻微的震惊,使读者在漫游诗人展示的神秘境界之余,获得一种若有所思的感觉。“当读这种诗时,我们好像被引到一个塔顶,通过一扇窗户,看见远处迷人的景色,吸引我们去思考它,但诗至此就结束了,却留下余音袅袅,久久使人不能忘怀。”
显而易见,赖特诗歌的写作方式与传统的英语诗歌相去甚远,也令不少西方读者迷惑而震惊。其实,如果我们从中国诗学的视角去解读他在诗歌中所追求的言简意赅、物我相忘、万物齐等、返璞归真,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形式与风格、主题与意境时,似乎更容易理解其创新之处。
四、《树枝不会折断》中的女性意象
道家始祖老子倡导“反者道之动”,大量使用了“柔”、“谷神”、“慈”、“玄牝”、“水”等词语揭示“道”之特质。阴柔的女性在其思想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以此矫正儒家之“阳”。同样,在赖特的诗中,女性是极为重要的意象之一,她轻盈飘逸,神秘莫测,往往与代表生命力之“水”意象和“夜晚”、“黑暗”等氛围关联在一起。在之前提及的《开始》(Beginning)一诗中,诗人描写了黑夜的林间“一位苗条的女子”,好似嫦娥一般轻轻地向月亮飞去。《庄子·外篇》有语:“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忘掉外物,忘掉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步入天空的少女形象成为诗人自在忘我、遨游天地的自由之象征。在《恐惧给了我活力》(Fear is What Quickens Me)中,一位出没于树林中的神秘“高个女人”(that tall woman)预知着动物们无处躲避的灾难的降临。而在《美国婚礼》(American Wedding)中,诗人描述了一位身心缺水的美国现代女性置身于现代荒原,垂死挣扎:
她梦见绵长的水域。
现实却是内陆,她醒来
带着擦伤的膝盖,迷失在
一片洋槐荆棘中。
她摸索着
向后的退路,朝向
大海的床头。
受伤的延龄草,
荒野中的,她
在带刺的叶子上休憩,
任凭风驻足抚慰。
现在她要学会
动物是如何
节约时间:
它们睡了整整一个季节
在哀歌和雪地里,
没有任何忧心的哭泣。
(笔者自译)
在道家中,女人与水密切相关,代表自然的阴柔与活力,所谓“上善若水”。而诗中的这位长期生活在干涸内陆的典型的美国已婚妇女(现代城市人)犯上了“缺水症”,几乎要饥渴而死。“延龄草”是北美常见的植物,但由于森林的过度采伐,生长环境被破坏,已经越来越少。受伤的女人披荆斩棘,四处摸索,试图寻找水源。其救赎之路就是像动物一样冬眠,学习它们的生活方式,回归“绵长的水域”。如《试着祈祷》(Trying to Pray)中所表达的:
这次,我已离弃我的身体,哭泣着
在黑暗的荆棘里。
依旧,
这世上存在美好。
是黄昏。
是美好的黑暗
当女人的手触碰面包。
一棵树的灵魂开始移动。
我触碰树叶。
我闭上眼,想念水。
(笔者自译)
“女人的手”(women's hands)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它可能是诗人曾经历过的美好感情,象征着恋人的触摸与人间烟火。当我“触碰树叶”(touch leaves),也是在触摸女人的爱。“树”意象代表了大自然的生命力,或象征男人伟岸的身躯,但如今“树”之魂已游移,只剩下残枝败叶。这是心与身的分裂、生者与死者的永别。诗人想念水(think of water)亦是对所爱者的无限追忆和渴望。“依旧”(Still),“是黄昏”(It is dusk)等句行只有一个或几个单词,简洁凝练,具有舒缓的节奏、静默的停顿与空白的想象。不难发现,赖特诗歌体现了庞德所谓的让语言直接表现物象本身的意蕴的能力,他通过清晰跳跃的意象和简明扼要的词语,赋予了现代诗歌一种意味深长的开放性和自由性:“美国语言正离开印欧语源,它离开拉丁语那种曲折的微妙细腻已经很远,相形之下更靠近汉语那种句法逻辑了。”
五、结语:跨文化语境下的他者之境
综上所述,赖特在《树枝不会折断》中自觉地融入了一些中国诗歌元素,体现了强烈的东方审美风格。他向唐代诗人杜甫、白居易致意,或引用其诗句,或化用其意象,或追慕“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品质和老庄虚境无为、豁达超脱的精神境界。像那些钟情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布莱、王红公、施奈德等美国诗人一样,赖特也善于模仿唐代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手法,借用汉语诗歌中意象并置/叠加的呈现方式,很少使用形容词、副词和修饰性词语,没有累赘奢华的修辞,尤其注重营造意境,在开始句和结束句中留有空白余韵。美国批评家詹姆斯·席伊(James Seay)对赖特的新诗总结道:“专注于每行诗的简化,在既定语句中提炼意象,使之更明显地为非理性所接受,而将解释减少到最低限度……诗歌的意象承载了更加光亮的大自然和如梦的流动性。”
如果把《树枝不会折断》置于20世纪美国新诗运动中考察,不难看出其独特的价值。对中国因素的吸纳和转化源自美国新诗力图突破来自欧洲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无所不在的强大的影响力,进行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内在驱动力。“20世纪美国诗歌理论和实践中一个不断再现的原则,是强调诗歌语言能够直接表现。因此,现代美国诗的基本倾向不仅是反浪漫主义的,而且是反象征主义的。在现代美国诗中占主导地位的庞德—威廉斯—奥尔森传统,是用对物象的临时感(immanence)来代替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也代替象征主义的替代暗示。”作为20世纪60年代初关键的诗集之一,《树枝不会折断》是美国新诗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寻求主体身份的产物。与中国诗歌类似,赖特的抒情诗聚焦于自然景色、田园风光、离别哀愁或日常生活中的瞬间感悟;它打破了传统英诗的意义和逻辑结构,尝试将抒情诗建立在丰富的意象和简洁的语词之上,其语言趋向简明口语化,诗歌的风格从前期较为恪守传统英语诗风,苛求修辞、韵律和严谨的逻辑转向了后期意象非逻辑化、语言简明朴素及口语化风格。与垮掉的一代的冗长说唱、自白派的过度宣泄不同的是,赖特诗呈现了深度意象派的别样风格:自然灵动,简朴率真,意象如梦如幻,它既摆脱了浪漫主义的崇高与繁缛,也不再为象征主义的深奥与超然所累,而更接近于东方诗歌的意境与空灵。
当然,赖特所受到的中国诗歌之影响也不应夸大其词,因为他同时受到了弗洛伊德无意识学说和西班牙“超现实主义”、奥地利德语诗歌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同时也融入了惠特曼式的自由体诗传统和诗人刻骨铭心、惨痛坎坷的人生感悟。作为深度意象派或“新超现实主义”的代言人,赖特十分关注主客分离与弥合、现代人的爱与伤痛、城市的生态危机、自然与文明的对立等问题,尤其善于从潜意识中挖掘主观意象和心灵幻象。这种难以预测的不定感与碎片化更接近现代人的人生经验。这些都是中国古诗以至中国当代新诗所忽略或缺失的方面,更多地体现了美国后现代诗歌的发展趋势。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当代诗人,赖特以自身的文化语境和创作理念为前提,创造性地借鉴或化用了来自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诗性智慧和艺术灵感,旨在反思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所面临的城市、家庭、婚姻、生态等多方面的困境,并提出了救赎之道。法国批评家于连(F.Jullien)把这种通过借用他者而进入自身的思考方式总结为“迂回与进入”:“这在遥远国度进行的意义微妙性的旅行促使我们回溯到我们自己的思想。”毫无疑问,中国古典文化为庞德、布莱、赖特、施奈德等美国诗人们的写作提供了一个突破英诗传统,有效观照、批判自身文化的距离,“正是中国诗这个异质因素使得美国现代诗人们在一点程度上认识到了现代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症候,从而建构出了一种既反浪漫主义又反象征主义的现代诗学,促进了美国诗歌的现代化”。反之,这也为我们思考中国古典诗歌在跨文化语境中的现代启示提供了一个“他者之自我”的反观视角。作为中国当代读者,阅读赖特的《树枝不会折断》,似乎能够感受到从太平洋彼岸吹来的北美之风,奇妙地共鸣在古老的华夏神州,恰是“似曾相识燕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