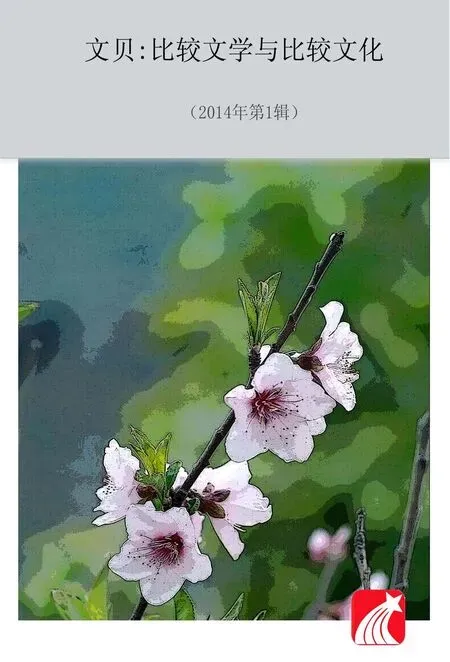如何制造中国式的善书?
——试窥赵韩《榄言》及其与明末西学的关系
李奭学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
如何制造中国式的善书?——试窥赵韩《榄言》及其与明末西学的关系
李奭学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
[论文摘要]
:明末出现了一套饶富意义的善书,称《日乾初揲》。书名中“日乾”二字出自《易经·乾卦》中“日乾夕惕”一词,示人以修身应有之道。《日乾初揲》一套五册,明显可见者有从闽人颜茂猷《迪吉录》“摘录”成书者,亦有合儒釋道于一体的“放生”与“广爱”思想的集子,更有正宗的功过格著作《心律》,总之中国传统三教善书的概念与实际表现,《日乾初揲》无一略过。有趣的是书首题为《榄言》的一册,全帙居然都揲自利玛窦著《畸人十篇》及所译《二十五言》和庞迪我的《七克》三书,内容俱是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阐扬所宗之作,而《二十五言》更是罗马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经典之作。由此可见,《日乾初揲》于中国传统三教之外,其“善书”概念也包含了天主教的著作在内,形成非常特殊的某种四教一家的现象,中国善书史上罕见。赵韩;《日乾初揲》;《榄言》;《畸人十篇》;《二十五言》;《七克》
一、赵韩家世并董其昌的因缘
赵韩(fl.1612—1635),字退之,晚年自号“榄生”。在这之前,他尝辑有《榄言》一书,亦称《榄言集》,广采万历年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刊行的《二十五言》(1604年刻)、《畸人十篇》(1608)和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的名著《七克》(1614)内文成书。《明史》赵韩无传,但《四库全书》卷二十沈季友(1654—1699)纂《檇李诗系》及乾隆《平湖县志》均有其人简传。《檇李诗系》且收赵韩诗作二十首,沈季友评其诗并人曰:“雄隽傲兀,刊落常调,诚一时之豪也。”从明末至清初,赵韩在嘉兴一带似乎诗名藉甚,《平湖县志》还称他继其父赵无声(1563—1644)起,“文名动海内”而有“大许小许之目”。纵然如此,我们对赵韩所知依旧有限,他和西学的渊源,尤难查考。《榄言》何以广采利玛窦和庞迪我著作中的珠玑与叙事文(narrative)成书,尤其成谜。本文拟从赵韩先世和交游入手,蠡测他和西学搭上关系的原来,由此再探《榄言》的编辑策略,借以了解明清之际,利玛窦和庞迪我等人的名著为人挪用的方式之一,顺此——最后——再窥当时西学影响力为人忽略的一章。
在友生或县志的记述中,赵韩诗才文名冠天下。是否如此,我尚难肯定,但推之赵韩先世,当真声名赫赫,乃有明之前赵宋一朝的缔建者,而且系宋太祖赵匡胤(927—976)的嫡脉。赵氏另有太宗一脉,和赵韩也颇富渊源。南宋初年,太宗一脉已经南迁,落籍浙江嘉兴府平湖(当湖)县。赵韩父赵无声(fl.1600—1635)和太宗支脉赵孟坚(1199—1264)先后移居海盐,时距三百年而前后辉映,并称诗画双杰,俱为赵韩之前,平湖地区重要的骚人墨客。无声名维寰,尝从黄宏宪(1544—?)习《尚书》,从游者包括董其昌(1555—1636)与冯梦真(1548—1595)等人。
嘉兴府在明末系科举名府,登龙者甚多,平湖尤着,乃后人所谓“第一科举大县”。万历二十八年(1600),赵无声举直隶顺天府乡试第一,看来顺理成章,无可诧异。之后他曾任杭州府海宁教谕,史家谈迁(1593—1657)尝在帐下,共修县志。无声着有《尚书蠡》与《读史快编》等书,对《尚书》琢磨尤细,颇得意于《尚书蠡》。崇祯八年(1635),此书初刊,董其昌为之作序,称:“吾友赵无声兴起当湖”,即“用《尚书》冠北闱”而“倾动海内外”,冯梦真且美其为“三十年所希觏”。所以赵韩一族虽移居嘉兴,文名不减,可谓平湖显世。
赵韩“初名京翰”,本字“右翰”,后改“退之”,系“万历四十年壬子副榜”,而来年的平湖教谕,就是有明一代在徐光启(1562—1633)、李之藻(1571—1630)与杨廷筠(1562—1627)外最重要的基督徒之一闽人张赓(1570—1649年以后)。张氏担任县学生员训导后五年(1621),因杨廷筠故而入天主教。松江府或整个大东吴地区,明末曾在此传教的耶稣会士多达二十八人,西学风行,可以想见。赵韩本人似乎视功名为陌路,重视的乃“李白腰间无媚骨,荆卿发上有悲风”,壬子后且自谓“得意皆庄子,浑身是楚词”,宁可“探梅云酒情,空似鹤人意”(《诗系》,23a),讲究的自是生活情调,故而寄情于山水间。所居虹岛在嘉兴南城门外,彭润章修光绪《平湖县志》,曾谓赵韩“家园久废”,寓虹岛只为“诗心”二字,所以沈季友甚重其人而评之曰:“退之文雄奇,故才大如海”(《诗系》,23a)。沈氏的《檇李诗系》,编辑自汉晋迄清嘉兴一郡之诗,而“檇李”即“嘉兴”的别名。张赓居平湖六年,“辛酉春”又尝“读书浙江湖上”,和赵韩一家是否有公谊私交,尚待查考。但话说回来,赵韩先世辉煌,平湖附近传教士又多,对我们了解他和西学渊源的关联确大,至少我们所知道的赵韩,为人有如同时的陈继儒(1558—1639)与屠隆(1543—1605)等清言家,写诗之外,也好以言体劝世,《榄言》可以佐证。
董其昌为《尚书蠡》撰序,称赵无声为“吾友”,又称与其子“同舍”而居,显示两人从受业于黄宏宪开始,交情匪浅,惺惜亦然。然而此中渊源最明白者,仍为《尚书蠡》实成于董其昌结社平湖之际,而且是由董氏偕其子并赵无声、赵韩父子于董府论校而成。董氏之序另谓赵韩是时曾“执经于余”,两人故可以“师生”称,学有渊源。赵韩的西学,可能循此而来。董其昌盛年之际,正当利玛窦和庞迪我行走华北之时。他是否认识庞氏,载籍有阙,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和利玛窦的联系,信而有征:1595年,程大约(生卒年不详)刊《程氏墨苑》,董其昌为当代画坛巨擘,不能无序。1 6 0 6年前后,程大约在所辑书末再添印利玛窦所献图、文数幅,此即后人所谓《西字奇迹》部分。其中利氏不但亲自撰专文赠程子,还附有他由西方携来的《圣经》图画数幅,艺史上早已交誉有加,视为中国最早引进的欧洲美术。董其昌和利玛窦即使未曾谋面,也应早已神交于《程氏墨苑》的墨林画丛中。莫小也抑且认为董其昌的山水画,还“具有中国绘画史上不曾有过的抽象性”,因其“构图新颖,明暗对比强烈,还出现了使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法面目一新的色彩绚丽的没骨画法”,而这一切正可说明董其昌和西洋绘画有所联系——虽则此事董氏或囿于夷夏之防,生前从未明白道及。尽管如此,董其昌生前结交的友生,天主教徒实则不少:绛州韩霖(1596?—1649)向称莫逆,为文字交,而在公务上,他曾极力支持过徐光启的救国大业。再据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董其昌大有可能还读过毕方济的(Francesco Sambiasi,1582—1649)《睡画二答》(1629),并在耶稣会所携器物或所布传说的影响下以西画笔法绘过和音乐、算学及地图学有关的希腊缪斯的图像。这幅图像颇不寻常,1909年即经人在西安起出。
董其昌的《容台集》刻于崇祯庚午年(1630),为之作序者系其“老友”陈继儒(1 5 5 8—1 6 3 9)。两人出身同郡,俱松江府治华亭人氏,在画坛亦齐名。然而熟悉明末西学东渐史的学者都知道,陈继儒于东来耶稣会士的著作熟稔异常,所刊《颜宝堂秘籍》不但收有利玛窦的《交友论》,而且还为之撰序,于五伦中“朋友”一伦的序位尝发惊人之语,早已盖棺论定,颇近后人谢文洊(1616—1682)“人生于五伦之中,朋友最为关系”之说。董其昌和西学的联击,陈继儒乃关系人之一,然而最直接的说明有二。一是董氏曾为利玛窦的《畸人十篇》撰序,而其文虽佚,其事利玛窦的《天主教中国开教史》(Storia dell' introduczione dell Cristianesimo in Cina)却暗示颇强,料应无误。二是董其昌另撰有《画禅室随笔》,详载某“曹孝廉”曾“视余以所演西国天主教,首言利玛窦,年五十余,曰已无五十余年矣”。董其昌是佛教徒,所著《容台集》有诗文自况,《画禅室随笔》这个书名更表明所宗为何。上引所示,一为董氏对天主教或其涵容的西学绝不陌生,故能“演”之。二则指出前此他应与利玛窦会过面,否则无可指正“曹孝廉”,告以是时利氏岁数“已无五十余年矣”。三则因有互文使然,更可指出董其昌读过《畸人十篇》,故能“演”其中之义。既然读过《畸人十篇》,又能“演”其义,董氏确可能如《天主教中国开史》暗示的尝为《畸人十篇》撰序。
这种种关系,可以说明董其昌于西人西学并不生疏。他的《玄赏斋书目》又胪列了利玛窦的著作五种:虽然《同文算指》与《几何原本》等这五本书殆属科学之作,但以董氏的中国中心论衡之,书目所刻未必就等同于家中所藏,何况上述诸书俱属《天学初函》中的“器编”之作,而“道编”中的《西学凡》也胪列于其中,其他文科与宗教类著作当也可能侧身其间,而上述书籍果为《天学初函》的“器编”内典,“理编”中除《西学凡》外,必然也包含庞迪我的《七克》。差别仅在如其画作,董其昌的中国中心论又起,不予刻入《玄赏斋书目》罢了。在某《题画赠陈眉公》文中,董其昌自谓尝为“图昆山读书小景”而有檇李之游,上述平湖结社的往事,或因此而来。不过董其昌游嘉兴,理应不止一次。他和平湖赵氏的关系之深,不言而喻,和赵无声互为文友,和赵韩谊在师友间,更是证据确凿,而这适又可说明对于西学,赵韩不仅可从董氏而有耳闻,甚至深入。他和庞迪我的《七克》及利玛窦的《二十五言》、《畸人十篇》之间的互动,兴许便肇始乎此。
二、谏果回甘之道
文前提到《榄言》之外,赵韩另著有《蜡言》、《蔗言》及《竹枝词》等书,沈季友《檇李诗系》及相关他著均称“并未刻藁”(《诗系》,2 3 a)。是否如此,《蜡言》、《蔗言》及《竹枝词》等书待考,然而《榄言》则非,而且早在明末即有刊本,并入套书《日乾初揲》之中,而且置于全套之首,可知见重。《日乾初揲》为宗教性善书,酒井忠夫尝谓刊刻于明末,约介于1 6 3 1迄1 6 4 1年间。我所见的《日乾初揲》系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的庋藏,共五册,第一册除《榄言》外,另收《至情语》,其余诸册则有《迪吉拈评》(第二册)、《纪训》、《心律》、《课则》、《读书日记》、《防淫警训》(第三册)、《广爱选言一》(第四册)、《广爱选言二》(第五册),甚至还有《牛戒汇钞》一编(第五册),多为当时著名的家训、格言、功过格、戒律,甚至是劝学类的儒释道善书。再据酒井,《日乾初揲》乃明末陈智锡(明卿;生卒年待考)编纂《劝戒全书》(1641)取材的对象之一,明白收录于书首《采用古今书目》之中,而该书也曾东传日本,影响甚且扩及德川时代日本的儒学家。在中国,清人在光绪年间曾予以删节,又辑为《删订劝戒全书》,可见《日乾初揲》间接的力量。此外,《日乾初揲》中如《心律》者,对同时或后世的功过格影响极大。至于《迪吉拈评》,显然则裒辑自晚明福建士人颜茂猷(?—1637)的《迪吉录》(成书于1622年,初刻于1631年)。颜著以儒学为本而出以宗教上的果报之说,确实看透了孔门的宗教本质,乃袁黄(15 3 3—1 6 07)《了凡四训》以外明末最重要的善书。酒井举出来的《日乾初揲》的成书上限,或许便因颜茂猷《迪吉录》的初刻时间而得,而其下限,或因《劝戒全书》付梓于1641年使然。
内阁文库本的《日乾初揲》目录载,这套书系丰后国佐伯藩第八代藩主毛利高标(1755—1801)所献。毛利家族藏书颇富,而内阁文库本既指《日乾初揲》为明末刊本,当非和刻,而是汉刻而后流入日本。《榄言》志在格言或清言类的辑集,儒家色彩重过其他,因此应该刻于《日乾初揲》成套之际:其卷头有案语,而这案语果为赵韩撰,则《日乾初揲》理应为赵氏亲“揲”。《广爱选言》与最后一册的《牛戒汇抄》,双双承袭《迪吉录》的劝善企图,从先秦经传选到汤显祖(1550—1616)、虞淳熙(1553—1621)、焦竑(1540—1620)、云栖袾宏(1535—1615)、顾钖畴(fl.1618—1645)与《道藏》、《大明律》等人、书之文,儒释道三家俱见,说来系当时阳明学派影响下的放生思想的极致表现。《牛戒汇抄》在清初力量极大,顺治皇帝(1638—1661)曾予重印,大学士魏裔介(1616—1 6 8 6)也因此而裒集诸书,再成《牛戒续钞》三卷。《日乾初揲》中,赵韩辑《牛戒汇抄》所用的动词和他辑《榄言》一样,都是“揲”字:“揲《牛戒》。”《榄言》刻成,看来确实就在1 6 4 1年之前,因为《广爱选言》或《牛戒汇抄》中似无选文的撰作年代迟于这个年份。
赵韩揲《榄言》,大致以儒门清言集自居,不过在功能上,我们可将之收为《福寿宝藏》归纳的“格言类善书”,一如范立本(生卒年不详)的《明心宝鉴》、吕坤的(1536—1618)《呻吟语》或上述袁黄的《了凡四训》。但是纵观《榄言》全书,赵韩所辑固多庞迪我《七克》、利玛窦《畸人十篇》与《二十五言》中他所喜好的文句,其中却也不乏叙述性的故事。赵韩编选的方法亦颇诡异,从《畸人十篇》揲出之文乃都为一体,夹在揲自《七克》者之中,不加注意,我们几难察觉,而摘自《二十五言》的段落,则都集中于《榄言》最后,非属行家,同样辨认不易。何以如此,原因殊难断定,赵韩或有隐藏之意,不欲为人知晓《日乾初揲》在儒释道等中国三教的传统之外,另有出诸天主教的文本。这些文本,容我再强调一次,记言与记事皆备,区别是:即使是叙事文,赵韩多半也会令其包含广义的“格言”在内,是以称《榄言》为“格言类善书”,不为过。
《檇李诗系》收赵韩《赠徐冶山国医》诗,首句为“却怪枚生《七发》诗”。明代一般士子,均以《七发》为庞迪我《七克》名称的来源,赵韩想亦知晓。至于“克”字,当取自《孟子·离娄上》“克有罪”一句。《榄言》从《七克》所出者,其数约在二百零八言;从《二十五言》中,赵韩又选取了十三言,而《畸人十篇》则辑录了五言。此一总数在二百二十五言间的合辑,每一言选来,赵韩几乎都有策略性的考虑,手法颇似比他稍晚的江西士人谢文洊的《七克易》。谢氏书名中的“易”字有玄机,因为他认为《七克》即“吾儒克己之法”,故而“为删其中失正者”,并“取其长而弃其短”以“置诸案头”,视同“修省之助”。《七克》全书七卷,“易”后仅得两卷,删削幅度颇大。《日乾初揲》中的“揲”字所蕴,也不是依《七克》原书之样画葫芦:“揲”字本意为“抽取”,但在《榄言》中,赵韩一无“占阄”式的随兴抓取之意,而是条条抓来皆有深意。如果所取西学或天学可称“原文”,赵韩所选可称“揲文”,那么两者间,赵韩绝无依利玛窦、庞迪我之意为意而编书之意,反有其个人的目的在焉,主要亦为表彰儒家“克己复礼”的思想,用为修身日省,以成其立命之学。
利玛窦与庞迪我的原文,在《榄言》中显然都已遭赵韩挪用。这点酒井忠夫似乎也有所悉,所著『增补中国善书の研究』一书,尝谓《日乾初揲》中“教会”的色彩悉遭抹除,而即使在日文中,这“教会”二字,指的应该也是天主教会,差别仅在酒井对《榄言》似难论断,不知所出之“教会”色彩系指何者,系出何书。我们细案《榄言》,反过头来亦可见从明神宗开始,利玛窦与庞迪我为中国明人接受确深,而《七克》、《畸人十篇》与《二十五言》在时人心中的烙痕不浅。
《日乾初揲》中的“日乾”一词,出自成语 “日乾夕惕”。李贽《代深有告文》谓:“夫出家修行者,必日乾而夕惕。”这句成语又有出典,系《易经·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易言之,赵韩揲《七克》与《二十五言》等书成《榄言》,首要目的当在以格言为鉴,惕励自省,甚且不乏出世之思。前谓《榄言》正文之前有赵韩的案语,可借以了解他揲文的准则与目的:“榄虽涩,味转则长。言虽微,绎思则益。昔人谓橄榄为谏果,我亦将以谏世也。”他因之而“揲《榄言》”。易言之,除了“谏果回甘”外,赵韩选辑《榄言》也有以书中格言谏世、醒世与警世的弦外之音。故揲文必须“言虽微,绎思则益”,读来有余味(《初揲》,1:1a)。《榄言》所属,正是善书“格言”类中的“清言”一类,最接近的自是陈继儒与屠隆等人所著。
在1608年之前,利玛窦重要的文学着译都已完成,庞迪我的《七克》在1614年前亦已镌版功成。我们且不谈庞著,单就赵韩摭拾利玛窦的《二十五言》,就可以想见“言体”在明末的文化界几乎无所不在。当其之世,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6—1640)还译有《励学古言》(1632)与《达道纪言》(1636),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则效《二十五言》别撰《五十言余》(1645)一书。这些耶稣会士所译或著,没有一本像《二十五言》——我们还可外加庞迪我《七克》中的多数言条——如此合乎赵韩“日乾夕惕”或“惕励自省”的慎独与修身标准?何况赵韩之志有甚于此者,每每希望所辑能如谏果回甘,读之而得思其然,从而谏世警世,劝人进德修业。
上述赵韩辑《榄言》的“准则与目的”,儒门“克己复礼”之说可以一言以蔽之,顶多外加佛道的醒世见解。我如是言之,不是毫无根据:《榄言》中的揲文,以庞迪我的《七克》为先,抑且占了全书三分之二强,而《七克》虽为西学,庞迪我却有意自我儒化,以故取《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纲,而以宋儒周敦颐(1 0 1 7—1 0 7 3)的“主静”标榜全书,劝人借此修养,盖“无欲故静”。众所周知,《七克》虽步武枚乘(?—140)《七发》等中国古典之名,所“克”者“七”,样样却都是天主教——乃至于整个基督宗教——力加排斥的“七罪宗”(Seven Deadly Sins)。用庞迪我的译词及排序,亦即骄傲(Pride)、嫉妒(Envy)、悭吝(Avarice)、忿怒(Wrath)、迷饮食(Gluttony)、迷色(Lechery)与懈惰干善(Sloth)等七宗(李辑,2:715)。静则无欲,七罪不犯。
天主教的七罪宗,原有《圣经》的根源(如窦5:21—22或27—28),但最早为之排序者却是东方教父庞义伐(Evagrius Ponticus,345—399)。他草拟了各种有损灵性的恶德,内容涵括“悲叹”与“自负”等八种。公元6世纪,教宗大额我略(Gregory the Great,c.540—604)再将这八种恶德略微裁并,约为七种。大额我略的排序,系依世人对“爱”过滥的程度为准出之。到了13世纪,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c.1225—1274)集士林神学之大全,才将“骄傲”定为诸罪之首,但要排列出如上庞迪我所定的顺序,我们却得归诸13世纪《教会法典》(The Canon Law)的笺注著奥斯帝亚的亨利(Henry of Ostia,d.1271),而其大行于后世,则得待反宗教改革时代的耶稣会士,也就是庞迪我的会中先贤了。
从庞义伐到阿奎那的时代,欧洲神学界众议佥同的是,“骄傲”乃诸罪宗之首,而“七”虽为犹太/基督宗教的圣数,却也是天主教《圣经》邪灵特属的数目。以《若望默示录》为例,其中便提到有一条水龙,其尾有“七”。他带队作乱的恶党,其数亦为“七”。这条龙指的当然是撒殚(12:3),“七”字在《若望默示录》里遂为邪数,而“七罪宗”的数目由来,自此奠下,并挟其所涵变成天主教的基本教义。阿奎那以还,讨论七罪宗及如何克之的美德的教牧手册(preacher's handbooks)纷陈,其数不可量计。庞迪我的《七克》虽名为“著”,其实也应有所本,乃译或转述自其数待考的证道手册,例如14世纪某道明会士著的《道德集说》(Faciculus morum),或稍后西班牙证道大师伊斯迪拉(Diego de Estella,1524—1578)的《浮世论》(Tratado de la Vanidad del Mu n d o)等,最后再自行添加儒门节欲导情的思想成书。就其文类归属而言,《七克》可纳为“恶德与美德专著”(tractatus de vitiis et virtutibus),应无疑义。
七罪宗的每一宗,都是天主教认定的人世大罪,既然有碍灵性,儒门修身无疑也会避之唯恐不及。庞迪我强调凡人若想“克己复礼”,则必先以天主教提出的“七天德”(Seven Heavenly Virtues)克服“七罪宗”(李辑,2:715—716),此即徐光启《克罪七德》所称之“谦逊以克骄傲”、“乐舍以克悭吝”、“贞洁以克淫欲”、“含忍以克忿怒”、“淡泊以克贪饕”、“仁爱以克嫉妒”,以及“忻勤以克懈堕于善”。赵韩绝非基督徒,但因明末嘉兴天主教盛行,重要的基督徒辈出,兼有师门与家学之便,从而得见《七克》等书,遂游走在七罪宗与七天德之间。庞迪我等人的文句,《榄言》大加裁剪改订,使之更加顺从儒门之旨而“去天主教化”,终于蜕变而为晚明善书中的一大言体新编。
至于《榄言》揲《七克》内文的手法,可用“多矣”形容。其中之一乃将纪事改为记言。再案《七克》,庞迪我中译了不少欧洲上古与天主教时代的名人轶事,甚至还引证了六则虚构性的伊索式寓言。其中不仅有耶稣会会祖圣意纳爵(St.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的“骄傲问答”(李辑,2:782),也有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伊索寓言如《乌鸦与狐狸》(李辑,2:752—753)。然而《榄言》里,赵韩时而剔除其中人事,独留相关警语成言。《七克·解贪第三》中,庞迪我提到罗马卓有清誉的政治家“加德”(Marcus Porcius Cato Uticensis,95—46 BCE),谓之“将终,以黄白金数亿寄其友人曰:‘我死之后,子孙作德善用,全予之;否,毫末勿予。’或问故。曰:‘金钱者,善用之为德器,否则为恶器。我子孙不必其为善,不愿助其为恶。’”(李辑,2:858)《榄言》里,赵韩刈除了“加德”之名,连他以黄白金寄友的故事也悉予剔芟,而最终所得,唯加德答友人之语:“金钱者,善用之为德器,否则为恶器。我子孙不必其为善,不愿助其为恶。”(《初揲》,1:29a)这里的“我”字可为泛指,而赵韩同类的揲文,使不谙西学者观之,必以为系儒门嘉言警语,诲人教化之态显然。如此“去叙事化”即“去西方化”,也可谓“去天学化”,《榄言》用来非仅娴熟不已,也足与前及《明心宝鉴》中的劝善之言媲美。
尽管如此,《榄言》有“例外”,道德性的叙事文仍不乏见,而且“史构”与“虚构”并存,各自保有不少。赵韩的删削,偶尔亦有其不可解的一面,“史构”中之尤者,乃波斯名王“实尔瑟”(Xerxes,485—465 BCE在位)的故事。《七克》原文中的第一句话是“昔有国王”,其后则为此王——
统百万众,布阵原野,私念:“百万之众,谁能御之?我为其为主,尊矣!大矣!”忽反念曰:“不然,不及百年,彼百万皆死,我亦死。以一死为众死主,何足矜?”(5b)
《榄言》中,赵韩删除了“昔有国王”这一句,致使整个故事的主词佚亡,我们读来遂不知所云。中文非属曲折语,固可省略主词,但在上引中,这“统百万众者”却不然,倘无主词引导,而读者如果也未曾得见高一志《达道纪言》中此一世说的原型,读来必定会因赵韩删削而生茫然之感,不知其后以生死自我惕励者究为何人:“实尔瑟大王统百万军。一日,从高望之,泣数行下。王叔问故,答曰:‘此众不百年,无一在矣。乃王者反以其民之众而傲之?’”就《榄言》所引的这则世说言之,赵韩把主词删得实无道理,仿佛只为隐藏“实尔瑟”之名,令人昧于其出自西学而已。可是这又不尽然,因为《榄言》引的是庞迪我,《七克》中的“昔有国王”并无西方人名的暗示,大可不必将之挥笔删去。如果这是刻工漏刻所致,情尚可原;设为赵韩个人的举措,那就令人生画虎不成之感了。
赵韩倘保住了主词,并其身份,他的删削实则不差。除了文句益简益洁之外,生动依然。《七克》第一卷中,上引故事全文如下:
昔有国王统百万众征行,布阵原野,登高望之,辄生雄心,私念百万之众,谁能御之?我其为主,尊矣!大矣!忽觉为傲,反念曰:“不然,不及百年,彼百万皆死,我亦死。以一死为众死主,何足矜矣!”(李辑,2:758)
两相对照,赵韩芟除了百万众“征行”二字,减少文意上的矛盾(既“征行”,又“布阵”),也砍除了“登高望之,辄生雄心”两句,亦即马上转到国王私念兵众虽多,但总有一日必死,自己拥尊荣之身,无上权力,来日却也不过是众鬼之王,“何足矜?”庞迪我的原译里,这三字之后另有“矣”字,口气是感叹的。赵韩削去“矣”,“何足矜?”反倒变成了地道的问句,而且是修辞反问(erotesis),“百万”与“一”所形成的数差辞效,益发可见,全句力量随而再增,可捋高一志的世说原型——虽然较之故事取典的希罗多德(Herodotus,c.484—425 BCE)《历史》(The History)中的原文,则又已纤瘦了许多。
同一个故事,我无以揣测赵韩何以芟冗,因何又生错削?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深知庞迪我笔底乃高一志明言的“伯西亚国”人。如此一来,赵韩对《达道纪言》似乎就不生疏了,而他欲儒化《七克》的故事,看来就非得拿掉主词不可。此外,还有个属于欧洲修辞学(rhetorica)的问题:庞迪我的故事在世说“背诵”技巧下,枝叶稍繁,而且庞氏还是东来西僧,中文总嫌不足,必有可删之处,改之应无不可。像最后一句话,由《七克》的感喟转为《榄言》的诘问,消极的语气随即变成积极,可窥赵韩何其手巧与心灵!这一来一往间,赵韩变成了反向在演练西方人的“修辞初阶”,将之“化繁为简”,而不是欧人习见的“由简入繁”。方之《达道纪言》,《榄言》果真大为不类。
然而不管赵韩如何参与这套西方人的修辞演习,他仍然不改“修辞初阶”以“世说”为修辞演练的基要,亦即不管世说的精神为何,由繁入简后,世说仍旧可以保有其原来的精神。实尔瑟的故事劝人终究难免一死,所以官大权大又何足傲?凡人皆应了解“伏傲”这个《七克》首布的篇章之旨,赵韩笔下的实尔瑟故事因可谓“一叶知秋”,盖“傲乃过分之荣显”,系“轻人而自以为异于众人”的心态(李辑,2:717),不足为训。中国文言好以卑微之态言事,“傲”字不轻易见之,“伏傲”这种军事化的语言自不必说。同样的概念,赵韩用的是较为激烈的儒门说法:“鸣谦。”(1a)
再回到形式问题。《七克》所含的虚构性叙述文,《榄言》更动较多,但仍有一字不易者。如上所述,《七克》中有六则伊索式寓言,其中《榄言》引出而完璧保存者唯下面一则:
孔雀,文鸟也,人视之,辄自喜,展翅尾示人;忽见其趾丑,则厌然自废,敛其采矣。禽兽无知,犹知以微恶废全美,人欲以微美掩全恶乎?(《初揲》,1:2b;李辑,2:784)
拙作《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中,曾约略论及此一故事,除了取利玛窦在《畸人十篇》所引的同一比喻对比之外,我也取高一志《譬学》一条以说明“叙事”与“陈述”之间的不同(《晚明》,55—59)。高氏的译文如次:“孔雀,文鸟也,以足之丑不敢傲其羽之美。智者恒视己短,省己过,以为克傲之资也。”(《三编》,2:631—632)其间差异,当然在庞迪我所译用了一个“忽”字。这个副词一添,其后的“见”字随即转为动词。《七克》前半句乃一陈述,但后半句转为叙述,全赖“忽见”之功,而“忽”字当然又使“见”字变得生动,读来有惊诧之感,称之为此一“故事”所以为“叙事文”的钥字,可也。若再方之高一志《譬学》中的同一述说,则高“译”只见描述,毫无动作,诚格言矣!我的比较并非无端,可借以说明培里(Ben Edwin Perry,1892—1968)之见:寓言与格言之别确在一线间,唯叙述与陈述有异耳。
上文旨在说明《榄言》挪用《七克》叙事文的另一方式,而赵韩喜欢叙事文,说来一点也不奇。颜茂猷的《迪吉录》,通书几乎都用叙事劝善,稗官野史俱入之。《日乾初揲》的第二册据《迪吉录》揲出了《迪吉拈评》一“书”,其中的揲文,读来即有如中国三教的“证道故事”(《劝善》,161—167)。其中赵韩的文字增损亦大,单是《迪吉拈评》的序文,他在不避颜茂猷的著作权的情况下就割裂了原本,也删削了顾锡畴的《迪吉录·序》,使各自都形成一新序(《初揲》,2:序1a—3b)。《榄言》中赵韩其余所挪用者,《七克》里的证道故事仍多,而且以“世说”称最,盖 “世说”本即含箴铭或训格之言的史事,读来确有谏果回甘之感。当然,一切西方史上的实人,赵韩早已消隐其名,庞迪我的名姓固无论矣。
《七克》言条的本身若不列名,赵韩揲来更为方便,《榄言》几乎一字不脱,直接引之。下面一则,可作范例观:
一人病,其师慰之曰:“尔为铁,以病错,则除锈。尔为黄金,以病炼,则增光,何忧乎?”(页18b)
这一条世说的前一条,乃某我尚难辨认的“圣若闇”(St.Johann)近似的训谕(李辑,2:942)。但一路走到了引文中这某人之“师”处,《七克》既省文了,赵韩当也可姑隐其名。世说的重点乃在借人说格言,不在故事本身,而《七克》这里本来就没名没姓,“原文如此”(sic.),赵韩似乎连“中国化”的程序都免了,照抄便是。
谈到格言,《榄言》身为言体,对之兴趣当然大了许多,而这也最符合中国经籍经常呈现的书写形式。赵韩为让《七克》的天主教格言变成儒家的清言,惯使的手法,乃是翦除天主教的圣人之名,包括业经天主教化的希腊、罗马异教的古贤。既然关乎西圣,则“天主”二字当然也在剔除之列,否则就得刈除“主”字,使之变成孔子或先秦他典常用的“天”字。下面一条故事又是世说,庞迪我写来如下——
或问天主雠傲,犹有在高位者,何故?曰:“使傲人登高,非增其荣,独重其陨。”(李辑,2:720)
赵韩删除“或问”这个世说常套,改“天主”为“天”,其余一仍其旧,通文因此变成“天雠傲,犹有在高位者,何故?曰:‘使傲人登高,非增其荣,独重其陨。’”(《初揲》,1:7a)世说精炼整饬的特色,《榄言》此地依旧保存,虽然懵懂者并不会知道这是欧洲修辞学特有的形式。由是观之而话说回来,赵韩的西学绝佳。他知道中国信仰中几无“天主”的概念,儒家教人的是尊“天”。删去“主”字,耶稣在世说中就变成了孔圣。加以“克己”的首要确为“节欲”,而“欲”之大者“傲”,是以孔孟都主谦。从宗教的角度看,儒家所尊之“天”,时而为人格神,时而非,可信的是这“天”绝非天主教所称那超越性的“天主”。只要把这个名词删个字,欧罗巴人庞迪我也会变成中国——尤其是儒家——的代言人,而且会变得神不知,鬼不觉。顺治与康熙在位时,都曾为天主教颁发“钦崇天道”与“敬天”的匾额。所谓“天”者何?顺治或康熙题字时当然心知肚明:一字之差,他们实则化西学为中学了。衡之《榄言》里赵韩所为,顺治与康熙在清代不过复制了他在晚明早已“玩”过的“易道”!
由是再看,赵韩的西学造诣确实不凡。纵然《史记》中已有“天主”一词,他也知道就《七克》的语境观之,同样的“天主”语意不同。赵韩揲《榄言》的时间殊难论断,下面我会再详。然而就《迪吉录》迄1631年才刊刻衡之,《日乾初楪》里《榄言》的刻本不可能早于此刻,而“此刻”距礼仪之争虽仍有年,但从1628年起,天主教在华业已禁用“上帝”一词,而且禁用的相关会议就在嘉定召开,距嘉兴并不远,何况此词《诗经》、《书经》与《易经》上俱可见,中国人读来未必带有天学的意涵。赵韩幼习坟典,乃传统士子,“上帝”一词必然知之甚稔,而这点几乎可以解释《榄言》下引长言里,赵韩何以不避“上帝”二字。《七克》步欲步,《榄言》趋愈趋:
人相爱有三。其一习爱,同居、同业、同情、同议等,相习生爱也。是者,易聚、易散,鸟兽亦有之,纵不恶,固非上帝所责我爱人之德矣。其一理爱。人皆自知生斯世也,同斯人也,不友爱任恤,不能成世道,不能立世事,不能备世变,是故恒求己所爱人,及爱己之人。此人间之事为爱也私,为德也微,恶人亦有之,亦非上帝所责我也。其一仁爱。仁者,视人与己同性,故爱之,而愿其得福。孰为福?生时能识上帝,行实德,死时升享天福,则真福、大福也。仁者,自先真爱上帝,转以上帝之爱爱人,故望人识爱上帝,以享生死真福,冀改诸恶,脱永殃也。若他福,无妨于此福,望之,否则恶之,是谓仁爱,乃上帝所责于我焉。若以是相爱者,真友也。非除贪妒、傲淫诸恶情,非心契于上帝真道实德,虽合于外事,弗能得焉。(《初揲》,1: 22b 23a)
上文中,我评道:《榄言》于《七克》此一长言“几乎”是“趋愈趋”,原因在赵引仍有异文:“仁者,视人与己同性”二句,《七克》中原为“仁者,视人为天主之子,与己同性”(李辑,2:821—822);赵韩抹除了《七克》这一句,再度避开“天主”二字,独留“上帝”这个原为儒家经籍中的至高神。赵韩稍后的明人中,基督徒如杨廷筠或韩霖等都坚持先秦古籍中的“上帝”就是己教的“天主”,即使非基督徒如魏禧(1624—1681),亦复如是,谢文洊就不用说了。魏禧尝为文评《七克》,称其中“所尊天主,细求之,即古圣所云上帝,先儒所云天之主宰,绝无奇异”。以故《七克》等书“每每于说理时无故按入天主,甚为强赘”。谢文洊也有近似之论:“与友论西学,力辟其[耶稣]降生[为人]之说。试问上帝有否?予谓上帝载之六经,何可说无?”繇是观之,赵韩纵不以儒家收编的先秦经籍为意,《榄言》中他也不会删除“上帝”一词,况且《日乾初揲》中的《迪吉拈评》或其所出的《迪吉录》,根本就是一本打着“上帝”或“天帝”名号叙事的劝善之书。《迪吉录》另又结合佛门的天堂观与儒家的地狱说,形成二教交混的果报观念,而颜茂猷通书就以此等思想构成,令“上帝”在人类史上奖善惩恶。赵韩既然没让《日乾初揲》错过《迪吉录》,则所揲怎可能抹除“天”或“上帝”?
此外,“爱”的观念也值得在此一提,中国古人好以“情”字代之,《日乾初揲》所收第二本书《至情语》的论述,主要是家中父子、夫妇、兄弟这三伦之爱,甚至还涉及情欲的问题。赵韩的前言用的便如书题,是“情”字,而其语法仿如清初盛世《红楼梦》的脂砚斋评笔:“世人多不情,当治以何法?仍治之以情而已。”中国古来,其实也会将“爱”用于亲朋之间,而对象若为世人,“博爱”一类说词用得益切,和天主教从《圣经》起即大力强调者实有落差。这一点,李之藻在《代疑篇》(1621)中早已历历指陈:这世人之爱必需扩及天主,而这点中国人可万难料到。庞迪我处理的方式是使之结合“仁”字,而既有“仁爱”,仁者也就“自先”要“真爱上帝,转以上帝之爱爱人”(李辑,2:821)。庞氏之论当然是典型的《圣经》论调,不过赵韩合“仁”以“上帝”,在明人的想象中几可免除天学色彩,至少减轻了许多。故上引文所成者,自是《颜氏家训》一类的儒门格言。不过儒家与西学这里有一矛盾,十分显然。《日乾初揲》诸书中,“爱”字用得最为寻常的,乃《广爱选言》与《牛戒汇抄》,其中满布由古迄明的涉“爱”之文。仔细看来,这“爱”的对象居然多非为人,赵韩揲得其实颇似儒门的“戒杀生”思想,而儒门的“全其仁心”、“民胞物与”等观念系此一基础再深一层的基础,赵韩抑且就承认思出儒门:“‘戒杀’一事,载吾儒经传,如日中天。奈何护生之功,专使佛氏主说于天下,甚矣!我辈咎也!……”(《初揲》,4:8a)。赵韩以儒自居而论爱,当然无可厚非,可是类此论调一和《榄言》源始的万物为人而设之说并比,矛盾立现,就出在“放生”这种“广爱”思想如依钱谦益(1582—1664)的弟子冯班(1604—1671)的观察,根本和基督徒主张的“杀生无报应”等《圣经》之说牛马互攻,理念绝难调和。不管如何,《榄言》的西学之“爱”,尤近似中国后儒以天地万物为一这种掺杂佛道精神的大爱。
《七克》里,《圣经》中言可想引之甚勤,不过赵韩揲《榄言》,可真详予筛检,“《圣经》曰”或“《经》曰”等词,绝难逃其法眼,绝难在赵韩笔下现形。下引《七克》言则不但有天主教名圣“系辣恋”或“喜辣恋”(St. Hilarion,c.291—c.371)现身其间,而且喜氏极可能还援引了《玛窦福音》论“真福八端”(The Beatitudes)最后数语(5:11—12),以解其自身的窘困,系典型的圣人言行与《圣经》交叠合一的叙事笔法:
系辣恋圣迹甚众,名播万方,来访者日众。圣人不悦,数徙避之,不获而哭。门人问故。答曰:“圣经云:‘凡欲循仁,必受窘迫。吾考前辈诸圣贤有实德者,无不因世苦辱,密就其德,以蒙天报。’今敬誉我者多,恐天主以是足我报于世乎?”(李辑,2:748)
圣杰鲁姆(St.Jerome,c.347—420)尝手书圣喜辣恋的传记。由所作来看,上引实为这位隐修圣人平生的行事风格:他常为了躲避俗誉而遁走林泉或荒野。不过圣杰鲁姆的喜传并无所答《圣经》一段,庞迪我或许有其“美德与恶德专著”中之所本。不管如何,上引经中之语,确为《玛窦福音》中“真福八端”最后数语。我们不难想象,庞迪我如此一言,《榄言》会剔除者何:圣喜辣恋的故事过于独特,不可能保留;在《七克》的语境中,《圣经》之名本身就是天主教的表征,赵韩也不可能容许存在。话说回来,这绝非意味着《圣经》箴言会见弃于《榄言》。相反,终《榄言》全书,至少五引《圣经》的训示。上引《玛窦福音》的话,赵韩抹除了碍他之眼的“《圣经》”与“天主”的“主”字后,随即照单全收,而“修改”后的言则,西学色彩几乎同样荡然无存了:
凡欲循仁,必受窘迫。吾考前辈诸圣贤有实德者,无不因世苦辱,密就其德,以蒙天报。今敬誉我者多,恐以是足我报于世乎?故曰:藏德以避虚誉,圣人也。(《初揲》,1:10a)
我之所以说此言中西学色彩“几乎”不存,系因此一“新言”赵韩揲来乍看百密,实则仍有一疏:中国古籍不用标点符号,是以赵韩难以辨明言中的“吾”或“我”字有别。前者乃《新约》中耶稣的自我指涉,所以那“考前辈诸圣贤有实德者”是耶稣,而所谓“今敬誉我者”中的“我”才是圣喜辣恋。《玛窦福音》的上下文中,“前辈诸圣贤”实乃我们今天译为“先知”(prophetas)的犹太/天主教人物,而后一名词,庞迪我的时代未见,天主教中人多解为“圣人”或“圣贤”,加以全本《圣经》此时仍未译成,赵韩理解有误,情有可原。然而话再说回来,揲文内《圣经》和天主俱杳,这第一人称谁属并不重要。明代不解西学者,读《榄言》这段话,也不一定会联想到天学。非特如此,为补足文气,强调“前辈诸圣贤”大多曾“因世苦辱密就其德”,赵韩复从《七克》毗邻圣喜辣恋传文的“圣泥哥老故事”再取一语,置于揲文之末,前面再加“故曰”二字以造成因果关系。因此他所成者,乍看下已像煞儒门的坚忍格言,而且还是包裹着耶稣或《新约》名言的“儒门”格言。罗香林考唐代《吕祖全书》,发现其内含有景教传来的天主教赞美诗。上引《榄言》,几乎也步上前尘,复制了《圣经》名句!不明就里,我们当会如赵韩所求于我们理解者,而知其然者,但觉有趣,或许还会打内心一笑:难道赵韩要人以为引文中的“吾”或“我”就是他本人?
所谓“圣泥哥老故事”,我指世传为圣诞老人(Santa Claus,or Saint Nicholas,Father of Christmas)的圣尼哥老的日常善举。《七克》谓“泥哥老”有乡人甚贫,三女难以出嫁,而“泥哥老”闻悉,遂于“暮夜挟赀,潜掷其家”,因使其长女于归有方。嫁次女,又复如是。待么女临嫁,这乡人乃于夜间潜伏,欲窥何方仁者行此善举,遂遇“泥哥老”。乡人当然感恩非常,“问何以报也?”而“圣诞老人”答以“我之行此,惟为天主,故恐人知。当我生时,尔弗告人,是报我矣”。庞迪我的叙述者讲到这里,就圣泥哥老所下之评,就是上引《榄言》最后一语:“藏德以避虚誉,圣人也。”(李辑,2:743—744)《榄言》这整个故事的趣味——包括其历史意义——当然不仅在“圣贤”及“圣人”(sanctus)赵韩混合用之,也不仅在“圣泥哥老故事”乃真人真事,是“圣诞老人”的源起首次在华现身,更在赵韩结合圣喜辣恋、圣泥哥老故事及《圣经》经文,终而化为一条就《七克》而言乃拼贴而成的三合一的《榄言》清言,在中文——不止中国——格言史上似乎前无古人,即使是严肃的来者也不多见。
赵韩删其名而存其言的天主教圣人为数不少,教宗大厄勒卧略(额我略)次数最多,余者中之荦荦大者尚有圣百尔纳(圣伯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1090—1153)、圣契理琐(圣基琐;St. Chrysostom,c.347—407)、圣法兰济(圣方济;Saint Francis of Assisi,c.1181—1226)与圣亚吾斯丁(圣奥斯定;St.Augustine of Hippo,354—430)等人。《圣经》中的人物,在耶稣之外,赵韩援用者,可想以圣葆琭(圣保禄;St.Paul the Apostle)盛名最负。至于异教中人,亚历山大大帝(亚立山;Alexander the Great,c.21—323 BCE)在中世纪早已天主教化,其师“亚利思多”(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E)亦然,赵韩揲得不少,而斯多葛学派和天主教关系密切,色搦加(Seneca,Jr.,c.4 BCE—65 AD)亦常经挪用。这一长串的西方上古与中古人名,可惜赵韩每因严于夷夏之防而删除了,否则《榄言》可能会是转录欧洲古人连“名”带“言”最多的一本纯由明代非基督徒士子所辑的专著。如其如此,《榄言》的意义就不止于揲选耶稣会的著作成书,而是另涵多端了。
《七克》的重点在“伏傲”与“平妒”等庞迪我用儒家“克己”以形容之的天主教德行,赵韩在《榄言》中则易之为“鸣谦”、“强恕”、“宁澹”、“闲情”与“荣进”等五个立命关目。不过“坊淫”一词,《日乾初揲》并未舍之,第三册便是《防淫警训》,而在《迪吉拈评》的《贞淫之报》栏首,赵韩甚且“指示”读者道:此栏“当与《榄言》中《闲情》与《防淫警训》参看”(《初揲》,2:12a)。这句话也是我认为《日乾初揲》系赵韩所揲的内证之一。职是之故,《日乾初揲》可非漫无计划之编,而是精心设计的结果。《防淫警训》的内容,我们观其名可以思之过半,《闲情》却不易猜透。七罪宗的克服之道自然有七,但赵韩约之为上述五个关目,《闲情》的揲文,大致包括《七克》以“坊淫”克淫的“方法论”。就某一意义言之,天主教士——耶稣会士尤然——大多是所谓“憎恨女人论者”(misogynists),每视女人为红颜祸水。赵韩从《七克》中得出“男女俱善,相近则污”这种极端之论(《初揲》,1:38a),不足为奇。他还让《榄言》揲出下文,似乎借《七克》在强调高一志《齐家西学》中的情色之见:
淫色者,如狭口之井也:入易出难。初意可蹔尝而后已,不知未试,发微易敌。既发,猛敌难矣!故自德堕淫者多,自淫迁德者寡:如鱼入笱焉,其入甚顺,出乃甚逆,万人无一出焉。(《初揲》,1:39a)
此一揲文意象鲜明,所谓淫色“如鱼入笱焉,其入甚顺,出乃甚逆,万人无一出焉”,可称妙喻,和高一志《齐家西学》(1630?)所称“束格辣(苏格拉底)恒悔结婚”的原因近似,或许就是从典故部分所出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3 century)的《名哲列传》变化而来。至于《齐家西学》继而之说,当从1世纪瓦勒流(Valerius Maximus)的罗马类书《嘉言懿行录》(Facta et dicta memorabilia)变化而出:“他日,或以婚问,[苏格拉底]答曰:‘鱼欲入笱易,欲出笱难。’”瓦勒流的世说,反映出罗马“新式高尚人格的修辞”(rhetoric of new nobility),无异于《齐家西学》的修身劝诫。然而庞迪我劝人以贞戒淫,倒纯从天主教的角度立论,为此他连耶稣会当时不敢对抗的儒家也公然撷之:《七克》多属译文,庞迪我硬在《坊淫》一支最后加进了自编的《婚娶正议》一节(李辑,2:1042—1052),借之大肆抨击中国古来的纳妾之风,认为是男性好色的表现,再不理孟子或官律“无后为大”的说法。就中国传统而言,如此“补儒”的论调似乎补过了头,和《旧约》合理化某些名人名王的多妻之风的说辞也不合。无论如何,庞迪我坚持一夫一妻制,看出纳妾衍生的家庭问题,令人不得不赞叹一声:庞氏以及明代耶稣会整体,早在《七克》中就为某种中国现代性预埋前提了。
尽管如此,赵韩以“闲情”概括“坊淫”,不无反将庞迪我一军的言外之意:淫念确实不可生,但非关国家大事,耶稣会反对纳妾这个重点,更不在他考虑之列。《榄言》从“荣进”的第三言开始,揲文正式转入利玛窦的《畸人十篇》,而由此踅回《七克》后,赵韩又进入利氏所译罗马大哲爱比克泰德(Epictetus,55—135)的《二十五言》:《七克》退居一旁了。《榄言》辟以取代《七克》的关目“容进”,理解较难。这个名词,史上并非鲜见,但以“接纳进用,拔擢任官”的常义度之,则恰与赵韩的命意相反。他可能因《世说新语》有《容止》一目,从而自创新意,略指人生不过白驹过隙,我们应珍惜眼前所有,但也不用强求,所谓“顺其自然”可也;倘能抓住时间,进德修业,更佳。《畸人十篇》的揲文,仅有五言,俱裁剪自首篇《人寿既过误犹为有》。
这篇对话录里,利玛窦谈话的对象是曾任南京吏部尚书的李戴(fl.1598—1603)。后者和利氏颇有私交,不过他笃信佛教,而佛教对寿无金石固的时间之见虽和天主教差异不大,对人世倏忽与生乃侨寓的看法更见和拍,然而一提到轮回之说则矛盾立见。《人寿既过误犹为有》不以寿长为念,反而以年寿既过,即消逝无踪为意,所以利玛窦和李载会面时虽当利氏五十初度,李氏问其年寿,利氏却以递减之法回道:“已无五旬矣。”(李辑,1:117)如此答法,董其昌稍后也会见证其然,文前已及:他提到利氏年已五十余,却对董氏道:“已无五十余年矣。”
利玛窦对有关自己年寿的答法的解释,出以荀赋开头惯用的句型,随之当然会像荀赋一样是个比喻,而且也用修辞反问为之收稍:“有人于此,获粟五十斛,得金五十镒,藏之在其廪,若橐中则可出而用之,资给任意,斯谓之有,巳巳空廪,橐费之犹有乎?”(李辑,1:117)利氏继之的解释,则以议论陈述,又以修辞反问为之收尾,其意甚明:
夫年以月,月以日累结之。吾生世一日,日轮既入地,则年与月与吾寿悉减一日也。月至晦,年至冬,亦如是。吾斯无日无年焉。身日长而命日消矣,年岁已过,云有谬耶,云无谬耶?(李辑,1:117—118)
利玛窦回李戴的话,和董其昌其后对他的解释颇为一致,赵韩读过《画禅室随笔》,可能性大增,所以《畸人十篇》中,他特揲利、李的年寿问答。董其昌之见发自释门,出自《法句经·无常品》,《明心宝鉴》亦曾引之,虽不可证《榄言》与《画禅室随笔》的关系,但可借以证前举天佛的比较:“此佛家所谓‘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无常义耳。”至于前引利玛窦的比喻与议论,《榄言》字字皆揲之(《初揲》1:44b),而天学与佛学,看来在此似可共存,差异不大。《畸人十篇》中,李戴对利玛窦的释词同样有惺惜之感,而利氏因此也做了一段《日咎箴》(李辑,1:119),《榄言》也没有放过,逐字照抄(《初揲》1:45a)。《人寿既过误犹为有》中,李戴和利玛窦谈得宾主尽欢,原因在利氏未曾当面辟佛,否则李氏必然不快。我相信两人如就时间问题续谈,结果必也如雪浪洪恩(1535—1607)与利氏之论心与物,又是风马牛不相干。尽管如此,在珍惜时间,勤笃修行这方面,利玛窦的话不唯无妨李戴心中所存,连赵韩应也一无异议。下面这一句话,赵韩只添了一个“故”字,使裁剪之句再度形成因与果,乃《七克》之外,他联璧而成的又一典型,而其主旨便在劝人珍惜光阴,从容生命,进德修业:“智者知日也,知日之为大宝矣,一日一辰犹不忍空弃也。‘故’至人者,惟寸景是宝而恒觉日如短焉;愚人无所用心,则觅戏玩以遣日。我日不暇给,犹将灭事以就日也,暇嬉游哉!”(《初揲》,1:45b;李辑,1:120—121)所谓“进德修业”,利玛窦指对越天主,但听在李戴耳中,却可能是修习菩萨道。不论何者为是,赵韩揲之入《榄言》,志在劝善,无可怀疑。
赵韩从《二十五言》揲得的言则,大多也带有一丝佛道的意味,尤其是佛教,不过每一言如实却也在反应儒家的实用哲学观。以下一例虽仅尝鼎一脔,仍然可概其余:
物无非假也,则毋言已失之,惟言己还之耳。妻死,则己还之;儿女死,则己还之;田地被攘夺,不亦还之乎?彼攘夺者,固恶也,然有主之者矣。譬如原主使人索所假之物,吾岂论其使者之善欤,恶欤?但物在我手际,则须存护之,如他人物焉。(李辑,1:338)此言赵韩选自《二十五言》的第十言,在《榄言》中则已推进至第二一八言了(《初揲》,1:53a—53b)。利玛窦译来虽隐带天主教——甚至是一般传统中国宗教如佛与道——的色彩,然而通言收尾的三句话,毕竟和《论语·学而篇》“泛爱众而亲仁”的精神契合(朱注,63)。爱比克泰德是罗马斯多葛学派的重镇之一,乃实用哲学的鼓吹者:“学贵乎用”这类概念,他如实实践。《榄言》所揲上引,利玛窦实则译自伊氏的《手册》(Enchiridion),而6世纪以希腊文笺注伊氏此书的柏拉图主义者辛普里基乌(Simplicius of Cilicia,c.490—c.560)有分教,认为强调的是“理性的知识”(rational knowledge),亦即人生世间,不应我执太甚。利玛窦的译法特异,因使上引含带万物皆有造之者之意,亦即把《手册》天主教化了,和辛普里基乌的柏拉图主义所差无几,也和中国民间信仰诠释下的佛道的物起论差别不大。但那理性思维带动的“随遇而安”之说最值得注意,说来几乎等同于孔门的世相之见。
较之爱比克泰德的《手册》,《二十五言》实乃节译,而且伊氏的五十三言中,利玛窦仅选了二十四言迻之。第四言似为利氏自撰。《二十五言》的开译,据徐光启的跋文,始自利玛窦仍滞留南京的万历己亥年(1599;李辑,1:327)。但万历壬寅年(1602)之前,利玛窦已译得十四言,因为是年王肯堂(1549—1613)撰《郁冈斋笔麈》,第三册就以《近言》为题全录之(《存目》,107:684—686)。不无意义的是,《榄言》不过从《二十五言》选了十三言,但除了殿军的一言外,余者居然全部和《郁冈斋笔麈》重叠。但赵韩不可能抄自王肯堂,盖《郁冈斋笔麈》这十四言的文字和《天学初函》本有异,显然是王氏自己的笔削添改。可以确定的是,赵韩乃抄自《二十五言》的单行本或《天学初函》本,不过他应该也参考过《郁冈斋笔麈》,故有重叠者,而文字却异乎王本。王肯堂是医家,博览群籍,明末亦卓有文名。他曾从游于利玛窦,《郁冈斋笔麈》故长文另演利氏的天文观(《存目》,107:680—682),并收录《交友论》(1595)全文(《存目》,107:682—684),还谈及利氏所赠欧洲纸质之佳(《存目》,107:715)。王肯堂系江苏金坛(常州武进)人,选为翰林检讨后,官至福建参政,万历二十年(1592)因故称病辞归。他的书第四册(成于1603年之后)颇多金坛之介绍(《存目》,107:747—752),应该刻于故里。赵韩有地利之便,日后不难窥见全豹。从《郁冈斋笔尘》四册所论或所收,我们可见王肯堂好佛,而他又是儒生,利玛窦“贻”其所成之十四言(《存目》,107:684),就夹杂在佛典儒籍与医家的论说里。
《榄言》其他出自《二十五言》的揲文,大多深具理性精神,而且入世者多过于出世者,如“遇不美事,即谛思何以应之”,或视人世如舞台,而帝王将相与那士庶奴隶不过“一时妆饰者耳”(《初揲》,1:53b—54a),劝人的是处世应有道,不必执著于世相。类此之见或比喻,把《榄言》揲自《二十五言》之言——甚至包括《榄言》其余诸言——都转成了以儒家为主而副以释道的“应用伦理学”,而这不仅和传统三教善书的目的桴鼓相应,也和善书中的功过格的形式若符合节。爱比克泰德这类思想,《二十五言》的最后一言言之最切(李辑,1:349),赵韩不可能看不出来,故此引之以终《榄言》全书:
学之要处,第一在乎作用,若行事之不为非也。第二在乎讨论,以征非之不可为也。第三在乎明辩是非也。则第三所以为第二,第二所以为第一,所宜为主,为止极,乃在第一耳。我曹反焉,终身泥濡乎第三而莫顾其第一矣。所为悉非也,而口谭非之不可为,高声满堂,妙议满篇。(《初揲》,1:55a)
此言看似劝学文,但利玛窦译之为“学”者,爱比克泰德实指“哲学”(philosophy)而言,而所谓“作用”,《手册》的原意系“定理的应用”(applying theorem)。“哲学”一说,辛普里基乌二度发挥柏拉图精神,解之为“科学性的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是要能通过检验查证的“真理”(what is true),而他所称验证之道无他,乃柏拉图惯用的“逻辑”(logic)精神带出来的“讨论”与“是非之明辩”。这一言,辛普里基乌编纂的《手册》列为倒数第二言,利玛窦则置于《二十五言》之末。赵韩同之,可知视同《榄言》压轴。不过,好一句“所宜为主,为止极,乃在第一耳”!赵韩不啻借此说明《榄言》通书所宗唯“作用”,唯四书五经,乃至于唯《论语》所强调的实用哲学或“学以致用”等观念是问。换言之,罗马大师爱比克泰德穿越重重的时空,亲自莅华鼓吹中士西儒都同意的某种“实学”,而赵韩也穿越宗教的云山雾海,用善书在响应明清之际这个“实学运动”了。《榄言》揲毕,赵韩如书前序言,加了句他以上引终《榄言》的原因:“自警也,亦所以警人也”,而且劝人道:“观者毋忽诸”(《初揲》,1:55a),应慎思详省,庶几不枉人世一游!
三、系年与意义
《榄言》上引《二十五言》的揲文,句句皆具“谏果回甘”之效。王肯堂称《二十五言》最早译成的十四言为“近言”,除了利玛窦初则可能如此题名之外,另有是编“若浅近而其言深远”的况味,可以为“座右”(《存目》,107:684),我们读来益可作“谏果回甘”的另类观。
虽然如此,赵韩的揲文多数仍然出自《七克》。我们从中国三教善书的角度看,这点不意外。儒家讲“谦”,佛、道也视“傲”为大罪:《西游记》前七回,孙悟空非但不“悟空”,反而反出“天帝”与“释天”的“天界”,思与天齐,甚至心比天高,天兵天将并诸佛菩萨要逮他,不啻视之如一中国式的“露际弗尔”(Lucifer)!“傲”是首罪,阿奎那论之已详,而此罪以外《七克》指出的诸罪,中国人其实多半也饶之不得。天学诸“罪宗”,本身即中文“过”字最好的说明:我指的是“爱”得“过犹不及”中的“过”,略如刘宗周(1578—1645)《人谱》所称“六重过”之“过”,或是但丁(Dante Alighieri,c.1265—1321)《神曲》(Divine Comedy)中对“罪”(troppo)的解释之一。故从《论语》有年龄之限的“戒淫论”到明末性别歧视强的“防淫观”在内,三教的卫道之士几乎都没放过。赵韩当然一一也都从《七克》中揲出,使《榄言》这部分变成了中西最早非理论化的“比较伦理学”,也是中西交流史上做得可能还要早于《七克易》的“应用伦理学”。
谢文洊重《七克》,比他年轻几岁的魏禧亦然。魏氏是江西宁都人,他评《七克》文非难天主,大讽耶稣为“荒诞鄙陋”而“可笑”,万没料到自己出身的“宁都”,日后在另一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Henri-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的《梦美土记》(1709)中,也变成了天主教“天堂寓言”的一部分。不过从谢文洊到魏禧,倒都认为拔除耶稣或天主之后的《七克》,其说理之精更在释道之上,最足以合儒:“泰西书,其言理较二氏与吾儒最合,如《七克》等类皆切己之学,所最重者曰‘亚尼玛’,即《大学》所云‘明德’,‘至美好’即《大学》所云‘至善’。特支分节解,杂以灵幻之辞耳。”易言之,若非“杂以灵幻之辞”,《七克》几乎是儒籍。魏禧之见,反映的当然是《论语》不语怪力乱神的基本立场。但只要去除“灵幻之辞”,天主教合儒,而此说甚至往下蔓延到了康熙盛世的彭师度(1624—1692),变成明末以来中国开明士子对西学的一般看法。彭诗《赠西洋潘子》云:“缁流糜金钱,玄宗匿浮慝。此独勤且廉,不废人间力。”刘耘华所云甚是,以为这里的“此”,特指“彭氏力辟释道,而认定天主教合乎儒家不弃人伦之义”。
赵韩诗名冠浙省,常与当湖名士游,诗酒唱和,所为诗《题双溪竹亭》云:“六逸无如李白放,七贤唯笑阿戎低。”(《诗系》,23a)虽取他典,却有自况之意。他的诗友之首为陆启浤(生卒年不详),尝客燕京二十余载,余者如陆芝房(1625年进士)、冯茂远(生卒年不详)、孙弘祖(生卒年不详)等人,似乎也都不谙西学,独董其昌例外。1635年,《尚书蠡》在董寓论成,但这年并非董其昌首度莅平湖,盖赵、董早有通家之好,是以在此之前,赵韩应该已是西学老手,对天主教的信理认识不浅。
前文指出,赵韩晚年自号“榄生”,但这并不能解释在“晚年”之前,《榄言》尚未揲成。至于《四库全书》与光绪《平湖县志》所称这“晚年”,到底又有多晚,我们目前也仅能约略蠡测。倘据高国楹与沈光曾等修纂的乾隆《平湖县志》(1745),我们知道“束发时”,赵韩承父命拜师,于万历壬午年(1582)入南雍,师事南京大理卿董基(1580年进士),并于崇祯末年为董纂的今、古《略书》(1638?)撰序,颇为其人“虽工为制举业,然意殊不屑焉”折服。赵韩这句话,似乎同为个人的写照,令其终身绝意仕途,从而效乃师“僊僊绝尘”,使“名利都尽”。这句话也可解释赵韩取法李白与竹林七贤,诗酒一生而好读性命之书,进而以书劝善,揲《榄言》,辑《日乾初揲》。入南雍之前,赵韩已因“过成山先生器重之”而“入北雍,与四方才士交”。所以入南雍之际的赵韩,年应近二十,而乾隆《平湖县志》犹拱之入“国朝”文苑,可见生命不短,至少由万历年间走到了顺治初期,是跨明入清的人物代表。如此漫长的生命滋生的问题是,《榄言》可能揲于明思宗崇祯中、上期,盖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目录载,我们如今可见的《日乾初揲》系明末刻本。李之藻辑《天学初函》,是在1629年,亦即崇祯二年。此函颇见流通,明清士人购罝并不难,当湖隔邑鉴湖祁理孙(1625—1675)的《奕庆藏书楼书目》即明载之,连康熙年间曹雪芹(1724—1763)之祖曹寅(1658—1712)的《楝亭书目》亦曾登录。至于单行本的《七克》、《畸人十篇》与《二十五言》,明载其上的书目总数更达五家以上,书肆多备。《榄言》的辑稿,若从赵韩与董其昌的因缘看来,当在李辑书成前后。
此外,赵韩这“晚年”的问题,同时显示《榄言》刻成最早的时间无过于1631年,因为除非赵韩早就认识闽人颜茂猷,看过《迪吉录》的手稿,否则颜书迄崇祯四年才刻成,赵韩无从揲之为《迪吉拈评》,无从并之入《日乾初揲》,而1631年这一刻,赵韩应已年近花甲,以时人的标准看,堪称“晚年”了。《榄言》所用的《七克》、《畸人十篇》与《二十五言》等书,纵非《天学初函》所收录者,单行本欲得更不难,文前已及,而我可以再加补充的是,函中的《灵言蠡勺》(1624)到了雍正年间,一般书坊犹可访得。至于《七克》,1857年还曾由遣使会士(味增爵会士)迻为官话二卷,题为《七克真训》,使非传播之广,断难出现方言改写本。就人物言,《七克》声名更响:明末徐光启(1562—1633)在《圣教规诫箴赞》中为《克罪七德》写过箴铭;王征(1571—1644)改宗天主教,是因读了《七克》使然;郑璟(生卒年不详)吟诗唱过阅读《七克》的感想;吴历(1632—1718)也曾化约庞迪我,在康熙年间将《七克》诸罪及其克服之道逐一演成一套七首的诗组《七克颂》,而教外中人如方以智,更在入清前就曾寓目《七克》,书为感想了。赵韩的“榄生”之号,若非命于崇祯晚期,就是在入清后不久。
赵韩子赵沺(生卒年待考)有父传,惜乎我仍缘悭一面,否则上述问题当可迎刃而解。《榄言》想来并无单行本,以致历代方志丛书皆称“未刻”。纵然如此,书成之后,而且大有可能还是刻成之后,康熙年间已留有阅读记录。时人杨万基(生卒年不详)著《西亭集》,其中有《读赵退之先生〈榄言集〉》一诗。杨万基出身柘湖,而柘湖乃古地名,明清之际隶属于松江府金山县,多盗匪。柘湖又毗邻平湖,杨万基慕赵韩之名并不奇,所为诗开头故此赞道“退之先生名久扬”,而杨氏是“髫年握发早景慕”。不过杨万基也隐喻赵韩的书不易得,盖“深山大泽藏其珍,出入蛟龙不敢抢”。杨万基终于得而翻阅,谓之“开卷洒洒复洋洋,韩潮苏海谁能仿”。读书的结论中,杨万基从而谓赵韩可称“笔摇五岳鼎足扛,力吞金牛势无两”,而且文走实在,“不夸伪体成独是,即挟齐竿滥缥响”,进而力赞其人为当时文坛的中流砥柱。杨万基显然不通西学,不知《榄言》乃揲自庞迪我与利玛窦的著译而成,因此他才会盛道赵韩,极美《榄言》,而这一切不啻又以诗在称扬《七克》、《畸人十篇》与《二十五言》。在1630年以前,这几本书与收录之的《天学初函》早已超迈中国,东向传入了三韩与扶桑之地,可谓声名远播。
赵韩不像杨万基,他能够清楚辨别“上帝”与“天主”,娴熟西学可称想当然耳。连《天学初函》中的《天主实义》,赵韩应该也读过,因为利玛窦此书曾力辩中国古经中的“上帝”就是天主教的“天主”(李辑,1:415—418)。不过《榄言》成书,最大的意义非唯赵韩杂抄西学,可借以说明《天学初函》——或约之而为《七克》、《畸人十篇》与《二十五言》——在明末盛行的情况,更在《榄言》收于《日乾初揲》之首,而此帙内收的他著如《广爱选言》与《牛戒汇钞》等书,皆可谓儒释道三家的劝善之书,辑录了不少“克己复礼”、“爱众亲仁”与“博爱众生”的嘉言警语,煞似范立本“撮通俗类书、蒙书与善书而成”的《明心宝鉴》。《榄言》确从三教立场收编天学著译,然而从天主教的角度反面观之,可以相捋者也不缺:韩霖稍后的《铎书》(1641)就是佳例,因为只要劝人为善,韩著纵为天主教乡约,也不避三教善书,同样将颜茂犹的《迪吉录》及袁黄(1533—1606)的《了凡四训》等书杂糅入书了(《徐汇楼》,709,820—826),再也不理会其中三教和本教有无干系。《日乾初揲》的“日乾”隐喻修行,就像前举李贽的诗,有其宗教内涵。所以《日乾初揲》一名,想亦效法李之藻的《天学初函》得来。赵韩可能想效李氏辑书,初揲之后还有二揲之集——虽则在历史上,两人都“功败垂成”。
在这种状况下,《榄言》不仅是明末言体著作的新例,深具宗教文学史上的意义,赵韩的揲文,也扩大了中国传统“善书”的范畴,使之连西学都可涵括进去,而这恐怕不是颜茂猷可以想见。崇祯丁丑年(1637)孟冬,颜氏尝应弟子黄贞(生卒年待考)之请于北京为《圣朝破邪集》撰序。他听闻艾儒略抵彰,“入其教者比比皆是”,而且“入欲买地构堂”,时人“目击心怖”,特为黄氏所集撰文,力主“三教并兴”已足,“治世治身治心之事不容减,亦不容增”。他岂知赵韩将《榄言》与《迪吉拈评》或《迪吉录》并列于《日乾初揲》中,轻易就把“三教并兴”暗地偷换,改为“四教共荣”,霍地形成历史反讽!
从天主教的角度再看,《日乾初揲》之集,甚至也削弱了冯应京(1555—1606)在万历甲辰年(1604)刊行《二十五言》,拟辟佛皈主的本意。而凡此之大者,厥为消解了徐光启《正道题纲》借下引之词攻击释道而一心向主的咄咄之力,再开历史新局:
总总魔障,欺世轰轰。立多教而遂各异,信孔孟略知根宗,笑李老烧丹炼汞,叹释迦暮鼓晨钟。说甚么斋僧布施,受福重重!打僧骂道,地狱魔中。事释迦而为僧役,礼十王借道行凶。呜呼惜哉,何不返本追踪?
《榄言》辑入《日乾初揲》中,因此说明了赵韩和谢文洊、魏禧同存宋儒陆象山(1139—1192)的语录: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西学天教倘可如此包装,裹进显然以三教为主的宗教著作中,恐怕仍属中国善书文化史上的第一遭,从而又使“四教合一”,再非“三教一家”了!
《日乾初揲》里,《心律》对其时及后世影响最大,其中的功过格有下面一条,明末耶稣会士读来必然心有戚戚焉,而我们如果睽诸高一志与艾儒略等利玛窦、庞迪我时人的著作,则意义愈显,关系到《榄言》揲编的性质:“造野史、小说、戏文、曲歌者,一事为廿过,因而污蔑贞良,五十过,传播人阴私及闺事者,一事为十过。”(《初揲》,3:20b—21a)如此严苛的他律道德,足以把汤显祖一类曲家之作如《牡丹亭》(1598)等“文艺之学”打入地狱,显示中国明末,民间自有一套不同于官府的宗教性约束基转。功过格或——扩而大之——“善书”的功能,由此可见一般。
话说回来,三教如此,天主教何尝不然?且不谈《铎书》这类乡约拢聚天主教徒伦理的力量,单就高一志某些著作言之,他写或译来,其实也有效法三教“善书”的企图。高氏《民治西学》就像上举《心律》中的功
过格,明文严禁“淫戏”。在《童幼教育》(1631)中,他又痛贬欧洲古来文界之“美文”,并引柏拉图为权威,称之为“邪书”,譬如“毒泉流行,推万民而毙之”。凡是可以砥砺人心之作,尤其是专论天学的书籍,高一志才称之为“正书”,而狭义说来,“正书”多数亦即教外所称之“善书”。赵韩揲《榄言》,其功在道德伦理与处世之道的教导与提升,自然同属高一志所称之“正书”,而凡属“正书”,高氏亦称之为“善书”。论述之际,高一志自然没有料到耶稣会同志的他著,当时的中国人来日或已经“重制”之而为《了凡四训》或《心律》以外的另类中国“善书”了。赵韩的贡献,因此在以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方式,提升了利玛窦与庞迪我等初代耶稣会士的伦理位阶,使《七克》、《畸人十篇》与《二十五言》堂皇现身于天主教外,一概挪为儒门——当然也兼带佛道意味——的著作,既“脱胎”,也“换骨”了。凡此种种,我们再说也奇,因其无不反讽地又以另类形式,体现了晚明上述天主教传教士在文化上拟会通中西,尤其是拟与儒家结合的来华初衷。《榄言》之为德也大矣!
How to Turn Christian Texts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Shanshu?A Critical Look at Zhao Han's Lan Yan and Late-Ming Western Learning
Sher-shiueh Li
Late Ming China saw the appearance of a series of shanshu or morality books,entitled Riqian chushe.Riqian derives from a line in the Book of Change,while chushe means the“first extractions.”The two terms mingle to imply how one should cultivate oneself to meet religious requirements through reading extractions.By“religious requirements,”Riqian chushe refers to tenets of Confucianism,Buddhism,and Taoism. Accordingly,the compiler of the series,Zhao Han,a scholar and poet from Southern China,includes in his series,consisting of five volumes altogether,extractions from morethan 50 texts in Chinese,including such well-known Ming morality books as Diji lu and Xinlü.What is interesting is that Lan Yan,the first book in this series,takes as its sources three books written or translated by Matteo Ricci and Diego de Pantoja:Ten Chapters from a Strange Man,The Seven Conquests,and the Twenty-five Discourses.The first two books are obviously written to demonstrate Christian doctrines,while the last one is a partial translation of the Enchiridion,a collection of proverbial passages by the Roman Stoic philosopher Epictetus.Zhao Han,however,does not clearly indicate his sources in the Lan Yan;through omissions,additions,and logic patchworks of different sources,he re-edits these texts,instead,to become an organic whole,thus“smuggling”Christian messages into Riqian chushe.This paper analyzes how Zhao Han edited the aforesaid Christian texts in his times to create a traditional Chinese shanshu.
Zhao Han,Riqian chushe,Lan Yan,Ten Chapters from a Strange Man,Twenty-five Discourses,Seven Conquests
Author:Sher-shiueh Li,who
his Ph.D.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Academia Sinica,Taiwan.He is also on the facul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Taiwan Normal University,and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Translation,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His recent works focus on the translated literature from Europe and its reception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between the Ming and the Qing.
李奭学,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及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合聘教授,并为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特聘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重点为明清之际欧洲文学的中译与接受史。电子邮箱:shiueh@gate.sinica.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