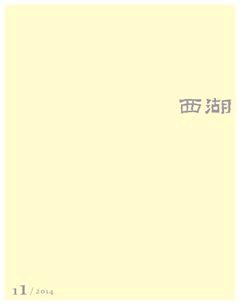“自我”即是“世界”
行超
每个“80后”文艺青年的记忆里都有一个周嘉宁,那个写过《流浪歌手的情人》、《陶城里的武士四四》和《夏天在倒塌》的周嘉宁。周嘉宁的小说有着强烈的个人特色,她作品中阴郁忧伤的氛围,有点残酷又有点伤感的青春经历,给同样时值青春期的“80后”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随着年岁的增长,青春期那种朦胧的忧郁渐渐远去,“80后”渐渐离开了校园生活,告别了成长的伤痛,面对的是沉重而粗粝的现实,于是,周嘉宁的文字便随着懵懂的青春期一起,悄然离开了我们的视野。
事实上,这些年,周嘉宁似乎也在主动地回避众人的目光。再次注意到她是2013年,《外滩画报》发起了一个“‘80后作家群像”的访谈,采访对象包括周嘉宁、张悦然、郭敬明、颜歌等。与其他“80后”作家相比,周嘉宁对自我的反思之深刻,令人诧然。回想自己刚出道时的作品,她甚至说:“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在不该拿出来的时候,被拿出来了。要不是很多媒体的炒作和无良书商的介入,之前很多书都是不应该被出版的。可以写,但那些东西不应该被发表。”2007年底出版长篇小说《天空晴朗晴朗》之后,周嘉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再出版新的作品。除了偶尔在《鲤》等文学杂志上刊出一些短篇作品或散文随笔之外,周嘉宁几乎退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2012年,周嘉宁带着长篇小说《荒芜城》再次出现在读者面前,人们这才想起了这个在写作高产期急流勇退的年轻作家。
当我们回过头来寻找这五年时间中周嘉宁的文学轨迹时,却惊讶地发现,这些年,她竟然先后翻译了珍妮特·温特森的《写在身体上》、《世界和其他地方》(合译)以及米兰达·裘丽的《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可以想象,在这段时间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对于周嘉宁而言,无疑是另一种学习的方式。不论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作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美国艺术家米兰达·裘丽,还是“恰巧喜欢女人”的英国女权主义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她们共同的特点是,于世独立、厌恶庸俗、敢于突破、气场强大。我想,对于特立独行的周嘉宁而言,这应该就是女作家应该有的样子吧。
爱是自我拯救
细细想来,在周嘉宁的众多作品中,几乎没有一部是全心全意致力于探讨爱情的。《往南方岁月去》中,周嘉宁借由“我”和忡忡这对好朋友各自的爱情故事,探讨了成长中的离别之痛与爱的无奈。《天空晴朗晴朗》中,周嘉宁化身许三三,以半自传的形式记述了青春期的成长故事。《女妖的眼睛》通过幻想的方式,开启了一个少女对情欲、死亡和宿命的想象。《陶城里的武士四四》讲述了陶城里的四四、张五、非非、张小西等略带颓废的少年,在冲杀和温柔中缠绵的青春……但是,不容否定的是,爱情(包括同性之间的感情),或者说对于爱情的幻想和想象,却一直是周嘉宁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那么,爱情在周嘉宁的小说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功能?或者说,对于写作者周嘉宁而言,爱情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长篇小说《荒芜城》架构于北京和上海两个空间内。在这两个具有不同气质的城市中,“我”经历了一次次的相聚,也经历了一次次的离别。一如周嘉宁以往所有作品那样,这部小说依旧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所有的笔墨几乎都用来书写同一样东西:人际关系——人与人的、人与世界的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小说着重描写了“我”与阿乔、大齐两人之间的情感。正如小说中的“我”所说,“近距离的相处常常只会带来伤害”。“我”和阿乔彼此相爱,却无时无刻不在嫉妒、猜疑中彼此折磨、相互试探,“我们对外界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没有任何共同的朋友,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俩的事情,因此我们也从不谈论其他人,我们只对彼此感兴趣,只谈论彼此,现在、过去,所有角角落落和细枝末节都不肯放过,一定剥去对方的皮,饮到对方的血,才能觉得放心。”阿乔恨“我”的沉默,而“我”深知,言语只能带来误解,在这样的挣扎中,两人最终“除了嫉妒、恨意、占有欲,几乎什么都没有再剩下,我甚至感觉不到爱。没有爱”。与阿乔的这段感情让“我”对亲密关系感到绝望,也更加确信了自己难以跟他人相处的秉性以及不会爱、不能爱的心理缺陷。
大齐与“我”的交往从一次失败的性爱开始,于“我”而言,大齐是一个在孤独境遇中难以拒绝的伴侣。大齐认为“不用把所有事情都搞得那么明白,两个人之间无非是相处”,于是,在相处中,他渐渐产生了与“我”“水到渠成”、共度余生的想法,这让笃信“近距离的相处只会带来伤害”的“我”感到不安。虽然一次次接受了大齐温柔的关怀和宽慰,“我”却始终无法确认自己对他是否有爱,更令“我”不安的是,“我”其实连什么是爱都不能确定:
“什么是爱呢?”我问她,我竟然对这样的核心问题感到迷惘。
“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始终要解决的问题是填满心中那个巨大的空洞,但是后来发现外部世界的运行准则不是这样的。如果想要感到快乐,就应该抛开这个空洞,再也不去想,而只是对别人不断地付出。”她说。
不管是与阿乔还是与大齐,“我”的两段感情最终都以道别而告终。“我”最终恢复到孑然一身的状态,决心“明天起来我要重新做人,我要成为宇宙的孩子,世纪的孩子。挥霍我自己的青春,然后放弃爱情的王位,去做铁石心肠的船长”。不管是面对深爱的阿乔,还是不知道爱不爱的大齐,“我”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爱情中所遭遇的对手,也不是彼此相爱的程度,而是那个深藏于“我”心中的心魔。在如何面对自我,如何面对自己内心对他人、对未来的恐惧等方面,“我”始终都是一个失败者。因此,感情的失败与其说是“我”与这两人关系的破裂,不如说是因为“我”从来都没能战胜自己的心魔,无法处理好与自我的相处之道。
《荒芜城》是周嘉宁的转型之作,在这部作品中,周嘉宁彻底从早期的青春写作中走出来,勇敢地直面自己的内心。书的封底上有一句话:“我们很多人,内心都是荒芜的,迫切需要一些炙热的东西,哪怕感情,去填满它。”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与生俱来地,内心都会有一团炙热的东西。而现代都市却是坚硬、冰冷的,日复一日的工作、循环往复的生活、道路以目的人际关系,孤独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内心存在着巨大的“空洞”,需要某些东西来填满它。于是,你需要一个伴侣,不一定厮守终身,却可以在寒冷的深夜里贴近彼此荒芜的内心,相互关怀、相互支撑。在今天,爱情对于许多现代都市人来说,已经渐渐从一种双向的心理、生理需要变成了自我拯救、自我安慰的需要,在小说《荒芜城》中,周嘉宁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
短篇小说《寂静岭》(《收获》2011年第6期)颇为暧昧地讲述了“我”、小湘、微微三个女人之间的感情。“我”嫉妒小湘和微微之间那种超越一切的亲密,嫉妒她们两个分享着一个“我所不知道的世界”,甚至嫉妒她们为了一个叫老虎的男人而产生了那么多秘密。这嫉妒的背后是一种无法挑明的同性之爱,这爱无关身体、无关欲望,只在于,微微和小湘,她们的内心走得那样近,比“我”与她们任何一个人都近。“我突然想起那两个我已经不记得名字,也不记得脸的女孩,微微说她曾经跟她们做爱,可是我却一点不嫉妒她们,真的,我觉得她们根本不值一提,肌肤之亲根本不值一提。可是我却嫉妒小湘,毫无道理,我嫉妒小湘留在了那个世界里,与微微站在一起,笑着,最后变得灰扑扑的。”多年后,当小湘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其实早已对她的生活不感兴趣,但是,每一次小湘试图与“我”分享一个秘密,“我”都会条件反射般地问她:“微微知道么?”小说最后,小湘不慎踩破了冰,掉进水里,眼看这一切发生的“我”却“没有朝小湘消失的地方奔过去,只是站在原地,感到精疲力尽”,“我”忘了应该伸手救起小湘,唯一想的是“我必须要回去,回去我的房间里,给微微打一只电话,告诉她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件事上,“我”终于与微微分享了一个小湘不知道的秘密。如果爱是相互体谅、相互关怀,那么,“我”与小湘和微微之间的感情,这份在猜疑、嫉妒和好胜心操控下的感情,它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让“我”享受爱之甜蜜,而是以此证明自己在这世界上是被需要的,在这世界上,有人与“我”分享着秘密,我,不是如此孤身一人。
孤独杀死亲密
必须承认的是,周嘉宁并不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作家。相较于故事,周嘉宁的写作更注重的是营造一种氛围、一种情绪,或是探究在某种特定情境下人的内心。从早期以成长主题和青春叙事为主的小说、散文,到近期探讨日常生活与女性处境的种种作品,周嘉宁始终没有放弃对人内心的探究。她喜欢将人物放置在某种近乎绝望的处境中,周围一片黑压压、湿漉漉、静悄悄——她写的是环境,你却分明感受到,这就是人的内心。
在周嘉宁的小说中,相爱的两个人不能唇齿相依,而是始终处于孤立与对抗的状态中,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嘉宁深刻洞悉了人之孤独。孤独是周嘉宁小说中挥之不去的氛围,也是一以贯之的主题。不过,在早期的青春文学作品中,这种孤独多少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正如在《扶桑岛上的青春札记》(收录于《鲤·孤独》)中,周嘉宁说:“我们阅读太多孤独的文字,却并未真的尝到孤独的滋味。我们未被留在孤独的操场,也未被直接抛进社会的洪流,在短暂的时间里,我们依然留存在青春期的尾巴上,不按时起床,每天什么都不做,糟蹋时光,任性伤感,毫不惋惜。”虽然在生理年龄上,“我们”早已告别了青春期,但在心理年龄上,青春期及其裹挟的难以名状的孤独、伤感,却时时刻刻缠绕着“我们”。更重要的是,在告别青春期而真正进入社会之后,“我们”终于真正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幻觉》(《收获》2010年第6期)中,失恋的“我”只身来到异地,投奔一个此前并不熟悉的异性朋友。在短暂的三天中,“我”借宿“他”家,努力尝试与“他”和所有陌生人拉近距离,寻找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感。然而,尽管“我”和“他”都费尽心力,但这费力营造的亲密不过像是服用安眠药后的幻觉,在某个瞬间就轻易地土崩瓦解了。“可是今天晚上,被他握着手,走在陌生的道路上,我突然受够了自己的幼稚,太疼了,与他们近距离的相处实在太疼了,现在我全都想起来了,那种骨头撞向浴室地板的疼痛。我明明知道周围的世界全是误解,却还要费尽力气去说,去说我原来是这样想的,去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还要去解释爱情。在孤独的绝境里,想要贴近另一颗心灵的举动,本身就是错误的,而我至今还是不得要领,与这个人,或者与那个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当“我”再次意识到自己已陷入“孤独的绝境”时,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这世界,仿佛又只剩下“我”一个人,孤独地面对所有未知的一切。
虚幻的亲密和永恒的孤独不仅存在于爱情中,即使在最为牢固、最坚不可摧的亲情中,周嘉宁小说的主人公依旧是孤独的。在长篇小说《荒芜城》和短篇小说《轻轻喘出一口气》(《上海文学》2013年第3期)中,“我”与母亲永远无法理解彼此,时刻处在误解、争吵中。心中偶尔泛起的愧疚感虽然一次次让我们缄默,却始终无法打通那堵横贯在母女之间的厚墙。在《尽头》(《人民文学》2013年第10期)中,爷爷的葬礼成了疏离已久的父女俩再次建立默契的机缘。两个有着最亲近血缘关系的人,似乎只有在这样残酷的场合中才终于原谅了彼此,重新回到应有的关系之中。然而,小说并没有就此结束,葬礼结束后,当“我”和父亲在停车场开车时,再次被对死亡和未知的恐惧袭击了:
“可是你看看,你开进了死路,你开到了尽头。”他瞪大了眼睛。
“哪儿有什么尽头?”
“这里!这里!”他的双手胡乱指着车里。
“你怎么了,你叫些什么?”我觉得他简直不可思议。
“你看看周围,这儿都是他们的车,这儿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他这么说着,完全是快要窒息而死的模样。我这才注意到车窗外,笔直一排排停靠着的都是殡仪馆的工作车辆。黑色的,四四方方的,车身没有窗户,身后有宽大的空间,足够放下一台棺材。它们默不作声地待在停车场的尽头,是故意要与平常的世界保持距离。而我们是格格不入的闯入者,带着热气腾腾的怒气,哀怨,惊恐和悲伤。
在面对另一个平行世界的恐惧中,最亲密的父女两人依旧无法彼此温暖。“我”与父亲一样,都是独自面对这绝望的境地。甚至,就像小说中这父女两人刚刚告别的爷爷,在面对死亡时,不也是孤身一人吗?在他的生命尽头,自己的儿子忙着与他人打官司打得不可开交,女儿远在异国,甚至不能见他最后一面。面对死亡时的孤独是人生最悲惨的却又是最无奈的,想想确实令人哀伤。
《末日》(《上海文学》2012年第2期)中,遭遇车祸的“我”想要与这世界说说话,以此证明自己还可以坚强地活下去,但是,“我拿出手机想要给那个人打个电话,或许可以讲一讲我搬家了,也可以跟他讲一讲我撞车了,总之这种时候,应该与谁讲讲话,讲讲话,好确认自己其实毫发无损,从此依然要艰难地活下去。电话铃响了很多下,没有人接,世界末日,真的也不过如此,所有的亲密关系都不再,所有的电话都变成空号。”最后,“我”只好拨通了维修电话,在接线员模棱两可的帮助下,“我”小心翼翼地开着事故车辆,拖着这满身伤痕、此刻唯一可以与“我”相伴的车子,孤身一人开往未知。
“自我”的哲学
如果说周嘉宁早期的作品大多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女对未来的想象,那么近年来,周嘉宁的作品便是扎扎实实地回到了现实。在这些作品中,她与读者分享了自己多年独居生活的经验(《一个人住第三年》、《成荫》),她思考女性写作者的困难与可能(《主妇真的能写作吗》),探讨各种文学写作的优长(《如何摆脱滞重》、《琢磨翻译腔》)……这一时期的周嘉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作家的专业和努力,她在生活中思考,在思考中发现人性、发现写作的种种秘密的门。
不过,十年前那个有着强烈个人特色的周嘉宁并没有消失。正如她的导师张新颖所说:“周嘉宁是同代作家中特别富于文学质感的一个”,当同辈作家正在努力向历史与现实等重大问题进发时,周嘉宁依旧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世界中,思考着爱情、人性、亲密关系、身体秘密等——那些在她的小说中永恒讨论却又永无答案的形而上问题。一定有人质疑她的写作主题是不是格局太小,视野不够宏大。在《让我们聊些别的》(《收获》2014年第1期)中,周嘉宁借小说中的“我”之口,道出了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
他真的醉了,开始颠三倒四地说话,“你写的那些故事永远只能打动一小部分的人,那些女人,她们都是与你一样的弱者。你知道那些伟大的作家是怎么样的么?海明威,他能打动所有人,男人,女人,像我这样的人。”
“像你这样的人?你以为这个世界上你这样的人是绝大多数的存在?”
“这不是我该思考的问题,你是作家,可是你对他人漠不关心。”
“你不该说出这样伤人的话。”
“不。是你的世界太小,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悲悯。”
“悲悯?我只是不关心地沟油。”
“那你关心什么?”
“人,人本身的样子,人的心。”
不难看出,周嘉宁对于自己写作所遭遇的质疑有着清醒的认识,她知道这种写作方式很难被大部分读者所接受,只能吸引并打动“一小部分的人”,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像她一样的“女人”。她知道这种写作方式很有可能遭受“对他人漠不关心”、“没有真正的悲悯”之类的责难,但她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她的解释是:关心“人,人本身的样子,人的心”比关心“地沟油”更能体现她作为一个作家的悲悯。
的确,周嘉宁的作品在对“人本身的样子”、“人的心”的开掘方面比大多数“80后”作家走得更远。爱情、孤独、死亡、梦境等,是周嘉宁小说热衷探讨的对象,她喜欢将人置于孤立、绝望、黑暗的境地中,以异乎所有年轻女作家的勇敢,一步步将小说中的人物,也一步步将自己逼入绝境,仿佛每一次书写,都在试图触及内心最底层的深渊,都在向着人类所能承受的底线挑战。由自我的经验出发,周嘉宁对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心魔”和难以填满的“空洞”有着极为深刻的观察,她也由此张开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由此拥有了对于人心与人性的大“悲悯”,这种探索当然是令人敬佩的。
不过,在一步步迈向黑暗的同时,周嘉宁的写作也几乎是陷入了绝地。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从自我出发的——“我”的故事、“我”的讲述、“我”所看到以及所思考的一切。她对“人心”的观察基本上就是对于自我的观察,对于“人”的理解也大多基于自我的经验。她从自我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这个世界,却忘了让小说中的其他人——父母、朋友、情人、陌生人——站出来说说话。因此,在周嘉宁的小说中,所有的叙述语调都好像出于同一个人,而这个人从始至终都是她自己。
当然,从本质上讲,人与人并没有太多差别。就像周嘉宁的小说中时常呈现的,人终究是孤独的,终究是孤军奋战地面对这个世界。但周嘉宁也许忘了,在人性本质上的相似之外,还有一些因素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明显差异,比如,成长的环境、各自的经历等等,而这些,似乎恰恰是她所不愿意关心的“地沟油”一类的问题。远离这些问题,多少让周嘉宁的小说看起来不那么贴近泥土丰沛的生活。
在《如何摆脱滞重》中,周嘉宁颇有见地地讨论了女作家立足于性别写作的局限性,她认为:“说到底,男人才是天生与世界发生连接的性别群体,而女人呢,多少都是通过男人才能和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因此女人总是赋予性和身体太多的东西了,试图用这些玩意儿来解释,来强调,来证明存在的意义。然而,这些和辽阔而有趣的世界相比,真是无聊透顶。”与这种写作的明显缺陷相似,对于自我与内心的过分关注,最终让周嘉宁的世界封闭了起来。我们当然不是因此要求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放弃她所擅长的写作方式,而是希望她能够走出自我的世界,去听听他人的生活,看看他人的内心,真正面对并走进“辽阔而有趣的世界”,由此,所谓“人心”、“人本身的样子”才是完整而丰富的。